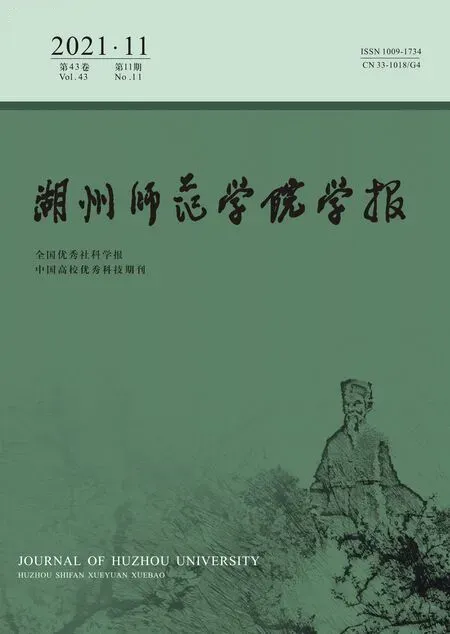13—14世纪域外纪行中的丝绸*
吴莉娜,邱江宁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由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托芬(Ferdinan dyon Richtholfen)提出的。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他通过关注中国的交通路线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商贸道路,同时结合西方关于“丝绸之国”的记载,第一次并且非常谨慎地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比起中国其他商品与世界贸易形成的交通路线,如玉石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等,丝绸之路更加绵长,历史更为悠久,而且丝绸所具有的利润含量、技术成分、文化意味更高,更能刺激中国以及世界的神经。所以斯文·赫定(Sven Hedin)感慨地说:丝绸之路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1]214-215,是传统中国以丝绸为贸易主体,与世界构架的对话之路。
众所周知,在欧亚大陆的两极屹立着中国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而古印度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等均处于丝路的要道上,是媒介文明[2]378。受到利益的驱使,这些丝路要道上的媒介者,尤其是波斯人,为垄断丝绸市场获取高额利润,故意隐瞒丝路真相,从而使得丝绸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因此,这一时期人们对丝绸的载记和表述也充满了想象。
13—14世纪,由于蒙古人的东西征略,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壁垒和道路障碍被大大突破,丝路和丝绸也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士兵、俘虏、商人、传教士以及各种身份使命的人们往来和留驻于丝路沿线,许多固有的知识概念因为交流而发生变化,这在纪行中有所展现。人们对丝绸的表述,从稀罕品、传奇物质到普通平常日用品,从模糊的地理和技术表达到细致、精确记录,域外尤其是西方人对丝绸的认知从神秘、传奇走向真实、平常。
一、13世纪之前域外文本中的丝绸表述

在那次战役之后,有关“赛里斯”的想象在西方话语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多次出现在古罗马诗人的隐喻中。维吉尔(Virgil)在《农事诗》中展示了东方幻境的魅惑:“叫我怎么说呢?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4]2在这里,维吉尔产生了丝绸来源于“羊毛树”的误解,他将“赛里斯”简单地当作一种植物纤维,也就是棉花[5]27-28。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距离的遥远、交通的不便、技术的保密,使东西方对彼此知之甚少。
华美的丝绸撩动人们的神经,“羊毛树”的神话似乎再也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人们对丝绸的生产有了浓厚的兴趣。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也称小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记载了当时人们的看法: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民族是赛里斯人(Seres),他们以取自与其森林的毛织品闻名于世。他们把叶片浸在水中之后,梳洗出白色的东西,此后我们的妇女还有两件工作要干,即纺纤维,再把纤维织在一起。[6]70
普林尼的《自然史》是一部有关公元80年前后罗马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真假混杂,但大致是当时人们所想到和所讲述的事情[5]35。普林尼仍认为丝绸来自“羊毛树”,但对纺织等生产工序有了相对准确的认知。普林尼生活的时代,即汉明帝(刘庄,字子丽,58—75年在位)执政年间,通向西域的陆路交通重新打通,此时,中国丝绸业已诞生千年。丝绸原料是蚕吐出的丝,人们把蚕安置在木格中做茧,在蚕变蛾之前把茧投入滚烫的水中,用树枝轻轻搅动,融掉树胶,蚕丝就会缠绕在树枝上,然后将丝缠绕成盘以备纺织[5]4-14。普林尼说的“纺纤维”可能指将丝缠绕成盘进行纺织的工序,虽然说法不一定准确,但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丝绸的生产不再停留于空白状态,而是有了相对准确的认识。
丝绸的诱惑吸引着大批的贩丝商人,丝路上商旅往来、络绎不绝,出现了“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7]2931的繁荣局面。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而罗马是丝绸的消费地,强大的波斯帝国在中间通过经营转手贸易赚取高额利润。为什么非要经过波斯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科斯马斯(Cosmas)《基督教风土志》的记载:
秦尼扎国向左方偏斜相当严重,所以丝绸商队从陆地上经过各国辗转到达波斯,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而由海路到达波斯,其距离却大得多。……所以,经陆路从秦尼扎到波斯的人就会大大缩短其旅程。这可以解释波斯何以总是积储大量丝绸。[3]183-184
科斯马斯是6世纪的希腊旅行家,其将自己的旅游经历著成《基督教风土志》一书。通过科斯马斯的记载,我们清晰地了解到罗马到中国距离漫长,陆路要比海路近得多且安全得多。波斯帝国占据着欧亚大陆的瓶颈位置,借助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阻断了东西方交流的通道。正是如此,波斯才能囤积大量丝绸,并以中间人的身份向过往商人牟取暴利。
综上所述,13世纪之前的域外文献对丝绸的记载充满了想象,丝绸的名称、来源等都被赋予“他者”的色彩。“实际上,这种人类对‘他者’文化的向往正是对‘缺乏之物’所抱有的渴求与欲望,古罗马作家对东方蚕丝文化的浪漫遐想正是如此。”[8]149-155
二、13—14世纪西方纪行文本中的丝绸
13—14世纪,蒙古人的世界征略打破了欧亚大陆自7世纪以来的隔阂与壁垒,统一完善的驿站系统,又使欧亚大陆的交往畅通无阻。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大增,所谓“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9]385,中国也第一次实现了沙漠与海洋两大出口的全球性开放格局。传教士、商人、旅行家等异质文化圈的人们沿着蒙古大军留下的道路进入中国,“赛里斯”的真实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人的纪行中。
在早期来华的西方人中,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i,又译普兰·迦儿宾、普兰诺·加宾尼、普兰诺·卡尔平尼 )和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又译鲁布鲁克、卢卜鲁克、罗伯鲁)是比较重要的两位。他们都是受教会派遣前往东方的传教士,身兼刺探蒙古军事实力和规劝蒙古皈依基督教的双重使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游记打破了幻想,开启了较为真实的东方形象。柏朗嘉宾在出使中已经注意到 “契丹”这个地方,而鲁不鲁乞则将契丹和古代的“赛里斯国”联系了起来:
其次,是大契丹(Grand Cathay),我相信,那里的居民在古代常被称为塞雷斯人(Seres)。他们那里出产最好的绸料,这种绸料依照这个民族的名称而获得赛里克(Seric),而这个民族是由于他们的一个城市的名称而获得塞雷斯这个名称的。我从可靠方面听到,在那个国家,有一座城市,拥有银的城墙和金的城楼。那个国家有许多省,其中的若干省至今还没有降服蒙古人。在契丹和印度之间,隔着一片海。[10]146
契丹一般指辽朝(907—1125),源出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东胡,曾建立横跨中亚和西亚的大帝国,名震欧洲,被西方史籍称为喀喇契丹(Qara-Khitay,Khitay即Cathay)。1218年契丹宗室于辽亡后所建的西辽被成吉思汗所灭,但契丹一名不胫而走,成为中国的代称[11]44-45。由于当时大部分丝绸都是以出产地的名称命名的,鲁不鲁乞在蒙古当地获悉契丹人生产丝绸,于是鲁不鲁乞准确地将契丹和“赛里斯”联系在一起。鲁不鲁乞的推测在西方文化圈中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他第一个很准确地推测出古代地理学上所称的‘塞里(雷)斯国’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终于从传奇步入现实[12]31。事实上,“他的论断虽然简单,但在西方的中国认知序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把契丹同西方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中国知识联系在了一起,接续了西方人头脑中的中国观念脉络”[13]41。

他们那里有的是丝绸,蚕儿就养在桑树上,无需喂食。因此,养得很好。在中国,丝绸是穷苦人的衣料,如果不是商人们哄抬价格,丝绸本来是不值钱的。他们要用多件丝绸衣服才能换回一件棉布衣衫。[14]540
这段话不仅表明人们对丝绸的名称有了准确的认识,更说明西方人已经打破了“羊毛树”的想象,明确地知道丝绸来源于蚕食桑叶所吐的丝。这也许和公元5世纪蚕种外传,“赛里斯”的真相被逐渐揭开有关。公元420年或440年左右,西域于阗王国与汉族公主联姻,但如果未婚王妃想穿丝绸服装,必须带来制造丝绸的东西。于是,即将和婚的新贵人便将蚕种偷包在纸中,梳在头发里[5]147。从此,精心维护了数世纪之久的蚕桑业的秘密被泄露,养蚕制丝业在中国之外的土地上建立起来。
蒙元帝国疆域空前,并且鼓励各国商人来华经商,这为中外交流、商贸往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又译马哥·孛罗、玛格博罗)在纪行中对丝绸的名称、产地、交易等有详细记载:
产丝多,以织数种金锦丝绢,所以见有富商大贾。[15]347
居人面白形美,男妇皆然,多衣丝绸,盖行在全境产丝甚饶,而商贾由他州输入之数尤难胜计。……此种商店富裕而重要之店主,皆不亲手操作,反貌若庄严,敦好礼仪,其妇女妻室亦然。妇女皆丽,育于婉娩柔顺之中,衣丝绸而带珠宝,其价未能估计。[15]360
马可·波罗不仅对不同品质丝绸的名称进行了准确无误的记载:丝、金锦、绸绢、丝绢等,他还指出了当时的产丝重地:宝应、高邮、汴梁、襄阳、镇江、常州、苏州、扬州、嘉兴等。马可·波罗在记述杭州丝绸交易繁盛时,使用的“尤难胜计”“其价未能估计”等都表现出市场的繁荣令人震惊,这是因为在13—14世纪的欧洲,尚处于黑暗的中世纪,饥荒、瘟疫和战争无处不在,与杭州城的繁华、遍地昂贵丝绸、商贸往来频繁形成鲜明对比。得益于13—14世纪蒙古帝国丝路的拓通、贸易的保护,马可·波罗将两条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一一走过,这也是马可·波罗获得真实认知的重要原因。
除了对丝绸的记载,马可·波罗还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纸币制造艺术,这种技艺和丝绸的生产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此汗八里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术点金,缘起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旋以此薄如纸之皮制成黑色,纸既造成,裁为下式。[15]239
751年,唐与阿拉伯在怛罗斯城(今吉尔吉斯)开战,大败。俘虏中有大批造纸工匠,中国的造纸术先传到巴格达,继而传到欧洲。马可·波罗于1275年左右到达元朝首都,这时欧洲虽有造纸术,但纸币直到16、17世纪才开始使用。马可·波罗用了一章来描写纸币制造,详细介绍了纸币的材料、制造工艺、形制等,记载之细较中文文献更甚,足见纸币所带来的刺激。马可·波罗之所以注意到纸币的制造,一方面与其作为商人身份有关,另一方面,纸币的原材料是桑树皮,风靡欧洲的丝绸也来源于蚕食桑叶吐出的丝。同时,马可·波罗赞扬纸币是“方士之术点金”,即在用桑树皮制成的纸页上加盖大汗的印玺,这纸页就具有了金子或银子的价值,这对于当时以聚金积银为富的普遍观念来说,十分不可思议。
文学家元好问在《论诗》中说道:“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16]205丝绸技术越保密,丝绸价格越高,丝绸税收也成为中国官府一大稳定的赋税来源,这也是“玉石之路”变成“丝绸之路”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罗马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和主要消费地,也是推动中国丝绸走向西方的源泉。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曾经对丝绸最渴望的罗马人身上,经过几个世纪,罗马人鄂多立克(Friar Odoric)如何描述东方的丝绸的:
人们从他们的君王那里得到诏旨称:每火要每年向大汗交纳一巴里失(balis),即五张像丝绸一样的纸币的赋税,款项相当于一个半佛洛林(florin)。他们的管理方式如下:十家或十二家组成一火,以此仅交一火的税。[17]66
八天后我抵达一座叫作临清(LENZIN)的城市,它在叫作哈剌沐涟(CARAMORAN)的河上。…… 我沿该河向东旅行,又经过若干城镇,这时我来到一个叫作索家马头(SUNZUMATU)的城市,它也许比世上任何其他地方都生产更多的丝,因为那里的丝在最贵时,你仍花不了八银币就买到四十磅。[17]69
第一段话是鄂多立克在杭州时所见到的情境,他注意到纸币的使用,并从外形的相似上,将两者联系起来。同时,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的税收政策。巴里失是蒙元时期的货币单位,佛洛林则是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流通的货币单位。“元朝平定江南后,将江南的部分人户分封给宗室,总数达八十万户左右。对于江南的投下封户,元朝政府没有征收丝料,而是征收户钞。”[18]403鄂多立克在这里所描写的赋税应该是户钞,总起来说,户钞是在江南临时代替五户丝而采取的一项措施。索家马头即沧州,物以稀为贵,鄂多立克正是由于当地丝绸价格低廉而猜测为世界产丝之最。
综上所述,13—14世纪,由于蒙古帝国的庇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传教士、商人等从西方历经艰辛到达传说中的“赛里斯国”,他们对丝绸的表述,经历了从稀罕品、传奇物到普通平常日用品,从模糊的地理和技术表达到细致、精确记录的过程。
三、13—14世纪东亚文本中的丝绸
无论是鲁不鲁乞、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还是鄂多立克,他们都属于异质文化圈,他们带着对“赛里斯”的想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了解它真正的名字、产地、交易等,并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来传播给西方,打破了西方人传统的认知。然而,“在13—14世纪,东亚文化圈中对元朝认同程度最高的是高丽,这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表述如同国人”[19]200-212。除了东北地区的高丽,西南地区的安南同样与蒙元王朝来往密切,他们对丝绸的表述各具特色。
14 世纪中叶,流行于高丽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尤其值得注意,“乞大”就是“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也有“中国通”之意。《老乞大》全书采用对话的形式,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展现了元末明初的中国社会,兼有旅行指南、经商指南的双重作用。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老乞大》中记载的元、高丽丝绸交易地区:
俺直往南济宁府东昌、高唐,收买些绢子、绫子、绵子回还王京卖去。[20]10
济宁府东昌(今山东省济宁市、聊城市)、高唐(今山东省高唐县)是当时北方重要的产丝胜地。这说明高丽商人对丝织产地十分熟悉,他们“不仅在商品聚集地如大都等商业城市购销商品,有时还到货物原产地购买,以期获得价廉物美的商品”[21]63-70,同时反映出元、高丽贸易往来之频繁。“绢子、绫子、绵子”等极富口语化色彩,表现出中国丝织品种类繁多,纺织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王京是李氏朝鲜首都,当时高丽已处于灭亡前夕,社会奢靡成风,丝绸是当时人们竞相追逐的奢侈品。这些丝绸部分来自官方赠予,更多地依靠商人贩运。因此,对话中高丽商人购买丝绸在王京倒卖,正是实际情况的反映。
除了对丝绸交易有所描述外,《老乞大》对丝绸的价格、品质、花色都有详细记载:
恁那绫、绢、绵子,就地头多少价钱买来,到王京多少价钱卖?
俺买的价钱,薄绢一匹十七两钱,打染做小红里绢。绫子每匹十五两,染做鸦青和小红。绢子每匹染钱三两,绫子每疋染钱,鸦青的五两,小红的三两。更绵子每两价钱一两二钱半。到王京,绢子一匹卖五综麻布三匹,折钞三十两。绫子一匹,鸦青的卖布六匹,折钞六十两,小红的卖布五匹,折钞五十两。绵子每四两卖布一匹,折钞十两。[20]10
这短短的一段话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清晰地表明了元代丝绸的质量,也反映出高丽商人的熟练。对话中高丽商人如数家珍般说起了丝织品在济宁府东昌、高唐、王京的不同价格,说明其与元商打交道经验丰富。出于利益的追逐,高丽商人把中国丝绸染色加工,分别染成小红里绢、鸦青,这也说明当时丝绸的产量和花色品种增加,质量大有提高,纺织、染色加工等生产技术十分成熟。通过计算,对丝织品进行染色加工并倒卖后,小红里绢和鸦青分别可以多卖三十两和二十二两,可谓是高额利润。当时,“棉花的普遍种植和棉织业在元代兴起,元朝灭亡后才传入高丽并发展起来。可以说,有元一代,高丽还不能生产棉布。因而,商人将中国上等的纺织品贩运到高丽,必然是供不应求且有利可图的”[22]45-60。总之,这段话不仅形象地说明了丝绸的价格、品质、花色,也生动地反映了元朝与高丽的贸易往来频繁。
元朝和高丽不仅可以通过陆路互市,海路也是重要的贸易通道。下面这段对话对高丽商人所经路线、所用时间、买卖货物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你自来到京里卖了货物,却买绵绢,到王京卖了,前后住了多少时?
我从年时正月里,将马和布子到京都卖了,五月里到高唐,收起绵绢,到直沽上船过海,十月里到王京。投到年终,货物都卖了,又买了这些马并毛施布(按:苎麻布。又称木丝布、没丝布,讹而为毛施布)来了。[20]10
由于元代广阔的疆土、完善的驿站制度,陆路、海路等交通事业空前发达。直沽是北方的海运港口,既是元代南北粮食运送到大都的港口,又是元、高丽往来经贸最便捷的港口。从上面可知,高丽商人正月从家乡王京携带马匹、毛施布等货物来中国,走的是旱路,然后把马匹、毛施布等货物卖出,到中国北方丝织原产地采购丝绸返回高丽,走的是海路,往返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些高丽商人赶马前来,带着毛施布,然后到京都卖掉,购买当地的丝织品再返回王京倒卖。可以说,马、毛施布、丝织品是元与高丽商贸往中十分重要的货物。马匹在元明两代与高丽的陆路贸易中承担着交通工具的重要作用,而更重要的是,高丽马在历史上十分出名,明太祖朱元璋就说过高丽自古出名马,所以马在元明两代的贸易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毛施布(音译,亦称木丝、没丝、耄丝布、苎麻布等),用白色苎麻织成。“高丽所产毛施布品质优良、经久耐用,深受中国市场的欢迎,所以高丽商人带往中国的商品或者高丽士人赠送中国人的特产往往有小毛施。”[19]200-212通过上面的对话,高丽商人在中国市场交易的情境跃然纸上,不仅可以感受到元与高丽的商贸往来的频繁,而且其口语化的叙述更是有别于异质文化圈的鲁不鲁乞、马可·波罗等人。
安南,今越南古称,得名于唐朝所设的安南都护府,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而存在。13—14世纪,安南与蒙元的交流臻至繁兴,使介往来频繁,纪行作品异彩纷呈。寓居中夏的安南文人黎崱亲撰的《安南志略》聚焦于安南的地理、风俗、物产、文化等内容,是西南纪行作品的重要代表。其在介绍安南的风俗时,对当地丝绸的用途有所记载:
三日,王坐大兴阁上,看宗子内侍官抛接绣团毬,接而不落者为胜。团毬以锦制之,如小儿拳,缀采帛带二十条。[23]41
这句话是在介绍安南的迎新风俗,宗子臣僚分班拜贺、各行家礼之后,于第三日,宗子内侍官抛接绣团毬为乐。由介绍可知,团毬的原材料、大小和外观都类似于中国本土的绣球。团毬作为王公贵族的游戏工具,由锦制成,可见以锦为代表的丝绸之高贵。与此同时,锦能用来制作绣球,也说明丝绸虽然高贵,但在当地并不缺乏。同时还说明,在当时的安南,丝绸不再罕见,已经成为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安南志略》除了介绍丝绸的用途之外,对当时中国与安南往来朝贡的现象也有简单记载:
今赐卿银五百两、细(色)绢帛一百匹。至可领也。[23]65
这句话出自度宗(赵禥,字长源,1264—1274年在位)赐安南陈光昺的诏书。陈光昺是越南陈朝第一任皇帝,1225—1258年在位,曾成功抵御蒙古帝国入侵。“基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中外关系体系——朝贡制度。”[24]76引文这句话即表明安南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往来朝贡赏赐,其中不乏丝绸。历史上,高丽和安南是东亚地区典型的朝贡国,他们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以此为标准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思想文化基础,并向中国称臣,定期遣使朝贡,中国则对其进行册封、赏赐等。因此,安南上等的丝绸来源和高丽一样,部分来自官方赐予,部分来自民间交易。
如前所述,13世纪之前,域外文献中的丝绸表述充满了离奇的想象。13—14世纪,随着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互联互通体系的建立,异质文化圈的人们进入中国,并在其纪行中采用纪实的手法,以积极融入的参与者视角来描述丝绸,“赛里斯”的幻想从神坛跌落,走进现实。同一时期,同质文化圈的高丽、安南对丝绸的表述如同当地人一样平常、熟悉。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接近,域外纪行中的丝绸形象逐渐由外在走向深入,由传奇走向客观,丝绸也远超出其物质层面的媒介意义,对文学、文化、经济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