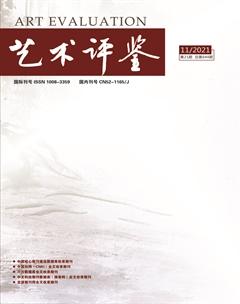文学黔军:贵州新文学的再出发
摘要:贵州新文学成为中国文坛的生力军,既要清理与总结20世纪以来贵州四代作家的地方文脉及其传统,也要面对新的时代所激发的历史使命与重大责任。贵州作家在代际传承中,本土题材是他们立足贵州走向全国的起点与方式,贵州作家写贵州值得大力肯定和充分开掘。积累不足、传承不够虽然与特定地域有关联,但也处在求新求变的同一起点上。文学黔军与黔派批评概念的提出,既需要命名与阐释,也需要清理呵护与推波助澜,同时期待走出一条贵州文学不断发展壮大的新路。
关键词:文学黔军 代际作家 黔派批评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21-0164-04
贵州新文学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学形态最先进入视野,然后才是以全国性文学板块方式彰显于世。贵州新文学在整个中国新文学格局中是一个地域性的存在,而且这个地域的存在并不是特别的强势、发达,让外界所羡慕。上海、北京等地的新文学往往站在全国的高度,具有全国性、中心性的特点。文学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中心和边缘是相对的,尽管我们自己也可以作为一个中心,但是放在全国格局中来看,贵州新文学是一个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学,虽然也有地域文学的优势,但在很多方面,往往以一种局限、不足的姿态出现。
如果大家对贵州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对贵州新文学研究界的现状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即被低看或被低估的现象。《20世纪贵州小说史》①和《贵州读本》②之类的书籍,对贵州文学的判断中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贵州文学是被低估、低看乃至忽略的文学。贵州新文学没能得到一个应有的、公正的、客观的评价,这一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我们本身的文学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显赫;第二方面,贵州文学往往是零散、各自为政、不团结的,贵州的文学界、评论界没能拧成一股绳,缺乏一个整体的力量。基于此,笔者尝试提炼出几个很重要的概念:一是文学黔军,或者文艺黔军的命名;二是黔派批评的命名。这两个概念没有正式提出来,也很少被各方面关注到。比如,贵州的文学批评,其实和文学创作是不相称、不对等的,也容易被人忽视。站在黔派批评的高度,贵州文学创作与批评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学、对自己的队伍、对自己的存在往往是以一种自卑的方式来看待。提到文学黔军,甚至会有人怀疑能构成黔军吗?黔军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的形象、地位、作用是否让人觉得可期待?或者是否让人觉得可以赞美?总之,怀疑论居多,这一切和贵州这个地域的精神文化积淀有密切的联系。
一
下面从三个重要方面依次展开:一是从贵州军阀(黔军)说到文学黔军;二是文学黔军的地方文脉及其传统,主要是通过20世纪以来的贵州四代作家来展现;三是再出发的议题,论述文学黔军新的的使命与责任。
首先是文学黔军的来历、命名。说到文学黔军得从军阀说起,贵州简称黔,贵州军阀简称黔军,发源于清朝灭亡以后兴起的地方军事势力。像北洋军阀一样,各个军阀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粉墨登场。贵州军阀的演变更替有三大特点:一是更替速度快;二是在更替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譬如借助滇军、川军、桂军的力量,甚至有些军阀通过借助外界力量崛起后把本省自己的利益又输送给了省外的军阀。三是不团结,贵州军阀不团结,内部争斗、刀锋相见的情形较为普遍,甚至同一个派系、有血缘关系的军阀之间也经常自相残杀。1928年至1935年左右这个阶段,贵州军阀演变之剧烈,频率之快,非常具有地域性和典型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曾经辗转来到贵州,改变了原来的前进路线,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贵州的黔军力量很单薄,不堪一击,留下了生存的空间。
接下来的是第二个内容,“文学黔军:地方文脉及其传统”,主要从代际作家与贵州新文学历史来展开,讲述四代作家的构成、流变,最后再涉及主要作家之外的群体。贵州四代作家的代表是指蹇先艾、石果、何士光再到欧阳黔森。首先是第一代作家,第一代作家的创作主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发力,直至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第二代作家主要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有影响力,即傳统意义上在“十七年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作家们,他们的出生时间在1920年-1930年之间居多。第三代作家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开始冲入中国文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出生时间多半在1940-1950年这十年之间。第四代作家大概在新世纪以来的近20年内取得突破性成绩,以60后、70后作家为主。第五代作家则是贵州文坛上的80后、90后作家。现在恰好是第四代作家、第五代作家交叉的时间,文坛主体是第四代作家,第五代中某些作家开始崭露头角,例如曹永、李晁等等。以上只是我的视野中一个宏观的整理,大概一代人间隔20-30年之间,当然每一个作家的情况不完全吻合,但大体差不多。
整体而言,宏观梳理贵州代际作家,第二代第三代作家已经沉寂,第四代作家现在正是写作的黄金时期,正在风头上,第五代作家开始兴起。除了以上所述的代表性作家,其它群体也十分重要。第一代作家包含寿生、谢六逸等;第二代作家包括廖公弦、张克、伍略等;第三代作家包括叶辛、李宽定、李发模、王鸿儒、唐亚平等;第四代作家包括冉正万、王华、戴冰、谢挺、唐玉林、赵朝龙、龙潜、肖江虹、肖勤等。在此列举的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比较丰硕、风格也比较独特、在整个贵州新文学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这些作家的研究还处于比较零散的情况,没有系统地去整理去挖掘。至于第五代作家,也就是80后90后作家,陆陆续续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个别作家创作量还比较丰富,但是整体而言还是属于一种生长的状态,也不好过早地做出客观而全面的判断,不过,我们应对他们寄予厚望。同时希望以后贵州文学的发展既有个体的创新性发展,也能抱团以集体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文学黔军的指向便在这里,这样避免单打独斗、孤身奋战,以文学黔军的新面目成为全国文坛的重要风景。
二
接下来,我们面对黔地四代作家的经验与传承,这是地方文脉的流动与运转。贵州四代作家在代际流变过程中,已积累了较好的历史经验,也有一些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作为地域作家的优势与局限。贵州地处山区的现实情况,既是局限,也是优势。贵州题材是贵州几代作家立足贵州走向全国的起点与方式,贵州作家写贵州是因为贵州这片土地值得大写特写。贵州虽地处山区,比较贫瘠,但却具有作为山区的独特之处,值得去大力挖掘。第二,贵州文学要努力走出去,这是黔籍作家走向全国文坛的进军之路。贵州文学目前出现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就是看重全国的高端平台,只要在上面发表了作品便得到奖励和鼓舞。比如有的作家在《当代》《人民文学》《作家》《中国作家》《收获》等平台上发表过作品,有的作家在省外发表作品并获奖,再返回到贵州本土,这样就有一个较好的轨迹。在某种意义上,贵州的作家还是需要这样去冲刺。笔者一直想研究一个题目——《贵州作家与<人民文学>》,贵州作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是从第二代作家石果开始的,后来的何士光、欧阳黔森、肖江虹等一批作家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较多作品。又如《收获》杂志,如果哪位貴州作家能在这个刊物发表一、二部长篇小说,那将是一、二部很重要的作品。第三,黔地作家中的黑马现象。贵州文坛常会出现文学界的黑马,比如80后作家曹永。曹永出生于毕节威宁,中学毕业便在当地干过各种营生,可以说是从底层走过来的。也许是这样的缘故,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比较卑微、平凡,或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年轻人,或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普通民众。他的作品往往以野马冲、迎春社为背景,作品的小人物,哪怕是乡间的组长、村主任的一句话也让他们感到害怕,其作品中展现的乡村伦理与1980年代路遥的《人生》所表现出的内容有些许相似,即年轻人无法去争取改变人生、改变命运的权利,只能听从父母的劝告,或是乡间的陋习,选择容忍、认命。曹永通过写作,赢得自己命运的改变,到目前为止,他创作出版了三四本小说集子。90后中脱颖而出的作家有蒋在、夏立楠等,他们已经开始集中发表作品,整个创作状态也很不错,年轻人的优势慢慢凸现出来了。现在80后、90后作家,正处在20岁到40岁这个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们能否把握住这个时期,以及相关部门能否采取一些手段和策略将他们推向全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积累不足、传承不够可能与地域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即长期以来我们处于一个封闭的、偏远的、欠发达的大西南区域。今天,贵州交通得到了改善,高铁、航空、高速路等四通八达,贵州与外界的交流与对话在大大加强,各种条件也大为改善。贵州文学在各个方面也将变得更强,在发展上慢慢开出加速度。贵州整个文艺界如果不发生大的质变,出人才、出作品的速度就会跟不上这个时代,就会仍然处于被外界轻视、低看或忽视的境地。这不仅仅是贵州作家的问题,也是贵州社会有识之士应该思考的问题。贵州作家的消隐与长期远离中心,与外界的交流不够、信息不畅通息息相关。譬如,我省的出版系统,我们的出版社可以给外省作家大量出书,却很少顾得上为本省作家这样做。笔者曾经有几个设想,第一是给贵州第二、三代作家出一套代际作家丛书,把队伍找回来,形成规模;第二是给数位贵州标志性的作家出几套全集。可是,这一现象至今也未出现。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贵州新文学整个历史的发展和趋势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不足和缺陷。贵州新文学积累不足的现象有各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作家自身的问题,比如我们很少有专门的签约作家、职业作家;比如有些作家稍微有些创作上的成绩,便担任了一些行政的职务,后来基本没有太大的出息;又比如,目前贵州作家能获茅盾文学奖的希望还很小,因为现在茅盾文学奖的评价标准之一就是看作家有没有长期的创作经历和积累,而不单纯是一部长篇作品的问题。就长篇小说而言,贵州作家中间能够写长篇小说的并不太多,拥有多部长篇小说的作家屈指可数,像冉正万、王华还能写出质量稍高的长篇小说。贵州作家中大多数都是擅长写短篇、中篇,写长篇就显得格局不足,有待突破。
三
贵州新文学的再出发,这是文学黔军新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文学黔军”在这个语境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对贵州新文学一百年来的回顾;第二层含义是站在当下,希望建立黔军的规模,打出文学的新口号,走出一条贵州文学不断发展壮大的新路。如今,贵州与全国一样经过脱贫攻坚之后摆脱了绝对贫困,真正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贵州的整个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贵州新文学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在贵州文坛,以60后、70后为代表的第四代作家,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第五代作家就是新时代贵州文坛的中坚力量,历史的重任自然就落在这两代作家身上。这也是贵州作家今后20年的希望之所在,若以后贵州能出大家也是在这两代作家之中。在此我以当下青年作家肖江虹和曹永为例略作展开:肖江虹,1976年生于修文,代表作有《百鸟朝凤》《傩面》等,他的小说主要以民俗为抓手,描写普通民间艺人、乡民村妇,书写贵州乡村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衰败、困顿,记录乡村世界中人心的崩溃、溃散。他的作品借民俗的外衣,书写今天乡村的现状,字里行间透出悲剧的历史意蕴。肖江虹的小说有思想,在时代主题上是逆向的生长。曹永出生于1984年生,由于他出生于社会底层,最初在学校接受教育时间不长,文化水平较低,所以基础并不太理想。但是,他在社会这所大学接受了教育,在社会底层磨炼出来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其大多数作品写出了乡间的冷酷、贫穷和愚昧。曹永能否成为贵州第五代作家之中的标志性作家,还需等待和观察,当然我对他也寄予了希望。
最后论述一下黔派批评,这个概念之前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是我首次正式提出来。我以后也会更多地扛起这个旗帜,也希望有更多的本土文艺评论工作者做出更为扎实的研究工作。众所周知,第一代作家、第二代作家、第三代作家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相匹配的有份量的批评家,直到第四代作家登上历史舞台,才开始有所好转。贵州文艺批评的实力整体上较为薄弱,没有人提及黔派批评也是实际使然。近十多年来,贵州文艺评论的总体形势有所好转,如何发挥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的积极性,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队伍的作用则十分关键。贵州的老一代评论家有何光渝、苑坪玉、杜国景、谢廷秋等多位,何光渝写过《20世纪贵州小说史》,杜国景写过《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等书,在创作界和评论界影响都很大,是黔派批评中的代表性著作。这一批标志性的评论家,有的至今仍活跃在评论的第一线。比他们年轻的新生代评论家,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较多,在全国不同高校受过硕士、博士等阶段的良好训练,队伍也较可观,大概有二十位左右是相对出色的。他们能否在黔派批评上有所作为,能否在当代贵州作家创作和当代作家评论两方良好互动,做出更为优秀的成绩,这是我们必须集中关注的,这也是文学黔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环节。关系到文学黔军的今后走向、成就,也关系到贵州文学的发展、繁荣。
文学黔军,既需要命名与阐释,也需要清理呵护与推波助澜。黔籍数代作家的轨迹与沉浮,关联着地方文学创作的方向、圈子、路径。因为中心与地方的空间异同与话语权重,文学黔军发展壮大显得较为艰难,这需要黔籍作家们埋头耕耘,也需要外力加以辅助。文学创作与评论不可或缺,加强黔派批评尤其显得迫切。一个省级区域内作家的轨迹与浮沉,与外界客观因素有关联,与各自的追求与努力有关联,也与偶然因素的潜在制约有关联。在贵州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二十世纪以来几代作家的更替与出现,启发我们进一步去审察、去倾听、去欣赏。文学黔军一路走来,在时代沧桑巨变中走来,在一边耕耘一边收获中走来,可谓一路皆成地方的风景。
作者简介:颜同林(1975—),男,湖南涟源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核心专家,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贵州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颜同林教授主持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贵州当代小说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GZZD24。
①何光渝:《20世纪贵州小说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
②钱理群等主编:《贵州读本》,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