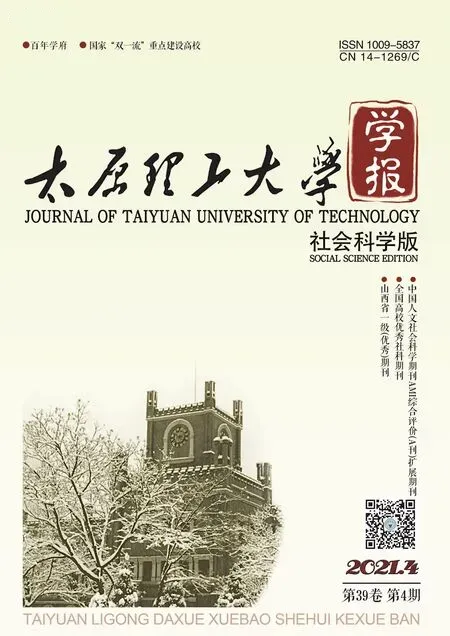秩序、迷信与民生:民国时期庙会形象建构的三重变奏(1912—1937)
黄 昆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庙会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为久远的公共活动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宗庙社郊制度[1]。“庙会”最初是指众人在宗庙聚集,共同祭祀,《后汉书·张纯传》记载:“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禘祭”[2],表达的就是此种含义。庙会一开始是与贵族宗法制相配套的祭祀活动,仅在上层社会中盛行;下层社会也流行公共祭祀,但不能称之为庙会。随着社会等级关系的逐渐松弛,尤其是佛教的民间化和道教的通俗化,“庙”的等级色彩日趋淡化,里面供奉的神灵也日趋多元[3]。学界对“庙会”的阐释是基于唐宋以降世俗空间的形成来界定的(1)《辞海》将“庙会”与“庙市”的含义等同,认为“庙会一般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是市集形式之一”。《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149.高占祥认为“庙会文化就是以寺庙为最初依托,以宗教活动为最初动因,以集市活动为表现形式,融艺术、游乐、经贸等活动为一体的社会文化现象”。高占祥.论庙会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1.小田认为,庙会应该具备三个征象:空间的结节性、主体的广泛性和内容的复合性。小田.“庙会”界说[J].史学月刊,2000(3):103-109.。如果将空间的概念引入庙会,唐代以前人们主要为便于公共祭祀而举办庙会,活动范围限于庙内。该空间称为宗教空间。此时宗教空间与庙会空间完全重合。唐宋以降,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庙会的功能日趋多元,成为人们从事经济和娱乐活动的重要载体。此时庙会空间也得以向庙外拓展,由庙内的宗教空间和庙外的世俗空间共同组成。庙会空间以外的范围称之为日常空间。
学界目前的成果多见于对明清庙会的研究,问题意识常聚焦于对庙会的地理空间、社会功能、区域比较、社会互动和历史变迁等方面的考察[4-8]。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剧变期,也是庙会研究的薄弱时段。以往成果多沿袭以上研究路径,或将其置于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宏大叙事中稍作提及,尤其对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庙会形象未能做出明显区分,因而遮蔽了庙会形象的多重面相。庙会是一个持续变迁的社会活动,要把握庙会发展的历史性特征,应当对其进行综合性的动态考察。本文以1912—1937年的庙会形象为考察对象,以庙会存废为研究视角,运用空间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庙会空间迭变的聚焦,透视这一时期政府、精英和民众的话语竞合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传统与现代:庙会神俗空间的时代性嬗变
唐代以前,庙会只有宗教空间,世俗空间尚未完全形成。唐宋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庙会的空间范围得以拓展,在宗教空间的外围地区出现了商品交易和文娱活动,世俗空间由此形成。唐宋以降,由于国家权力对民间信仰的控制和规训,宗教空间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意涵,在庙会空间中居于主要位置。唐宋时期,上层统治者通过赐额、封号等形式对地方神灵进行招安,试图将民间的祀神行为纳入国家礼治体系之中[9]。明清时期,为宣扬王朝教化,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神灵祭祀标准,将“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10]。以城隍神为例,由于被纳入国家正祀,每逢城隍庙会,地方官都亲临致祭,“凡天下属祭,必以城隍主之,由是天下郡县,莫不皆有城隍祠也”[11]。在权力的规训作用下,城隍神成为“保障一方”[12]和“鉴察善恶”[13]的象征,格外彰显了城隍庙会宗教空间的神圣性,从而确保了对世俗空间的牵引。
民国时期,由于国家权力退出民间的祀神仪式,清朝祀典亦遭废弃,“昔之载在祀典之城隍、土地、昭忠祠及诸佛偶像等,亦多受时代之淘汰矣”[14],褪去了官方色彩的宗教空间,在庙会空间中渐居从属地位[15]。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除偶像、破迷信,庙产充公,改设学校,信奉者少”[16],神灵信仰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遭到精英阶层的强烈质疑与批判。陈独秀认为,“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17],都应该予以破坏。陈的观点虽较为激进,但却道破了神灵崇拜的荒诞性,一旦信仰诉求在现实中屡遭挫折,人们对其精神的寄托也随之动摇。从这两个维度来看,民国时期的宗教空间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去神圣化的过程,宗教空间对世俗空间的牵引明显弱化。1933年江苏省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的调查报告显示:交易型庙会占一半以上,其次是香火型庙会,最后是娱乐型庙会。民众参与庙会“不过是借着求神拜佛的幌子,而做他们的交易买卖及游艺娱乐的勾当罢了”[18]。在洛阳农村地区,由于人们“对宗教信仰不如往昔之尊重,故庙会活动之性质亦渐渐已由宗教活动转变为经济活动,更进而成为乡民同乐大会”[19]。
民国时期,宗教空间与世俗空间的地位发生置换,这与世俗空间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民国以前,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在一些经济发达、交通便捷地区,兴起了大批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镇。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由于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品交换市场,庙市成为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每逢庙会期间,人流熙攘,组织者以酬神为名,安排唱戏、演剧和歌舞等文娱活动。从历史上看,经济活动和文娱活动分别是华北和江南地区世俗空间内的主要内容[4]。虽然两地差异显著,但从二者的关系来看,世俗空间均以宗教空间的存在为前提。民国时期,世俗空间内的经济活动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从商品种类来看,由于外国商品的输入和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庙会上的商品种类更为丰富,与传统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乡人农圃之用具,婚嫁之妆奁,以及居家日用所需,率皆取于庙会”[20]。从参与主体来看,因为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业群体和行业组织,而身份和职业的平等为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奠定了基础,“不但农人需要立可解决,即商业金融亦借此活动补助社会”[21]。从庙会的空间分布来看,由于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庙会的空间范围不断向外延伸,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商品交易区,呈现出与传统时代完全不同的商业景观[22]。随着庙会交易的异常活跃与逛庙人群的广泛聚集,世俗空间内的文娱活动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既有戏剧、游艺、杂耍等传统节目,也有骑术表演、电影放映、自行车比赛等新式娱乐活动,传统与现代娱乐方式交相辉映[23]。此外,国家权力的直接退出和参会主体的身份平等,使世俗空间的公共性和参与性得以凸显,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和社会思潮的新旧交替,促使其逐渐成为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启迪的重要公共舞台[24]。
庙会神俗空间的嬗变还体现在庙会空间与日常空间形成了新的空间演变关系。民国以前,庙会空间向日常空间连续拓展,这源于世俗空间的边界在不断向外移动,总趋势是庙会空间持续扩大,日常空间持续缩小。民国时期,因世俗空间的不断扩张,日常空间的边界实际仍在收缩,但这种空间演变关系是非常态的。在传统社会,因为国家权力的直接参与,载于王朝祀典的神灵,其庙会举办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宗教空间与世俗空间之间联系紧密。民国时期,由于国家权力的直接离场,使得取缔庙会的风潮此起彼伏。在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北洋政府时期的庙会空间间歇性地被日常空间填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因“反迷信”运动的推行,宗教空间与世俗空间呈现一定的分离趋势,庙会空间一度完全转变为日常空间,直到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渐趋稳固后,政策才有所松动,庙会空间因此得以恢复。
二、秩序与民生:北洋政府时期世俗空间的内在紧张感
民国时期,由于宗教空间的时代性嬗变,世俗空间在庙会空间中渐居主要位置。虽然世俗空间与宗教空间渐呈分离趋势,但二者相互依存,互以彼此为存在的基础。庙会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和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是多重历史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庙会是否仍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成为地方当局和民间社会普遍关注的新的时代命题。纵观这一时期的“取缔庙会”风潮,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和民间的博弈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但在问题聚焦的空间和宣传话语的使用上颇有差异。北洋政府时期,“取缔庙会”的博弈聚焦于世俗空间,秩序和民生成为双方构建出来的一对主流话语,其他话语被嵌入其中,构成这一时期庙会形象的两个主要面相。
清民鼎革,随着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北洋政府宣告成立。在政权来源的合法性方面,北洋政府一方面承嗣了前清政权的政治法统,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共和制度。这让北洋政府的政权合法性来源颇为正当,也是其兼顾传统与现代,制定各项政策的重要考量。虽然王朝祀典已然废除,国家权力亦从宗教空间中退出,但是作为从传统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会现象,庙会仍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针对各类民间神灵信仰,北洋政府仅将文庙改为孔子庙,由官员定期致祭外,其余神祠皆退出官方祭祀行列,国家对祭祀对象和祭祀行为的态度是听之任之,既不保护,亦不禁止[25]。由此可见,虽然历代封建王朝通过颁布国家祀典来宣扬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北洋政府在废除旧的祀典之后并没有颁行新的国家祀典。这源于新政权法统正当,无须采取尊崇或者打击民间信仰的方式来宣扬政权的合法性,从而让自身陷入矛盾的境地。鉴于民间信仰在各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北洋政府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就不难理解。
北洋政府时期,关于庙会存废的讨论频繁见诸报端。与对宗教空间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形成对比,地方当局对世俗空间却管控甚严。纵观整个北洋政府时期,虽然舆论对宗教空间的报道趋向负面,但从官方层面而言,取缔庙会大多不是因为宗教空间延续了人们对神灵的信仰,而是世俗空间的扩张引发了严重的公共秩序危机。首先,随着公共设施和城市建筑的大量兴建,世俗空间向外延伸的边界受到了限制,经济和文娱活动的异常活跃,使得狭窄的空间范围难以承载不断增加的逛庙人数,造成公共安全事件频发[26]。其次,由于北洋政府时期传统道德体系的崩坏,儒家价值观被视为封建糟粕而招致批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却又迟迟无法构建;随着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道德价值观的评判进入了一个模糊期,世俗空间作为公共空间之一,为社会上的各类越轨行为提供了方便之所[27]。最后,因为北洋政府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持续的政局动荡和人口自由流动给社会增添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而庙会举办日期的固定性和人口的大量聚集,给治安维护[28]和疫情防控[29]增加了潜在的难度。因此,从官方层面而言,由于世俗空间内的公共秩序问题频发,引起社会舆论的普遍挞伐,而地方当局又疲于应对,取缔庙会也就成为通行的处置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从北洋政府时期取缔庙会的情形来看,各地方当局拥有很大的处置空间,对庙会采取的措施也并非千篇一律。从中不难窥见,虽然这一时期对取缔庙会的讨论没有形成统一的舆论风向,但精英阶层的迷信话语却为官方的秩序话语所湮没。虽然政治权力从庙会空间中退出,庙会的举办完全沦为民间的自发性行为,但官方需要履行公共秩序的管控责任,并承担庙会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不良后果,颁布取缔庙会的公文,有时是经过反复权衡的理性决策,有时则是处置过度的懒政行为。毋庸置疑,地方政府对庙会的取缔必然会引发相关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为了促使当局弛禁庙会,相关利益群体以世俗空间内的民生话语来应对地方当局的秩序话语。
庙会每年在约定俗成的日期举办,时空的固定性为商品交换与文娱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庙会举办时间的间歇性,有利于保持对邻近地区民众逛庙的持续吸引力;庙会本身所承载的信仰诉求,有利于淡化逛庙人群在同一空间环境下身份等级和性别差异的彰显[30]。这一时期的禁庙行为对庙会空间内的民生造成了巨大影响。首先,祠庙管理者是最直接的被波及者,甚至让他们全年衣食无着。为维持庙中香火,他们往往以惠泽世俗空间内的民生为由,向当局申请重开庙会[31]。其次,商贩是被波及范围最为广泛的群体,尤其在商业萧条、货物滞销之时,所有商贩的生计均受牵累,“一旦悬为例禁,则强者流为盗贼,弱者转于沟壑矣”[32]。再次,禁庙为民众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每逢开庙之期,“四方商贾云集,凡婚嫁所需物品,悉于此时购之”[33],俨然已成为人们一种例行的消费习惯,取缔庙会无疑给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诸多困难。最后,庙会期间是游人出玩的极佳时期,此时“农工商贾俱放假出游,乡间赴会者络绎不绝”[34],而小贩“搭建凉棚,以备遊人休憩、饮茗,藉兹谋生”[35],取缔庙会让闲暇之际的游人失去了愉悦身心的难得体验。
综上所述,在北洋政府时期,庙会的世俗空间呈现出明显的独立性特征,宗教空间依附于世俗空间而存在,对世俗空间的牵引仅限于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而已[36]。从这一时期庙会形象的建构来看,虽然社会舆论对宗教空间多有斥责,但地方当局对宗教空间却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将禁庙行为聚焦于世俗空间,使得精英阶层的迷信舆论最终湮没于官方的秩序话语和民间的民生话语之中。这对话语不仅让这一时期的世俗空间充满了内在紧张感,而且还成为政府与民间博弈背景下庙会形象被建构出来的两个主要面相。
三、迷信与民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宗教空间的外在张力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关于庙会存废问题的讨论仍在延续,但与北洋政府时期不同,这一时期关于庙会存废问题的角力聚焦于宗教空间,而非世俗空间。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国民党为贯彻其党治理念,纯洁民众的精神信仰,强化新政权的合法性,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迷信运动。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下文简称《标准》),对民间祭祀对象和祭祀行为进行法律性规范。凡祭祀不符合标准的神灵,一概斥之为迷信行为,由地方当局勒令禁止,试图以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旗帜,塑造新政权锐意进取、政治革新的精神风貌。兹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今则不仅神权已成过去之名词,即君权已为世人所诟病,我最优秀之神农华胄,若犹日日乞灵于泥塑木雕之前,以锢蔽其聪明,贻笑于世界,而欲与列强争最后之胜利,谋民族永久之生存,抑亦难矣[37]。
依据《标准》,凡先哲类、宗教类、古神类神祠,民间可以祭祀;在此三类之外者,皆为淫祠,应严加取缔。淫祠分为四类:附会宗庙,实无崇拜价值者;意图藉神敛钱,或秘密供奉开堂惑众者;类似依草附木,牛鬼蛇神者;根据齐东野语、稗官小说、世俗传说,毫无事迹可考者[37]。此外,对民间的祭祀行为亦提出规范:
现查旧日祭祀天地山川之仪式,一律不能适用,即崇拜先哲,亦重在钦仰其人格,宣扬其学说功烈,凡从前之烧香跪拜冥锵牲醴等旧节,均应废除。至各地方男女进香朝山,各寺庙之抽笺礼忏,设道场、放焰口等陋俗,尤应特别禁止,以蕲改良风俗[37]。
从历史延续性来看,中国封建王朝在政权确立之初,往往通过颁布祀典来规范民间祀神行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标准》似乎不足为奇,但在实践层面却与王朝时代有根本性不同。与洪武礼制相比,从实施内容来看,这一时期虽然制定了可供祭祀的神祠范围,但官祭从中退出,祭祀对象也大为缩减,祭祀礼仪更具规范性;而洪武礼制对淫祠的规定较为简单,即“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10],显然不如这一时期更为具体。从实施目的来看,洪武礼制主要是宣扬王朝意志,正祀与淫祀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实际上提供了淫祀向正祀转化的可能,保持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张力,有利于巩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而《标准》在两者之间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从根本上断绝了这种转换关系的可能。由此可见,在近代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鼓动下,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宣扬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南京国民政府似乎展现了与传统神灵信仰相决裂的决心。
虽然“淫祀”带有贬义色彩,但作为一个从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名词,如果不对其赋予现代性的批判意义,就无法凸显南京国民政府取缔庙会的现实诉求和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感。为实现取缔淫祀的目标,塑造反淫祀运动的正当性,国民政府地方党政部门将不符合《标准》的祠庙一律贴上迷信标签,试图借助精英阶层长期以来的反迷信话语,重构人们对“淫祀”这一既有历史现象的固有印象[38]。早在国民政府北伐期间,国民党地方党政部门就运用反迷信话语,在江苏[39]、山东[40]、北平[41]等被占领的省市掀起了一股破坏神像、没收庙产的毁庙运动。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逐渐扩大,大规模的反迷信运动使得“城中各庙的神被拉了十之八九”[42],这些有利条件为《标准》的颁行奠定了基础。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国民政府地方党政部门严禁民众为不符合《标准》的神灵举办庙会[43],对烧纸、点烛、娱神等事关迷信的行为进行严厉制止[44]。总体而言,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掀起的反迷信运动,让宗教空间的神圣性完全湮没在官方的反迷信话语之中。这对各地庙会的打击是广泛性的,对民生的影响是长时段和多层次的。
从短期来看,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反迷信运动达到庙产兴学和破除迷信的目标;从长期来看,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而且还衍生出一系列的民生难题,让自身陷入困境,甚至背离了政策制定的初衷。这一时期对庙会的取缔跟北洋政府时期不同,是由国民政府全面统筹而实施的,对民生的波及已延伸至庙会空间之外,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首先,在国民党执政初期,由于各地方党政部门开展疾风骤雨式的反迷信运动,祠庙被毁者不计其数,大批以此为生的群众纷纷失去了生活依靠[45]。其次,毁庙兴学涉及土地和财产的争夺。在国民党统治基本稳定之后,因侵占庙产而引起频繁的地方纠纷,促使政府出台详细的处理细则[46],将没收的私有庙产返还原主[47]。再次,由于宗教空间内不准烧纸、点烛和燃放鞭炮,使得许多工厂被迫停产,商店被迫停业,造成大量劳工失业[48]。复次,由于庙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社会公共活动,祠庙被毁以后,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上的方便,仍然遵照以往开庙之期,在原址附近开展商品交易和文娱活动[49]。最后,虽然国民政府各地方党政部门掀起反迷信运动,但显然没有做好相应的民生配套措施。每当自然灾害降临,民众只能无奈向神灵祷告,而政府为了转移矛盾和规避责任,甚至参与到民众的祈福禳灾活动中,试图借助封建时代官民共祀模式重塑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这种做法显然已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景背道而驰[50]。
综上所述,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为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宣扬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国民党借助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掀起了大规模的捣毁祠庙和没收庙产的反迷信运动,这对各地庙会的存续发展造成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国民政府各地方党政部门对庙会的取缔与限制对民生领域波及甚广,但却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甚至将自身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因而招致民间社会的强烈反对,《标准》一度被迫暂停执行[51]。从这一时期的庙会形象来看,为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话语延续性,历史上的淫祀话语在此时已被迷信话语所替代,成为官方推动禁庙运动和建构庙会形象的主导性话语;而民生话语仍是这一时期民间社会对抗官方迷信话语的主流话语,继续构成了庙会形象的另一个面相,但使用的群体范围却远较北洋政府时期广泛。
四、余论
唐宋至明清时期,庙会的世俗空间依附于宗教空间而存在,二者联系紧密。民国时期,庙会空间结构发生嬗变,二者的主从位置发生置换且渐呈分离趋势,但宗教空间转而依附于世俗空间而存在。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当局对庙会的取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世俗空间的秩序问题,庙会屡被禁止,宗教空间亦被牵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因反迷信运动的破坏,宗教空间已不复存在,世俗空间也就自然随之消亡。在北洋政府时期,政府与民间关于庙会存废的冲突聚焦于世俗空间的秩序与民生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迷信与民生则构成双方博弈的主要话语。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秩序、迷信、民生构成了庙会形象建构的三个主要面相。
如果说秩序话语体现了北洋政府在应对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焦虑,那么迷信话语则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历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政府或政党用来操纵国家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一种象征或工具”[52],国民政府企图以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来推动反迷信运动,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诚如部分学者所言:“近代政权在意识形态上泾渭分明的不妥协态度,常常导致自己处于民众的对立面,也常常反过来,使自己为社会平衡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行为,失去合法性理据。”[53]如何应对因禁止庙会所引发的民生问题,在北洋政府时期,地方政府主要在秩序与民生之间做出权衡,并没有统一遵循的政治准则;南京国民政府早期是在废除庙会的前提下兼顾民生,由于效果不彰,后期实际上默许了宗教空间与世俗空间共存的事实。
庙会是历史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产物,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其传承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为基础,不为精英阶层的话语所垄断,总是生生不息,甚至比国家权力确立的官方纪念日更有生命力,这也是庙会历史悠久且永葆活力的根源所在[54]。民国时期,庙会持续存在的基础是普通民众物质和精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国民政府用暴力手段摧毁了迷信的外在具象,却无法铲除民众迷信的精神土壤。“无论何种迷信,既以避灾求福为本旨,则虽其愚可笑,而其意亦属可怜。”[55]庙会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迷信话语来消灭庙会,反映了国民政府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美好愿景,但也不应忽视庙会与民生之间的紧密关联。如果能够满足民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那么庙会或许无须取缔,因为其可能会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