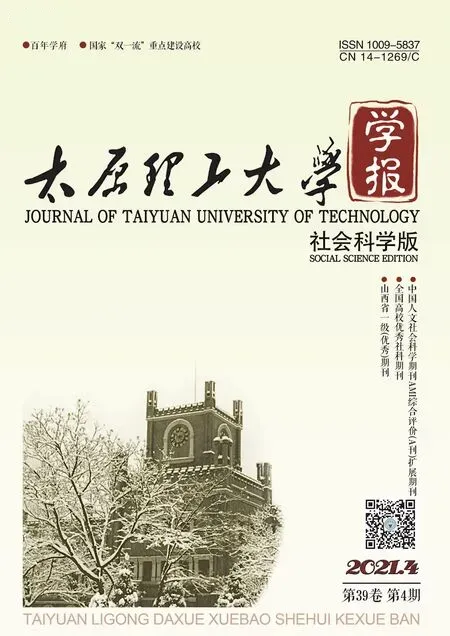吕大临的《中庸》阐释
——兼论与张载、二程的《中庸》诠释之异同
吴喜双,张培高
(1.闽江学院 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2.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吕大临,先受学于张载,后转投二程(程颢、程颐),因此他的思想既兼有关洛的特色,又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一学术特点在他解读《中庸》的著作中有较明显的体现,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庸》之“诚”“中”及“鬼神”等概念的诠释中。本文以吕氏之《礼记解·中庸》和《中庸解》为中心,略抒管见。
一、“理”与“诚”
二程“体贴”出天理后,就把“理”上升到最高的层次,作为世界万物及社会道德伦理的最终依据。从整体上说,在此问题上,吕大临继承与发挥了其师的思想。当然,在某些具体的说法上,吕大临与其师也有不同的地方。
张载提出了“知太虚即气则无无”[1]8的气本论思想。吕大临受其影响也非常注重气,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并认为“气”充满于“太虚”之中。他说:“天生人物,流形虽异,同一气耳。人者,合一气以为体”[2]349,又说:“五行之气,纷错于太虚之中,并行而不相悖也”[2]306。同时,还认为世界之所以能生成、运动的关键在于气本身具有内在的动力。他说:“大气本一,所以为阴阳者,阖辟而已。”[2]182基于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他对《中庸》之“鬼神”的解释了。他在解释“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时说:“万物之生,莫不有气,气也者,神之盛也……鬼神者,二气往来尔。物感虽微,无不通于二气”[2]284,“所屈者不亡、所伸者无息”[2]484。显然,这一解释是受到张载的影响,而不同于二程。张载的解释是“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1]9,“鬼神往来、屈伸之义”[1]16。二程对“鬼神”的解释是“聚为精气,散为游魂;聚则为物,散则为变。观聚散,则鬼神之情状著矣。万物之始终,不越聚散而已”[3]1270,“鬼是往而不反之义”[3]81。二程把“鬼神”解释为气的聚散,并认为“鬼”是往而不返的。之所以会有如此看法,乃在于二程认为“既返之气”不能为“方伸之气”。张载与吕大临皆认为气可以往来屈伸且是永恒存在的,而二程则认为气是会消亡的。正由此,朱熹一方面说:“吕氏推张子之说,尤为详备”,另一方面又说:“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溃反原之意,张子他书亦有是说,而程子数辨其非”[4]74。不过,虽然吕氏在上述的内容上与叔同于张载而不同于二程,但在理气关系上,他明显背离了张载而趋同于二程。张载是在气本论的前提下探讨理气关系的,理是从属于气的,有自然规律之意,如他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1]7。二程则不同,是在理本论的前提下探讨理气关系的,气是形而下的,理是形而上的,他们说:“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3]118。受此影响,吕与叔说:“实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从来,有以致之,物之始也;有所从亡,有以丧之,物之终也。皆无是理,虽有物象接于耳目,耳目犹不可信,谓之非物可也”[2]300。显然,在理与物的关系上,理是最根本的。二程还把“诚”上升到与“理”相等同的高度:“诚者,实理也,专意何足以尽之?”[3]1169吕大临也如此主张,“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是用……故曰:‘诚者,实理也’”[3]1169,又说:“诚者,理之实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2]295。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吕氏对“诚”的解释与张子的不同。虽然在此,吕氏与张载“诚则实也,太虚者天之实也”[1]324一样,用《中庸》的“诚”来肯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但他们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张载没有把“诚”上升到与理等同的高度,无疑吕氏之主张乃是受二程影响的结果。
二、论“中”
中庸是《中庸》的重要概念。与郑玄、孔颖达相比,二程对此解释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分别从体用上对“中庸”进行了解释。一方面他们说:“理则极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3]119,此处所说的“中庸”是从方法论上说的,即无过不及之意;另一方面他们又说:“‘极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极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极”[3]367。在此,他们认为中庸即是天理,这是从本体论上说的,中庸与天理一样是最高的概念。由此可知,二程是从体用上来讲“中庸”的。与此相一致的是,小程还把“中”分为“在中”与“时中”:从体上说,为“在中”,为未发;从用上说,为“时中”,为已发。他说:“喜怒哀乐未发是言在中之义,只是一个中字,但用不同……既发时,便是和矣。发而中节,固是得中,时中之类。”[3]201实际上,小程说的“未发”就是指“理”“性”。他说:“以事言之,则有时而中。以道言之,何时而不中?”[3]200-201但小程的这一说法是在经过与吕大临探讨后才提出来的。
从总体上看,吕氏对中庸的看法皆是在二程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故而师生之间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同之处。
从体用上说,二程认为“中”,从体上说为“天理”,从用上说为“时中”。与小程相比,吕大临对“中”的诠释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不同。所谓同,即吕氏也是从体用两个方面来阐释“中庸”。如他说:“所谓中者,性与天道也”[2]273,又说:“时中者,当其可之谓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当其可也”[2]275。所谓异,即在中与心、性的关系上,探讨前小程的看法与吕氏有较大的不同。不过,经过探讨,两人的观点虽仍然有所差异,但已经比较一致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在《论中书》中有集中体现。先交代一下,小程与吕氏探讨的时间(1)卢连章、陈俊民等学者认为,他们的探讨时间为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卢连章.程颢程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419;陈俊民.蓝田吕氏遗著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1993:642.应出自吕氏作《礼记解》与作《中庸解》之间,因为从小程对吕氏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小程所引吕氏的话都是出自《礼记解·中庸》。经过探讨后,虽然吕大临最根本的观点没有改变,但在一些说法上有所不同了。整体上观之,程颐与吕大临的争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在中与道的关系上,吕大临在《礼记解·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即所谓中;‘修道之谓教’,即所谓庸。中者,道之所自出;庸者,由道而后立”[2]271。在此,吕氏认为“中者,道之所自出”,“中即性”。对此,小程表示反对。以“中与道”的关系来说,小程认为吕氏之说有“支离”之病,因为这一说法把中与道分成两物了。他说:“(吕与叔)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语有病。”[3]605“中即道也。若谓道出于中,则道在中外,别为一物矣。”[3]606小程进一步认为吕氏没有区分体用的不同,他说:“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当。大本言其体,达道言其用,体用自殊,安得不为二乎?”[3]606这就是说性、命、道各有所指,大本与达道是体用关系,而体用是有区别的。实际上,在“中与道”的关系上,师生之间并无根本的分歧。理由在于吕氏之所以会说“中者道之所由出”关键在于他把“中”解释为本心和性,因此所谓“中者,道之所由出”就是指“循性而行莫非道”[3]606和“良心所发,莫非道”[2]271,并不是说“道”中别有“中”。至于大本与大道之“体用自殊”的问题,两人也无根本的分歧,因为吕氏也说:“论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别而言之,亦不可混为一事”。“论其所同”强调的是体用不二,“别而言之”强调的是体用有别。吕氏自己也不认为在此点上与老师有根本不同,他说:“所谓大本之实,则先生与大临之言,未有异也”[3]608。
在中与性的关系上,小程说:“‘中即性也’,此语极未安。中也者,所以状性之体段。若谓性有体段亦不可,如假此以明彼。如称天圆地方,遂谓方圆即天地可乎?方圆既不可谓之天地,则万物决非方圆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谓之性,则道何从称出于中?盖中之为义,无过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为性,则中与性不合……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体,而不可与性同德”[3]606。在小程看来,吕氏之说之所以不能成立,乃在于“中”只是“状性之体段”(即“形容词”),而不是实体。在此,小程还认为“中止可言体,而不可与性同德”。这是不是说中只可言理,而不可言性,理与性有别呢?后来,小程发觉到这个说法不妥当,于是说“谓不可与性同德,字亦未安……以中者性之德,却为近之”[3]606。又说:“前论‘中即性也’,已是分而为二,不若谓之性中。”[3]609所谓“性中”就是指性符合不偏不倚的状态,实际上也承认了未发之中就是性。由此可知,在中与性的关系上,两人的主张刚开始时是有不同的,但经过探讨后两人趋同。
在中与心的关系上,吕氏在《礼记解·中庸》中说:“大本,天心也,所谓中也……理之所自出而不可易者,是为中,赤子之心是已”[2]307。可见,在吕大临看来“中”就是“赤子之心”,所以在与小程探讨的时候,他也说:“喜怒哀乐之未发,则赤子之心。当其未发,此心至虚,无所偏倚,故谓之中。以此心应万物之变,无往而非中矣……大临始者有见于此,便指此心名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细思之,乃命名未当尔。此心之状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3]607。当吕氏说“今细思之,乃命名未当尔”时,似乎意味着这次的争论就告一个段落了,也似乎可以认为吕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
首先,小程与吕氏的探讨并没有结束,小程不认同吕大临把“未发”解释为“赤子之心”与“中”,因为“赤子之心,发而未远于中,若便谓之中,是不识大本也”[3]607。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小程认为“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赤子之心”当然是“已发”,而“已发”只可谓之“和”,不可谓之“中”(“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3]200);二是小程认为“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有别,“赤子之心”只能是“已发而去道未远”,“圣人之心如镜,如止水”[3]202。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圣人之心如镜”之说是小程后来的看法,而促使他改变看法的正是吕大临。当吕氏听到其师说“不识大本”时,便产生了疑问和茫然(“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3]607),于是向老师请教:“先生谓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然则未发之前,谓之无心,可乎?窃谓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具在,已发乃心之用也”[3]608-609。闻此言之后,小程对“心”的看法改变了:“凡言心者,指已发而言,此固未当。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3]609。后来,当小程与苏季明探讨时,虽依旧认为“赤子之心”只能是“已发而去道未远”,但他肯定了“本心”的说法,即“圣人之心如镜,如止水”,而“圣人之心,未尝有在,亦无不在,盖其道合内外,体万物”[3]66。由此可知,在中与心的关系上,探讨前师生之间的看法有较大的区别,经过探讨后虽然两人的观点仍然有所不同,但已经比较一致了。
其次,虽然在这次探讨中吕氏有“此心之状可以言中,未可便指心名之曰中”之语,且在《中庸解》中已不说“中者道之所自出”了,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中庸解》中仍然说:“情之未发,乃其本心。本心元无过与不及,所谓‘物皆然,心为甚’,所取准则以为中者,本心而已”[2]481。又说:“理之所自出而不可易者,是谓之中。”[2]493在此,吕氏仍然把“中”当作实体,即本心。
总之,在对“中庸”的解释上,二程与吕氏的观点大体相同,但也有差异,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小程与吕氏之间。正因有异,故他们所主张的修养工夫亦有所不同。
三、“体验未发”与“反身格物”
二程及其门人(包括吕大临)都主张变化气质的方法,只不过具体的主张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说,吕大临的修养工夫虽带有张子的特色,但基本上已经与大程较为一致了,而与张载、小程有所不同。
(一)“体验未发”
“中和”(未发、已发)问题,自司马光以来,就一直受到新儒家的重视[5-6]。当然,此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理学家讨论的重要问题,乃是由小程与其门人吕大临、苏季明的探讨所造就的。
吕大临把“中”解释为“本心”,又认为“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具在,已发乃心之用也”[3]608,并且“圣人之学,以中为大本”,所以“求中”是君子为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吕氏说:“圣人之学,以中为大本。虽尧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执其中’。中者,无过不及之谓也。何所准则而知过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动,出入无时,何从而守之乎?求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而已。”[3]608吕大临之所以会如此重视“心”,这与二程的教育有密切关系。元丰己未(公元1079年),吕大临东见二程,面对吕与叔“思虑纷扰”的问题,二程都提出了解决之方。大程说:“前日思虑纷扰,又非礼义,又非事故,如是则只是狂妄人耳……闲邪而诚自存,诚存,斯为忠信也。如何是闲邪?非礼勿视听言动,邪斯闲矣……敬以直内,则须君则是君,臣则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7]564小程说:“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车,流转动揺,无须臾停,所感万端。又如悬镜空中,无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心若不做一个主,怎生奈何?”[3]52-53这两条方法有一致之处,皆旨在强调心要有主。在《东见录》中,大程还批评了吕氏的“穷索”方法,而主张“识仁”。吕氏受此影响,综合了张载“无成心者,时中而已”[1]25与大程“心是理”[3]139“识仁”[3]15的思想,从而提出了“中即本心”的思想及“求之于未发之际”的修养方法,但这一方法与小程主张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小程明确反对这一修养方法,对苏季明说:“即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思与喜怒哀乐一般”。又说:“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还说:“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涵养久,则喜怒哀乐发自中节”[3]200-201。小程认为在未发之前(之际)不可求,只能涵养,而吕大临则认为可以。吕氏的这一方法更接近于大程所讲的“识仁”工夫,即直觉体仁的工夫。
(二)反身格物
虽然二程与张子对“尽性”与“穷理”的先后次序看法不同(2)《二程遗书》卷十载,二程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只穷理便是至于命。”子厚谓:“亦是失于大快,此义尽有次序。须是穷理,便能尽得已之性,则推类又尽人之性;既尽得人之性,须是并万物之性一齐尽得,如此然后至于天道也。其间煞有事,岂有当下理会了?学者须是穷理为先,如此则方有学。今言知命与至于命,尽有近远,岂可以知便谓之至也?”《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5页。,但他们皆讲穷理与尽性。即便如此,大程与张子、小程之间仍然有所不同。二程都主张“明庶物,察人伦”[3]638的“穷理”之方,但大程主要倾向主张“尽性”(反身),而张载、小程则认为反身与格外物两者必须兼备(3)如大程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二程集》,第20页。小程则说:“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察。”《二程集》,第193页。。在此点上,具有二重身份的吕大临与张子、小程不同,与大程较为一致。
吕大临在东见二程时,大程对他的“险检、穷索”工夫提出了批评,尽管大程并不完全反对“穷索”(“理有未得,故须穷索”[3]17),但他认为“穷索”不是根本,于是提出了“识仁” “诚敬”的修养方法。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3]16-17据说,吕氏对此“默识心契”,于是作《克己铭》发挥之。《克己铭》确实提出了“存诚”的方法(“大人存诚,心见帝则”[2]590-591),后在《礼记解·中庸》与《中庸解》中,继续发挥了这一思想,如上文所说的“求之于未发之际”的工夫与“存诚”并无二致。这方面的思想,在《礼记解·中庸》及《中庸解》中还有更详细的论述。不过,在论述此修养方法之前,必须先指出的是,虽然吕氏对大程的主张“默识心契”,但他并没有放弃“防检、穷索”的方法。吕大临认为践行“道” “中”的必要前提就是要先认识“道”与“中”,而识“道”与“中”的方法即是穷理致知的方法。他说:“志学者,致知以穷天下之理,则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于实然不易之地,至简至易,行其所无事,此之谓‘明则诚’。”[2]298又说:“虽有共行之道,必知之体之勉之,然后可行。”[2]291若仅此论,当然难以看出吕氏的修养工夫与张子的不同,似乎可以认为他仍然保留关学的特色,然而一旦涉及“穷理致知”的方法本身的含义时,他与关学的不同就立即体现出来了。
虽然张载、大程、小程皆认为“察己”与“格物”是“变化气质”的方法,但大程倾向前者,吕氏亦是如此,故他极力强调“求本心”“反诸身”。他说:“君子贵乎反本。君子之道,深厚悠远而有本,故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本我心之所固有也。”[2]308又说:“为学之道,造约为功,约即诚也……学也问也,求之外者也;闻也见也,得之外者,不致吾思以反诸身,则学问闻见,非吾事也……慎其所以思,必至于得而后已,则学问闻见,皆非外铄,是乃所谓诚也。”[2]296在此点上,他不同于张载和小程,明显与大程一致。大程明确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3]20实际上,吕氏所言的“造约为功,约即诚也”即同于大程的“敬而已矣,便是约处”。
当然,虽说吕大临的修养工夫与大程相近,与小程、张载有所不同,但并不是说他们所追求的境界和目标与张载、小程也不同。在此点上,理学家都是一致的。他们追求的境界是“物我一体”“无物无我”“从容中道”的境界(4)如张载说:“‘君子庄敬日强’,始则须拳拳服膺,有出于牵勉,至于中礼却从容,如此方是为己之学……此皆变化气质之道也。”《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9页。又如二程说:“圣人无私无我,故功高天下,而无一介累其心。”《二程集》,第1271页。。吕大临也说:“诚即天道也,天道自然,无勉无思,其中其得,自然而已。圣人诚一于天,天即圣人,圣人即天。由仁义行,何思勉之有?故从容中道而不迫。”[2]295他讲“内圣”的最终目标与其他理学家(5)陈俊民:《蓝田吕氏遗著辑校》,第283页。其他理学家如周敦颐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页。又如小程说:“君子怀负才业,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怀自守者,盖时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岂君子之志哉?”《二程集》,第801页。一样仍然是“外王”:“达则兼善天下,得志则泽加于民”[2]283。
总之,在对《中庸》的解释上,虽然二程与吕氏之间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二程及吕氏对《中庸》的解释在朱子看来都有不妥之处,要么杂有佛老之因素,要么与《中庸》原意不合,要么意有不尽等(6)如朱子批评大程云:“至于修道,则程子‘养之以福’、‘修而求复’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9页。又如批评吕氏在解《中庸》第十三章时说:“吕氏改本大略,不尽经意。旧本乃推张子之言而详实有味,但‘柯犹在外’以下为未尽善。”同上,第71页。,故而对他们皆有批评;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解释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朱子所吸收,如对忠信的解释[8]64-65,为其作《中庸章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子把《中庸》与其他三书编成了《四书》。后来元明清三朝把《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四、余论
吕大临不仅在学术上成就甚多,著有《礼记解》《易章句》《中庸解》等解经著作,以发明关洛之学;而且特重礼仪之践行,与其兄弟吕大均等编有《吕氏家祭》《吕氏乡约》[2]631-634,以化民俗。与之同时,尽管吕与叔(公元1042年—1090年)距今已有900多年的时间,但他对“中庸”所做的诠释,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这一意义主要表现为有助于我们调节身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之达到和谐的健康状态。
首先,有利于调适心理,达到身心和谐。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界定可知,健康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具有社会适应能力。其实,后者也可归属于心理方面。因此换言之,健康就是指身心健康。虽然两者的标准有所不同,但两者实有共同之处,即当身体或心理处于良好的状态时,那么就可以认为是健康的。生病的原因有多种,有些原因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如遗传以及受到不可避免的外部环境的影响等,但大多数的原因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正如古人经常所说的“病者,过也”。所谓“过”就是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或范围。当身心所承受的能力超过一定的度时,就会出现病变,而出现后,又不加注意,日积月累,就会发展成为严重的疾病。比如近年来,有数据表明患颈椎病或精神障碍的患者越来越多,甚至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2018年8月3日,《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转载了一篇文章,文章说:“目前全国大约有7%~10%的人患上了颈椎病”,“这种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增高,并且明显趋向低龄化。特别是中小学生颈椎病的发病率正快速上升”[9]。据2016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1600万人。”[10]虽然这些疾病的患者发病的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其中也有共同之处,即颈椎或心理没有及时得到放松,而是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具体言之,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流行,年轻的“低头族”越来越多,每天低头看手机或电脑的时间太长,于是使颈椎长期处于紧张之中,长年累月必然会导致颈椎病。有些精神障碍患者也是如此。在刚出现自卑、虚荣、烦恼、焦虑等认识障碍或情绪障碍时,未及时得到调节,而随后的日积月累,当量的积累突破个人承受能力的峰值时,便会产生精神障碍;若再得不到调节,便会长期处于紧张之中,从而导致严重的精神障碍,进而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在此情况下,吕氏所说的“本心,中也”的本体论和“求中”的方法论对此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中”不一定指“中间”位置,而是说此位置或状态一定是恰到好处的。如上所述可知,在吕氏看来,人心之初就是处于恰到好处的和谐状态,后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使之发生了变形,丧失了原初的和谐。所以吕氏认为必须通过后天的“求中”工夫恢复先天的状态。这一工夫的实质就是以“中”(或恰到好处)作为处事的原则与方法。比如,在使用电脑或手机时,须遵行“适度”的原则,也就是说要做到张弛有度,每隔一段时间(如1小时)就休息一下,使紧绷的肌肉得到应有的放松。心理紧张也应按这个方法进行调节,经过不断的调整,心理就能处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之中,自然就不会产生精神障碍了。
其次,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预示着工业社会的来临,而随后的第二、三次工业革命更使人类进入到一个生产力更加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然“善亦进,恶亦进”。换言之,当我们在沉浸由发达生产力所带来的富裕物质生活之中的同时,也默默承受着因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而导致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等严重生态问题,并承受着由此带来的巨大伤害。早在20世纪60年代生态问题就开始受到关注。1962年,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雷切尔·卡逊出版了一部名为《寂静的春天》的著作。在书中,他以大量生动而严峻的事实描绘了滥用工业文明之成果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如大量使用DDT剧毒农药后,导致了鸟类的大量死亡,村庄一改往日的喧闹而处处呈现出一片令人悚然的死寂。尽管该书出版时受到企业家们的非议,但随后便得到了世人的理解与接受,并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消耗自然资源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使我国也出现了雾霾、沙尘暴、水污染等方面的严重生态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11]390。因此,生态环境的治理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便成为国人的诉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12]233。在环境的治理上,有效方式除了“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13]210外,所有的企业和全体居民均以“绿色”“环保”作为生产、生活原则也是一种对环境治理有积极作用的方式。而这一方式的实质就在于以“中”(恰到好处)作为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若用吕氏的理论来说,“中”不仅是心之原生态,也是客观事物本身(包括人与自然)的原初状态。当人与自然之原生态受到破坏时,也可按照“求中”的方法加以恢复。具体地说,如耕地实行轮作休耕制度,即在某一段时间使耕地闲置、不种庄稼。如此,既可避免土壤的退化和地下水的超采,又可增加土壤的肥力,进而使农作物增产,因为土地的肥沃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土地是财富之母”[14]208。又比如,在某一段时间实施休渔制度,尤其在鱼类繁殖、成长期间实行休渔,如此就可以增加鱼类的数量,恢复生物链上的平衡。而这些举措背后的哲学原理就是古人所说的“中庸”(恰到好处)。
总之,吕大临虽生活于北宋时期,但其思想或观念在今天仍具有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