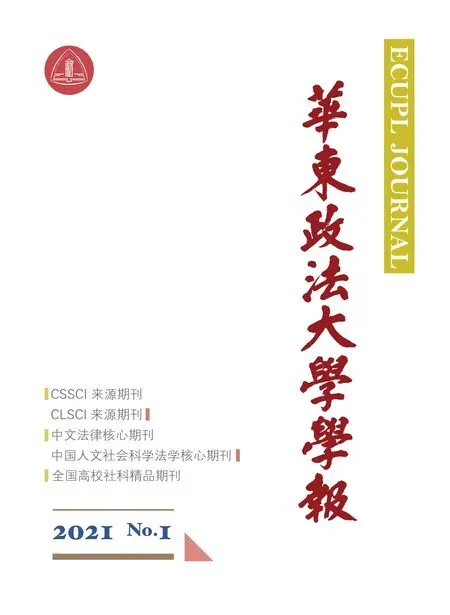“司法克制”的法律方法分析
——以美国法判例为线索
安恒捷
一、引言
司法是现代稳态社会的均衡器,亦是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通过司法达致社会正义是民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社会法治化治理的必然选择。〔1〕参见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209-284 页。在社会转型发展时期,司法究竟应该克制,还是能动,背后映射的是不同的司法哲学,以及对经典司法功能形态的不同认识。虽然中国法治语境下的“能动司法”与固有语境中的“司法能动”具有实质性区别,但是如何更好地厘定与实现司法的功能,始终是中国法治新时代要思考和回应的问题。
目前,学界关于“司法能动”的研究已相对丰富,而对“司法克制”的研究仍有待深化。除了部分学者从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的应然角度展开对司法克制及其相关理论的阐述外,〔2〕参见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 年第6 期;吴英姿:《司法的限度: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载《法学研究》2009 年第5 期;顾培东:《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4 期;陈金钊:《司法意识形态:能动与克制的反思》,载《现代法学》2010 年第5 期;程汉大:《司法克制、能动与民主——美国司法审查理论与实践透析》,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6期;杨知文:《司法能动主义与当下中国的能动司法——语境和语义的考察与比较分析》,载《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 年第1 期。其他的研究或者通过介绍霍姆斯、波斯纳等域外研究者的学说来阐述“司法克制”的概念内涵,或者从与“司法能动”相对应和区别的视角来界定“司法克制”的含义。〔3〕参见李辉:《论司法能动主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版。由此可见,已有关于“司法克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司法能动”概念的澄清与反思中描述“司法克制”的应然状态,某种意义上导致了相关的研究欠缺更为细致的方法论层面的梳理。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以司法的含义为切入点,从法律方法的角度对司法克制的固有语义加以分析和阐发,试图以此来厘清司法克制的基本含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美国司法判例的梳理和要件提取,对技术层面的“司法克制”及其方法论意涵进行阐述,明确司法克制对司法权威乃至法律权威的重要意义。作为描述和刻画中国司法功能形态的重要概念工具,“积极司法”具备理论和概念逻辑上的优越性与自洽性。以此为基础,从技术和方法层面阐明司法克制作为一种经典司法功能形态,对于发挥司法在转型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充分实现司法的审判职能,实现司法和法律的权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司法克制”的概念意涵
(一)从“司法”到“司法克制”
联合国《司法机关独立若干基本原则》文件规定:“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4〕参见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IndependenceJudiciary.aspx, 2020 年11 月10 日访问。此外,1982 年10 月22 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国际律师协会第十九届年会通过了《司法独立最低标准》,1983 年6 月10 日在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举行的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会议通过了《司法独立世界宣言》,1985 年8 月至9 月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七届联合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1989 年5 月24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实施程序》,1994 年1 月20 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基本原则》,1995 年8 月19 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六届亚太地区首席大法官会议通过了《司法机关独立基本原则的声明》,都对“司法”的含义作了较为相近的描述。〔5〕参见李步云、柳志伟:《司法独立的几个问题》,载《法学研究》2002 年第3 期。其中主要包含司法活动的主体(法庭)、对象(案件争议)、方式(运用证据认定事实,依据法律裁判)、属性(独立无偏)等内容。归纳而言,“司法”就是公正无偏的法庭,针对具体的案件争议,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解释适用法律,推断做出权威性法律决定的活动。〔6〕参见张志铭:《司法判例制度构建的法理基础》,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6 期;张志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载《法制日报》2015 年10 月28 日,第11 版;于浩:《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话语、实践及其反思——以“司法”定义切入》,载《山东社会科学》2015 年第10 期。
基于上述司法的概念可知,司法是国家司法权机关适用法律裁决纠纷的专门活动,其功能在于针对个案争议作出法律决定。由此,司法的功能形态关涉的是在原理层面上司法如何行使其权力。当然,理解司法的功能形态不仅可以从宏观角度观察,也可以从微观层面理解。微观层面主要包括两对基本概念,一组是“纠纷解决”和“规则创制”,另一组是“对抗制”与“讯问制”,前者是一对从权能意义上对司法功能进行理论解析的概念工具,后者是一对从诉讼结构或审判方式层面对司法功能的实现方式、形态进行解说的概念工具。一般认为,随着审级的提高,纠纷解决的功能将相对弱化,规则创制的功能则相对增强。然而,无论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都将贯穿上述概念,并成为相应的分析工具。更为准确地说,正是在法院协调纠纷解决和规则创制功能的过程中,“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这一对概念获得了分析法院行为与司法决策的实践空间。当然,能动司法或者司法能动主义有其固有的语境和语义。对于描述或者刻画中国语境下的司法功能形态而言,“积极司法”是一个在逻辑上更为圆融、自洽且符合司法规律的概念工具。〔7〕参见前注〔2〕,张志铭文。
(二)作为经典司法功能形态的“司法克制”
美国联邦法院的司法实践对于理解作为一种经典司法功能形态的“司法克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选取了美国联邦法院裁判历史上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若干位大法官的论述,比如罗杰·布鲁克·托尼(Roger Brooke Taney)、法兰克福特(Frankfurter)、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等人。
罗杰·布鲁克·托尼法官是继马歇尔法官之后最为典型的自制法官,他做出了大量恪守司法自制原则的司法判决,比如最有代表性的卢瑟诉博登案(Luther v. Borden)〔8〕该案是确立司法不应裁判政治问题这一司法克制原则的主要渊源。See Luther v. Borden, 48 U.S.1 (1849).。托尼大法官对于司法克制立场的理解体现在如下判决书中的一段话中:“原告所提出的大部分理由均涉及政治权力和政治问题,而法院被要求对以上问题发表意见。我们拒绝这么做……虽然法院应该随时准备去解决宪法托付给它的问题,但它同样不应该超越其行为的适当范围,并注意不使自己卷入到应当属于其他部门解决的争论中去……依据这个国家的体制,每个州的主权属于该州的人民,而且他们可以依据他们自己的愿望去改变政府的形式。但他们是否改变了政府或废除旧政府代之以新政府,这是一个需由政治权力解决的问题。而政治权力一旦做出决定,那法院就有义务注意并遵从。”〔9〕Luther v. Borden, 48 U.S.1 (1849).
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在1962 年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 Carr)中所发表的异议迄今为止仍然被视为关于保守主义司法哲学最为经典的表述:“无视本院司法权有效行使的内在限制而介入本质上属于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有关人口与立法代议制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即由政治力量决定,于今亦然——不但注定徒劳无功,而且可能严重损伤本院作为‘本国至高法律’最终解释机关之地位,因为诸多必须由本院裁判的法律问题,常与民众的感情紧密相连。本院既不管钱又不握剑,其权威委实深植于民众对本院道德裁判的恒久信赖之上。而此种信赖感须由本院在实然与外表上均完全摆脱政治纠葛,并避免深陷政治决策时政治力量之间的折冲。”〔10〕Baker v. Carr, 369 U.S.186 (1962).
美国联邦法院司法克制立场的形成与其司法审查的实践密切相关。司法克制对于司法审查而言就像是汽车的刹车,因为司法审查本身被视为一种对抗多数民意的力量。〔11〕亚历山大·M. 比克尔在《最小危险部门》一书中专门讨论了司法审查中的“反多数难题”。See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司法克制的诸项原则与一个个涉及司法审查的案例相关联。比如,坎普诉霍金斯案(Kemper v. Hawkins)一案形塑了“违宪必须明显”原则;奥格登诉桑得斯案(Ogden v. Saunders)形塑了“有效推定标准”和“超出合理怀疑原则”;前述托尼大法官法院裁决的卢瑟诉博登案(Luther v. Borden)则形塑了“政治问题回避”这一重要司法克制原则;芒恩案(Munn v. Illinois)则形塑了“合宪推定原则”。〔12〕这些司法克制的诸项原则均表明司法机关一方面要尊重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立法和行政部门做出的决定,另一方面应当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政治荆丛”中。参见刘练军:《论司法自制——以美国案例为材料》,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 期。
波斯纳法官《司法克制的含义》一文中认为,人们一般在五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司法克制”一词:(1)一位自我克制的法官不允许自己的政策观点影响司法判决。(2)法官在引入自己的政策观点时会非常小心、谨慎甚至迟疑。(3)法官会非常留意司法权力运用中的实际政治限制。(4)法官的判决会被唯恐混乱的权利司法创造导致诉讼中的法庭陷入泥淖而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担心所影响。(5)法官会想要减少与政府其他部门相关的法院系统的权力。〔13〕See Richard A. Posner, The Meaning of Judicial Self-restrain, 59 Indiana Law Journal 1 (1983).而在《司法反思录》一书中,波斯纳法官总结了关于司法克制的三种经典定义。他认为,我们应当认真对待以下三种含义:(1)法官就是适用法律,不制作法律(“法律要我这么做”);(2)法官尊崇其他官员的决定——上诉法官尊崇初审法官和行政机构,所有法官尊重立法和行政决定。(3)“宪法性克制”,即不情愿以宪法为根据废除立法。〔14〕See Richard A. Posner, Reflection on Judg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50-151.中译本参见 [美]理查德·波斯纳:《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73-174 页。此外,波斯纳用谷歌词频统计程序(Google’s Ngram Viewer program)的方式总结了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词频”,以此表明司法克制的衰落趋势,该程序的主要目标是统计一个词或短语在谷歌扫描的数百万本书籍创建起来的数据库中出现的相对次数。See Richard A. Posner, Reflection on Judg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63.
综上,“司法克制”就是试图通过司法权运作的自我约束来平衡权力分立与共和制的权威。〔15〕Kermit L. Hall, James W. Ely, Jr., Joel B. Grossman,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42-544.具言之,司法克制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彰显和维护司法权威:其一,组织结构上的限制,尊重联邦制对司法权力的限制、权力分立和法院在司法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其二,解释上的控制,遵循先例、制定法或者宪法文本、宪法设计以及宪法传统施加于司法自由裁量之上的边界;其三,个人克制,避免因当事人或者自己对问题的观点导致对裁判的歪曲。〔16〕参见 [美]玛丽·安·格伦顿:《法律人统治下的国度——法律职业危机如何改变美国社会》,沈国琴、胡鸿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19 页。
三、司法克制的裁判风格与基本进路
(一)司法克制的裁判风格
英美司法的克制品格不仅表现在裁判理念上,也体现在具体的裁判场景中。诚如培根所言:“法官在审判中,有四件任务:(1)调查证据;(2)主持庭审时的发言,制止与庭审无关的题外话;(3)宣示审判所根据的原则,总结案情;(4)根据法律宣判。如果超越这四件事之外,那就做得太多了。”〔17〕[英]培根:《论司法》,何新译,载孙国栋主编:《律师文摘》2002 年第1 辑,时事出版社2002 年版,第229 页。
这种自我克制的风格贯穿着案件庭审的过程。例如在交叉询问环节,控辩双方提问一般证人和鉴定人士时,格林勋爵(Lord Greene MR)劝他的同事切勿卷入提问证人之战的忠告,经常被人们引用,他又说,这样的法官是“下竞技场,视线容易被冲突的烟尘所遮蔽”。〔18〕Yuill v. Yuill [1945] 1 All E.R. 183.俗谚云,“多嘴法官不动脑”,英美法官的作用可能较为消极,因为他们起初对案情一无所知,他们必须在诉讼进行中了解案情。当事人及其律师发挥主要作用,其原因与根深蒂固的下述观点有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如何才能最好地获得真实情况或接近真实情况。他们认为最好是让当事人通过辩论来发现真实情况,对有关案件,各方都提出自己所认定的主张,并为之辩护,法官消极静坐一旁,基本上是单纯地对遵守辩护的竞技规则情况予以监督。〔19〕[德]茨威格特、 [德]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年版,第488-489 页。
(二)司法克制的三种进路
基于英美法传统上的当事人主义,波斯纳总结出与司法克制有关的三种共同进路。〔20〕Richard A. Posner, The Federal Courts: Challenge and Refor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3-334. 中 译 本 可 参见 [美]理查德·A. 波斯纳:《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也可参阅Jeff A. King,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to Judicial Restraint, 28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09 (2008).
第一,尊重进路(deference),即法官应当在裁判中避免与政府其他分权部门的决定产生矛盾。〔21〕Richard A. Posner, The Federal Courts: Challenge and Refor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14.波斯纳认为,尊重的对象主要包括对联邦和州一级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决定。这一进路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被便捷地加以测度。在个人权利的司法保护中,“尊重进路”一般会导向较为严格的个人权利的宪法构建。个体权利在宪法上的扩张解释常常被视为能动主义司法的典型表征。当然,这一进路也并非绝对与个人权利的司法保护所不相容。比如,洛克纳一案中,立法机关设定的权利反而催生了其他更多类型的权利形态。尊重进路的适用领域主要集中在行政法及涉及个人权利的宪法诉讼中。波斯纳将文本主义、原旨主义以及严格遵循先例排除在“尊重进路”之外,因为如果按照文本主义的方法,有时候会导致在司法上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决定效力的丧失。这就使得法院的判决在克制与能动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甚至矛盾。但是,这种排除并不具有普遍性。在司法克制诸原则中,涉及尊重原则或者说尊重进路的,可以用“守门性原则”(gatekeeping)加以概括,主要包括案件争议原则、诉讼资格原则、司法救济不能要求进行司法审查。
第二,缄默进路(retience),即法官应当在裁判中避免作出道德以及可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选择。〔22〕Ibid.具体来说,司法克制的核心要旨可归纳为“法官不应当制定政策性判决”,也有的学者认为,司法克制要求法官应当尽量避免道德、政策、政治、无法实现以及多中心主义考量等理由。缄默原则最主要的理论障碍在于如何解释法官应当做出某些基于道德考量的判决而避免其他基于道德考量的裁判。从逻辑角度分析,缄默原则可以证立文本主义和尊重先例原则,但是它很难明确地证明司法克制的“守门性原则”,如案件争议原则。
第三,审慎进路(prudence),即法官应当避免做出一些会使得削弱他们做出其他决定之能力的判决。〔23〕Ibid.波斯纳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审慎原则。一是政治审慎克制原则,二是功能性审慎克制原则。政治审慎克制原则主要指法官应当避免做出相较于原判决而言有可能引发政治报复的判决,因为这会影响司法机关做出其他司法判决的能力。比克尔则主张一种更为巧妙的观点。他认为,司法克制原则或许会被运用于司法判决对宪法价值的尊重,进而促进日常政治和立法过程中能够形塑一种更为合适和明智的决策。通过这种选择性的适用,政治审慎克制原则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以及促进法院的权威。〔24〕See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6.
功能性审慎克制原则指法官应当避免做出有可能导致法院超负荷工作因而无法充分胜任未来案件的解决的判决。这一原则关注的主要是法院在实质性判决上的工作负荷。这是一种传统的“防洪闸”论点:通过创设新的实质性的权利,法院或许会增加他们自身的工作负荷,以至于他们不足以胜任未来案件争议的解决。这一原则比政治审慎原则所能够解释的司法克制原则更少,尽管能够解释遵循先例原则,但是无法充分说明文本主义原则。这两种进路都是一种法律现实主义的主张:法院所给出的判决理由并不一定是司法判决的最终决定性理由。〔25〕John Daley, Defining Judicial Restraint, in Tom Campbell& Jeffrey Goldsworthy, eds., Judicial Power, Democracy and Legal Positivism, Ashgate Publishing, 2000, pp. 286-290.
四、司法克制的裁判基准点
司法克制最终需要落脚到案件裁判中。美国法判例中发展出了一套基于司法克制立场的裁判基准点,用来判断一个纠纷是否属于司法管辖的范畴,以及应当如何做出具体的判决。爱德华兹法官将这样一套裁判基准点理解为美国联邦法院权力运行所遵循的原则,并称其为“可裁判性”原则。〔26〕Justiciability 又可理解为“可司法性”。一般而言,“可司法性原则”被视为对于美国联邦法院权力之限制,主要包含两种类型:宪法性限制和审慎性限制。其中,宪法性限制主要源于美国《宪法》第3 条第2 款的文本内容(即“案件争议”要求)。See Erwin Chemerinsky, Constitutional law, Aspen Publishers, 2019, p. 50-53.相关研究也可参阅G Marshall, Justiciability, in AG Guest ed.,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65, 267-268; R Summers, Justiciability, 26 Modern Law Review 530 (1963).具有“可裁判性”的案件是指可以被联邦法院听证并作出裁决的案件,从而在更为具体的意义上刻画了司法克制的含义。一项争议具有可裁判性,必须具备如下条件。〔27〕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12-227 页。
(一)案件必须符合“案件”或“争议”要求
按照司法克制立场,在美国审判实例中,一个案件能够被法院判决,必须符合美国宪法第3 条第二款意义内的“案件”或“争议”(case and controversy)要求。〔28〕Aetna Life Ins. Co. v. Haworth, 300 U.S. 227 (1937).这种“争议”必须是明确、具体、真实、实质的。同时,“争议”主要是指民事性质的诉讼,其在概念外延上不如“案件”全面。但是,它们的共性在于:第一,均为现实且已经发生的内容,也因此适合进行司法判断;〔29〕Osborn v. United States Bank, 22 U.S. 738 (1824).第二,它们均不同于猜想、假设或者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分歧,也有别于学术层面上的争论;〔30〕United States v. Alaska S.S. Co., 253 U.S. 113 (1920).第三,它们不仅明确、具体,并且将会通过程序而最终导出针对一方当事人的不利益,〔31〕South Spring Gold Co. v. Amador Gold Co., 145 U.S. 300 (1892); Fairchild v. Hughes, 258 U.S. 126 (1922); Massachusetts v. Mellon, 262 U.S. 447 (1923).也就是存在具体的请求权基础、可以通过某项法定程序而获得权利救济,而非仅仅就某种设想中的事态进行推断并给出法律建议。因此,在为这些现实已经发生的案件或争议提供解决程序、实施权利救济、实现定分止争方面,法院都必须依据立法机关的授权,在其具体的授权范围内行事,而不能做出游离于“案件”或“争执”之外的“咨询意见”(advisory opinions)。〔32〕当然,限制“咨询意见”存在例外情况。《元照英美法律词典》中“咨询意见”词条项下内容包括:1.国际法院应联合国及其授权的专门机构的请求就某一问题所提供的解答意见,但不具有法律拘束力;2.在美国,指法院应政府或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就某事项如果提交诉讼,法院将如何裁决所提供的意见。它是对法律的解释,但无法律约束力。通常州法院才提供咨询意见,联邦法院因宪法规定其管辖权限于审判案件和争议,所以它不提供这种咨询意见。在某些司法区,法院应立法机关的请求也可提供咨询意见;3.在美国,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就某一法律点(point)所提供的意见;4.在联合王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应请求也可以提供咨询意见。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缩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43 页。
在这里,“拒绝提供咨询意见”要求存在现实而非拟制的争议,可谓司法克制原则的“原初状态”,最早可以追溯至美国建国初期。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任期内,联邦最高法院就表示,做出咨询意见并不具有合宪性,原因在于,关于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建议并非源于某个案件或者某项争议。华盛顿总统曾经通过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询问法官,他是否能够咨询法官关于战争中的相关法律问题(比如在保持中立的前提下,能否在国内港口向英国和法国同时出口武器),其中,美国是英法战争之间的中立国。根据美国宪法第3 条,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回信答道:“三权分立中三个权力部门之间在某些领域的互相制衡以及最后一锤定音的法院法官(这些制度设计)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即坚决反对司法权力部门不当地超出范围裁决争议,尤其是涉及宪法所赋予总统的权力。咨询司法权力机关负责人的意见,似乎已经刻意且明显地归属于执行机关。我们为任何可能导致您政府部门尴尬的事件而表示深深的遗憾,但是令人宽慰的是,您的理性将会做出正确的选择。”〔33〕Geoffrey R. Stone et al., Constitutional Law, Wolters Kluwer, 2018, pp. 87-88.
(二)原告应当具备诉讼资格
原告必须具备诉讼“资格”(standing),这决定“谁可以起诉”的问题。从概念上,设置“诉讼资格”是为了确保一方当事人在案件的最终结果中有足够的利害关系,以便保证提交到法院的是真实的案件或争议。〔34〕新近相关判例可参见Rucho v. Common Cause, 588 U.S.(more), 139 S. Ct. 2484 (2019); Lamone v. Benisek, 588 U.S.(more)(2019); Gill v. Whitford, 585 U.S.(more), 138 S. Ct. 1916 (2018).诉讼资格的有些要素是宪法所要求的,有些要素是法院为了有效地司法管理而提出的要求。有时候,某些规则究竟应属于哪种类型界线也很模糊。假如对诉讼资格的限制是“法院审慎做出的”而非宪法要求的,那么这种限制便可能被国会推翻而不损害有限司法权力这一宪法结构。
在美国宪法中,诉讼资格的最低宪法要求是指原告必须确定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实际伤害原则(injury),其已经遭受或马上遭受实在的、具体化的伤害;第二,因果关系原则(causation),该伤害是由被告的被质疑的行为造成的,即伤害可以公平地追溯到被起诉的行为;第三,救济可能性原则(redressability),该伤害很可能(而不是主观臆测)通过法院的有利判决得到补救。〔35〕See Erwin Chemerinsky, Constitutional law, Aspen Publishers, 2019, pp. 64-85.相关代表性案例包括; Linda R.S. v. Richard D, 410 U.S.614 (1973); Warth v. Seldin, 422 U.S.490 (1975); Simon v. Eastern Kentucky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 426 U.S.26 (1976); Duke Power Co. v. Carolina Environmental Study Group, Inc. 438 U.S.59 (1984); Allen v. Wright, 468 U.S.737 (1984); Lujan v. Defenders of Wildlife, 504 U.S.555 (1992).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三项涉及“诉讼资格”的规则限制:第一,提出第三人权利规则,原告不得主张或依赖没有诉诸到法院的第三方权利;第二,普遍性不满规则,原告向法院的陈述不能仅仅是所有或大多数公民所共有的“普遍性的不满”(generalized grievance);第三,利益范围规则,原告必须属于制定法或宪法条款意欲保护的“利益范围”之内。〔36〕同前注〔27〕,宋冰书,第214 页。See Erwin Chemerinsky, Constitutional law, Aspen Publishers, 2019, pp. 90-111.
有学者认为,之所以要对诉讼资格进行限制,主要是有以下考虑:“对诉讼资格的限制会带来一些政策上的益处。第一,可以促进宪法所体现的权力分立,因为它尽可能地减少了司法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冲突。第二,诉讼资格原则可以提高司法效率,因为它防止了那些对案件结果仅有抽象的、意识形态上的利益的人提起诉讼。第三,诉讼资格原则可以改善法院的决策质量,因为它可以保证法律问题是在具体的事实背景下被决定的,并且保证案件中拥有足够利害关系的对立当事人。第四,诉讼资格原则可以促进公正,因为它可以保证人们只提出自己的权利和所关心的问题,而不插手他人的事务,从而保护那些没有寻求法院帮助的人。”〔37〕Erwin Chemerinsky, Constitutional law, Aspen Publishers, 2019, pp. 61-63.约翰·达利进一步批判性地给出了限制诉讼资格规则的理由:“法官应当严格适用诉讼资格规则,除非当事人在结果中具有某种紧密的个人利益,否则法官应当拒绝继续审理该案件中所涉及的实体性法益。诉讼资格有时候被描述为一种要求,即法律对于当事人而言具有比一般公众更大的影响。这一公式是具有误导性的。比如,尽管法律的术语是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的,当存在针对某个当事人的刑事诉讼时,某个当事人就具有诉讼资格。真正的标准在于,结果中的紧密个人利益关联。越多的克制型法官要求当事人具备某种明确清晰的个人利益,也就越容易将它与一般公众的利益相区别。”〔38〕John Daley, Defining Judicial Restraint, in Tom Campbell& Jeffrey Goldsworthy, eds., Judicial Power, Democracy and Legal Positivism, Ashgate Publishing, 2000, p. 282.
(三)案件必须具备成熟性、既往性等可裁判特征
案件具备可裁判特征,主要是指案件满足了以下特征:第一,案件必须是“成熟”的,亦即已经到了进行司法审查的合适时间。约翰·达利认为:“法官应当仅仅针对现实的争议做出裁判,他们不应当针对某个法律问题做出一个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是模拟的判决。克制型法官要求当事人的利益属于传统法益类别范围,并且要求确保法庭的裁判将会切实地影响案件当事人。案件的既往性(mootness)有时区别于案件的成熟性(ripeness)。如果任何救济措施都无法影响诉讼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那么秉持两个原则的法官都会拒绝考虑受理此类案件。如果当事人之间的争端已经结束了,因而法院的救济将与被告方无关联,那么一个案件就是假想的;如果当事人必然在将来(而非当下)会发生争议,法院的介入切实影响被告人,那么一个案件就是不成熟的。既往性与成熟性都是‘案件争议’所要求的要素。”〔39〕Ibid, p. 281.可见,在案件裁判成熟性的判断上,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其一,争议是否宜于作出司法决定;其二,法院考察如果不考虑该案时对当事人的伤害有多大。
第二,案件不能是“已失去实际意义的”,亦即进行司法审查的时机不能过晚。这首先与司法审判的“既往性”有关。如果不存在法院可以解决的实际争议,案件就成为既往,法院便失去了管辖权,但这一原则存在三项重要例外:其一,即使主要伤害已经解决,但仍存在次要或“间接”伤害的案件;其二,不法行为被认为是“可能重复但不易被审查的案件”;其三,被告自愿停止被质疑的行为但可能随时恢复该行为的案件(“自愿终止”)。〔40〕See Erwin Chemerinsky, Constitutional law, Aspen Publishers, 2019, p.126-137; 同前注〔27〕,宋冰书,第223 页。
第三,这一点也跟案件裁判的内容是否为现实的“争议”和“案件”有关。由于司法部门是唯一不主动实施法律或计划的政府部门,因此司法机关的任务是“解决对立的当事人向该部门提出的案件或争议。至少根据美国的法理学,法院的首要职责是确定其是否对向其提出的具体案件具有司法管辖权,该案件是否实际存在或是否为实际争议,而非理论性或假设的争议。”〔41〕[美]海格:《法治:决策者概念指南》,曼斯菲尔德太平洋事务中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4 页。
(四)案件争议内容不应涉及政治议题
司法克制理论的一项核心裁判基准点是案件本身不涉及政治议题,又或者说不构成“政治问题”。〔42〕新近的代表性司法判例包括Rucho v. Common Cause, 588 U.S.(more), 139 S. Ct. 2484 (2019); Lamone v. Benisek, 588 U.S.(more) (2019).约翰·达利认为:“法官应当避免裁决包含最好由其他政府部门决定的特殊事项的‘政治问题’。尽管这一原则是在美国发展建立的,但在澳大利亚并没有形成这一原则。司法克制型法官会通过解释政治问题这一原则将某些特定的事实纳入更大范围的案件类别之中。”〔43〕John Daley, Defining Judicial Restraint, in Tom Campbell& Jeffrey Goldsworthy, eds., Judicial Power, Democracy and Legal Positivism, Ashgate Publishing, 2000, p. 283.这是因为,“司法克制是司法决定制作过程的一种弥散性特征”,“在学术领域,司法克制包括多重含义,比如尊重立法和行政决策、遵循先例(谨慎地推翻先例)、制定法解释中的文本主义者或者严格建构主义者、案件诉讼资格或者具有既往性、司法政策考量以及法官应当避免做出道德或者政策选择。”〔44〕Kavanagh, Aileen, Judicial restraint in the pursuit of justice, 6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25(2010).
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不仅应当避免对政治议题做出判断,也应当避免根据他们自身的争执判断和政策判断而做出判决,这就是司法克制理论所内含的“避免纯粹的政治判断”和“避免纯粹的政策判断”原则。曾任美国联邦政府首席检察官的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认为,司法克制至少包含如下三个要素:第一,法官应该审慎的——或者不应该——从“法律的正当程序”与“法律的平等保护”这类宪法概念中阐释出更为具体的价值。第二,在选择相冲突的价值之时,比如在经济自由与雇工福利之间,法官应该慎重地——或者不应该——用他自己的判断去取代立法机构的偏好。第三,法官不能过于仔细地检视宪法中的事实问题。〔45〕[美]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院与宪法》,田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0-161 页。考克斯认为,司法克制主义者通常强调四项因素:1.代议自治政府和多数主义规则——政府的基础在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根据上述这些价值的要求,在如“正当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这些模糊的宪法词语下,作为寡头体制的最高法院应该审慎地将自己的社会、经济或政治观念施加给整个国家。2.联邦制让州与地方政府有机会做出地方性的政策制定,这一价值要求作为全国性机构的最高法院应审慎地运用模糊的宪法词语,最终把州法与地方法令丢在一边,而推行全国性规则。3.在法官逐步构建先例和其他法律渊源以及宪法习惯表达出的智慧累积,相比于法官个人或九个大法官中的多数人的观念,前者可以更好地指引宪法问题并获得明智的解决。4.即便在危机时期,即便司法机构既无钱袋权,亦无刀剑权,法院作为一个负责执行联邦宪法对民选立法和执法分支的限制的机构,它判决的有效性必须加以保证。参见 [美]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书,第372-373 页。
不难发现,这三项内容都要求法官不应过度把裁判思路引向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在本质上又跟社会重大权利纠纷和政治议题密切相关,因此才有了“宪法回避理论”。这是美国制定法解释的一项“根本原则”。权威的理解是:“当一条制定法可接受的解释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宪法问题时,法院解释制定法应避免这一问题,除非该解释明显违反国会意图。”〔46〕See Trevor W. Morrison, Constitutional Avoidance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106 Columbia Law Review 1189 (2006).由此可见,司法克制回避解决政治议题的立场,不仅体现在美国宪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中,也是基于司法审判传统的自我克制要求,意味着司法克制是一种最小限度的司法权实现方式。
(五)其他涉及司法克制的裁判基准点
除了上述四项与司法克制有关的基础性裁判基准点之外,与之相关的裁判基准点还应遵循以下九项原则。
第一,穷尽权利救济手段原则。约翰·达利认为:“法官不能受理某个案件,除非当事人穷尽了其他救济手段,比如内部行政审查以及在司法系统中向较低层级法院提出申请。这一点或许可以考虑被归入案件不应当被裁决除非它是成熟的这一教义的要素之一。基于其他救济手段的无效性或穷尽其他救济在某个案件中并不能起到任何作用,能动型法官会更愿意降低适用这一规则的标准。”〔47〕John Daley, Defining Judicial Restraint, in Tom Campbell& Jeffrey Goldsworthy, eds., Judicial Power, Democracy and Legal Positivism, Ashgate Publishing, 2000, p. 282.
第二,利益/负担原则。当事人已经根据某项具体的法律而受到法律上利益或受到法律拘束。具体来说,如果当事人已经受益于某项法案的好处,法官就不应当考虑该法案的合宪性。这一教义在澳大利亚法理学中并没有明显对应的部分。司法克制型法官很可能更乐意发现某项法案提供了某种“利益”,同时也更乐意发现当事人的某些行为等同于接受那种利益。〔48〕Ibid, p. 282.
第三,重要性原则。法官并不需要考虑案件对宪法发展的重要性,可以称之为“重要性原则”,即法官不应当考虑没有重大价值的宪法争议。这也是“微量原则”(the doctrine of de minimis)在宪法性法律中的应用。司法能动型法官更乐意寻找某项轻微的宪法性侵权在事实上具有重大的影响。〔49〕Ibid, p. 282.
第四,事实问题原则。裁判时只关注法律层面的争议,尽量回避事实问题的审查,只审查法律问题,拒绝审查已由行政机关或初审法官所决定的事实问题。当然,众所周知,事实/法律这一区分很难精确把握。司法克制型法官更乐意将问题概括为是法律问题而非事实问题,不太愿意放松特定案件中的这一教义。这一教义的适用同样取决于具体的语境。然而,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一般会拒绝批准一些特殊案件中事实问题的提出,法院并不会仅仅由于宪法的适用开启了某个事实问题,就拒绝考量某种宪法性挑战。无论如何,在宪法性案件中,克制型教义倾向于选择一种解释方法,即无论是手头的还是未来的案件,都倾向于审查法律问题而非事实问题。〔50〕Ibid, pp. 282-283.
第五,遵循先例原则。法官应当在原始先例之中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层面上,严格地适用先例。司法克制型法官不乐意基于既有的先例性规则创造新的例外,同时也不倾向于不在原始规则的射程范围内将既有的规则适用到新的情况中。〔51〕Ibid, p. 283.
第六,司法节制原则(judicial parsimony)。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节制,而不应过度介入法律之间的争执。如果某个宪法性争点包含了一个制定法建构问题进而使得该宪法性要点变得失去实际意义,那么法官不应当裁决该宪法性事项。〔52〕Ibid, p. 281.
第七,合宪性推定原则。法官应当假定某项制定法具有宪法效力,除非存在“显明”的论点能够证明相反的情况。对秉持司法克制立场的法官来说,他们更不倾向于寻找某种相反的“显明”论点。
第八,立法动机推定原则。法官应当假定立法和行政动机是正当的,除非存在显明的证据能够证明相反情况的存在。换句话说,法官应当对立法和行政行动做温和解释。
第九,可分离性原则。法官应当界定任何无效的条款都是可以与其所在的制定法相分离的,司法克制型法官更倾向于认为,某个无效的条款对于制定法其余内容的效力而言并不重要。
五、结语
尽管中国与美国在政制框架和司法体制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也造成了司法克制或司法能动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含义,甚至造成误用,但就现代司法的一般规律而言,中国司法仍然分享作为上位概念——司法的一般特征和规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强调中国司法应当遵循现代司法的一般规律,力求实现司法自身依法裁判的职能,正是实现司法终极价值目标——社会正义的必然选择。
现代司法的一般含义决定了司法过程的基本特性,主要包括判断性、中立性、职业性、终局性、程序性。〔53〕张志铭:《司法沉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61-263 页。这五项基本特性决定了现代司法的一般规律:(1)司法以裁决案件争议为己任;(2)司法者应该被动而非消极地行使司法权力;(3)司法者应该独立无偏地行使司法权力;(4)程序司法者应该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行使司法权力;(5)司法活动是一种职业活动;(6)司法对于案件和争议裁决具有终局性。司法活动应当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宗旨,在遵循最低限度共识的基础上彰显司法规律,唯有如此,司法的公正价值才能实现,司法权威也才能最终确立。
可见,司法克制恰是真正贯彻司法含义、彰显司法权威的行动立场。通过对美国法判例中司法克制理论的梳理,可归纳出尊重立法、尊重先例、文本主义、避免实质性政策判决以及尊重行政机构和个人决定等司法裁判方法要点,且可以进一步在裁判中展示出:(1)待决案件具有现实意义,符合“案件”或“争议”要求;(2)原告具备法律或判例所确定的诉讼资格;(3)案件裁判已经成熟,具备可裁判特征;(4)争议内容不涉及政治议题,法官也不会依据自身对政治和政策以及道德的理解做出裁判等。这些裁判基准点不仅是司法克制立场对于案件裁判的判断标准,也是保守主义司法哲学对司法审判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它代表着传统意义上法院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应当持有的基本立场和思路。
在转型中国社会中,司法实践所遭遇的困境与司法的功能定位具有十分紧密的关联。相较于行政权的管理属性,司法权具有独特的判断、裁决属性。〔54〕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载《法学》1998 年第8 期。有必要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廓清司法功能的案件裁决属性而非案件解决属性。尽管一字之差,背后折射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司法理念与功能定位。在我国纷繁而反复司法改革实践中,诸如执行体制改革、法官员额制改革所遭遇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囿于对司法本身的功能定位不清晰、功能实现不完全,进而有损于司法审判职能的充分实现。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强调判例在审判工作中的参考和指导意义,强调严格依法审判对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意义,说明司法克制理论不仅其理论价值逐渐为中国法学界所重视,其方法论意涵因自身的技术性意义而跨越法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建构自主的中国司法审判理论以至司法哲学理论提供参考,从而彰显司法规律,从根本意义上提高司法判决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