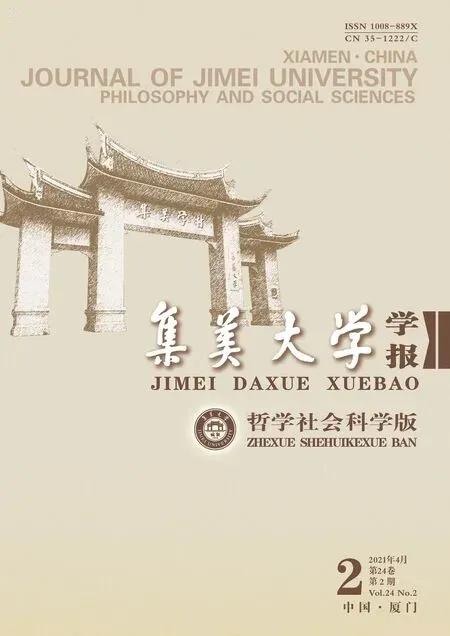历史人物重塑的人文表达
——希拉里·曼特尔《狼厅》叙事研究
王艳萍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一、引 言
2009年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1952—)凭借小说《狼厅》,一举击败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度问鼎布克奖的J.M.库切和前布克奖得主A.S.拜厄特等强劲对手,摘取第41届英国布克奖①布克奖诞生于1968年,距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已成为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文学奖项之一。的桂冠。布克奖评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诺蒂认为《狼厅》篇幅适中、语言“潇洒驰骋”、场景壮阔,是一部“优秀得不可思议” 的作品[1]1。《狼厅》 是“克伦威尔三部曲”的第一部,②“克伦威尔三部曲”的第二部是《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2012),该部小说获得2012年度布克奖,第三部是《镜与光》(The Mirror and The Light)。它以历史人物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视角展开叙事,以亨利八世废黜凯瑟琳、迎娶安妮·博林这一事件为中心,讲述了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宫廷争斗、宗教改革和百姓生活等。
《狼厅》出版后,在国外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写作技巧、语言的现代性及本土化、历史真实与虚构、“道德的模糊”[2]35、政治生活与人物命运等。国内研究则相对处于起步阶段。刘国枝等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并于201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后出现了为数不多的评论文章,有的通过克伦威尔解读英国的民族共同体文化,有的分析小说中的神话色彩,还有的阐释小说所体现的“历史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总体而言,研究角度较为单一,且缺乏应有的深度。
《狼厅》是一部优秀的新历史小说,它与近40年来英国文坛出现的其他新历史小说具有共同特征:“质疑传统历史叙事,解构宏大叙事,建构文本化的历史。”[3]108新历史小说家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种叙事方式而已,“只有通过文本化的形式,我们才能接触历史”[4]67。我们只能循着文本踪迹找到关于历史的叙事而不可能找到“原生态”的历史。既然历史书写具有不可避免的主观建构性,我们难以知道真正的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去探寻与思考它?历史重写有什么用处?能给当代人什么启示?这些小说家们的创作从不同角度回答了以上问题。法雷尔(J.G.Farrell)的《围攻克里希纳普尔》 (The Siege of Krishnapur,1973)具有强烈的“日不落”帝国迷恋情结。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1981)和彼得·凯里(Peter Carey)的《奥斯卡和露辛达》 (Oscar and Lucinda,1988)揭露并反思英帝国殖民统治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伤害与痛苦。库切(J.M.Coetzee)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1983)反思战争的残酷性。
相对于这些小说来说,曼特尔的《狼厅》更注重对复杂人性的剖析和重写历史的现实意义。曼特尔在《狼厅》中按照自己的理解、意愿和目的去重新阐释历史,通过重塑托马斯·克伦威尔肯定了通过自我奋斗、关爱他人建立起稳定自我主体的意义;通过重塑托马斯·莫尔抨击了保守宗教观,暗示宗教信仰的“美美与共”“与时俱进”才是人类和谐相处的一剂良药;通过重塑阿拉贡的凯瑟琳、安妮·博林这两位女性形象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怀。作者以新历史主义的叙事方式让都铎王朝这几个重要人物在自己和读者的心灵中复活,表现出强烈的人文意识。
二、重塑克伦威尔:肯定自我主体的建立
在传统的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中,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一个善于谄媚、人格卑鄙的奸佞小人。如在乔治·卡文迪什(George Cavendish)《已故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生死录》(Thomas Wolsey,Late Cardinal,His Life and Death,1554)中,克伦威尔是个阴险狡诈、虚伪残忍的人物;在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八世》 (Henry VIII)中,他是个举止粗鲁、无关紧要的小配角;在肯尼思· 威廉斯(Kenneth Williams)所著的《坚持啊,亨利》 (Carry On,Henry)中,他是个善弄权术、十恶不赦的阴险小人;在电影《永远走红的人》 (A Man for All Seasons)和《都铎王朝》 (The Tudor)中,他是迫害《乌托邦》 (Utopia)作者托马斯·莫尔的历史罪人。英国诗人斯温伯恩曾说:“他就是个无棱无角,无魂无韵,既无能又无用还很愚蠢的垃圾!”[5]20然而在《狼厅》中,克伦威尔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反面走向正面,从扁平人物转变为圆形人物。小说的叙事以他的视角徐徐展开,读者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窥见了他是如何通过自我奋斗、关爱他人而建立起稳定的自我主体、进而实现自我价值的。
亘古以来,“我是谁?”这一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众说纷纭的话题。海德格尔提出:“这个‘谁’ 是用‘我’ 自己、 用‘主体’、 用‘自我’来回答的。这个谁就是那个在变动不居的行为体验中保持其为同一的东西,就是那个同外界多样性发生关系的东西。”[6]133本研究中“自我主体”取海德格尔的这个解释,相当于“自我”“自我认同”或“自我意识”。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人文主义者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提出了普遍人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人“自我主体”的原发性、自主性和自足性。18世纪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提出,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就是实现人的主体性,即充分发展人性。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它包括人道、爱、公正、正义、尊严、坚持、毅力,等等。《狼厅》中所叙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6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时期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曼特尔重塑的克伦威尔完美地诠释了文艺复兴时期个体生命对自我奋斗、个人尊严及人性之美、生存意义的追求与崇拜。
克伦威尔的前半生一直处于“自我迷失”状态中。他的童年是在孤苦伶仃、穷困悲惨中度过的。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沃尔特是个性情暴戾的铁匠。小说一开始就是小克伦威尔被父亲暴打的场面,“他被打倒在地,头昏眼花,说不出话来,只是直挺挺地趴在院子里的鹅卵石上。他侧转脑袋,眼睛朝大门口望去,仿佛有人会赶来救他。现在只要再结结实实地来一下,就可能要他的小命”[1]3。他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他出生时,他父亲显然已经烂醉如泥;而不难理解的是,他母亲则自顾不暇”[1]23。出生日期是一个人生命的开始,是一个人有了身份及自我的标记。没有这个,这个人会感到不安与无根。
小克伦威尔无法忍受被父亲虐打,于是逃离家庭。他去过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荷兰。他当过雇佣兵、水手、听差、仆人、厨工、小商贩,历经坎坷,艰难度日。他偷过、骗过、乞讨过,他的身份不断转换,自我迷失感愈加严重。他根本没时间考虑自己到底是谁?下一步做什么?他要去哪?会遇到谁?会走向何方?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仿佛风中飘絮、雨中浮萍,任凭命运之手摆弄,就如后来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所说:“你很像一条低地人用绳子套着牵来牵去的方头斗狗。”[1]83
然而,如同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克伦威尔始终没有向困难低头,他一直在不断地同命运抗争,探求自我存在的意义。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以一种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一套特殊的记忆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他快而准地记住商务数据和周边人的细节。他还勤学苦练,把《圣经》都熟记在心,和别人争论时,他能够信手拈来其中的字句。他孜孜不倦地学会了好几种语言。通过不断的努力与进取,他积累了非凡的智慧与才能,“他能起草合同,训练猎鹰,绘制地图,阻止街上的斗殴,布置房屋,摆平陪审团。他会恰到好处地引用传统作家的名言,从柏拉图到普劳图斯①普劳图斯是罗马第一个有完整作品传世的喜剧作家,也是罗马最重要的一位戏剧作家。,然后再倒回来。他懂新诗,还可以用意大利语朗诵”[1]30。他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他总是在工作,起得最早而睡得最晚”[1]30。过人的天赋加上勤劳与毅力使他从社会底层挣扎到顶层,“先后担任财政大臣、掌玺大臣、首席国务大臣,并被封为埃塞克斯伯爵,最终到达权利的巅峰”[7]50。克伦威尔最终赢得了他人的尊重与羡慕,建立起稳定的自我主体,找到了自我认同感。
《狼厅》中克伦威尔让读者看到:人的本质并非与生俱来、永固不变,人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和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的观点十分吻合,“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因此我们称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区别于‘人的实在’之存在的”[8]56。简而言之,存在就是自由。虽然存在的终点是虚无,但是存在本身具有无限的意义。人存在的意义在于他有自由选择与发展的能力,在于他能按自己意愿不断地去设计、谋划未来,进而不断超越自我。
人要发挥主体性,一定离不开社会和他人,一个完整的自我是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中实现的。克伦威尔稳定自我主体的建立不但是通过自我奋斗实现的,而且也是通过关爱呵护他人的过程实现的。在这过程中,他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回到了心灵的本真状态,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克伦威尔深爱妻子丽兹,对她呵护备至,从来没有让她哭过。妻子得黑热病去世,他悲痛地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月。万圣节前夕,他独守空房,毫无睡意,想象着丽兹会回来找他,“她会知道怎样找到我。她会循着香火和烛光,穿过两个世界的间隙来寻找我……”[1]145曼特尔用寥寥数笔就将克伦威尔失去妻子的肝肠欲断、“生死两茫茫”的悲戚之情描写出来。妻子去世后他终生未娶,还继续照顾妻子的妈妈和妹妹一家。
克伦威尔舔犊情深。婚后一年,儿子格利高里呱呱坠地,他抱起小家伙,“亲着他毛茸茸的脑袋,说,我对你一定会和蔼慈爱,绝不会像我父亲对我那样”[1]41。后来又有了两个女儿:安妮和格蕾丝。他经常给她们买礼物、讲故事,陪她们玩耍。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他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然而命运弄人,两个女儿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也相继染病去世,他的悲痛如潮水般袭来,几乎将他吞没。克伦威尔和姐姐感情十分深厚,姐姐去世后,他收养了姐姐的两个儿子理查德和沃尔特。他还收养雷夫和克里斯托弗这两个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像亲生儿子一般关心疼爱他们。
克伦威尔对陌生的穷苦人们也充满了怜惜之情,经常救济他们。“他派人把啤酒和面包送给那些站在他家门外的人,当早上的凉意加重时,还送肉汤”[1]311。他对大街上流浪的人从不傲慢跋扈,总是真诚地和他们问好,“早上好,上帝保佑你们”。[1]312他很关心在他家里做工的仆人,“他一本正经地在本子上记下他们的专长:西蒙,会拌沙拉和敲鼓,马修,会背主祷文。这些小伙子一定能培养成人”[1](321)。他希望这些人在他家里能学会一技之长,将来可以独立谋生。他对老主人红衣主教沃尔西忠心耿耿,在主教落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在国王面前为其美言,他让雷夫长途跋涉去给沃尔西传信,将进展及时准确地告诉他,红衣主教说,“他是我在这场灾难中最真诚、最可信、最可靠的人……是我最亲爱的克伦威尔”[1]211。
克伦威尔对妻儿、亲人、朋友及周围的人都怀有一颗爱心,在关爱呵护他们的过程中,克伦威尔体会到了人性之美及自我价值。根据传统的史料记载,克伦威尔是一个心狠手辣、虚伪残忍的政治家、权谋家。他在红衣主教失势后见风使舵迅速成为亨利最亲近的宠臣。他见亨利迷恋安妮·博林,就安眉折腰事安妮,力促亨利与凯瑟琳离婚。而后当亨利对安妮失去兴趣又爱上简·西摩时,他又立刻出谋划策,与亨利沆瀣一气最终将安妮送上断头台。而曼特尔有意避过克伦威尔身上的阴暗面,尽力去挖掘其人性之美。历史上关于克伦威尔进入宫廷以后的史料很丰富,但其前半生的经历及其家庭生活的资料是十分匮乏的。而这种匮乏恰恰是曼特尔所喜爱的,它给作者提供了发挥想象力的巨大空间,就如她自己所说:“写《狼厅》前,我研读过许多关于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资料,但发现那都不是我想要表达的角色。史学家不可能挖掘证据重现克伦威尔的私人生活和情感,但作为小说家,我却能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9]30
历史上真实的克伦威尔是什么样并不是曼特尔关注的问题,她笔下的克伦威尔通过自我奋斗、关爱他人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自我主体,进而实现生存的意义。这个有血有肉、丰富立体的新克伦威尔形象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及心理需求,会潜移默化地给读者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
三、重塑托马斯·莫尔:批判保守宗教观
曼特尔对托马斯·莫尔的重塑是具有颠覆性的,他笔下的莫尔因其保守宗教观而给读者留下负面印象。长期以来,英国的史料记载、文学传记与影视作品等都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托马斯·莫尔形象:他是阅历丰富、才华横溢的学者和政治家,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创作了名垂青史的《乌托邦》。他的好友伊拉斯莫说他生性愉快,衣食朴素,天生爱好友谊,在宗教方面虔诚而不迷信。
然而曼特尔不轻易相信历史资料的记载,写作之前她花了大量时间作研究,寻找关于场景和事件的描述、人物的背景资料和传记。在接受访谈录时她如是说:
“我把这些材料逐一比对,寻找矛盾和缺失之处。而这些空白 (被抹杀)之处恰恰就是小说家可以淋漓尽致发挥之处。关于历史的任何时期,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发生了什么,对于为什么发生,我们往往草率做出推断……我在思考每个事件的时候,都试图找到矛盾点、对立处及转折点。我试图找到历史的戏剧性结构……”[10]42
基于对历史的批判性思维,对莫尔的综合判断以及个人独特的理解,曼特尔大胆重塑了莫尔的形象,打破了他是一个圣人、一位基督教殉道士的神话。
《狼厅》中的莫尔傲慢残酷,是一个偏执狂热的天主教徒。他的“衣服里面穿着一件马毛短上衣。他用有些神职人员使用的那种小鞭子抽打自己”[1]84。他常常把自己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以极端的方式表达对上帝赎罪的诚意。莫尔对异教徒大肆迫害和屠杀,“无数的男女教徒因为自己的信仰而丧生,男人被砍头,女人被活埋”[1]575。商人翰弗里·蒙茂斯因藏匿《圣经》英译者威廉·廷德尔而被投入伦敦塔监狱。商人约翰·皮蒂特遭监禁,狱中被施以酷刑以致终身残疾。学者小比尔尼被长期监禁,而后被处以火刑,他被烧了很久才烧死,因为“大风不断地把火焰从他身上吹开”[1]468。还有其他殉道者,例如,修士贝菲尔德,约翰·图克斯伯里、托马斯·索梅尔以及数以万计没有留下名字的无辜者。莫尔使用的酷刑可谓五花八门,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砍头、绞刑、活挖器官、火烙、火刑、肢刑①肢刑是一种折骨断筋的刑法,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五马分尸。,等等。他还发明出一种火刑工具,将受刑者投入熊熊大火中每烧一下就提到空中一下,以便让观众看到其痛苦神情,然后再将其放入火海中,如此反反复复,直到十几个小时之后犯人才被折磨致死。
较之传统历史,曼特尔笔下的莫尔更有张力,读者恨之愈深,反思就会愈深。她用这样一个邪恶的莫尔来表达自己对宗教的一些看法。
首先,她认为人应该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自由发展。中世纪以前的人们受基督教“原罪”思想所束缚,受“上帝无时无刻都在审判自己”的思想所折磨。曼特尔从小也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她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受家人影响笃信天主教。但是12岁时她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在回忆录《放弃鬼魂》(Giving Up the Ghost,2003)中,她说天主教给她留下挥之不去的印痕:
陈腔滥调,罪恶感。成长中你一直认为自己是错的,是坏的。而我呢,因为我是个对别人告诉自己的东西都会认真思考的人,于是就养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苛刻的习惯。所有的事情都一团糟。就好像在身体里放置了一个警察,并且还时时改变着法律法规。[11]215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圣经》的解释权归属大主教、主教、神甫等神职人员,普通民众没有自由阐释理解《圣经》的权利。曼特尔在《狼厅》中借用克伦威尔表达了她赞扬路德宗教改革这一立场。克伦威尔认为廷德尔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英语,将《圣经》的解释权回归到普罗大众的手中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当他的爱妻和爱女死去的时候,他诉诸于廷德尔的《圣经》寻求心理慰藉,而不是他妻子深信的天主教。他说:“在英格兰,有八百年的蒙骗,只有六年的真理和光明;是英文福音书开始进入这个国家之后的六年。”[1]443曼特尔通过小说传达出来的宗教反思是:宗教的迷信导致人性的迷失,只有在“上帝”走下神坛时,人性才能觉醒,人的思维创造、批判想象能力才能尽情发挥,才能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其次,曼特尔用莫尔这样一个反面形象抨击了天主教的腐化堕落、虚伪功利。她赞扬克伦威尔对新教徒的宽容态度。小说中的克伦威尔不但不迫害新教徒,而且还尽自己所能保护和帮助他们。沃尔西对异教徒虽不宽容,但也不残酷,“沃尔西会烧书,但不会烧人。”[1]38沃尔西烧书只是做做样子,而莫尔烧人却是灭绝人性的暴行。曼特尔在小说中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斗争来暗示当今世界各宗教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对立。英国的穆斯林移民以及穆斯林恐怖袭击等是当今英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伊斯兰教已成为英国第二大宗教,如何处理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是今日之英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曼特尔曾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生活过四年,对穆斯林文化了解很多。她的小说《加萨街的八个月》就是基于在沙特阿拉伯生活的一手资料而创作的,小说描述了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曼特尔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尊重、和谐相处,不应以宗教信仰为借口挑起民族矛盾和种族仇恨。
再次,曼特尔认为“爱”与“平等”是宗教的核心。当克伦威尔提到用德语翻译的《圣经》时这样说:“如今在懂德文的人中,还有那么多的爱,真是没有想到。”[1]38他认为那些读德语《圣经》的人对上帝有一种很纯洁的爱,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也乐于传播德语《圣经》。小说中,她对廷德尔赞赏有加,“廷德尔说,要保持信心、希望和爱,甚至三者兼有;但三者中最重要的是爱”[1]145。除了“爱”,“平等”也是曼特尔所强调的,“廷德尔说,在上帝的眼中,厨房里洗盘子的孩子与布道坛上的传道士和加利利岸边的使徒一样让人喜爱”。[1]117人与人是平等的,无关种族、地位、出身、职业、信仰及性别,这是曼特尔所要传达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文精神。
历史上的莫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并不是曼特尔所特别关注的,她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小说传递她本人的人文立场。她认为,现代社会人们对宗教不应像莫尔那样受狭隘、保守的思想所限,而应秉持宽容、进步的态度。真正的宗教应该以人为本,以“爱”及“平等”为核心,各种宗教之间不但应该“美美与共”,而且应该“与时俱进”。
四、重塑都铎王朝女性形象:关怀女性命运
曼特尔在小说中重点重塑了两个女性形象,阿拉贡的凯瑟琳①凯瑟琳出身在西班牙王室,16岁时因为政治联盟背井离乡嫁到英国,婚后几个月其丈夫亚瑟就病逝了。然 后,亚瑟的弟弟亨利八世娶她为妻。与安妮·博林②安妮·博林原本是凯瑟琳的侍从女官,在1533年与亨利八世秘密结婚,三个月后亨利八世对她的热情消退。1536年安妮流产一男婴,从此亨利弃之如敝履。1536年5月2日被捕入狱,关进伦敦塔,5月19日以通奸罪被斩首。,即亨利八世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妻子。这两位女性品格、秉性截然不同,但是她们的悲惨结局却是相似的:前者抑郁而终,后者被砍头。通过小说,曼特尔既表达对都铎王朝女性卑下地位、不幸命运的同情,又表达了对女性不屈不挠抗争命运之精神的肯定和赞许。
在历史书籍、小说、戏剧、影视作品中,凯瑟琳是一个经常被边缘化的人物,是男权社会中扮演受害者和服从者的逆来顺受的女性。然而曼特尔用大胆的想象及细腻的笔触成功刻画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
凯瑟琳的丈夫亚瑟病逝后,她的公公亨利七世为了和西班牙王室联手打击法国,软禁了她,不仅不让她回国,还殴打、折磨、虐待她,令她受尽屈辱。但是凯瑟琳从不向命运低头,不绝望、不放弃。她是个立场坚定的女人。虽然她一直尊重丈夫的意见,但是当亨利提出要和她离婚时,她坚决反对,“有生以来第一次,她不想满足他那些需要。一个女人难道必须唯夫命是从吗?”[1]81克伦威尔建议:在等待法官对他们婚姻做出裁决之前,“他们应该分居并让她离开宫廷”[1]81。凯瑟琳坚决不同意,“她可以微笑,但是却寸步不让”[1]444。克伦威尔威胁她,告诉她法官们认为她在嫁给亨利八世时已不是处女,所以这个婚姻无效。这个时候,凯瑟琳义正言辞地说:
“你的红衣主教也会问同样的问题。仿佛我在这儿是外人。我要告诉你,就像我告诉过他一样,我第一次被称为威尔士王妃是在我三岁的时候。十六岁那年,我来到这儿嫁给了我的丈夫亚瑟。他去世时,我十七岁,还是处女之身……但是,我对红衣主教讲过的话不会对你全部重复一遍。我想,关于这些事情,他肯定给你留有记录。”[1]278
凯瑟琳的言说有理、有力、有节,敢于挑战国王和权威的勇气实在令人赞叹。已有的史料记载和文学作品中,凯瑟琳从未像在这部小说中这般坚强。她虽然生活在都铎时期,但是却具备现代新女性的风骨与气节,她在命运面前不低头,在强权面前不懦弱,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同时,她也是一个心地善良、对爱情忠心耿耿的女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命运也不垂青于她。她被逼迫与亨利离婚后,被逐出皇宫,后半生贫困潦倒,直至抑郁而死。
安妮·博林是作者浓墨重彩所刻画的另一个重要女性人物。她是这本小说中作者按照自己的理解而诠释的、与历史出入非常大的人物。大卫·休谟在他的《英格兰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1688)一书中,对安妮的命运表示同情,并赞美其纯洁与天真。他描述,在其加冕大礼上,英格兰人民为拥有这样一位优雅美丽的皇后而欢呼雀跃。
《狼厅》中的安妮与大卫·休谟的安妮有天壤之别。她性情冷酷,举止轻浮,“她的眼里满是邪邪的笑意”[1]286。她视权如命,为了当上王后不惜冒任何风险,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她坦言:“有预言说,有位英国王后会被烧死。但预言吓不倒我,就算是真的,我也甘愿冒险。”[1]236她对阻碍其前进的人恨之入骨。红衣主教反对亨利和凯瑟琳离婚,安妮“恨不得把红衣主教的内脏装在盘子上喂她的猎犬,并把他的四肢钉在约克的城门上”[1]234。手足情及爱情对她来说一钱不值。她的姐姐玛丽在她之前就是亨利的情妇,并为亨利生了一个儿子。安妮担心亨利会对玛丽旧情复燃,不择手段地把她赶出宫去,她对克伦威尔说:“我已经厌烦玛丽了,我想甩掉她。她该嫁人了,免得碍我的事儿。我永远不想见到她……我早就想把她嫁给哪个无名小卒。”[1]420当她迷惑住亨利以后,立刻将未婚夫哈利·珀西弃之一边,丝毫不顾及对方的感受。
安妮看待一个人的标准别无其他,就是看对方是否有利用价值。当克伦威尔还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时,“她的目光总是越过他,落在某个更吸引她的人身上。那双黑眼睛微微凸起,像算盘珠子一样闪闪发亮”[1]160。然而,当克伦威尔位高权重的时候,只要其一进入她的视线,“她的长脖子就会向前一伸;她上下打量着他,考虑着可以怎样利用他,而那双发亮的黑眼珠也滴溜溜地转动着”[1]160。她工于心计,做任何事之前都处心积虑、步步为营。她挑动起亨利的情欲,但却不立即和他发生肉体关系。“她像士兵一样使用自己的身体,保存着她的资源;像帕多瓦的解剖学校的老师一样,她把身体逐一分解,为各部分进行命名,这是我的大腿,这是我的胸脯,这是我的舌头……”[1]384侯爵的头衔只是让亨利“买到了摸她大腿内侧的权利”[1]384。曼特尔对安妮的描述真可谓幽默风趣,极尽揶揄讽刺之意味。《狼厅》彻底改变了评论家内尔明对安妮的印象,她说:“我对安妮·博林的感情一直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从没有想象到,读完这本小说后我会那么厌恶她。”[12]98可见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刻画是非常成功的。
历史上真实的安妮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晓。作者在小说中借主人公克伦威尔之口传达出她自己的历史观,“在每一段历史下面,都有另一段历史”。[1]64也许这部小说中的安妮更真实,因为休谟的书写于1754年,那个时候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虽然去世了,但其影响还在,所以休谟有美化安妮之嫌。曼特尔之所以这样塑造安妮是有其良苦用心的。虽然她笔下的安妮自私贪婪、残酷无情、道德卑下,但是读者读起来依然会唏嘘感叹。她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优雅美丽、风情万种,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好几国语言。可是不幸的是她成了其父亲、舅舅升官加爵的政治筹码,是他们将她送进王宫,利用她的美色去勾引国王,而国王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可以生产子嗣的工具,目的落空后就除之而后快。她像一只飞蛾不顾疼痛与灼烧奔向看似绚烂的火焰,殊不知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即使一个女人多么智慧超人、手腕高超,也难逃宿命之劫。
作者借助凯瑟琳与安妮这两个女性形象的重塑表达了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怀。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从正反两方面暗示了在男权社会中,女人完全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无论忠贞不渝还是深藏城府都以悲情结局。
五、结 语
曼特尔大胆颠覆了传统历史叙事中都铎王朝的几个重要历史人物形象,按照自己的理解、意愿和目的重新阐释历史。通过重塑这些人物,曼特尔从三个不同方面表达了自己的人文思想与关怀:克伦威通过自我奋斗、关爱他人建立起稳定的自我主体,体现了人性之美与生命意义;莫尔所代表的保守宗教观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宗教信仰的“美美与共”“与时俱进”才是人类和谐相处的一剂良药;凯瑟琳与安妮·博林表现了身处男权社会的女性与不幸命运抗争的精神。这些历史人物会引发当代读者对自我价值、宗教信仰及女性地位与命运等问题的思考。克罗齐说:“只有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故而,过去的事情一旦和对现在生活的兴趣相结合,它的关注点就不再是过去,而是现在了。”[13]120在曼特尔的眼中,历史就如一根脐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通过重温已然消逝的“过去时”的历史与历史人物,她为处在“进行时”的当代人提供反思空间,以便能更好地书写当代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