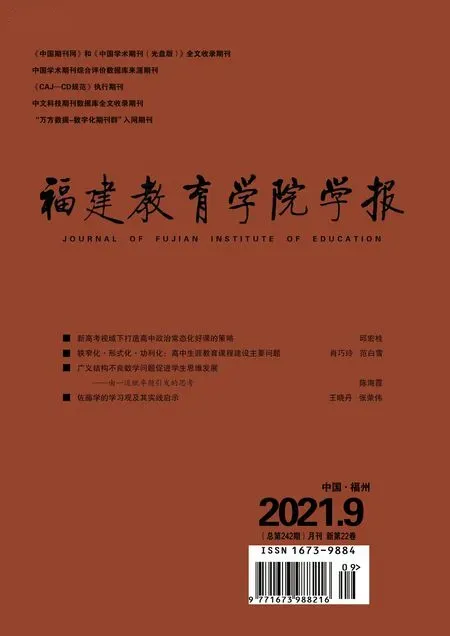佐藤学的学习观及其实践启示
王晓丹 张荣伟
(1.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泉州 362000;2.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福建 福州 350007)
杜威曾认为学习是一个从已知到未知的过程,佐藤学深受启发,进而将学习视为一段从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的旅程。基于苏格拉底的对话思想,佐藤学将学习重新定义为与客观世界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的交往实践,换言之,即创造世界(认知和文化实践)、建立伙伴关系(社会和政治实践)、寻找与发现自我(伦理和存在的实践)。[1]就其本质而言,学习不仅仅是个体自主发生的活动,也是与外界的人、事、物的沟通与交流,我们每天与新的知识相遇,与新的思想碰撞,在此基础上更新自己的认知,进而升华自己的思想。可见,佐藤学对“学习”的定义已不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而是上升到了个体生命活动的层面。
一、学习的三种“异化”现象
学校中制度化的学习文化所呈现出的是个体的、孤立的、竞争性的学习。佐藤学认为现实中的学习存在三种“异化”。第一种是学习对象的异化。所谓的学习对象的“异化”指的是对于教材或者文本资料的疏离,此处的对象指的是文本、教材。例如学习者对于文本进行五分钟阅读与讨论这种情形,就是佐藤学所指出的对象的“异化”,因为它剥夺了“学习”的“探究”性质。第二种是“他者”的异化,这里指的是学习者以个体的形式自我学习。例如课堂上教师经常表达的“请同学们独自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之类的情形,这对于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学生而言,即使多思考几分钟也仍然不理解。在佐藤学看来,一个人的学习是无法成立的。第三种是“意义”的异化,这是一种学习者处于不知道自己在学习什么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的学习处于顺应环境的学习,仅停留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学习”阶段,由于环境的刺激产生了反射的被动的学习状态。学习的这三种“异化”剥夺了学习的“目的性与活动性”“共同体社会性”和“知性与伦理性”。[2]佐藤学曾说:“古今中西,学习就是一种旅程。”这种隐喻是很贴切的,旅程中除了有与风景(客观世界)的相遇与对话,与旅人的相遇与对话,还有与自我的相遇与对话。因此,与对象世界的对话、与他者的对话、与自我的对话,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是“学习”,即基于对话性实践的学习——学习应该是活动的、合作的、反思的实践。由此可见,佐藤学对于学习的理解,主要是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阐释学习者的内部活动世界。
二、学习的“修养”与“对话”传统
佐藤学在追寻学习的思想源头时指出,学习应当被传承的两大传统是“作为修养的学习”与“作为对话的学习”,即“作为修养的学习”是研究学习的本体论,而“作为对话的学习”是关于学习关系的探讨,这两种传统的连结为复兴学习的渠道做了准备。
这里的“作为修养的学习”是指基于文化和素养来恢复自我的整体性,使自己更好地完善自我的学习传统。这里的学习以“悟性”和“救赎”为主题,是存在某种缺陷的人通过修行以达到更完美的存在的一种谋生。[2]“作为修养的学习”源于12 世纪法国圣·维克多修道院休(Hugh)的《学习论》,他的这本书所表达的思想是:人通过学习,把不完善的自己向完善的自己逼近,从而引导人的内心世界走向完美修养。休认为学习是一种体悟,是认识自然和自我的本性,是认识自然的秩序,是一种“修行”与“矫治”的学习,其最终目的在于完善自己的内部世界。[2]《学习论》中的“学习”被形容为“远游异乡”“异乡人的学习之旅”“孤独之旅”等,他认为“学习”是自我的内部世界之旅,是自我智慧的默默吟味,是同自己内心世界的持续不断的对话。[2]将学习比喻为“旅行”意味深长。旅行本质上就是一个表示“向外”的词语,有远行之意,作为目的地的“异乡”本应就是自己的“外部世界”,而这里却意指为自我的内部世界,换言之,“作为修养的学习”并不是简单的通过接触外部世界向我们展现知识的创造,而是一种从“外”到“内”的旅程,只有通过内化才能将自我所欠缺的部分完善,所以它的本质是“潜入”自身世界。[3]
另外,“作为对话的学习”是对他人(对象)开放的学习,这是通过与他人交流的行为来寻找对象的意义的行为——通过与对象、他者和自己的对话沟通来学习。这里的对话学习并不是将学到的知识视为自己所独有的东西,而是将知识公开、分享,与他人共享知识。学习被视为通过沟通对话参与文化公共圈的谋生。[2]“作为对话的学习”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对话理论,主要体现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苏格拉底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引导贵族青年美诺,围绕“德是否可教”这一话题来对其展开道德教育。此外,现代学习论中将学习界定为基于沟通对话的社会过程的主要代表是杜威和维果茨基。杜威的“问题解决思维(反省性思维)”就是基于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他认为学习的经验不仅是个人活动的过程,同时是社会活动的过程。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也以“对话学习”为基础而展开。所谓“最近发展区”,就是指学生独自学习就可以达到的水平与通过教师、同伴等人的援助能够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区域。维果茨基认为儿童与教师的沟通十分重要,儿童发展的可能性就在于“最近发展区”。正如佐藤学所言,学生现有的发展水平对其学习发展只具有回顾性,“最近发展区”可以预测学生的学习发展。“学习首先是一种发生在主体之间的社会性的活动,然后才是一种发生于主体内部的思维活动,学习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他人思想和自我见解之间的对话,它首先是一个社会过程,然后才是一个心理过程。”[4]
《学习论》中关于“修炼的学习”的阐释,强调的是学习中自我内部的完善对于个人学习、成长的重要性。佐藤学也将重视经验的杜威的“反省性思维”与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作为依据,强调与他人“对话”在学习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他其实是尝试着将近代以前的主流模式“作为修养的学习”向更深层次的“作为对话的学习”的模式打开,让“对话”置于教育的核心。正如他所提到的,学习是与自我的对话、与他人的对话、与客观世界的对话。
三、“三位一体”学习论的内涵
真正的学习并非个人的孤立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性的交往活动。学习就是构筑世界、构筑伙伴和构筑自身的实践,是一种意义的编织过程。[2]佐藤学受杜威和维果茨基学习理论的启示,将学习重新界定为(世界、伙伴、自身)“三位一体”的实践关系,并特别重视主动对话的交往功能。
(一)与客观世界的相遇与对话——展开活动性学习
日语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语“勉强”,用以揭示学习的特殊涵义,然而“勉强”一词在中文中的释义有:(1)使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并非心甘情愿地做事;(2)将就或凑合;(3)能力不够还尽力去做。为何汉语的“勉强”一词会成为日语中的“学习”?是因为在一个寻求知识的社会中,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走向美好未来,所以即使学生对于这种制度有所厌恶,也只能唯命是从。这里也体现了追求大量知识的古老学习观。[5]学生所追求的学习,应该是愉快的、享受的学习,而不是不情愿的学习。学习不应被理解为对知识的大量累积,而应以是否获得了自我学习和自我思考的能力来衡量。佐藤学正是主张将强迫学习转变为真正的学习,认为学习是与教材的相遇与对话,是一种活动性的过程。学习者在进入特定的目标世界,接触教材和文本的同时探索并理解世界的各种意义和价值。[6]他特别强调学习是蕴含于作为对象的知识(教材和文本)中的活动,并以心理学家列昂捷夫(Alexei Nikolaevich Leontiev)的观点作为理论支撑:活动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对象性,也就是说对象的概念隐含在活动的概念中,无对象的活动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还是学生课后的背诵复习,从真正意义上讲都只是对信息的接收。这种“信息接收式”的学习是单向且单一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在佐藤学看来,学习应该是一种与人、物、工具及素材接触而进行的“媒介化的活动”[7]。活动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媒介,学生通过教材认识世界,活动性学习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观察、实验、讨论、交流对话等各种活动,才能产生更深层次的学习。
(二)与教师、同学的相遇与对话——发展协同性学习
学习是建构伙伴关系的“社会性实践”。学生最主要的学习伙伴是同学和教师。学生通过与伙伴的对话交流,与多元思想的碰撞,才能构建自己的思想,从这个层面上看,学习是一种协作性的活动。柏拉图认为人类之间的思想交流能更接近真理并创造出更多的新知。[8]亚里士多德的整体论思想道出了协同合作的强大力量。协同合作也是杜威的民主教育观念的核心。[9]需要指出的是,“协同学习”追求的是在相互协作的情况下追求差异性的存在,即产生“多种多样的人共生”的积极态度,这样也能减少学生之间的刻板印象、偏见、歧视和欺凌等问题。佐藤学对学习的重新定义就是基于维果茨基的学习观:所有学习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交活动,包括与他人的关系。因此,学习是通过与社会或共同体中其他人的交流而发生的。“协同学习”需要建立一种“相互倾听的关系”,而发展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协同学习,有利于维持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只有教室里呈现融洽的学习氛围,学生不再孤军奋战,而是拥有共同理想的“战友”,在“相互依赖”中讨论、分享,学习才能成为一种友好的社会性实践。
(三)与自己的相遇与对话——促进反思性学习
学习是探索自身模式的“伦理性实践”。正如佐藤学所言:只有与多样的思想的碰撞,实现与客体的相遇与对话,才能产生并雕琢自己的思想。[10]将自己原有的思想进行沉淀、雕琢,这是一个反思的过程。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同理,未经反思的学习,不是真正的学习。佐藤学认为,学习是一种自我发现、自我内省的活动,通过自我反思来内化、重构自己原有的知识,形成内心世界的思考、情感和意志。学习的最佳境界便是自我反思,反思性学习是经过回顾、检验、总结后对自己所习得知识的验证的往复过程,也是知识内化后的自我审视过程。在自我反思中与新的自己相遇,与新的知识相遇,形成自我教育的“伦理性实践”。
学校应该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而非将知识填满每个学生的大脑。佐藤学的“三位一体论”,体现了学习的三个层面,即独立学习、相互学习和深度学习,是一种层层递进的过程,而从独立学习走向深度学习也体现了学习的质的变化。
四、佐藤学学习观的实践启示
在这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仅仅靠知识的往复记忆、机械式的技能训练已无法应对世界的变化。今日,教室中因学习方式不当而产生的问题日益显现,而佐藤学指出的日本教室中存在的问题,也正是当下我国教育所面临的困惑:整齐划一的课堂教学方式只为追求教学效率,导致学生的学习沦为孤立的、排他的消极状态。佐藤学将“学习”视为交往性的实践活动,强调了学习的生命意义。学生的学习应从“自我完善”的个人学习中突破,走向活动性、协同性和反思性的学习。
(一)重建学习方式
在课堂教学中,如果省略了具体操作的活动及活动对象的话,构成对象世界的有意义的学习必然会被简化为基于预定知识的获取的学习,也就无法出现杜威学习理论中所强调的工具性思维和问题解决思维。[11]这也正是佐藤学所谓的剥夺了“探究”性质的学习。学生的学习不应只停留于对知识的简单记忆和片面理解,而应探索知识的本质意义和生命价值。佐藤学认为应追求“知识的意义功能”的学习,即基于知识活用的思考与探索的学习。教师要适当引导学生去探索与发现,使学生养成探究和怀疑精神。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曾说:“正是怀疑和问题鼓励我们去学习、去观察、去实践、去发展知识。”学习应该具有目的性和活动性,学生除了要养成思考“为什么”“怎么得出这个结果”的习惯外,更要学会运用所学知识,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且从中验证自己的疑问。日语中表达学习之意的有“勉強”和“学び”两个词,而在佐藤学看来,“勉強”的学习不是真正的学习,“学び”才能呈现学习的真正意义。“学び”是作为与人和事物相遇并且对话的经验,与“勉強”的区别在于过程中是否存在“对话”。在佐藤学的学习观中,格外强调对话性的协同学习,他认为只有在得到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学生才可以发挥自己的潜力而到达一个更高的认知水平;在协同学习的过程中,“讨论”不是必需的,而“学习”则是必需的。协同学习与以往我们耳熟能详的合作学习不同,它不是一种相互“说”的学习方式,而是一种相互“学”的方式,如果只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而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那么学生同样无法得到成长。[12]合作学习是大家进行分工合作,得出1+1=2 的结果,而佐藤学主张的协同学习,是学生之间的不同观点、想法的相互碰撞,是异质性的相互交流,它得出的是1+1>2 的结果。学生的学习要真正成立,除了追求协同学习,还要重视基于学科本质的挑战性学习。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除了要掌握那些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共有课题外,还要追求那些基于理解的富有挑战性的“跳跃的学习”。目前,学习的过程往往在一个方向上被认识,即“理解→应用”,但“应用→理解”的过程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教学关系而言,那些在小学阶段总处于“只等待教师和同伴帮助”的学生,到了初中和高中阶段后,便会不可避免地怨恨自己从前的“等待”状态。真正的学习是探究性的学习,学会思考并探讨不懂的问题。此外,协同学习成立的前提在于“相互倾听”关系的建立。杜威也主张“倾听”的优先性,他在其作品《公众和公众的问题》中表达了听觉的重要性,认为观看是一种旁观者的行为,而倾听才是参与者的行为。相互倾听的关系使对话性的沟通得以生成,而对话性的沟通为学习作好了准备。孤立的学习无法走向真正的学习,学生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使自己的学习潜力得以发挥,走向卓越的学习。
(二)重建课堂文化
根据独白的语言来组织教学是当前课堂教学中的一种常态,正如我们日常所见的景象:各种讨论拘泥于传统的“提问—回答—评估”的标准语言操作,由知道正确答案的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回答问题,然后教师对答案进行评估。这种常态剥夺了学生与教师对话交流的权利。由于传统教学根深蒂固,学校教育并不鼓励学生的自我认识与个性化表达。实际上,这些问题正是“同步教学”所映射的典型特征。教师总是预先单方面地给学生传递规定的知识和技能,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地学习。课堂中,教师占据中心者的位置,不断地讲解着早已为学生设定的需要习得的知识点,学生只能集中精力听课并埋头记笔记。夸美纽斯曾主张以印刷厂为模型对学校进行改革,他认为学校教育来自教师的声音(墨水),就如同印刷版式的发明能够一次将大量印刷品准确地转移到纸上,也能将知识(印刷)一次性地刻在学生的精神(纸)上。[11]在佐藤学看来,仅仅是信息的简单接收这种方式难以构成真正的学习。佐藤学强调,要尊重学生的想象和语言并将其对象化,从而反思性地进行自我关系对话。[11]课堂本是学生的主场,学生应在课堂中发声,将各自的观点表达出来。教师和学生要勇于打破常规课堂,进行探究性、协同性、反思性学习。佐藤学总结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三大策略:“倾听”“串联”“反刍”。在课堂教学中,不仅应重视学生之间的“相互倾听”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倾听也十分必要。倘若教师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把课堂知识像洪水一般倾泻而下,相信没有学生能够招架住。教师对学生的“倾听”行为,体现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表达了对学生的尊重,并且教师只有在认真倾听学生声音的情况下,才能根据学生的学情进行教学。教师必须认清一点,教学不单纯为了传授知识,还要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教师在课堂中应将学生的各种思路、观点联结起来,进行串联,才能帮助学生将思路理清,以媒介者的角色促进学生倾听其他同伴的声音,进行异质性交流。[13]“反刍”策略在教学中是比较容易受忽视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适时地停下步伐,对课堂前一阶段的活动进行“反刍”,这有助于“挑战性学习”的进行,而只有基于对前一时段的内容进行“反刍”,重新出发,或者在小组活动中进行“反刍”,才能让学生进行切磋、交流异质的观点,从而促进“挑战性学习”。[13]
(三)走向真正性学习
虚假的、表面的学习只能停留在对知识的机械记忆和浅层理解的层面,而走向探究性、协同性、反思性的学习,则能使学生在知识、人际关系的获取中重构自我并走向真正的有深度的学习(authentic learning)。佐藤学特别强调真正性学习(本质性学习)这一概念,常在批判“学校性知识”(school knowledge)的文脉中使用,而“真正性”一词的哲学起源与卢梭的“对内的声音(内心的声音)”有直接关系。如果回溯“真正性”的词源的话,会发现它与“作者性(authorship)”一样,都由拉丁语的“作者(autor)”一词派生而来。因此,在追求教科书中知识的“真正性”的同时,还应该追求学习者学习的“真正性”及“作者性”。学生作为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以读者的身份去学习、理解文本中的知识,更要尝试以作者的身份去理解、思考、探究文本中的知识,这就是佐藤学的学习“三位一体论”中强调的“与自我的对话”。“三位一体论”中所主张的学习的三个维度强调,作者通过对教材的探索,在与伙伴一起探究与合作的基础上,反思并重构自身。学习的目的在于构建知识和周围事物的意义世界,“我们自己是探寻者、意义的构建者,是与我们周围的人们一起参与建构和重建现实的人”。[14]同时,与伙伴的探究合作可培养学生的人际交流能力,增强学生个人的自信心,使其乐于学习进而善于学习,形成一个积极循环的交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