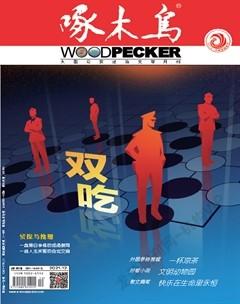寻找马小丽(短篇小说)
蒋军辉

一
这年月居然还有人写信!没错啊,浙江省上虞市两湖镇光明村2弄123号,地址没错,是这儿。马小丽,马小丽是谁?这儿是我家,我家没有叫马小丽的,我叫王大力,这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大名,他希望我长大了有力气,会挑粪,种地是把好手;尽管我现在长得像条蚯蚓,又黑又细,可我还是叫王大力。我老婆叫李翠花,她拖着两条鼻涕、穿着开裆裤到处跑的时候,我就一直叫她李翠花。小时候她追着我跑,长大了我追着她跑,她跑到上海我追到上海,她跑回上虞我追回上虞,就把她追到同一张床上去了。她到现在还骂我,死鬼,要不是你像蚂蝗一样叮着我,我早就做董事长夫人了,你可把我这辈子害惨了。我抿着老酒嘿嘿地坏笑,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就是打败了一个叫马蔚华的男人,娶到了李翠花。马蔚华现在是我们这块地方最大的老板,华强集团董事长,当然,他和我抢李翠花时还在大桥边的路口摆摊儿卖汽水,五分钱一瓶。
想起来还真玄乎,要不是我打败了马蔚华,现在哪来我家那小子。我家那小子,他叫王非。不是那個王菲,他不会唱歌,他是个警察。以前专门潜伏在步行街抓小偷,抓了二十多个,离他自己制定的一百个的目标有很大距离,后来小偷成了稀罕物,他就去当片儿警。他刚毕业干的是刑警,因一桩大案没破,不好意思在刑警队待下去,就去当了片儿警。你看,我家没有一个叫马小丽的。我家的房子倒是出租过,西边底层,三百一个月,来来走走的,租过的人倒有十几个。一个礼拜前刚被我轰走过一对夫妻,男的是个酒鬼,喝多了打老婆,把老婆打得鬼哭狼嚎的,搞得鸡犬不宁,邻居们抗议了,只好赶走。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女的是干那个的,在通江路的洗头房。难怪天天打架。想想,哎,想不起来了,好像也没有叫马小丽的租客啊。
这信,看来邮递员投错了。
那个麻秆似的邮递员又来了,你看他又粘在马丽华家门口走不了身了。我估计他是看上马丽华了。人家可是有老公的。每次骑进这个弄堂,麻秆就拼命按他那辆破电瓶车的喇叭,好像有许多人挡住他的去路似的,其实路上什么也没有。马丽华听到喇叭声就走出门口,问麻秆,麻秆,有没有我家死鬼的邮包?现如今谁还寄邮包?都是快递。麻秆一踮脚,刹车,说,没有,我留心着哩。然后两人嘀嘀咕咕,嘻嘻哈哈,打情骂俏。马丽华的老公在上海做包工头,常年不回家,据说在外面有女人,得过性病,马丽华不让他贴身。我从来没见过她老公给她寄过邮包,但这不妨碍她每天打听一下,反正她也是闲着。
麻秆,这信投错了。我说。
知道了。麻秆不耐烦地说。他踮了一下脚,回头不舍得地望了一眼马丽华,骑了过来。马丽华闪身进屋去了。
浙江省上虞市两湖镇光明村2弄123号,没错啊,就这地址,你这儿不是浙江省上虞市两湖镇光明村2弄123号吗?
是啊。没这个人。
这我不管。他显然对我很生气,也许我打搅了他的好事。他一踮脚,骑走了。
你不管我也不管,我把信随地一扔。照理说这信查无此人,他应该退回去,他居然不管。
进了屋,我改主意了。我想看看这封信里写了些什么。我知道这不道德,可找不到主的信,扔了也就扔了,看看又有什么关系?我这人好打听,好琢磨别人的事儿,这也是做人的乐趣,别人的生活是部电视连续剧,偷窥这部电视剧比看真正的电视剧有趣多了。我喜欢看这样的电视连续剧,它是人生的另一面,沉在生活的水底。
撕了,看吧。
娘:
我叫李小够,听我娘说,你是我亲娘。我娘说,你生我的时候只有十六岁,你不晓得肚子里怎么会掉下块肉来,就把我生下来了。我是我娘接生的,那天我娘在捡垃圾,碰到了你在地上滚,就把我给接下来了,你就把我送给了我娘。娘,我今年十五岁了,日子过得很幸福,你不用担心。我娘去年死掉了,不知生的是什么病,在床上躺了一年,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去医院,就不知道是什么病。我爹在我娘死后,就去外面捡垃圾了,他是沿着铁路走的,一直往前走,越走越远,不知现在走到哪里了,还认不认得回家的路。娘,我现在一个人过日子,没人管,很幸福。娘,六年前的时候,你给我娘牵(寄)过最后一次钱,还写过一封信,我娘不认得字,是我给她念的。我读书读到初一,成绩不好,同学们看不起我,欺负我,他们把厕所里的粪用棍子挑来,擦在我的衣服上,说我比粪缸还臭,老师不让我进教室,说我一年不洗澡,把教室重(熏)得臭气重(熏)天,我就不读书了。娘,你牵(寄)来的信,我藏得很好,没有事的时候就拿出来读一读,就像见到了娘。娘,这些年,你给我牵(寄)过不少钱,却只给我写过一封信。可惜,家里屋漏,老天又经常下雨,我的床淋湿了,枕头下的信也潮掉了,许多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我是辨认了很久,才认出了你的地址。娘,我写信,就是想告诉你我过得很幸福,你不要挂念。
李小够
字歪歪扭扭的,整个信面像铺了一地的乱树杈,信纸右上角还有一摊可疑的颜色。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姓名。看邮戳,模模糊糊的,好像来自河南。
我把信给李翠花看。李翠花五十岁都不到,就已经又老又丑又唠叨了,整天嗡嗡嗡地唠叨个不停。更要命的是,她现在把住了家里的钱,搞得我袋子里一分钱都没有。早知道会是这个下场,当初我把她让给马蔚华算了。唉,现在便宜了那家伙。
一封寄错了的信。我把信递给她。
马小丽是谁?你相好吧。她接了信,看了看。她读过五年小学,认得一箩筐的字,尽管不常用,但模样还大致认得出。
一个杂种,搞不定是个骗子,故意把信寄错,类似的事以前有过,是部连续剧,这是第一集。她把信扔给了我,说完,看电视去了。她现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待在电视机前,家里脏乱得像猪圈,王非都不好意思把女朋友领进门。
他又没提钱。
以后会提的,你没见他把自己说得很可怜吗?
你认为还有下一封信?
对,下一封就提钱啦。她洞察秋毫地说,谁不知道你钱多人傻好骗,赔两万块,让你出名啦?
人家可是河南人,你看邮戳,这两个字,像河南吧?
河南人就不能来上虞打过工?搞不好以前就是和你同一个厂的,知你的底。现在的骗子,什么花样没有?她盯着电视说。
我不想和她纠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把生活当电视剧了。儿子回来了,我把信给儿子看。
你妈说他可能是个骗子。
也有可能。儿子说,现在骗子的骗术五花八门。他掏出手机,打开一个短信给我看:请把钱打入农行账号19-515900460043675。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他说,这样的短信我收到过好几次了,骗子是在撞大运,或许正好有人要把钱给对方,让对方告知银行账号,一粗心,没看手机号码,就照着账号把钱打进去了,这样的事,一百个人里碰不到,一千个人里碰不到,一万个、十万个里就不一定了,撞上了就是大买卖。
马小丽?好像是河南的邮戳。王非看着信封发呆。
怎么啦?我问。
还记得六年前的那个凶杀案么,死者名字也叫马小丽,不过字不是这几个字,那个女人名叫麻晓莉。王非沮丧地说。
我知道这件事是他的心病,他就是因为这个案子破不了,才离开了刑警队。每年的8月25日,那个女子遇害的那一天,王非都会去龙山上的案发地点,在那里放上一束鲜花,鞠一个躬。他一直没从那个案子里走出来。
这六年来,他一直都惦记着这个案子,独自偷偷在查。她死得太惨了,他说,把罪犯绳之以法是我的职责,是不?可惜我没有能力尽自己的职责。这六年来,只要有这个案子线索的蛛丝马迹,他就会死抓不放,到处去查,整宿不睡觉,胡子拉碴的。那些案卷,他翻了一遍又一遍。一有空,他就和同事谈那个案子,以至于后来,同事们见了他就躲。
他以前谈过一个女朋友,挺好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受不了他神神道道地谈那个案子,和他分手了。半夜三更地跟我谈案子,都是血腥的场面,把我吓得整晚做噩梦。她说。
后来他就一直没找女朋友,一副不破案子不结婚的架势。把我和李翠花急的,唉。
不会是同一个人吧。我说。
可能性不大,这不是传奇故事。看看有没有来第二封信吧。王非用手抹一把脸说。这年月,看什么人都像是骗子,一切皆有可能。
我拍拍他的肩。
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我不认为写信的人是骗子,这附近一带的人家都把房子租出去了,这几年来来往往多少房客啊,没准这信就是写给某个房客的。不过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是另外的事。每个人的生活都像一条向前流动的河,别人只看到河的上面,还有许多事沉在河的下面,就像王非,谁都认为他是个快乐的警察,可谁会知道,他内心被一个破不了的案子谴责。同样的,这封信揭示了一条女人河的下面的某个部分——假如这个女人真的存在。透过这个部分,可以使人产生丰富的遐想。我想到了我自己,我也有许多被河水覆盖的生活,这些生活,连李翠花都看不到,它只属于我自己。十年前,我曾作为一家建筑公司的施工员,在上海工作过一年,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叫王丽萍的女人,她是负责开吊车的,我们混得很熟,都记挂上对方了,周围的人看出了我们的苗头,常常拿我们开玩笑,但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懂得克制。后来工程结束,工程队散伙,她回她的老家。
我们怕再也见不着了。她站在新楼的楼梯口说。
還有下一个工程呢,继续干吧。我说。
不了,我得回去了。她说。
我请你吃顿饭吧。我说。我没有追问她为什么非得回家,她总有她的理由。
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度过了一个夜晚,在分开前、相识以来唯一一个夜晚。她没有给我留电话号码,也没有要我的电话号码。显然,她不想我去打扰她的生活,也不想来打扰我的生活。
我没有上环,现在是排卵期。从旅馆出来,她发了一会儿呆,说,不过,我能处理好。
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让我牵挂了十年,它具有丰富的可能性,会把王丽萍的生活引向不同的道路。她自愿隔断了和我的生活联系,行走在我完全看不到的另一条生活道路上,所以我也看不到自己被王丽萍带走的那部分生活——也许有,但愿没有。
二
第二集到了。李翠花把一封信扔给了我,说。是李小够的信。李翠花已经看过了。我抽出了信。
娘:
上次给你写的信,不知你有没有收到,你放心,我不会来找你的,我长大了,懂事了,知道娘不方便见我,娘现在有一个家,有弟弟妹妹。娘,我现在出来了,在一家耐火材料厂做事,在粉碎车间拉奋(畚)斗车。这个车间,是要把做耐火砖的石头啊、煤查(渣)啊等等东西扎(轧)成粉末。车间里灰尘像烟一样浓,一米外看不清别人的脸,只要在里面待半分钟,人的头发胡子眉毛就全白了。我做事时都戴三层口罩,可下班的时候,鼻孔里还是一团一团的白泥。听老牛说,干我们这活儿的,要多喝红糖水,红糖会把身体内的脏东西洗掉。老牛回家天天喝红糖水。我没有钱买红糖。我力气小,拉车慢,装得也浅,要不是这活儿没人干,老板就不要我了。老板每个月给我开一千块工资,实际只给了我四百块,还有六百块,老板说,他先替我攒着,将来我娶媳妇时可以花。娘,我没钱买红糖。听说在这个车间里待久了,有可能得尘肺,得了尘肺,人就会死掉。有一个以前在这个车间做过的人,据说得了尘肺快死了,医院不肯下尘肺的诊断书,医生说,他没有这个权利,下了诊断书,他的饭碗就没了。娘,老板只让工人做半年,半年后就把工人辞了,我现在已经做了两个月了,还有四个月可做,四个月后,我就没工作了,我年纪小,身体弱,没人要的。娘,你能不能给我寄些钱来,给我买红糖吃,我怕得尘肺,我才十五岁。还有,娘,天越来越冷了,我出来时只带了一条破毯子,像铁皮一样硬,没有一点儿热气,你能不能给我寄条被子来。我现在的地址是:河南省××市裕德耐火材料厂。我们的厂很大,没有几个人知道李小够,我会天天去门卫那儿问的。
娘,你给我留下的包袱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的是娘你吗?远处那个向你招手的男的是不是我爹?娘,你长得真好看,我天天拿着这张照片看。我娘说,你当初把照片塞进包袱,就是为了让我想你的时候,可以看看照片。
李小够
这孩子太可怜了!我读着信,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说得没错吧,来要钱了,把自己说得多可怜啊。他要的就是你的同情。李翠花说。不管你有没有寄钱给他,都会有第三集。
为什么?
你不寄钱给他,他不会死心;你寄钱了,他还会再要。
他不是留了地址吗?去查一下不就得了。
你没看见信里倒数第二段最后一句话?我们的厂很大,没有几个人知道李小够。他早预料到你要去查他,查了也白查,厂子这么大,没人知道他,他只要串通门卫就行了。还有,你看看信封上写寄信人地址姓名没有?为什么不写?李翠花老于世故地说,省得退回去呗。
荒谬透顶。我说,万一不是骗子呢,得找到这个马小丽,把信给她,否则这孩子会冻死。
切。李翠花不屑地说。
第二封信来了吗?王非回到家问。他似乎对这封信来了兴趣。
来了。我把信递给他。他打开看了一遍,站着发呆。如果还有来信,跟我说一声。他说。
怎么啦?是诈骗团伙在作案吗?我们提供线索协助破案,有没有奖励啊。李翠花说。
就你事多。我说。
半夜里,王非敲开了我们的房门。那两封信能借我再看看吗?他说。
我把信给他,他拿到自己房间里去了。第二天他把信还给我,看他一脸憔悴的样子,估计昨晚没怎么睡。那两封信他一定是研究了一个晚上,他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嚼一遍。
我对这个叫马小丽的女人产生了兴趣,我决定去找到她,为了那个可怜的孩子。如果马小丽还住在这个小城,我应该把信交给她,这是一个人应有的善良。当然我还心存侥幸,万一这个马小丽就是那个麻晓莉,那么,我可以为破案提供点儿信息,案子破了,王非的心结也了了,他也可以去解决终身大事了。我年轻的时候,曾向往当一个警察,现在,有一个神秘的事件来到了我跟前,我当然有责任去揭开它的面纱。
既然李小够把信寄到了这里,那么这个马小丽很有可能在这一带租过房子。我拿着信挨家挨户地打听,乡邻们努力追忆,纷纷说没这个人。这种没头没脑的信,你管它干什么。他们说。
搞不好是麻秆在戏弄你。邻居王干说。
我跟他无冤无仇,他戏弄我干什么?
你把马丽华管得跟自己老婆似的,他怎么下手?能不记恨你?
我什么时候管过马丽华!我生气地说。
每次麻秆送信路过,和马丽华调情,你都不是盯着他们吗?人家老公都不管,你管个屁啊。
我顿时面红耳赤。我只是喜欢偷窥别人的隐私,还以为自己神出鬼没,没想到自己也在别人的偷窥之下。
可是,邮戳是河南的,他总不能跑到河南去寄一封信吧。
他是邮局的。用橡皮雕一颗印只要五块钱就够了。
那他应该给我写恐吓信啊!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我随手丢了他不是白忙了吗?我说。
那我就不知道了。王干说,可他为什么明知查无此人,还是不肯收回信?
我原本还想去向马丽华打听的,被他这么一说,就不好意思去了。
后来我打听到有一个叫马晓丽的人幾年前曾租过马友仁的房子。马晓丽?马小丽?马晓莉?马小莉?谁知道呢?马友仁说这个马晓丽以前在藕舫路的开心理容院做过,让我去那儿打听打听。谅你也不敢去。他不怀好意地说。
我要去开心理容院打听马小丽。回到家,我对正陷在沙发里看电视的李翠花说。
去吧,不用找借口。她说。她的目光没有离开电视机。我看了她一眼,走出了家门。走到藕舫路,开心理容院门口站着的一位小姐向我招了招手,我就进去了。
先生里面请。一个长得很肉感的小姐缠了上来,想把我往里屋拖,先生需要什么服务啊?
我甩开她的手,说,我是来打听人的。
先生如果是来捣乱的,就出去。她说。我忽然看见屋子的角落里还坐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他正警惕地盯着我。
给我敲敲背吧。我说。小姐的背敲得有些暧昧,充满挑逗,显然她还想发展其他生意。
小姐在这里干了几年了?
八年了,老职工了。
你们这儿以前有一个叫马晓丽的吗?
马晓丽?让我好好想想,哦,有过,六年前,有过一个叫马晓丽的,不过后来就离开了。
为什么不干了?
长得不好看呗,在我们这种档次的店里,长得不好看,只配端洗脚水。
这个马晓丽有过孩子吗?
孩子?不知道。
她没跟你说过?或者,她有没有经常偷偷地拿出一张孩子的照片看?
看照片?好像看到过,是不是孩子的照片就不知道了。不过她挣钱很卖命的。她当时是我们这里年纪最大、长得最不好看的一个,我们都看不起她,我们懒得接待的客人都让她去接待。
她现在在哪儿?
怎么?她是你相好?哦,你跟她生了个孩子!
嗯,她在哪儿?
不知道,据说在人民大桥下站了段时间,后来就消失了。
哦。我付了钱,走出理容院。
出了理容院,我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去向马丽华打听一下,看看她知不知道马小丽这个人。马丽华的房子比较大,租出去的房间有十来个,她接触的人多。
我把信递给马丽华,马丽华的神情有些愤怒,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这信是寄给我的?显然,这两封信的内容,已经通过邻居的嘴传给她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慌忙摆摆手,说,我只是想问问,这些年,有没有一个叫马小丽的女人租过你的房子。
没有没有。她一个劲儿摆手,说。
哦,那没事了。我转身就走。
那信,能让我看看吗?她忽然说,我只是有些好奇。
我转过身,疑惑地把信递给了她。
她的手有些抖,脸上的笑有些僵硬,像生硬的雕刻。她掏出信纸,看得很仔细,看完一遍,又浏览了一遍。
就这些事儿?那孩子已经十五岁了?她的笑脸舒展开了,像融化的冰。
嗯,信上是这么写的。
马小丽经常给他寄钱?
信上不是写着吗?我不耐烦了。这女人今天真啰唆。
她似乎如释重负,吐了口气,说,这孩子,太可怜了!
我向她告辞,她有些走神,没听见我的话。我疑惑地迈出了她家的院门。我说过,每个人的生活是条河,一部分生活袒露在河上,还有一部分生活沉在河底。我现在没有兴趣去探究她河底下的生活。
走出院门时我碰上了王干,王干问,第三集开始了没有?
还没。我说,大概快了吧。我望着天空发了会儿呆。
王非回家后,我向他讲起了开心理容院里那个叫马晓丽的女人。听说这个女人失踪了,会不会就是那个麻晓莉?这可是一个线索。我说。
我们早就查过了。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人。王非淡淡地说。
没事别去那种地方,我们又要扫黄了。他接着说。
我是经过你妈同意才去调查的。我满脸通红。
三
你的信。麻秆挑衅似的挑起嘴角笑着,把信扔给了我。
你不怕我去你们单位告你?我说。
去吧,去告吧,反正这活儿老子也干腻了,早不想干了。他说着一踮脚,骑走了。
我看了他一眼,拆开信。
娘:
我给你写了两封信,不知你有没有收到?娘,你是不是不高兴了?从小,我就讨人谦(嫌),同学们都叫我李小狗,有的人叫我狗。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做一条狗,因为做了狗,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有一家公司的保安室里有一条狗,很凶,我们去捡垃圾的时候,保安就把狗放出来,赶我走。狗跑得很快,我跑不过它。我希望自己是一条狗,和它咬一架,这样它就不会咬爹和娘。娘,我病了,老牛说是冻病的。我发高烧,躺在铺上,没有人理我,我没有钱去卫生院看病。老牛说,只要多喝开水,就能熬过去的。娘,你不用担心,我命贱,熬一熬就好了。老板这个月沒有按时发工资,听说他很忙,他在外面养了四个小老婆,被他的大老婆发现了,他忙他的老婆们去了。听说他的老婆们要分他的家产,他现在都要上吊了。娘,老板不发工资,我这个月怎么过啊?还有,娘,天越来越冷了,你的被子寄出了没有?
娘,我现在天天拿着你的照片看,我想你,你长得真好看,你嘴角那颗痣特别好看。
李小够
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第三封信到了,叫你寄钱是吧?李翠花得意地说。
我感觉这件事不是个骗局,我厌恶地说,给我五百块钱!
干什么?
人应该有起码的善良。
你这是蠢。她说,我不会给你钱的,我不能看着你被骗。
即使真的是骗局,被骗一次又何妨?我叫道。
不许寄钱,否则,我就认为他是你的私生子。她轻蔑地看了我一眼,顾自看电视了。
我走出屋子,去找王非。你想去干吗?是不是去汇钱?李翠花关了电视跟了上来。王非派出所的电脑上应该有暂住人口的资料,我可以让他查一查近几年有没有一个读音叫马小丽的女人在我们这一带居住过,现在又住在哪里。
王非看了信,嘴里喃喃自语,她嘴角有痣?他有些坐立不安,双手不停地在裤腿上擦来擦去。
你怎么啦,儿子。我问。
哦,没什么。找马小丽是吧,好的,我这就找。
王非查到了三年前确实有个叫马小丽的人在我们这一带暂住过,尽管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但哪儿有这么巧啊,有人写信找马小丽,这儿恰好有个马小丽。我看到了希望。资料显示,这个马小丽是个河南人,她现在在石狮商贸城开皮具店,租了盛丰家园的一套单元楼。
我决定去石狮商贸城找她。我在商贸城的服装皮具区打听,果然打听到那个叫马小丽的人。她的门面不小,里面箱包皮具琳琅满目,都是中等档次的东西,给人感觉这家店很殷实。皮具店以她的名字命名,叫小丽皮具。店里有两个人,女的坐在桌子后面点钱,男的在搬箱子。
我假装看皮包,女的走过来打招呼。
听口音老板娘不是本地人?我说。
先生好耳力,我是河南的。
哦,不容易啊,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拼,打算在这儿落脚了吧?
嗯,打算买房子。
那个男的在店里,我不敢把信拿出来,我想这是一个人的隐私,最好还是私下里跟她讲,免得她下不了台,说出违心的话,或做出激烈的举动。我在店里东翻翻西看看,后来那个男的终于拖着装皮具的纸箱出去了,我拿出那三封信,说,你叫马小丽,是不是?
你想干什么?她警惕地看着我说。
你以前在两湖镇光明村租过房子,是吧?
你什么意思?她后退了一步,说。
这三封信是不是你的?你看一看。
她犹豫了一下,接过信,看了看信封,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抽出信纸看。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她看完信说。我没有看到她脸上神色的波动。我有些失望。
真的不是你的?我问。
你是不是想讹我?她说,当心我报警。
那就算了。我有些灰心,正要拿回信,那个男的进来了,见了那几封信,说,谁的信,让我看看。说着就伸过手来了。那个女的连忙把信塞给我,对男的说,别人的信,你看什么?
我想把信塞进袋子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把信抓过去了。
马小丽?不就是你吗?你的信怎么会在他那里。他对女人说。
事到如今,把信抢过来反而会使他多疑,不如大大方方给他看信。女人也没有阻止,到桌子后面做账去了,不时抬头瞟一眼男人。
这几封信寄错了地方,寄到我家里了,我对他说,我已经找了好几个叫马小丽的女人了,她们都说这信不是写给她们的,你认不认识其他叫马小丽的女人?
好啊,原来你都在外面生出杂种了。男的还没看完信,就叫了起来。我连忙抢过信溜之大吉。
我跑出了石狮商贸城,正在停车处取车,那个男的赶了出来。他握住了我的手,激动地说,大哥,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只乌龟,现在我知道了,原来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在外面找女人,可我没有生出杂种来,她连杂种都生出来了,她有什么资格骂我!大哥谢谢你啊,尽管她死不承认,这事落谁身上也不会承认,要是我,我也不会承认。从现在开始,我要抬头做人了,我出了一次轨,就被她搞得半辈子抬不起头,现在,老子抬头啦,原来我们都是同一种货色,谁也别嫌谁,大哥,谢谢你啊。
我哭笑不得。
不过,大哥,说句实话,你这么拿着信找人家,太不地道。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愣了会儿,沮丧地回家。到家门口,正好碰到王非从屋里出来。我出一趟远门,要过段日子回。他走了老远才背对着我喊了一嗓子。
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内心充满了担忧。他不会又陷进那个案子里了吧。
四
后来几天我都没有出门,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再去找这个马小丽。马小丽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谁是马小丽?是藕舫路开心理容院的那位小姐?她现在在哪儿?还是小丽皮具店的老板娘?看她不动声色、事不关己的样子,很难说。不过,像她这种人,什么样的事没经历过?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心里不管起多大的波澜,表面上还是风平浪静。当然,这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她也许叫马小丽,也许不叫马小丽——马小丽可能就是一个化名,她们都可能是这封信的主人。我想,如果这只是一个故事,那三封信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头,然后呢?不同的马小丽,就会发展出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深入到马小丽人生的河面以下部分,刺痛她和李小够的心。而我们呢?我们只不过是个看客。
我走出房门,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天冷了。我忽然想,這么冷的天,那个孩子有棉被了没有?他怎么样了?
我向王干借了五百块钱,按信上李小够留下的地址寄了过去,这样,我的内心会平静一些。
几天后,王非背着他的黑色背包走进屋,他胡子拉碴的,很憔悴很疲惫的样子,他把背包一丢,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妈,给我煮碗面。他说。
好的。李翠花跑去厨房,边跑边担心地回头看看王非。
案子有线索了?我问,声音很低。
什么?
六年前的那个案子有线索了?我说。
没。
哦。我有些失望。
也不是同一个人。他说。
哦。
破案没那么容易的,要等待时机,时机到了,才能瓜熟蒂落。他看我一眼,说。
嗯。总有一天时机会到的。我安慰他道。
是啊。他躺在沙发上,眼望天花板。
破案不影响找女朋友的。听说王莉也没再找男朋友。
嗯。这次是她陪我去的。
哦。好!好!中午喝一杯?
不了,我得买一束鲜花,去一趟龙山。
好吧。
对了,你先借我点儿钱吧,哦,我得找我妈借,我身上的钱都给那孩子了。
好的。我说。
这是故事的另一种可能。我想。
责任编辑/张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