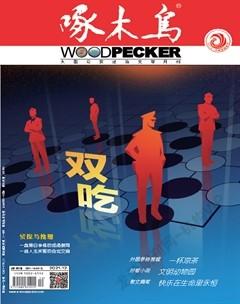白太阳(中篇小说)
李治邦

一
李重在男人群里算是个儿高的,一米八几的个头,人长得白净,五官也清秀,看起来比较扎眼。其实李重是个特别低调的人,在哪儿一待就不喜欢让别人看见。为了照顾患了心脏病的母亲,他从下面一个县公安局的副局长,调回到省城一个中心区的派出所,当了所长。李重本来是要当县公安局局长的,而且已经上了会,
就差几天的公示了。在这个当口儿母亲心脏出现了梗死,急需要照顾。父亲是个吃粮不管闲事的人,只能让唯一的儿子李重调回来。
李重回来的时候,县公安局的人都出来送他,几乎每人都含着眼泪,足见他在这里的人情分量。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亲自送他到车站,握着他的手说,你在公安局是一条动脉,你走了,我这里就梗死了。
副书记说完扭头走了,李重站那儿品味着刚才副书记的话,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好的评价了。
他所在的那座城市在长江以南。母亲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了,吵着嚷着非要回家,李重问大夫,大夫说,不敢保准,你母亲随时会心肌梗死。李重劝母亲继续住,母亲说,让我死在家里吧。
李重从小就听母亲的话,无奈把母亲接回家。其实,他干公安这一行也是母亲定的,他原本是喜欢数学的,在中学里当个数学老师是他的心愿。可是高考的时候母亲一定要让他报考公安大学,说,干公安吧,你穿上警服好看。为了这个好看,李重舍弃了自己喜欢的职业。父亲反对母亲的意见,说,让孩子当老师挺好的,也有寒暑假。但是,没有办法,李重只能尊重母亲的意见,父亲在家没地位,尽管父亲是一位律师,家里靠他支撑着生活,但这样也挡不住母亲的专权。
李重的婚姻也是母亲做主的,老婆莲的母亲跟李重的母亲是同事,母亲看中了莲,跟同事一说就定了。其实,那时候李重在公安大学喜欢一个女同学,叫倩,两个人在快毕业的时候动了真感情,在宿舍里亲热了一次。可母亲不管这个,就死活定了莲。李重抵抗了一阵子,后来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看不得母亲流泪。他后来也跟倩流泪,倩看不了一个大男人为自己流泪,就狠狠地说了一句,你就不是一个男人。
父亲照顾不了母亲,李重到了派出所,一大堆事。另外,自己刚来就请假,也实在说不过去。在为难的时候,老婆莲对李重说,你别犯愁,我让我母亲伺候你母亲,每个月你多给我母亲一千块钱,比请保姆合算。李重觉得是个办法,岳母人细心、会做饭,照顾母亲一定不错。李重征求母亲意见,母亲问,你岳母是个精细的人,给她每月一千元,人家能答应吗?父亲插话,我看行,都是亲家,人家也不会把钱看得那么重。母亲瞥了父亲一眼,悻悻地说,你了解她?父亲说,我们以前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她从小就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母亲苦笑着,你从哪儿看出她有情有义了?父亲摇着脑袋,我不跟你矫情,你是需要人照顾的,所以我才这么说。
李重愕然,他真不知道岳母跟父亲还是同班同学,觉得父亲和岳母的嘴封得真严实,另外,母亲知道也没有说。他回家跟莲说,莲说,我早就知道,你难道不知道?李重皱着眉头说,你们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李重跟岳母一说,岳母有些犹豫,但还是答应了,说,你们也真会想,一千块钱就打发我了。李重说,不行,我再给您添一千。岳母说,这又不是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你父母知不知道我的分量。说完了,还不放心地问,你父亲也是这个意见?李重点点头,岳母脸色很不好看,但也没有再说什么。
省里干公安的都知道李重的名字,因为他破过一个几乎不可能破的案子。当时,一家银行被抢了460万元,是两个人蒙脸半夜干的,没有留下一丁点儿的痕迹。李重三天就破了这个案子,案子的侦破过程在公安圈子里传得很神。
李重刚到派出所赴任就赶上一个案子,有个画商自称能高价购买名画家的作品,后来有一个人拿着著名画家吴待秋一幅斗方大小的山水画给了这个画商,当时就在画商自己公司的会议室里。画商看后认为是真迹,最后两人敲定了七十八万元成交。画商先付了五万元的定金后离开会议室,说是让同事来签这个合同。送画的人等了半个小时没有见画商回来,慌忙找这家公司询问。这家公司的人说不认识这个画商,送画的人目瞪口呆,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他在你们公司会议室里跟我说的,还有你们公司的人给他开门、给我倒水。公司的人解释说,真的不知道,我们不可能给他开门、给他倒水。于是公司的人让这个送画人挨个儿办公室寻找那个开门和倒水的人,最后也没有找到。
这个案子出来后便成了死案,因为所有的漏洞都堵住了,打了一个死结。
市局把这个案子交给了派出所,说是现在一些刑侦工作要下移到派出所,后来才知道,就是为了等着交给李重。
送画人是省城一位有名的收藏家,认识很多人。这件事在网上被炒作得沸沸扬扬,连省厅的领导都在过问。李重去了那家公司,知道会议室和走廊都没有安装摄像头。那家公司是做文化创意产业的,也就是字画交易。所里的人都认为是公司搞鬼,做了一个局。但是认为归认为,没有证据也是白费。李重在那家公司待了两个多小时,都是很随便的询问,一地的碎片。所里跟着去的人暗暗失望。李重问得最多的就是会议室钥匙,还有开水房、水壶在哪儿搁着。公司的罗总经理就像祥林嫂一样一再地回复着同样的话,他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见过这个作案人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偶然进到会议室的公司副总老黄。
老黄跟李重描述了作案人的长相,瘦高个儿,脸色很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黑色外套,其他就不知道了。李重认真地问老黄,你跟他说过话吗?老黄说,没有,只是听他跟那个送画人不断地说。李重问,什么口音呢?老黄仔细想了想说,普通话,不是咱们当地口音。李重又问,你认识那个送画的人吗?老黄说,见过几次面,沒有打过更深的交道。李重皱着眉头问,你进来没觉得哪点儿异常吗?老黄想了想说,我们公司来的人比较多,真的没有在意。
李重带着所里人出来,所里人说,我们曾经怀疑过老黄,可查了半天也没有个子丑寅卯。李重他们出来时没有乘电梯,因为所里人说过,电梯间摄像头没有记录下这个人,他就带着大家走楼梯,六楼很快就走下来。所里人说,楼梯的摄像头里也没有这个人,大厅只有送画人进来的画面。李重找到一个后门,顺着后门走出去,是一个停车场。所里人马上说,我们也查了,这个停车场有摄像头,但没有这个人的画面。李重还想再说什么,所里人说,我们调出了这两天的录像,都没有发现此人的踪迹。李重笑了,你们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所里人说,能调查的我们都调查过了。你问过的,我们也问过了。
李重说,一定是哪条路梗死了。
所里人没有听明白,李重又说了一遍。
二
晚上,岳母离开后,一般都是李重伺候母亲。父亲对岳母很客气,每次岳母回家都是父亲亲自送,回来都是满脸微笑。如果因为李重的事情多,下班回来晚了,岳母也等他回来了再走。每次父亲都对亲家说,你走吧,这点儿时间我能够照顾。岳母笑着说,你要是能照顾,我就不用来了。母亲在旁边看着也不搭话,父亲和岳母就这么一句句地说,听不出所以然。可是每次岳母走了,母亲都对父亲说,还是你们老同学好,看着那么亲切。父亲也不回答,就是一个劲儿笑。
莲在铁路上也是干公安的,一个礼拜回来两三次。莲要是回来都是她做饭,父亲说莲做的饭可口。晚上,父亲在另一间屋子专心看电视,他特别爱看电视节目,尤其是古装片,一般都要看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李重跟母亲睡一间,父亲自己住一间。
李重和莲的房子距离父母家比较远,靠近火车站,一套不足六十平方米的小两居。那房子其实就是一家客栈,一般回去就是为了夫妻团圆。李重说,咱俩不能再拖了,要一个孩子吧。莲说,怎么要,谁照顾,指望着我母亲?我母亲现在照顾着你母亲。李重不说话了,他喜欢孩子,莲之前做过一次流产,当时因为两人没调在一起。这要是到现在,都能上学了。
每天晚上,李重给母亲洗完了脚,然后铺床,他就睡在母亲身边。李重每次跟母亲聊天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今晚又开始了。李重说,我小时候学习古诗,有“白日依山尽”的句子。我多次举手问老师,不都说太阳是红彤彤的,怎么会有白色的呢?老师不耐烦地对我说,你自己用眼珠去看了吗,以后别瞎举手,好像就你小子能耐。回家我问您,有白色的太阳吗?您想也没想就回答,有啊,太阳是用火烧的,火烧没了就成白色的了,就跟煤球一样,烧到最后煤球就是白色的。人也跟太阳一样,要是死了,也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光了,生命就完蛋了,变成白色的了。
母亲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李重觉得母亲的笑神经很发达,他说什么母亲都爱笑,而且笑的声音很畅快。
说到要孩子的事,母亲说,我心脏不定什么时候就梗死了。因为我,你们要不了孩子,我让你们遭了多大的罪,没有办法,我还是快点儿死吧。李重说,我没那意思。母亲说,我有这个意思。我想跟你父亲吵一架,然后一生气就死了算了。可就是吵不起来,你父亲就是不生气,他不生气,我一个人怎么生?母亲说起死来就这么轻松地笑着,李重想哭,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市公安局又一次催问李重盗画案子的进展,限期一个礼拜结案。所里人知道了,都替李重捏把汗,因为案子没有任何进展。越没有进展,网上就越传得离谱。
这时,所里管辖的一个小区,有一辆宝马车半夜被盗走了。车主是一家快递公司的老板,很有钱,在市电视台新闻里总能看见他。李重那天回家很晚了,父亲还在等着他,父亲说,电视里说了,都已经三天了还没有破案,不知道警察都干什么吃的。李重气哼哼地说,您也信这话?父亲说,你不是很有本事吗?李重没有说话,因为父亲是个大律师,哪次都说不过他。
李重回到所里开会,大家七嘴八舌,说得最多的还是那个盗画案子。小高递给李重一张人像图,是小高找人通过老黄描述,画出来的一张作案人头像。李重看了看小高,又看了看这张图,人很瘦,白净脸,金边眼镜,眼睛很窄,眉毛十分浅淡。小高自信地说,我们也跟送画的人核对了,基本就是这个样子。李重没有说话,小高又补充说,已经跟有前科的人核对过,没有类似的人。
负责盗车案子的大马说,监控镜头里只看见宝马车被人开走的视频,但看不见里边的人。车开的速度很快,好像很熟悉这个地方。我们接着跟踪,跟踪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就突然找不到了。李重诧异地问,怎么找不到了?大马说,十字路口的左拐弯处有一个渔具市场,他开车进去以后就不见了。里边的岔道比较多,许多地方还没有摄像头,我们去里边也找了,没有。也没有见这个宝马车出来。李重问,那转天呢?大马说,转天也没有,连续两天都没有发现车出来。渔具市场里很大很复杂。会开到这里似乎进展不下去了,所有的线索又都断了,大家都盯着李重。
李重站起来说,又都梗死了。
三
李重晚上回家后,照例给母亲洗脚,然后上床睡觉。
母亲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问,你是不是碰上什么不好办的案子了。李重说,您睡吧,我尽量不折腾。没多久,母亲安心地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李重一直没有困意,琢磨着这两个案子的出口在什么地方,他想,不可能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拿走画的人肯定是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溜走了,只不过他在哪儿溜的我们暂时没有找到。宝马车也一样,开进渔具市场,就肯定会离开那里,不会一直在渔具市场里待着。他瞬间觉得,既然这辆宝马车没有出来的镜头,是不是还在哪儿憋着呢。
月亮好圆,李重心想,月亮都有缺的时候,何况人呢?
转天,李重跟送画人见了一面,谈了一个多小时。跟他去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在他们看来,那就是聊闲天。比如怎么跟作案人认识的,其实就是在一次拍卖会上,当时拍的是吴湖帆的画。而吴待秋和吴湖帆都是民国时期影响海内外的著名画家,与赵叔孺和冯超然一起被誉为“海上四大家”。作案人坐在后面,送画人恰巧坐在他旁边,两个人就聊起这四大家。作案人很熟悉吴待秋,说得头头是道。这时候,送画人就说自己有吴待秋的画,是一幅山水画,叫作《春头》。作案人竟能说出这幅画的来龙去脉,让送画人瞠目结舌。后来就谈成了这笔交易,定下什么時间去送,以及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两人前前后后谈了十分钟,先走的是作案人,说了一声“我走了”,就不见了踪影。
李重问送画人怎么有的这幅画。送画人说是在朋友家看见的,当时怎么开的价,怎么谈成的交易,怎么兑现的等等。这件事过去有七八年了,没几个人知道他有这幅画。李重又问了一些他卖画这个朋友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场景。李重问得很轻松,就跟聊家常一样。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李重透过窗户看见一块儿大玉盘挂在天空。父亲这时急切地打电话告诉他,你母亲不行了,快回来!李重马上开车向家里赶,这时,硕大的夕阳快落山了,李重瞅见夕阳坠入天边的最后一刹那,流露出漫天刺眼的白光,他朝西天喊了声——妈!眼睛就模糊了。
楼下一个电梯在修理,另一个电梯排着队,李重撒开腿就朝六楼疯跑。父亲打开门,他扑到母亲身边,母亲只是努力看了他一眼,嘴唇抖动着不知道说什么。李重连忙凑近母亲的嘴边,隐约听见母亲说,你父亲看上你岳母了,你别拦着……李重回头看着父亲,父亲在那儿站着,闭着眼睛。母亲笑了笑,闭眼的时候费力抬起了手,朝窗外指点着。李重顺着母亲的指头往窗外看,天空上漂浮着一轮月亮,圆圆白白的,闪烁着一缕缕的银光。
母亲最后的话说的是白太阳。说完,头一歪,身子就软了。李重扑在母亲胸前号啕大哭,母亲的怀里依然还有余温尚留,暖着李重。父亲怔怔地看着已经闭眼的妻子,脸上的表情像是木雕。莲和岳母也走了进来,李重把母亲的衣服脱下来,母亲赤裸着身子,泛着青光。莲问他,你干什么要给妈脱得这么光?李重说,这是我和母亲说好的,她死了就脱光了,她要让身体每一个部位都疏通了,不想梗死。李重说着又哭,父亲拿来已经预备好的新衣裳。那是典型的中式小棉袄。李重拿酒精棉花细细地给母亲擦拭着,然后轻轻拍打着母亲的身体,母亲的眼睛陡然睁开了,怎么也闭不上,深情地看着李重。李重和母亲的眼光对视,依然还能交流。父亲过来用白毛巾轻轻盖住了母亲的眼睛,好久才拿开。
这时,母亲的眼睛终于闭上了,眼角溢出泪,烫烫的。岳母过来,攥住了母亲的手,对李重说,我觉得她好像有话对我说。
李重望着母亲的遗体,想起就在两天前的半夜,他突然醒来,发现母亲掉在床下,身子冰凉。李重抱起母亲,心疼地问她,您为什么不喊醒我?母亲平静地说,我看你睡得那么香,不忍心啊。
四
发丧完的当天下午,李重带人去了管辖的那个小区,快递老板在那儿等着他。李重问,你上次说,你的车换过钥匙,是在你被盗车的前两天对不对?快递老板说,我原先的车钥匙不好用,于是让我手下的人又重新换了一把,很好用。李重说,你说你的车保险也是你手下人给办的?快递老板摇着脑袋说,你别朝下说了,我知道你怀疑我手下这个人。你们所里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他不可能偷我的车。要是他偷的,我头朝下走。李重笑了,说,我没有说是你手下人偷的呀。快递老板一脸不高兴,问,那是谁呀?李重说,你手下人在哪儿配的钥匙?快递老板说,就在前边不远小区里的铺子,你们的人也去了好几次。李重说,你跟我走。
说着,李重拉着快递老板上了车。其他人也跟着上了另一辆车。车拐进一个渔具市场,李重头一个下来,走进一家商铺。迎面一个小伙子走过来,一脸狐疑地问李重,你找谁呀,就开我家的门?说着,小伙子后面跟着出来一个瘦高个儿。李重挥挥手,有人过来就铐住了那个瘦高个儿。李重又走到后院,那里放着一辆车,用油布盖得很严实。李重喊了一声,给我揭开。几个人揭开,是一辆白色的宝马车。快递老板跟过来连声说着,不对呀,我那辆是黑色的。又看了看车牌,说,这车牌也不对呀。李重打开后备厢,里边有一个红酒盒子,打开一看是德国的葡萄酒。他回身问快递老板说,这箱子德国葡萄酒是你的吧?你朋友从德国慕尼黑给你带来的。快递老板看完顿时傻了眼,你怎么知道的?李重问,你再仔细看看,这辆宝马车是不是你的?快递老板来回看了看,对李重说了一句,是我的,这四个轮胎是我新换的。
李重就在这家小院子的里屋坐下,那两个人杵在那儿一言不发。快递老板云里雾里地直瞪瞪看着李重。大家也围坐在那儿。李重对那个瘦高个儿说,你盯着人家的宝马很久了吧。瘦高个儿没有说话,李重继续说,你特别喜欢宝马,已经偷了三辆了吧。所有人一惊,瘦高个儿有些吃不住劲,就蹲下来。李重说,你跟这辆宝马车很久了。你先是把车的钥匙孔弄不好使了,其实你一直想直接开走,但这辆车的防盗系统特别好,你打不开,就花钱买通了那个小区配钥匙的。所以,那天快递公司老板派人去配钥匙,你就在那儿等着。你等了一整天,好不容易等到了,你就想法子支开那个配钥匙的,之后你就得手了。拿到钥匙后,你没有马上就开走,而是等了好几天。你找到渔具市场这个小伙子,因为他家有个足够大的后院,这也是你事先踩好点的。你知道怎么能躲开摄像头,知道车开到这儿就能躲开,而且你迅速私下找人上门改变了宝马车的颜色,还换了假的车牌。你跟这个小伙子许诺,一旦成功了,你将给他多少钱。小伙子犹豫了几次,你就带过来一个风流女人。坏就坏在这个女人身上,她跟这个小伙子上完床以后不甘心,逼着你多给钱。结果你没有给,这个女人一气之下就在外边说走了嘴。
说到这儿,小伙子也蹲下了。李重站起来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说,我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找到你家的。第一天我还就疏忽了你的院子,因为你这个院子在里边,巷口逼仄,宝马车根本開不进来。后来我再看,发现巷口那个石头墩子是可以搬开的,而且,我找到了搬动的痕迹。小伙子哭了,说,我这是给人家看房子的,房主就等着拆迁赚钱呢。你别关我行吗?我把所有的钱都退了。
李重回头喊了一声快递公司的老板,说,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的案子就算清了。说完,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对瘦高个儿说,你小子对宝马太偏爱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你盗取别的宝马的停车处,让我震惊呀。你不卖,就这么保留着,而且天天把车擦洗得干干净净。瘦高个儿愕然,李重继续说,而且你都刷成了白色。白色本来是很圣洁的,却让你给污染了!
转天,很少下雪的这座城市下雪了,一片洁白。
网上发出来宝马车失窃案告破的消息,其中一张照片是李重从那个院子走出来的画面,那个快递老板低头哈腰地跟在后面。这张照片传得很快,李重很不高兴,对大马说,告诉相关部门不要再传了。大马对李重说,过去都是市局刑侦队的办大案,吃大鱼;我们派出所的办小案,吃小鱼。所里好几年没有这么快就破案了,让大家高兴高兴也好呀。李重说,人家快递公司老板看了会怎么想,我是谁呀,怎么拍得人家低三下四的。我们是为群众服务的,不是群众的主子。
快递公司老板非但没有意见,还非要跟李重喝酒。李重说,我不可能喝,我们是有规矩的。老板说,我就是想问问,你怎么就能跟讲故事一样,不紧不慢地就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李重笑了笑回答,破案子就是疏通所有梗死的地方,顺了,案子就自然破了。
这个盗窃宝马车的案子破了,可那幅盗窃名画的案子迟迟没有进展。市局又开始催促,说,别破了一个案子还留着一个,现在网上还在继续炒这个案子。也有人放风,说拿走那幅画的人已经走了,这个案子就是死案。随着这幅名画案子的发酵,吴待秋的画价在市场上也越走越高。
母亲去世后,李重就回到自己的家。父亲说,你再陪我住几天,我有些恍惚。李重就住了一晚上,给父亲洗了脚。他对父亲说,天冷了,血管容易堵,您也得格外注意。夜深了,父亲说,你就跟我一个床铺吧。两个人就一起躺在那儿,父亲叨叨着,你母亲生你时难产,险些就走了。我那时忙着办案子,你母亲一个人带着你过日子。你小时候得了软骨病,不愿意吃鱼肝油丸,一吃就恶心。你母亲就自己吞下鱼肝油丸,吃给你看,还故意吃得津津有味。
李重觉得乏味,不太搭理父亲。他想着这些天来,事情一个接一个,所里有个警察带嫌疑人去看守所,结果开车过快,在路上翻了车。这个警察腿骨折了,嫌疑人也成了脑震荡,醒过来就几乎谁也不认识。嫌疑人家属不依不饶,天天缠着他。
过去有了案子,都是上报。可现在破案子成了派出所的事情,推都推不掉。李重上任后让人把武器库打开,每天都让大家擦枪,然后拆卸一遍,重新装上。
父亲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的手机响了一下。李重下意识看了一眼,是岳母发的微信,上面就一句话,你应该想好以后咱们的事情。李重眨巴了一下眼睛,努力想睡觉,但就是睡不着。脑子里都是母亲的身影,后半夜他突然发现母亲坐在床头看着他。他知道这是在梦里,于是努力睁开眼,依稀看见母亲在昏暗中握着他的手。母亲的心脏不好是老毛病,老躺床上,得了褥疮。李重从下面调回省城,找到了一种中药膏,叫作“厚德门”。他每天给母亲擦,后来居然都好了。母亲哭了,说,褥疮就是肉和神经都梗死了,这回你给我疏通了。李重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母亲总爱用“梗死”两个字,弄得他也受了传染。
五
交通队送来一个摩托车酒驾者,在加油站发现的,可能是喝酒后比较兴奋,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说着。李重问交通队的,喝了多少酒?没等交通队的人说话,酒驾的就自己说,喝了三大杯,不喝不行,都是老朋友。李重又问,查了酒精含量多少?酒驾人又抢着说,一百多毫克,不算多。交通队的人走之前对李重说,李所,那个名画丢失案破了吗?李重有些不自然,说,没有破。交通队的人笑了笑,说,还有你破不了的案?
交通队的人走了,酒驾人还在缠着李重,说,是说拘留给窝头吃吗?我可吃不惯。李重没好气地说,让你吃馒头。酒驾人说,我那帮子哥们儿太不够意思了,非让我喝,我不喝,他们还跟我急。你想,他们哪是我的对手,都让我喝晕了。李重说,你喝酒了还骑摩托车,撞到人怎么办?酒驾人笑着比画着,我的技术好,那天我带一个人,转了好几个巷子,巷子窄那么多人我都没有撞着,那天喝酒比今天还多。李重感兴趣地问,你带的谁呀?酒驾人说,我也不认识,反正给了我不少钱。李重追问,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了吗?酒驾人说,就拎着一个包。李重拿出一张照片,对酒驾人说,是这个人吗?酒驾人看了看,犹犹豫豫地说,有一点儿像,但不是,是个女的,留着长发。李重拿出一张城市地图对酒驾人说,你们走了哪几个巷子?酒驾人兴奋地戳着,这个这个这个,谁说我喝多了,我记得很清楚。
第二天上午是打靶时间,靶场在郊区。大家分乘三辆车去,每一个月的打靶是李重绝对不放松的。因为申请子弹和打靶都很困难,他就跟市局领导磨。他对市局领导说,派出所的枪不是假的吧?如果用时拉不开枪栓、子弹打不出去或是打得不是地方就是我们的耻辱。在靶场上,每次都是李重先打,一般是站姿和蹲姿,每人十发子弹。李重都是枪枪命中靶心,然后站在那儿看每一个人射击。谁跑了一发子弹,他就在旁边喊着,你放跑了一个罪犯!那声音很刺耳,在空空的靶场里来回撞击着。
回来路上,李重坐的吉普车在后面,开到一条热闹的马路时,吉普车被前面一辆奔驰车挡住了。可正道上都是车,奔驰就占着右拐道上。李重这辆车后面排满了车,都一个劲儿地按喇叭。李重的司机开始慢慢地在一个小缝隙里开,终于开了过去。司机气不过,就摇开车窗对奔驰车司机说,你会开车吗?车窗摇下,李重瞬间瞥见一个人瞪着司机,还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街,发现那人竟是那家文化传媒公司的黄副总。这个黄副总,那天还很谦恭很有气度的一个人,但现在是个不可理喻的无赖。李重的车拐过来,发现后面就是那家公司的楼,近在咫尺。
回到派出所,他把大马和小高几个叫在一起,说,查查这个黄副总的背景,有关他的一切都要查。大马问,什么叫一切都要查?李重说,他怎么到的这家公司,怎么当的副总,他懂不懂画。如果懂,他都跟画界的谁熟悉。还有,他最近的资金使用情况、账面上有没有进钱、进了多少,以及他家里有什么人、有谁懂画。说完后,大马不说话了。李重提高了嗓门,两天都给弄清楚了,不能有梗死的地方。
李重回到家,发现岳母在里边收拾着。洗衣机在滚动,窗玻璃干净如水。岳母是浙江人,弄得一手的杭州菜。她烧了一个鱼头豆腐和东坡肉,焖了一锅白米饭。李重和岳母第一次这么吃饭觉得很别扭,岳母不断给他夹菜。吃到最后,岳母说,你母亲死前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李重警惕地看着岳母,敷衍着说,没有啊。岳母说,说就是说了,你别瞒我。岳母的眼圈有些紅,说,你父亲帮助我打赢了那场根本打不赢的官司,我才能咸鱼翻身。李重问,什么官司?岳母说,我曾经借给邻居张大哥十万块钱,是给他治病用的。后来,张大哥病没有治好就死了。我朝他老婆要钱,他老婆说,不知道这件事。我跟张大哥之间没有任何凭据,就是他口头说的。当时的十万块也算是一笔钱了,是你岳父死的时候给我留下的。我是念张大哥平常对我挺照顾的,才借给他。李重好奇地问,我父亲怎么打赢的呢?岳母说,他疏通了所有的关系,解开了所有解不开的扣儿,这才赢了。李重问,那也得有凭据呀。岳母说,张大哥住院期间,我曾去看他,他当着病室的几个人说让我放心,就是砸锅卖铁一定会还我十万块钱。你父亲四处跑,找到了那几个病友,让他们出具了证据。岳母扑簌簌地流着眼泪说,我就是想对你父亲好,又不知道怎么报答你父亲,我只有贡献出我闺女,所以,你母亲一提,我就满口答应了。李重摆着手,说,严重了,您这么一说好像我霸占了您闺女。说完,他笑,岳母却绷着脸,李重赶紧收敛笑容。岳母说,后来,你母亲总说你父亲有外心,有时甚至说得神乎其神,其实我跟你父亲是清白的。李重说,我母亲都驾鹤西去了,您就别耿耿于怀了。再说了,我父亲和您真有那意思我也不拦着,我父亲生活得很孤独。岳母青紫着脸,那也是你父亲的想法!
李重知道岳母是为了说这番话来的。岳母又絮絮叨叨说了很多,李重也不怎么搭话,岳母走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案子依旧拖着,新案子不断地进来。一栋高层楼连续几家失窃,不是从门进的,而是从窗户进的,都是在七层。李重查看了现场,这几家都没有安装护栏。查了录像,因为都在夜里就很模糊。只是在小区的路上,李重看见一个模糊的背影,走得很快,还不时地回头张望。摄像头反复定位在这人身上,就是看不见脸。在小区的一个拐弯处,人不见了。李重接着查墙外的录像,没有。李重说,查街上的录像,他是翻墙头过去的。街上果然出现了,但依旧是不清楚的背影,李重说,他是老手,他知道摄像头在哪儿。有出租车的镜头,但没有人上车的镜头。出租车停了片刻又朝前开走了。李重说,查这个司机。派出所找到了这个司机,司机说,确实载过一个人,他从左门上的,我还不高兴,说,那个门是不开的。李重说,他那是为了躲避摄像头。司机说,那人在夜市下的车,没有扫微信,而是给的我现金。他戴着一个黑口罩,就露著两只眼睛。李重带人查看了夜市的摄像头,倒是发现一个人从车上下来进了夜市,但很快就混进人群里了。半个小时后,一个人走进摄像头,谁都没有在意,李重大声说,他换了衣服,就是这个人。大家面面相觑,李重肯定地说,他走路的姿势有个特点,就是两条胳膊摆动的幅度比较小。摄像头顺着这个人走,捋到最后,发现他进了一家典当铺,好久没有出来。李重说,这个案子破了,到典当铺抓人吧。李重带人在典当铺找到了这个人,他总来典当,其实老板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是不点破。李重对大家说,这个人有前科,开始查吧。
派出所的人开始对李重刮目相看,因为谁都没有注意这个人换完衣服后的走路姿势,而这个细节被李重抓住了。李重说,关键是细节,每一个案子都是靠无数细节组成的。凡是堵的地方,或者说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就要学会寻找疏通的地方,细节就是钥匙。盗窃案的嫌疑人交代了,他从小学过武术,曾经因偷窃被判过三年。
李重并没有因为这个案子破了而开心,盗画案没有破,始终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着他。
父亲总是喊他回家,他回去就睡在母亲的床上,嗅着熟悉的味道,觉得母亲依旧在身边。那天他开车回去,发现车位被一辆奥迪车占着,而且还斜着车身,霸气十足地占着两个车位。他生气了,给交通平台打电话,接线员说,车主始终不接。李重就站在那儿等着,他也在较劲,一定要疏通这个事,并继续给交通平台打电话。晚上的风凉了,像是小刀子在割脸。李重没有犹豫,就杵在那儿等着,他觉得自己很奇怪,平常很冷静的自己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执着。
半个小时后,李重想起这个小区属于自己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就给所里值班民警打电话,说要找到这个车主,并让值班民警看车主有没有前科。几分钟后,值班民警回应了一句,联系上了,车主马上到。
随着值班民警的话音,两个一高一矮、光着脑袋的人晃晃悠悠地从另一栋楼走出来,到了李重跟前。高个儿瞪着李重说,你想干什么,让派出所的人找我是吧?你以为你是谁,派出所人来了我就害怕了?李重说,你占了我的车位,我没有地方停车了知道吗?矮个儿走过来推了李重一下,李重一个趔趄。矮个儿满不在乎地说,占了你的车位怎么样,这儿的所有车位我们都能占。你有本事也占别人的,说着指了指远处,那不还有空的吗?李重说,车位是我的,我占别人的干什么?高个儿笑了笑,挑衅地说,我占了你的车位能怎么样?我想听听。李重终于不微笑了,虎着脸说,那就不行,懂吗?你的车停到你的车位。高个儿仰着脑袋说,我要是不去呢?李重没有说话,高个儿呵呵笑道,这个小区占的本来就是我们村里的地,政府不是想占也占了吗,给了擦屁股那点儿钱。李重说,这是两码事,我买了小区的房子,也买了车位,你们赶紧挪车。
两个人围着李重,矮个儿接着说,我们玩牌玩得正是挣钱的时候,你小子让派出所出面给你挪车位,坏了我们的兴致,懂吗?李重说,我坏了你们又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在这儿没有车位呀?矮个儿打量着李重说,就是没有车位,就是想占你的车位,我们占了好几年没有人敢惹事。你是想惹事吗?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李重看见在夜色里跑过来的大马、小高和所里几个警察。那两个人没有把跑来的警察放到眼里,矮个儿继续问,你是谁呀?还能把警察调来,调来我就问问,占了我们的土地,赔偿的钱我们花完了,是不是还得继续给我们啊?李重说,政府是你们的提款机呀,给你们的钱不少了。高个儿说,不够!
大马、小高和几个警察跑过来,小高气喘吁吁地给李重敬礼,说,所长,来晚了。李重指着这两个人说,他们占我的停车位,还在家里赌博,查清了处理。说完,几个警察向他俩围了过去,李重说,给我腾车位。矮个儿梗着脖子,喊着,我要是不腾呢,你们谁敢把我怎么样。一个警察上前,他继续跺脚说,惹急了,我还召集我的人,跑到政府给你们闹事,看谁闹得过谁。这时,所里值班民警打来电话,说,这两个人都有前科,除了赌博,还嫖娼,其中一个还是被追查的对象。李重放下电话看着矮个儿,说,你有前科吧,你因为什么抓进去的?矮个儿不说话,李重又看着高个儿逼过去说,你也有前科吧,你比他还厉害,对吧?最近,你们又开始犯事了,犯的事还不小,对吧?两个人有些忌惮了,李重说,是还想进去吗?是准备在这里继续挑事吗?两个人朝后退着,大马、小高和几个警察上前控制住二人。
李重说,让他们先给我腾车位!
派出所开盗画案子的分析会,大马和小高汇报说,没有查出黄副总什么破绽,所有李重提的问题都没有什么进展。李重说,梗死了。大家面面相觑,李重说,就是怕都给堵住了。
李重告诉大家,市局领导来电话了,说送画人见咱们没有动静,直接把事情捅到了上面。这幅画在社会上早有影响,吴待秋的画收藏在哪儿都有记载。大马问李重,那人是不是有问题呀,这么贵重的画就这么轻易送过来,随便就交货,而且跟盗画者又不怎么熟悉。马上就有人呼应,说,这是不是设了一个局,故意让咱们跳呀。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转移走了,没有人惦记着他的画,他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大家忽然兴奋起来,认为这个分析有了突破。李重沒有说话,只是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说了一句,下午,小高跟我去美术馆,让他们调出两个月前举办的那次吴待秋、赵叔孺、吴湖帆、冯超然“海上四家”的展览录像,展览了四天,都调出来。
大家有些懵,李重已经走出房间。
李重带着小高在美术馆看了一下午录像,终于在最后一天闭馆前的一个小时,看见了黄副总一个人慢悠悠地在里边转的影像,黄副总看着吴待秋的画很入神。李重兴奋了,盯着屏幕上的黄副总许久后才让小高截图留下来。他对小高说,你们调查不是说黄副总不喜欢画吗,而且还拿出那么多证据。小高皱着眉说,他去看美展也不能说明什么呀?李重笑着说,很能说明问题,你注意看他后面几米远站的谁呀?小高在人堆里发现了一个人的半张脸,惊呆了,竟然是模拟画的那个盗画者。虽然只有半张脸,但还是跟模拟的很相似。
走出美术馆,李重说,不要惊动黄副总,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这个盗画者。小高说,直接找黄副总摊牌不就完了吗?李重摇头,必须先找到这个盗画者!
分手时,小高问,你怎么知道要到美术馆去找线索?李重挥了挥手,没有说话。他很想告诉小高,要知道线路在哪儿堵死了。
六
第二天上班,小高传来话,这个盗画者瘦高个儿在福建晋江被发现,是一个开画廊的。李重说,迅速去人抓捕。隔了两天,小高等人将那个瘦高个儿抓捕归案。
黄副总被带到了派出所。市局派来两位预审官,也在现场等候。讯问室显得很拥挤,空气凝重。李重坐在旁边,小高是主审官。
黄副总进来的时候抬了一下头,惊讶地看着这阵势。小高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黄副总想了想说,我叫黄显白。小高问,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吗?黄显白笑了笑说,真不知道,估计是跟盗画案有关系吧。小高接着问,你认为跟你有什么关系吗?黄显白沉稳地说,我见过这个盗画者,但一切你们都调查过,我是清白的。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一个目击者。小高拿出来手机给他看,问,你和他为什么同框,都出现在美术馆,而且距离这么近?黄显白看了一下手机,戳了戳屏幕,漫不经心地说,站在我后边这个就是盗画者吗?小高问,怎么这样巧?黄显白淡然地说,我哪儿知道,他是奔着画去的。
小高不说话了,李重突然开口道,你老家是福建晋江的吧?黄显白的眼神一灰,低下头。李重说,这个盗画者叫柳江华,也是福建晋江人。黄显白努努嘴,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李重走到黄显白跟前说,柳江华跟你是高中同学,这不是巧合吧?你为了这幅吴待秋的画可以说费尽心机,专门回去一趟与柳江华密谋。然后,你就开始布局。不仅给柳江华详细描述了你们公司的情况,而且专门用手机录了他的所有行动图。你的疏漏是让柳江华去了一趟美术馆,因为送画人的这幅画当时在美术馆借展,你怕他看走了眼。你知道送画人手里有模仿的一幅画,你怕柳江华上了送画人的当。你回来告诉柳江华这幅真迹在哪儿能够看出来,因为你是放鹰的,不想被鹰啄了眼睛。柳江华虽然是画廊的老板,但他也没有想到这个送画人把这幅模仿吴待秋的画弄得天衣无缝。所以,那天送画人给你送的画是赝品,你后来知道了,柳江华却没有看出来。你被送画人耍了,白白给了五万元。
李重说这番话的时候,在场人都惊住了,黄显白忍不住骂了一句难听的话。李重忽然变了脸,指着黄显白大声说,你再骂这句街,小心我揍你!黄显白一愣,李重说,你在车上骂我们,当时我就想出手,骂什么都行,就是不能侮辱母亲!
晚上,李重和大家在派出所吃的盒饭。市局两位预审官对李重说,这幅画是赝品我们事先不知道啊。李重笑了笑说,小高把柳江华带回来时,他手里有送画人送来的那幅《春头》的录像。我马上找来市美术馆的两位鉴定专家,他们看了半天说是赝品,虽然在吴待秋的落款章上出了破绽,但无论从吴先生的画风、笔墨、题款,抑或气息都与真迹相同,且极精致。而且,这幅赝品是三十多年前仿的,现在市场价也不低。
其中一位预审官笑了,说,李所长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呀。李重说,我就是想把所有事情都疏通了,不能堵在一个地方!那位预审官又好奇地问,那个盗画的人是怎么走出大楼的,为什么所有的迹象都没有显示出来呀?大家也看着李重,李重说,这个盗画人化装成了一个女人,从大楼后门走的。他戴了一顶帽子,遮住了脸。预审官说,那怎么看出来化装了呢?李重说,他不是女人走路的姿势,所以被我抓住了。上次骑摩托车酒驾的人提起的那个女人提醒了我,帮助我疏通了堵塞的地方。
当晚,李重和莲去了父亲的家,父亲和岳母搬到一起住了。岳母做了一小桌杭州菜。岳母把头发烫了,穿一身花色鲜艳的衣服。父亲很开心,给岳母削苹果,削出一串果皮花。李重没怎么说话,莲却跟两位老人谈笑风生。父亲认真地对李重说,选择你岳母是因为了解她,我一个人生活也很寂寞。父亲看李重没说话,又继续解释,说,你别瞎想,我真的动念头和你岳母在一起,也是在你妈死了以后。我觉得和她结婚,你们也显得方便不用改口,你们称呼也自如。我结婚,也是为你们好。李重看着父亲,觉得他的想法也很奇怪。莲安慰着父亲,说,我们没事,只要你们过得舒心,做儿女的就高兴。李重看着莲,想起她有天晚上说的话,以后我和你离婚都难。
回来的路上,李重看见窗外飘起了雪花,他奇怪这个冬天怎么总是下雪,雪总是想方设法装饰着城市的清白。他感觉自己像是发烧了,脸颊烫烫的。
七
也就是在盗画案还没有完全了结的这天晚上,李重派出所辖区的洗浴中心发生了两个团伙的火并,表面上是偶遇,实际上是两个团伙的有意较量。
李重得到消息后带人火速赶到了洗浴中心,市局的防暴队也在途中。李重带着大马和小高五六个人持枪进到里边,看到两个团伙的首领都在拿枪指着对方,剑拔弩张。
在路上,李重就跟大马和小高交代,如果真的动起手来,大马的枪对着黑头,小高的枪对着大白。如果有谁开枪,必须一枪把他们手里的枪打掉,只有一枪的时间。大马应了一声,小高没有说话。李重问,你没有把握?小高只得点点头。李重说,我替你补一枪。大马介绍说,这两个团伙都有枪,其中黑头的枪法准,大白的枪法差一些。黑头不是咱城市的,但总爱到这里显摆。大白的父亲是一家超市老板,从小就娇惯他。这家洗浴中心是大白父亲开的,接待来往的客人,没有什么小姐,他父亲烦这个。
李重从大厅窗户跳了进去,其他人也都跟着跳。到了大厅中心,就见到了双方僵持的场面。李重已经在路上熟悉了两个团伙首领的相貌,他看见黑头就冲他一个劲儿地笑,手枪的枪口对准了他。李重说,是黑头吧。黑头说,你就是李重吧,你在你原先的地盘敲了我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枪伤,一个中腿,一个中胳膊。李重迅速回忆着,他突然想起自己过去的一次行动幕后操纵者就是黑头,当时没有逮住他,但那时李重只知道黑头叫朱小磊。黑头冲着对峙的大白拱拱手,说,谢谢你,今天我算是找到了我的仇人。李重扭头看,大白的枪口也对准了他。大马和小高都怔住了,知道今天晚上是一个局,那就是仇人商量好了,找李重报仇来了。
事情就是这样,一切都是布局,李重今晚就被这个局梗住了。李重记得,他把朱小磊的一个女人抓了,这个女人开车撞人后逃逸,在公安局拘留时逃脱。后来被李重在火车站抓到,她当时抗拒抓捕,被李重当场铐上手铐。朱小磊公然派人去劫车,被李重一枪打中了劫车人大腿,当场流血倒地。后来朱小磊就放言,一定要找李重报仇,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黑头对李重说,我知道找不到你,这场苦肉计是想引你上钩,果然你就自己找上门了。李重说,朱小磊,你以为你就能得逞吗?黑头举枪走近李重说,你们这五六个人有几个敢开枪的,我和大白兄弟有二十几个人都敢开枪。我知道你枪法准,但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捻几个钉?大马和小高上前要说什么,被李重制止住。
李重把自己的手枪扔在地上,对黑头和大白说,你们不是找我吗?我让我的人全退出。大白没有说话。黑头说,不行!李重啊,我要让你的人看着你受罪,绝对不会为难你的人。小高气得高喊,你算什么东西,敢对我们这么说话,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是人民警察!黑头又要举枪,李重挡住了小高。李重说,我把枪扔地上了,你这么拿枪对着我们的人是不公平的。黑头笑了笑,你倒是舍生忘死,看我怎么让你受罪。
这时,李重突然蹲到地上。黑头问,你怎么了,害怕了?李重痛苦地说,我有心脏病,好像,哪儿梗死了。黑头靠近李重,也就是瞬间,李重从腰后面拔出手枪,迅速开枪击中了黑头的腹部,然后再开枪击中了几米远的大白腹部。大马、小高和几个警察迅速站在了黑头和大白身边。太快了,大白倒下了,黑头蹲下了。李重挪到了黑头跟前,黑头惨叫着。
两拨团伙的人都懵在那里,因为李重的动作太快了,快到谁都没有看出来就结束了。派出所的人在清缴武器的时候,防暴队的人也冲了进来。
李重突然眼前一黑,就倒在地上。
他最近闹了好几次心绞痛,但都被他忽视了,这次倒在地上的一刹那,他有些后悔没去医院看看。莲也在说他,说他早晚有一天会后悔的。他还嫌莲说话不吉利。
八
李重被送进医院,确诊心梗了,幸亏抢救及时。
他醒过来的时候,看见父亲和岳母守着他,莲在跟大夫说着什么。父亲没有说话,岳母握着李重的手哽咽了,说,你不能拿命赌啊,你现在是你父亲的最大牵挂。他平常不说什么,其实他最在乎的是你,你是他儿子。
很快,市局领导和派出所的人也走进病房,大马说,我不知道你带了两把枪,你拔枪速度太快了。李重嘿嘿笑着。小高说,我服了您了。市局领导说,你被提名市局的副局长,很快就上任了。李重說,我心脏不好,还是在派出所当所长轻松。市局领导说,我问大夫了,你就是太累了,歇歇就好了。李重摇头,问题是当了副局长我就打不了枪,破不了案子,那就把我美好的线路梗死了。
大家笑了,可李重却笑不出来。
傍晚,李重躺在病床上,看着窗玻璃上残留着一片橘红色的暮光。他渐渐有些迷糊,觉得很累很乏。莲说出去接个电话,但很久没有回来。他刚闭眼,就恍惚看见母亲躺在身边,直勾勾地看着他。他想喊母亲,可张不开口。母亲说,你别拦着你父亲和你岳母了,我认了。李重想解释,就看见母亲从窗户那儿飞走了。他知道自己是在梦里,又依稀见一个人影在朝自己移动,是一个男人,很狰狞,这个男人举着枪,对他说,我来替我兄弟报仇,说着就开枪了。李重“啊”的一声大喊坐起来,一身大汗。
等缓过来,李重下了床,没开灯,静静地站在黑暗里,他扭头看见窗外一轮月亮,白白的,像是白太阳,他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
李重走到窗户前,感受着那轮白太阳特别的温暖。
他感觉母亲就在跟前站着,而且紧紧地拥抱着他。他梗死的心脏疏通了,浑身的血像泉水一样流淌着,跳跃着……
责任编辑/张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