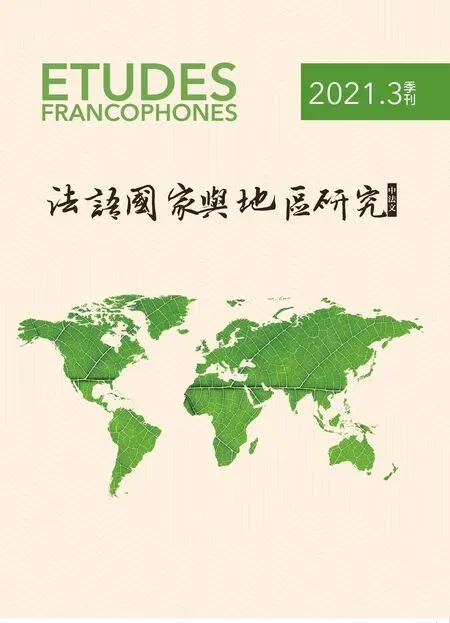布瓦洛诗学的内在品质
王 夏
内容提要 布瓦洛诗学长期以来被等同于古典主义,这种观点关注对布瓦洛诗学的生成语境和时代诉求的考量,固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了对其内在品质进行全面的考察,即忽略了对布瓦洛的人生经历、人格理想、诗学信仰与诗学观点以及古典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研究。如果对布瓦洛的人生轨迹及其作品进行参酌细读,便可发现他对古典主义的推崇既是当时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必然要求,又是其人格理想和诗学信仰与古典主义思想范式融为一体的自觉行为。这种内化于心的古典主义理性文学观,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古典主义代言人”,也使他的诗学具有一股向上向善、追求卓越的内在品质。
尼古拉-布瓦洛·德普雷奥(Nicolas Boileau, dit 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是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对古典主义的推崇是社会、历史与时代的必然选择。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17世纪法国呈现出社会混乱、却又人心思治的倾向,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成为当时历史的必然要求。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肇其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的政治整合开其势,布瓦洛的诗学建树扬其风。换一个说法,在近处看,法兰西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形成,布瓦洛诗学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远处讲,自柏拉图(Plato,前427年—前347年)以来的理性诗学经文艺复兴到17世纪,复古崇古蔚成风气,这将是欧洲思想文化的又一个亮点。追求理性、高雅、严谨、明晰、整饬、规范和简洁的古典主义风尚,在布瓦洛那里得到集中的体现。表面上看,路易十四授意布瓦洛创作《诗的艺术》(L’Art Poétique)是一个偶然事件,往深处发掘,就可以明白,布瓦洛最终成为古典主义的代言人,不仅有其时代的要求,而且有其更为内在的必然联系。布瓦洛及其诗学的问世,有古典主义标志掩映的内在特质,这正是该诗学的品质所在。本文力求剥开古典主义的标签,深入布氏诗学去领略其个中三昧。
一、理性
17世纪中叶,古典主义进入了发展的繁荣时期,笛卡尔理性哲学备受推崇。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论确立了“思想”与灵魂的主体地位和“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决不把它当成真的东西”的信条开启了理性文学的新时代。他那套从简单到复杂、从特殊到一般,分析与归纳结合,注重次序和“正确地运用才智”①笛卡尔.《谈谈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9.的方法成为17世纪法国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文艺现象的方法。“直到17世纪中叶,法国作家要想有条不紊地处理较大的题材,从中得到一点可靠的知识,他面前唯一可以采用的方法就是笛卡尔的方法”②朗松.《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271.。同时,笛卡尔对真善美的认识也转化为古典主义对文艺创作和评价的要求和准则。③朱立元.《西方美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169.求知、理性和批判成为17世纪的时代精神。虽然笛卡尔学说曾遭受多次的查禁与压迫,但最终却把法国17世纪后半期变成了“笛卡尔的世纪”④施璇.《笛卡尔学说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的遭遇——对笛卡尔圣餐变体论思想的一个哲学史探讨》.哲学动态,2016(4):68.。因此,笛卡尔哲学在17世纪后半叶得以广泛流传,并占据主导地位。著名的法国文学史学家朗松(Lanson Gustave,1857—1934)指出,“在1650年出生或者受教育的人,则在正当年的时候接受了笛卡尔的影响”。⑤朗松,前揭书,第253页.毫无疑问,对于在笛卡尔科学理性主义的浪潮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布瓦洛而言,耳濡目染,自然对笛卡尔思想有所涉猎,他是文学理性主义的拥护者。
在《诗的艺术》中,布瓦洛教导诗人们“首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布瓦洛 2009:5)在布瓦洛那里,理性就是笛卡尔所言的“那种正确地作判断和辨识真伪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是人人天然的均等的”。⑥笛卡尔.《谈方法》.载《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62.然而,很多人对布瓦洛的“理性”提出质疑。“他受到笛卡儿主义的影响不多,以至于梅和(Méré)说他只是‘笛卡尔的一个小学生’。”(Boileau 1966 : XVI)安东尼·亚当(Antoine Adam)这样说道。朗松也曾经指出,布瓦洛的“理性”并不代表笛卡尔思想“可以区分、明晰的、属于纯粹心智”的概念。“他在诗中呼唤理性,但归根结底,却没有关于‘理性’的确切的定义,而只有形象的相似性。”⑦Luc Fraisse.« La littérature du XVIIe siècle chez les fondateurs de l’histoire littéraire ».Dix-septième siècle, 2003, 218 (1) : 23.朗松对布瓦洛“理性”的批判直接触及古典主义的空想和说教性质。但如果我们把视线稍微放远点,不局限于古典主义的“法典”——《诗的艺术》,看一看布瓦洛的其他作品⑧这里指除《诗的艺术》之外的布瓦洛的其他作品,如《论蒙娜丽莎》(Dissertation sur Joconde)、《讽刺诗》(Satires)、《唱经台》(Le Lutrin)、《诗体书简》(épitres)、《讽刺短诗》(épigrammes)、《传奇英雄的对话》(Dialogue des héros de roman)、《读朗吉努斯感言》(Réflexions sur Longin),法语译本《论崇高》(Traité du Sublime)以及致友人的信札等作品。在国内,目前除了《诗的艺术》,布瓦洛的其他作品并无完整的中文译本,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对布瓦洛诗学的研究与接受。,我们就会发现,朗松的这种批判难免有些过于牵强和苛刻。
布瓦洛对“理性”(la raison)的理解,源于笛卡尔思想,是对哲学的“理性”的移花接木。既然换了生长的“土壤”,其供养(阐释的方式)的方法必然不同。布瓦洛诗学中的“理性”自然不可能是前者的照搬,也不可能完全作为科学推理的抽象概念,而强调的是一种审慎、克制的尺度,一种判断是非、鉴别善恶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还指向一种符合当时社会理想的意识规范、甚至是从经验所得出的常识常理。它在表现形式上决定了诗歌语言的明晰、规范、简洁性要求和用韵、选词以及情节安排等环节的严谨与合式性原则,在思想内容上决定了诗歌的高雅旨趣和伦理导向。理性之于布瓦洛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既是他的诗歌主张,也是其人生的信仰与追求。
他对于理性的追求最初并非来自《诗的艺术》中的“理性”观,而是来自社会和生活所激发的“理性”意识,即对是非、善恶的判断态度和情感寄托。布瓦洛成长于文艺复兴之后,法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年代。当时社会一方面深受文艺复兴的影响,复古崇古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也面临人性解放后随之而来的思想混乱与迷茫。布瓦洛自小就表露出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浓厚兴趣,尤其推崇荷马(Homère,约前9世纪—前8世纪)、朱韦纳尔(Juvénal,1—2世纪)、贺拉斯(Horace, 前65年—前8年)等古代诗人,并对马莱伯(François de Malherbe, 1555—1628)、拉康(Honorat de Bueil, seigneur de Racan,1589—1670 )或受神灵启示的人满怀敬仰,学习他们的职业操守和尊严,“十五岁起见坏书就觉恶心”(布瓦洛 2010:92)。在目睹人性和社会的诸多混乱与衰败之后,他毅然决然放弃家庭为他铺就的神学和法学之路,立志学习古代伟大的诗人,致力于讽刺诗以改良社会道德。这种基于是非、善恶观的“理性”意识最终成为布瓦洛的人生信仰和追求。在他看来,理性抵制愚昧和无知。从对粗俗、虚伪、贫穷的批判,到对妇女和婚姻的厌恶;从对“无知医生”的控诉,到对愚昧的人类的痛惜,他的一生始终在追求理性。甚至在他垂死之际,他仍然对“这个愚昧的时代”感到遗憾:“离开生命,我没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每天都在产生更多的愚昧。”⑨伊莎贝尔·布利卡.《名人死亡词典》.陈良明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60.
在讽刺诗中,布瓦洛以诙谐嘲讽的口吻控诉人类的愚蠢、无知、贪婪和迷茫。《多样化诗歌和讽刺短诗三十三:致医生》(Poésies diverses et Epigrammes XXXIII : A un médecin)中的诗句“从无知的医生变成灵巧的泥瓦匠”(Boileau 1966 : 254),虽然隐射的是不自量力的克罗德·贝洛(Claude Perrault,1613—1688),但也流露出布瓦洛对“无知”的痛恨。因为夺去他的至爱伊和斯(Iris)幼小生命的真凶就是那些“无知的医生”。
在《讽刺诗四》(Satire IV)中,布瓦洛致信勒瓦耶(Le Vayer)神父,他用讽刺的口吻说道:“理性通常是我们所有不幸中最糟糕的事情,它与享乐为敌。讨厌的后悔呀,前来克制我们的欲望。”(Boileau 1985 : 85)类似的批判同样出现在《讽刺诗五》(Satire V)中,布瓦洛致信勒·马古斯·德丹戈(Le Marguis de Dangeau),谈论崇高与荣誉:“一种毫无意义的愚昧麻醉着理性,悲伤而可耻的荣誉不再合时宜” (Boileau 1985 : 88)。愚昧成为崇高与荣誉的绊脚石。《讽刺诗八》(Satire VIII)笔锋一转,直接批判人类的愚昧:
但是人类呢,不停地进行非理智的赛跑。思想不停地漂浮。他的心灵,总是浮于众多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也不知道他不想要什么。有一天他厌恶的一切变成他希望的一切。(Boileau 1985 : 98)
在布瓦洛看来,人类所做的这些“非理智”的行为以及漂浮不定的内心都源于理性的缺失。他赞同诚实的道德和文明的风俗,实际上是在呼唤理性。因为理性与“非人性”的粗俗相对,意味着克制、法律和礼节:
让人们看看这些诚实的道德和文明的风俗吧。统治者、大法官和国王让人们观察礼节,服从法规。这是真的。但是没有法律就没有礼节,也就不用畏惧警务人员、修道院的院长和司法的帮凶。人们看见这些凶狠的狼群,是否就像非人性的我们打劫那些跑遍各条大道的狼群一样?(Boileau 1985 :100)
在《讽刺诗十》(Satire X)中,布瓦洛表达了布瓦洛对妇女和婚姻的厌恶之情。他批判妇女的傲慢无礼和奴役男性的态度。在感叹妇女由婚前温柔的天使沦为粗暴无礼的魔鬼后,布瓦洛写道,“然而她曾经在圣西尔寄宿学校⑩原名Saint-Cyr(la maison de Saint-Cyr),指由德·曼特农女士(Madame de Maintenon)为保护和教育在上流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年轻女子而建立的机构——圣西尔寄宿学校,位于凡尔赛附近。受到了理性的沾溉”⑪布瓦洛这里并非讽刺当时王港修道院(Port-Royal)和圣西尔寄宿学校(Saint-Cyr)对年轻女子实行的严厉、清戒的教育,事实上他对德·曼特农女士教育年轻女子的行为赞赏有加。他旨在表明对女性普遍存在的自负、任性、爱慕虚荣、贪图享乐、放纵等缺点以及婚姻的批判,并认为这些固有的缺点可能战胜她们在修道院的所受的“理性”教育。在《讽刺诗十》的序言中,布瓦洛表明了他写诗反对妇女的初衷:“事实上,我在《讽刺诗十》中所描绘的这些画面是如此普遍,因此我并不惧怕妇女们被触怒。”(Voir : Nicolas Boileau.Œuvres complètes.Paris : Gallimard, 1966.p.62—63.« Mais au fond, toutes les peintures que je fais dans ma satire sont si générales, que bien loin d’appréhender que les Femmes s’en offensent.»)布瓦洛在《讽刺诗十》写道:“你娶的妻子,行为无任何约束,据说在王港修道院,她被教育遵守伦理道德,用义务、法则规范和克制她的欲望,但谁能向你保证,她能战胜享乐?”(Voir : Nicolas Boileau.Œuvres complètes.Paris:Gallimard, 1966.p.66.« L’épouse que tu prends, sans tache en sa conduite / Aux vertus, m’a-t-on dit, dans Port-Royal instruite / Aux lois de so n devoir règle tous ses désirs.Mais qui peut t’assurer, qu’invincible aux plaisirs.»(Boileau 1985 : 132) 。这是解开布瓦洛对待妇女态度的锁钥。真相就是:布瓦洛对妇女的顽疾感到失望,但她们并非布瓦洛最终批判的对象,隐藏于这些问题中根深蒂固的野蛮人性和无理性才真正令诗人深恶痛绝。
总体看来,布瓦洛对无知与愚昧的批判与他在文学思想上对“理性”的恪守是统一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在文艺领域的投射,二者都源自对“完美”人性的期望。布瓦洛对“理性”的理解融入了他自身的人生体验,一方面,幼年丧母、身体羸弱、恋人伊和斯夭折等悲惨遭遇使他的性格忧郁、敏感,渴望幸福,信奉伊壁鸠鲁学说;另一方面,布瓦洛受到冉森派的思想影响,他与冉森派领袖阿尔诺(Antoine Arnauld, 1612—1694)和出生于冉森派家庭的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悲苦的经历与相对自由和包容的宗教态度使他对社会和人性的理解更加深刻。也许这种感悟未能达到形而上的思辨的高度,但却丰富了理性的内涵,甚至助推了他在文艺领域对理性的恪守和执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布瓦洛诗学中的“理性”是文艺与社会的共同问题,其多义性统一于古典主义以艺术的理性化寄予人类的最高理想,即“通过恢复秩序,进而恢复由于人类堕落而遭到破坏的人性。”⑫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0.正是如此,当浩浩荡荡的“厚今派”以“进步论”的申讨声袭来,布瓦洛并未一味膜拜今人的进步,而是以他对“理性”的独特理解,坚信理性对培植人性的重要意义,在“古今之争”中守候着古代的价值。“他不像18世纪的唯理主义者一样相信社会的不断进步,也不承认人类精神的跌落。”⑬John Richardson Miller.Boileau en Fr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Paris : Les Belles Lettres, 1942 : 78—79.
二、真实
在布瓦洛的诗学中,“真实”(le Vrai)是一个关键的字眼。真实崇尚“自然”,是布瓦洛在文学创作中坚守的信念。他所谓的“自然”指的是人性,是“逼真性”(la Vraisemblance),即艺术创造的逼真,而非客观世界的真实。
“切莫演出一件事使观众难以置信:有时候真实的事很可能不像真情。我绝对不能欣赏一个背理的神奇,感动人的绝不是人所不信的东西。”(布瓦洛 2010:33)“逼真”意味着艺术形象必须符合常理常情,是“人们所信”的事物。这就要求艺术创作者要依据理性进行虚构、加工、删节“稍涉荒诞”的、“读者自己不信”的东西。他对文学对象和创作过程遵循真实的要求说到底还是其文学“理性观”的延伸。在这种文学“真实”观的导向下,想象、虚构和情感就必须让位于理性,甚至有可能导致朗松所说的“简直有点可笑的逼真”、“刻意而忠实的”,不带任何感情的“现实主义”倾向⑭朗松,前揭书,第348页.。他反对绝对的真实,要求作家要“艺术地摹拟”真实。
不但对创作对象要求“真实”,而且对文学的创作主体,布瓦洛也要求“真实”。只是这种真实不是“艺术的摹拟”的逼真,而是“内心的真诚”。在《诗体书简》(Epîtres)中他写道,“没有比真更美了,只有真才是可爱。”(布瓦洛 2010:101)在《诗的艺术》中,他不惜重言“只有真才能算美,只有真才得人怜,并能长久得人怜。”(布瓦洛 2010:106 )他要求作家首先对自己真诚,有自知之明,正确衡量自己的才华和实力;其次在接受批评时不能做执迷不悟、为自己辩护的“傻子”;最后要求写悲歌要表达自己内心思想,避免“违心之论”。因为“如果内心不真诚,才调易使人厌倦”(布瓦洛 2010:106),还因为“作品反映品格和心灵”。正是这种“文如其人”、道德文章一体的认知模式使布瓦洛对创作对象和创作主体的“真实”要求达成统一。
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布瓦洛而言,真实是绝对的,与虚伪和欺骗相斥。在《讽刺诗十一》(Satire XI)中,他认为:
世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剧院。在那儿,每个人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彼此互相欺骗,他们所演的角色通常和自身相反。(Boileau 1985 : 143)
这种对虚伪人性的否定促使他开始思考真正的“荣誉”:“唯一坚固的荣誉就是始终以真实作为向导,就是对一切事物都重视理性和法规,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是完成所有上苍启发我们的善行, 总而言之就是保持公正。”(Boileau 1985 : 146—147)同时也激发他不断追求“自由的真理”。在《诗体书简五·致德吉列拉格先生》(Epîtres V: A M.De Guilleragues)中,布瓦洛写道,“自由的真理是我唯一的追求”(Boileau 1985 : 188)。
在所有人都在为国王“荣誉”讴歌的17世纪,布瓦洛却执着地追求着他所热爱的真理和正义,在思想上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在颂诗和讽刺诗之间,他坦言自己没有写颂诗的才能;在做史官期间,他深知“真实难求”,选择了“只忠实于诗歌”;在以异教徒为敌的国教统治下,他坚定地保留对冉森教派的好感,无论是抗议危险信仰和天赋谎言的冉森派作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为宗教事业疲于奔命的冉森派领袖阿尔诺,还是与冉森派纠缠不清的伟大作家拉辛,都是他尊敬的人。除此以外,《诗体书简五·致德吉列拉格先生》中对自己前后期创作的总结,《致法兰西学院院士贝洛先生函》(A M.Perrault,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中与贝洛的亲切交谈,《友谊之信——1687—1698年间的通信》(Lettre d’une amitié-Correspondance 1687—1698)和《致布霍斯特的信》(Lettres à Brossette)中平常而真挚的情感,《诗体书简》中那个乐于在奥特伊(Auteuil)生活,在那儿热情接待朋友,与园艺师亲切交谈的平实的老人,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位严肃的诗人真诚的心灵。无论是他对文学道路的选择,对安静和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向往,还是对冉森教派的好感与欣赏,无不体现出他的真实。这种真实也许带有“不迎合别人而牺牲自己利益”(Boileau, Racine 2001 : 248)的实用主义特征,但它却是特殊时期对自我的一种解放,是布瓦洛对人生的一种彻悟与热爱,更是一种王权至上的社会中“极其艰难的坦诚”(Boileau 1966 : XXVII)。纵观布瓦洛不平凡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真实”已经内化为一种人格理想,成了他的人生准则和行为规范,或者说,布瓦洛的人生,就是真实的典范。
尽管“真实”在布瓦洛诗学中呈现出多种义项,它并非完全是本体论层面的“真实”。对于布瓦洛而言,“真实”是“艺术的摹拟”,是“内心的真诚”,是善行,是公正,也是自由。但透过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表层,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其中连接的纽带,即真善美合一。这就是“真实”的力量。提倡文艺作品的“不真实”(虚构和加工)是为了“使真理闪闪发光”;呼吁作家的内心“真实”是为了有“反映品格和心灵”的作品;反对社会的虚伪是为了“保持公正”和“求善”;追寻真实的内心,是为了“追求自由的真理”。由此可见,布瓦洛尚真诗学观与其对社会伦理之真的思考以及真诚的人生哲学之间实现了融合,共同体现了以“真善美”为信念的古典主义诗学逻辑。
三、至善
安东尼·亚当(Antoine Adam)曾说:“布瓦洛全身心地喜欢法国传统和重视道德的、严肃的、有点悲伤的基督教主义,它曾经是帕斯卡尔和博叙埃的基督教主义。”(Boileau 1966 : XXV)诚然,宗教与道德的关系是神学界和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探求布瓦洛诗学的内在品质中不可忽略的一个考察点。
布瓦洛的一生与宗教关联甚密。布瓦洛的哥哥雅克致力于神学事业,受其影响,布瓦洛曾经很想进入教堂,并于1662年接受了剃发礼,几年后获得博韦(Beauvais)教区的隐修会会长一职。也因哥哥雅克的关系,布瓦洛经常接触很多知名的神父。对于从小生活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环境里的布瓦洛来说,“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观念早已深入内心。基督教的道德律令规定了上帝作为至善的化身,是基督教世界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审判者和立法者。尽管基督教主张原罪说,但“罪恶从属于善良。在永恒的对立中,恶与善并非是两种均衡的力量,善在本体记(原文如此,疑为“本体论”)上处于优先的地位;而恶是对善的否定,是对宇宙万物的本来目的的破坏。”⑮查尔斯·L·坎默.《基督教伦理学》.王苏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74.这种“性善论”的优先性使布瓦洛这样的基督徒始终相信善可以胜过恶。面对糟糕的社会道德,他仍然坚持改良的愿望,仍然践行着博爱的教义观。他自愿在1699年拉辛逝世后照顾他的妻儿,并在1711年逝世后立下遗嘱,规定财产的受益人除了他的家庭成员外,还有侍者和堂区的穷人。
尽管神学贯穿布瓦洛的一生,但他最后的阵地却不是神学,而是文学。他立志用文学改善社会道德,但宗教伦理却不曾在其作品中缺场。在诗体书简和讽刺诗中,对上帝的爱经常是他不忘表达的思想。在《诗体书简十二》(Epîtres XII)中,他写道:“人类,作为上帝唯一好的、可爱的作品,他应该爱这个上帝,他真正的父亲吗?/最刻板的作者也敢确定这是事实。”(Boileau 1985 : 223)
上帝是支配“世界的主人”, 是“连接信仰、美德和圣事的唯一纽带。”(Boileau, Racine 2001 :248, 251)爱至善至美的上帝,这是布瓦洛诗歌中的宗教宣言。这种忠诚把宗教之善交织在文学作品中,并把它引向绝对的理性化。
布瓦洛诗学的这种至善品质是他的宗教信仰与诗学信仰融合的一种体现。这在17世纪并不奇怪。因为在那个年代,上帝是哲学、神学与文学的盟友,是唯一的、绝对的、至善至美的象征。因此,布瓦洛诗学的这种宗教式的向善的维度与其理性的哲学思想并不构成冲突。基督教神学对于布瓦洛这样一个文学思想家而言,不是反面阻碍,而是动力之一。笛卡尔哲学不是也在其理性之中交织着神学底色吗?正是如此,笛卡尔哲学的“理性”可以让人选择善,并与神学至善的信仰统一。布瓦洛诗学有理性,其理性也有基督教神学的深层支撑。这是他们那个时代文化人的真实的精神世界。
四、崇高
“上帝说:要光明形成,光明就形成了。”《旧约·创世记》(l’Ancien Testament: La Genèse)中的这句话多次出现在布瓦洛的《论崇高》(Traité du Sublime)的法译本序言和《读朗吉努斯感言》(R éflexions sur Longin)中,用来论证崇高。布瓦洛认为朗吉努斯引用这个例子,“把造物界对造物主的那种服从,标示得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崇高,并且有点神的意味呢”。(布瓦洛 2010:195)造物主是谁?何谓“神的意味”?对这些问题的深究必然让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崇高论的哲学基础在于以至善至美的上帝为世界的本体。
这种基于神学本体论的“崇高”对于人类及其活动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论崇高》第29章,布瓦洛这样翻译:
大自然并未把人类看作一个低级和卑微的动物,而是赋予他生命,把他带到这个就像盛大聚会的世界,让他做造化万物的观光者。我说,它还把他引入只有一个勇敢的雅典人才应该感受到的荣誉的乐趣中。所以它一开始就在我们的心中植下一种不可抗拒的热情——对一切似乎比我们更伟大、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因此,对于人类思想所及的广度,整个世界也不够宽广,我们的思想所能达到的深度往往比天空还要深远,它能潜入更深的周围界限,并邻接所有的事物。(Boileau 1966 : 389)
对人类境况的认识,在于强调人并非卑贱之物,有待不断地完善,寻求超越。在布瓦洛看来至善至美、万能至上的神和上帝,就成为了人的心灵追求超越的对象和行为的典范。这种建立在神学本体论基础上的崇高就必然促使人摒弃卑鄙的陋习和卑微的心灵,向往和追求与上帝一样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⑯田英华.《朗吉努斯、博克、康德论崇高》.兰州学刊,2007(6):157.这意味着崇高的哲学基础为人类的一切思想、活动和行为都提出了可以参照的范本,文学本身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对于布瓦洛而言,文学本身就代表崇高。在《诗的艺术》第四章,布瓦洛追述了人类由野蛮暴力到文明和谐的演变历史。在他看来,诗歌传达了神的旨意,并建立了人类的文明秩序。因此,他高呼:“巴那斯多么崇高!”(布瓦洛 2010:3)由此看出,在很大程度上,崇高的神学本体论性质规定了文学追求卓越的品性。在此基础上,文学的高雅旨趣和伦理导向就成了题中之义。
首先,崇高意味着思想高尚和情感高贵。因为在崇高形成的五个因素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能使我们成功地思考的某种高尚的思想”(Boileau 1966 : 349),而且这种“高尚思想是伟大心灵的反映”(Boileau 1966 : 351)。因为“一个真正的演说家所必须具备的首要品质是他绝对不能拥有平庸的思想。事实上,一个生活中只有卑鄙、琐屑的情感和倾向的人,不可能产生值得后人尊崇的、杰出的思想。”⑰Longin.Traité du Sublime.Paris :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95, p.84.这是为什么布瓦洛不论在创作论,还是在批评论中都格外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的原因所在。一方面,布瓦洛反复提醒作家,“你只能示人以你的高尚小影”(布瓦洛 2010:62),“你要‘爱道德’(Aimez la vertu),使灵魂得到修养”。(布瓦洛 2010: 63)“我要求讽刺诗中作者如璞玉无瑕,绝不容无耻之徒也跑来侈谈风化。”(布瓦洛 2010: 28) 另一方面,布瓦洛又规定作品内容讲求理性,不违背道德和荣誉,不涉及荒诞、卑污和粗俗。在《传奇英雄的对话》(Dialogue des héros de roman)的序言中,布瓦洛坦言,他年少时也读斯居代利小姐⑱的小说,但最终却发现它们与理性相悖,极其幼稚(Boileau 1966 : 445);他批评斯居代利小姐的小说所传达的“糟糕的道德”(Boileau 1966 : 445);他教导诗人“好好地研究宫廷,好好地认识都市”(布瓦洛 2010:54),在对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和拉辛的戏剧问题上,布瓦洛表现出对高乃依的崇高由衷的赞许,虽然他也肯定后两者的艺术成就,他忍不住要抱怨莫里哀“太爱平民”(布瓦洛 2010:54),拉辛写爱情太多,认为“它们(以感情为主题的戏剧)引起了灵魂的混乱,败坏了道德风尚。他欣赏拉辛本人胜过作家拉辛”⑲。因为高乃依的崇高最能体现“思想的崇高”(布瓦洛 2010:200—201),是理性的崇高。
其次,崇高意味着超越和完美。像朗吉努斯一样,“谈着崇高,他自己也就很崇高”(布瓦洛2010:189),这是布瓦洛的人格理想。“他的见解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不但标志一种崇高的才思,还标志出一个超群绝伦的灵魂。”⑳(布瓦洛 2010:192)在肯定了朗吉努斯兼具“君子的性格”与“崇高”的才思之后,他表达了自己崇拜朗吉努斯,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的强烈愿望。这种强烈的愿望逐渐演化成一种超越低俗和丑恶的诗学理想。为此,布瓦洛立志“用讽刺诗改良道德风尚”,他放弃了家庭为他铺就的神学和法学之路,选择了讽刺诗这个“倒楣的行业”(布瓦洛 2010:90);他不畏权贵,抨击诗坛的不正之风;他孜孜以求,坚守“崇高的巴那斯山”(布瓦洛 2010:3)。
这种以“思想的崇高”为导向的诗学理想最终与其人格理想融为一体,“崇高”论的超越性既成为其诗学思想的归宿,又成为布瓦洛践行“古典”的目标。
“古典”是布瓦洛追求的文艺风尚。无论是他的诗学思想,还是他在古今之争中的表现,都与“古典”休戚相关。“古典”的“古”和“典”两个义项包含了布瓦洛诗学中的两个关键点:一是以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家作品为典范,二是趣味典雅。布瓦洛崇古、习古、追求高雅的文艺趣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可朗吉努斯的崇高论。
这位哲学家教给我们另外一种途径。如果我们根本不想忽视它的话,它会引领我们走向崇高。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这就是对生活在我们时代以前的杰出诗人和作家的模仿,并与他们展开竞争。这是我们总应该引起注意的目的。
朗吉努斯的这一观点与布瓦洛的“古典”情结极为契合,也为他崇古的主张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崇古成为走向崇高的有效途径。
在《致布霍斯特的信》中,布瓦洛再次阐明了崇古的最终目的:“您会从中发现力量和温和,对古人的崇高的模仿,为了你能了解我们的学院尽可能地反对这个世纪的坏趣味。我们所有人会支持古代。”
由此可见,崇古是为了反对坏趣味,从而建立典雅的趣味。布瓦洛要求诗人研究“宫廷和城市”,以上流社会考究、简洁、明晰、严谨的语言作为最高标准,同时排斥一切粗鄙的思想,通过这样形式和内容上的规定以接近和达到“思想的崇高”。
正是这样,“崇高论”最终促成布瓦洛的诗学思想和批评原则与古典主义的文艺取向之间的高度统一,后者的理性、节制、简洁、明晰、高雅等要求经布瓦洛的演绎之后,表现为具有伦理导向和高雅旨趣、思想性强的文艺思想。
结 语
追求卓越与完美是布瓦洛诗学世界的内在精神。无论是对无知与愚昧的批判,还是对社会伦理、文学之真、宗教至善和崇高思想的体悟,都源自他对完美人性和纯净诗坛的美好期许。换言之,他以真美善的信念追求崇高,体现了捍卫和坚守文学理想的责任和担当。他对古典主义思想的理解融入了他自身的人生体验和诗学理想,并将之作为一种精神范式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和理性的思考之中。其诗学集中体现了理性哲学、宗教至善、诗学信仰与其人格理想的高度融合。作为古典主义的旗手,布瓦洛推崇的是以理节欲的、较为刚性的文艺取向,这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是以往将布瓦洛诗学与古典主义等同的主张所持的依据,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古典主义与布瓦洛人格理想和诗学信仰的高度契合,这种契合更加凸显了其诗学的古典主义特征,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古典主义代言人,也使其诗学具有一种理性、向善和超越的内在品质。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规律在布瓦洛精神气质中的“这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