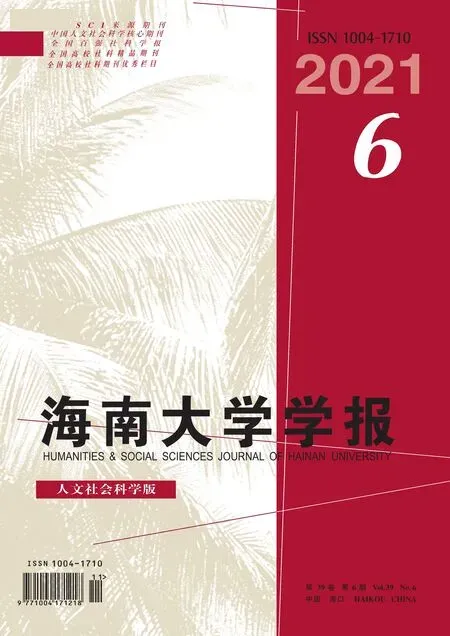炼成与消隐:老舍风格化文学语言
徐仲佳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风格化文学语言是老舍在文学场占位的主要资本之一。老舍被奉为语言大师,主要是缘于他在文学实践中表现出对北京方言的纯熟化应用:“老舍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把北京话中的精华锤炼成具有特色的文学语言,既有浓烈的京味儿,又合于规范的汉语语法,既有自己的风格,又能让全国的读者读得兴味盎然。”①苏叔阳:《北京话与“文学语言”和老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04页。梁实秋认为:“我最初读老舍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二马》,未见其人,只觉得他以纯粹的北平土语写小说颇为别致。……我之所以注意老舍的小说者尽在于此。”②梁实秋:《忆老舍》,见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3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梁实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苏叔阳15岁入京,二人都对北京文化十分熟稔。他们称道老舍文学语言中的北京风味应该是有说服力的。风格化的文学语言是一个作家特征性的话语系统。这种特征性话语系统一经形成就会成为作家稳定的、区隔性最好的资本。
一、“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老舍语言大师地位之确立
初进文学场的老舍没有建立风格化语言资本的自觉。在《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中,“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处”。老舍希望借这种文白“夹裹”达到幽默的效果:“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帮助一些矛盾气,好使人发笑。”此时,幽默是老舍着意建构的文学资本,文白夹杂是其工具。白涤洲最早指出《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中的文白夹杂是“讨巧”。不过,老舍当时还没完全理解文白夹杂的不利之处,反而把它当作是提高白话地位,使之雅俗共赏的工具:“我当时还不以为然,我写信给他,说我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话里,以提高白话,使白话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③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白话文的合法性是文学革命胜利的标志之一。很显然,老舍此时对于文学语言的理解还没有达到新文学场共识的高度。
当然,作家只要进入了文学场,文学场共识就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规范着他。语言问题常常成为文学场占位斗争的焦点。老舍进入文学场的时候,经过文白之争,白话文的合法性已经确立起来了。不过,白话文并没有一统江湖。在当时权力结构多元的社会里,文学场的信仰也是多元的。老舍自称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赵子曰》就是旁观者的产物④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168页。。作为一个“旁观者”,老舍对于新文学阵营的激进主义文化策略也许并不怎么佩服。不然,他也不会在《赵子曰》中将学生当作挖苦的对象。这一态度也体现在老舍的语言策略上。他为“文白夹杂”辩护就是这种语言策略的体现。
白话文的合法性是政治场与文化场同构的产物。政治场的除旧布新是文学场“弃鬼话、取人话”的最根本理据,因此,它是难以动摇的。新旧的区隔显然要比雅俗的区隔具有更多的权威性。在新文学场规范面前,老舍的“文白夹杂”很快就被视为“违规”而挑出来。朱自清在评价《老张的哲学》《赵子曰》时认为它的文笔“近于‘谴责小说’”:“老舍先生的白话没有旧小说白话的熟,可是也不生。只可惜虽‘轻松’,却不甚隽妙。”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中,朱自清有意将这两部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相类比,而没有将它们视为与《阿Q正传》相类似的现代小说,其原因就是“文白夹杂”。只是在谈到《赵子曰》的悲剧结尾时,朱自清才将其“严肃的收场”视为“异于‘谴责小说’而为现代作品了。”①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见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29-730页。因此,老舍最初的“文白夹杂”虽有意使白话文雅俗共赏,但它与文学场的规范相悖。对于一个后来者来说,这可不是好事。
作为后来者的老舍不可能不意识到语言的重要作用。在《我怎样写〈二马〉》一文中,他正面阐述了他在《二马》写作时对“文字风格”的自觉追求:“《二马》的细腻处是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里找不到的,……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随着年纪而往稳健里走,可是文字的风格差不多是‘晚节渐与诗律细’的。读与作的经验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老舍所说的《二马》中对“文字的风格”细腻、“形式之美”的追求,就是对《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的自觉区隔。当然,老舍在创作《二马》时对小说“文字的风格”的追求也许并不像他在1935年追溯时那样清晰。下面的说法可能是事后的自我加冕:“所谓文艺创作不是兼思想与文字二者而言么?那么,在文字方面就必须努力,作出一种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在《二马》中我开始试验这个。”②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1-173页。
老舍1935年突出《二马》文字风格的区隔性,是与他对风格化语言资本的自觉有关,也是文学场语言规范塑造的结果。文白之争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场已经形成的共识,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新的占位斗争:一面是国民政府尊孔读经带来文言文重张势焰;一面是左翼阵营提倡“大众语”,挑战“五四”白话文。汪懋祖在1934年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与《中小学文言运动》两文,提倡文言文。汪懋祖的立论逻辑与国民政府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是一致的。其核心是试图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转化,以应对新的时代命题,“在隐性层面,还有加强思想统治的追求。”③黄道炫,陈铁健:《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因此,汪懋祖的言论被新文学场视为政治场思想统制的代言。这不能不引起强烈反弹。五四运动之后的十余年间,白话文不仅在文学场确立了地位,而且在政治场中也无可替代地扩展开来。官方文告、法律文件等大多使用白话文表述。因此,这场论争中的文言文已经是一只死老虎。
20世纪30年代的语言占位斗争,除了胜负已分的文白之争,另一个焦点是“大众语”讨论。“大众语”讨论1934年正式开始,由非左翼的陈望道等人发起,似乎政治色彩不是特别鲜明。事实上,“大众语”的合法性在之前左翼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就已经出现了④王瑶:《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40页。,而且其中的政治场干预痕迹十分明显。据刘丹丹考证,瞿秋白1929年在苏联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包含拉丁化中国字的方案和写法规则。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针对华工的扫盲运动中,它被认为是一份很理想的解决方案。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和以拉丁化字母扫除远东华工的文盲的决议案⑤刘丹丹:《拉丁化新文字及其运动》,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2-23页。。这一决议带有鲜明阶级斗争的色彩。首先,决议认为文言“是中国统治阶级的言语”。这种“特权者的言语,成了中国劳动群众普遍识字的‘万里长城’”。其次,“大会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国语统一运动’。所以不能以某一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的标准音。”⑥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版,第54-55页。显然,共产国际把大众语的推行视为其阶级斗争之一翼。据焦风回忆,国际作家联盟曾经有决议,要“左联”“坚决地实现中国话写作拉丁化”。虽然“左联”当时并没有接到国际作家联盟的这一决议⑦焦风:《三十年代中国世界语者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一点回忆》,《文字改革》1963年6月30日Z1版。,但在其后的“大众语”讨论中,其阶级斗争逻辑却贯穿其中。如瞿秋白把“五四”以来的白话称为“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士大夫的骡子话”,主张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普通俗话”来写“大众文艺”。瞿秋白所说的“普通俗话”是无产大众在“‘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交流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普通话”,是“各地方土话的相互让步”的结果①史铁儿(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1932年4月,第14页。。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语”讨论的逻辑在当时获得了社会领域的大量认同。夏丏尊虽然不是色彩鲜明的左翼人士,但他所设想的语言改造途径与瞿秋白十分相近:“用词应尽量采取大众所使用的活语。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尽量地吸收方言。凡是大众使用的活语,不论是方言或是新造语,都自有它的特别情味,往往不能用别的近似语来代替。……放弃现成的大众使用着的活语不用,故意要用近似的语言来翻译一次,再写入文中去,这就是文言文的毛病。白话文对于这点虽经痛改,可惜还没有痛改得彻底,结果所表达的情意还不十分亲切有味。”②夏丏尊:《先使白话文成话》,见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上海:启智书局1934年版,第73-74页。这表明,“大众语”的合法性已经成为普遍共识。这也许是对国民政府复古、专制的反弹。
《二马》是老舍风格化语言实践的开端。“我试试看: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言语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话,让我代他来试试。什么‘潺湲’咧,‘,‘凄凉’咧,‘,‘幽径’咧,‘,‘萧条’咧……我都不用,而用顶俗浅的字另想主意。倘若我能这样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则宁可不去描写。这样描写出来,才真觉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说出;用文言拼凑只是修辞而已。……我以为,用白话著作倒须用这个方法,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文言中的现成字与辞虽一时无法一概弃斥,可是用在白话文里究竟是有些像酱油与味之素什么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儿。”③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2-173页。老舍这一段关于《二马》语言选择的追述包涵着当时文学场文白之争、“大众语”讨论的规范:对文白夹杂的自觉贬抑,对洋车夫言语(大众使用着的活语言)的自觉追求等。
但是,老舍并没有将自己的风格化语言实践与“大众语”讨论联系起来,而是将其视为共产国际所反对的“国语运动”的产物。当时“北平国语运动盛行”引导他的《二马》“尽量将白话的美,提炼到文字中”。个人机缘则是“几位干这运动的朋友”④老舍:《读与写——卅二年三月四日在文化会堂讲演》,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从《猫城记》(1933年)中所表现出的对阶级革命的隔膜出发,我们有理由怀疑,老舍的追述可能有故意与左翼的“大众语”讨论相区隔的意图。不过,老舍最具风格化语言特征的作品如《离婚》《骆驼祥子》与“大众语”讨论几乎同步出现,且具有一定的同构性,这确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的现象。
《离婚》《骆驼祥子》是老舍自觉以北平口语为主干的风格化语言实践的成功之作。其中的自觉是鲜明的:“既决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地决定了文字要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因为要求平易,我就注意到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板。恰好,在这时候,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在平日,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现在,有了顾先生的帮助,我的笔下就丰富了许多,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因此,《,《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⑤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在这一段自述中,老舍对《骆驼祥子》的语言所做的评价:“亲切、新鲜、恰当、活泼”,可以看做老舍对“活的”语言这一区隔性资本的自信与认可。
几乎与此同时,文学场对老舍文字风格的加冕也出现了。1936年9月《骆驼祥子》开始在《宇宙风》连载。一个月后,叶圣陶即撰文揄扬这部小说的语言具有独特的风格:“老舍先生文章的风格,第一,从尽量利用口头语言这一点上显示出来。现在虽然大家在写语体文,真能把口头语言写得纯粹的还是不多。……老舍先生特别注意到这方面。……他是从纯粹的口头语言出发。再进一步,在气势与声音上,在表现意思是否正确显明上费心血,使文章不仅是口头语言而且是精粹的口头语言。这就成为他的风格。”⑥圣陶:《老舍的〈北平的洋车夫〉》,见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3-654页。叶圣陶对老舍风格化语言的区隔和上引老舍的自我评价有着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性来自于文学场的规范。文学场的加冕是老舍成为语言大师的决定性步骤,反过来它也会深刻地塑造作家的习性。从此,老舍便将以北京方言为标志的文字风格和幽默一起视为自己的文学资本,并逐渐内化为自己的习性。
文学场的规范一旦内化为作家的习性,就会保持长久的稳定性,甚至成为作家的癖好。曾经与老舍在“文协”长期共事的萧伯青回忆,老舍在川八年没有受到四川话的影响。萧伯青猜测,老舍是为了保证其基于北京口语的文学语言的纯洁性:“他的创作自始至终以用北京话为特点,他为了忠于自己的创作,便要保持自己在实际生活上说纯粹的北京话。他如果把语言弄成南腔北调,以致影响到自己创作用语,那岂不是大错!不过,这个我不曾当面请问过他,不知他是否这个意思?”①萧伯青:《老舍在武汉、重庆》,《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第146页。萧伯青的推测应该是有道理的。老舍的确有维护风格化语言的自觉。老舍1941年明确地提到他对北京口语的依赖:“这时候,正是我开始学习写小说的时候;所以,我一下手便拿出我自幼儿用惯了的北平话。……我自己的笔也逐渐地,日深一日地,去沾那活的、自然的、北平话的血汁,不想借用别人的文法来装饰自己了。我不知道这合理与否,我只觉得这个作法给我不少的欣喜,使我领略到一点创作的乐趣。看,这是我自己的想象,也是我自己的语言哪!”②老舍:《我的“话”》,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5页。1948年老舍借《离婚》英译本在美国出版的机会,再次发掘了其文字风格的资本价值:“自这部小说起,我建立了自己的文字风格。中国当代文学是用白话表达的,这当然是一种新的尝试,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如何将这种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的大众语言的美用文字表达出来。在写《离婚》时,我决定抛弃陈腐的文言文,而尽量用接近生活的语言来表达。我极力思索:当一个苦力看到一个极美的落日,他将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所有古代诗人表达落日余晖的诗句都是死的东西。我希望用一般平民百姓的语言去创造一种新的美感。我不清楚我这种观点和我的小说是不是无足轻重,但我希望人们能时时记起:我在《离婚》中所用的语言是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好的,文字简洁清新的典范。”③老舍:《关于〈离婚〉》,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页。将《离婚》的文字风格看做是中国“当代”文学场中的“典范”,显示出老舍已经把以北京口语为基础的个性化文字和幽默、文化批判共同作为他的区隔性资本。“文字风格”一经形成并得到文学场的承认就会成为作家稳定的,具有区隔性的资本。老舍对此是十分自觉的。
二、一体化文学场的语言规范化与老舍的退守
文字风格作为一种文学资本,是最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在“政治-文学”一体化文学场中,这种资本也是最安全的。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问题》于1950年介绍进中国。它明确地阐述了语言的非阶级性:“语言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服务作用,不是替一个阶级服务而损害另一个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替全社会服务、为社会所有各个阶级服务。”④本社编辑:《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俄华对照),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版,第11页。斯大林关于语言非阶级性的判断在当时的苏联的社会科学界,连带着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校正了自“大众语”讨论起就存在的语言论争的阶级色彩。语言的超阶级性也成为文学场中文学语言这一资本的护身符,作家们可以借助这一资本在文学场立足的惊涛骇浪中获得安稳的一角。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当中国当代文学场中的一体化进程越来越急进的时候,老舍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文学语言问题,或者用来守护自己的文学资本,或者借此而王顾左右。
老舍回国之初,新的文学场有意让老舍从事通俗文艺的改造。老舍对新的文学场规范还不熟悉,语言问题便成了他谈论较多的内容。在《谈相声的改造》(1950年2月)中,老舍一方面赞同“放胆放入新名词去代替文言”,一方面又要求保留旧相声中活泼的方言表达:“相声中的白话部分,用的是纯粹的地方话,并随时加以歇后语、俏皮话,最为生动好听。在改编相声时,我们须学习怎么运用这种活生生的语言。”⑤老舍:《谈相声的改造》,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2页。《大众文艺怎样写》(1950年3月)提出的首要问题也是语言:“应该学习的事很多,可是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恐怕是语言了。……这个发现使我们登时感到我们的真正有用的字汇与词典就是人民的嘴。人民口中的语言是活的。因为它是活的,所以才有劲,才巧妙。除非我们能把握住这巧妙的、活生生的语言,我们就没法子使人民接受我们的作品。”①老舍:《大众文艺怎样写》,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其他如《“现成”与“深入浅出”》《民间曲艺问题》等,意见大同小异。老舍对他回国之后第一部话剧《方珍珠》的语言十分自得:“这剧本中的对话相当流利。我是北京人,我应当用北京话,这没有什么新奇。……我避免了舞台语,而用了我知道的北京话。我的话,一方面使一部分演员感到困难,因为他们说不惯或说不好地道的北京话;另一方面却使演员们能从语言中找到剧中人的个性与感情,帮助他们把握到人格与心理。此剧中的人物所以能生动,一部分是受了活的语言的帮助。再说,活的语言也美好悦耳,使听众能因语言之美而去喜爱那说话的人。”②老舍:《谈〈方珍珠〉剧本》,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239页。他在自称为“简单的自我检讨”的《〈老舍选集〉自序》(1950年8月)中也自信地认为:“我很会运用北京的发言,发为文章。”③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老舍此时(1950年2月到8月)对自己语言资本的坚守,是认为它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方言、土语等群众语言的合法性来源于两方面:动员功能和作家思想改造的必要途径之一。
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语言建设包含两方面的内容:语言规范化(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推广)与文字改革(汉字简化)。这一运动中,方言、土语的动员功能的合法性遭到贬抑。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强调语言规范的重要性:“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在这篇社论中,“正确的语言”指的是规范化的统一语。方言、口头语、外来语的使用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他们不但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而且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词。”当然,方言、土语的动员功能虽然遭到贬抑,但作为思想改造途径的合法性依然存在。同一篇社论在谈到词汇规范化的时候,仍然强调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重要性。这种内在的矛盾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向苏联学习之间的矛盾。
对这次语言规范运动,老舍很快就有了反应。他在《怎样写通俗文艺》《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我怎样学习语言》《怎样运用口语》《民间文艺的语言》等文章中论证语言规范化的合理性。在写于1951—1952年的这些文章中,老舍既按照政治场的规范阐述文艺中的语言问题,也试图根据新的规范重新阐释自己的语言资本。前者如《怎样运用口语》中就谈到口语与规范语(普通话)的差异:“口语里有许多土话。土话在一个地方现成,在另一个地方就不现成,所以我们用土话的时候得考虑一下。假若我们的一篇文字是专给一个地方写的,用些土语自然很好;可是,假若我们是写一部电影剧本,我们便应少用土话,因为电影是要在全国上演的。在小说与戏剧里,为了使人物与背景鲜明,往往非用一些土话不可,但是我们也要留神,别用得太多;我们得设法教我们的语言既带一点地方色彩,又大体上容易教一般人看得懂。我们用土话,好好下个注解,省得教读者乱猜。”在这一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立论的标准正是政治场对统一语的要求。土语的合法性仅剩了“使人物与背景鲜明”这一点。与土语的合法性被大幅削减相对,老舍极力揄扬新政权所产生的新词的合法性:“一个新社会的兴起,必产生许多新词新字。这些新词新字足以丰富我们的语言。在今天,我们能够不用‘抗美援朝’‘’‘国际主义’这些词汇么?不能!这些词汇已经成了大家口头上的,而且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它们。它们也就都现成。”④老舍:《怎样运用口语》,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新词是新政权意识形态生产的符号工具,其合法性是由政治场所赋予的。在“政治-文学”一体化的文学场中,文学场对这种新词合法性无缘置喙。老舍的这一增一减,正是政治场规范的直接反映。
在一体化文学场里,来自于政治场的文学共识并非像自主性文学场里的文学共识那样可以被随意质疑。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文学场中,因统一语与人民群众语言(方言、土语)的内在矛盾性,在作家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缝隙。老舍对待自己的语言资本也时时犹豫。他一方面强调来自政治场域的新词所具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的场合提到,运用这些新词还应该谨慎:“通俗化的文艺作品里不许生吞活剥地把革命的道理,用一大串新名词、专名词写了出来。我们应当把大道理先在心中消化了,而后用具体的事、现成的话写了出来。这才是文艺作品,这样的作品才能被人民接受,从而扩大了思想宣传的影响。不先消化了道理,我们自己就没有确实明白那个道理的把握。我们自己没把道理弄清楚,所以才仗着名词术语支持我们的文章。一旦我们真把道理消化了,我们才会把它用具体的事实表现出来——这就由照抄道理,改为以文艺形式表现道理。”①老舍:《谈文艺通俗化》,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老舍在这里明确指出,政治场的专有名词进入文学场必须经过文学化的转译。当然,老舍的态度是很谨慎的,他巧妙地借着文艺通俗化这一政治场所赋予的合法性来谈论新词的文学转译问题。在一体化文学场中,谈论文学场的独立价值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承认文学场存在着独立的规范,那么,政治场对文学场的直接干涉就会受到怀疑。如果认为文学场不存在独立于政治场域的规范,那么,文学场域中的标语口号就会盛行。后一种状况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起一直到“文革”文学,都是经常出现、令人头痛的现象。老舍在一次发言中明确地指出过这种倾向的普遍性:“今天剧本中的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话往往表现了剧作者的思想,而不是表现剧中人的思想。剧作者的思想是要宣传抗美援朝,或镇压反革命,他就叫剧中人三转两转喊叫出来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特务分子。这样,剧中人就变成了剧作者的麦克风,而剧中的语言便不能精彩,不能动人。我们必须作到,剧中的对话时情节所致,必然如此的,而不是忽然从外边飞来的。”②老舍:《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老舍上述对于来自政治场域新名词的怀疑,对文学场域相对自主的文学规范的维护,基本上出现在1955年之前。
新中国的一体化文学场最初也为方言、土语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即以“人民群众的语言”这一符号为其提供了合法性。新中国一体化文学场力图通过深入生活和作家思想改造来解决统一语与方言在话语结构中的矛盾。这使得文学的实践者有了各自发挥的空间。老舍便抓住了“人民群众语言”这一根稻草来维护自己的语言资本。他将人民群众的语言称为“大白话”,将之与文言、五四的欧化语言相对立:“我们应当即刻从思想上解放了我们的笔,教它光荣地服务于人民,教它光辉地给大白话放出光彩。”“我们必须相信白话万能!否则我们不会全心全意地去学习白话,运用白话!”在论证“大白话”的正当性的同时,贬抑后两者,称固守后者的人为“顽固老儿”“存着点崇洋病”③老舍:《怎样写通俗文艺》,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79页。。从某种程度上说,老舍对群众语言的揄扬是借文学场域的赋权来确认自己的文字风格的文学资本有效性。在一体化文学场中,创作主体首先要考虑“我必须要求自己写得‘对’,而后再要求写得‘好’。”④老舍:《为人民写作最光荣》,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页。在这种情境里,文学场的独立价值必定会让位于政治场的规范;创作主体的算计会代替其习性的自然外化。此时,文艺界的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开始,老舍还可以小心谨慎地持其两端。
随着镇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等决定性工作的完成,语言统一被正式提上国家议事日程。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教育部共同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同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汉民族共同语。随后,两部门又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在全国推行新的汉语规范。郭沫若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开幕词中谈到汉语规范化的目的:“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全国人民在个个部门、个个岗位上都进入了大规模的集体生活,共同劳动,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一个规范明确的、统一的民族共同语,以便于我们在一切的活动当中调节我们共同的意识和行动。”⑤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编:《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郭沫若的讲话清晰地指出了新生政权推行语言统一的意图:是为了大规模的集体生活;是为了调节人民的共同的意识和行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议》对文学语言提出了“正确、精密、纯洁、健康”的要求,同时要求作家与教师、翻译工作者、广播工作者、戏剧电影工作者一道,“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推广普通话的情况下,必须加强语言的规范化,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①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编:《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第216页。
此次语言规范化运动进一步挤压了方言、土语存在的空间。老舍的文学语言资本面临着更大的窘境。老舍于1955年春被任命为《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委员。他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发言中,除了“拥护民族共同语的推行”外,还检讨了自己创作中“爱用北京土话”的缺点,认为这是“卖弄和偷懒”,表示要“少用土语方言”:“我不再随便乱用我所熟悉的土语,而要经过考虑,把真值得保存的保存下来,丰富我们的语言。……从普通话里创造出文学语言才是作家的责任与本领。”②老舍:《我拥护大力推行民族共同语》,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4-615页。老舍向大会提交了《普通话和方言运用问题》的研究题目,但并没有看到老舍完成这个题目。1956年2月10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成立,老舍被任命为副主任。在同年3月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老舍被要求以“关于语言规范化”为题做大会发言。老舍围绕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决议进行发挥,把推进语言规范化看做是作家的“政治任务”:“我们若再乱用方言土语,问题就严重了,因它不符合民族利益。现在有些作家喜欢用方言土语,这是与规范化背道而驰的。作家没有乱用语言的自由。不争取规范化就是落后。”③老舍:《关于语言规范化》,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统一语言(包括语音、语法、词汇),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语言越纷歧,越不利于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谁爱惜土语方言,就是保守,方言迟早是一定要灭亡。”④老舍:《关于业余曲艺创作的几个问题》,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类似的工作,老舍在其后仍然做了很多,如1956年为鞍山的业余作者做的《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报告、《关于业余曲艺创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57年的《文字改革是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的报告等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老舍不再试图小心谨慎地在文学规范和维护自己的语言资本之间游走。没有持其两端的余地,老舍不得不有意识地修改自己的语言资本。在《西望长安》中,他有意减少土话的使用。老舍强调,《,《西望长安》虽然减少了土话的使用,“并不见得表现力就弱”⑤老舍:《关于语言规范化》,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当然,对于最后一点文学资本的放弃,老舍应该心有不甘。在1956—1957年文学场的小阳春中,随着政治场和文学场控制的缓慢放松,老舍又不时表现出对他的文学语言资本的维护。1956年老舍为《老舍短篇小说选》写的后记就表现了这一点。他把选集中的作品称为“古董”。在这一略带自炫的谦辞背后,老舍对过往文学实践中的语言资本不无留恋:“在文字上,像‘北平’之类的名词都原封不动,以免颠倒历史。除了太不干净的地方略事删改,字句大致上未加增减,以保持原来的风格。有些北京土话很难改动,就加上了简单的注解。”⑥老舍:《〈老舍短篇小说选〉后记》,见老舍:《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这一后记的写作与《关于语言规范化》时隔不久,但态度有微妙的差异。在这一个后记里,老舍拒绝修改他的小说中的北京土话。这种拒绝并非是简单地是因为“很难”,而是内心不愿改。这种不愿,正如这篇后记中老舍对这部选集所选作品的矜持:这些作品带有古董的价值。北京土语也应该属于此类吧。不然,很难说明白,为什么选集中的某些作品的“不太干净的地方”可以“略事删改”,而那些“北京土话”却“很难改动”?这也说明,1955年老舍对自己语言资本的贬抑是高度仪式化情境中的策略选择,而非其本心。关于语言规范化问题,老舍作为决策的局外人并没有予取予夺的权力,但在这一规范化实践中,老舍主动修改自己文学资本中最稳定的语言资本,是一个令人深深叹惋的事件。
三、结论
风格化的语言是一个作家最难获致、最稳定的文学资本。它有赖于文学场的塑造,更有赖于作家个人经验、习性,因此,其区隔性更为突出。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以北京口语为基础的文学语言资本,既是文学场围绕着语言占位斗争的结果,也是老舍的自觉文化选择。当年文学场多元的权力结构使得老舍依据其习性获得这一资本。1949年之后,一体化文学场对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文学资源进行统制。老舍在这种情境下不得不一步步放弃自己的语言资本。在今天看来,这一变化过程的启示性意义仍然很大:文学场域相对自主性的存在是文学真正繁荣的基础。只有在相对自主的文学场域中,作家才能在接受文学场域塑造的同时,根据自己的个体经验、习性获得具有个性化的文学资本,而这些具有鲜明区隔性的文学资本才会带来真正的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