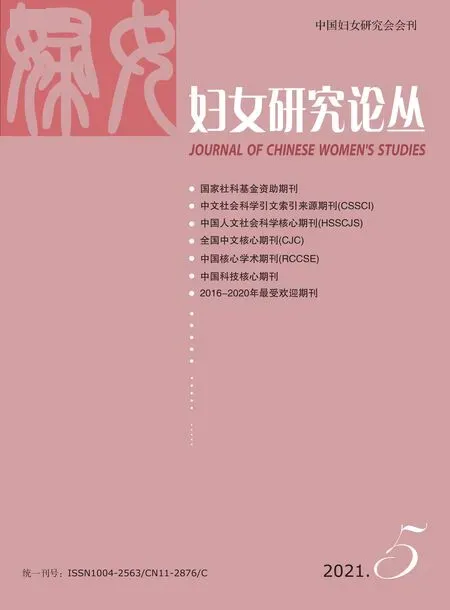共同财产制下离婚经济补偿的价值基础、教义构造与体系协调
汪 洋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2001年《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该条首次确立了中国法上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明确以夫妻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为适用前提。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2017年“室内稿”增加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述,“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2018年“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夫妻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这一适用前提。最终《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删除分别财产制的适用前提,是否具有实质合理性?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如何具体构建离婚经济补偿的教义学结构?在离婚救济的制度框架下,如何对离婚经济补偿、离婚帮助以及离婚损害赔偿三者进行体系协调?
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对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未予规定,2005年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吸纳了《婚姻法》第40条内容,于第47条第2款增设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并于2018年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时予以保留。2021年《民法典》正式施行,又恰逢《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在酝酿新一轮修正,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在吸纳《民法典》第1088条内容基础上,于立法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二、共同财产制下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价值基础
《婚姻法》第40条为何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分别财产制?官方释义书的理由是,“因夫妻双方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归属各自所有,当一方付出较多义务,并因此牺牲自身的发展机遇,致使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远低于另一方,她们的利益无法在婚姻关系终结时得到必要保障;而在共同财产制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在离婚时予以分割,法院在分割之时会尤其注意维护家务劳动繁重而经济收入较少的妇女一方的权益”[1](PP 167-169)。可见,在《婚姻法》时代,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规范目的是作为克服分别财产制固有缺陷的纠偏措施,解决一方家务贡献难以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下获得合理评价的问题[2](P 80)。而共同财产制下,离婚时的共同财产均等分割已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若叠加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会导致家务贡献的重复计算与评价[3](P 137)[4](P 142)。因此应当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限缩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下。
《婚姻法》施行之后,由于分别财产制并非中国法定财产制类型,适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数量相对较少,从而极大限缩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空间[5](P 93)。在裁判文书库中,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及《婚姻法》第40条的婚姻家庭与继承纠纷裁判文书共计仅一百余件,且绝大多数案件中,法院都以不符合分别财产制的适用前提为由,拒绝了当事人的离婚经济补偿请求(1)参见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0民终495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4民终145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吕梁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1民终921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8民终108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琼01民终1959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终241号民事判决书。。一些地方高院的指导意见明确反对在法定财产制下承认离婚家务劳动补偿。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1)》第24条规定:“夫妻没有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即实行共同财产制),离婚时,一方以抚育子女、照料老人等付出较多义务为由,根据《婚姻法》第四十条要求另外一方补偿的,不予支持。”
《民法典》第1088条为何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拓展至共同财产制?官方释义书的理由是,“一方因付出较多义务牺牲了自身的发展机遇,致使自己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远低于另一方,不论是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产制,如果他们的利益在婚姻关系解体之时得不到有效保障,将对子女的成长极为不利,对社会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6](P 229)。
从《婚姻法》与《民法典》官方释义的表述中可以得知,无论是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产制,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前提都在于“一方付出较多义务”,其正当性源于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1](P 166)。家务劳动是指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为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所从事的劳动[3](P 137)。其价值在直接间接两个层面得以体现:直接层面,家务劳动作为一种劳动形态,自身具有市场价值,如果双方都不承担家务劳动,则需要以有偿方式由家政服务人员承担,由此导致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因此家务劳动对于家庭财富的积累具有间接贡献[7](P 159);间接层面,家务劳动的总量是恒定的,一方从事较多的家务劳动意味着另一方从事较少,从而可以把更多时间精力投入职业工作,使得从事家务劳动较少一方有更大机率提升自己的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市场价值,这一结果受益于另一方从事的家务劳动[7](P 102)[8](P 155)。
共同财产制缘何也存在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可能?第一个正当性理由在于官方释义所言的“利益在婚姻关系解体之时得不到有效保障”。一方面,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家庭共同财产的积累是一个非线性发展的过程,婚姻初期往往对应着青年阶段,双方事业刚在起步期,无论是收入还是人力资本价值都处于缓慢积累爬坡阶段;婚姻关系存续一段时间后,人生步入中年阶段,通常意味着收入增长和职业晋升,家庭财富积累初具规模,人力资本价值也得到较大提升;婚姻关系持续至人生进入壮年阶段,收入与人力资本价值曲线或都处于高点,夫妻共同财产基本达到最大化。因此,若在婚姻初期或婚姻关系存续时间不长便离婚,此时尚未积累到足以补偿付出较多义务一方的家庭财产[9](P 33)[10](P 30),出现付出较多义务一方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权,却无财产可供分割之实的失衡状态。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中国家庭的主流情形是“双薪制”而非“主妇制”,但传统观念下“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务分工模式并未因女性外出工作而发生实质性改变[7](P 158),大多数家庭中妻子在辛勤工作的同时,承担了更多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家务劳动,仅仅依靠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未必能够合理评价双薪制下家务劳动付出方的贡献和价值[11](P 80)。
前民法典时代,鉴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只能适用于分别财产制,有学者就主张在共同财产制下,通过分割共同财产时对承担较多义务一方予以照顾,迂回实现家务劳动补偿的目的[12](P 165)。一些地方法院也采取了迂回方案,强调法院可以通过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来间接补偿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2)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指南(2010)》:“付出较多义务一方要求的补偿以及困难一方要求的帮助均是因无法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获得补偿和救助,从而要求另一方以其个人财产支付。如果有足够的夫妻共同财产,则应适用上述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原则。”。
第二个正当性理由在于官方释义所言的“一方因付出较多义务牺牲了自身的发展机遇”,涉及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作出的家庭分工造成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损失及其补偿问题。付出较多义务一方在职业发展方面受到不可逆的负面影响,未来的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价值都面临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从事家务劳动较少一方有更大几率提升自己的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价值。婚姻存续期间,遭受收入能力损失的一方通过共同财产制,得以分享另一方收入的提升而得到相应回报,并使得整个家庭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一旦离婚,当初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而作出的家庭分工,却使得双方面临天壤之别的损失抑或收益[13](PP 40-50)。付出较多义务一方未来职业发展机会的丧失,无法继续通过另一方收入的提升而得以弥补,付出较多家务劳动这一抉择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未来依旧持续;但是得利一方继续享受着之前家务劳动付出较少而在职业发展方面带来的红利[2](P 84)[12](P 79)[14](P 83)。这一面向未来的失衡局面无法通过离婚时的共同财产分割得以矫正,需要引入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解决人力资本价值损失的补偿问题。
第三个正当性理由在于官方释义所言的“将对子女的成长极为不利,对社会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即在后果层面,由于未能在离婚之际对收入能力损失予以重新分配,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婚姻行动的扭曲[14](PP 40-50),对子女抚养以及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如若可以合理预期从事家务劳动带来的收入损失在离婚时将会得到补偿,家务劳动一方在婚姻关系中会以家庭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采纳最佳的婚姻分工模式,通常也最有利于教育和抚养子女。如若不能合理预期从事家务劳动带来的收入损失在离婚时将会得到补偿,则原本投入家务劳动一方会以自身利益而非家庭整体利益作出选择,放弃最佳的婚姻分工模式,投入相对较少时间精力用于家务劳动以及教育和抚养子女,对子女成长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既然夫妻双方都以个人利益而非家庭整体利益为重,婚姻家庭何以稳定运行?收入和人力资本价值更高一方可能的离婚动机何以得到抑制?
综上所述,在共同财产制下,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避免婚姻关系不同阶段家庭财产积累的差异导致双方利益失衡;矫正家务劳动牺牲一方未来收入无法通过离婚共同财产分割得以完全弥补的损失;避免不当的激励机制扭曲婚姻行动从而对子女抚养以及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三、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教义构造
《民法典》第1088条在构成要件以及补偿标准等方面都过于笼统,需要在不同类型下进行更细致化的教义构造,以期为后续司法实践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导。
(一)例外情形下对家务劳动价值进行补偿
依据第1088条文义,夫妻一方只要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无论分割得到多少夫妻共同财产,均有权请求另一方予以额外补偿。一方面,这无异于重复计算了家务劳动的价值,不符合本条的规范意旨;另一方面,若制度导向是精准计算家务劳动总量及双方承担的比例,会陷入由司法对家庭贡献进行实质性评价的歧途,婚姻共同体本应是相互奉献、支持,彼此牺牲、妥协且受益的关系,对双方日常生活中的付出和抉择进行精确计算,无异于消解了婚姻家庭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石。有鉴于此,在共同财产制下,原则上不对家务劳动贡献方的家务劳动价值进行补偿。只有在符合“离婚时通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得到适当补偿的”例外情形下才适用第1088条,使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与共同财产制相衔接。
正如前文所述,共同财产制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第一个正当性理由,在于付出较多义务一方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权,却无财产可供分割之实的失衡状态,以及“双薪制”下家务劳动付出方在家务劳动上的贡献和价值仅仅依靠分割共同财产无法得到合理评价。因此,例外予以补偿的构成要件为“离婚时可供分割的共同财产数额较少”[8](P 106)以及“家务劳动贡献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未从他方收入中获取必要收益”[15](P 167),囊括实践中离婚时夫妻无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因外出打工或感情不和等原因长期异地分居且未负担家庭开支、一方将收入挥霍于个人消费、双薪制下夫妻一方主要负担了家务劳动等情形(3)参见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益法民一终字第499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宜民终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曲中民终字第1355号民事判决书。。
另外,夫妻一方用夫妻共同财产供一方继续深造或职业培训,因此获得的学位文凭、技术职称、职业证书等无形资产并未计入夫妻共同财产,使得这类由夫妻共同财产转化而来的无形资产成为一方的个人财产,离婚时也无法分割,通过经济补偿制度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一不公平现象[7](P 160)[16](P 355)。
(二)对“负担较多义务”或“特定牺牲决策”导致收入能力受损的补偿
正如前文所述,共同财产制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第二个正当性理由在于“一方因付出较多义务牺牲了自身的发展机遇”,即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作出的家庭分工造成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损失。应当对第1088条“负担较多义务”的表述采广义解释,本条中的“义务”如“协助另一方工作”,并不限于履行法定义务,包括因“抚养子女、照料老年人”等家务劳动所做出的特定牺牲决策,以及因“协助另一方工作等”非家务劳动范畴做出的特定牺牲决策两种类型。
特定的牺牲决策要求在后果层面造成该方未来收入能力的损失。例如,夫妻一方因育儿或养老等家务劳动,辞去工作、拒绝了收入更丰厚的工作机会、拒绝了岗位晋升机会、选择了收入低但工作量小的工作、延迟或取消了可以提升未来收入的进修计划,以及并非因家务劳动,而是为了配合另一方工作迁移至某地,放弃了原工作机会或潜在就业岗位。
特定的牺牲决策要求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原则。如果仅仅只是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用于育儿或养老,则不应认为存在特定的牺牲决策,只有在符合前文所述的例外情形,才能主张针对家务劳动价值本身要求补偿。如果不存在育儿或养老负担,比如在无孩家庭中,夫妻一方退出就业市场担当家庭主妇,可能仅仅是出于个人生活方式的偏好[14](P 64),不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原则,不应予以补偿。成年人只有存在特殊需求,如生病、年老或残疾时,配偶一方完全或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以满足这一需求,进而主张补偿的主张才被认为是适当的[17]。
判断是否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原则时,考虑到婚姻家庭并非一个完全依照“经济理性”进行决策的共同体,需要平衡家庭的短期收益与长远收益,以及情感和伦理因素对行为决策的导向作用。例如,鉴于目前中国一线城市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如果子女升学构成了夫妻婚姻生活至关重要的目标,并且夫妻双方对此有相同的意愿倾向,则夫妻一方即便辞职照料临近升学的子女,导致家庭总收入的下降和自身人力资源价值的减损,也应当认定为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判断标准。
(三)补偿数额的认定和计算
因家务劳动价值在离婚时通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得到适当补偿的例外情形下,对家务劳动贡献方进行补偿时,补偿数额可以根据当地同种类家政服务的市场价值为参照标准,结合婚姻存续时间以及育儿或养老期限[17](P 356),在个案中根据具体事实进行评判。
因负担较多义务或特定牺牲决策致使收入能力损失的情形下,应该如何认定补偿数额?在前民法典时代,司法实践中根据《婚姻法》第40条做出的支持离婚经济补偿主张的判决,补偿金额通常在五千元至五万元区间内。法院依据的参考因素包括“当地生活水平及支付方的过错程度”(4)参见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鹤民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宜民终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书。、“未尽子女抚养义务时间的长短、支付方的经济能力”(5)参见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少民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等等。
美国法律学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于2002年颁布《家庭解体法的原则:分析与建议》(PrinciplesoftheLawofFamilyDissolution:AnalysisandRecommendations),将受损配偶的收入能力损失与配偶双方的收入差距挂钩,认为“相较于随机抽取的人群,配偶双方在结婚之初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要更为接近,将请求权人的收入能力与其配偶而非一般群体相比较,所得出的对收入能力损失的估算或许要更为精确”[18]。《民法典》官方释义书表述为“自己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远低于另一方”[6](P 229),暗含着对夫妻双方的收入水平进行比较的意味。但是,单个个体的收入能力受到家庭条件、自身天赋个性、勤奋程度、专业选择、人力资本投资、行业发展趋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简单将收入能力差距归结于家务劳动负担较为牵强。
具有实操性的补偿标准仍然应当围绕着“特定牺牲决策”展开,因为特定牺牲决策所带来的收入能力损失相对容易计算和识别。可以对比家务劳动贡献方做出特定牺牲决策前后的收入能力进行判定,比如辞职之前的收入、放弃更好的工作岗位的收入与现有收入之差,等等。在补偿数额的计算上,还可以参考类似教育背景、职业背景人士现阶段平均收入等官方统计资料。
四、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体系协调
2001年《婚姻法》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基础上,增设了离婚经济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三项制度共同构成中国离婚救济的制度框架。《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第1090条规定了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第1091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延续了《婚姻法》以来的离婚救济框架和格局。第1091条吸收了《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过错情形,并新增“(五)有其他重大过错的”作为兜底条款,为其他重大过错情形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可行空间。第1090条相较于《婚姻法》第42条,明确了经济帮助以具备负担能力为前提,并且删除了住房等帮助形式的具体列举。
三项制度的规范意旨虽各不相同,但在功能层面均旨在消除离婚过程中存在于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缺损状态[18](P 340)。《婚姻法》第40条对分别财产制这一适用前提的限制,使得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与其他两项制度进行了显著区分,《民法典》第1088条将适用范围扩大至共同财产制下,意味着三项制度重叠适用的可能性显著增大。当离婚案件中付出较多义务一方同时又是导致离婚的过错方,并且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形,同时满足三项制度的构成要件,如何具体适用三项制度,从而达到离婚救济法的价值融贯与体系协调?
三项制度服务于不同的价值目标,经济补偿是基于权利人为家庭共同生活所作贡献抑或牺牲等事实的客观评价,与夫妻哪一方过错导致离婚并无关联。即便付出较多义务一方是导致离婚的过错方,也不能因导致离婚的过错而忽视甚至否认该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家庭做出的贡献或牺牲。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对过错行为作出了评价,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过程中不应予以考虑,否则会构成重复评价。离婚经济帮助的前提则是一方生活困难且另一方有负担能力,着眼于生活困难一方的客观需求,不考虑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贡献或牺牲以及对于离婚是否存在过错。
离婚损害赔偿与离婚经济补偿两项制度原则上并行不悖,独立判断是否符合各自的构成要件。经济补偿数额与损害赔偿数额分别计算,如若付出较多义务一方是导致离婚的非过错方,则补偿数额与赔偿数额相加;如若付出较多义务一方是导致离婚的过错方,则补偿数额与赔偿数额可以适用抵销规则。在损害赔偿以及经济补偿之后,再行判断赔偿金额或补偿金额与分割所得的共同财产相加之后,双方的客观状况是否仍满足第1090条的“生活困难”以及“具备负担能力”。如若原本“生活困难”的客观状况因损害赔偿或经济补偿而得以消解,则不能叠加适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换言之,是否存在生活困难这一客观需求,受到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后果的影响。因此,应当在第1088条与第1091条得以适用的法律效果之上,评估具体案件是否仍然符合第1090条的构成要件。
另外,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第2款,“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子女抚养费源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该义务不因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的解除而受到影响。《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抚养费的规定较为细致(6)参见《民法典》第196条、第1067条、第108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2条、第49-53条、第55条、第58条。,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仍然需要继续付出家务劳动或做出特定牺牲决策。但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无权再通过离婚补偿制度得到救济,只能根据《民法典》第1085条第1款规定,主张由不直接抚养的另一方负担全部或大部分抚养费,通过减少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支付的抚养费比重的方式,对其继续付出的家务劳动或做出的特定牺牲决策进行间接补偿。
五、结论
《民法典》第1088条对《婚姻法》第40条进行了重大修改,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拓展至夫妻共同财产制。正当性基础有三点。一为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权、却无财产可供分割之实情形下,双方利益失衡;双薪制下家务劳动的贡献和价值依靠分割共同财产未能得到合理评价。二为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作出的家庭分工,造成牺牲一方的收入能力损失,这一面向未来的失衡局面无法通过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得以矫正。三为后果层面由于未能在离婚之际对收入能力损失予以重新分配,不当的激励机制导致婚姻行动的扭曲,对子女抚养以及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民法典》第1088条在构成要件以及数额确定等方面规定得过于笼统,需要进行更细致化的教义构造。首先,在共同财产制下,原则上不对家务劳动贡献方的家务劳动价值进行补偿,只有在符合“离婚时可供分割的共同财产数额较少”以及“家务劳动贡献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未从他方收入中获取必要收益”两种例外情形下才进行补偿,补偿数额根据当地同种类家政服务的市场价值为参照标准。其次,针对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作出的家庭分工造成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损失应当予以补偿。应对第1088条“负担较多义务”采广义解释,包括因“抚养子女、照料老年人”为代表的家务劳动所做出的特定牺牲决策,以及因“协助另一方工作等”非家务劳动范畴作出的特定牺牲决策两种类型。最后,特定牺牲决策在“家庭利益最大化”层面应具有正当合理性。判断是否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时不能仅仅采用经济理性标准,需要考量家庭短期收益与长远收益,以及情感和伦理因素的导向作用。补偿标准应当围绕特定牺牲决策所带来的收入能力损失进行判定。
离婚经济帮助、离婚经济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三项制度共同构成中国离婚救济的制度框架。离婚损害赔偿与离婚经济补偿两项制度原则上并行不悖,独立判断是否符合各自的构成要件,经济补偿数额与损害赔偿数额分别计算。在损害赔偿以及经济补偿之后,再行判断赔偿金额或补偿金额与分割所得的共同财产相加之后,双方的客观状况是否仍满足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适用前提的“生活困难”以及“具备负担能力”。如若原本“生活困难”的客观状况因损害赔偿或经济补偿而得以消解,则不能叠加适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继续付出的家务劳动或作出特定牺牲决策,放在子女抚养费的框架下处理。
《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在酝酿新一轮修正,可以在《民法典》第1088条内容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笔者建议将《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第2款修改为:“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男方工作等家庭利益需要,负担较多义务或者牺牲了自身的发展机遇,利益在离婚时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