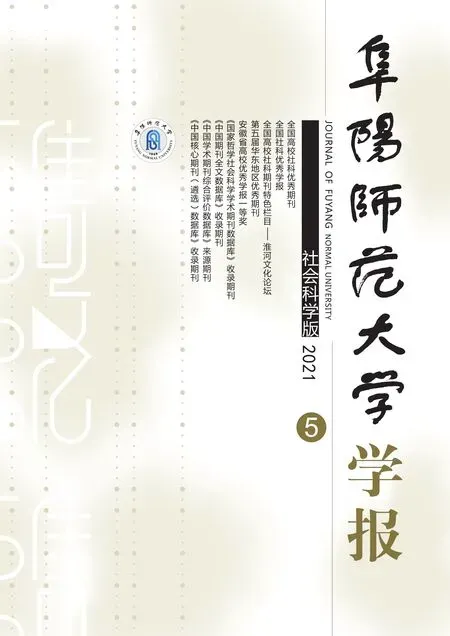名士之殇:论祢衡孔融杨修被杀的深层原因
谢启平,刘运好
名士之殇:论祢衡孔融杨修被杀的深层原因
谢启平1,刘运好2
(1.亳州学院 中文系,安徽 亳州 236800;2.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名士祢衡、孔融、杨修被杀,往往被认为是曹操忌贤滥杀的典型。其实,三人之死既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且不能“通物方,弘时务”的名士痼疾有关,更与三人的主体认知偏差、人格心理缺陷有关。祢衡狂悖,不识世道人心,成为矫世佯狂的个性牺牲品;孔融迂执,不明时势变化,成为依附皇权的政治牺牲品;杨修不敏,不能慎言谨行,成为太子之争的权力牺牲品。三人游走于权力刀锋之上,渴望最大限度地攫取政治利益,结果却成为强权政治的屈死冤魂,他们自己也可能不明白因何而死,但历史却都给出了必死的理由。当然,不得不承认,名士被杀也的确暴露了作为封建统治者曹操狰狞残忍的一面。
名士;祢衡;孔融;杨修;曹操
在汉末的历史中,曹操是一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是一位最具有鲜活魅力且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后人交口称赞;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又颇遭责难非议。其中名士祢衡、孔融、杨修的被杀,更将曹操推向责难非议的漩涡。
其实,杀人是封建时期政治家一种常用的手段。要专擅朝纲,必须清除政敌;维护威仪,必须杀戮逆臣;严厉执法,必须戡除乱党;统一天下,必须消灭劲敌。哪一代封建王朝不是建立在累累的白骨之上?然而,统治者杀人,也有非杀不可和滥杀无辜的区别。曹操虽非如董卓那样狼戾不仁,却也有狰狞残忍的一面。
青年时期“任侠放荡”的侠士性格,一直深入曹操骨髓,几乎伴随终身。侠士固然重义,但是侠士之“义”是江湖之义,而不是儒家之义。江湖之义轻是非,重然诺,唯我独尊,剑影刀光视如霓彩虹影,取人性命犹如利刃割韭,这就造成侠士的另一面:无原则的滥杀。曹操最受后代史家诟病的莫过于讨伐陶谦过程中的滥杀无辜。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嵩罢官,率领小儿曹德还乡,因董卓之乱,道路不通,不得已避难琅琊,被陶谦部下劫掠财物,残杀全家。后来,曹操率兵复仇,东伐陶谦。“破彭城傅阳。……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1]2367因为复仇,竟然杀数十万百姓,以致于尸横泗水,河水为之不流;此后五县城中,人烟绝灭,这是何其残暴!所以王夫之愤怒地说:“惨毒不仁,恶滔天矣。”[2]240不过,这时的曹操尚未成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军阀的残忍和游侠的滥杀叠合,复仇的火焰焚毁了人性和良知,为复仇逞一时之快而酿就了这一令人发指的灾难。
这是曹操一生中难以饶恕的罪行。后来,随着地位的擢升、思想的成熟,历史责任逐渐自觉,民本思想也逐渐萌生,在战争中尽量关注民瘼,成为其思想、行为的主流。这在他一系列军令中有清晰的反映,“割发代首”是一次典型行为[3]。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历史学家之外,曹操这一滥杀无辜的罪恶并未引起后人的强烈关注,而受到后人强烈关注的反而是名士祢衡、孔融、杨修的被杀。后来,经过文学家的反复渲染,名士之殇,几乎成为曹操滥杀无辜的铁证。那么,三人被杀是否真是屈死的冤魂?造成三人被杀的深层原因究竟为何?当代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虽有系列专题论文,也部分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如白水河《孔融之死与汉末政治》[4]、郭耀武《孔融、杨修之死的悲剧共因》[5]、王允亮《祢衡之死与汉末士风》[6]等等,但是从整体上更多关注三人悲剧发生的时代原因及其共性特点,而对于悲剧发生的主观性、差异性则缺乏深度阐释。这一问题又直接涉及对曹操的定性评价,故笔者不揣谫陋,试图从历史的原点上,发掘其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比较三人悲剧的同异。
一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祢衡被杀。一般认为祢衡死于曹操“借刀杀人”,这固然事出有因,但考其史实,乃刘表假黄祖之手杀之,究其本质,是祢衡狂妄矫世的性格缺陷以及贪欲权势的隐蔽心理所造成的人生悲剧。
《后汉书·祢衡传》的开头就揭示了祢衡悲剧的性格:“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辨,而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7]2652没有追溯祢衡的家世,说明他非出身世家。对于积极用世者而言,素族出身有一种先天不足:缺少盘根错节的政治资源。虽然,最初汉末清流名士因矫时尚气而获得时誉者比比皆是,祢衡能够跻身名士也是时代风气使然,但是,渴望建立辉煌的功业,仅仅凭借矫世浮华的名士招牌几乎毫无用处。而且祢衡成名之后,时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在这种形势下,激浊扬清的政治取向,嘘枯吹生的空谈名理,皆退到历史的幕后。历史给予名士的选择,或是避世蹈隐,老死山林;或是积极用世,择主而依。若选择后者,就必须放下名士身段,广交天下豪杰,互为奥援;选择非常之主,附凤翼而成就功业。然而,祢衡不明时势变化,刻意维护“刻情”“尚气”“婞直”的汉末名士风度,自恃才能出众,能言善辩,任性傲慢,目空一切。本想积极入世,以求宏图大展,却又自毁入世根基,在思想与行为的分裂中,自导自演了一幕绝大的人生悲剧。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朝廷建都许昌,祢衡从荆州匆匆北上,“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或问衡曰:‘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对曰:‘吾焉能从屠沽儿耶!’又问:‘荀文若、赵稚长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7]2653怀揣名帖,又无处投人,直至名帖的字迹都已模糊。这说明两点:一是南漂许都,本为求官而来;二是声名不彰,无人可以投靠。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问他:你何不投靠陈群、司马朗?他回答说:我怎么能追随屠户卖酒者!又问:荀彧、赵融如何?再答说:荀彧颜值超群,可以借他的脸蛋去吊丧;赵融大腹便便,可以用他的胃口去监厨。祢衡所蔑视的四人,都是当时许都名士,才能出众,很受当权者重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在祢衡之下。对于一个既无祖荫可以托庇,且无根基能够立足的人来说,本应广结豪杰,互为援契,却“恃才傲逸,臧否过差”,乃至造成“人皆以是憎之”“众人皆切齿”的结局[8]311。尚未立足,就将自己的社会根基抽空殆尽,其性格悲剧已经露出端倪。
因为少府孔融深爱其才,上书朝廷,鼎力推荐,后来又“数称述于曹操”,曹操求贤若渴,才“欲见之”。是时,曹操已经是朝廷的实际统治者,对于积极求仕的祢衡来说,这本是附凤翼以成功的一次难得机遇,偏偏故作清流,不齿依附当权,自称有“狂病”而不肯见之。既不齿依附当权,何以从“避难荆州”而北漂许都?不见也罢,却又口无遮拦,言语放诞,激怒了曹操,只是“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而已。为折其傲气,曹操故意任命为人所不屑的鼓史。若衡心知羞辱,自可拂袖而去,却又屈辱接受这一卑贱之职。在一次朝廷大会宾客时,却又借题发挥。先是不愿身着鼓史之服,选择声音急促悲壮的《渔阳参挝》。击鼓之时,表情愠怒,声节悲壮,使听者无不慷慨悲叹。并一边击鼓,一边走向曹操,在小吏“鼓史何不改装而轻敢进乎’的呵斥之下,先是当众脱下内衣,裸体而立,然后缓缓穿上鼓史衣服,再击鼓参挝而去,并且毫无羞态。这种名士狂态,固然“矫时慢物”,博人眼球,也得到了羞辱曹操的目的,但是在一脱一裸一穿之中,名士毫无羞耻的丑态也毕露无遗。所以,就连与他同气相求的孔融也看不下去,直接批评他说:正平,大雅君子,本来就不该如此!并且向他传达了曹操对他的真实用心。在孔融斡旋下,曹操非常高兴地答应再见之,并且“勑门者有客便通”——可见曹操何等希望他幡然自悟。然而,祢衡不仅不思悔过,反而变本加厉,又演出辕门骂曹的闹剧。击鼓骂曹时,曹操尚且微笑说:“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辕门骂曹后,曹操愤怒地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只是因为天下混乱,正是用人之际,祢衡又有虚名,唯恐杀之而失天下士人之心,才放他一条生路,遣人将他送给宽以待士的刘表。
祢衡初到荆州,生存环境和人际环境都大为改善。“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7]2657俨然成为荆州文人群体的核心。即使他将刘表与手下文人精心结撰的章奏撕毁掷地,刘表虽也震惊不满,却并未严厉指责,而且还因祢衡重新草拟的章奏“辞义可观”而“益重之”。然而,由于祢衡痼疾难改,自视过高,于是狂态复萌,“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其实,刘表虽然不算雄杰,但当时荆州安宁,经济繁荣,刘表又招纳贤才,礼遇文士,所治理的荆州因为人才济济而文化学术欣欣向荣,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王粲、经学家宋忠、綦毋闿等都聚集荆州,王粲《登楼赋》就创作于荆州,所形成的“荆州学派”也成为影响三国学术走向的一个重要学派。几乎所有流寓荆州的贤才文士都受到礼遇,刘表怎么可能不能容下一个祢衡?足见祢衡的狂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即使向来宽容文士的刘表也孰不可忍了。于是将他转送给性情暴躁的江夏太守黄祖。刘表料定黄祖必不能容忍祢衡的狂悖,如果说借刀杀人,刘表确实心存此念。
祢衡初至黄祖处,也特受“善待”,黄祖对他的文才尤其欣赏。“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7]2657是何其器重!祖长子黄射为章陵太守,与祢衡尤为友善,也曾在黄射宴请宾客时,有客献鹦鹉,即兴创作《鹦鹉赋》“文无加点,辞采甚丽”,而才惊四座。然而,后来在一次大会宾客时,祢衡又狂态复萌,出言不逊,黄祖呵斥之,他竟然辱骂黄祖已是死人,不必多言!黄祖勃然大怒,命令有司以军棍笞之,祢衡更是破口大骂,祖遂令杀之。黄射闻知,“徒跣来救,不及”,终至被杀。
纵观祢衡,刚愎狂悖,不自量力,不知进退,不甘人下,不能隐忍,心里深处又隐蔽着对权势的贪婪。渴望积极用世而无用世之道,渴望笼盖一世而无盖世之才,渴望攫取权力而无进身之方,试图以一己微薄之才遍折天下豪杰,所以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舐血于政治的锋刃之上,穿梭于权力的刀丛之中,即便黄祖不杀,也必有他人杀之。后来,京剧《击鼓骂曹》把祢衡塑造成一位头脑清醒、政治敏锐、欲清君侧的仁人志士,与历史不啻霄壤之间。而且,那时的曹操心系汉室,何曾有半点“上欺天子”的不臣之心!所以,祢衡被杀,虽也令人同情,实是咎由自取。也并非曹操“借刀杀人”而酿造的一桩冤案。试想,曹操能重用辱骂他“赘阉遗丑”的陈琳,宽容“薄其为人”而不与之交的宗承,何曾不能容忍一个狂生祢衡?当然,“整个社会由桓灵以来,盲目崇拜名士,好立异行以求声名的浮躁风气”,也是导致他人生悲剧的时代原因[6]。所以祢衡被杀具有必然性,这一点与孔融大不相同。
二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孔融有三点与祢衡不同:祢衡出身寒素,孔融出身高门;祢衡终身布衣,孔融身居高位;祢衡怒骂曹操是出于任性狂悖,孔融讥讽曹操是因为政治取向。所以,祢衡被杀,波澜不惊;孔融被杀,耸动士林。
《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世祖霸,为元帝师,位至侍中;父亲伷,太山都尉。年十岁,随父拜谒清流名士领袖李膺,因善于应对而受到李膺“必为伟器”的赞誉;山阳名士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构陷,朝廷下令州郡逮捕俭。是时,“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并收褒、融送狱”[9]2262。在狱中,融与兄长争相赴死,由此名震天下。出狱后,“与平原陶邱洪、陈留边让齐声称。州郡礼命,皆不就”[9]2262。为司徒杨赐所辟,进入仕途。在官举报贪浊官吏,陈对罪恶,义正辞严。后迁官虎贲中郎将,董卓专擅朝政,孔融因屡次忤逆卓旨,被外放北海相。任北海相期间,置城邑,办学校,彰表儒术,荐举贤才,为传承儒家文化不遗余力。建安元年,“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9]2264,也算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尤其重要的是,在袁绍、曹操都处于鼎盛之时,孔融深知二人的政治目的都在图谋汉室,所以不依附任何一方,部下左丞祖劝其结纳其中一方,以为政治靠山,融“怒而杀之”。范晔说他“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9]2264,确实识见高明。
从史籍看,孔融早期与曹操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才会屡次向他举荐祢衡;对曹操靖乱安邦也充满期待,在李傕、郭汜之乱时,明确表达“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对曹操迁都许昌,挽救汉室,也充满赞叹“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六言诗》)。但是,后来二人渐行渐远。孔融出于维护汉室的政治目的,眼见曹操军事崛起和专权朝政,其政治野心也渐渐暴露,既无力遏止,又无法忍受,于是以一种名士玩世不恭的方式,故意言辞不拘正理,讥讽曹操。第一,曹操攻下邺城,曹丕贪图袁熙之妻甄氏的美貌,私纳为妾。孔融与操书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本来,历史上的妲己,因为红颜祸水,导致商纣亡国,被武王斩下头颅,悬挂于白旗之下,以儆效尤。孔融却说被赐给了周公,所以曹操不知孔融所说有何依据,问“出何经典”。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9]2271意思是按照您现在的做法,推想武王也应该如此呀。这不仅调侃曹操父子的行为荒唐,而且讥讽其行为违背古制。第二,曹操北征乌桓三郡,本来是关乎国家北方统一的大计,而缺少远见的孔融竟又嘲笑说:“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氏不贡楛矢,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9]2272肃慎是西周古国,苏武是西汉使节。所谓肃慎国不来进贡、丁零国盗走苏武牛羊,这两件事与曹操北征乌桓毫无关联。孔融之所以拉来作为调侃的材料,实际上是讽刺曹操“师出无名”。第三,因为灾荒,兵粮不足,操上表请求禁酒,以节约粮食,这本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可是孔融又作书于操说:“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9]2273一言以蔽之,无酒则不能成就大业,“和神定人,以济万邦”,非酒莫属。曹操答书,“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融又“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于是二人渐生嫌隙,愈行愈远。
与祢衡不同的是,孔融对待曹操态度的反转,也并非仅仅是名士脾气使然,而隐蔽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既见操雄诈渐着,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随着时势的发展,又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对曹操,也不再流于名士式的调侃,而是进行政治上的反击。曹操北征乌桓三郡之后,北方基本平定,他将邺城作为自己的政治核心,隐隐形成了许昌、邺城两大政治中心,其封王之势已成。坐卧不安的孔融上奏献帝,应该按照古代制度,在王畿的千里之内,不应分封诸侯,试图将曹操势力驱逐出许都千里之外,这就彻底触碰了曹操的政治红线。“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虽然忌惮孔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却“潜忌正议,虑鲠大业”[9]2272。在这种情况下,御史大夫郗虑望风承旨,奏请献帝罢免孔融官职。二人的政治对立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曹操直接写信,告诫孔融“喜怒怨爱,祸福所因”,而且暗示说:“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9]2273实际上曹操已经亮剑,唯还未架到孔融脖子上而已。一年后,孔融也由将作大匠、少府降为闲职的太中大夫,却仍然无所收敛。“好士,喜诱益后进”,授人“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的口实。及赋闲职,一面享受“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名士风流,一面仍然不能忘怀世事,关注政治风云变幻。如此反复地触犯禁忌、批逆龙鳞,最终必然招致杀身之祸。
必须说明的是,孔融被杀时,曹操正在南征刘表。御史大夫郗虑与孔融不睦,又揣摩曹操嫌忌孔融,就使丞相军谋祭酒路粹上表诬枉孔融“招合徒众”“欲谋不轨”“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大逆不道”,从而酿就了这一冤案。尤为令人发指的是,郗虑不仅深文周纳,罗织孔融罪名,而且竟然“夷其族”,连两位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徒留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一句溅满鲜血的成语。
平心而论,孔融和曹操的前期冲突,本质上是崇尚空谈的名士和唯在务实的政治家之间的冲突;后期冲突,则涉及维护汉室威仪以及唯恐天子大权旁落的问题。孔融出身孔府,自然恪守传统的忠君观念。二人政治身份的区别、文化底色的差异、政治取向的不同,导致孔融悲剧的发生。孔融虽也身居高位,本质上仍是一介书生,所以虽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贡献颇多,却既无政绩,也无军功,对于政治的风云变幻感觉迟钝,“不懂权变,不合时宜”[4],唯善于在朝堂上发表鄙睨朝臣的宏论而已。这一人生悲剧既不同于祢衡,也不同于杨修。
三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九月,丞相主薄杨修被杀。杨修虽出身世族,其父杨彪官至太尉,然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远远不及孔融,也不及祢衡。祢衡还留下千古传诵的《鹦鹉赋》,杨修无论事功还是文学,都没有留下任何特别值得称道的东西,因此史书无传。倒是因为被曹操所杀,再经过《三国演义》的描写渲染,才成为家喻户晓的才子。生前寥落,死后哀荣,恐怕也是杨修始料未及的吧。
曹操为何要杀杨修?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即使在杨修被杀之后,曹操《与太尉杨彪书》也没有明确说明。于是杨修被杀,成为一桩历史疑案。《三国演义》所谓的“杨修之死”,乃是小说家言,半是史实,半是虚构,不能以此作为依据,判断杨修死因。至于《三国志·陈思王传》所载:“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10]558这一说法显然牵强。魏国初建,正是用人之际,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尚下令求贤,何以因“颇有才策”而杀之?曹操彻底消灭袁氏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何以到了这时才翻历史旧账,因“袁氏之甥”而杀之?至于《与太尉杨彪书》所说:“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自然也只是杨修被杀的莫须有的罪名。《三国典略》说杨修“谦恭才博”,进入曹操麾下后,“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10]558。这说明:杨修并没有依仗“豪父之势”,而是谦恭做人;虽身处多事之秋,作为丞相主薄,总揽内外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都能让曹操“称意”,这说明也并非每每不与曹操“同怀”。应该说,起初,曹操对杨修是十分信任的,否则怎么可能让他“总知内外”?
那么杨修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史书只是模糊地说明两点原因:《三国典略》载:“至(建安)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10]560也就是说“漏泄言教”“交关诸侯”,才是杨修被杀的真正原因。然而对于这两点原因还必须作具体分析。所谓“漏泄言教”,就是泄漏军事教令的机密,或许同《与太尉杨彪书》所谓“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应该有丝缕联系。然而《三国志》除了“鸡肋”一条,杨修触犯了曹操的军令禁忌,似乎与“漏泄言教”有所关联外,其他也别无所载。而被罗贯中写入《三国演义》,出自《世说新语·捷悟》的“一盒酥”事件、改造园门事件等,虽有名士恃才放旷的嫌疑,却与“漏泄言教”无关,并不足以因此而遭忌被杀。嫉贤妒能也非政治家之所为,何况曹操又一向标榜“唯才是举”而又是魏国用人之际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交关诸侯”——“诸侯”专指曹操已被封侯的诸子,“交关”就是交结封侯的诸子。“漏泄言教”实质上是“交关诸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非指泄露“鸡肋”之类的教令。
自从曹植私开司马门事件发生(参见《曹操集·临菑侯曹植犯禁令》)之后,曹操对于诸子可能出现“争夺太子”的问题引起了高度警惕。因为曹植私开司马门,并非名士的放旷任诞行为,在“僭越”行为的背后,隐蔽着一种对权力巅峰的渴望。所以曹操这时做了两件事:第一,自己率兵出征总是将已经封侯的诸子带在身边,并且专门下达了《下诸侯长史令》,杜绝诸子部下因为猜度人主之心而选择“政治站队”现象,实际上是防止“兄弟阋于墙”的悲剧发生;第二,尽快落实太子封号,以平息其他封侯之子对于太子之位的觊觎之心。《立太子令》专门下达给具有特殊军事才能的曹彰,个中含意也特别值得玩味。因为诸子中,曹彰武功最为了得,专门下令给他,既是重视,也是警示。但是,在曹操看来,这件事并未就此画上圆满句号。因为在曹植和曹丕身后各有一批党羽,而以曹植的党羽最为活跃。杨修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员,而且与曹植私交甚密。《三国典略》载:“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世语》又载:“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曹操)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10]561预先揣度曹操意图,然后协助曹植确定对策,这才是“漏泄言教”的本质。可见,杨修已经彻底裹入了太子之争的漩涡。
最为重要的一次:“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10]561曹操下达的两道敕令互相矛盾:一是下令不准任何人出城门,二是下令丕、植二人出城门。也就是说,无论出城门,或不出城门,都违背曹操敕令。然而,这两道敕令又有本质不同,“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是私家之令,不具有强制性;“密敕门不得出”是军令,具有强制性。曹操试图通过二人执行这一矛盾敕令的行为,考察二子品质。曹丕不因后令而否定前令,二者兼顾,既恪守“天威在颜”的为臣本分,又不因私废公,且行为宽厚;曹植则以后令而否定前令,顾此失彼,虽是执行后令,却又否定了前令,既因私废公,又挑战了“天威”,且行为峻刻。可以说,杨修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既误人也误己。虑事洞若观火的曹操,一眼就看出这是杨修在背后作祟,所以《世语》在叙述此事之后,特别点明“故修遂以交构赐死”。而《三国志·曹植传》又说:“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曹操既怀疑杨修对曹魏的忠贞,又因为他谋略过人,有可能在事有仓猝之时,使太子之位发生反转,即“虑终始之变”。加之,这一年三月曹操出征刘备,十月返回洛阳时已是病染沉疴,他不得不考虑为太子顺利即位扫清障碍,所以杨修也就不得不死了。从卞王后给杨彪夫人的信,也可以推知,杨修被杀,是在军中。由此可见,曹操杀杨修在心理上已有点迫不及待了。杨修被杀百余日,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也丢下亲手创造的偌大基业而撒手人寰。
杨修之死,并非曹操妒忌其才能,乃在于杨修卷入曹植与曹丕的“太子之争”太深,从而成为封建时代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其实,即使曹操不杀,曹丕得势也必然杀之。曹丕嗣位之后,曹植的几位密友如丁廙、丁仪等,不都被族诛了么?相比而言,杨修还算幸运,毕竟曹操只杀了他一人。
最后,必须补充交代隐蔽在杨修之死背后的两点历史关联:第一,与杨彪有隐约的联系。“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彪以疾罢。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11]1788此时,曹操志匡国难,并无不臣之心,杨彪之所以对操心生厌恶,实际上是蔑视其“赘阉遗丑”出身,深层反映了世家大族和新生权贵之间的矛盾。后来曹操当政,抓住杨彪与袁术联姻的把柄,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虽在孔融奋力营救下,“操不得已,遂理出彪”,但新旧权贵的矛盾则已白热化。曹操始用杨修,是对天下名士的一种政治姿态;终杀杨修,是对世家大族的一种政治警示。第二,与孔融也有隐约的联系。上文已述,孔融出仕乃受杨赐所辟,赐是修之祖父,所以孔融不仅与杨彪忠于汉室的政治取向一致,而且与杨氏家族也有盘根错节的政治联系。曹操将杨彪“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将作大匠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11]1788。杨彪、孔融都是旧世家大族的代表,杀孔融和杀杨修,本质并无二致。可见,曾经的政治积怨、新旧权贵的矛盾,也是杨修之死的深层原因。
四
有时,历史也会让人啼笑皆非。狂生祢衡,目空一切,唯有崇拜“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何曾想到,后来孔融、杨修却无意成为他“白首同所归”的难友。所不同的是:祢衡狂悖,陋于不识世道人心,成为矫世佯狂的个性牺牲品;孔融迂执,陋于不明时势变化,成为依附皇权的政治牺牲品;杨修不敏,陋于不解君心难测,成为太子之争的权力牺牲品。范晔《后汉书》对名士简要评述曰:“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12]2742三人游走于权力刀锋之上,渴望最大限度地攫取政治利益,结果却成为强权政治的屈死冤魂,他们自己可能不明白因何而死,历史却给出了必死的理由。当然,不得不承认,名士被杀也的确暴露了作为封建统治者曹操狰狞残忍的一面。
[1]班固.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367.
[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0.
[3]刘运好.回归历史原点:再论曹操[J].中原文化研究, 2020(6).
[4]白水河.孔融之死与汉末政治[J].西北民族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6(2).
[5]郭耀武.孔融、杨修之死的悲剧共因[J].领导科学,2015 (36).
[6]王允亮.祢衡之死与汉末士风[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3(3).
[7]班固.后汉书:卷八十下·祢衡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平原祢衡传[M]//三国志:卷十.裴松之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59.
[9]班固.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陈思王传[M]//三国志:卷十九.裴松之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班固.后汉书:卷五十四·杨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班固.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5.
On the Deep Reason for the killing of Mi Heng, Kong Rong and Yang Xiu
XIE Qi-ping1, LIU Yun-hao2
(1. Chinese Department of Bozhou University, Bozhou 236800, Anhui; 2. Chinese Poetics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The celebrities, such as Mi Heng, Kong Rong, Yang Xiu, were killed, which is always regarded as the typical example of Cao Cao’ envy of the wise and murder of the innocent. In fact, the death of the three celebritie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ir obstinacy of “dependence on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to decorate oneself and can't understand and involve current affair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ir subjective cognitive bias, personality and psychological defects. Mi Heng, who was presumptuous and couldn’t recognize the current states, became the victims of his personality; Kong Rong was stubborn and couldn’t recognize the current affairs, who became the political victim attached to imperial power; Yang Xiu was not clever and could not be cautious about his words and deeds, who became a victim of the prince's struggle for power. The three people swam on the edge of power, eager to seize political interests to the maximum extent, which turned out to be the aggrieved and wronged ghost of power politics. They themselves may not understand the reason of their death, but the history gives it. Of course,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killing of the celebrities actually expose the ferocious and cruel side of Cao Cao as a feudal ruler.
celebrities; Mi Heng; Kong Rong; Yang Xiu; Cao Cao
2021-05-26
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曹操集解读》”。
谢启平,男,安徽安庆人,亳州学院中文系主任;刘运好,男,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1.05.12
I206.2
A
2096-9333(2021)05-008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