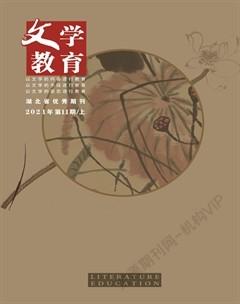例谈白先勇哲性乡愁的书写与探寻
邓凯月
内容摘要:乡愁是白先勇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却地域乡愁和文化乡愁,哲性乡愁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白先勇在不同作品中借人物对于自身存在的思考进行终极的哲学拷问,是文化和地域乡愁基础之上的升华。本文以《台北人》为例,梳理白先勇哲性乡愁的生成机制,以及《台北人》中哲性乡愁的特点及表现,由此还原白先勇对于精神原乡的追寻过程。
关键词:哲性乡愁 白先勇 《台北人》
乡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怀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而一切的有目的的、有指向的思考都可以在情感层面上被称为乡愁。龚刚教授在他的《从感性的思乡到哲性的乡愁——论台湾离散诗人的三重乡愁》一文中提出了“三重乡愁”的概念,即“洛夫先生离开大陆后的故土之思是地域乡愁, 侨居北美时对中华文化的怀恋是文化乡愁, 他对性命安顿之处和本真状态的追寻则是哲性乡愁, 也就是为“终极信念”而生的终极乡愁。”所谓“哲性乡愁”,超越了家国情怀,更多是对于人性原初和本真状态的追寻,在这一追寻过程中,人们找到自己,也在寻找生存的意义和最终的归宿。白先勇的《台北人》不仅包含着思念家国的地域乡愁和思念文化的文化乡愁,更是隐含着作者对于人存在的探寻,以及人在精神世界应该如何立足的思考。白先勇的哲性乡愁是如何产生的,他在小说中如何通过人物的命运来进行他自己的独特探寻,笔者将循着龚教授的足迹,拟在下文逐一解答。
一.哲性乡愁的生成:从地域和文化乡愁开始
如果说“哲性乡愁”可以理解为在精神上对于本质本真的探寻与回归,对于离散书写而言,它首先是建立在地域乡愁和文化乡愁之上。通过具体的、形而下的情感体验,才能够走进“哲性乡愁”的自我追溯之径。首先要对原初性的地域、文化有着真切的思念,才能对自我的存在有清楚的判断,最后才能催发对于本真和归宿的探寻意图。
白先勇的乡愁从地域乡愁发端,然后落在文化乡愁之上。白先勇在书中曾谈到:“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并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综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想得厉害。”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白先勇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复杂的,但中国文化逐渐变成一个符号,引得白先勇时时回顾。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也逐渐深沉,乡愁逐渐抽象、升腾,成为一种淬炼后的复杂态度:从思念家乡、思念风土人情开始,到思念文化,以至于对整个文化都抱着“感时忧国”的关怀。他回忆道:“在写《台北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悼念的感受。写小说时,身在美国,常常反思中国文化。
而由文化乡愁继续上升为哲性乡愁,这与白先勇独特的自身经历和敏感善思的个性分割不开。他辗转多地生活,家境几经起落,与别人有许多不一样的感悟。25岁他离开台湾去美国读书,一切都充斥着迷惑、茫然,他不知道自己的来处和归处。在寂寞中,他以充沛的感知去关照他所面对的一切,竟有超拔于现实的顿悟,这种顿悟产生于跨越广大空间和时间的体验。这样的顿悟使得白先勇的对于人与历史的思考有更有纵深感,他也渐渐地开始对于形而上的、关于人存在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索。
二.哲性乡愁产生的契机:《台北人》中的回望姿态
《台北人》开篇引用了刘禹锡的《乌衣巷》,作者写道:“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已然定下了怀念的基调。而白先勇在《树犹如此》中对为什么要引用这首诗做了一个解释:“我写《台北人》时……借西晋迁都金陵的历史,比喻民国政府渡到台湾。我用这首诗作题词,已替这本书定了个调子。那是年纪轻,大约二十五六岁,但已经有意无意地想写这个主题,跟刘诗暗合”。白先勇在创作中把人物置于错位的时空中,即把本该“活在过去”和“活在大陆”的人,放置在“现在”和“臺湾”的时空中,通过他们的生死沉浮来表达自己独特的家国忧思。
白先勇在《台北人》中描写了遗民们面临的多重困境:亲人分别、家庭破碎、精神漂泊无依,同时还有社会发展进步的普遍困境,如新旧观念冲突、人性本恶等等。面对这些困境,人们会产生向过去、向自身深处回溯的冲动,通过不断回望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但是,一直保持回望的姿态而不转向当下,将会招致苦痛,自身的意义也无法确认。《岁除》中的赖鸣升无法忘记曾经英勇战斗的历史,认为曾经自己的副排长如今做大也只是因为“捧大脚的屁眼事”,而他到如今也仅仅是怀着打回四川的心愿,住在遥远的台南,度过余生。《思旧赋》中的两个老妇人,面对残破的李公馆和后嗣凋零,除了不断感慨昔盛今衰,也是毫无办法。《一把青》中的朱青,曾经羞涩单纯、重情重义,如今是穿梭在年轻军官中间游刃有余,用游戏人生来麻痹自己。《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一直善良质朴,心里一直挂念着罗家小姐,当愿望破灭,他就丧失了一切对于美善的期待,与洗衣妇苟合,最终死得凄凉。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了能有一口气好好活下去,只能通过回望找到精神寄托,或者不闻不问过去,只是想尽办法找到乐子,以低级的快乐延续自己的人生。
三.超越回望姿态的哲性乡愁:对于存在的思考
白先勇的《台北人》中表现了一群移居台北的大陆人,他们曾经快乐、青春、拥有充沛的生命力,到了台北后却年老、悲伤、生命不断流逝、处境凄凉。白先勇在小说中表现了他们如何痛苦地追寻自己的存在。夏志清曾说《台北人》就是一部民国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除了提供遗民在台湾生活的图像,白先勇也在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中思考了人应该如何存在的问题,因此《台北人》的创作也可以看作是白先勇对于这一问题追索思考的过程。白先勇以这样一群遗民为例,从形而上的角度思考人应该如何存在,人的最终归宿是哪里这样的命题,也在文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诚然,他们的生活是贯穿着无法排解的苦痛,但白先勇也在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中给出了他的态度,即人必须清醒地活着,麻痹自己终将招致死亡。尹雪艳是一个隐喻,她是所有一切关于美好的幻想。她能抚慰所有的痛苦,安慰每一个不幸的人,却不能让他们清楚地做出判断,认识到丑陋痛苦的现实。吴经理的风湿和沙眼是痛苦的,尹雪艳安慰他老当益壮的话语是温暖的,一时听来的确抚慰人心。里面的人物喜爱尹雪艳,以为得到了尹雪艳的面面俱到的照顾和温柔的关爱,即是自己真的拥有这些东西。徐壮图脾气突然暴躁,招致了他的死亡;王贵生想要赚更多的钱,最终落了个官商勾结的重罪。他们都以为自己抓住了美好,实际上却在追逐缥缈的美好时丧了性命。这即是白先勇的判断:麻痹自己是无法真正看到自己的存在的,需抛却对于美好的已然不存在的事物的留念才能完成。
在《台北人》中,人物对于生存意义的探索有深浅之分,有些人物能够确认自身的意义,也踏上了追寻精神原乡之路,有些人物没有能力追溯自身,去思考纯粹存在的意义。回望是一个契机,确定了身份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幽微的、形而上的、个人化的探寻之径。
《台北人》体现了白先勇对于处于多重困境的人物应该如何存在的思考,他们是谁,他们从何处来,将要去向何处?《台北人》不仅写了台北人,更写了所有的人。我们可以看到白先勇给出了他的回答,即人应该清醒地存在,才能认识自身,因此对于过去和未来才能作出判断。人与历史的关系也在《台北人》中得到解答,人是渺小的,人只有通过回望历史才能确认自身的存在,也是在观望历史的基础上得出关于未来的走向的判断。白先勇在《台北人》中体现的哲性乡愁,大抵如此。
如果经历了悲剧能从痛苦中得以升华,那么人物的精神就能得到淬炼;反之,痛苦将会是徒劳的。白先勇的哲性乡愁最终从地域乡愁和文化乡愁中抽离出来,变成了对于人普遍命运的思考,《台北人》正是他思考的产物。他从琐碎的生活中看到存在的痛苦本质,并最终得出人关于肉体和精神该往何处去的结论。《台北人》的创作体现了白先勇对于终极哲学问题的拷问,他在此过程中思考自己的去向,这即是白先勇哲性乡愁的真正内涵。
参考文献
[1]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朱坤领.论洛夫的哲性乡愁[J].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23(04):10-14+
21.
[3]龚刚.从感性的思乡到哲性的乡愁——论台湾离散诗人的三重乡愁[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8(01):2-6.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