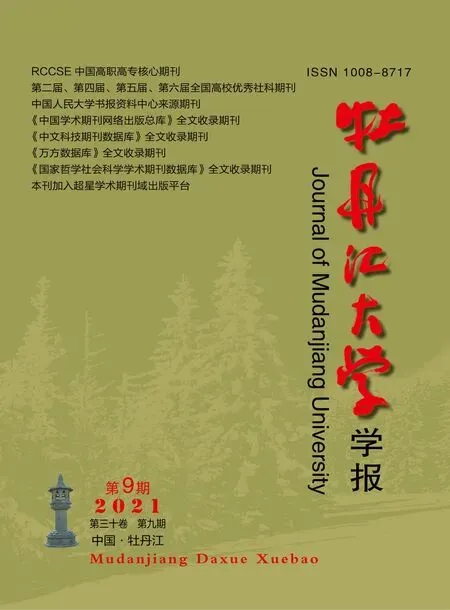从《箧中集》看元结的诗教观
邹 婷
(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种批评方法,选本通过对入选者其人及其作品的筛选,可以看出选本者的文学观念与艺术追求。周树人曾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为一集……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①由此看来,选家所选文集不仅能够让我们窥见当时较有特征的作家的作品,也能在浇筑他人酒杯的同时,诉己之衷肠,寓己之思想精髓,让我们深刻了解选者的审美倾向和文学观念,更有甚者,通过选本我们甚至可以透视某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政治风云变化。所以,元结的《箧中集》有着别样的价值。
一、《箧中集》的选诗标准
《箧中集》是盛中唐诗人元结于乾元三年所编选的诗集,在该集中收录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张彪、赵微明、元季川、孟云卿共七位作家的24首诗。虽从表面上看,这本集子似乎只是七位作家的作品集,所体现的也只是七位作家的创作特色与文学观念,但实际上此选集的序文就已经表明元结本人的诗歌观念:
元结作《箧中集》,或问曰:“公所集之诗,何以订之?”对曰:“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死而已矣,谁云无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②
从《箧中集》的序言中,我们可以获取以下信息:一,元结编选该集的原因主要是有感于“风雅”传统之不兴,所谓“风雅”传统即是《毛诗大序》所强调的“美刺”思想,也就是强调诗歌关注现实,言志讽谏的作用,而这种诗歌传统在盛唐诗人繁华绮丽的笔锋下几乎是销声匿迹了;二,元结有意批评当时诗坛“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以流易为词”的诗歌创作风貌。自汉魏时期文学逐渐走向自觉开始,到齐梁绮靡艳丽讲究形式及格律诗风的形成,再到盛唐诗人在纠正反拨中继续延续浪漫华丽的诗歌创作风貌,诗歌创作重视格律对仗,追求形式之美,重形式,轻内容的弊病依然存在,而这显然与传统诗歌所强调的“归于雅正”的文学创作风貌相背离;三,在元结看来,诗歌如果只是单纯的用于娱情悦性,宴享取乐,那必然会影响到精神人格的健全发展,甚至在更大范围内还会影响到时代风气、社会氛围,因此大雅君子、方直之士应当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在元结所选的这24首诗歌中,没有恣意汪洋的情感喷薄,相反诗歌的情绪是相对含蓄内敛的。元结继承汉魏诗人的观点,在他看来,情感只是言志的手段,诗歌的最终目的也是期望君主能够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改革弊政。诗歌不是为了抒情而产生的,情只是与外界现象沟通的媒介,是客观现实的导向并与现实相交汇融合,以此达到相应的政治目的,所以诗歌只是用来反映情绪,情绪是政治的手段,政治才是最终的目的。[1]
由此,通过以上三点,元结《箧中集》择诗尺度已然明了。《箧中集》中七人“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③,他们正直贤良忠信,怀揣德礼之心,但大多仕途不济,被当权者厌弃,被贵族阶层排斥,他们的人生是灰暗的,诗歌也是充满了人生的幻灭感,但之所以能入选,是因为在元结看来他们能够“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④。他们的诗歌,不是一味迎合开元、天宝诗人那种极致理想主义的浪漫欢歌,他们在慷慨任气、逞才使能的社会风气中,以敏锐的触觉最先察觉到盛世背后潜藏的波涛汹涌,繁华背后隐藏的重重危机,他们脱去理想、浪漫与华丽,直面现实的锋刃,他们真切感受到现实的凄怆与惨淡,唱的都是盛世环绕下的低沉之调、灰暗之音。因此,他们的诗歌不是繁华绮靡的盛世赞歌,而是沉入底层社会的真实书写,他们用诗歌来展示现实、刻画现实的冷暖、表达真切的感受,同时,诗歌又被他们寄予丰富的社会容量。他们要求诗歌不仅具有察的功能,同时还要有讽的功能,言志以讽,救时劝俗,针砭时弊。诗歌的这种功用,正与元结在其《二风诗》序言所说的“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⑤的思想相吻合。元结之所以另辟蹊径,与世迥殊,选择这七位无论是名声还是诗歌创作都在时代风气之外的作品,也正是看中了他们诗歌中所包孕的“讽谏”亦或是“规讽”意识。[2]
二、《箧中集》中的诗教观
颜真卿评价元结:“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⑥诚然,推崇“古”的审美观是元结最为突出特点之一。在诗歌创作形式上,他公开与当时流行的近体诗唱反调,反对当世文学,主张创作文辞古雅的五言古诗。而他在《箧中集》中所选的24首诗也正是五言古诗,这显然是符合他的选诗标准及其文学观念的。元结宣扬其文学思想,一开始便打着“复古”的口号,在其创作的《元次山集》中也多次提到“复古”这一观念,于他而言,复古不仅是对当前时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否定,同时更是要恢复先秦时的礼治教化,甚至是恢复太古时期的文化礼乐制度。元结期望通过这种复古的思想观念达到以诗歌干预现实的作用和目的。[3]
何谓“风雅”,简而言之,就是诗歌言志讽谏、关注现实、救时劝俗的政治功能。《毛诗序》在提到“风雅”时是这样说的:“是以一国之事, 系一人之本, 谓之风;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事, 谓之雅。雅者, 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⑦也就可以这样理解:“风”是反映政教风俗的,“雅”是言王政兴废的。在《元结的诗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一文中,作者认为,所谓“风”“既是指在用诗层面上发挥诗歌以诗观风、言志讽谏的功用”,[4]同时要求创作者在作诗层面上要学习借鉴《诗经·国风》对风俗人情、民生社稷的关注与表现,展现出淳朴的诗歌风貌。所谓“‘雅’则是指诗歌要具有‘雅正’的特点,即诗歌的主要功用在于教化而非娱乐,诗中所抒之情应以陈志言怀为旨并具有修身立德的化人作用。”[4]由此看来,“风雅”文学观在大体一致的情况下,实际上包孕着各具特色的内涵。“风”侧重于讽谏与规劝,而“雅”则是在言志抒怀的同时要求创作者重视个人的品行与操守。
综合前文所述,笔者认为元结《箧中集》中所体现出来的诗教观即为“风雅”的文学观念。下面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箧中集》与言志讽谏的诗歌观念
《唐代文学史》一书中论及元结及其《箧中集》作家群时写道:“使我们了解到在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诗坛上,出现了一个在内容上以沉实的调子抒写现实人生、形式上以恢复古调来对抗近体格律诗的创作倾向和文学流派。”⑧暂且抛开七位诗人的创作是否都是以写实著称不谈,但可以肯定的是《箧中集》选本中的诗歌一定是以写实而被元结所看重,继而被单独选订成本。
《箧中集》中的诗歌最大的特色就是写实。如王季友的《寄韦子春》中的“雀鼠昼夜无,知我厨禀贫”一句真实地再现了自身的窘境,生动地刻画了仓储稀绝,雀鼠不至的境况,从雀、鼠的层面来反映自身的尴尬处境。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除了与国家政局动荡,民生日渐凋敝,百姓食不果腹的社会现状有关之外,更与自身有贤才却始终不能得到重用有莫大关系,哀叹改变不了现状,也无法扭转事实,只能在山木再春之时,“食我山中药,不忆山中人”。于逖的《野外行》中同样有如此真实的描绘。“老病无乐事,岁秋悲更长。穷郊日萧索,生意已苍黄。小弟发亦白,两男亦不强。有才且未达,况我非贤良……水清鱼不来,岁暮空彷徨。”⑨这首诗开篇便呈现出一片悲伤凄凉的意蕴,在悲秋中感叹自己年老多病而无乐事可以愉悦心情,甚至连着这秋天似乎也更加漫长,无形中也加重了这种悲伤感、凄凉感。自己身处穷郊野外,无法经营人事往来暂且不提,兄弟也在岁月的打磨中日渐苍老。都是有才却不能通达,只能死守困境之人,造成这种困境更多的是因为君王不能识清贤才,只有徘徊独伤心。在这首诗中,尤其是“有才且未达,况我非贤良”一句,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作者在感叹自己未能进入官场显赫通达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并非贤良,但从“水清鱼不来”一句来看似乎作者又在否定这种观点,久处穷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自己不是贤良,而是因为就算是德行兼备、文质彬彬,如果无法得到君主的赏识与任用,最终也只是徒生叹息而已。张彪的《杂诗》(其一)更是唱出了贫富差距而导致不同的人生处境的哀歌:“富贵多胜事,暮亦常苦饥”“儒生未遇时,衣食不自如”,仕途的顺利与否既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会造就不同的人生处境,归根结底,这种处境个人无法扭转,最终需要的是明君贤臣的共同努力,但事实是否能够如期待般美好,想必张彪心中已然明了。
通过以上几首诗歌的分析,不难发现,《箧中集》的诗人们在完成自身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深入现实,扎根现实,写尽了现实的贫富差距与冷暖人情。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王权的威胁,外戚干政破坏朝政,君王沉迷声色、昏庸无能,国家处于困顿的局势之中。诗人们面对这样的处境,他们挣扎,反抗,埋怨,用诗歌来陈述现实,用诗歌来警醒君主,感化君主。[5]可以说,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先觉者,于繁华书写中最先走向写实,用诗歌来反映现实,干预政治,期望能够实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的政治愿景。
《箧中集》的24首诗歌,全为风格古奥的五古,一改盛唐诗歌的浪漫浓烈,用语古朴简切,明白晓畅,继承并发展“儒家有关诗歌应当文质得当、文风端正的主张”⑩,坚持儒家诗论的“风雅”传统,坚持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追求与审美倾向。[6]在元结的选诗标准下,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被突出强化,诗歌不仅能够观风俗之盛衰,同时也能够观王政之兴废。他希望能够利用诗歌向君主展示目前危机潜藏的社会局势及腐朽不堪的政治环境,以期发挥诗歌作用于现实政治的同时,也能够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7]
(二)主文而谲谏的规讽方式
据《毛诗大序》之意,诗歌是可以用来干预政治的,但是要讲究方式和原则。在《毛诗大序》的作者看来,“下以讽上”要坚持“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即是说言辞要合乎社会道义与礼仪规范,社会道义和礼仪规范从大的范围来讲是整个社会文化制度与风气的要求,但实际上也是对个体的内在自我要求。同时,在讽谏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主文而谲谏,要求创作者用委婉而含蓄的方式劝谏,而不是直言其过失,这对于诗歌创作者而言不仅是对文学修养的考验,同时更是对作家品行操守的考验。[8]有情有怨有恨有怒,但是这些情感不能随便在字里行间喷涌倾泻,而是要有节制。这其实就反映出作家在借诗歌陈志言怀的过程中也要不断约束自我,节制情感。毕竟个体的情感最终无法完成诗歌体系的构建,只有经过理性筛选后的情感才能进入到艺术创作层面上来,才能最终合乎“雅正”的要求。显然,《箧中集》的诗人是有做到这一点的。[9]
沈千运的《濮中言怀》描写自己一生苦读诗书,坚持高远之志向,树立崇高之品德,但是终未能获得帝王的青睐,以至于“五十无寸禄”,更有甚者,昔日同门友,今日却早已“贵贱易衷肠”。坚守高尚的气节,却深处衰颓贫贱的处境中,是非颠倒,雷同毁誉,倒不如归隐田园,扎根于朴实无华的自然生活中。老之将至,想到前尘往事,也忍不住感叹一番:“老大无筋力,始觉前计非。”诗人在暮年推翻、颠覆自己前半身的坚守,否认自己前半生的功绩。细细想来,诗人的这番感叹绝不是空穴来风,他怨恨自己在衰颓之际依然一事无成,无所作为,同时也是埋怨政局的昏聩,仕途的壅塞导致人生的坎坷多舛,对君主、对整个国家充满了愤怒和不满,甚至劝告自己的子女不要步己之后尘:“童儿斯学稼,少女未能织。顾此忘知己,终日求衣食。”知己到底是指君王还是其他客体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以前的种种憧憬幻灭之后,倒不如归隐终日为衣食奔波来得单纯明朗,此后不再过问家国大事,潜心顾好小家,在无奈与哀怨中舍弃大家。
再看他的《山中行》,开篇诗人便点明自己归隐的原因:“栖隐无别事,所愿离风尘。不辞城邑游,礼乐拘束人”11,诗人道隐居只是为了远离世事、风俗的束缚与限制,但事实是从“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代之为相,意味着开元清平政治的结束。到天宝初,随着景云、开元时代的一批较为贤明的官僚先后去世,政治日益腐败。”12从诗史互证的角度来看,诗人隐居的真正目的是因为政治的日益腐朽,朝政败坏,“咳唾矜崇华,迂俯相屈伸”的社会风气,导致是非不分,仁智不辨,只能像许由和巢父一样,隐居深山,不再终日为名利与功名奔波劳碌。
通过以上两首诗可以看出来,沈千运胸怀满腔的爱国热忱,虽然他抱怨自己“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感叹“衰退当弃捐,贫贱招毁誉”的黑暗现实,否定前半生的坚守与抗争,企图以隐居避世的方式逃避现实政治的磨折与刁难,毋庸置疑,他对当前的国家境况是充满了绝望感、无奈感的。但是正如有关论者所言,无论是元结本人还是《箧中集》中的七位诗人,就算他们再怎么埋怨痛斥社会的凋敝,他们的思想深处其实仍然还存留着对君主的愚忠,对封建王朝依然抱着希望与幻想,他们作诗讽刺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劝谏君主力兴图治,改革弊政。[4]所以这在本质上也就决定了他们在作诗讽谏的方式方法上不会像嵇康等人一般狂放无礼,直指酷虐的政治局势,虚伪狡诈的社会氛围,他们只是希望以一种温柔敦和的方式使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归于淳朴雅正。因此,《箧中集》中的其他诗人,如于逖、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人,他们虽然也在诗中抱怨现实的艰难处境,如“与君仍布衣,岂曰无其才”,“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余里,贫贱多是非。人生早艰苦,寿命恐不长。二十学已成,三十名不彰。岂无同门友,贵贱易衷肠”13,“上德兼济心,中才不如愚”,但是情感始终是理性、平和的。这些语词中虽然流露出诗人的愤懑与无奈之情,但是他们对朝廷的讥讽,对君主的埋怨,对政局的鄙夷,并没有任流铺张扬厉般的情感肆意喷流,相反,他们的恨与痛、忧与愁皆付诸笔下,化作点点滴滴,娓娓道来。情感的诉说与表达是相互关联的,《箧中集》的诗人在陈述他们亲眼所见的黑暗现实时,采用的是冲和平淡的表现方式。同样,他们在黑暗面前,所传达出的对志向、气节、质性的坚守,对家国的担忧与关注,也是含而不露,深情委婉的。如“君子有褊性,矧乃寻常徒”“人生为有志,岂不怀所安”“人生各有志,在余胡不激”。
诗歌是诗人情感与主流政权沟通的媒介,往往需要借助赋、比、兴三种手法完成诗人情感的寄托与传递,虽然这些表现手法在七位诗人的笔下表现得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他们借助诗歌,采取委婉含蓄的方式,向上传达民情,向下排遣民怨,不直指君主之过失,较少运用政治性的话语,柔风细雨般的情感传递方式,继承与发展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歌美学。在借诗歌讽刺政治,暗寓时弊中,也包孕着《箧中集》诗人们及其元结本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国家和君王的忠贞之心。[10]
三、《箧中集》与元结
虽然《箧中集》中的诗歌并非元结本人亲手所作,但是从他所选的诗歌中,无论是伤离愁别恨还是怨政治凋敝,社会凌乱不堪,皆可见其人之德行、学识与文化观念。郭绍虞先生曾说:“《箧中集》原序毕竟喊出中唐现实主义的先声。”通过七位诗人的创作与共同的艺术追求,不仅弘扬壮大了元结的诗歌主张,同时也可以视为“是唐诗由浪漫回到平实,由天上回到人间,由华丽回到平淡”14的真实反映。言志讽谏、陈志抒怀的诗歌表现功能与主文而谲谏的情感表达方式,元结通过对这些诗人的创作呈现出他对盛唐欢歌式的创作方式的反拨,对先秦、汉魏文学诗教观的继承与发展。[11]
元结编选《箧中集》,虽然是个体的行为,但以《箧中集》为中心毕竟形成了一个“箧中集”式的诗歌创作群体,这一作家群,在元结的首倡之下,继承儒家诗教观,实现诗歌反映现实、干预政治的政治目的,发挥诗歌感化君主,教化人民的功能。《箧中集》中的7位诗人的诗歌,以其美刺的内容,质朴的风格,平实的情感,[12]体现了元结“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的诗歌观念的践行,强调文学必须反映生活、反映政治、反映时代,在借诗歌以达到规劝、讽谏君主目的的同时,也是对自我文学观念的重塑。
注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04.
②③④⑨〔唐〕高仲武、元结等编选,《唐人选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7,27,27,30,29,31.
⑤⑥〔唐〕元结著,孙望校《元次山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10,170.
⑦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选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2.
⑧乔象钟、陈铁民,《唐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584.
⑩韩彩丽,《元结诗体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4.
⑫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9.
⑭胡适撰,骆玉明导读,《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