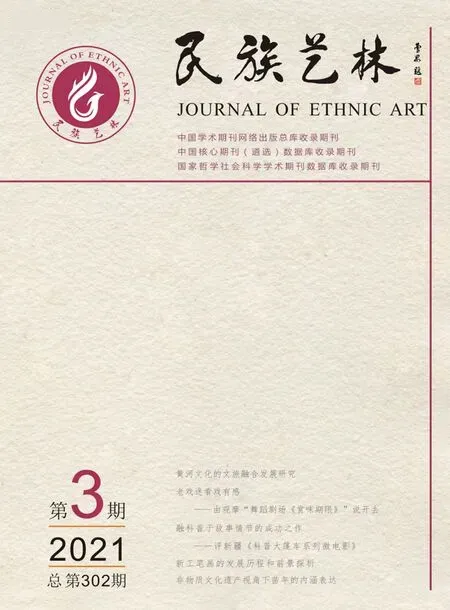沉寂时间、游荡叙事诗与时间晶体
——论毕赣电影中的“时间”影像构建
王 彬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4)
作为贵州新力量导演的毕赣,从短片《金刚经》(2012)、《秘密金鱼》(2016)到长片《路边野餐》(2016)、《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一直都坚守着他的艺术电影创作之路,延续着其一贯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他以对“时间”的探索进行触及心灵与在地情感的先验性艺术表达,在故乡凯里的氤氲幻梦中交织着实在与潜在、想象与回忆。塔可夫斯基认为导演工作的本质“就是对时间进行雕刻”[1],毕赣是雕刻时光的诗人,“时间”影像是其“作品序列”中“某种近乎不变的深层结构”[2],他将古老佛经《金刚经》中“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的时间观念注入他的电影作品,创造出并置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荡麦乌托邦”,构建出德勒兹所言的“时间-影像”(time-image)。蕴藏在日常时刻中的沉寂时间、沉沦于时间之网的游荡者和现实与潜在无限循环的时间晶体,共同构成了毕赣电影文本内在的时间结构。
一、时间-影像
伯格森区分了两种时间,一种是机械空间化的时间,另一种是真正绵延为本质的心理时间。心理时间是人意识流的意象化,是一种生命体验。法国电影理论家德勒兹在其著作《时间-影像》一书中以伯格森的第二种时间“绵延时间”为基础提出一种以“时间-影像”为核心的电影哲学观。他认为:“某些电影可以将绵延时间的流逝予以视觉化,他将它们称为‘时间-影像’。”[3]这一类电影有别于经典电影的“动作-影像”,呈现的不再是“感知-运动情境”,而是纯视听情境。二战后的现代电影中多体现为这种“时间-影像”,尤其是在欧洲的艺术电影中,如费里尼、安东尼奥尼、阿伦·雷乃、塔可夫斯基等作者电影中。而以塔可夫斯基为标榜的毕赣在他的电影作品中继承了这种“时间-影像”的特质,不以因果逻辑来结构戏剧化的叙事,而是以非时序性时间的心理逻辑结构故事和人物,时间的流逝凭其自身而呈现,过去、现在、未来相互交织,在时间与记忆中召唤“潜在影像”。人物沉浸在“感知-运动”断裂的情境之中,成为时间之网中的游荡者。
在短片《金刚经》中,陈升与老歪进入荡麦,过去杀人的情节与现在取钱的路途碎片化地穿插交错;在《路边野餐》中陈升在寻找侄子卫卫的路途中进入荡麦,经历过去、现在和未来;《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下简称《地球》)中罗武在追寻情人万绮雯的旅程中踏进荡麦,欲望、记忆与梦魇交织。纵观其作品,主人公都是在时间的迷宫中经历“实在”与“潜在”,“时间”是贯穿毕赣电影作品的母题。毕赣电影的“时间”影像在日常时刻的绵延中积蓄着一种沉寂力量;人物梦游般地游走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成为时空的游荡者,最终在现实与潜在循环的时间晶体中达成与过去的和解。
二、沉寂时间
德勒兹在谈到小津安二郎的作品时提到他以纯试听影像替代以因果逻辑结构叙事的“动作-影像”,在日常时刻的平凡影像中弥散着沉寂时间,毕赣电影中也存在着这种“沉寂时间”,“自然或沉寂被定义为连接着日常的‘统一而又永久’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空间是个人生活的物质与精神的一部分。空的空间或空白使时间延宕在静物或景观中,这些影像(静物、空镜或风景)抑制了表面运动,同时寻回固定镜头的力量。这种能量不仅释放出文化与美学的元素,更重要的是,它赋予场面一种直接的穿透,因此创造了纯粹时间的节奏”[4]。“日常”与“关键时刻”不再对立,纯粹的心理时间绵延在画面的沉寂中,在平凡日常的情境中积蓄着一种“沉寂力量”[5]。
毕赣的影像中充斥着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多展现黔东南小镇凯里人的生活面貌与日常情境,以纪实化的手法真实再现南方小城人的日常时刻。《路边野餐》通过粗糙颗粒质感的镜头再现凯里人的生活状态,简陋的凯里小诊所,镇民看病打针,医生光莲迟缓的烧水,镇民百无聊赖的打牌,无所事事的打台球,陈升在阴湿隧道中买香蕉,闲散的打气球,小吃摊的“打两碗粉”,酒鬼“打酒”等,生动地再现了小镇底层人的状貌。这种日常生活的写实影像绵延着沉寂时间,在平凡中蕴含着一种沉寂力量——乡愁。日常时刻的生活影像中充斥着个人的情感与记忆。毕赣对故乡凯里的乡愁如同汾阳之于贾樟柯,贵州之于陆庆屹,在电影中“自动书写”着对故乡人事的依恋与怀念,在沉寂的平凡影像中回归心灵的原乡,记录着个人体验的地方记忆。毕赣将自己的经验记忆雕刻为影像中的乡愁文化,在沉寂时间中凝结为集体记忆。
同样,对白、诗歌在较长的空白中绵延,也充盈着沉寂时间。小镇诊所中陈升与医生光莲的对话勾连出光莲与“爱人”的前尘往事,爱人为自己取暖,买衣服的约定,磁带的意义,以及陈升与妻子的旧年遗憾。往事娓娓道来,在漫长的静寂中延伸,口述往事的零散叙事取代因果逻辑叙事,以“听觉符号”在口述的记忆碎片中拼凑起记忆脉络,在对白绵延的沉寂时间中观众得以深入窥探人物内心的悲痛与梦魇。时间在话语的流动中涌现,过去通过话语被召唤于现在,从“潜在”走向现实。用凯里方言吟诵的诗歌是毕赣影像文本所独有的文化标志,诗歌承载着时间,勾连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诗歌的沉寂时间中不仅内蕴了人物情绪,而且达成推动叙事的作用。《路边野餐》中陈升坐上成年卫卫的摩托车进入荡麦,画外音响起陈升用凯里方言吟诵的诗:“通往岁月楼层的应急灯/通往我写诗的石缝/一定有人离开了会回来/腾空的竹篮装满爱/一定有破碎像泥土/某个谷底像手一样摊开。”诗歌开启与过去、未来相逢的魔幻之旅,同时蕴含着陈升对过去的怀念与追忆,期待着与往事旧人的重逢,于梦境中完成内心创伤的弥补与救赎。“而在日常语言中,词建立了一种与‘生活形式’同构的及物性,由于其口语的、地方的、民间的特征,乡愁叙事得以借助日常语言安顿人的情感、记忆与认同”[6]。诗歌用凯里独特质感的语调吟诵,蕴含着一种沉寂力量,表现着人物的乡愁与情感认同。
不仅是日常情境与诗歌会绵延沉寂时间,静物与空境中也蕴藏着这种沉寂时间。小津安二郎《晚春》中,纪子出嫁前与父亲的最后一次旅行,旅馆中的花瓶静置于屋角一隅,静默的花瓶是人物内心活动的外化,积蓄着人物的泪与笑,直接承载着时间的纯粹绵延,又包含着一种沉寂时间。毕赣电影中的静物也充盈着这种沉寂时间,在凯里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平庸中沉寂着不凡。
时间延宕在静物中,静物呈现纯粹的时间。毕赣电影中的静物带有时光印痕的寂感。“寂”一词源于日本,“”是朴素自然的粗糙美,“寂”是时光流逝的光泽痕迹。“寂”是自然的锈迹,时光的印泽,带有寂感的静物是时间的纯粹影像。位于黔东南地区的贵州凯里是毕赣导演的故乡,更是他的主体精神世界。一方面,在毕赣的影像中显现凯里在城镇化的历史性建设下遗留的物质化存在静物,《地球》与《路边野餐》中锈迹斑斑的房屋、简陋的录像厅、漏水的房间、破败的台球厅、防空洞、废弃的轿车、废弃轮胎、破旧的沙发、老式绿皮火车、杂乱的摩托车修理店等。万物由盛而衰,由喧而寂,这些静物充满自然的锈迹与时间的岁月感,无言诉说着历史变迁下生活境遇的痕迹。而这些最平凡或说最日常的废弃物却在无言的静寂、看似无用的废弃时间中释放出德勒兹所言的“沉寂力量”,反映黔东南农村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与城乡转型剧变下隐匿的阵痛。另一方面,影像中也容纳了导演私人记忆中的静物,《秘密金鱼》中的乒乓球拍、舞厅灯光球、鸟、水池、歌舞厅、瀑布、镜子、破旧的椅子等,作为个人情感容器的静物直接展现作为本质的纯粹时间,成为重建记忆的“视觉符号”。而这些“视觉符号”包含着过去能指的个体乡愁意识,形塑了“记忆”影像,召唤毕赣对过往时代的怀旧想象,观众在“凝视”这些静物时也静静参悟时间的流逝。
空境下的静物是纯粹绵延时间的直接显现。贵州的氤氲雾气、多雨潮湿、重峦叠嶂承载着导演个人的成长记忆,特有的地域孕育出似梦似幻、神秘迷离的超验性“时间”影像,使凯里成为毕赣标志性的影像符号。在短片《金刚经》中的回忆片段,陈升和老歪在山涧歇息,空境固定拍摄氤氲的烟云水雾升腾,两岸峭壁耸立,山雾缭绕,绿阴清幽,一种寂感油然而生。在镜头绵延的时间中,凝固着被良知拷问的悔恨与怅惘。《路边野餐》陈升出狱的回忆片段中,长镜头主观视角跟拍陈升驾驶车辆在盘旋的公路上,观众跟随陈升一起在这段漫长的空境中“凝视”前方雾气笼罩的公路与两旁湿润阴沉、葱郁的树木,时间在镜头中绵延行走,沉寂时间默默涌动,展现出贵州黔东南地域寂性的美感与诗意,并默默蔓延着陈升不可言说的人生况味。“‘寂’并非把人的心灵引向死寂。它是对某种缺憾状态的积极接受,是对‘欲界’的超越和解脱,是洞悉宇宙人生后的睿智与机趣。”[7]在寂静物中询唤记忆,此时的静物不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和时间的,毕赣就在这独特寂魅力的静物中与世界对话,洞察人生。
三、游荡叙事诗
“德勒兹通过分析《德意志零年》《斯特隆博利火山》《意大利游记》等影片,指出现代电影中的人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电影更像是游荡叙事诗,其中的人物成了幻想者、梦游者,他们被安置在一个杂乱无章的环境中,只是被动地看、听和记录,却不能回答、行动、判断,作出积极的反应。”[8]时间正是以这种“游荡叙事诗”的形式存在于毕赣的影像中,漂泊的游荡者与“在路上”的“游荡形式”孕育出“时间-影像”。人物表现为某种运动无力,沉浸在“感知-运动”断裂的情境之中,成为时间之网中的游荡者。毕赣的电影就如同一首首游荡叙事诗,游荡者梦游般的在时间旅行中询唤记忆的乌托邦,凝视过去、相遇未来,在时间与记忆中召唤“潜在影像”,释放无意识的梦幻。
毕赣被称为“凯里王家卫”,在他的作品中有某种气质与王家卫相像,影片的潮湿质感,对时间和记忆的追溯,沉沦于时间罗网中的游荡者。这些游荡者表现着某种运动无力,而世界化的运动取而代之,以绵延的时间连通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王家卫的《阿飞正传》中,阿飞是一个异乡的游荡者,他漂泊在寻找母亲的路上,最后换来的却是亲生母亲的拒之门外。母亲的缺席致使他流浪的心灵无处安放,灵魂充满无尽的空虚。同样,毕赣电影中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种游荡者,在漫长时间的漂泊中无所依从。《路边野餐》中的陈升童年母亲缺席,出狱后母亲去世,母亲是他生命中的“不在场”,时常梦到母亲的蓝色绣花鞋如梦魇一般缠绕着他,踏上镇远之旅去寻找侄子也是缘由母亲的临终嘱托。陈升如同一个梦游者坠入“荡麦”的超现实时空之旅,在这里他凝视过去,见到失去的妻子,遇见未来,重逢成年卫卫,达成与过往人事的和解。但当魔幻的荡麦之旅结束后,他依旧是无家可依的游荡者,带着宿命般的无奈。《地球》中的罗武幼年时母亲出走,以母亲命名的“小凤餐厅”被去世的父亲留给继母,他成为无家可归的游荡者。母亲的缺席留给他精神上的创伤,因此他被化了妆酷似母亲的万绮雯所迷惑,将对母亲的“俄狄浦斯情结”投射到万绮雯身上,成为万绮雯的“枪”,替她暗杀左宏元。罗武呈现出孤独至极的精神状态,在时间中游离踏入荡麦。在荡麦的梦境中他重逢母亲、情人,完成与过去的告别与释怀,但当梦醒之后,他能否找到万绮雯是无果的。现实中的他是无父无母,离婚后无依无靠的中年困顿者,是情感无依的游荡者。梦醒之后留下的只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无奈。陈升与罗武正如不曾停息的无脚鸟一般,永远逃脱不掉漂泊的命运,挣扎于时间的牢笼中,趋向于“时间”影像中的游荡者。
德勒兹认为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中充满了散漫的“游荡形式”“他的作品借用游荡(叙事诗)形式,如火车旅行、打的、乘公交车郊游、骑自行车或远足……”[9]毕赣的电影中的人物也是以这样一种“游荡形式”展现一种“在路上”的游离状态,时间在游荡的绵延进程中涌动。《金刚经》中陈升与老歪踏上去荡麦河边取钱之旅,搭乘货车到达荡麦地界,又步行穿过荡麦,在游荡的旅途中感觉到的是时间的流逝。人物游走于荡麦中,“游荡形式”展现出人物无根的漂泊状态;《路边野餐》中,陈升骑摩托车漫游凯里、登上火车去寻找侄子卫卫,又坐上成年卫卫的摩托车进入荡麦,交通工具作为一种“游荡形式”起着串联时空的作用,牵引置身于时间中的游离者,也串联了碎片化的影像。火车行进象征着时间的流逝,是引发时空变换的交通工具。陈升坐上通往镇远的火车时,低角度拍摄火车从隧道中急速驶过,预示着时间变奏,即将闯入梦幻空间——荡麦。而当梦境结束,陈胜乘坐的火车呼啸而过,对面火车上所画的时钟逆行,象征着时间的溯回。
“与‘公路电影’中的旅程相区别的是,‘游荡’不是通过动作来衔接情节,而是让角色融进空间的持存与时间的流逝之中。被强调的是他们的‘看’而不是动作的创造。”[12]从《金刚经》《路边野餐》到《地球》,毕赣的影片有着公路片的外壳,但经过导演的拆解、重塑,一反公路片戏剧化的情节,以游荡形式来消解故事性,人物在游荡的过程中凝视时间的流逝,呈现一种生命的时间体验。
四、时间晶体
毕赣的电影中现实与梦境、想象与记忆错乱交织,让人无法辨识真假,在这种不可辨识的状态下时间脱离运动而存在,现在与过去、实在与潜在互相循环凝结成时间晶体。“德勒兹指出现实影像本身具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潜在影像,并认为现实影像及其潜在影像构成最小的内在循环(晶体循环),至少是一个尖点或一个点,但这个最小的内在循环是一个具有不同元素的物理点。二者不同,但又不可辨识,就像彼此不断交换的现实与潜在。”[13]在时间晶体中我们看到的是非时序性时间,现实影像(现在)与潜在影像(过去)的不断循环。在毕赣的影像中,过去与未来、现实与梦境相互交织,在时间与记忆中召唤“潜在影像”。
首先,在时间晶体中现实与潜在的循环是通过“镜子”来实现的,“镜像对于镜子反映的现实人物而言是潜在的,而就镜像只给人物留下某种简单的潜在性并将其推到画外的镜子而言,又是现实的。”[14]这种镜里与镜外,实在与潜在的无限循环如同钻戒的不同面相,凝结成时间晶体。《路边野餐》中采取镜中镜的构图,透过镜像看到陈升与酷似前妻的女人在理发店聊天,陈升回忆自己与妻子的往事,帮大哥寻仇的经历,将潜意识中的隐匿的伤痛宣泄出来。陈升是现在的,妻子是过去的,过去是“潜在影像”,是镜像。在《秘密金鱼》中,当小男孩将乒乓球拍扔进水池,下一个画面从倒立的瀑布衔接到梦境。水的出现如同“镜子”,透过水面我们仿佛进入晶体的内部。在歌舞厅面对面放置的镜子成为不断反射回忆与潜意识梦幻的活动镜子,真实与想象不可辨识。《地球》开头的舞厅灯光球不断旋转反射五彩斑斓的光影记忆,如同一个混合实在与潜在的时间晶体,预示人物即将进入超现实的赋魅世界。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玻璃、水、镜子,这些事物承担着“镜子”的功能,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时间的双向运动,每一刻都成为过去,又不断地走向未来。现实与想象、回忆与梦幻交替沉浮,不断旋转映射着人物的心理镜像。
其次,毕赣在近似“幻影之旅”镜头的绵延流动中呈现在尖点的共时性,将过去、现在与未来并置于同一坐标上,形塑时间晶体。让观众和人物一起沉浸在虚实游离之间感悟时间的存在,在现实影像与潜在影像的不断循环中给予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审美体验。“第一人称视角的‘主观’运动镜头,似乎镜头代替了眼睛,令观众感觉到自己离开地面漂浮,且跟随镜头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中穿行、运动、飞舞和漫游。这样一种镜头被称为‘幻影之旅’(phantom ride),它带给人们一种‘被推动’的‘超现实’体验。”[15]毕赣就在这种超现实的“幻影之旅”中形塑他的时间晶体。“幻影之旅”的长镜头保持着时间上的连续性与流畅性,承担着心理时间的“绵延”功能。在长镜头塑造的“梦幻”影像中时间摆脱运动的桎梏,进入深层梦境,观众感受到的是时空连续体的流动。《路边野餐》用42 分钟的长镜头将过去(妻子)、现在(陈升)、未来(成年卫卫)并置于想象中的“荡麦乌托邦”,人物在这里与时间重逢,弥补遗憾。观众以“幻影之旅”镜头的视点穿行其中感受虚拟的幻觉魅力,在过去时面与现在尖点的共时中,想象、记忆与真实变得难以分辨;《地球》用长达一小时的3D 长镜头让观众与罗武一起沉浸在超现实的荡麦梦境中,重逢过去(凯珍、疯女人)、未来(小白猫)。过去、现在与未来并置于氤氲的绿色幻梦中,在超现实时空中含混着潜意识与自我分裂,逝去的时间/记忆凝滞于梦境中。毕赣不仅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置于同一镜头坐标中,而且以“幻影之旅”镜头的主观体验推动观众感知“潜在影像”,召唤情感与记忆的再现。罗武与凯珍漂浮到小镇,映入眼帘的是小镇古朴简陋的建筑;罗武跟随凯珍的主观视点展现小镇居民夜晚的日常生活,唱歌、跳舞、打篮球、吃面、卖货。梦幻的荡麦是现实凯里的镜像,这些“潜在影像”与“现实影像”一一对应,询唤着主人公与毕赣导演双重的情感记忆与怀旧想象,在时间与记忆的交错中构建家园乌托邦,书写个人的文化乡愁与怀旧情绪。实在与潜在的不可辨识凝结成时间晶体,呈现着虚拟现实的艺术魅力,而观众随人物一起漂浮、穿梭、走动,感受的是超现实的主观体验。
五、结语
毕赣以观照个体生命经验和触及心灵的影像进行对“时间”的探索,以一场“追忆似水年华”的回溯之旅,展现时间的深层次自由;借“时间”影像描绘记忆中的情感特质,窥探最深层次的心灵自由,直观表达人的精神和意识活动。在平凡日常的沉寂时间中“自动书写”对故乡人事的依恋,聚焦于凯里人的日常时刻,回归心灵的原乡;游荡者梦游般地在梦中虚境询唤记忆的乌托邦,凝视过去、相遇未来,在时间与记忆中召唤“潜在影像”;在时间晶体中实在与潜在相互循环,实现个人情感与文化乡愁的双重补偿。毕赣以“时间”影像的构建完成了他在地性的艺术表达,为中国艺术电影开拓了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