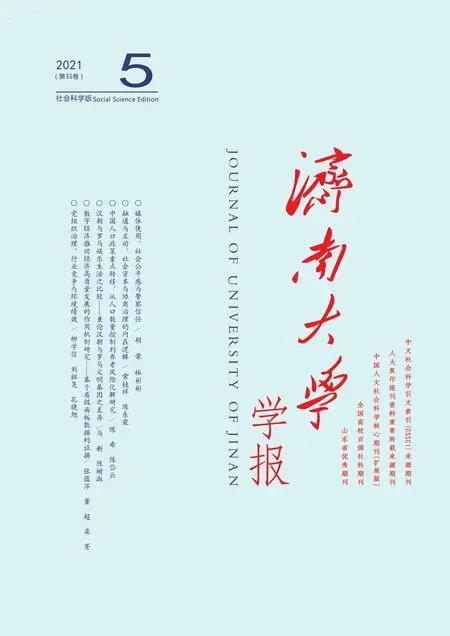明清时期山东乡贤崇祀文化探析
宋 暖
(山东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002)
山东乡贤崇祀文化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地域特色。其萌发于上古的“尚贤”社会意识,汉代以降,统治者的尚贤促使尚贤文化的萌发与形成,为后来的乡贤崇祀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明、清朝廷明文规定举荐和祠祀乡贤,又使山东乡贤文化的发展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进一步促成其成熟,并通过祀典崇祀的教化功能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文化。
一、明清乡贤崇祀形式的演化
从唐宋到明清时期,山东乡贤崇祀的形式经历了若干变化。乡贤崇祀纪念、表彰的方式主要有立碑、刻石立传,建坊旌表、修建专祠,以及在儒学(府州县学)学宫建乡贤祠附祀,乡贤传记与地方志书写等几种。
通过石刻、碑刻方式,为乡贤树碑立传,用墓表、碑文等形式追怀先贤。本地乡贤人物去世后,为之刻石立碑,表其事迹于墓碑。明清时期,莘县对出仕或在乡有德望的乡贤,要为其建立“德望碑,悬匾额,旌其门”。历城乡贤张养浩,为元代著名政治家、诗人、散曲作家,在任职聊城、堂邑期间多有善政,深受民众爱戴,以至在其调离十年后,百姓仍然为之立碑颂德。《堂邑县志》载有元明善所撰写的《县尹张养浩去思碑》的碑文,对其一生大加赞扬。
以建坊旌表、送匾额等方式对乡贤加以表彰。明清时期,对于在科举、公益、官绩、义行等方面做出突出成就的乡贤人物,地方上往往借助兴建牌坊来加以表彰。即如有关方志所言:“贤人君子,实德著于当时,余芳流于后世者,每赖坊表以奕耀”。例如明朝嘉靖时,莱芜的四史坊,就是为表彰监察御史高朗等人修建。弘治年间当地还为“出粟赈济者”李本修立了义民坊(1)嘉靖《莱芜县志》卷4,建设志,坊表,明嘉靖刻本。。主持建坊旌表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是为了表彰先贤,朝廷颁旨颁发旌表敕令,兴建牌坊、设置坊表,即“奉旨建坊旌表”。如清代新城王之辅的“廉能任事”坊,王之垣、王象乾的“父子尚书”坊表,王重光的“忠勤报国”坊表,王麟等四人的“四世宫保”坊表,王象垣的“纲纪中台”坊表,何世济的“理学名臣”坊表等(2)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26,杂识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一种是由州县地方官主持修建的牌坊,或是对急公好义的乡间热心公益的人物送匾额,以示表彰。如晚清时寿光县城内尚有刑部尚书赵鉴祠、太常司少卿刘铳坊,明代大学士刘祤的专祠昭贤祠等,即为当地地方官员动议兴建(3)光绪《寿光县乡土志》,地理,清末抄本。。
修建专祠,纪念先贤。在设立乡贤祠之前,多为专祠,即以单个人之祠的方式纪念某位先贤或某几位先贤。明清时期,济宁的学宫内即设有仲子祠、任子祠、高子祠、樊子祠、曹子祠、郑子祠、陈子祠、司马子祠、何邵公祠、二贤祠等(4)民国《济宁县志》卷2,法制略,民国十六年铅印本。。清代山东几乎所有州县都有各式各样的先贤祠,如茌平的四贤祠(崇祀乡贤鲁仲连、淳于髡、马周、张镐),新城县的三贤祠(崇祀鲁仲连、诸葛亮、宋文忠公)。地方先贤崇祀专祠的设立,延续了古代崇贤、尚贤的观念,强化了对本地先贤的精神认同,为明清时期乡贤崇祀文化的兴起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
兴设乡贤祠,使乡贤崇祀制度化。乡贤崇祀源于对先贤的崇祀,山东唐代就开始有先贤崇祀,但所祀先贤的籍贯并非本籍。自宋代起,开始将有宦绩道德的官员入祀乡贤祠。宋元时期,乡贤和名宦统称为先贤,混祀在一起。先贤祠并不区分任职官员与土著先贤,这恰能说明当时的土著先贤(乡贤)影响力尚不足以激劝本地士民,而需要以更为社会所认可的名贤为表率,因此有影响力的名贤,即便是外籍也可以在地方名贤祭祀中占据重要地位。宋元时期在庙学祭祀名宦、乡贤(先贤)虽已出现,但远未普遍化,相关制度还未建立。
到了明代,普遍把名宦、乡贤祀典放在庙学并成为一种制度。在严格的州县学籍和户籍制度下,士人的地域归属意识逐渐强化,官员、地方贤哲混同祭祀,已无法满足日益成熟的地域认同意识。致仕官员必须回原籍的规定,使官僚已经无法如宋代一般随意迁移它地,多是返回原籍,官僚将注意力放在原籍之地方社会,在地方兴文教、施教化,使其家族势力逐步在当地积累,家族势力、族人遂谋求在当地建立文化权威地位,地方祭祀制度随之改变。明洪武四年(1371),朝廷诏令州县学校各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守令,右祀乡贤。先贤祠大多于孔子的正殿两侧分设祠堂,春秋仲月附祭于孔庙(5)雍正《山东通志》卷14,学校志,名宦乡贤祠,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自此,山东民间自发而松散的先贤崇祀被纳入到政府祭祀体系之中。
审视明代山东各地名宦、乡贤二祠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在天顺、成化、弘治年间多承袭旧制,以先贤祠作为乡贤崇祀的场所,一般采用“同堂合祀”的方式,祭祀名宦、乡贤。成化朝进士文林,曾为博平县令,他在该县“敬遵常典,建祠三间于新学之东南,合乡贤名宦而祀之”(6)文林:《文温州集》卷8,《博平县先贤祠记》,明刻本。。既是“常典”,也就表明乡贤与名宦合祀在一座建筑内,“同堂合祀”为当时各地普遍遵用的形式。
大致在弘治末年,朝廷推出在地方各级庙学建立乡贤祠和名宦祠的制度。该制的基本内容为:学宫中的先贤祠被界分为乡贤祠和名宦祠,“宦于其地而去后见思,是之谓名宦;生于其乡而众共称贤,是之谓乡贤”(7)(清)汪森:《粤西诗文载》文载卷39,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大部分学宫(庙学)都确立了名宦、乡贤崇祀,两者对称,分别建祠,布列学宫戟门左右。
到明正德、嘉靖之后,乡贤祭祀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德年间,山东各地相继兴建先贤祠和乡贤祠,到嘉靖中叶发展至一个高峰期。嘉靖十三年(1534),明朝廷明确了乡贤、名宦入祠资格,规定“仕于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及于民者,謂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谓之乡贤”(8)顺治《蠡县志》卷4,清顺治八年刻本。。对于兴立先贤祠则规定,“果有遗爱在人,乡评有据,未经表彰,即便及时兴立祠祀,以励风化”(9)(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85,《严名宦乡贤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崇祀乡贤制度受此影响,不管是标准,还是人数较前都有变化,对本朝乡贤的祭祀开始普及。从天一阁藏嘉靖年间的山东方志文献看,这一时期,乡贤祠和名宦祠已经分开,乡贤祠逐渐独立,“二祠分祀”成为主要形式。只有个别县没有分开,如淄川县学还是一室二祠。由合到分,在各地的时间不一,但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乡贤祠“祀本地名流”“祀邑绅之负德望者”,祭期一般在春、秋仲月丁日,祭祀先师后,主祭官率士儒、僚属祭于乡贤、名宦二祠。
明代中期乡贤、名宦二祠的普遍化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朝廷积极推动各地庙学乡贤祠的建立,州县地方官则是“奉诏令而为之”(10)嘉靖《临朐县志》卷2,官政志,学校,明嘉靖刻本。,以改建或新建名宦、乡贤祠为己任。在各州县普设乡贤祠、名宦祠的基础上,乡贤祠与名宦祠大多分祠祭祀,使得乡贤的祭祀进一步规范化。乡贤祠成为祭祀当地品德风节高尚、文章著闻、政绩卓著者的祠堂,并构成文庙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崇祀制度的确立,提高了乡贤在社会大众中的地位,推动乡贤文化呈现出扩散的态势,对促进乡贤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无论先贤祠抑或乡贤祠,所祀人物大致分为两类,即前朝人物与本朝人物。前朝人物上溯至春秋战国,下迄元代,多为历代名臣、硕学大儒等;本朝(明朝)则有府、县(州)的差异。府学乡贤祠所祀均为廷臣大吏,而州县所祀多为知县(州)、教谕、训导一类的下层官员。各县所祀乡贤人数基于本县历史文化、教育发展而多少不等。以青州府属各县为例,府学34人、博兴5人、高苑8人、乐安8人、寿光8人、昌乐2人、临朐7人、安丘3人、诸城24人、蒙阴1人、莒州9人、沂水3人、日照5人;武定州7人,州所属阳信2人、海丰4人、乐陵3人;另外,武城13人(武城旧志载30余人,到嘉靖时减为13人)(11)嘉靖《青州府志》卷10,人事志,祀典,明嘉靖刻本;嘉靖《武定州志》附,属县志略,明嘉靖刻本;嘉靖《武城县志》卷4,祀典志,乡贤祠,明嘉靖刻本。。
满族入主中原,沿袭下来诸多有利于其统治的明代制度。“顺治初年,定直省府州县,建名宦、乡贤二祠于学宫内,每岁春秋释奠,于先师同日,以少牢祀名宦、乡贤,皆地方官主祭行礼”(12)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8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自此,乡贤祠、名宦祠与当地庙学进一步结合起来。
到清雍正时期,仍延续崇祀乡贤的做法,各县多重建乡贤祠,绝大多数学校都设立了名宦祠和乡贤祠,乡贤祠几乎都是与名宦祠对设,其位置、建筑绝大多数与名宦祠相同。入祠的乡贤,通常将其姓名镌刻于碑上,定期致祭。
从乡贤崇祀的发展演变看,推荐乡贤入祀乡贤祠,以明代最为兴盛。清初为了缓和满族入主中原后的矛盾,也极为重视举荐乡贤入祀,乡贤崇祀有过复兴。但自清中叶后,因社会动荡,乡贤崇祀逐渐衰落。到清末,一些地方原乡贤祠所祀部分明代乡贤的事迹已经“失考”湮灭。以冠县为例,乡贤祠崇祀的人物明代之前的1人,明代14人,清代仅1人。光绪之后,不但乡贤失考,而且先贤祠也残颓荒圮。“迨改建民国,国体变更,此项祀典几等弁髦,祠内木主亦散失殆尽”(13)道光《冠县志》卷4,学校志,学宫;卷8,人物志,乡贤,民国二十三年补刊本。。
扩展变易乡贤书写,赓续乡贤崇祀文化。明清时期,乡贤崇祀文化通常是祠祀与传记书写并重,二者交相为用。基于乡贤的崇德教化功能,乡贤崇祀文化自然会围绕着乡贤事迹,向着乡贤书写扩展。关于乡贤事迹的书写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专门的传记著述,如清代的《掖邑乡贤考记》《潍县乡贤传》《安丘乡贤小传》等;另一类是地方志书,这是乡贤书写的主要载体。
乡贤见于山东地方志书最早始于明代,明万历《邹志》有贤迹志,但多数州县志尚未见乡贤专条记载。明代嘉靖《青州府志》不载乡贤,只是在人物志(传)中排列圣贤、封建、名臣、宦绩;在人物中列忠义、孝友、儒林、文学、武功、隐逸、侨寓、卓异。到清代,在志书中乡贤书写便较为普通,不少志书专列乡贤一目,或归类于人物志,内中收取本地乡贤人物。乡贤传记书写逐渐成为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志书关于乡贤的书写,没有统一的样式,且不同朝代、不同地方书写标准和范围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单独列专目,有的则将其他类目并入。如清康熙《邹县志》卷一有圣贤志,后贤志。菏泽“旧志分圣贤、乡贤、贤行诸目,张志合而一之,而别分儒林、文学、忠节、孝义四门”(14)光绪《菏泽县志》卷10,人物志。按:“旧志”系指康熙、乾隆《曹州府志》,“张志”系指张东所修乾隆《菏泽县志》(未刊)。。民国时期乡贤书写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化,如民国修纂的《清平县志》,乡贤范围包括耆旧、孝行、义门、方技、流寓、笃行、义烈、艺术等八类,几乎将所有本地人物都纳入了乡贤范畴。
晚清民国时期,在乡贤崇祀衰变更易的背景下,受时代思潮的激荡,各地所发掘与书写的乡贤在标准范围上进一步扩大,完全溢出了传统乡贤的范畴。人们选择的地方乡贤,不仅在时间上上溯至先秦先贤,下迄民国辛亥英烈,而且选取的范围扩大,超出旧有的高官显宦、儒学名士,人物选取的标准不再只是功名仕进、荫庇乡里、学术著述,而是扩及到政治、实业领域的进步人士,甚至还包括了反清革命、兴办新式教育(创办小学)的人物。如博山辛亥志士蒋衍升,曾领导成立同盟会山东支部,主编《晨钟》周刊,宣传革命,积极投身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和参加反袁斗争(15)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卷11,人物志,乡贤,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去世后作为乡贤写入地方志书中。
随着诸多不同于传统认知的“另类”乡贤载入史册,在基层社会树立起新的乡贤形象,进而改变着乡贤崇祀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使乡贤文化由祀典崇祀向着借助媒介宣扬转变。通过志书的形式,将新人物纳入乡贤专志,并得到政府认可,最终确立了“新乡贤”在本地文化中的地位。
二、乡贤选择的方式与标准
在明清传统社会,乡贤选取有着一定的程序和标准。明代乡贤的入祀通常要按照一定的规范与步骤,而“推贤”是首要环节。府州县学校是“推贤”的重要部门和“公论”所出之地,即由府县儒学教谕、生员、乡绅、里老共同推荐,呈请入祀,此为“公举”。“公举”既有共同推荐之意,也代表着地方公众的统一态度。“公论”最能体现所推举者生前死后的口碑,即乡贤所获得的德行、功业及学养的评价。故而,“公论”成为乡贤入祀的舆论依据,并成为审定乡贤的主要标准。
所祀乡贤、名宦经过本地士绅、儒学生员的推举后,还要经府县儒学的“勘结”,呈请上一级官府批准。如明代正德兖州知府童旭,政务之余,阅览府乘史志,和府县师生、当地故老集议,得名宦、乡贤若干人,继请示巡抚赵磺、巡按和布政、按察、提学诸上司,赵磺等咸以为宜。适值礼部奉诏命天下学校撤去文昌祠,童旭便以其地建乡贤祠,又辟乡贤祠西隙地建名宦祠,设主其堂,写明朝代、名氏、官爵,以春秋仲月祭祀(16)李东阳:《李东阳续集》文续稿卷2,《兖州府乡贤名宦祠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62页。。
清初延续明制,本地乡贤人物要获得入祀乡贤祠的资格,除了具有道德、事功、学问外,还要得到本地士绅的推举,经过官方的认可。雍正二年(1724)定例“嗣后名宦、乡贤,除故明以前不议外,所有本朝应入二祠人员,皆由提请,经部议覆,而后定”;同时还规定,乡贤入祀“皆由学臣督抚采访为政”,提督学政对入祀乡贤有鉴定批语(“看语”)(17)道光《观城县志》卷4,秩祀志,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从这一程序上看,乡贤选取过程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到清中叶后,乡贤入祀规制有所松弛,如清代菏泽乡贤是指那些“其德行、文学、功名、节义、信誉皆曹人后起之师”的人物(18)光绪《菏泽县志》卷10,人物,清光绪十一年刻本。。教育上的标准也有所放宽,乡间人物即使没有多大功名,只要德行足以垂范乡里,也可入祀乡贤祠。
乡贤入祀有着严格的资格和选取标准。一般而言,乡贤祠所祀人物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其一,乡贤是本地人士。明中叶之后,强调所祭祀乡贤必须是本地人,否则祭祀非其人,则无法体现尊贤追往的意义。清代祭祀乡贤更是将是否沾溉乡里作为入祀乡贤的重要标准,原因在于“一乡之贤,里闬相接,封畛相连,而其人之德行、风节、文学、事功、遗风余烈洽于所见所闻,所传闻者至亲且切,有不待旁求远访而后知也”(19)(明)徐一夔:《始丰稿》卷7,杂述,清武林往哲遗著本。。当地民众由于熟悉乡贤的生平事迹,有着地缘关系,更容易接受和学习,教化就更容易推行。其二,乡贤是本地德行、事业、功绩著闻之人。按照不同的标准,乡贤的事业功绩体现在宦绩(如为官清正等)、德行(如孝行、风节)、善举、学术文章建树等方面,并由此型塑出垂范乡里的不同乡贤类型,即所谓:“乡之先贤有以德行称者,有以风节闻者,有以文学著者,有以事功显者,然皆我之师也”(同上)。明万历时,曾在州县实行“举乡祠”,即推举乡贤人物入乡祠。推举标准为宦绩(多为县官一类的基层官员)、孝行、德行等,如明万历入祀乡贤的岳维乔,在乡时,“孝事继母,友爱诸弟,勤读书,尚德义”,出仕为官时,“以济国安民为事”。以教育、笃行入祀乡贤的人物,须“勤学砥行,设教不计脩脯,友爱多让”“造就人才日益众”(20)道光《观城县志》卷8,人物志,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德行是乡贤入祀的重要条件,它既表现为个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又构成了地方社会的价值共识。
明清山东传统社会乡贤的评判标准固然基于其个人活动事迹,并以此产生了乡贤的分类,但从当时社会阶层分层的角度看,乡贤崇祀人物的来源则可分成官僚、绅士、平民三类。再具体言之,官僚又可分为取得举人以上功名、官职在知县以上的中上层人物,教谕、训导等下层人物;绅士又可分为“已仕而致政归里者”,即退职家居的上层绅士;取得诸生(贡生、生监等)功名、拥有文化知识而没有入仕的下层绅士。平民则主要包括未取得功名的儒生、商人、技艺人及少数劳动者。
在山东各府州县,有功名在身、任过官职且有宦绩和德望者,往往构成先贤群体的主体。清代光绪朝,菏泽乡贤祠崇祀的乡贤共40人,这些人物大部分为曾供过职的大小官员,只有二人为本朝岁贡生,一人为孝隐(李允成)。德州从汉代到元代崇祀乡贤9人,明代27人,这当中只有一人没有功名,其余都有功名并任过官职;在清代12位乡贤中,只有一人是以孝子推为乡贤(21)民国《德县志》卷2,舆地志,祠庙,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有宦绩、职位高的官员多数可以入祠乡贤,但官职高低并非乡贤推选的标准,下层官员只要德行高尚、有声望,即使职位卑微,低如县教谕,也可入乡祠。如在德州,入祠乡贤人物上至历史名臣、大学士、尚书,如董仲舒、东方朔、刘怀珍、刘怀慰、高冯、田雯;下至知县、教谕。
实际上,官员入祀乡贤的首要条件在于宦绩。具体而言,乡贤的宦绩主要体现在:一是为官廉正,推行廉政。明代曹县乡贤李秉,有“铁面尚书”之称,“忠直刚毅,无私无畏,惩治豪强,为民申冤,弹劾贪官,严整吏治”。单县乡贤尚书秦紘,刚正不阿,廉洁绝俗,忠于职守,疾恶如仇,身居高位竟“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22)王志民总主编:《山东区域文化通览·菏泽区域文化通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255页。。二是推行善政。“劝善惩恶”“振纲肃纪,问民俗,祛吏弊奸豪,凛凛有神明之称”的廉正官吏,如明万历年间,观城人王维贞任新乡县知县时,“除强暴,革杂税,禁滥征,申条教,善政毕举,冰操自励,苞苴无敢行者”。当地人民对其甚为爱戴,民间亦有歌谣颂其德政:“邑县歌之曰,新乡公清且廉,只领新乡一杯水,不受新乡一文钱”(23)光绪《观城县乡土志》,清末抄本。。明代临沂人宋日就,在陕西富平为官时,“爱民如子,邑有疑狱,廉得其隐,立释之”,卒祀乡贤(24)民国《临沂县志》卷9,人物一,民国六年刊本。。三是抵御外族侵略,保卫疆土。如“区处刍饷调度,战守悉合机宜,疆域赖之”的守疆将领,死后祀乡贤(25)民国《朝城县乡土志》人物,李继宗,民国九年重刊本。。明代滨州乡贤中就不乏有抵御外侮的将领,如威震海疆的兵部左侍郎谷中虚、礼部尚书杨巍、抗倭名将董邦政等。
很多乡贤在为官期间“治民有政,化民有礼”,归里后还积极致力于家乡的发展,这也是被入选乡贤的条件之一。如东平戴祚升,“致仕归里,尤多善行,远近称长者,殁祀乡贤”。长山县袁承绂,官至户部郎中,为官时“剔弊恤民,居乡好施与,里人建专祠致祭,并请入乡贤祠”。同地的李化熙,官至刑部尚书,“多善政,好施予,代完周村市税。卒后赐祭葬,祀乡贤”。同县的赵之随,康熙进士,官至云南学政,“旋里后,多善事,卒后祀乡贤”(26)光绪《平度县乡土志》,清末抄本;光绪《长山县乡土志》,耆旧录,清末抄本。。由于他们本身地位高,只要稍稍顾及乡里之事,就有可能对地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他们被推举为乡贤的原因所在。
明清时期,尽管大小官员是乡贤群体的主体,但入祀乡贤的标准并不受是否做过官的限制,没有做官但为乡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也能被选为乡贤。尤其是清朝,在选拔乡贤时更注重是否沾溉乡里。在科举制度下,下层绅士主要由贡生、生员和监生组成,他们既拥有一定的特权又很少有机会出外任官,这无疑促使这一群体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较多地贡献于地方社会事务。他们以各种方式推动本乡社会的发展,具体包括下列几种:设义仓、建义田;设义学、课学子;建桥、修路等。如章丘乡贤郝其章,“凡族党子弟有贫不能读书者,俱延师成就之。济困扶危,终身不倦,里人奉为矜式”。历城乡贤金宝符,勤政爱民,为历任抚军所倚重,“尤拳拳桑梓寒畯,举廉俸所入二千金,捐入泺源书院,为士子膏火资。殁后,乡人呈请入祀乡贤祠”(27)道光《章丘县志》卷10,人物志,清道光十三年刻本;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卷40,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绅士在道德上能按照儒家规范自我约束,为人楷模,只要在乡里获得声望,就有可能被推举为乡贤。如明代菏泽诸生李允成,虽身为诸生,但道德品格上“性孝友端方,以古贤哲自期,躬耕乐道,不慕荣利”,死后得以祀乡贤。另一人物邢敦,“岁进士,品行端方,居家孝友,敦宗睦邻,为乡党所推重,殁后公举奉崇祀乡贤”(28)光绪《新修菏泽县志》卷5,学校;卷10,人物,清光绪十一年刻本。。明永乐年间,清平县叶天新,“性严厉,规尺自持,人不可干以私,好学攻书,然不屑为科举之学,故终其身诸生”,尽管没有官职,但却是“一身之仪型足式”的乡间楷模式的人物,因而得入祀乡贤(29)民国《续修清平县志》,人物志,乡贤上,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明永乐冠县人卢慎只当过河南扶沟县教谕,但“居乡端谨,为后学式”,照样可以成为后代奉祀的乡贤(30)民国《冠县志》卷8,人物志,民国二十三年刻本。。
有些乡贤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洁身自好,“虽一生无奇节异行,而庸行庸言亦足以风于乡矣”,也得以入祀乡贤。如新城(桓台)人张耀枢,在山西任中下层官吏,任上并无显著事迹,但是在“中年困厄时,一家糟糠不饱,而高堂甘旨……”,故死后列为乡贤。有的人虽无官职,但“处家喜怒爱憎不专主于己,惟亲意之从”,故也纳入乡贤之列(31)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卷11,人物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明永乐朝冠县人卢慎,只当过河南扶沟的教谕,但“居乡端谨为后学式”,这种按儒家修身处世之规范来律己者,也可进入乡贤之列(32)民国《冠县志》卷8,人物志,民国二十三年刻本。。传统的孝行是衡量一个乡贤人物的基本标准。在这一标准形范之下,有些人即使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但居乡在家有孝行,即有可能列为乡贤。
进入民国时期,乡贤举荐制度虽然废止,但乡贤书写和祭祀乡贤在山东各地仍具有一定的存在空间。乡贤概念的范畴更加扩大和延伸,乡贤人物的选取范围也在扩大,选取道德标准不再只是忠义、清廉等个人修养,而是将其与爱国、进步相联系,以与民族国家关系的远近,如政治、实业、教育、民生的兴衰为衡量选择标准。新的标准为各地方民众提供了可供寄托与效仿的新乡贤形象,显示出乡贤文化对时代进步和民族国家的认同。乡贤人物不仅包括反抗异族、爱国尚武的英雄,还有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英雄,如投身地方自治、经营实业、兴办教育、海外殖民、精通医术的的民间人物。例如清末清平县乡贤人物中,由化明“农耕外,肆力商务,不惮艰苦,与子景法远赴楚、豫,遂以锅厂起家”。金克俭“弃儒由农而商,因成素封”。金毓珍诸生出身,在清末热心公益,兴办教育,“又以为国家贫弱,由于实业不振,复创办肥田料厂,轧花公司,试种美棉,兴办帽辫等事,以期挽回利权”(33)民国《续修清平县志》,人物志,乡贤下,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三、山东乡贤崇祀文化的特点与意义
除一般功名仕进、荫庇乡里外,山东乡贤崇祀文化还具有若干自身的地域特点,这些特点表现为崇尚儒学及其道德追求、强调文功、家族化等。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儒家的政治观念、道德说教及人生理想,不仅是维系封建国家政教传统的核心准则,也是世家大族传承数百年而不衰竭的根本命脉。作为儒学发源之地,齐鲁之邦乡贤的功德亦表现在对儒家典籍的研习、传播上。山东儒学传统悠久深远,明清时期乡贤文化的兴盛正是在崇尚儒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乡贤的家教门风均源自儒家,乡贤的功德亦表现在对儒家典籍的研习、传播,他们是践行儒家思想的典范。入祀乡贤者即便不是高官显爵,也不一定有突出的事迹,或显赫的声望,但只要有深厚的儒学学养,就有资格入选乡贤。南朝梁时期成武县的崔灵恩因“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解经析礼甚精微,京师旧儒咸称重之”,而在明代被崇祀为乡贤。北魏的崔浩因“博通经史,留心制度科律,长于谋计”,并著有多种儒学著作,而入祀乡贤祠(34)光绪《成武县乡土志》,清末抄本。。宋朝东阿张万公,熟读儒家典籍,从儒家安民、恤民的思想出发履职从政,祀为乡贤。历城乡贤张养浩在为政中主张对民施行“仁政”,爱民、忧民、恤民,是儒家思想的忠实践行者,把儒家仁爱精神作为人生实践的基调和孜孜以求的目标,无论是为政实践还是言论著述,始终把“修己以安百姓”“达则兼济天下”放在首位,祀为乡贤。明代临沂人王之屏“乡举未仕,以理学德行著,卒祀乡贤”(35)民国《临沂县志》卷9,列传上,民国六年刊本。。
强调文功(文化贡献),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艺文创作、学术研究、文献收藏等方面。如德州明清两代入祀乡贤祠的著作家就有19人之多,超过了以政绩入祀的人数(36)光绪《德州乡土志》,清末抄本。。
在崇尚家学家风的氛围中,许多地方的乡贤崇祀呈现家族化现象。明清时期,山东仕宦家族和家族文化随着科举制度的盛行得到充分发展。累代参加科举,家风家学世代相传,形成了十分厚重的家族文化,并与乡贤崇祀相结合,成为乡贤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明清时期的新城王氏、新城耿氏、夏津崔氏、寿光刘氏、诸城刘氏、海丰吴氏等等,均是家族化乡贤的范例。如新城县王氏,“名贤代起,多出一门”,就是乡贤家族化的代表。明代王氏家族先贤辈出,自王重光始,先后有王之辅、王之垣、王之翰、王之城、王之都、王之猷、王象晋、王象乾、王象春、王象恒、王与胤等,祖孙四代共十数人入祀乡贤(37)康熙《新城县志》,先贤,清康熙三十三年刊本;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7,人物,先贤,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夏津崔光、崔鸿、崔劼等三代入祀乡贤。寿光刘氏、诸城刘氏家族都是著名的官僚世家和文化世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明清时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各地乡贤祠逐步普遍化和制度化,乡贤崇祀也随之成为一种地方文化。产生这一文化现象的原因,在于乡贤、名宦祠“可以显忠良,可以仰眷德,可以维风教”的社会教化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意义(38)嘉靖《夏邑县志》卷8,明嘉靖刻本。。
自明代嘉靖、万历开始,乡贤祠陆续迁入文庙(明清以前称孔庙),而州县学宫通常都设在文庙内或文庙旁,从而凸显了乡贤祠在教化中的作用。先贤乡贤崇祀的教化功能,明代方志中说得很清楚:“先圣先贤之有祀,以崇德报功焉”,而乡贤名宦之有祀“以景贤敦化焉”。又说“祀以立报,报以立劝,祭岂无义也哉”(39)《淄川县志》卷3,建设志,祠祀,明嘉靖刻本。。由此看来,乡贤崇祀意义在于教化乡村民众,垂范吏治。明清时期山东乡贤祭祀所寄托的教化寓意可归结为三点:一是报功崇德,即通过木主、祠宇等固化物和一定的仪式,营造肃穆氛围,强化忠孝精神,崇德尚贤,彰显后人对先贤功德的报答;二是教化垂范后世后人,敦往劝来,乡人受乡贤德行的感召,而体认儒家之道,而乡贤亦以其行履,移风易俗;三是祈福,即把先贤的功德神化,视作连接超自然力量的桥梁,对人间具有超凡的影响力,敬重先贤可获默佑。
正是由于乡贤崇祀的政治与社会教化功能,乡贤崇祀在明清时期具有了特殊的社会意义,有着其他社会治理、社会文化所不具有的功能。其一,乡贤文化是官府与民众间的精神桥梁。官府与民众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二者经常对立,而乡贤既是统治阶层的成员,又是能够影响民间社会的有威望的人,因此乡贤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他既传达出统治集团的意志,又在很多情景中代表着地方民意,反映了民众的诉求,是地方公益事业的维护者;其二,乡贤是地方教化的承担者。任职此地的官僚(名宦)与土著贤哲(乡贤),其劝勉的对象有所不同。任职此地而被尊为先贤,多是此人任职之时,政绩斐然,造福一方。地方士民祭祀其人,实则含有对继任官员的期待,期待后来者能以此人为榜样,同样惠及百姓,它是指向主持祭祀的地方官员。而祭祀土著先贤,或以其行履道德,或以功名宦业,能激励后人,弘扬礼教,为一方风化的代表,对地方社会而言,更为重要;其三,乡贤文化是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承的主要力量,也是对民众实施教化的主体。乡贤由于亲近民众,又熟悉教化内容,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乡风,所以在宣示、维护教化方面有着官府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传播文化、培育后人方面,丰富了地方文化的内容,推动了地域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