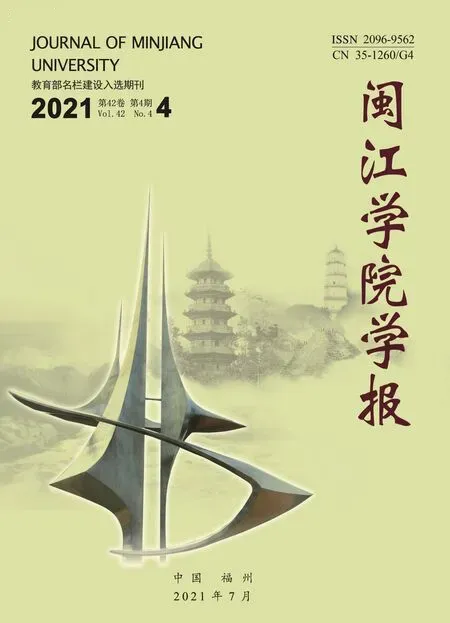倚与不倚:何振岱心灵诗学探析
北 塔
(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 100029)
何振岱诗词的词汇量极大,关键词也不少,但有几个字是非常特殊的,比如他好用“倚”“依”及其近义字“傍” “凭”“借”“靠”“托”“待”等。这些字隐藏着大量信息:抒情主人公的世界观、人生观、诗歌观、审美心态以及修辞策略等。
一、何振岱诗歌中多用“倚”及其近义字的原因探析
(一)对宇宙和人生关系的注意及思考
“倚”揭示的是宇宙存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多用“倚”及其近义字来表现这些关系,表明何振岱平时对宇宙和人生中这些关系的注意和思考。首先,物和物之间存在着“倚”与被“倚”的关系。何振岱诗《舟至马江亲朋来迎》云:“方舟拍手齐巾髻,一塔昂头倚翠微。”(1)文中所引何振岱诗词,皆出自《何振岱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后文不一一注出。塔很高,还昂着头,但它被修筑在山上,所以看上去像是倚靠着“山”。
其次,人和人之间更是存在着“倚”与被“倚”的关系。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父母”这是对年轻人而言的。到了中年,父母老了,甚至没了,而自己还在外面行走,就更要倚重朋友。而且,中年人已经成家立业,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根基,所倚靠的朋友,可能不是物质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这便是《纪别》诗所云:“情感倚亲朋。”
再次,人与物之间存在着“倚”与被“倚”的关系。何诗《洪山桥酒楼小集(四首选一)》云:“枫叶芦花都未有,只凭寒日看秋江。” “看”的主语是人,因此,是人凭依寒日看着秋江,秋江本来就给人以萧瑟的凉意,连江上的太阳都冷了,人何以堪?再如《孤山独坐,雪意甚足》:“钟定声依无际水。”钟声是人工产物,“无际水”是自然之物,而钟声会倚着无边的流水传向远方。
(二)道家和佛家的思考向度
事物关系中的相互依赖性一直是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和佛家所重视的思考向度。道家和佛家这两家哲学体系追求的是主体个我的纯粹性、独立性和超越性,思考更多的是“倚”给主体所带来的压力、伤害和削弱。
庄子《逍遥游》曰:“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30“御”者“驭”也,列子的坐骑是风,他能乘风而腾云驾雾,已经是非常厉害了。但在庄子看来,这不是最高的境界,因为他还是要倚靠风的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风跟马甚至跟驴子没有多大区别。最高的境界是“无待”,不需要倚靠任何外物。你一旦倚靠外物,就有被外物所累的危险,从而无法达到“无己”的“至人”境界。若到了那样的境界,还需要倚靠什么呢?“御六气之辩(通‘变’)”的意思是:无论阴、阳、风、雨、晦、明这些天气如何变化,“我”自岿然不动。此处,“御”的意思相当于“以静制动”的“制”,显现的是主体的高度主动性。庄子说“至人”能“忘物”,其前提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庄子·齐物论》)。因为无论是身还是心,如果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那么也都是物,既是“待”的主体,也是“待”的对象;在忘了别的物之前,先得忘掉此二者,然后才能“无待”。正如何诗《香山寄宜园雨花阁》云:“槁灰已到能忘物,深密悬知善解经。”
佛家强调“无执”,如“明空无执”和“无执禅定”等。表面上看,“无执”与“无待”似乎是一样的,但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追求的“无待”境界是“自我的完成”,通过否定自我——“无我”来肯定自我。而佛家的终极目标是彻底的自我否定——“灭我”,甚至“无无”(不仅无我,而且无无我)、“空空”(空诸所有,包括“空”本身),这就是所谓“绝对无待”的涅槃境界。
何振岱是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孔子的拥趸者,但他并不排斥道家和佛家。相反,他一生以道家心态研究并传承儒家。到了晚年,他基本上成了一个佛教徒。因此,多用“倚”等字,显现了何振岱熟悉并较多思考道家所说的“待”与“无待”、佛家所说的“执”与“无执”等关键性的概念和观念,并且予以灵活应用。
何振岱的底色毕竟是儒家,所以,他虽然强调自我的完整性和自足性,但并不怎么说“忘我”或“无我”,更不曾说“无无我”。这表现了他跟纯然道家和佛家哲学的区别。
二、由孤而倚、由倚返孤的孤独辩证法
(一)叩寂寞以求外
也许是因为孤标傲世的性格使然,或者是因为何振岱学问太渊博,才华太高卓,所以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他喜欢深交,不喜欢泛泛之交;他喜欢深谈,不喜欢泛泛而谈。在社交上,他秉持的原则是宁缺毋滥,甚至宁少勿多、宁静勿动。能与他深入地论学谈诗的当世诗人学者,尤其是侪辈,太少。因此,他一般喜欢安静、独处,享受孤独。
但是,正如叔本华所概括的,人如刺猬,相互挨着的时候,会因嫌恶或伤害而隔离,隔离久了,又觉得凄凉,又要相互靠近。[2]孤傲的何振岱也有孤苦的时候,尤其到了晚年。他何曾不渴望知音、交流乃至陪伴?他在晚年一再感慨乃至感叹的就是这种孤寡的人生况味。《赠吴家琼序》曰:“予里居寡侣。”[3]90《与邵生季慈、田生古序书》曰:“吾老年无深友,欲与深言者已少其人。”[3]85“深友”乃深交之友,仅次于挚友。这样的朋友何其少也。《与耐轩、坚庐书》曰:“足与深言者偏远暌遐隔,而不足与言者所在皆是。人生安得不孤?孤固今日之分,不可怨尤,而不能使此心之不悲也。”[3]69虽然他明知能与他同起同坐的同道中人不可多得,但他还是为此而感到悲凉孤凄。
“深友”者“神交”也,何振岱交友论文的最高标准是两个:一是合于古,二是通于天。《再赋晚菊》云:“解趣故应天上月,可言惟有晋时人。”是天上的月亮跟诗人趣味相投,而不是地上的人。只有晋朝的人(指陶渊明)才能跟诗人深言畅谈,而不是现在的人。正是因为他喜欢尚友千古,喜欢恣游九霄,所以时时有知音难觅之感。
儒家哲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探讨的中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应该具备的关系。二是视角和目标都非常世俗化,但又排斥庸俗。《竹韵轩记》云:“盖古之君子,不能绝人而居,而又不能苟谐于俗。每托物之类己者,流连玩赏,以见其意。”[3]105社会和家庭都是人和人在一起组成的,每个个体周围都是各种各样的人;但在何振岱看来,芸芸众生中的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庸庸碌碌的俗辈,他不愿意委屈自己去跟他们周旋,浪费时间,影响心情。所以,他宁愿寄情于类己之物,托物以表意。他认为,屈原所依靠的是兰,陶潜所倚靠的是菊,他自己所依托的则是梅。因此,他写了大量的“梅”诗,晚年甚至还自号“梅叟”。可以说,“梅”是何振岱用以塑造自己形象、表达自己心志的“所托之物”。
诗人在两个向度上缓解或者解决孤苦无依的状态,一是向外的,二是向内的。
何振岱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有时也不得不理性地看待人生,向现实妥协。人首先要生存,即要吃饭,所以文人也需要为稻粱谋。如果在本地没有这样的机会,则还得“宦游”他乡。何振岱被江西布政使沈瑜庆(沈葆桢之子)聘为藩署文案,不得不向家人,尤其是母亲告别。在《纪别》一诗中,他感叹道:“人生倚稻粱,去为就食凫。”人就像野鸭一样,为了活着,不得不在人生的苦海里,不停地觅食。“凫”不是某一个人的“所托之物”,而是亿万人的“所托之物”。
向外的努力就是寻找“所托之物”。此处,“物”是泛称,“所托之物”可理解为“所依靠的对象”。这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鹧鸪天·鹤氅云边倚晓寒》云:“鹤氅云边倚晓寒。”再如《忆梦》:“忆梦曲栏碧,倚风双袖凉。”“寒”与“风”都是无形的,但能诉诸我们的感觉,所以也有“物感”,能让我们倚靠。
由于种种羁绊,我们往往会长时间羁旅异乡。当思念浓烈时,你就会感到孤寂。《晚江》云:“无梦到家山,何人慰岑寂?”本来以为,在现实中无法做到的,倚靠梦可以做到,但有时候,并不一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要么梦到的不是你所思念的,要么干脆就无梦。这时候,你的孤寂简直到了无处排遣的地步。“合为一片愁,迷茫傍芦荻。”当我们的“愁”浓得化不开时,当我们在茫茫宇宙中感到迷惑失落时,当身边没有朋友慰问我们时,一根芦苇就可能是我们情感的救命稻草。
写诗填词可能是消愁驱闷的良方,也是寂寞时人们经常用来倚靠的“所托之物”。《鹧鸪天·鹤氅云边倚晓寒》云:“毫浣露,纸薰兰,新词一卷托心肝。”笔蘸的是露水,纸染的是兰香,用这样的笔和纸写就的诗词,可以用来寄托我们的肺腑;或者说,这样的笔和纸扮演着我们倾诉的对象。
在宇宙所有的存在中,最终能让我们倚靠的,应该是“天”。前面说“天上月”应该可以帮诗人“解趣”,从而“解闷”。“天”本身更是诗人寄予厚望的最高救主。《祭陈渔隐文》云:“参呗语于邻刹,依精魂于上方。”[3]128“呗语”(佛教歌词)可以到附近的寺庙里去聆听、参悟,而那超越词与物的精魂当然是在天上,靠着天人才有存在之居所与可能。
何振岱所体验的孤独并不是凡俗意义上的那种仅仅因为没有人陪伴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事实上,他身边一直有家人、弟子和朋友。尤其是在晚年,他作为福建文坛一代宗师,想要去拜谒、求教的各色人等络绎不绝。也许正是因为找他的人太多,而他素喜清静,讨厌热闹,所以才选择拒绝。有众总有俗。与众保持距离就是远离俗气。因此,他的孤独是超越世俗的,是带有终极性价值、形而上意义的大寂寞。
他曾力图通过借助天地万物,包括艺术、诗歌以及“天”本身,来驱逐这大寂寞。但他发现,这种求助于外的努力,是徒劳的。于是,他转向内,转而追求自我心理的调解与外界力量和解,通过丰富内心达到对万物的包容,不是心托于物,而是物倚于心,且心这个内宇宙不仅有着外宇宙一样的富藏,同时主体自我觉得更容易挖掘。
(二)自求于心之孤与足
在多年向外寻求依靠的努力终告失败之后,何振岱转而求助于内。《赠邵生季慈序》曰:“遂出游大江南北数年,无心得而归。乃杜门寂处,闇然自求。”[3]89《暗修篇寄赠林敦民》曰:“晦迹自求,孤心内映。”[3]93把门关起来,如同进入了闭关静修的状态;这样的寂处不是被动安置的境地,而是主动追求的境界。他依然感到孤独,但这种孤独不再是消极情绪,而是自我内省、自我观照、自我反思的一面镜子、一个契机,所以具有正面价值。
最终让他相信的不是那个貌似坚实的外在世界的任何事物,而是自己的内心。《答刘生蕙愔》曰:“所靠得住而不转变者,惟自己寸心。”[3]60这时候,他大概开始信服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二十二《杂说》)的豪言,并且尊崇王阳明的心学,开始了心灵诗学的探索,即他的诗歌创作不再以任何外人、外在的目的为旨归,而是完全遵循内心的感受。他牢记孔子 “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的教导,倡导诗文为己。《与林生秋旸书》曰:“最忌为人,一涉为人,则反害矣。果能为己,即浅些都不妨,浅可深也。”[3]53因为强调 “为己”,他不惜把孔子的语录断章取义,让“为人”和“为己”对立起来。他在日记中也曾写道:“书画自为之,则可以娱心;若为人为之,所损实多。”[4]7如果是为了别人而进行创作,则不仅无益,反而有损。其实,两者是可以兼容的,所谓“内圣外王”,所谓“达己又达人”,而且“达己”的目的是为了“达人”,修身养性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当然,何振岱晚年清醒地认识到,他已经没有机会和平台在“外王”方面建功立业,只能退而求其次,或者说反躬自求“内圣”,或在立言上追求“文圣”。
那么,他何以走上心灵诗学的道路?换言之,他的心灵信仰的理由和力量来自何处?
首先,他认为,心灵信仰可以让我们树立真我的根基,捍卫本我的立场,产生“撼山易撼自我难”的气魄。《答所知书》曰:“自树根基,孰能浮沉我者?盖因人者,我也;不因人,亦我。我失其为我矣,安往不随人?我还为我矣,彼何力能夺我?”[3]75如果自我的根基稳定了,那么,外在势力无论如何强大乃至猖狂,都不能左右我、主宰我;载浮载沉,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与别人无关。哪怕跟别人有关,哪怕因为别人而去说什么、做什么,其前提也是自己预设的,其后果也是自己愿意承担的。自始至终,“我”还是“我”!心灵信仰是儒家讲的“君子自强不息”的刚毅性格的保障。
其次,心灵信仰是自由主义意志的体现。《与张生浣桐》曰:“风蝉笛韵,独有遐情……因思冷性如余,野意自遂。”[3]85人的自由的最大内涵是心灵的自由,庄子说他梦中的蝴蝶是“自喻适志与”[1]35。风中的蝉何尝不是如此?它的鸣叫也许在有些人听来是聒噪,是歇斯底里,是不合时宜,但在诗人听来却“野意自遂”,就要保持自己这份与文明之耳不和谐的野性,让自己遂愿。
再次,心灵可以是自为的。如果我们具备了刚毅的性格、自由的意志,那么,我们的心灵不仅不会取决于外力,不再依傍于外物,相反,还能把外物内化、幻化,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审美的客体,这样的心灵是创造的场域和活力的源泉,能够千变万化,能够补偿现实的缺憾、美化物性的粗粝。如《南行别庭中海棠》云:“半年仰树待花发,却到花时赋远游。去去渐生江上月,将心化月满枝头。”抒情主人公翘首以盼,等待开花,达半年之久;但真到花开时,自己却不得不前往远方,无法欣赏花朵的美丽。不过呢,心灵可以帮他把物质现实中的失落找补回来,因为他的心中有月有花,那棵现实生活的树也就不会有任何匮乏。心不仅能化成月亮,而且能化育月亮,即自己发光。《金居士谈湛愚老人心灯》云:“宝光欲烛天,是名曰心灯。导尔出阴谷,扶之登大陵。”[3]269这心灵的灯甚至可以在黑夜里引导我们走出阴暗的山谷,登上高峰。不是去反映他物,而是自生其象。如《广意》云:“力微不足摄群动,乃令方寸生荆榛。”又如《东坡生日小集分赋》云:“何由内溉俾自滋?善养心苗长灵穗。”这荆榛和苗穗都不是来自泥田,而是来自心田。心灵不是认万象为宾客,而是本身在滋生万物,仿佛成了另一个造物主。《红叶与郁离》云:“与君老去秾华在,一寸诗心万象收。”这样的心如同一面镜子,可以摄万物。他的这一思想渊源自释家,如慧能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坛经》)更来源于中国本土的儒家,如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王守仁说的“心外无物”(《传习录》)。
最后,心灵可以是自足的,之所以要空,是为了要满,要足。心灵可以是自满、自信的,无所依傍不是求之不得,而是没有必要。《张园荷花池上晓坐》云:“更无人与分荷气,只觉风来是露香。一水自含无限碧,片时足占十分凉。”整个庭院里、池塘里的荷花香气只属于这个庭院和池塘及其主人本身,在这样芳香四溢的环境里,连风和露都是香的。这是一首七绝,后两行中的“无限”“足”“十分”点明此境此人是完全自足、别无他求的,这样的空间看似局限,实则无限;表面是孤独的,内里是满足的。因为它被心灵化了,或者说本身就是心灵的外化和寄寓。
人的心灵的理想状态是足,同时又是孤,因而何振岱整个的心态是“孤足”,因孤而足,或因足而孤。前引“惟自己寸心”之“惟”,“独有遐情”之“独”,都是“孤”的近义字。又《孤山独坐,雪意甚足》云:“山孤有客与徘徊,悄向幽亭藉绿苔。”亭与苔共绿,山与人同孤。此处,“甚足”的不仅是雪意,还有山意,更有人意;无论是哪个主体的满足状态,都以孤独作为前提。何的恩师谢章铤评价他的诗时说:“独有寸心贯金石,不妨只手障烟尘。”
当一个人的心是自满(自我满足)的时候,孤独就不再是一种负面情绪或不堪状态,而是象征着某种遗世独立的品质和高尚不俗的气度,具有十足的正面价值。
由此,诗人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趋向重新由倚返回到了孤。通过把“倚”的状态扭转为 “不倚”,“孤”的价值内涵也由负面转为正面。也因此,他的思和诗总体上包含着这种孤独辩证法。
何振岱对“孤”作为一种正面状态的体验比“孤”作为一种负面状态的体验要深得多、强得多。《江城子·孤山梅花》云:“修到梅花愁独自。”他一生,尤其是晚年爱梅如痴。这“愁”和“独自”因为属于梅花,所以也就不再是负面的,而是他所欣赏甚至是自恋的。《今亦》云:“春浅花新茁,风来絮自飞。”“絮”自由自在地飞,哪管风从哪个方向吹来,哪管有没有风;也许风是絮的敌人,风想押解絮,想要管控絮;但絮我行我素,视风如无物。《再赋晚菊》云:“何因未入匡庐社?独自悠然是性真。”诗人认为,自我或本我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独自的,而不是群体的,因为在群体里没有“悠然”可言。
何振岱还把他所解悟的“独”的价值应用于诗学研究和阐发。《答人论诗题书》曰:“考《诗》大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知志是未发之诗,诗为已发之志。未发之诗,独知、独觉;已发之诗,有声有韵。”他的诗学的最大优势,当然也是同光体诗学的最大优点,就是综合唐宋。一方面强调诗歌艺术的共性和传承,另一方面又重视每个诗人、每首诗的个性和创发,发前人所未发。这不仅指修辞上的戛戛独造,更指思维上的与众不同,即独特的认知和感觉。
三、何振岱诗歌美学范畴中的倚与不倚
在哲学上或者说养性上,心灵的孤独状态已经自足、自为,毫无倚靠任何事物的必要。但在艺术上,似乎情况有所不同、有点复杂。
首先,知音难觅的感慨源于对知音的寻找的冲动,也就是说,再难找也还是要找,乐人弹奏时都有潜在的听者对象(古代语境中所谓的“解人”),有时候我们的措辞、调子和语言姿态都会或多或少倚赖他们的喜好、习惯和趣味。《鹧鸪天·鹤氅云边倚晓寒》云:“鹤氅云边倚晓寒,琴丝碧海为谁弹?何曾仙佛无凭准,但惜人间解意难。”“凭准”关乎艺术演奏的标准意识。这一标准意识不是作者自己单独所能决定的,而是要虚拟性地与读者一起往还商略,要符合读者的接受期待。“为谁”云云则分明点出了潜在听客的存在。
其次,心灵的状态,包括情感、情绪等等,都是抽象的、无形的,诗人在表达心态时,都要采用形象化的策略,从而倚赖形象。比如《浣溪沙·不悔当年作计差》云:“少小心情同苦檗,中年身世似杨花。”“心情”和“身世”都不是具体可感的某物,所以要分别用“苦檗”和“杨花”作比喻,才能让人感觉到那是什么样的心情和身世——心情像苦檗一样苦楚,身世像杨花一样飘零。再如《江城子·孤山梅花》云:“夜阑峰影写迷茫。”“迷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夜阑”和“峰影”则诉诸视觉,其妙处在于:此二物似乎看得见摸得着,但还不是那么容易一看就看清,一摸就能摸着,而是隐隐约约,模模糊糊,所以还是酷似迷茫的状态。
再次,何振岱是诗艺精湛的大诗人,他善于用象征手法,象征手法的核心组件是意象和寓意,把寓意藏起来,只让意象呈现在读者面前,也就是说“意”对“象”有相当程度的倚赖。如《题明人画李香君小像》中“吁嗟培塿无乔松,却见青泥生芙蓉”,寓意类似于“著意栽花花不发,等闲插柳柳成荫”(典出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第二折)。你日夜栽培,那树木却还是没有长成参天大树,所谓事倍功半也;芙蓉花极为美丽,但不是有人故意去种养的,而是自长自发的,所谓自我成才也。
还有,不同艺术种类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倚赖的关系?多数人都习惯说各门艺术形式之间相辅相成、相通相助,所以古代文人往往琴棋书画样样擅长,而且融会贯通。何振岱琴棋书画皆精,但他更关注的是各门艺术之间的分,而不是合。每个人都有其长项和短处,每一门艺术都有其独特性和适应性。比如,他曾为大学者、大诗人的字写不好辩护,说他们太忙或专注于阅读和思考,不太在乎书法。旧体诗词往往依赖于音乐,所谓“合乐”或“入乐”,但他说“吟成不倚筝琶和,声出烟霄缥缈间”,诗歌本身的成功与是否合乐没有多大关系,其价值并不取决于音乐,而是有着更加高远的境界和韵味。因此,《竹韵轩记》曰:“韵将在君,不仅在所托之物矣。”[3]106不同的艺术在“器”的层面是不同的,即各自用其材料、器具,但在“道”的层面上是相通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就是要用“道”去克服乃至超越“器”,其审美效果就体现于“韵味”,它是及物的,但又不依赖于物。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何振岱诗学的最基本观念是:诗是介于心和物之间的艺术,以心为主,以物为辅;物是用来衬托心的,心是用来统驭物的。心与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某一种心态可以用不同的物来象征,物对心的来往、附着,具有偶然性。也因此,物的存在和呈现,不影响心灵的孤独与自足,有了物,心灵可能依然是孤独的,没有物,心灵可能依旧是自足的。且看他的夫子自道:“书画皆有困境,打过困境,则到自在之境。”[4]7“困境”者,心为物所役也,心倚于物也;“自在之境”者,心游于物外也,无所依傍而自为自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