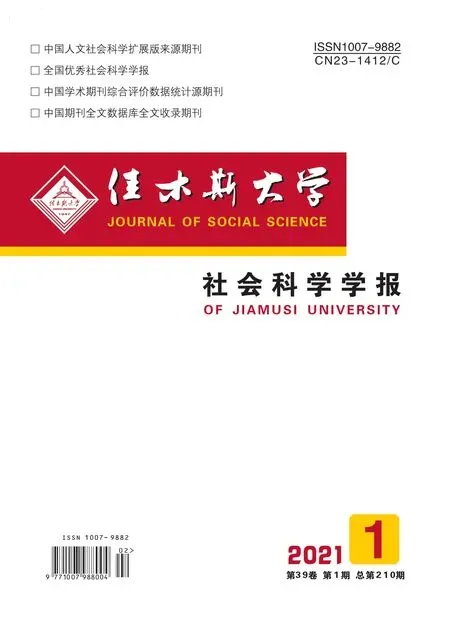民法典视域下失信被执行人的被遗忘权研究*
邓皓迪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一直以来,“执行难”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充斥着许多有能力履行判决书而拒不履行、逃避执行、规避执行的执行案件,使法院生效判决成为“盖了官印的白条”,让债权人的权益无法实现,司法权威受到威胁。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若干规定》),从此正式确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该制度为形成“一处违法、一处失信、处处受阻”的社会信用体系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助力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各级人民法院可以向社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督促失信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截至2020年9月,全国法院正在公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达603万人①,有效助力解决“执行难”问题。
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存在“过度记忆”现象
在促进我国解决“执行难”问题同时,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也是一把“双刃剑”,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布内容、公布平台、退出机制和权利救济等方面的问题在推行中逐渐浮现出来,导致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出现“过度记忆”的现象,使被执行人合法权益遭到侵犯,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信息公布内容不规范
《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了应当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内容,除了被执行人姓名、失信行为等,还规定法院可以记载和公布“其他事项”,法院在具体操作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各地法院在实践中公布内容各异,除了公布执行案号和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外,有一些法院将《若干规定》中没有规定应当公布的信息公开。
(二)信息公布平台具有随意性
由于《若干规定》中未明确限制信息公布平台,法院在信息公布的平台选择上具有随意性。有些法院为了给被执行人带来舆论压力从而提高执结率,于是利用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微博、手机APP、微信公众号推送等互联网新媒体来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或通过与搜索引擎公司合作,将失信人信息在搜索引擎置顶显示,甚至公布相关当事人定位②;部分法院还利用商业繁华地段的商场、广场LED显示屏滚动播放失信被执行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欠款额、失信情形等。这些措施对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生效判决义务确实有较强的震慑力,但对其亲属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可能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同时,《若干规定》未能限制其它媒体平台转载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若信息被大量无关媒体广泛转载,可能出现传播失控现象。
(三)退出机制亟待完善
失信被执行人已经履行完毕确定义务后,人民法院会将其有关信息从名单库中删除。然而法院只是失信惩戒措施的信息源头,不是惩戒实施的实际控制人,仅通过法院的信息更正不足以改变已实施的惩戒现状。例如,经过二次甚至多次传播的其它平台上的失信内容无法因法院信息的更正而改变。在法院已将失信被执行人从名单中删除后,个人信息仍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事实上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并未完全退出。
(四)失信被执行人的救济权利有限
《若干规定》第11—13条规定了失信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纠正、删除信息的程序及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责任,但未规定转载、利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媒体和数据控制者的责任。失信被执行人因信息“过度记忆”造成的侵害,应当如何行使救济权利,救济程序应当如何启动,造成的损失是否可以请求国家或信息处理者赔偿等均未予以明确。除此之外,是否可以采取诉讼方式要求及时删除信息,以控制名单公布造成的影响,也未作出规定。
在这样的立法现状下,我们在网络上搜索“失信被执行人身份证号”即可完整地浏览几年前失信被执行人的详细身份信息;即便其信息从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删除,在失信信息公开期间被其他网站转载、利用以及保留在纸媒上的信息却依然留存,通过“弹窗”等方式通知到他人的失信被执行人相关信息,也永远印刻在了他人的记忆里,在失信被执行人已履行义务后的数年,依然能对其造成生活、工作上的影响。
失信被执行人因违背诚实信用,应当受到一定的惩戒,而其正当的权益也依然应当受到保护。在已经履行义务后,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不应当被“过度记忆”,而应当一定程度地“被遗忘”。
二、失信被执行人的“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主要指信息主体对其被发布在网络上的过时的、不恰当的、可能会影响其社会评价的信息,可以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的权利。[1]近年来,欧盟、美国兴起的被遗忘权相关理论在个人信息保护上起到一定作用,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保护具有重大启示。
(一)“被遗忘权”相关立法与实践
2014年的“冈萨雷斯诉谷歌案”是“被遗忘权”通过司法判例确认的第一案。[2]1998年,冈萨雷斯因保险费用纠纷而不得不拍卖房产,西班牙报纸《先锋报》刊登了其保险费追偿公示及房产拍卖公告,这一信息后来被谷歌搜索引擎收录,多年后冈萨雷斯仍可在谷歌搜索引擎中找到该信息,对其生活造成影响,故要求谷歌公司删除这一网络链接。最终欧盟法院支持了冈萨雷斯对谷歌公司的控诉。基于该判例,公民可要求搜索引擎删除其不恰当或已过期的信息内容。2018年5月25日正式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规定了符合当前大数据时代的“被遗忘权”范围和例外情况,也规定了数据控制者拥有使数据“被遗忘”的义务。
美国虽未明确规定“被遗忘权”相关概念,但加州“橡皮擦法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被遗忘权”的法律精神,该法案规定未成年人可以请求删除过去发布在社交网站上的有关文字和图片信息的一切记录。我国《若干规定》第4条虽规定人民法院不得将未成年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与“橡皮擦法案”未成年人的保护方式并不相同,美国“橡皮擦法案”的侧重点在于保护未成年人对其曾发表的网络信息记录的处分权。
任甲玉诉百度公司案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被遗忘权”的第一案。[3]2015年,当事人任甲玉发现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自己的姓名,会与自己曾就职过的某教育公司相关词条一同出现,而该教育公司商誉不佳。任甲玉要求百度公司删除自己与某教育公司相关词条未果,故以姓名权和被遗忘权被侵犯为由向法院对百度公司提起诉讼。尽管最终本案判决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原因是原告主张应当“被遗忘”的信息理由不充分,不具有受法律保护的必要性,而并未全盘否决“被遗忘权”本身,说明我国通过司法途径请求“遗忘”不恰当的个人信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二)失信被执行人“被遗忘权”内涵
欧美“被遗忘权”所保护的内容和义务主体虽有区别,但从本质上来说,“被遗忘权”的权利核心是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处分权,有权控制信息本身,保护自身名誉和隐私。“被遗忘权”的相对义务主体是能够收集、处理或利用个人信息数据的信息处理者,其负有不过度处理以及删除信息主体不恰当的个人信息的义务,所谓不恰当的信息不仅包括虚假、伪造或错误的信息,也包括已过期的真实信息。
所有信息主体都应当拥有这种“被遗忘权”,也包括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被遗忘权”的相对义务主体主要是有关信息处理主体和人民法院。信息处理主体负有删除不当信息的义务,法院有义务以恰当的方式和平台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及时修改或删除失信被执行人已过期或错误的个人信息,并限制无关媒体转载,同时还要保证失信被执行人拥有充分的救济渠道,达到惩戒失信行为和保护合法权益的平衡。
三、民法典视域下的“被遗忘权”保护
新出台的《民法典》在人格权编中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信息保护,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和责任等。尽管《民法典》未直接规定“被遗忘权”,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精神,站在民事基本法的高度为“被遗忘权”保护提供根本保障。
(一)明确个人信息的界定
《民法典》第1034条就个人信息的定义重申了“识别”标准,类似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国外个人信息立法的认定基准。《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范围采用列举方式进行明确。除自然人基本身份信息、生物识别信息等《网络安全法》中已列举的信息种类外,还加入了电子联系方式、行程信息甚至健康信息等,在实践中更为精准且具有可操作性。再次强调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明确“被遗忘权”所保护的个人信息范围,进一步为“被遗忘权”保护奠定基础。
(二)明确处理个人信息要遵循“必要原则”
由于当前电商平台及手机APP等收集个人信息的方式越来越隐蔽,存在着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滥用和违法使用的安全隐患。《民法典》第1035条在遵循《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既有规定的基础上,不仅首次提出了“个人信息的处理”的概念,并且再次重申了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强制要求“不得过度处理”个人信息,这也是对“必要原则”的深化,呼应了“被遗忘权”要求“遗忘”不必要、不恰当的个人信息的观点。
(三)明确个人信息主体的删除权
《民法典》第1037条规定了公民对个人信息具有查阅、复制、请求更正和删除的权利,由此公民对个人信息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决定性。尤其是关于请求删除权,《民法典》在参考《网络安全法》第43条的基础上,将行使条件规定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这使得现实生活中自然人可以及时通过行使自力救济,从而减少个人信息被侵害的风险。而个人信息主体对不恰当信息的“删除权”,即为“被遗忘权”最核心的内容。
由此可见“被遗忘权”可以体现在受法律保护的其他民事权利中,如今《民法典》进一步强调了对个人信息及隐私权的保护,为公民行使“被遗忘权”保驾护航。
四、民法典视域下失信被执行人“被遗忘权”保护路径
(一)公布方式中的“被遗忘权”——遵循“必要原则”
现有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中规定的某些应当公开的信息会导致失信被执行人的隐私权、财产权、名誉权等正当权益受损,根据“必要原则”的要求,应当慎重考虑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布的内容。
首先,对于应当公开的信息内容与方式可以通过正面列举的手段加以明确规定,让各地法院及信息处理主体在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时有明确参照依据。其次,可以用排除法规定不能公开的信息以及不能用于信息公开的手段,例如应当排除用带侮辱性质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形象照片等内容,因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作为一种执行手段,对被执行人实行的应当是信用惩戒,让被执行人在信用上受损,削弱其开展经济生活的能力,而不是在名誉上对其进行贬损,降低其整体社会评价。[4]再次,要明确禁止公开与身份信息无关的信息,如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所在地等,进一步规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开内容。最后,可进一步规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布范围,公民可依申请查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信息的资格应当被审核。可参考德国“债务人名簿制度”,1995年德国《关于债务人名簿规定的修订法》规定,仅“与登记目的符合、无法拒绝的”第三人有资格查询相关债务人信息。我国的国情和法治发展情况与西方国家有差异,因此对于其他国家的做法不能直接舶来。但我们可以以此为借鉴,进一步规范现有制度。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目的是督促其更快地履行法律义务,其权利让渡的程度应当以足够促使其履行法律义务为限。
(二)公布平台中的“被遗忘权”——防止“过度记忆”
根据《民法典》第1135条,应当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不得过度处理。在设置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布平台时应当更为审慎,平台范围应当规定明确,防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在公布平台上被“锁定”,以致于“过度记忆”。
第一,应当明确《若干规定》第7条中公布平台的“其他方式”具体所指,若列举过于繁琐,则可用排除法规定不可作为公开平台的种类,例如,尽量避免使用纸质媒体刊登失信信息,慎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互联网传播方式向社会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可以在辖区内公开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总体情况,但尽量减少通过无差别、广范围的手段直接散布失信被执行人的具体身份信息。一方面要保持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司法和舆论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要从长远上降低侵犯失信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风险。第二,应当明确限制媒体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收录和转载,法院允许的除外。因为在当前自媒体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不可控性,即便人民法院已在名录中删除了失信被执行人已过期的信息,但失信信息依然会随着被转载的媒体而长时间在网络上继续传播,纸质媒体上刊登的信息甚至会永久保存。“冈萨雷斯诉谷歌案”的起因就是谷歌搜索引擎收录了纸质媒体数年前已过期的信息,造成当事人利益受损,从而致使诉讼发生。
(三)退出救济中的“被遗忘权”——保障删除权
《民法典》保障自然人依法对个人信息行使删除权。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布制度的退出和救济途径,保障失信被执行人“被遗忘权”, 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做法,明确规定信息处理主体的删除义务。我国失信被执行人在满足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退出的三种情形后,首先,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若干规定》在要求时间内删除名录中的信息,并及时对接公安管理系统和征信系统将相关数据进行更新。其次,已经在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互联网平台上的信息也应当采取删除措施。人民法院可与互联网平台建立联系,人民法院及时更新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并要求互联网平台将过时的信息删除或封存。若这些互联网平台未能及时将过时的信息删除或封存,并对当事人造成名誉权、隐私权、财产权等权利的损失时,应当赋予当事人以该事由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的权利。尽管这种做法在技术上可能暂时还有一定的难度,但可以一层层推进,逐步完善我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退出机制,从而维护失信被执行人的“被遗忘权”。
[注 释]
①参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本网址最底端可看到相关数据,但数据为实时更新。
②参见中国文明网,http://www.wenming.cn/jwmsxf_294/cxjszdh/sjts/201807/t20180716_47599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