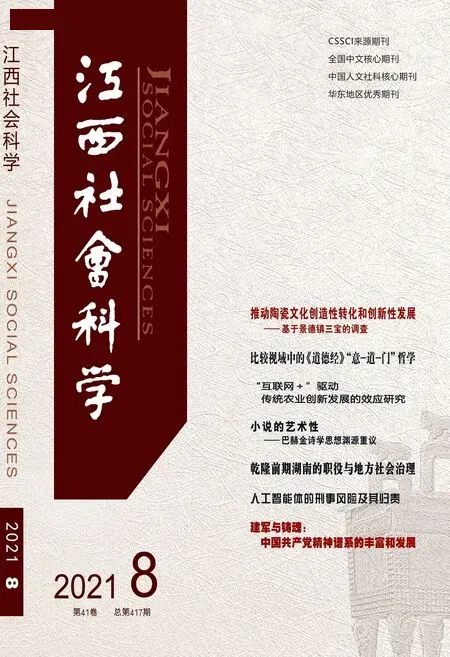重建启蒙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
■唐 苇
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主张宗教与世俗之间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相互学习、互为补充,他真正的用意在于通过交往行为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以弥补理性在自我反思意识上的缺失,从而达到修正和重建启蒙理性的目的。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对缓和当代国际范围内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和矛盾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以世俗理由为前提的模式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对信仰的优越感,其现实意义也势必受到具体国家和社会状况的限制。
在《后世俗社会注释》(2008)一文中,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后世俗社会”①(postsaekularen Gesellschaften或postsecular society)的典型特征与政治影响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正经历着一次“宗教复苏”现象,欧洲社会可以被称为“后世俗社会”,是因为它仍需调整自己以适应宗教团体在世俗化②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持续存在的情况。[1](P17-29)简言之,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认为宗教将在世俗化过程中持续存在,他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宗教复苏的形势下重启宗教与世俗和谈之门,倡导世俗和宗教之间互相学习、互为补充,使知识和信仰在一种自我反思的状态下共存。
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与他早期的宗教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首部重要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中,他把宗教视为理性的他者,将宗教排除在作为公共理性形成空间的公共领域之外。“宗教自宗教改革以后变成了私人的事情”,“教会在公民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失去了其作为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性质”。[2](P266)在《交往行为理论》(1981)中,他使用“神圣者的语言化”(the linguistification of the sacred)概念将宗教和理性视为此消彼长的对立事物。认为“神圣领域的祛魅和失势过程借由仪式上受保护的基本规范协定的语言化而发生,伴随着交往行为中理性潜力的释放。”[3](P77)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主张现代性必然导致宗教式微的世俗化理论开始受到质疑③。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将宗教与理性对立起来的立场受到了许多神学家和理论家的猛烈批评。他开始意识到世俗化理论的局限,并改变对信仰的态度。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和《后形而上学思想》(1988)中,他不再将宗教视为理性的对立面,而是开始从正面肯定它。进入21世纪以来,哈贝马斯对宗教的公开论述显著增多,他想进一步打破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关系。在2001年10月的一次题为“信仰与知识”的演讲中,他督促宗教和世俗在多元社会背景下都应积极进行反思:宗教应该放弃使用暴力手段,在不影响社会凝聚力的前提下认识到政教分离的世俗立场在后世俗社会中的真正意义,而世俗政府应保持中立,避免在做政治决定预判时偏袒知识与信仰中的任何一方。[4](P327-337)此次演讲可以说是“这位持启蒙立场的哲学家对宗教问题的首次公开、系统检讨”,因为哈贝马斯“放弃了理性与信仰、世俗与宗教的截然对立,提出理性有其宗教根源”[5](P93)。2004年1月,在与红衣主教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的辩论中,哈贝马斯积极倡导后世俗社会中宗教与世俗资源之间互补性的“双向学习过程”[6](P43-47)。在《在自然主义和宗教之间》(2005)中,哈贝马斯认为世俗与宗教双方都应积极反思并“在公开辩论中相互倾听和学习”[7](P3)。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代表了他在宗教问题上立场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视为哈贝马斯的神学或宗教转向④。然而,哈贝马斯的思想是否真正发生了宗教转向?他的宗教观缘何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其真正意图何在?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将他的宗教观转变置于其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整体框架下进行分析。
一、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转变
作为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和社会理论家之一,哈贝马斯深受前辈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人的启蒙批判理论的影响。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示出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与人的主体地位不断膨胀的发展趋势,并认为启蒙终将演变成新的神话,从而导致文化工业与法西斯主义的悲观结局。“因为启蒙带来的科技强制执行同一性,把万物都纳入科技系统当中,仿佛纳入了启蒙之前的神话系统当中。况且,追求启蒙而高举人的主体,使得人的主体不断地膨胀成神话人物”[8](P192)。与两位法兰克福学派师长的观点不同,哈贝马斯并不否定启蒙现代性,而是意图通过修正与重建启蒙理性对抗激进的反启蒙运动,从而促进现代性事业的顺利完成。对他来说,反启蒙运动的众矢之的是以主体意识哲学为根基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通过目的行为将主体的意愿强加于客体之上,对客体进行压制,是一种主客二分的不平等理性,最终导致“生活世界”被“系统”⑤殖民化的后果。哈贝马斯致力于通过主体间平等对话和协商的交往行为将启蒙理性从工具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校正理性的发展方向,恢复理性为人类文明服务的维度。有学者评论到:“哈贝马斯认为,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现代理性虽然有缺点,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解放潜能的方案,对现代性的启蒙必须从主体哲学中剥离出现代性的规范理性,并把它安置在一个新的可靠的基础上,这一基础就是所谓的交往理性概念。”[9](P29)
由此,哈贝马斯开始允许宗教进入作为其理论体系核心的公共领域之中。作为公共舆论和公共理性的生产空间,公共领域奠定了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根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以及民主宪政国家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不同立场和背景公民的团结一致和共同协商。这样一来,将宗教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立场便与他倡导的交往理性范式产生了冲突。于是,他不得不对改变自己对宗教的看法。他开始正视宗教中的积极因素,认为宗教不仅可以为特定的人群提供情感性资源,而且蕴藏着具有普遍意义的认知性内容。1999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
对于现代性的规范性自我理解,基督教起到的不仅仅是先驱或催化剂的作用。普遍的平等主义是犹太教正义伦理和基督教仁爱伦理原则的直接遗产,由此又衍生出自由理想及团结互助的集体生活方式、生命和解放的自治行为、个体的良心道德、人权及民主。这份遗产基本保持未变,一直受到批判性的重新利用和重新阐释。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事物能替代它。有鉴于后国家时代遭遇的挑战,我们现在必须像以前一样从这种物质中汲取持续性力量,其他一切都是无用的后现代空谈。[10](P149)
不难发现,哈贝马斯不再将作为西方文明根基之一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当成一种陈旧的世界观,而是视之为与现代民主宪政体制息息相关的存在,并承认其不可替代性。在他看来,犹太—基督教中的许多规范性教义和伦理原则,如正义、平等、互爱等,为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和社会秩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当前西方现代文明遭遇一系列危机与挑战的形势下,为了帮助现代性事业摆脱困境和推动其向前发展,对宗教中的有益资源进行批判吸纳显得尤为重要。除此之外,哈贝马斯还积极肯定犹太—基督教传统与作为西方文明另一根基的希腊哲学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关系:
基督教与希腊形而上学的相互渗透带来的不仅仅是神学教条的精神形式,以及基督教的希腊化(并非在每种意义上都是件幸事),它还促进了哲学对于真正的基督教理念的吸收。这项吸收工作在规范性概念群落中留下了痕迹,产生了重要意义,如责任、自治与合理性;历史与记忆;重新开始、创新与回归;解放与实行;外在化、内在化与具体化;个体性与集体性。哲学确实已经改变了这些术语最初的宗教意义,但并没有以打击和耗尽的方式掏空它们。[5](P44)
在他看来,希腊哲学与犹太—基督教传统之间并非截然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移植与借用的关系。两者在许多概念规范和伦理启示上具有重叠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启蒙理性及民主宪政体制正是希腊哲学与犹太—基督教传统相互吸收和交融的产物。哈贝马斯主张以哲学和宗教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的关系打破两者截然对立的偏见。
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后世俗理论。他认为,当今世界与宗教事务相关的变化与争端骤然增多,使我们不得不对认为宗教已经退出公共领域的世俗化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哈贝马斯对宗教或信仰本身发生了真正的兴趣。相反,哈贝马斯更为关心的是后世俗社会中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前景问题,即如何在后世俗社会中确保现代国家在文化与宗教世界观多元性不断增长的形势下保持其社会关系的民主度。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公共民权和文化差异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政府在宗教问题上需采取一种中立立场,在面对信仰争端时需缓和争执方之间的关系,寻求方法使敌对信仰之间达成和平共处并对之进行监督。民主政府只有做到政教分离才能保证公民的宗教自由平等权。与之相似,所有的亚文化群体,不管信教与否,也需要解放对其个体成员的束缚,使他们作为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平等成员得到互相认可。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民主政府、公民社会与亚文化群体自我维护之间的新型关系才是正确理解当今世界两股本应相互补充却相互争斗的力量的关键。因此,他提出互相认可基础上真正包容的主张。这种包容不应显示出纡尊降贵的态度,也不应只是简单的理解和尊重,而是真正意识到对方作为一个享有平等权利的共同体公民成员的事实。
从上文的阐述中可以发现,哈贝马斯的真正意图在于使多元异质的公民实现相互包容、团结互助、平等协商。从将宗教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到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他的宗教观发生了从世俗立场到后世俗立场的重大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意味他的理论思想体系发生了神学或宗教转向,哈贝马斯真正用意在于对宗教中的积极资源进行批判吸收和转化,通过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修正和克服理性的工具化属性,使启蒙理性获得一种自我批判和反思意识,从而推动和促进现代性事业的顺利完成。
二、信仰语言的转译与不对称的负担
虽然哈贝马斯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与理性交往协商,但信教公民要想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还需将宗教语言转译成一种普遍理解和接受的世俗语言。这也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内在要求。作为交往理性的现实表现形式,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旨在让不同背景的主体在没有任何约束与压制的环境中进行平等交流与协商。他提出宗教通过语言转译进入公共领域,旨在让宗教中的积极资源进入与世俗理性民主商谈和决策的过程中。
针对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有关公共理性运用的政治自由主义主张,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中所有公民(不管信教与否)都有均等的机会运用公共理性获得辩护的观点表示赞同,但他不赞同罗尔斯对政治公共领域中理性的公共运用设置的一个“限制性条款”(Proviso):“首先是,任何时候,合理的整全性学说,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有可能被引入公共政治讨论中来,只要在适当的时候有正当的政治理由(而不是仅仅由整全性学说提供的理由)被提出来,且这些理由足以支撑整全性学说可以支撑的任何事物。”[11](P5-6)哈贝马斯认为该限制条款迫使宗教团体和信教公民不得不脱离其宗教背景才能在政治公共领域讨论中发声,从而对他们造成一种不平等的负担。他主张取消这种不平等的限制。“与那些触及自由主义自我理解之根基的修正主义建议相对峙,我发展出一种构思,这种构想在两者间发挥调解作用。自然,只有当世俗和信教的公民实现了那些特定的认知预设,并相互将对方归于相应的认识立场上去的时候,他们才能实现对自由主义国民角色的那些规范的期待。”[12](P23)可见,哈贝马斯认为这个过程需要信教公民与世俗公民的双向意愿才能完成。具体来说,对信教公民而言,他们必须对世俗环境采取一种更开明的态度,并将自己宗教的语言翻译成一种普遍可用的语言才能在公共领域中做出贡献。而对世俗公民而言,如果不想让他们的信教公民伙伴们遭遇不对称的负担,也必须对宗教中可能包含的真理性内容敞开心扉。
为此,哈贝马斯将罗尔斯的限制条款修改为一种他认为更宽松的“制度性翻译限制条款”(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proviso):
自由国家不能将制度上不可或缺的政教分离原则转化为对其信教公民的过度精神与心理负担。当然,它必须期待他们承认在对相互矛盾的世界观保持中立的状态下行使政治权力这一原则……信教公民可以很好地认同这一“制度性翻译限制条款”,而不必在参与公共讨论时将自己的身份拆分成公共的与私人两块。因此,当他们无法找到与其信仰对应的世俗“翻译”时,应该允许他们用宗教的语言表达和论证自己的信仰。[11](P9-10)
从该条款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哈贝马斯允许信教公民不脱离自己的信仰背景进入政治公共领域,却是有附加条件的。首先,信教公民在对宗教语言进行转译时必须承认和接受世俗国家中立性的原则。其次,国家机构代表的政治公共领域的通用语言是世俗语言,因此,信教公民有义务让自己的宗教主张与世俗语言关联起来。再者,只有当信教公民无法用世俗语言转译自己的信仰主张时,才允许他们用宗教的语言表达自己。依此可见,虽然哈贝马斯的初衷在于减轻信教公民的负担,让他们进入公共领域与世俗公民平等协商,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世俗对宗教的优越感以及对信教公民的不对称要求。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对哈贝马斯的批判: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他总是指出世俗理性和宗教思想在认识上的不相通,并赋予世俗理性更加优越的地位……但是这个认识上的差别仍适用于他。由此,当谈论到国家的官方语言时,宗教的参考不得不被抹除。[13](P49)
在泰勒看来,哈贝马斯宗教立场转变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宗教中的积极资源服务于民主宪政体制,其实质仍是以偏袒世俗理由为前提的,并没有摆脱罗尔斯条款的世俗主义立场和公共理性的自由主义局限。
事实上,哈贝马斯本人也承认民主宪政国家的信教公民与世俗公民在交往商谈的过程中,必然会对信教公民造成一种不对称的“认知负担”,因为“对宗教理由的翻译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世俗理由制度上的优越性,都要求信教公民努力学习和适应,而世俗公民则免于这种努力”。[11](P13)然而,他认为这种不对称的负担可以通过对世俗公民施加一种“不要拒绝宗教贡献中可能的认知内容”的负担来进行补偿,理由是“世俗公民也同样无法免于一种认知负担,因为在与信教公民伙伴们的期待合作中,光有一种世俗主义态度是不够的”。[11](P15)换句话说,哈贝马斯认为信教公民要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必须将其转译成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世俗语言,而世俗公民由于其语言本来就具有普遍可接受性,则可以免除转译的义务。可见,尽管哈贝马斯给世俗公民强加了一种义务以解决这种不对称负担,但两者之间实现难度的对比仍凸显出世俗理由对宗教理由的优越性。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哈贝马斯‘中立世界观’的中立性比较弱,他对信教公民提出认知条件上的不平等负担,体现出一种哲学上的特权和世俗欧洲文化帝国主义的形象。”[14](P86)
由此可见,虽然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旨在建立世俗与宗教的平等互助关系,却是以信教公民承担不对称的认知负担,并在政治公共领域中向世俗理由做出妥协为前提的,其实质并未摆脱世俗与宗教二元对立的局限。究其原因,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是其哲学动机与思想进路在其宗教观上的集中体现。哈贝马斯的整体哲学框架都是围绕现代启蒙理性的修正和重建为中心的,他致力于通过交往行为理论实现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变,用主体间平等对话的沟通理性取代启蒙运动以来主客二分的工具理性,其最终意图是为了促进启蒙现代性事业的顺利完成,这就决定了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也是以偏袒世俗理由为前提的。
三、理论贡献与实践局限
哈贝马斯关于后世俗社会的讨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如何看待他的后世俗理论的实践意义呢?
首先,应当肯定哈贝马斯对当代世界范围内宗教与世俗将持续并存这一形势的正确认识。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范围内呈现世俗化进程加速发展和信教人口下降的趋势⑥。另外,中东宗教极端组织的崛起、欧洲各国“恐伊症”(Islamophobia)加剧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颁布的禁穆令等事件,都表明世界范围内宗教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正在持续扩大。
其次,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对缓和宗教与世俗的矛盾有着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以西方世界与中东世界的冲突为例,双方自古以来就互相充满敌意,近现代西方文明将中东文明视为非理性与危险的他者,并对其进行殖民剥削,导致中东国家内部种族、教派冲突不断。冷战及苏联解体之后到现在,中东国家虽然纷纷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但西方仍然通过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对这些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意图在中东世界的土壤上推广和培育其民主宪政体制。然而,西方的干预措施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得双方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一语中的地指出,西方自恃清高的优越感与中东国家自身的妄自尊大才是双方冲突不断且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15](P241)由此可见,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现实当中要对两者进行调和,必然困难重重。双方要想真正平等对话、互相学习甚至团结合作,就必须遵循哈贝马斯摒弃各自的成见,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世界观并进行自我反思。否则,双方将进入相互冲突和斗争的恶性循环,危害世界政局稳定与公共安全。“如果双方都不愿意进行自我反思,那么,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将如同分工一样协力通过新兴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两极化使政体的凝聚力陷入危险。”[6](P2)
然而,哈贝马斯后世俗理论对宗教特质的忽视和对世俗理性的偏袒,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宗教与世俗平等对话的设想。如上所述,哈贝马斯试图使宗教和世俗在自我反思与互相妥协的“学习”与“翻译”过程中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实际上却对宗教提出更为严格和不对称的义务与要求。换言之,宗教的排他本质决定了它无法对外来价值观做出妥协与让步,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信仰的不虔诚或背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宗教形势下,又多少凸显出几分理想主义的色彩。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在他对未来社会精心描绘的时候,人们不能不为他的热忱所感动,但同时也不能不怀疑哈贝马斯走上了一条在幻想的彼岸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之路。”[16](P43)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哈贝马斯学术思想进程中,他对待宗教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折,由早期视宗教为“理性的他者”的世俗主义立场转为现阶段认为“宗教将在世俗化过程中持续存在”的后世俗主义立场。哈贝马斯提出后世俗理论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交往行为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以弥补理性在自我反思意识上的缺失,从而达到修正和重建启蒙理性的目的。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宗教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的形势下,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对缓和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和矛盾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但这种以世俗理由为前提的模式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对信仰的优越感,其现实意义也势必受到具体国家和社会状况的限制。正如斯坦利·费希(Stanly Fish)所说:“宗教拒绝充当友好多元主义的快乐参与者并坚持其教义对所有人的正确性。自由理性致力于多元主义而无法证实除了它自己(空洞的)程序主义之外任何事物的正确性。哈贝马斯呼吁的借鉴关系与单方面让步似乎还不足以达成一种真正富有成效的友邦关系。”[17]可以说,当前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教与世俗的摩擦与冲突仍将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之一。各国政府要想真正化解两者的矛盾,就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基础之上,建构一种真正平等前提下宗教与世俗相互开放和相互学习的交往模式。
注释:
①据詹姆斯·贝克福德(James Beckford)考证,最早使用“后世俗”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格里利(Andrew Greely)。在其1966年的一篇题为《世俗性之后:新礼俗社会:后基督教附言》(After Secularity:The Neo-Gemeinschaft Society:A Post-Christian Postscript)的文章中,格里利使用“后世俗”这一术语来指称教会内部出现的一种新型类似礼俗社会的社群。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对“后世俗”的讨论开始急剧升温,但对于该概念的具体意思却众说纷纭。进入21世纪,“后世俗”的使用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广泛,但意义也变得更加多样和复杂。贝克福德将这些用法大体归为六类。参见:Beckford,James A..“SSSR Presidential Address Public Religions and the Postsecular:Critical Reflections”.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2012,Vol.51.
②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认为世界的世俗化过程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和“除魅化”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宗教中终极和崇高的价值观从公共生活中退出,人类不再把来世的生活看得比现世的生活更重要更确定,不再像野蛮人一样需要向魔法力量求助,科学技术替代魔法力量成为人类新的依靠。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言说》(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33页)。
③例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20世纪下半叶证明现代世俗主义欢呼宗教衰亡以及保守主义者担心宗教将导致可怕后果都是毫无根据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亨廷顿援引吉利斯·凯伯尔(Gilles Kepel)称之为“上帝的报复”(la revanche de Dieu),它遍及世界上所有文明与国家。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彼特·伯格(Peter Berger)认为自启蒙时代以来的世俗化理论在经验层面已经被证伪。首先,现代化在产生世俗化影响的同时也激发了“反世俗化”运动。其次,社会层面的世俗化与个人意识层面的世俗化并没有直接联系。再者,世俗化虽然使宗教的影响力受到减弱,但是宗教并没有消失。相反,旧式与新型宗教在个人生活中依然具有影响力,且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复兴的趋势。参见:Peter L.Berger.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Washington D.C.: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1999.
④奥斯汀·哈灵顿(Austin Harrington)认为哈贝马斯在其近期的作品“展现出一种与神学家论争的颇为同情的互动,至少在表面上与他早期的世俗主张形成了戏剧性的自我疏离”。与他将“生活的政治舞台视为思考哲学问题的最高和最有意义框架”的一贯作风不同,哈贝马斯的宗教观转变可能表明他“正试图将宗教与世俗的政治关系转移到哲学与神学的存在关系上”。参见:Austin Harrington.Habermas’s Theological Turn?.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2007,Vol.1.
⑤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由代表交往理性的“生活世界”和代表工具理性的“系统”两部分组成。生活世界“表示非正式的、未市场化的社会生活领域:家庭和家务、文化、非党派政治生活、大众传媒、志愿者组织等等”,而系统指的是“系统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子系统:金钱和权力。金钱和权力一方面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各自的‘操纵媒介’(即内在的指导、协调机制);另一方面形成了国家行政管理及相关的机制,例如公务人员和国家认可的政党等。”参见:(英)芬利森(Finlayson,J.G.)《哈贝马斯》(邵志军,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⑥根据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全球宗教信仰和无神论指数”(WIN-Gallup International GLOBAL INDEX OF RELIGIOSITY AND ATHEISM)2005年和2012年的数据,全球信教人口比例从2005年的77%下降到2012年的59%,而无神论者比例从2005年的4%上升到2012年的13%。转引自:加润国《全球信教人口有多少》(中国民族报,2015-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