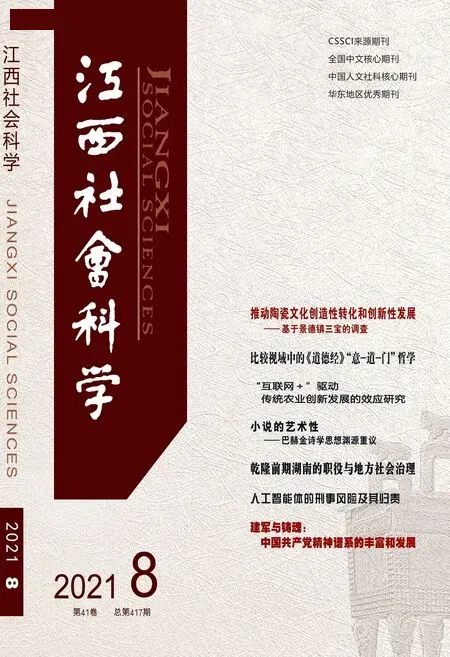东方想象:外籍译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删改与整合
——以伊万·金为例
■马宇晴 李宗刚
1945年,伊万·金于纽约出版的《洋车夫》,是对老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进行翻译及删改的产物,其后续译作也一再对其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予以删改。伊万·金大幅删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却能够广受英语世界读者的追捧,可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融入英语世界过程中对外籍译者主体创作意识的妥协和包容。因其外籍身份而体现出的文化书写差异,体现了外籍译者与作家、外籍华裔译者和中国国内译者在分别试图构建东西方文化空间时的拉锯痕迹。以伊万·金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的外籍译者,是中国现代文学内涵的重要书写者,他们以“接受—创造”模式进行跨文化交流实践,缓解中国译者译本传播效率低、效果差的困境,为中国故事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鉴的思路与方案。
外籍译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外籍译者的删改与整合为作品打上了深刻的异域文化烙印,由此使得其译本与原作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我们拟借助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的英译本,深入探讨外籍译者在翻译时所表现出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
《骆驼祥子》的首部英译本名为《洋车夫》(Rickshaw Boy),由美国纽约的一家出版社(Reynal and Hitchcock)出版,译者为美籍译者伊万·金(Evan King)。其译本作为《骆驼祥子》在英语世界最初的主要版本,可以当作关于现代文学作品译出研究的典型个案。老舍所著的《骆驼祥子》,以地道的北京地方语境塑造了一个底层小人物“祥子”,表达了个人主义奋斗在封建的旧中国必然会走向失败这一思想。而伊万·金的译文,以一个乐观、勤劳、积极向上的Happy Boy(快乐男孩)来表达个人的奋斗精神对社会整体性的作用,其归化的翻译策略构建了一个符合西方想象的现代中国男孩形象。因此,伊万·金的这部译本与后续的三部《骆驼祥子》译本相比,既在现代文学作品海外传播史与文化史上有着相对重要的位置,获得大量国际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又因其对文本内容删减、改写过多,而遭受到研究者尤其是中国国内研究者的质疑。也正是因其删改较多却传播较广的特殊性,使得此译本有着“再评价”的多种可能性,特别是伊万·金为什么会选择一部需要他如此大幅度删改的作品进行翻译,及以伊万·金为代表的外籍译者在跨文化翻译及其接受中体现出怎样的普遍特征和规律等问题仍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如果能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融入英语世界的过程的脉络,并为文学名著西行传播图景的历史面向和未来面向提供一种以译者为主体的研究路向。
一、两类外籍译者构建的东方想象
中国现代小说名著英译本来源于国内出版社有目的性的主动译出与国外出版社有选择性的主动译入,其背后的出版推动力各不相同,但构成东方文学想象主导力量的,仍是海外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译本,而其中参与出版的外籍译者,往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1917—1949年间,包括米尔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伊万·金、王际真、梁社乾等在内的外籍译者都曾参与翻译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如果将他们出版的译作并置进行考察,可以看出,不同的外籍译者或经意或不经意地将自己的身份标签打入了译作中,提升了西方翻译的文化学派所描述的目的语系统内的东方想象的丰富度。
目的语系统是相对于源语系统而言的,其是一个独立完整评价文学作品的史学研究范畴。以《骆驼祥子》的英译本为例,对《洋车夫》的研究和评价,应在西方文学场域内的文学发生论视域下进行,而不能直接将其转移到原作及作家老舍身上。然而,在探讨英译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时,人们却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所谓的现代中国小说“英译本”并非中国的现代小说,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小说,即译者主导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作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主体的现代中国小说英译本,其所探讨的并不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本体,而是西方化的东方文学想象。因此,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作为主要影响西方文学场域内现代小说评价的外籍译者持怎样的基本态度,构建出怎样的东方想象?
关于译者的基本态度,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早在1923年就提出了翻译成就原著的见解。他认为,被主动挑选成为译本的小说都存在自己的“可译性”,因为原著的“可译性”才吸引了翻译者,原著的生命得以延长。[1](P279-290)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不同的译者所关注到的“可译性”内容是不同的,甚至是天差地别的。
外籍译者对原作的主动挑选,一直存在着对中国现实、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辨析和过滤,因而文学中塑造出的东方想象愈加倾向于浪漫、不顾及现实、积极正面的特征。即使原作中有对中国现实、战争形势的极度关注,但译本忽略革命意味并将故事主线收敛、窄化到经历战争的个人生命历程上。比如,1943年在伦敦翻译出版的谢冰莹的《女兵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Girl:A Genuine Autobiography),及1942年在纽约翻译出版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Village in August),译本的“可译性”体现在其通过对战争的事态描绘能够引起大量西方读者关注,但是这种“可译性”并不能阻止外籍译者减少对于原著中革命精神的翻译和对革命人物主体形象描绘的删改,传递出的革命思想是模糊的,甚至是歪曲的。于是,这些译本在外籍译者的部分接受与再创造后,造就了瑰丽、独具魅力的东方形象和人物形象,却失去了有东方独特价值的思想意识与文化传承。
与此相对,外籍译者中的华裔译者,他们正视中国现实社会与压迫下显露出的革命意识,有着民族传统知识分子肩负改良中国社会的潜在意识。诸多华裔译者秉承还原文学作品原貌的翻译策略,造就了符合现实压抑的社会现状的、破除西式想象的东方意象和正在经历痛苦的中国民众的典型形象。如美籍华裔译者梁社乾在翻译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鲁迅的《阿Q正传》等文学作品时,就算曾被一些批评家认为“僵硬”“不自然”“极为难读”“墨守了直译法”①,仍旧坚持了自己的“尽量贴合原文仔细翻译”的译介美学②,努力构建出一种修饰后的表达现实的东方想象,探讨的核心内容离不开现实苦难和社会灰暗,政治问题与革命意识仍能得到部分体现。
查明建认为:“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所译作品的情况。”[2]对于挑选和翻译《骆驼祥子》的伊万·金来说,他既无须顾忌西方文学读者和研究者会对他所塑造的东方想象进行真实与否的评判,也没有传递中国思想、价值观的想法,作为译者,他只需关心读者的喜好并符合当时美国意识形态的框架。“译者会尽量使自己的选材符合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3]这也就意味着以伊万·金为代表的外籍译者与外籍华裔译者相比,不存在有为中国民族文化印象增辉的原始冲动和民族自豪感,也不会有华裔译者的“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4]与彰显民族荣耀的潜意识倾向。因此,伊万·金等外籍译者构建出的东方人物形象拥有乐观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并且人物不会围绕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原著中悲观的人物形象大多模糊和被删掉,不管东方现实世界如何,翻译时都不会出现前途灰暗、对现实社会绝望的东方人物形象。
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译者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不同的东方文学文本形象与东方风情想象,并以他们不同的理解和标准,各自修正着西方文化领域的东方图景。不过,外籍华裔译者所构建的较真实的东方文学想象,在西方读者和汉学界只能够处于边缘,引发的关注与讨论仅存在于少量汉学家的研究中,对普通市民读者影响较小。
在1919—1949年间,有14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译本在英语世界出版,其中便于普通市民读者进行阅读的小说单行译本仅5部,伊万·金的译本就占据3部之多③。于是,以伊万·金为代表的外籍译者,虽然与华裔译者形成极强的对抗性,但其无疑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文学场域内讨论的空间。因此,这种令伊万·金译本显露出的对抗性及其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伊万·金翻译《洋车夫》的文化心理结构
伊万·金作为外籍译者,经其翻译、删改的作品成功走入了美国大众的视野,同时,伊万·金对《洋车夫》文化上的重构贯穿作品始终。关于伊万·金对《骆驼祥子》原著进行的删减与改写的具体情况,国内学者已经就此进行过全面的比对。④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就伊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为什么会进行删减与改写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没有深入伊万·金的内在文化心理结构中加以确认与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的过程并不是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硬译”过程,而是翻译者基于对翻译作品内在精神的独特把握,将其整合到自我的、既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然后再外化为译入语的过程。具体来说,伊万·金翻译的《洋车夫》对《骆驼祥子》的删减与改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伊万·金把骆驼祥子纳入美国文化体系中,尤其是纳入“美国梦”这一主题之中,这便将骆驼祥子作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置换成了个人奋斗的成功者,由此使得骆驼祥子承载了“美国梦”的丰富内涵,使《骆驼祥子》得以“美国化”。
骆驼祥子在经历了人生“三起三落”的折磨之后最终走向了精神的崩溃,并由此开始了人生的沉沦历程。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5](P122),但也不乏一些在性格上缺少韧性的国人。老舍通过祥子个人奋斗的失败,揭示了其悲剧根源既有时代和社会因素,同时也与祥子的自我性格缺陷有着直接的关联,从而“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自觉”[6]。然而,祥子这一人物形象在伊万·金的笔下则完全褪去了这一性格弱点。取而代之的是那种为了梦想而永不放弃的韧性,并最终修成正果,完成了人生的逆袭。这样的一种置换,显然已经不再是中国的骆驼祥子,而是美国的“洋车夫”,是一个完全美国化了的车夫。在“美国梦”的驱策下,每个前往美国进行淘金的移民,无一不是历经人生磨难而绝不放弃才修得正果的一批英姿勃发的进取者。正是在这种既有的文化理念的烛照下,历经了“三起三落”便放逐了自我梦想的骆驼祥子,自然难以获得伊万·金的认同和赞许,也不符合其对《骆驼祥子》的既有心理期待,因此,对其进行必要的置换乃至改写便成了他在翻译时无法抑制的内在驱动力。
其二,伊万·金从根本上颠覆了《骆驼祥子》的故事情节,这就使得原作的矛盾冲突中的悲剧性内涵被过滤和扭转,悲剧被置换为大团圆的结局。伊万·金将中国的骆驼祥子改造为美国的Happy Boy(快乐男孩),把小福子改造为Little Lucky One(小幸运),由此使得《骆驼祥子》被整合为《洋车夫》,进而使该作品最大限度的“美国化”。当然,《洋车夫》中不只是祥子和小福子被进行了改造,作者与译者对情节发展走向的不同规划还导致了关于曹先生的情节的处理上出现分歧。如原著中曹先生没有补给祥子被孙侦探敲诈的大洋,而译本中曹先生却补给了祥子这一笔钱,显现出老舍和伊万·金对曹先生这一人物形象设计目的的根本不同。老舍的《骆驼祥子》里,曹先生表面上看似对底层劳动人民表现出一定的关心和同情,曹先生在文中更被祥子直称为“圣人”,可老舍在描写这位“圣人”的时候,又没有塑造出一副全然没有私心的人物形象。老舍一边描绘着曹先生的“人道主义”,另一边又描写了他心理真实的一部分想法是“贪图夜间的雪景”。在祥子拉着曹先生不小心摔了的时候,“祥子一回头,脸上满是血”,曹先生的表现是“害了怕,想不起说什么好”,到了家,自行先跑了进去。如若真是描写一个绝对的圣人,是不必加上曹先生也有自己“赏雪景”私心的,或是在祥子摔了跤之后,也是不必多增添笔墨描写出曹先生些许冷淡、自私的一面的。老舍曾在《骆驼祥子·后记》里说,“在书里,虽然我同情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好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看到革命的光明,不太认识革命的真理”。[7](P668)所以,曹先生这个知识分子形象并不能成为给祥子生活带来希望的人道主义“革命者”,或是成为一个带领祥子找寻出路的引导者。
而伊万·金所崇尚的,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鼓吹的个人、自由、平等、自治等西方价值观,他在译本中对曹先生和祥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译者导向的判断和改写,出现了译者自行创作的情节和塑造的人物形象,导致译文中的曹先生形象能够抛开原作中社会氛围的影响,对祥子做到了切实的帮助。曹先生凭“一己之力”,偿还了祥子被敲诈的买车的钱。译作挥散了老舍所描绘出的个人在社会中的无力感,将原作中激烈的矛盾冲突化解,悲剧色彩随之减淡。
其三,伊万·金将原作中描绘的个人的毁灭与渺小在行文中解构,将小人物个体的光和热放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结尾是否按照伊万·金设置的大团圆结局发展,小人物的底层形象与生命历程都已经有了质的改变。与其说伊万·金笔下的主人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希望,不如说是小人物本身蕴含的能量在伊万·金的眼中和笔下是能够击破社会的“黑屋子”的,小人物是能够摆脱外在社会环境以及时代束缚的独立个体。这是符合西方精神的主动改写。
伊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并没有得到老舍的授权,老舍甚至对自己这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也不知晓。当伊万·金把老舍的《骆驼祥子》翻译成《洋车夫》,并在大洋彼岸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老舍才知晓此事。然而,老舍发现自己的《骆驼祥子》已经被删减和改写成了《洋车夫》之后,他并不认同,而是提出了异议。⑤从老舍的文化立场来看,他对于个人主义至上的利益追求不可能认同。但是,如果伊万·金完全按照老舍的要求翻译《骆驼祥子》的话,那其被美国读者接受的情况到底怎样,将是一个未知数。毕竟,在美国读者的文化视野中,祥子最终放弃了自我奋斗,这与美国文化所张扬的“美国梦”以及美国精神相去甚远,便会成为美国读者拒绝这部作品的现实理由。
事实上,伊万·金针对《骆驼祥子》的质疑曾经这样斩钉截铁地传达到老舍那里去,“要不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作了进一步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老舍则抨击伊万·金“再也不会恢复成一个好人了”。[8](P634)正是站在译者与作者各自民族文化的立场上,两方才会互不理解和产生矛盾。换言之,产生这种势不两立的对峙情绪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差异。这也进一步说明,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出现删减乃至改写是很难避免的。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过程中,而且还出现在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如林纾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当时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恰是林纾在翻译时不断删减和改写的自然结果。[9]如果翻译仅仅是一一对应的直译,那只能是一种基础意义上的翻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毕竟,离开了翻译主体的文化整合,很难谈得上翻译作品的跨文化语境传播与接受。
三、从外籍译者内化方式看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
伊万·金作为翻译的主体,自然拥有翻译《骆驼祥子》的权力,他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按照《骆驼祥子》的原貌进行翻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删减和改写《骆驼祥子》,这一翻译本身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是什么力量促使伊万·金以这种方式来删减和改写《骆驼祥子》,由此使得中国的《骆驼祥子》被“装扮”成了美国的《洋车夫》呢?
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成为伊万·金删减和改写《骆驼祥子》最为重要的力量。学术界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对此进行论述。如有学者认为,“英语文化的强势地位和美国的社会意识形态”[10]是伊万·金删减和改写的主要原因,这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结论。然而,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到底怎样内化为伊万·金的文化观念,并由此成为其文化实践的内在自觉?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然而,这却是我们应该追问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才是真正促成《骆驼祥子》“美国化”的最大驱动力。
其一,“个人”化精神书写成为外籍译者解读、转变、内化20世纪上半叶东方文学的主要方式之一。伊万·金在《洋车夫》的翻译过程中,对《骆驼祥子》中“个人—集体”的社会性认知进行了颠覆性的转化。“集体”的概念在《洋车夫》中不再像原作中那样突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指出,老舍这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观点令人吃惊,尤其是作者对主人公的公开轻蔑:“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着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11](P159)而维系人与人的关联的“人情世界”在《洋车夫》中变成了“个人”对“个人”的单线联系。小福子的命运可以不被她的家族吸血至死。译者的这种“个人”化的精神书写冲动成为《骆驼祥子》“美国化”的一大推动力。
这样的删改并不仅仅存在于针对老舍小说的译作中,在近乎同一时期,伊万·金对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进行英译⑥,同样对于其中的关键核心——革命的主体,进行了改头换面,甚至不惜改写情节,塑造出了更符合西方读者喜爱的人物形象。
显然,中国现代作家身处传统与现代的间隙,无论是旧时宗族伦理的集体意识还是现代秩序中隐含的人情世故,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都无法符合外籍译者立足于“个体”对应“个体”的现代性立场。因此,对于外籍译者的文化重塑,其意义也就不限于研究其对中国人情社会关系的不够了解所带来的“群体”特征的削弱,还在于研究强势文化如何接受和纳入弱势文化。
其二,美国读者的阅读惯性及其接受心理成为伊万·金删减和改写《骆驼祥子》的又一重要的力量。任何一部作品的价值实现都离不开读者的阅读和评价,这就导致译文中随时随地流露出贴近美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饱含“亲切感”的描述。比如,在原作《骆驼祥子》中,主人公祥子“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12](P13),而在《洋车夫》里,这段话被翻译成了“他只关心他的车,车能生产热的小圆面包卷、蒸米饭以及他的其他食物”[13](P21)。虽然同样是将车的重要性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民很重要的土地来凸显,有着身家性命的重要意义,但是在伊万·金的翻译中,往往出现“美国化”的处理手法。对比来看,原作中祥子所提到的烙饼主要成分即是来自于小麦(wheat)磨出的面粉,而译本中却使用了大米(rice)一词。伊万·金选择了西方读者熟悉的东方食材——大米进行翻译,替换了老北京的、拥有北方特色的食材——小麦。类似的替换还有很多,例如将中华传统食物“饼子”换成了西方饮食文化中的对应品“蛋糕”(cakes)。这不仅是伊万·金对东方食物的一种想象性的拆解和西方视角下的重构,更是一种有目的性地提升读者“亲切感”的翻译策略。很多学者认为伊万·金的这种给美国读者“亲切感”的翻译是一种有意识或潜意识下的“误译”,但他所传达的“符合美国意识形态的、不真实的中国社会衣食住行的状况的身临其境”“个人主义在压迫下的力量彰显”“人应该如何追求梦想的奋斗精神”等文化内涵,回应了“二战”后美国读者鼓舞士气的现实需求,同时满足了美国读者对中国的猎奇心理。这些影响作品阅读、评价的内在文化逻辑,是促使《洋车夫》删改原作的另一主要驱动力量。
其三,伊万·金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学,这使他有了选择《骆驼祥子》进行翻译的文学基础。伊万·金在1942年就曾翻译出版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并被《时代周刊》称为“对中国知根知底的极少数美国人之一”[14],这使得他“中国通”的特殊身份获得了美国读者的进一步确认,为其在翻译《骆驼祥子》时进行删改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空间。严格来说,伊万·金并不是一名普通的新闻记者,也不是一名普通的翻译家,而是一名肩负着美国政治使命的外交官,他的这一独特身份赋予了他特殊的政治理念和文化诉求,由此深深地影响其文学翻译,使得其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融入了美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诉求。从这一维度来审视伊万·金翻译的《洋车夫》,其便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老舍创作的《骆驼祥子》,而是作者与译者思想和情感的“混血儿”。
伊万·金作为前驻外使馆外交官,在“二战”后致力于搭建中美文化、文学交流的平台,积极促进中美文学的对话与交流。正是基于这一文化立场,他才把目光聚焦于《骆驼祥子》这部反映都市社会底层的文学作品,通过对骆驼祥子这一人物形象的改写,把中国的骆驼祥子改造、置换成了“洋车夫”——不仅是一名“快乐”的“洋车夫”,而且还是一名“快乐”的“男孩”,这不仅令人联想到了美国俚语中的Playboy(花花公子)。美国文学作品中的骆驼祥子,已经不再是那个朴实到有点木讷的祥子,而是一个饱含着快乐人生诉求的祥子。正是在这样的基调下,祥子的人生不仅是“快乐”的,而且还是“成功”的。快乐男孩犹如在美国大地上那些怀揣“美国梦”的奋斗者一样,成为美国文学世界里的奋斗者和成功者。而祥子的悲剧人生则退居于历史的幕后。也许,正是基于这一根本性的改写,才导致了老舍与伊万·金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改写在老舍看来,可以说是几乎不能被接纳和容忍的;同理,把骆驼祥子的人生按照老舍的原貌表现出来,这对伊万·金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
我们如果对伊万·金翻译的文学作品作一扫描,便会发现,伊万·金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都是一些反映社会底层普通人的作品,而很少涉及知识分子等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一方面说明了伊万·金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自有其独立的一套解读的理论和模板,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其所皈依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在伊万·金的思想深处,他对革命、知识分子等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力量并不十分认同,甚至还带有某种抵触的态度,这与记录同时期中国社会现实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有着根本的区别。埃德加·斯诺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并写出了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从而使美国及世界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但伊万·金则不然,在伊万·金翻译的文学作品中,他所关注的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城市拥有“赤子之心”的底层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珍视个人尊严、坚守自己的爱情观和价值观”[12](P13)。显然,这些人物形象既是中国的,更是美国的,是伊万·金在翻译过程中对生活在中国的小人物的“文学想象”。
四、结语
20世纪上半叶,在与国际关系变迁息息相关的跨文化汉学交流中,外籍译者的删改行为几乎完全配合了意识形态的“政治风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研究中,其也大多被研究者放置在权力话语与翻译审美的“天平式”解读结构中。伊万·金对萧军、老舍小说的主动翻译和大幅删改,既无法脱离政治意识形态,也离不开译者创造更能受到译入国读者喜爱的东方故事的思考。正是以伊万·金为代表的外籍译者的主动努力,拓展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学术思考、论争空间,也体现了其与外籍华裔译者翻译行为之间存在的矛盾,而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融入英语世界之初所必经的阶段。
翻译活动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字转译,而是翻译主体把外来语言建构起来的文学大厦在价值和意义上的整合。而往往这种情形下,翻译主体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大厦不再承载原来的价值和意义,而是成为承载了翻译主体的内在价值和意义体系的综合体,原作的独立主体价值和意义也被消解了。
正是在此基础上,译作在获得了价值和意义的重新赋予之后,才开启了从思想到文字的转化过程。具体到伊万·金而言,则是从汉语到英语的过程。从翻译主体来看,则是从语言到思想,再从思想到语言的过程。能够在西方出版并获得译入国读者接受的现代中国小说的英译本,实则是西方世界话语与译者文化选择及偏好博弈的结果。所以,在此过程中,拥有接近译入国读者的思想文化的外籍译者的译本,出现所谓的删减和改写,使其获得较广泛的传播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与此同时,外籍华裔译者和中国译者在20世纪上半叶,努力祛除逐渐固化的东方民族形象,也在努力改变由外籍译者所造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文本意义日益西化和窄化的局面。
注释:
①参见:甘人《阿Q正传的英译本》(《北新周刊》1927年第47期),戈宝权《谈〈阿Q正传〉的英文译本——鲁迅作品外文译本书话之二》(《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汪宝荣《异域的体验——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阿Q正传〉两种早期英译本描述性研究》(《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5年第1期)。
②参见汪宝荣《译者姿态对中华文化外译的解释力——以梁社乾英译〈阿Q正传〉为例》中所转引的《阿Q正传》英译本译者序,以及1931年版《苏曼殊全集》中载梁社乾所著《英译断鸿零雁记序》,可知梁社乾在《英译断鸿零雁记序》和《阿Q正传》英译本译者序中都曾指出,他在翻译时尽量紧贴原文,几乎“逐字翻译”是他翻译秉持的一贯风格。
③此统计涵盖中国现代著名作家50余位,依托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MCLC数据库、美国罗彻斯特大学世界文学资料中心数据库(Three Percent Translation Database)、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资料中心(Language Resource Center)以及国内外相关论文的数据。
④如:孔令云《〈骆驼祥子〉英译本校评》(《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孙会军《〈骆驼祥子〉的四个英译本比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1期),李越《〈骆驼祥子〉四英译本翻译风格对比分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苏天颖《Evan King英译〈骆驼祥子〉中的“误译”分析》(《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版2015年第12期),等等。
⑤参见1948年3月29日赛珍珠致劳埃得的信件:“事实上,他(老舍)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本来就十分不满。”
⑥据夏志清在197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73页考证,出版于1942年、1943年的《八月的乡村》英文全译本的译者为伊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