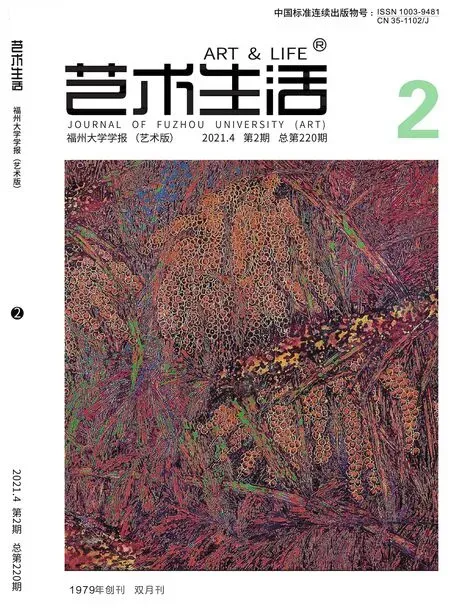谈北碑与南帖审美风格之差异
邹广胜
(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书法中用笔书写与用刀刻字是书法美学中的重要问题,如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其纸本早已不存,除流传下来的《兰亭》唐摹本外,大多是从刻石上复制下来的拓片,其艺术效果与书写在纸上的原初效果根本不同,正如各种《兰亭》拓本与陆机《平复帖》的审美效果不同一样,这也是中国书法史上 “刀笔” 与 “碑帖” 之争的根本问题,因为刀、笔的不同书写方式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书法的不同审美气质。关于碑帖之争,如果以帖的风格与尺度来评价碑,那确实只能看到生硬与土气,但如果以它自身的尺度,那就会看到刚强与质朴。关于《兰亭》之争既有 “真赝” 问题,也有 “妍媸” 问题,前者是求真的考古学问题,后者则是求美的图像学问题。郭沫若于1965年发表了著名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中以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及其他晋代砖刻文字基本上都是隶书体作为论据,认为王羲之的字体也应该是 “没有脱离隶书笔意” 的。而现存《兰亭序》的字体则与唐代的楷书一致,因此,《兰亭序》的真实性是存在问题的。[1]郭沫若的观点受到了高二适、商承祚等学者的反对。究其两派争执的焦点除了历史、文学、书法等内容外,还有一个根本的书法图像学问题,也就是书法作为一种图像艺术,其字体、书体、书风的发展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关于《平复帖》的争论也是如此。晋陆机《平复帖》作为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比王羲之《兰亭》略早50年,其草书与篆隶结合,浑圆高古,然其文字内容却让历代鉴赏家 “苦不尽识” 。历代关于《平复帖》内容的争论不仅仅是文字语义的争论,更是书法字形字体的争论,对《平复帖》内容合理的解读必然要与当时的语言文字及草法书写的规范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成。
一、以刀代笔的北碑与墨迹书写的南帖
魏晋南北朝造像、造像记是艺术家们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石质上创作的精美图像艺术,这些精美的艺术与山林、石窟、墓室、石阙等融为一体,再加以其内容丰富多彩,多为历史故事、神仙鬼怪、奇禽异兽,花草树木等,往往都是语言艺术与图像艺术完美融合的综合艺术体。魏碑造像记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审美风格的书法形式,其书写的内容是文字,其外在的形式则与绘画相通;书法以笔墨、色彩、构图彰显自身,它对线条美有无上的追求,线条本身的形状、变化、结构、质地就是形象,彰显了书法作为视觉艺术的本质,所以书法是以语言为载体,同绘画一样是以笔墨线条为图像,供人欣赏的空间图像艺术。
魏碑造像记不但是一种书写艺术,更是一种雕刻艺术,是融文、书、刻三者合一的综合艺术。新疆和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卷和残纸说明当时纸已经取代帛书和竹木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用笔在纸张上书写与在竹简上书写根本不同,从而也产生了根本不同的审美效果。与纸张及竹简根本不同,魏晋广泛流行的石窟造像与摩崖石刻则依山势造窟凿石,雕刻与书写也常常随山体的高低之势与石质的硬软不同而不同,造像与山体融为一体,往往产生气势宏大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与拿在手中直接观看的纸质书卷所产生的优美可爱根本不同,其审美效果迥然有异。书法的媒介有石、木、铜、玉、竹、帛、绢、砖、墙壁等,其中墨迹的书写与金石的碑刻给人以截然不同的视觉感受。在《兰亭集序》墨迹的临摹与翻刻流传过程中,翻刻的尺寸、行列的安排、字迹的缺失、字口的磨损、字的界格及装裱等因素都直接影响《兰亭》的视觉审美效果,再加在翻刻过程中具体的技术问题,如双钩、填墨、上石木、雕刻、翻拓等,在这些过程中不同人的技术工拙、材质的软硬、操作的时间与环境等都直接影响《兰亭》会以一种截然不同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切最后都要呈现在翻拓的纸张上,翻拓就是二次创作,纸张的质地、薄厚、燥湿,用墨的浓淡、轻重、明暗,拓者的技术与情绪等也都使《兰亭》翻拓的效果出现不同。这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刀笔、碑帖之争,其本质乃是关于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审美媒介所产生的不同美感进行的争论,启功 “透过刀锋看笔锋” 的说法也是要尽力融合二者的审美特点,既要看到用笔的特点,又能明确字的结构,使人不要偏废刀笔给人的不同审美感受。启功《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谈到碑刻参杂了刻书者的审美趣味时说: “特别值得指出:在看碑刻的书法时,常常容易先看它是什么时代、什么字体、哪一书家所写,却忽略了刻石的工匠。其实无论什么书家所写的碑志,既经刊刻,立刻渗进了刻者所起的那一部分作用。(拓者,又有拓者的一部分作用)。” “书法有高低,刻法有精粗,在古代碑刻中便出现种种不同的风格面貌。”[2]81-82在启功看来,《龙门造像》厚重方棱效果明显是刀刻的结果,用毛笔很难能直接书写出这种艺术效果,至于《升仙太子碑额》则精确表现了原毛笔的效果。
当然碑刻有刻工的加工作用,但刻工的作用毕竟有限,也不可片面夸大,更不可认为刀刻的作用都是正面的,刀刻无疑丧失了很多毛笔本身所特有的书写美感。《爨宝子碑》的方切特点自然有刀刻的作用,但同样也反映了用笔本身的特点,如赵之谦那样把魏碑的刀趣和书法的墨韵完美结合起来,产生丰富多姿的艺术风格。因此,碑刻是书法家、刻手与材质,甚至是时间、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米芾在《海岳名言》中就提出了著名的 “石刻不可学” 的观点,他说: “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唯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差,乃知颜出于褚也。”[3]976沙孟海在《碑与帖》一文中说: “有些北碑戈戟森然,实由刻手拙劣,信刃切凿,决不是毛笔书丹便如此。”[4]162-163书刻是书法家与刻字人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刻字人的介入自然会加入自己独特的理解与风格,因此相对于原初的书写,自然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与失真,但并不意味书法由此变丑,而是以一种新的姿态与风格呈现在观者眼前。至于石刻由于长期保存自然原因造成的剥损、风化、模糊、干裂等产生的 “金石之气” ,也会给拓本带来特有的风韵,以满足书画家特殊的喜好。
关于《兰亭》的真伪之争,不仅仅是关于《兰亭》文字内容的争论,更是关于兰亭的书写风格之争。郭沫若认为《兰亭》是伪作不仅仅是因为《兰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与王羲之的思想内容不尽吻合,更重要的是《兰亭》的书体与当时出土的各种墓志的书风不同,而反驳者高二适也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了自己的论证。总之对《兰亭》的认识是从两个根本不同的方面来进行的:那就是文字的内容与书写的外在图像特点,现存《兰亭》的书写风格确与《平复帖》给人的阅读及视觉审美效果迥异。但我们从现今流传下来的魏晋南北朝的书迹来看,当时已经出现了非常规范的正书字体。当然,即使是同一人,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及情绪之下写出的作品也是不一样的。书法家在书写不同的作品时,由于书写内容的不同,再加以书写者的精神状态不同,作品最后所呈现出的精神气质也是不同的。孙过庭《书谱》在谈到王羲之的书法形式与其书写内容之间的关系时说: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5]88王羲之在写《乐毅论》《东方塑画赞》《黄庭经》《太师箴》《兰亭》等不同的文章时,会产生不同的书风,如《乐毅论》中的感伤忧郁、《东方塑画赞》的瑰丽奇巧、《黄庭经》的虚无缥缈、《太师箴》的抗争曲折、《兰亭集序》的惠风和畅、《告誓文》的压抑悲惨等都对王羲之的书写产生了不同影响,当然各种书写与书写风格必须以当时流行的字体为依据,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字体而独创一体,而只能以书写时代流行的字体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清中后期随着碑学兴起,书法界也就出现了魏碑风格的《兰亭》,启功就曾发现清代伪造的魏碑《兰亭》[6]72,这种以刚劲的魏碑风格书写的兰亭,和传统的典雅潇洒的风格相比,给人以一种怪异的感觉。这也许正是主张目前存世《兰亭》为假的学者所认为的《兰亭》应该具有的风格,因为这正是那个时代普遍具有的风格。但从陆机的《平复帖》来看,魏晋流行的书风也并非全是魏碑风格,魏碑刚劲峭拔的风格主要出现在造像石刻之中,且多是由刀刻的加工手段造成,其实质也就是书法的介质对书法风格与书法审美趣味的影响。古碑多尊重内容,形式上也多具有凝重朴厚的风格,由于刻于金石之上,再加多年的风吹雨打,日晒剥蚀,多沧桑之感,也就形成了书卷所无法代替的美感,正如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原驰蜡象的莽莽苍山,又如罗中立所画《父亲》饱经沧桑的脸,给人以无限的历史遐想,这些感受都不是书卷所能给予的。
二、北碑与南帖差异的文化及审美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文风及书风的巨大差异是这个历史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关于南北民风之不同在《礼记》中就说过: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7]21北方黄河流域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其朴实甚至是彪悍的民风及个性气质直接影响了北朝文化、文学及书法碑刻的审美风格。对南北文学之不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道: “习俗上的关系。南人惊新,北人笃古,所以北学每存两汉之余风,南人则深受魏、晋之影响。承两汉余风者大率质朴,受魏、晋影响者大率清浮。”[8]169北朝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颜之推《颜氏家训》的著作所呈现出的文学风格及语言特征与谢灵运、鲍照、谢朓等为代表的南方诗风也表现了明显的不同,至于以《敕勒歌》《木兰诗》为代表的北方民歌与南方代表性的民歌《西洲曲》《子夜歌》的不同就更为明显,所以《隋书·文学传》说北朝文人 “重乎气质” ,南朝文人 “贵于清绮”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也说 “北朝文人,舍文尚质” ,与郭绍虞的看法基本一致。北朝书法风格上也基本如此。《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郑文公碑》《石门铭》等著名碑刻多法度森严,充分展示了北方文人严整庄重的理性风格。据王壮弘《六朝墓志检要》,北朝书法多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河北一带,这些北魏刻石书法又多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作品,洛阳作为北魏都城,为官僚贵族的聚集地,自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崇尚规整端庄的审美趣味,其平和典雅,方正浑朴的书法风格也与其都城的地位相统一,与其他地区豪放雄奇、古拙奇巧的风格相区别,整体上和南方典雅流畅的书风形成对比。虽然南方也出现过气势雄强、大刀阔斧的作品,如《天发神谶碑》,但总体而言,由于北方特有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及人物性格,仍多苍劲朴茂之作,而南方则多流畅清雅之作。
南北不同的书风除了不同的地域、民风、文化传承,还与不同的书体与不同的书法介质及其不同的功用有着密切的关系,书法的功用、目的与各种工具材料都直接决定了书风的最后形成。不同的字体、书体给人以不同的审美趣味,产生不同的风格。北方多碑榜,少行草,这与北方多宗教宣传的庄严形式相关。如《北史·儒林下》说北周书学家赵文深: “当时碑榜,唯文深、冀俊而已”[9]2751。《北史·文苑》说北周诗人庾信: “群公碑志,多相托焉。唯王褒颇与信垺,自余文人,莫有逮者。”[11]2794说北周诗人王褒: “明帝即位,笃好文学,时襃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11]2792不同的介质对书风的影响也很大,北方多石质碑板,书法家以刀代笔,坚硬的金石经历多年风吹日晒所形成的金石之气,与年久风化点画剥蚀漫漶所产生的虚朦浑朴的自然之美,都与纸张绢帛的书卷之气迥然不同,对书风的最后形成直接产生重要影响。岩石的硬度及攀岩雕刻的难度也同样对雕刻的效果及最后书风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坚硬的岩石很难像在纸张上面书写那样运用自如,自然也很难传达表现纸张上的笔墨韵味。纸上书写的笔迹与石上的雕刻是根本不同的,因为用笔书写的纸张与用刀具刻写的石头质地软硬不同,刀刻石头很难表达毛笔于纸上书写所表现的潇洒流畅的韵致,所以何良俊《四友斋书论》说: “赵集贤学李北海书,未入石者皆咄咄逼真,可谓妙绝,但一入石,便乏古意。”[10]867北朝书法主要表现在摩崖石刻、造像记、碑、墓志、写经等上,特别是墓志盛行,虽不易于雕琢,但却易于保存,能传之久远,而不像手卷墨迹那样,流传下来的多是临摹的作品。北朝摩崖往往字多,体制很大,如《郑曦上下碑》共2000多字,北周《铁山摩崖》也1000多字,甚至每个字幅也很大,有些径达三尺,给人以宏伟的气魄,可谓巨制,特别是《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更是杰出代表。再如,北魏永平四年(511)山东省莱州云峰山摩崖石刻郑道昭题自作诗在云峰山上,《北魏郑道昭论经书诗》用书法的形式来使自己的文学作品传世。《北史·郑羲附道昭传》说其子道昭 “好为诗赋,凡数十篇”[11]1305。其将自己文学作品刻入崖壁,以传后世,实开先河。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分析了南北朝碑的风格之美: “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12]826-827在康有为看来,古今书法只有南碑与魏碑可宗,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有 “十美” :魄力宏大雄强,气象静穆浑厚,笔法跳跃生动,点画峻爽丰厚,姿态奇异飘逸,精神飞扬动人,趣味酣畅淋漓,骨法超迈通达,结构自然天成,血肉丰美。特别是魏碑即使穷乡儿女的造像也是骨血峻健跌宕,拙厚中有一种奇异之态,结字紧实,譬如江汉游女之诗,汉魏儿童的歌谣,含蓄古雅,自有后世士大夫所不能及的。康有为还特别强调了《龙门造像》的书法说: “《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12]836用 “雄峻伟茂” “方笔之极轨” 来表述《龙门造像》书法的刚健雄强之美,可谓推崇之至。当然,书论史上也有南北兼重的。刘熙载就反对阮元、包世臣重北轻南、重碑抑帖的思想,就南帖北碑书风之不同,他在《艺概》中指出: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隶欲精而密’,北碑似之。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讽咏,北如斛律金之《剌勒歌》。”[12]697在刘熙载看来,南帖如篆法重视婉转通畅,北碑如隶法要求精准绵密。北书以骨气胜,南书以韵味胜。南书温雅,北书雄强。南书如袁宏在牛渚讽咏诗篇,北书如斛律金草原的《剌勒歌》,各有特点,各有千秋。
三、北碑与南帖流传之差异
随着清朝碑学的兴起,重北碑的风气与书论也就蔚为大观了。清朝阮元《南北书派论》说南北不同书风: “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独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尊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12]630阮元从南北派不同的地域、风格、书体、书家甚至时间论述了南北不同的书风特点,同时指出,唐太宗在南帖北碑发展变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王羲之一家独尊地位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南北的不同乃是就大致而言,并非南北书家都是如阮元所说的这种风格,而是一种基本的书风倾向。同时,《北碑南帖论》又论说了碑帖的不同审美特点: “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12]637书写短笺长卷,充分表达潇洒的神情,则帖擅长;界格方严,表达庄严的思想,则碑更有优势。包世臣《艺舟双楫》说南北朝不同碑的不同特点: “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 “南朝遗迹,唯《鹤铭》、《石阙》二种,萧散骏逸,殊途同归。” “《书评》谓太傅茂密,右军雄强。雄则生气勃发,故能茂;强则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强也。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李仲璇》《敬显俊》别成一种,与右军致相近,在永师《千文》之右,或出卫瓘而无可证验。”[12]651-652在包世臣看来,北碑书体多旁出,唯独《郑文公碑》端严,篆书的体势、分书的韵致、草书的情趣无不具备。南朝的遗迹,唯有《鹤铭》《石阙》萧洒骏逸,书体不同,给人以相同的美。《书评》说钟繇茂密,王羲之雄强。雄强就生气勃发,所以能茂盛;宏大就神完气足,故能密。北朝的书法也是各种风格并存,有出自《乙瑛碑》颇具云鹤海鸥翱翔之美的,有出自《孔羡碑》,颇具龙威虎震雄风的,同时也有与右军风格相近的。包世臣指出了碑所特有的端严茂密雄强之气,虽然具体各碑也是风格各异。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则分析了书法史上为何一段时间南帖流行而北碑默默无闻: “元常之获盛名,以二王所师。嗣是王、庾品书,皆主南人,未及北派。唐承隋祚,会合南北,本可发挥北宗,而太宗尊尚右军,举世更无异论,故使张、李续品,皆未评及北宗。夫钟、卫北流,崔、江宏绪,孝文好学,隶草弥工,家擅银钩,人工虿尾。史传之名家斯著,碑版之轨迹可寻,较之南士,夫岂多让!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臮《述书》,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述书》所称,皆亲见笔迹:晋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齐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陈二十一人。而北朝数百年,崔、卢之后,工书者多,绝无一纸流传,唯有赵文深兄弟,附见陈人而已,岂北士之笔迹尽湮耶!得无秘阁所藏,用太宗之意,摈北人而不取邪?”[12]802-803在康有为看来,钟繇之所以有名就在于他是二王的老师。此后王僧虔、庾肩吾论书,都注重南方人,没涉及北派。唐承接隋本应该发挥北派,但太宗尊崇王羲之,举世没有异议,张怀瓘、李嗣真评论书法也都没涉及北宗。在北方流传的钟繇、卫觊、崔悦、江式、孝文帝等人的书法,大都刚健有力,史家的著书与碑板遗迹中都能看到,和南朝的书法相比,并无逊色!但是书家评论,竟无一个流传,窦臮的《述书》记载也很少,这样对待古人,显然是不公正的。《述书》所论述的都是晋、宋、齐、梁、陈人,北朝数百年间善长书法的很多,但无一纸流传,只有赵文深兄弟,还附在陈人后面,这明显是太宗摈弃北派的表现。
在中国书论史上,对南北书风有着不同的评价,有重南帖书风的,有重北碑书风的,也有南北书风并重的。唐朝统治者无论从血缘还是文化传统上均来自北方文化,但为了建立更为广泛的统治基础与更加多元的文化,便扩大对江南文化的吸收与宣扬,这在李世民偏好王羲之书风上得到了明确的表现,同时承继王氏书风的书家也受到了更加重要的关注。欧阳询笔力险峻,实为北碑书风的延续,就不受太宗赏识,他赏识的是大王书风的承继者温柔适中的虞世南,正如张怀瓘《书断》中说欧阳询书: “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 “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10]192虽然欧书持中谨慎,法度森严,如他在《八诀》里所提倡 “不须怒降为奇。四面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12]98。《传授诀》也说: “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攲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即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12]105。但欧阳询险劲刚直重骨力的北方书风和虞世南温柔雅致有妩媚之气的南方书风的对比还是很明显的。苏东坡《东坡集·论唐氏六家集》说欧阳询字 “妍紧拔群”[13]54。朱长文《续书断》卷上《妙品》说欧书 “戈戟森列” , “有正人执法,面折廷讼之风”[12]329。洪耀南说: “欧阳询的北方书风及重立法的书论与虞世南的二王书风及强调意的书论,或不无政治之意涵,但更可能是书家性情涵养及精神理念之所致,然而亦难排除所有的政治因素之影响。李世民的书论则显然具有较浓的政治意图,他又亲赞王羲之和陆机传,这与他的皇帝身份应该颇有关联。又其在书法方面崇羲抑献,固然有融合南北的政治诉求,但亦不无建立‘清绮’与‘气质’并重的文艺审美标准的意图。”[14]344后世崇王书风的流行,反对北方质朴之气的书论一再出现,崇尚晋韵的杨慎在《墨池琐录》说: “北方多朴而有隶体,无晋逸,谓之毡裘气。盖骨格者,书法之祖也;态度者,书法之余也。毡裘之喻,谓少态度耳。”[9]801在杨慎看来,北方多质朴之气,缺乏晋朝书风的潇洒韵致。随着明朝以二王为师的古典派进入末流,清朝出现了碑学与篆隶的复兴,浓郁的金石之气与朴拙烂漫的民间书风融为一体,使很多艺术家出现了融金石气与书卷气为一体,二者兼美的书法风格。
四、结语
北碑与南帖不同的审美趣味表现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巨大差异。北碑大多是民间书法,多具自由大胆、天然率真、随势变化的风格,其古拙浪漫的气质对突破传统的僵化模式,如对清代碑学的兴盛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康有为对北碑审美特点的论述与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对民间文化特点的论述是相通的,魏晋南北朝上层精英的喜好与普通民众的喜好,文人雅士与乡野村夫的趣味自然不同,他们对书法的判断也迥然有异。魏晋南北朝碑刻的书写者大都是处理文书的普通小吏,且多不署名,即使很多著名碑刻署名者,如《孙秋生造像记》之萧显庆、《始平公造像记》之朱义章、《石门铭》之王远等,也多史无记载。这些优秀的民间艺术家,其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及审美趣味自然也与那些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华美妩媚的风格根本不同。他们饱尝风吹日晒,在文人雅士游山玩水之际,用汗水与艰辛雕琢了一件件完美的艺术品。这种艰苦的劳动是那些生活优裕身体柔软无力的达官贵人所无法承担的,同时这些不囿于成见的无名书法家又往往具有无限的创新魄力,其生动自然、不拘一格的鲜活精神也是那些生活在沉闷死板的宫廷之中的文人雅士所不及,因此魏碑造像的宏大有力、舒展刚强的风格是在那些文人雅士艺术家中所根本没有的,也无法企及的。魏晋造像碑刻保留的这些大量民间艺术家的伟大成就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坚忍不拔的气概。
——晚清以降颜氏书风在湖南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