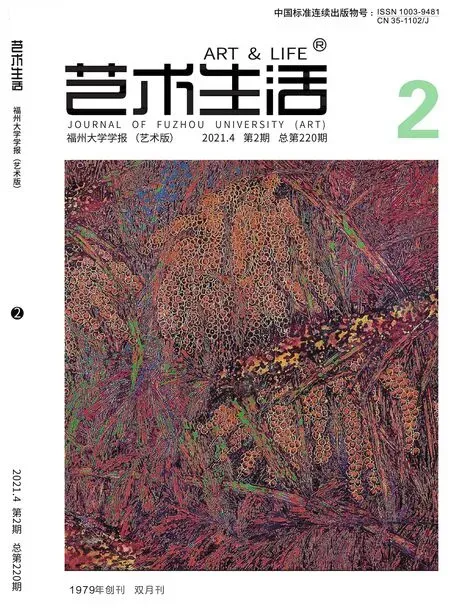传统刺绣作为艺术的本源探究与历史嬗变
邓茗予
(江西服装学院 时尚传媒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刺绣作为一门传统手工技艺,其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历史久远且发展无中断,这使刺绣得以拥有丰厚的历史积淀和与之对应的物质基础。《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载: “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五采,备谓之绣。”[1]说明远在商周时期,刺绣便已经和绘画一同成为服装装饰的重要手段。但纵观刺绣发展史,除去考古出土的刺绣实物之外,文献典籍中对于刺绣的记载凤毛麟角,没有专门记录刺绣技艺和纹样的书籍,即便是在提及刺绣相关的文字中也仅仅是一笔带过,这种现象直到清代才有所改观,丁佩《绣谱》以及由张骞代笔、沈寿口述的《雪宧绣谱》成为传统刺绣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两本工艺专书。而在刺绣相关记载稀少的同时则是刺绣品之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此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为何会 “偏科发展” ,重技艺而轻理论,这是笔者之于刺绣作为一门艺术的疑惑与思考。诚然,刺绣更加偏重技能性,这是其自身特性所决定的,是符合刺绣工艺不断发展繁荣的客观规律。但与此同时,刺绣作为一项成熟的艺术门类,其所包含的精神性和物质性理应同等重要,精神与物质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共同促进才能更好发展。如果仅仅重视技法,对于形式过分倚重,那所表达的内容在精神层面上将会大打折扣,甚至受到形式的支配而丧失其本性。因此,对于刺绣的艺术价值探索便显得很有必要。探究刺绣纹样背后的时代文化、探寻刺绣技法对于中国艺术理念的继承与创新、探索刺绣作品所产生的美学趣味等对传统刺绣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至此,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与分析,以期能够得到一个较为合理与客观的答案。
一、原生的物质特征
刺绣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性所致。远古人类用骨质(石质)的针将兽皮、草叶等物串缝起来用以御寒和保护身体,其上所留下的 “针的纫迹” 便是刺绣的雏形。在骨针发明之初,主要用做缝纫的是由兽筋、草叶所搓成的粗线,随着纺织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形态更为细腻、色彩更加斑斓的麻线、棉线、丝线等开始出现并用于刺绣[2]。自此,刺绣艺术的物质条件方才完备,刺绣开始跟随社会的需求而不断改变,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刺绣逐渐脱离缝纫技术而主要用做服饰等日常用品的装饰与加固。在《尚书·益稷》中有舜和禹的对话: “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1]这里所记载的被称为 “十二章纹” 的刺绣纹样便已经明显用于装饰衣物和彰显穿着者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缀缝衣物之用,这也是刺绣开始拥有艺术内涵的先潜之机。刺绣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缝纫技术与纺织技术,针、线和布是刺绣物质性的体现。众所周知,刺绣艺术的主要载体是绣于各种材质面料上的丝线,在一幅刺绣作品中,线段的运动态势、组合手法和色彩搭配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其中,点作为线的起始与收尾是组成线的基本要素,而绣品幅面的构成是无数线纵横交错而来,这是线在运动中表现绣品的体量感和立体感的必然结果。点是组成绣品样貌的基础手段,面是体现绣品最终效果的视觉呈现,点与面均是绣品构成的重要元素,但作为承上启下的线则是点延展为面的关键所在,而绣品幅面的具化和质变也同样无法离开线的轨迹运动[3]。因此,线在刺绣艺术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各种刺绣针法的发展与创新均适用于绣品的线性表现,这也从实用角度证明了线段对于刺绣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在绣制纹样的过程中,丝线的长短、粗细,其倾斜的角度、色彩的变换、针法的勾连等都影响着最终效果的呈现。比如,垂直线条接针而成的树木与截针倾斜而来的树木就明显有树龄的长幼之分;小树初长成,笔直的躯干蓬勃可爱,而擎天的老树盘根错节,不规则的枝干便是岁月雕琢的痕迹。当欣赏一幅刺绣作品时,跟随光影变化,观赏者能够感知到作品之上线的走势和律动,有的线富有盘旋之美、有的线则注重放射之感、有的则更加倾向于错落交替,以形成一种立体的视觉效果。这些变化均是透过组成画面的线而来,线不仅形成了纹样,更将纹样所蕴涵的精神意蕴表现出来,其复杂而又精致的律动是刺绣艺术最为独特的展现[4]。
刺绣起源不同于绘画、音乐和舞蹈等,这些典型的艺术门类往往是伴随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而演变的。其天然蕴涵强大的精神性和审美规则,刺绣艺术则更贴近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发展,其天然的物质优势引导着刺绣发展之路,同时也 “阻碍” 刺绣向艺术、向精神领域的探寻。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不论是皇族贵胄、还是布衣百姓,大家对于刺绣品的需求始终迫切且不胜其多,对于人们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天子之家专用的刺绣纹样是等级划分的依据,婚礼之上的织绣嫁衣是人生大事的指示物,高悬于庙宇之内的佛陀绣像是通往彼岸世界的精神依托等。但这些暗含丰富精神意味的刺绣品被具体实际的物质用途所归类,在成为生活一部分的同时,也局限了其精神性的发挥与创造。
刺绣艺术高度依赖其物质性,这是刺绣的本源。相比于绘画艺术创作材料的广泛性,刺绣艺术的物质创作条件非常狭窄。比如,西方的油画创作多使用帆布和油性颜料,而我国传统的山水画则偏爱宣纸和水性颜料的使用。如果从宏观看待绘画艺术,只有用能够着色的物质在另一物质载体上体现出绘画的构图、线条、色彩、审美观念、精神追求等便都可归入绘画的范畴,因此则诞生了远古的洞穴岩画、各具特色的绘画流派,以及遍及世界的现代涂鸦。而刺绣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始终使用针、线和布匹来进行刺绣品的创作,不论时间、地域、民族、流派等如何变化,刺绣品总是以针在布上留下的线迹作为其物质表现手段,这种基于专一物质媒介的特性将刺绣艺术的创作规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其丰富多变的精神内涵必须通过 “线迹” 这一物质条件而展现,毋庸置疑,这要摒弃一些不适合以针、线和布匹来诠释的内容,但也正因如此,刺绣艺术的精神性通过物质性的有效筛选而变得更加专精,更能凸显刺绣本质的独特韵味。
二、以女性为主的群体特征
众所周知,刺绣隶属女红范畴,是主要由女性掌握、制作和传承的一门手工艺。刺绣肇始并没有从业性别与身份的明确划分,但是由于男性与女性生理条件的天然差异,身强力壮的男性需要从事狩猎、耕种等体力消耗巨大的工作;而身手灵巧、心思细腻的女性便承担起纺织、炊饮等更具技巧性的工作。古语有 “妇无公事,休其蚕织” “匹妇蚕之、匹夫耕之” 等记载,这种原始朴素的社会分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细化,逐渐形成了 “男耕女织” 的、以性别为依据的社会分工体系。刺绣制作依托于针、线和布匹,且以室内工作为主,刺绣工艺丰富繁琐,需要耐心、细心等精神品质,这些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刺绣艺术的性别归属,女性自然成为刺绣的主要创作者与传承者。
关于刺绣群体的身份定位亦是基于性别归属而逐步制度化与明确化的。家庭式的刺绣生产结构长期存在于刺绣历史当中,并以之为主体,其中家庭中各类女性角色是刺绣生产的主要劳动者,刺绣品也以供应家庭所需为主,次之以赠送亲友、礼尚往来之用。刺绣技艺的传承主要通过家庭中女性成员的互相学习和交流而来,这种基于 “闺阁” 的传承手段在赋予刺绣鲜明地域性和神秘感的同时,也局限了刺绣向着艺术层面深入发展的道路,丰富多样但凝聚力欠佳的刺绣工艺于不同地域、多样民族和个体鲜明的家庭中隐秘流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刺绣相关的理论化和艺术化。明清时期,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萌芽,工厂式的刺绣生产模式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这种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大致始于汉代的 “织室” ,《汉书·匈奴传》中记载:汉孝文帝六年,赠匈奴 “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5]。这种专供皇家的织室有织工上千人,生产的锦缎绣品数以万计,并主要用于贵族的生活所需和馈赠之礼。随后,唐代的 “织造局” 、宋代的 “文绣院” 等不断开拓刺绣生产的集约化局面,官造和民办两大刺绣生产系统在各自的社会体系内不断扩容,直至明清两代达到了顶峰。《明史·食货志》中记: “明制,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6]此外,明代皇陵中大量出土丝织物,其中以有织绣纹样的服饰和配饰为主,这从侧面反映了官办织造业的繁荣,而同时期的民间织造业也更多地进行商品化生产。清代时期江宁、苏州与杭州三大织造局的设立可以佐证,民间刺绣业亦随着愈发频繁的中西方交流而不断繁盛,织绣品成为中国出口海外的重要商品之一。但不论是家庭式的还是工厂式的生产模式,其刺绣创作人员依旧承袭传统,以女性为主。不断充实和拓展传统刺绣的发展脉络,逐渐形成了 “苏绣” “湘绣” “粤绣” “蜀绣” 等各具特色的刺绣流派和以 “汴绣” “京绣” “杭绣” 为代表的宫廷刺绣。
从以上分析可知,刺绣群体的身份定位一别有二,其一是家庭中的女性角色,这些女性往往附属于男性,继而使得归为女红的刺绣艺术同女性一样被深深锁入礼法等级的桎梏之内,不能有效发展;其二是专门机构中的女工,她们是专司绣案的女官,虽然脱离了家庭的束缚,却成为了织局的 “劳工” 。刺绣因天生的物质性与生活必需性被划分为 “技” ,隶属工匠匠艺范畴,织局需要量产以供应巨大的需求,刺绣的艺术性被需求模式化,刺绣的自由属性被遏制,各种纹样被法度规定,各种配色有严苛的等级划分。因此,刺绣被放置在 “技艺” 的范围而不断远离所谓的 “艺术之路” ,这是刺绣群体在特殊时期的特殊社会地位所致,亦是历史上对于刺绣群体的认识局限所致。但也可看到,自清代已来,刺绣这项历久弥新的古老手工艺开始进入艺术审美的视野。《绣谱》成为传统刺绣史上第一部有关刺绣工艺和刺绣心得的著作,其作者丁佩也是第一位主动关注刺绣理论记述和探索的工艺美术大师。随后的沈寿又以《雪宧绣谱》蜚声海内外。这说明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刺绣的艺术会被不断开拓与发展。
三、实用与审美的辩证置换特征
刺绣附着于人类的日常用品之上,起到加固、装饰的作用,从刺绣的发展历史看,实用性始终是刺绣品的基础属性,也是刺绣艺术能够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键要素之一。刺绣品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各种具体的功能和功用,大到封建社会时期明示身份等级的皇家刺绣纹样,小到为孩童趋吉避凶的彩绣虎头鞋、虎头帽等,这些富含精神意味的刺绣品与人类的各色活动息息相关。将刺绣与纺织、浆染、缝纫等门类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刺绣的创作过程更为自由和主观,而纺织、浆染、缝制等工艺门类,由于制造工具的机械化和生产需求,很多创造性的制作工艺和制作想法无法很好施用和大规模推广。刺绣艺术也正是因其自身的随意性和流动性而拥有更加广阔和辽远的创作空间和艺术内涵,虽然刺绣技法有着与生俱来的程式化和模式性,但在这有限的范围之内,施绣者可以发挥无限的创造力和创新性,刺绣艺术需要 “界限” 来创造自由,在有限的空间中发挥无限的想象力,施绣者在传承刺绣传统纹样寓意和工艺技法的同时,必定将个人的情感、思想、艺术感悟等融入所绣制的作品之中。即使同一位绣者绣制同一题材式样的作品,但在不同的时空、情绪和生活境遇下,其所倾注于绣品之上的 “功夫” 必定有所不同,而便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刺绣作品。
但在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对于刺绣艺术而言,一面是实际生活中对刺绣品的庞大需求,一面是有关刺绣艺术系统梳理和理论著述的缺失。前文提及的清末刺绣大师沈寿所著的《雪宧绣谱》,其成书初始也并不是沈寿大师的主观为之,而是实业家张骞感念中国刺绣工艺专书历史的空白,遂在沈寿大师晚年请求其口述多年来积攒的刺绣技法与心得以为著书之用,张骞在《雪宧绣谱》的叙中写道 “寿有独立自足以传之之艺,故从金石书妇女特例”[7],这充分肯定了沈寿作为一代刺绣大师的卓绝贡献,但我们从此例中亦可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施绣者本身也一般不注重刺绣艺术的理论发展,她们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刺绣作品的实际创作和刺绣技法的改良之中,心得体悟满满,却只存于心间与言传身教之中。此类现象在传统刺绣的发展历史之中并不是特例,而是惯常现象。人们对于刺绣艺术的成果往往给予高度评价,这是基于对刺绣品视觉感受的功能性评价,是依旧侧重于刺绣实际展示结果的肯定,其中所蕴涵的深层精神内容则很少触及,比如前文所举划分等级的皇家服饰,儿童所穿的虎头鞋、虎头帽等。人们关注的虽然是刺绣纹样本身,但我们却将这些刺绣品归入 “服饰类” 和 “鞋帽类” ,刺绣品的主体性被具体的物质类别划分所打破,成为了各种实用品的视觉要素之一。我们发现,对于刺绣品的艺术性欣赏往往带有先天的功利主义,其实是用特性分散了欣赏者的部分注意力,从而导致对刺绣品的艺术性欣赏不纯粹,对其精神层面的研究不深入。
但兴于宋、承于明清的绣画则是刺绣艺术实用性与审美性辩证置换的有力实证。 “绣画” 一词多指以针代笔的刺绣作品,即用刺绣技法来表现绘画之境,追求 “如画” 之感,强调刺绣品的 “画意” 。宋代经济繁荣、文化兴盛,书画艺术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上至皇家、下至乡野,习书作画之风蔚然,社会的总体艺术氛围由书画艺术引导,刺绣亦不例外,绣画的出现是应时之机,更是将刺绣欣赏品从日用品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 “绣画鉴赏体系” 。明代张应文在其所著的《清秘藏》中写道: “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巉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生态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8]绣画运用书画的笔墨意趣来构造视觉图式,又因其丝线独特的色泽和细腻程度使画面呈现更加丰满通神,比之于画更胜一筹,比之于绣又更具神采。绣画最大程度上摒弃了刺绣作品的实用性,同时又借助书画意境将自身的审美性极致提高,形成 “如画” 之感。绣画的出现是刺绣历史上的重大突破,是第一次将刺绣技艺提升至艺术高度的创举,虽然是借助了书画艺术作为羽翼,但绣出来的 “画” 毕竟和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作品有本质不同,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精神追求承袭传统刺绣内涵,又创造性地呈现出新的面貌,是刺绣艺术发展中一次可贵的尝试。
四、结语
自古至今,无论是宫廷出身的职业绣娘,还是民间的刺绣能手,均以刺绣实践为重,对于技法程式性继承,创新创造也更加偏重刺绣实用功能的发挥。毋庸置疑,这对于刺绣技法的不断发展和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深藏于刺绣技法与刺绣品背后的艺术趣味和哲学思考则鲜有人知,刺绣纹样强烈的装饰性与刺绣内涵稳定的模式化很少能涉及刺绣艺术的精神根源,比如刺绣品所包含的美学意图为何、其所传达的深层文化内涵为何、其所沉淀的历史脉络又为何,这些看似已经潜移默化深入至刺绣艺术本身的诸多美学意境需要更为全面、更加精细、更能凸显刺绣艺术独特性的梳理研究和分析探索来诠释与注解。对于传统刺绣艺术的理论研究需要更为系统、立体,这是刺绣艺术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其审美性的不断延展为刺绣成为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刺绣品中繁杂的纹样、绚丽的色彩、精良的质材等均是为了表现 “美的追求” 而诞生的,传统刺绣艺术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历经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也使其拥有丰富的美学内涵与精神气质。当前社会,传统刺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但传统刺绣的诸多实用功能已经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消散而消弭,当代人更加关注的是刺绣作为艺术的装饰性和欣赏性,是更加具有创造性的 “刺绣精神” 。因此,对于传统刺绣的新发展与新气象,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溯源求新,更应该遵循刺绣艺术的自身发展规律进行改革,使其能够更加适应社会的演变,从而在历久弥新、去粗取精之中得到更为完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