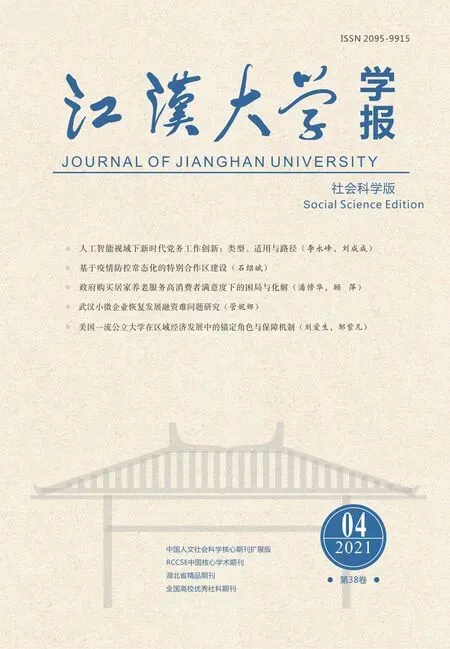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行为人有无救助义务
魏汉涛,向 梅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我国刑法理论将不作为犯区分为真正的不作为犯和不真正的不作为犯,真正的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因而在作为义务的认定方面并无较大争议。不真正的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由于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真正的不作为犯中作为义务的来源无论是最初的“三分说”,还是现在的“四分说”,先行行为一直被认为是产生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先行行为能够产生作为义务已成共识。然而,先行行为的范围理论上仍存争议,尤其是犯罪行为能否成为先行行为理论上分歧较大。理论上的分歧演绎到司法实践,导致相似的情形判决结果大相径庭。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行为人有无救助义务的确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因为如果否定存在作为义务,结局可能是一罪;如果肯定存在作为义务,结局可能是数罪。因之,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些有益的探索,希冀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实践中的分歧和理论上的纷争
犯罪行为引发的危险行为人是否有救助义务令不少学者纠结,让不少司法工作者困惑,理论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实践中出现了相异的判决。
(一)实践中的分歧
“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当遇到犯罪行为引发的危险行为人是否有救助义务的案件时,司法工作者无法回避,只能做出选择。从司法判例来看,不同司法工作者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让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案例一:2011年6月26日晚,韦风驾驶摩托车在无锡市崇安区广勤中学附近看到被害人李某(女,殁年17岁)独行,即上前搭讪,后将被害人李某强行带至无锡市通江大道安福桥南岸桥洞下斜坡处,采用语言威胁、拳打、卡喉咙等暴力手段欲对李某实施强奸,因遭到李某反抗而未果。被害人李某在反抗过程中滑落河中,被告人韦风看到李某在水中挣扎,明知其不会游泳,处于危险状态,而不履行救助义务,并逃离现场,最终李某因溺水死亡。①
案例二:2018年9月某日,被告人李某让其同事田某代其买回一盒粉饼。当李某向田某要该盒粉饼时田某不给,因此发生争执并发展为厮打。李某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把水果刀朝田某左后腰部捅了一刀,然后向门外跑去,田某手捂腰部在后边追赶,追至大门口倒地。李某发现田某倒地后返回查看,发现田某不能动弹,于是站在不远处观看田某约10分钟后,再次返回田某身边,发现田某伤势严重后慌忙骑车逃跑,田某后因伤势过重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②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犯罪行为导致他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因没有及时得到救助,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例子。第一个案例如何定性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有两个行为,一个是强奸行为(未遂),另一个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行为,应当按两罪实行数罪并罚。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没有杀人故意,不应再单独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所以只应定强奸罪,被害人死亡应当作为强奸罪的量刑情节考虑。最终法院采纳了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韦风对强奸行为导致被害人处于危险状态有救助义务,按强奸罪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实施数罪并罚。第二个案例如何定性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虽然李某最初只有伤害其同事的故意,但在明知自己的先前行为致其同事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就有义务也有能力采取救助措施,但行为人没有实施相应的抢救行为,应转化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还有人认为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因为行为人没有杀人的故意,对死亡结果持不希望的态度,行为人对自己的故意伤害行为引起的危险没有救助义务。最后法院支持了第二种观点,判决李某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
这两个案例均为先前的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处于危险状态后不予救助,最终被害人因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但两个案例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明显差异。第一个判决认为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危险有救助义务,因而不仅要按前行为构成的犯罪处理,而且要对后面的不救助行为另外评价,所以要数罪并罚。第二个判决认为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危险没有救助义务,所以只应按前面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定性,不实行数罪并罚。这两个判决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犯罪行为导致的危险行为人是否有救助义务,如果有救助义务,则要评价两个行为,构成数罪;如果没有救助义务,则只需对先前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定性。
(二)理论上的分歧
犯罪行为导致的危险,如果否定行为人存在作为义务,则与更轻的违法行为可以产生作为义务不相协调;如果肯定行为人存在作为义务,又容易导致罪名的认定及罪数计算上的困难。正因为这方面的困惑,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否定说、肯定说和区分说。
否定说认为,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可以是合法行为,也可以是一般违法行为,但不应包括犯罪行为。如果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会使绝大多数一罪变为数罪。[1]支持否定说的理由有二:一是没有期待可能性,法律不能期待犯罪人去救助自己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因为危害结果很可能是犯罪人所追求的,因而只能按其先前的犯罪行为定罪处罚;二是对后续的不作为进行处罚,可能造成重复评价。否定说可以从历史渊源上找到支撑,早期英美法系国家通常将犯罪限定为作为,原则上不承认没有刑法明文规定的不作为可以构成犯罪。当今,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渐渐接受不作为与作为一样可以成为犯罪,但仍然不承认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行为人有作为义务。[2]
肯定说认为,不应将先行行为局限于违反义务行为,任何人实施行为时都有某种责任感,且不能漠视这种责任感。[3]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是肯定说的支持者,他认为“在先行行为是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先行行为与不作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4]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行人有无作为义务,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一直在修正。早期张明楷教授主张否定说,认为如果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行为人没有作为义务,会不当地使绝大多数一罪变为数罪,对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行为人没有阻止结果发生的,只成立原犯罪行为的结果犯或者原犯罪行为的结果加重犯。[5]后来张教授又转向折衷说,认为应当分情况区别对待。在某种犯罪行为被刑法确立为转化犯或者结果加重犯时,因加重结果已经适用了升格法定刑,行为人就不再另行产生作为义务。而在刑法没有规定结果加重犯或者转化犯的情形下,如果行为人的前一犯罪行为造成另一法益危险,行为人必须对后一法益履行救助义务。[6]在2016年出版的《刑法学》中,张明楷教授彻底转向了肯定说,认为无论过失犯罪还是故意犯罪,都与一般违法行为一样可以成为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7]张明楷教授是我国刑法界公认的知名学者,他的观点一直在修正,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区分说认为,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行为人有无作为义务不能一概而论。有学者通过罪过形式的差异进行区分,认为故意犯罪行为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先行行为,过失犯罪行为可以成为不作为犯罪的先行行为。[8]还有学者借助客观归责理论进行区分,认为应当将客观归责理论用于不作为犯罪领域,进而演绎出合法驾驶行为、生产销售产品行为引起的危险行为没有救助义务,但故意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行为人有救助义务。[3]
二、犯罪行为原则上属于不作为犯罪之先行行为
犯罪行为导致的危险是否能够产生作为义务,会严重影响到行为人最终的定罪量刑以及罪数问题,因而这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在我们看来,不能完全否定犯罪行为引发的危险行为人有作为义务,否则很多案件将得出不接地气的结论。
(一)从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看犯罪行为
19世纪初,费尔巴哈在康德法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形式的法律义务理论”,由此产生了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这一理念。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最初是“三分说”:(1)法律上的规定;(2)职务或业务上的规定;(3)先行行为。[9]随后发展成为“四分说”,即在三分说的基础上增加了法律行为。无论是原来的“三分说”还是后来的“四分说”,都对先行行为能够产生作为义务予以肯定。
先行行为最早由德国法学家斯特贝尔提出,该理念的提出立基于生活的实际感觉与明白的法感情。[10]换言之,当一个行为使法益处于危险状态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正义法律情感,从保护法益出发,行为人就有义务消除自己先行行为引起的危险。关于何谓先行行为,不同学者的认识有所差异。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所谓先行行为,是先行于成为问题的侵害法益的行为。”[11]张明楷教授则认为:“由于行为人的某种行为而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排除危险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积极义务。”[5]133仅从先行行为的涵义并不能明晰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之本质,就形式的四种作为义务来源而言,王莹教授认为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较其他三种来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质。该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先行行为的危险具有偶然性,应当在否定原有“准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上从先行行为中寻找真正的因果关系,其主张“先行行为必须与风险的实现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先行行为必须创设了结果发生的危险。惟有如此,先行行为人才负担使这种风险降低的义务”。[12]
根据我国主流观点,先行行为包含合法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诸如将路边重伤的老人抬到车上的合法行为,就产生了救助义务,理由是其救助行为阻断了受害者被他人救助的可能,只能依赖于救助人。从这个角度考虑,合法的救助行为在使被害人得到救助的同时,又增加了一定的风险。对于一般违法行为,如故意殴打他人(未致轻伤),虽未达到犯罪程度,但给他人的法益造成了一定的危险,由此产生作为义务。由此可见,合法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之所以能够作为先行行为都是以“产生一定危险”为前提。此外,我国主流观点认为,先行行为只要足以产生某种危险就可以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无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11]245周光权教授提出:“先行行为本身性质关键不在于其合法还是违法,而在于产生的结果是否超出了合理范围而增加了行为之外的危险,因而要求行为人对其加以防止。”[13]换言之,成为先行行为的关键在于是否对法益产生危险,就形式的作为义务层面而言,能够产生法益危险即可成为先行行为。按照此种观点,犯罪行为本身就是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则必然会产生作为义务。这一论述也得到了陈兴良等教授的赞同,他们认为对于过失犯罪,“只要某一结果是包含在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之内,则该过失犯罪不能转化为同一行为的故意犯罪。除非这一结果是超出某一过失犯罪的,该过失行为才有可能成为不作为的先行行为”。[14]陈兴良教授虽然对过失犯罪作为先行行为的范围作出一定的限制,但同时也肯定了过失犯罪可以作为先行行为。孙运梁博士通过客观归责理论对先行行为进行限定的同时,也确认了故意犯罪可以成为先行行为。再者,如果只承认合法行为能够产生作为义务而否认犯罪行为,在理论和实践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例如,甲故意伤害乙,导致乙重伤血流不止,明知不将乙送入医院治疗会导致其死亡,仍然逃离现场(地点人流量较多)。路过的丙看到,将乙抬上车后发现其受伤严重,害怕受其连累,又将乙放在半路,由于路径偏僻,乙没有得到救助死亡。如果否认犯罪行为能够产生作为义务,则实施合法行为的丙承担乙死亡的责任,而故意伤害的甲反而没有责任,这一结论显然不公平。因此,基于“产生一定危险”理念和公平理念的考量,应当将犯罪行为纳入先行行为之内,成为作为义务产生的根据。
(二)从作为义务的实质来源看犯罪行为
由于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过于笼统,导致过多的行为被纳入了作为义务的范围。于是,理论界开始转向从实质层面探究作为义务的来源,试图揭示作为义务的实质。当前,学界对作为义务的实质也存在分歧,出现了诸如“控制支配说”“事实上的承担说”等学说,但其中“功能二分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即将实质的作为义务区分为对特定法益的保护和对危险源的控制监督义务。[15]
1.对特定法益的保护
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法益,无论是对作为形式义务的讨论还是对实质义务的探究都是如此。将犯罪行为纳入作为义务来源之中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犯罪行为产生的不作为犯的构造可能描述为:先前的犯罪行为→制造、增加法益危险→不作为→发生危害结果。很明显,产生作为义务的犯罪行为必定以犯罪行为制造或增加了法益危险为前提,当犯罪行为没有制造、增加法益危险时,当然不产生作为义务。
在先前的犯罪行为制造、增加了法益危险的情况下,大多是先前的犯罪行为与后面的不作为分别侵害了不同的法益。例如,甲违反国家规定捕猎珍贵野生动物金丝猴,在用枪射击金丝猴的同时打到另一捕猎者乙,致乙重伤,明知不立即救助会致乙死亡,但仍故意不予救助致其死亡。此种情况下,甲先前的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为国家对珍贵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度,后续的不作为犯罪侵害的法益为他人的生命权,正是先前捕猎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导致了他人生命权被侵害的危险。此时,应当承认犯罪行为能够产生作为义务,否则将会导致后者的生命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与保护法益的初衷不符。
先前的犯罪行为制造、增加了法益危险,也存在于先前的犯罪行为与其后的不作为侵害了相同法益的情况。例如,甲想要杀害乙,捅乙数刀后任由其死亡不管。此种情况下我们不认为有作为义务,只评价前面的杀人行为即可,而不评价其后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反对犯罪行为能够产生作为义务的学者大多认为此种情况下再评价后面的不作为会导致重复评价,加重犯罪人的责任。然而,并不是所有侵害同一种法益的情况都会导致重复评价。例如,仓库管理员张三不小心将打火机掉落在地上,引起小爆炸,随后引起周边杂物燃烧。此时只要张三及时打电话告之单位的相关部门,或者召集邻近部门的工作人员前来帮助灭火,就完全可以扑灭。然而,张三为了逃避责任偷偷从仓库溜出,意图制造自己不在现场的假象,最终导致整个仓库被烧毁。在这个案件中,张三的前行为至多构成失火罪,但他对自己过失引起的危险没有采取积极救助措施,造成严重后果,此时就不能再评价为失火罪,而应该根据不作为犯罪理论评价为不作为的放火罪。由此可知,即使前犯罪行为导致的危险与后续的不作为危及同一法益,从保护法益的目的出发,有时也要求行为人履行救助义务,对犯罪行为引发的后续不作为进行评价。
2.对危险源的控制监督义务
我国刑法理论将对危险源的控制监督义务划分为三种:对危险物的管理义务、对他人危险行为的监督义务、对自己先行行为的监管。[16]耶塞克以及日本学者山中敬一等也作出了类似的分类,认为对危险源的监督义务包括:因危险的先前行为产生了对他人危险的情形、存在于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危险源、对受其监督之人的行为进行监督的义务。[17]由此可见在作为义务实质来源的主流观点中也包含着对先行行为的认定,只是实质作为义务来源中的先行行为要比其在形式作为义务中的限制更为严格。根据周光权等教授的观点,在实质的作为义务来源中,先行行为不仅应当使他人陷入危险,还应当具有义务违反性。但该种限制也仅是在先行行为中排除了正当防卫行为以及个别合法行为,而并未对犯罪行为作为先行行为产生影响,犯罪行为在严重危害他人法益的同时,必然具有义务违反性,理应符合实质作为义务来源中的先行行为特征而成为义务来源。另外,在我国的理论分类中无论是危险物、他人的危险行为还是自己的先行行为,能够产生作为义务都是源于其设定了法益危险。具体而言就是自己管理的危险物、他人的危险行为、自己的先行行为使法益陷入危险才会产生作为义务,只是在三种不同情形时承担作为义务的主体分别为监管人、行为人而存在差异,承担义务的理由并无本质不同。由此可见,在危险源的控制监督义务这一实质来源中,“成为了危险源,给法益制造危险”才是产生作为义务的关键,而不应是其后的“控制支配”。不可否认,当行为人对危险源有控制支配能力时,更有利于作为义务的实现,但如果行为人致使他人陷入危险,即使不具有对危险的控制支配能力也应当认为其有作为义务。尽管其最终可能因不具有作为可能性等原因不成立不作为犯罪,但最终是否构罪并非是作为义务层面应当考虑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在行为人制造了危险时,就应当产生作为义务,不以必须对危险源有支配力为前提;基于制造法益危险的考虑,犯罪行为作为危害社会的行为之一,原则上可以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
综上,在形式的作为义务来源中,犯罪行为完全可以归纳到先行行为中,由此认定其可以产生作为义务。在实质的作为义务来源中,无论犯罪行为制造、增加的危险是否危及同一法益,出于保护法益的考虑都应当认为行为人有作为义务。
三、犯罪行为产生作为义务之条件
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因而我们不仅要证明真理存在,而且要进一步探究真理的存在条件。在肯定犯罪行为原则上可以产生作为义务以后,还必须进一步廓清犯罪行为导致的危险在什么条件下行为人才有作为义务。
(一)犯罪行为产生作为义务之条件
从保护法益和防止施加不必要的义务出发,我们认为对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仅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情况下行为人才有作为义务。
1.犯罪行为制造或者增加了重大法益风险
法律之所以设置不真正不作为犯,是因为在某些情形下设置作为义务有益于保护法益。因之,犯罪行为导致的危险要产生作为义务,不可避免地要以制造法益危险为前提。如果犯罪行为并未制造或者增加法益危险,则不会产生作为义务,也就不存在不作为犯罪。[11]154例如,甲想要杀害乙,便邀请乙第二日到家中吃饭,想要投毒将其杀害,甲早早地将有毒的饭菜准备好等待乙,乙在去甲家的途中被车撞成重伤,甲见乙许久没来便去寻找,发现乙在路边重伤,心想“这样死了就和我没关系”,径然离去,最后乙不治而亡。此案中甲先前的故意杀人预备行为并不是导致乙重伤的原因,该行为还未来得及使法益遭受危险,因而甲不会因为其先前的犯罪行为产生救助义务,所以对甲只能评价其先前的杀人预备行为,不能评价其后的见死不救行为。需要说明的是,犯罪行为不仅要制造或者增加法益危险,而且要求危及的必须是重大法益。主要原因是,如果微不足道的法益,即使转化为实害也不会导致重大损害,从刑法谦抑原则出发就不宜上升到刑法范畴,所以不宜科加刑法上的作为义务。
根据这一原理,如果行为人先前的犯罪行为没有制造或者增加危险,危险是由被害人自主决定导致的,先前的犯罪行为不产生作为义务。[5]154以德国的海洛因注射案为例,甲作为一个常年吸毒的人,委托乙购买器具供二人注射毒品,注射毒品后,甲又独自吸食大量毒品,最终因吸毒过量而死。虽然乙先前购买注射器具的行为使甲的法益遭受一定的危险,但作为一个有吸毒经验的人,甲应当有足够的经验知道过量毒品的危险,因而甲的行为属于自陷风险,乙对此没有救助义务。
2.法益遭受的风险具有作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法益遭受的风险具有紧迫性,是指如果不积极加以防止,就会立即转化为实害。例如,撞人之后不积极救治,受害人就会死亡;失火后不积极灭火,就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一般而言,紧迫性与必要性密切相关,而且通常保持一致,[18]当危险迫在眉睫时就必然具有作为的必要性。然而,不紧迫并不意味着一定不必要,在某些情况下法益遭受侵害的危险虽然不紧迫,但一旦转化为现实,就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这种情况下也应当认为危险具有救助的必要性,应当要求行为人对自己引起的危险具有作为义务,以便促使其积极阻止危险转化为实害。例如,甲想要杀乙,便给乙准备了一杯有毒药的水,毒药七天后才会发作致死,但碰巧丙口渴难耐先将有毒的水喝下。甲的犯罪行为使丙的生命权遭受风险,毒药需要七天才会发作,此时风险虽不具有紧迫性,但甲也因其先前的投毒行为产生救助义务。此种情况下,如果只要求法益侵害具有紧迫性才有救助义务,必然出现不公平的结论。
3.能够期待行为人积极作为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仅在有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法律才能期待行为人履行作为义务。“为了防止结果发生的作为必须是具体的、可能的(作为可能性),因为法律不可能给不能履行义务的人赋予义务”。[19]法律制度要贴近生活,理论研究要亲近人性,脱离生活的法律注定会成为空中楼阁,背离人性的理论必然会被抛弃。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问题,就是要求相关人员在特定情形下实施一定的行为,以便挽救法益。如果在没有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法律仍然要求行为人去救助法益,表面上看有利于救助法益,实质上不仅无助于救助法益,反而会让民众认定法律是恶法,不利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就像是对于溺水的人,一般情况下行为人有救助义务,但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就不具有救助义务。[20]如果是行为人的过失犯罪导致被害人落入水中,即使行为人不会游泳,如果法律仍然要求行为人积极救助,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行为人也可能跳入水中施救,结果不仅先落水的人得不到救助,反而又增加一条人命,相信这样的结局任何人都不会接受。
(二)作为义务相关问题解说
虽然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研究重点正在从作为义务转向支配可能性,“尽管学者们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分析方法各异,但大体上呈现出一个走向,即从不履行作为义务的‘不作为’向支配、控制、引起侵害法益结果的客观事实转化,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学说印象,即作为是引起因果流程,不作为是放任因果流程”。[21]于是,有人将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具有支配可能性也作为不作为犯中作为义务的限制条件。
对危害结果具有支配可能性是德国学者许逎曼教授提出,其认为只有当行为人对危险源存在一种常态的控制支配关系,行为人能够支配发生危害结果的原因时,才会产生作为义务。[21]这种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如日本的山口厚教授指出:只有当行为人支配了结果发生的原因时,该行为人才有作为义务。[22]我国学者黎宏教授也持相似立场,不作为人现实、具体地支配了因果经过的场合,才能说行为人具有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义务。[23]张明楷教授在常态控制支配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当结合社会分工的原理考虑支配性,仅考虑常态下的控制支配性会过于苛刻。他还举过一个例子:甲在高速路上撞伤他人,警察刚好就在身边,此时应当由警察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20]同样地,甲撞伤乙,如果丙将乙送往医院抢救时,也不认为甲有作为义务。
应该承认,对危害结果有无支配可能性有刑法意义,但笔者认为对危害结果具有支配可能性不是作为义务的成立条件,仅能成为作为义务强弱的根据,仅具有量刑意义。根据对危害结果具有支配可能性的观点,当有优势地位或者其他保证人更有利于保护法益时,就不认为行为人有作为义务;只有由行为人一人或者由行为人保护更有利时,才认为其有作为义务。但这种观点有疑问,就上述案例而言,若直接因存在警察的救助行为就否定甲的作为义务,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甲的责任。而且如果警察在送受害者到医院的途中因紧急情况不得不将伤者搁置一旁去执行特别职务时,由于犯罪行为人的作为义务已被否认,若无其他救助义务人,则无法保障受害者获得有效救助,这与不真正不作为犯保护法益的思想不符。事实上,当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支配性时,行为人必然有作为义务;但即使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支配性,只要其犯罪行为引起法益侵害危险,且有必要救助时,就应当赋予其作为义务,不应以无法控制结果是否发生为由否定作为义务。当然,在特定情况下行为人的作为义务会因优势地位的保证人的履行义务而削弱,由救助义务转化为一定的注意义务。如上述甲撞人案,甲的救助义务不能因警察的救助而消灭,仅因警察的优势履行而削弱,其无须亲自救助,但应当对警察的履行进行必要的注意,确保受害者得到救助。
四、犯罪行为是否产生作为义务具体解析
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有两种情形:一是犯罪行为与其后续的不作为危及同一法益;二是犯罪行为与其后续的不作为危及不同法益。下文结合前述犯罪行为产生作为义务之条件对这两种情形进行具体解析。
(一)犯罪行为与其引发的危险危及不同法益
当先前的犯罪行为与其引发的危险侵害的法益不同,且危及的法益重大时,因为制造了新的重大法益风险,且大多数情形有救助的必要性和期待可能性,所以行为人原则上有作为义务。具体可以分四种情形分别讨论。
1.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上为故意,后续的不作为主观上也为故意,此种情形应当认为行为人有作为义务。例如,甲违反国家规定捕猎珍贵野生动物金丝猴,在用枪射击金丝猴的同时伤及另一捕猎者乙,致乙重伤。如果甲明知不立即救助会致乙死亡,仍故意不予救助致其死亡。此案中甲的犯罪行为造成了新的重大法益危险,如果不及时救助就会引起严重的危害后果,完全符合犯罪产生作为义务之条件;如果否定行为人有救助义务,会漠视对生命法益的保护。因之,这种类型不仅要按前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定罪,而且要评价后续的不作为所构成的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2.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上为过失,后续的不作为主观上为故意,应当认为行为人有作为义务。例如,某化工企业老板刘某违反国家规定指使员工乘下雨偷排污水,本以为污水会随雨水流入长江,但由于排水沟旁边的一栋房屋因下雨倒塌,堵塞了排水沟,使污水溢出流进了旁边的水库,导致水库大面积污染,水库中的鱼因污染而死亡。附近一些村民捡起死鱼准备拿回家吃,刘某明知那次排出的污水中含有有毒物质,吃了因污染而死亡的鱼可能导致失明,但因害怕公安机关将要来抓捕,没有制止村民,也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就逃逸,最终有三个村民因食用受污染的鱼而失明。这个案例中,化工企业老板刘某指使员工偷排污,造成污染事故,构成污染环境罪。他的行为同时又对村民的健康造成了危险,制造了重大法益风险,这一风险也有紧迫性,也能期待刘某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所以刘某有采取相应措施的作为义务。因之,刘某的行为不仅要按污染环境罪处罚,而且要对其后续的不作为进行处罚。
3.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上为故意,后续的不作为主观上为过失,应当认为行为人有作为义务。例如,甲抢夺乙,争夺财物过程中乙摔倒,头碰到石壁上昏迷,甲以为乙不久就会醒来,所以任由乙在野外不管,后乙被冻死。此种情形应当认定甲有救助的作为义务,抢夺行为致乙陷入危险而不救助,不仅侵害了乙的财产法益,而且使乙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对后续的不救助行为完全可以按不作为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处罚。由于刑法在抢夺罪中规定了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加重犯,对后续的不作为致人死亡可以一并作为结果加重犯予以评价,不需要数罪并罚。
4.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上过失,后续的不作为主观上也为过失,应当认为无作为义务。例如,甲在进行自住房屋翻建时未注意到乙从旁路过,致乙被拆除掉落的房梁砸成重伤昏迷,甲拆除结束后也未发现乙的存在,遂离开现场返回家中,最终乙未被及时救助而死亡。此案中甲先前的过失致人重伤行为本身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同时危及被害人的生命这一更大法益,符合增加了重大法益风险这一条件,但由于行为人当时没有发现乙受伤,所以不能期待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积极救助,即在当时情况没有期待可能性,因而行为人没有作为义务。需要说明的是,实践中这种情形几乎都按一个过失致人死亡罪处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最终的死亡结果是由前行为导致的还是由后续的不作为构成的,证据上难以证明;二是按照因果关系理论,行为人实施了过失行为,过失行为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按构成要件符合说完全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至于过失行为导致死亡的因果过程不重要。
总体而言,先行犯罪行为与其后的不作为行为侵害不同的法益时,由于侵犯了数个法益,为防止遗漏评价,应当赋予行为人有作为义务,由此实现对两个法益更周延的保护。但如果因其后续的不作为侵犯了更重的法益,刑法因而规定了结果加重犯,能够通过结果加重犯包容评价前后两个行为,就没有必要采取数罪并罚。例如,本文第一部分所举的第二个案例,李某虽然既侵犯身体健康权又侵犯了生命权两个不同的法益,但刑法为故意伤害罪规定了结果加重犯,且生命法益能够包容身体健康法益,行为人自始仅有伤害故意这一主观罪过,并不存在罪过转化的问题,因此仅按故意伤害(致死)这一结果加重犯处理即可,不必实行数罪并罚。
(二)犯罪行为与其引发的危险危及相同法益
犯罪行为与其后续的不作为危及同一法益时,仅在前犯罪行为所涉犯罪保护法益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大的法益风险,行为人才有可能有救助义务,所以犯罪行为与其后续的不作为危及同一法益时,原则上没有作为义务。具体可以分四种情形讨论。
1.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上为故意,后续的不作为主观上也为故意,此种情形原则上认为行为人无作为义务。例如,甲意图杀害乙,捅乙数刀后,看着乙慢慢死亡而不予救助。这个案例中甲最初的目的就是杀害乙,用刀捅乙既没有危及故意杀人罪之外的法益,又没有超出故意杀人所保护法益之外对法益增加危险,即没有制造或者增加重大法益危险。换言之,最后的结果完全在甲先前故意杀人罪的预期范围之内,并为其积极追求,要求甲去防止乙死亡结果的发生,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再者,先前的故意杀人可以完整地包容后续的不作为行为,因而无须再单独对不作为进行重复评价。但在共同犯罪场合,为了保护法益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作为义务。例如,甲意图杀害乙,捅乙数刀后又于心不忍,便打算送乙去医院,正好路过的丙极力劝阻甲不要送乙到医院,甲采纳丙的意见打消了救助乙的念头,最终乙因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由于丙的教唆行为坚定了行为人的犯意,应当认定成立不作为犯罪的教唆犯。但许成磊等学者认为,“大体上可以否定不作为教唆之可能”,主张不作为犯罪中并无教唆犯存在的余地,丙仅成立不作为犯罪的帮助犯。[24]但无论是认定为教唆犯或是帮助犯,事实上都是对行为人甲作为义务的承认;否则,如果不承认甲有救助乙的义务,则不应对丙定罪处罚。当然,这种情形虽然认为甲后续有救助义务,但没有必要按两个故意杀人罪处罚(一个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一个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只按一个故意杀人罪处理即可。
2.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上为故意,后续的不作为主观上为过失,应认为行为人无作为义务。例如,甲意图杀害乙,便故意将乙推入池塘中,看到乙在池塘中慢慢滑动,以为乙会游泳,觉得自己的杀人计划失败便离开,最终乙因溺水而亡。此案中甲的行为一般只需要单独认定故意杀人既遂即可,主要原因还是前犯罪行为没有制造或者增加构成要件保护范围之外的重大法益危险,行为人没有救助的作为义务,所以不必按故意杀人罪未遂加过失致人死亡罪实行数罪并罚。根据构成要件符合说这种案例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行为人有杀人的故意与行为,最终被害人也因行为人的行为而死亡,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既遂的标准,没有必要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事实上,要求犯罪人对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危险有救助义务,目的在于督促行为人积极履行救助义务,从而保护法益,但对这种情形即便法律科加行为人有救助义务,行为人也不会救助,因而这种情形不应认为甲有救助义务。
3.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上为过失,后续的不作为主观上为故意,此种情形应当认为行为人有作为义务。例如,刘某在公路上超速行驶致张某等三人重伤(刘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刘某下车查看发现三人伤势严重,且周围没有车辆和行为,为了逃避责任,刘某置三人的生命危险不顾驾车逃离,最终其中二人因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③刘某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使张某等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如果不及时救助将会造成更大的法益损害,在当时情况下也能期待行为人进行救助,所以行为人应当有相应的救助义务。对这种类型司法实践中有不同处理方式,有的判决按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处理,有的判决按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处理。事实上,两种处理方式实质上都是对行为人有救助义务的肯定,交通肇事使被害人生命处于危险状态,此时行为人就负有救助的作为义务,但行为人没有履行这种救助义务而致人死亡,这种危害结果实际上就是因不履行救助义务而产生的不法后果。[21]需要说明的是,对犯罪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有些情形刑法是通过结果加重犯的方式进行评价,上述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就是这种情形。如果刑法没有通过结果加重犯的方式评价后续的不作为行为,就要对后续的不作为另外定罪处罚,否则就很难实现罪刑相适应。
4.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上为过失,后续的不作为主观上为过失,应当认为行为人无作为义务。例如,甲不小心将在岸边的乙挤入水中,以为乙会游泳便未予救助,后乙因不会游泳而溺水身亡。这种情形前后两个行为具有连续性,在评价前面的过失致人死亡行为时就能够包含其后不作为导致的死亡结果,无须再单独评价其后的不作为行为。
简言之,当先行犯罪行为与其引发的危险危及同一法益时,只有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观上为过失,后续的不作为主观上为故意时,才认为行为人具有作为义务,其他三种情形或者因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或者因为后行为是先行为的合理延续等原因,不宜认为行为人有作为义务。
注释:
①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锡刑初字第20号。
② 这个案例是根据一个真实案例改编而来。
③ 参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刑事判决书(2018)冀02刑终8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