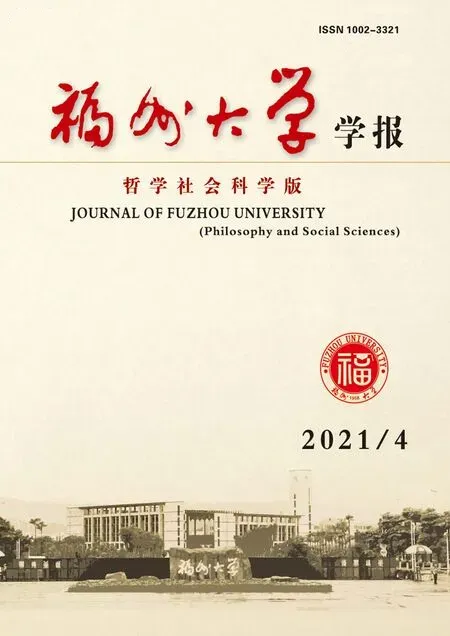古代“装扮类面具”谱系与“人”“神”观念演变
燕 筠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自人类诞生以来,因其有模仿本能而产生面具。面具内涵的丰厚复杂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眼光。对于具有形象展示意义的装扮类面具,学界将目光更多聚焦于傩面具在傩戏中的用途及造型解读,而傩面具却只是装扮类面具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种表现类别。本文试图对装扮类面具的关注贯穿于其发展变化的各阶段,运用谱系勾勒面具的不同阶段下的造型变化及其“人”“神”观念由来。怀着对装扮类面具的图谱解读的兴趣,我们提出以下问题:从装扮类面具展现的符号形象,其丰富的能指、多重义项,构成怎样的形象谱系?追溯面具起源,从原始人类巫术面具的相似模拟,到戏剧面具的角色标识,其变化经历了人关于面具、关于“自我”怎样的认知观念演进?“装扮类面具”在怎样的表述语境中发挥其特殊的“娱神”或“娱人”的功能,以及进入到戏剧领域的面具又有哪些符号化象征意义?
一、原始巫仪面具与“人类”认知滥觞
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面具是存在于新石器时期的陶制面具。著名的新石器时代仰韶半坡人面鱼纹彩陶,以及国内外发现的人面岩画,这些图符被推断为原始人面具使用的痕迹。2003-2004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发掘的一些成型的陶面具以及残片,是目前中国发掘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距今7000-8000年。据北福地发掘报告介绍:北福地所有制作面具的材料均来自于陶直腹盆残片,以腹部残片为主,其次为底部残片。这些面具是由先行制作的陶制直腹盆再行切割而成。这些陶面具是人面或兽面雕刻陶片,材质为夹云母陶片,因其烧制火候不太高,硬度较低,比较适于雕刻操作。这样制作的面具有弧度、五官凹凸明显而呈现立体。北福地完整陶面具边缘分布有几个小穿孔,应该是方便系戴时穿绳使用。北福地面具的人面,或猪、猴、猫科动物等兽面,多数大小与真人面部相当。从比较完整的人面与兽面面具形制来看,其中有典型的女性人面陶片面具,“技法完全采用较细而浅的阴刻线条,勾勒出眼睛、鼻部及口部轮廓,三者有机连接为一体,线条流畅,面目端庄清秀,颇具女性妩媚”;猴面具则“正圆形镂空双眼与歪斜鼻口”;还有“镂空双眼,斜立”“阴刻短竖线表示露出的牙齿,面目狰狞恐怖,双眼凶光,颇似猫科猛兽”等[1],尽管原始先民的雕刻技法朴素或不成熟,其充满抽象写意的造型却颇有意趣。其图案内容不是对人面或兽面的单纯模仿,而是通过适度象形或变形手法,简笔勾勒并夸张放大某些部位,如眼睛、牙齿等,既准确提炼表达兽的特征,又揉入人类对兽面与人面的比较认知,可见先民对于该种动物的熟悉。
北福地先民为何用陶器残片制作面具?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与野蛮社会的界限。“陶器给人类带来了便于烹煮食物的耐用器皿”[2],而陶器的制作有火候与土质方面的技术要求,北福地面具质地较软,易于雕刻,或许正是烧制失败后的陶器的再利用。据大多数的原始社会资料显示,远古面具多在原始祭祀场合中出现,而北福地陶面具的发现却是在远离祭祀坑的灰坑和“房址堆积层内和居住面上”。北福地发掘者段宏振等学者借鉴了对仰韶人面鱼纹的假面判断结论,认为北福地的陶制面具应该是狩猎巫术或舞蹈中巫师装扮所用。[3]北福地面具制造与放置地的随意,让我们怀疑其被重视的程度,面具在这里似乎缺少类似后世傩仪中那般神圣与尊崇的意味。事实上“宗教或巫术只不过是史前人群日常生活中普通一页,一如他们的饮食起居一样”[4]。《国语·楚语》中载有原始时代民间祭祀权利还没有被垄断的“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时期,就描述的是古代“巫术”使用的日常化,面具作为巫具在巫仪中使用。
史前陶制面具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原始人类的巫术需求。面具在不同阶段的制作,是与当时古人的制作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原始先民制作面具的动机,源自人类对生存的祈愿,先民赋予面具最为实用的功能:为狩猎的成功,装扮兽类,以获得能延续生命的食物。弗雷泽在《金枝》中指出:原始人根据“同类相生”的“相似律”思想原则,引申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5],这叫做“模拟巫术”。因而产生了以模拟为基本方式的原始人绘画、舞蹈等巫术形式。需要强调的是,原始人绘画、舞蹈等在原始人眼中是必要的获得生存的巫术手段。面具也是原始人使用巫术的一种手段,它通过模拟而发生作用,原始人相信他们“能够相当自由的根据人类意志使用它们(巫术)”[6]。
面具作为原始人意识形态的外在呈现,反映了人类对动物与自我的认知。人类在朦胧意识里,对动物与自身的认识掺杂交织,并借助于对动物的认识表现出来。在先民具有巫术色彩的面具修饰中,他们发现了动物与人的异形同构,人面和兽面的互换通过面具达到。北福地面具是史前人类朦胧的自我认知等意识的外在投射与物化形态。它们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是,先民超越了动物本能,从混沌的物我一体中分离,逐渐建立关于“人”的认知观念,并以此为起点,开启并发展围绕“人”的造物行动,越来越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被制造。这一时期,人类使用巫术为自己服务,巫术思维之下,面具只是一个模拟相似物,它是先民用以达到目的的巫术手段。
二、祭祀图腾面具象征之“神”“人”交际
面具的神圣化,与人类从图腾观念到祖先崇拜相关。闻一多先生把“典型的图腾主义的心理”描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人的拟兽化”,“人根据图腾的模样来改造自己”,图腾形象完全是动物,原始人企图因此获得图腾的属性和力量;第二阶段为“兽的拟人化”,图腾形象表现为“半人半兽”,“按照自己的模样来拟想始祖”,“兽形图腾蜕变为半人半兽的始祖”;第三阶段“始祖的模样变作全人形”。[7]在一个原始思维的框架内,图腾面具表述的是先民对于“神”的认知。
“图腾”来自于原始人“万物有灵”观念中产生的对超自然力的崇拜。人们利用面具装扮为神灵,面具因“与神相似”带有了特殊“灵性”,带上面具,就改变了凡夫俗子的身份而获得神力。这当然也是巫术,而与前期巫术的不同在于:原始人对面具神灵“形象”的崇拜。人类最早尊崇的神灵是动物。恩格斯说:“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尸体,是动物,由此就产生了动物崇拜。”[8]尊崇动物神体现的是人类本能的对食物链的崇拜,先民对凶猛动物崇拜的遗留观念影响了面具的造型,使其样式狰狞可怕。沟通天人,与神相通是巫师佩戴面具的首要目的。在颛顼“绝地天通”之后,祭祀权利集中于统治者手中,颛顼本人就是大巫王。巫觋面具的使用严格限制于少数拥有特权的氏族首领,他们被尊为巫王,对面具的佩戴使其具有祖先与英雄意味。因此,以动物为人祖的图腾观念得以确立流传下来。《史记》载:“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氏族英雄化装成各种禽兽,头戴各种兽形面具或以其他方式装扮为动物,直接以野兽之名称之,而这些野兽,就是各氏族的图腾。古代商民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郭沫若考察周帛画后称“凤是玄鸟,是殷(商)民族的图腾”“龙是夏民族的图腾”[9];叶舒宪考证,在中华民族的图腾谱系中,“黄帝时代的图腾是熊”[10],刘毓庆认为炎帝族“以牛羊为图腾”[11];而范三畏认为“华夏族以伏羲为虎图腾”,“虎是猎牧时代的最高图腾,龙是农耕时代的最高图腾”[12]。在图腾崇拜阶段,人们对其祖先的崇拜就表现为对图腾动物的崇拜。《尚书·舜典》记载的“百兽率舞”表现的就是先民狩猎仪式或舞蹈中的图腾崇拜:“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3]这里“百兽”的装扮中,佩戴面具一定是其中重要装扮类型,而“百兽”面具造型可能是部落图腾,亦或是人们崇拜的神兽。
在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神兽面具是饕餮纹面具。在先秦礼器如青铜铸鼎上,可以见到饕餮纹。其形状复杂多变,基本样貌是:圆眼突兀,耳鼻卷曲,左右对称,有一种神秘庄严感。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说:“从纯粹形式的观点来看,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古代中国青铜器的饕餮面像看作是面具。”[14]郭净也认为,饕餮“是一个典型的面具形象”[15]。因此饕餮纹面具可以说是狞厉兽面的典型表达符号。前辈学者在考证时,经常论及饕餮、蚩尤、方相氏与面具的复杂关系。《周礼·夏官》中载有“方相氏驱傩”的事例屡屡被研究者征引,且被公认为是在傩仪式中使用面具的例证。“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郑玄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时难,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却凶恶也。”[16]“黄金四目”被解释为戴面具;所带面具名曰“魌头”。王国维《古剧脚色考》“馀说二”中提出,周时驱傩之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时,已经产生了面具。[17]傩仪式中的“方相氏”装扮,是古籍中对面具的最早记录。方相氏佩戴面具是何种造型形象?周华斌先生认为:“黄金四目”实际上是虎口兽角的饕餮型青铜面具。商周时期的巫师方相氏,装扮的乃是一种半人半兽的神兽或战神形象。[18]常任侠《关于我国音乐舞蹈与戏剧起源的考察》提到:殷墟出土有饕餮纹方相氏青铜面具。[19]陈多《古傩略考》认为“方相、蚩尤,其实一也”[20]。蚩尤“铜头铁额”及至《龙鱼河图》所谓“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都说明蚩尤之面貌凶悍。宋代罗泌《路史·后纪·蚩尤传》注:“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者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像率为兽形,傅以肉翅。”暗示蚩尤之状就是饕餮纹。顾朴光在《方相氏面具考》中,把方相氏与上古的蚩尤联系起来,他认为,方相氏面具由假面(蚩尤)和假头(熊首)两部分组成,一方面,方相氏佩戴状若蚩尤形象的假面,希望借助蚩尤的神威震慑敌人和疫鬼;另一方面,他又佩戴用黄帝部落的图腾物制作的假头,以祈求得到图腾祖先的庇护。由于方相氏把当时最强大的两个部落的图腾合为一体,他担负起防夜、威服天下和驱鬼逐疫三重任务。[21]因此,蚩尤面相凶悍;饕餮纹象征狞厉、凶狠;方相代表祛邪;三者的形象在传播中叠加而逐渐确立,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具有威仪与神性的面具文化符号。
图腾面具的功能价值在于其背后藏着的那个神灵或超自然物。饕餮类丑恶狞厉的形象具有驱邪力量,驱邪力量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戴面具的人,而在于其所佩戴的面具形象。这种非人化的可怖形象具有神性正反映了古代先民对于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是一种物我两分的状态中。人类的认知视域被外在于他的动物世界所占据,使得自我的意识与神秘的外在世界联系起来。在自然面前孤立弱小的人类眼中,万物皆神,他们需要与具有强大力量的动植物结成血缘关系而获得保护,带上面具,通过仪式与动植物达成模拟,就会获得神秘的威力,图腾作为他们的第一保护神成为祭仪面具中的重要形象。图腾图像对面具的造型有极大影响。如山西寿阳爱社的傩舞戏面具称为“鬼面”,但在造型上却似龙形:其鼓目、阔口、獠牙、豁鼻的造型集合了“龙与上古帝王的面相特征”。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达,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丰富,先民力图从围绕着它们的自然力中分离出来,崇拜对象从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神转变为半人半兽的祖先,以及逐渐演变为完整的人祖形象和英雄形象时,面具形象依然作为宗教图像而存在,依然具有强大的威仪与神性。比如在傩仪式中出现的关公面具、钟馗面具等,其实质都是具有神性的图腾面具的衍化。
三、戏剧面具的“角色”赋形
“戏剧角色”的概念来源可以追溯于古希腊戏剧中面具的运用。古罗马戏剧批评家贺拉斯在《诗艺》中写到:“埃斯库罗斯又创始了面具和华贵的长袍,用小木板搭起舞台……”[22]古希腊剧作家的戏剧创作中,剧中人物大多在六到七人,而真正扮演剧中人的演员只有两三人,而且都是男演员,这时候,泰斯庇斯带着面具进入到戏剧表演中。可以说,面具用于戏剧,是专门为剧中角色所创造的,面具的使用起到了“角色的切换”的重要作用。演员们用最直观简朴的方式扮演着自己所饰的角色,在这里,面具更多的是作为道具,它用来区分人物角色,表现人物的身份、类型和性格。古希腊面具并非只遮脸,而是将整个头部兜住,只露出眼睛、耳朵和嘴巴,嘴部大张,圆形的开口嘴型使表演者可以清晰流利的念出台词,借助面具,几个不同的角色由一个演员饰演轮换呈现,以此解决演员人数不足与剧中人物众多的矛盾。古希腊面具上的“悲伤”或“快乐”的凝固表情,代表了悲剧或喜剧的特征,戏剧面具将生活中的种种悲喜情绪放大提炼,表示皱纹的线条、表示恐惧的大眼、开口笑的嘴巴、深陷的眼窝让观众辨识并记住它们的特征,而往往每一部戏剧都有自己的一套面具。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的即兴喜剧使用面具区分各种类型化、脸谱化角色,在即兴喜剧中,谈恋爱的男女青年并不使用面具,而只在作为配角的“商人”“军官”“仆人”等类型化人物角色扮饰上使用,这类人物,在剧中有着固定化的性格、动作以及社会阶层,因此,面具的表情也是夸张的,它们与服装一起塑造着角色。
中国戏曲解决演员不足与角色(剧中人物)众多的矛盾找到的方法是“脚色制”,“以类型为中介,演员皆归入类型化的脚色中,通过类型化的脚色”兼扮串演“去观照众生万象”。[23]面具在戏曲中的出现常常是以“神头鬼面”模样,代表了“面具神性”在戏剧中的遗留。面具的装扮角色功能在汉唐时期的“百戏”“歌舞戏”中蓬勃发展起来。汉代的面具假头受到外来民族影响,造型样式非常丰富。《汉书·礼乐志》载汉哀帝时乐府人员配置有:“凡鼓八,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24]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专门引出颜师古注释:“孟康曰:‘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韦昭曰:‘著假面者也。’”[25]象人是一类专门的演员,其表演内容应该是假形扮饰一类。象人之称谓表明人们对乐舞百戏中“模仿形象”类型表演的喜爱与重视。张衡《西京赋》记载:“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薛综注:“仙倡,伪作假形,谓如神也。罴豹熊虎,皆为假头也。”[26]象人扮演的苍龙、白虎等珍禽异兽舞蹈跳跃,仙女女娥唱歌,种种奇异景象。制造仙境和假扮各路神仙,戴假面的表演、动物面具的表演,在汉代已非鲜见,面具功能扩大化而用于娱人为目的的宴乐百戏。在这些民间百戏表演中,面具用于角色扮演而受到西域等地民族影响,造型更为自由。南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27]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一曰:“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麿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羂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啗人民之灾也。”[28]姜伯勤等学者将《钵头》《苏摩遮》等戏舞均考为面具戏。[29]白居易的《西凉伎》介绍了这种乐舞的表演形式以及扮相:“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假面胡人应该是“深目多须髯”“深目高鼻”的面貌特征,假面狮子是传自于西域的兽面。由于胡商们做生意四处游走,西域的表演影响遍及大江南北,明代袁宏道有“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假面胡头跳如虎,窄衫绣裤槌大鼓”的诗句,“假面胡头”独树一帜的表演,与本土“神性”傩面的交融,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精神。葛承雍《日本胡人假面形象溯源》认为,日本胡人假面来源于西域龟兹到盛唐的文化传播,并且指出:“胡人假面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面具艺术,边跳边舞虽想象恣肆,但基本面相并不是畸形鬼脸,没有妖魔化,而是现实人物的夸张化。在‘钵头’胡人真实形象背后有着生与死、善与恶的悲悯情怀,是人神勇斗野兽的象征符号,有着驱邪纳福、珍爱生命的表意性质。”[30]由于娱乐性表演形态的影响,傩戏中的面具也逐渐融入世俗。歪嘴秦童是一种典型的市井化形象。它通过五官的夸张来塑造秦童的角色特征,面具的夸张先从歪斜的嘴巴开始,鼻梁是歪的,眼睛是歪斜不对称的,整个面相脸盘都是扭曲的非对称造型。它们突破了在傩戏中原有的神面的威仪,而呈现出世俗的活泼与戏谑。“它显示出傩戏表演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即人神沟通过程中人与神的位置、身份、角色的变化与转换,从神灵崇拜,人依附神,转向人出神离、自娱自乐。”[31]通过非正常五官的塑造与破格重组呈现出来的“歪嘴秦童”类世俗人物角色出现在祭神祈福的傩戏表演中,表明了人们在思想意识上对神灵依赖的逐渐脱离,人类主体性意识进一步增强。
面具自汉唐以来便是民间娱乐表演中的重要道具。它满足人借由“遮蔽隐藏”充分释放自我的条件。面具的佩戴者得到“面具扮演”的掩护,通过“角色转换”活动使情绪得到宣泄、欲望得到满足。在戏剧文化中,面具佩戴者一旦戴上面具,他与面具所指代的对象便产生了一种角色认同,他要像戏剧中的角色那样说话和行动,通过观众的参与,这个认同又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和强化。戏剧由此与宗教仪式分离开来,成为一种具备自身品格与规律的艺术品种。在这样的戏剧表演中,面具“娱神”以沟通天人转变为“娱人”以丰富人之生活。人的天性和意志成为首要准则,面具的“赋形”奠定了后世戏剧的作为娱乐样式的根基。
“装扮类面具”谱系将多元形态的形象展示面具连接于一个研究框架内,划出其发展脉络,或者亦能体现世界其他地域面具的共性发展。而我们更注意到,中国古代面具形态受到巫祝文化的极大影响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因此,我们希望界定出的是关于中国古代“装扮类面具”的概念来源与形态,也希望其作为面具谱系研究的一个起点。
注释:
[1][3][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10-134,110-134,245页。
[2][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冬莼、马雍、马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5][6][英]J·G弗雷泽:《金枝》,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39页。
[7]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网站PDF版,第63页。
[9]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14225正片),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0]叶舒宪:《汉代的天熊神话再钩沉——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申论》,《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
[11]刘毓庆:《华夏文明之根探源——晋东南神话、历史、传说与民俗综合考察》,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12]范三畏:《伏羲虎图腾与中国文化》,《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3]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8页。
[14][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05页。
[15]郭 净:《漫谈中国面具的质·形·色》,《民族艺术》1991年第3期。
[16]郑 玄、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7]王国维:《戏剧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18]周华斌、方相:《饕餮考》,《戏剧艺术》1992年第3期。
[19]常任侠:《关于我国音乐舞蹈与戏剧起源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
[20]陈 多:《古傩略考》,《戏剧艺术》1989年第3期。
[21]顾朴光:《方相氏面具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22]亚理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57页。
[23]解玉峰:《“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
[24][25]马美信:《宋元戏曲史疏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26][南朝梁]萧统:《文选(张衡〈西京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7][28]师若予:《古代丝路上的佛教假面艺术交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8期。
[29]姜伯勤:《敦煌悉磨遮为苏摩遮乐舞考》,《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
[30]葛承雍:《日本胡人假面形象溯源——评龟兹乐舞有关的学术考释新收获》,《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3期。
[31]丁淑梅:《从歪嘴秦童看傩戏面具的变形与异出》,《民族艺术研究》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