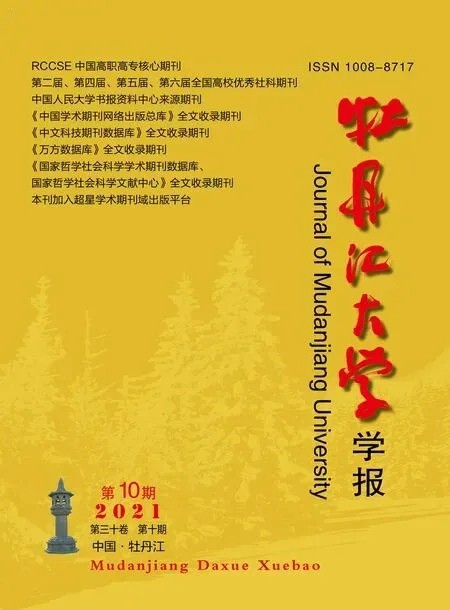精神分析学视角下《洛丽塔》中主人公的情结书写
王振平 盖雪莹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 300222)
一、引言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洛丽塔》(Lolita)是其最为著名也是最具争议的一部小说。小说讲述了成年男子亨伯特与少女洛丽塔间的不伦之恋。作者对两位主人公病态的爱情与人格描写为精神分析理论提供了经典的文学范例。
《洛丽塔》自面世以来就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评论视角各不相同。外国学者对《洛丽塔》的研究远早于国内学者,有针对小说中的道德问题进行解读的,[1]有强调小说中的爱情主题的存在与意义的,[2]有研究《洛丽塔》中的语言表达技巧,如文字游戏、双关、反讽等的。[3]国内学者对该小说的研究虽然相对较晚,但已颇具深度和广度,其中有针对小说中畸形爱情所引发的道德问题评论,[4]有从昆虫学角度对洛丽塔的人物形象进行变态化解读的,[5]有从纳博科夫捍卫自由的立场对小说中人物进行批评的。[6]无论国内还是或国外,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小说表现的道德问题或写作技巧的研究,少见从心理学角度对主人公人格和情结所导致的悲剧结局进行解读的。小说中主人公心理与人格的特异性不但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决定了小说的命运,作者对主人公心理和人格的特异性描写,正是小说与众不同的地方。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主人公进行解读,探究其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或可让我们重新认识创伤及其产生的情结对人的心理和人格塑造的影响,也会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认识《洛丽塔》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二、精神分析学与《洛丽塔》中的情结书写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不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心理学研究或精神疾病治疗,也被应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即精神分析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是一种试图离开美学理论来揭示人类行为的动机和方式,它是一种文学阐释的方法。”[7]将精神分析理论用于文学批评,用于剖析作品人物的内心、本能冲动与欲望,是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的现实应用。精神分析文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对人物性格进行深入、系统的剖析,挖掘文学作品的内涵,进而获得对文学作品的多元理解。由于主人公精神心理的特殊性,《洛丽塔》为精神分析批评提供了绝佳的实验园地,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亨伯特与洛丽塔的创伤与情结进行解读,我们或可从新的视角认识作品,寻找两位主人公不伦行为和病态人格的根源。
弗洛伊德将情结归为性本能的驱力作用,既有性行为本身的内驱力,也有追求快乐的行为及情感活动,包括恋母情结、恋父情结、阉割情结等。随着人们对精神分析学的认可,荣格在后期提出了更为精炼的情结理论,“情结是由于创伤的影响或者某种不合时宜的倾向而分裂开来的心理碎片……情结干扰意志意象,扰乱意识过程,它们起骚扰记忆和阻碍一连串联想的作用。它们能在短时间里围困意识,或者用潜意识影响言谈与行动。”[8]不难看出,情结与创伤之间有直接联系并且隐藏在潜意识当中,当个体察觉到情结的潜在危险时,它已经对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荣格同时指出,情结的养成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来自于个人经验所产生的创伤意向或体验,二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个体人格内容。”[8]《洛丽塔》中主人公的情结大部分来自于荣格所说的第一种情况——由外界创伤所导致的情结。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洛丽塔》男女主人公的情结虽然各不相同,但情结的塑造皆源自其成长过程中人格结构的失衡。亨伯特作为性变态者,具有精神分析学中所强调的人格结构失衡的典型特征,在三层人格建构中,自我是本我与超我间沟通的纽带,它作为协调者,一方面满足本我对快乐的追求;另一方面使行为符合超我的要求,一旦自我的力量无法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人格结构就会失衡,导致不健全人格与病态化精神的形成。由于超我在道德层面上的干预,亨伯特的本我欲望长期受到压制,自我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点,继而形成无法自愈的变态心理。幼年失爱使他的爱情心理极度扭曲,进而产生偏执情结,这种偏执情结使他将自己的幻想投射到一个不合适的客体身上。在与洛丽塔的恋爱中,亨伯特又表现出一种自恋情结,安全感与归属感缺乏导致的低自尊状态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养成提供了肥沃土壤。由于渴望得到洛丽塔的认可,他通过贬低其他女性来夸大自己的容貌和人格魅力。表面上的自大掩盖了他面对洛丽塔时的低自尊,同时也导致了他的矛盾情结。在与洛丽塔的旅途中,亨伯特内心充满焦虑与不安,他一方面怕恋童癖的事实被揭穿,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他不能在本我与超我之间找到平衡点,于是呈现出趋于病态的自我。如果理性思考不能内心冲突,那么不和谐人格的塑造便在所难免。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有最丰富多彩的本能倾向,其基本发展过程取决于儿童期的经验。”[9]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洛丽塔幼年丧父,母亲不负责任,几乎使她处于弃儿的境地,学校与社会环境的不理想更是加剧了她遗弃情结的养成。洛丽塔在没有任何规约的环境中度过了儿童期,她过度放纵本我,养成了错误的价值观、爱情观,继而造成了人格结构的不稳定。她与亨伯特之间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遗弃情结所导致的恋父情结,一种病态的爱情心理,一种依赖感,而这点却恰好被亨伯特利用,导致了这场病态的爱情。
三、亨伯特的情结书写
《洛丽塔》中的亨伯特是典型的“纳博科夫式主人公”,他作为最经典的文学形象之一,淋漓尽致地将由多种情结共同塑造而成的病态人格展现在读者面前。他是现实中的逃亡者,精神上的流浪者,偏执地追求已经逝去的青春,徘徊在寻找与重现的路上。由于13岁时经历了一场铭心刻骨的初恋,寻找逝去的阿娜贝尔便成了他一生的追求。他渴望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初恋情人的替身,将昔日情感延续,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行为的病态与不可实现,但还是不计后果地踏进了种种病态情结编织而成的牢笼。
(一)偏执情结
偏执情结即偏执型人格障碍,属于精神心理疾病,在亨伯特身上表现为爱情心理失调,进而导致了性变态。“偏执型人格就是一种由于‘片面’‘缺失’‘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变态人格。这种人往往智力发育正常,但却表现出无端猜疑、人情冷漠、自以为是、主观固执、自私自利、怨天忧人、嫉贤妒能等不协调的情绪及心理反应,其思想、语言、行为明显偏离正常。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极不和谐,具有偏执的分裂性人格。”[10]这类人经常处于戒备和紧张状态,寻找怀疑和偏见的根据,歪曲他人的中性或善意的举动,做出的反应不是敌意就是藐视,容易产生病理性嫉妒。亨伯特身上不乏这种偏执情结,这也是其拥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重要原因。
亨伯特的偏执情结主要来源于早期失爱与后天打击。他年仅三岁就失去了母亲,“我那位非常上镜头的母亲死于一次意外事故(野餐,雷击),那时我3岁,因此,除却存留了黑暗过去里一小袋的温暖,在记忆的洞穴和幽谷中,她一无存在。”[11]父亲角色时有时无,各种女性时隐时现,少年亨伯特成长于动荡不安的环境,缺少关心、爱护与指点,于是,当他第一次面对爱情时,就难免过分投入,以至于失去挚爱对他的人格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阿娜贝尔是亨伯特所有幻想的来源,洛丽塔只是阿娜贝尔的影子与延续。亨伯特与阿娜贝尔的爱情被成年人的约束与疾病所中断,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亨伯特都没有得到满足。他期待再续前缘,于是偏执于小仙女,偏执于重现海边场景,他的爱情心理年龄停驻于少年。他的年龄在增长,可他心仪的对象依旧是少女,于是,在普通人眼中他是一个性变态者。弗洛伊德称,“当一个人的自我无法压抑住本我中的力比多能量的时候,一种性变态的形态便会逐步呈现。”[10]如亨伯特所言:“阿娜贝尔的死引起的惊骇更顽固了那个梦魇般夏天的挫折,成为我整个冰冷青春岁月里任何其他浪漫韵事的永恒障碍。”[11]原生家庭与初恋受挫是造成亨伯特偏执情结的主要原因,而他与洛丽塔所谓的“爱情”便是这种偏执情结的直接后果。
亨伯特在旅途中的种种行为其实就是偏执情结的病态表现。他用心缜密,时时刻刻观察着洛丽塔的心情与态度,对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过分解读,甚至猜疑。他对周围环境极端敏感,即使是来自外界的好意都会把他吓得他心惊胆战。亨伯特在一家名叫“着魔的猎人”的旅馆第一次占有了洛丽塔,自此,他就像是着魔的猎人一样看守着自己的猎物,拒绝外界干扰,对洛丽塔的关爱达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他们的旅途看似漫无目的,但亨伯特的话语中一再透露出要带他心爱的人去海边。他一心想继续少年时中途夭折的爱情,结果为时间所困,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偏执情结中。
(二)自恋情结
自恋情结属于一种人格障碍,典出希腊神话人物那喀索斯(Narcissus),传说中他因贪恋自己水中的倒影而憔悴身亡。精神分析学将自恋型人格障碍定义为一种认知、情感行为,是一种夸张强调独特自我的表现。亨伯特狂妄自大,以自我为中心,这在小说伊始就可见一斑。他对自己的认识是:“除去我的不幸,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英俊出众的男性——稳健,高大,柔软的黑发,有一种抑郁但格外诱人的风度。……我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我选中的所有成年女性。”[11]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他的过度自信。“自恋源于力比多,随着个体健康地发展,个体自身所产生的力比多会投向客体。在投向客体的过程中,如果遭遇挫折,这种向外爱的力比多会返回个体,形成继发性的自恋,也就是病理性的自恋。”[12]换言之,自恋情结就是一种低自尊人格的自我保护模式。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往往具有自恋与低自尊两种心态,他们企图通过贬低他人和抬高自己来抵抗自身的脆弱。亨伯特少年时期恋爱受挫,所受创伤造成的偏执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导致之后的爱情屡屡遭遇挫折。在巴黎遇见妓女莫妮卡时,他发现她身上的烟火气并不符合他的期待;寻求“专业人士”企图找一位年轻的少女来满足欲望时,遭到敲诈;与瓦莱丽亚病态的婚姻更让他懊丧不已。种种情爱、际遇都重重打击了亨伯特的自尊心,进而促使他用自我保护模式来降低滑稽生活对自己的打击。自恋情结一天天加重下掩盖着的是他极其脆弱的自尊心。“自恋者的内心经常处在分裂之中,雄心与卑微的感觉、希望与绝望的降临、忧郁与暴怒的频繁转换。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爱与恨的矛盾中失去自己。最终,自恋者与世界联系的试图就被其保留在或隐或显的自我理想中。”[13]
亨伯特用尽心思,不吝金钱地讨好洛丽塔,企图与她建立一种舒适又长久的关系。奎尔蒂的出现让他梦想破灭,洛丽塔的出逃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亨伯特脆弱的自尊被击得粉碎,他的生活失去了目的,他虽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但他成年爱人的身上却有着洛丽塔的影子,甚至连名字——丽塔,都与洛丽塔相像,他还带着丽塔按照他曾和洛丽塔走过的路线巡游。丽塔善良而简单,体谅、安慰他,但却永远无法替代洛丽塔。亨伯特的自恋终于变成了失望,自恋情结变成了失望的死结。
(三)矛盾情结
亨伯特身上的种种矛盾导致了其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即人格分裂。人格结构的坍塌是造成人格分裂的直接原因。虽然小说中并未出现对多重人格病理性状的描述,但读者能依稀感觉到它的存在。最为明显的一处是,当黑兹夫人因车祸离世后,亨伯特与洛丽塔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他想做洛丽塔的恋人,做回青少年的自己,举止与心境都和第一次得到自己的爱人时一样,又激动又恐慌,甚至连噩梦的内容都表明他如同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洛丽塔在他身边时,这种表现成了常态。随着旅行的进行,在超我道德意识的影响下,亨伯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反常,愈加变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青少年状态被识破。于是,他披上了洛丽塔继父的外衣来保护自己与这场不伦之恋。在理智与欲望的斗争中,他如同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就准备逃跑。暂居塞耶街时,洛丽塔对他模糊的称呼“亲爱的”或“父亲”也让他混淆了自己的角色与身份,他不知道该屈服于本我的快乐愿望还是遵从超我的道德准则。当自我无法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时,他的人格结构便濒临崩塌,继而引发焦虑和恐慌。这也正是他们从不在某一地点过多停留的一个原因。
奎尔蒂这一人物的出现别有意味。亨伯特与奎尔蒂看似敌对,其实有一定的共性。亨伯特憎恶奎尔蒂,不仅因为他夺走了洛丽塔,还因为在某些方面他们是相似的,这严重地干扰到了他身份的稳定。一方面,他与奎尔蒂有同样的罪恶,但奎尔蒂的超我并不给予其自我以道德限制,他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可以心安理得地让未成年少女拍低俗电影,无止境地伤害洛丽塔。让亨伯特懊丧和纠结的是,这样的人竟能将洛丽塔从他身边夺走,并毫无歉疚地糟蹋她。奎尔蒂如同亨伯特的阴暗面,一个可以逃脱超我约束,不用背负愧疚之心的亨伯特。所以亨伯特无法将自己与奎尔蒂明确区分开来,他一方面渴望成为奎尔蒂,毫不掩饰自己的罪恶需求,一方面他又憎恶奎尔蒂。杀死奎尔蒂更像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杀,他渴望通过这种行为来弥补洛丽塔,使本我的欲望屈服于超我的控制,以达到恕罪和摆脱矛盾情结的目的。可事与愿违,他的超理性癫狂行为终于使自己陷入更加无法自拔的矛盾境地。
四、洛丽塔的情结书写
洛丽塔同样是个悲剧人物,造成她悲剧的原因有很多,最直观的就是亨伯特对她的迫害。显然,直接原因并不是所有原因,她的悲剧来源于方方面面,家庭、学校、社会及其自身缺点都难逃其咎。复杂的家庭让洛丽塔从小缺失父爱和母爱,没有体会到真正的情爱;复杂的社会、传统的教条、膨胀的物欲与教育的缺乏,对她情感的变异和心理的扭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洛丽塔最终结束了与亨伯特和奎尔蒂的不正常关系,与一个普通男子结婚生子,作者却给予她一个难产而死的结局。这表明,作者并不认为洛丽塔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改变她悲剧的结局。生活赋予她的种种情结影响着她生命的每一步,并最终与其他社会因素合力将她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一)遗弃情结
洛丽塔身上最明显的表现是遗弃情结。被遗弃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进而催生了病态爱情心理。心理学家塔拉·班奈特认为:“遗弃不仅指身体的被遗弃也指精神的被遗弃,那些失去父母,没有家庭关爱的孩子是弃儿,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也是弃儿。……由于家庭和父母,社会对个人价值的排斥与不认可,个体精神世界的漂泊感也会使人产生遗弃情结。”[14]洛丽塔生长于一个不完整家庭,从小缺失父爱。母亲夏洛特不但不称职,更谈不上尽责。她和洛丽塔并不像母女,她莫名其妙地嫉妒洛丽塔与亨伯特的亲密关系,于是就有了寄宿学校与夏令营的闹剧。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高度重视儿童时期,认为儿童时期接受能力最强,对后续人格发展影响最大。夏洛特的教育方式实际上使洛丽塔在儿童时期就遭到了遗弃。精神上的无所依靠是洛丽塔对亨伯特产生兴趣的重要原因,这也正中亨伯特的下怀。夏洛特的意外去世更加坐实了洛丽塔的无依无靠,精神创伤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她必须抓住救命稻草,使自己获得金钱、精神,甚至肉体上的支撑。洛丽塔潜在的遗弃情结在这时暴露无遗,这也正是她身边从不缺少男性陪伴的原因,这种陪伴并非爱情,只是一种依赖,是对遗弃情结的一种抗拒与补偿。
如果说家庭因素是造成洛丽塔遗弃情结的根本原因,那么学校与社会监管的缺失则是外部原因。洛丽塔生活的时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病态的美国梦大行其道。洛丽塔对亨伯特的痴迷就部分源自对金钱的渴求。亨伯特让她参加话剧社,带她四处旅行,用金钱满足她的爱好与愿望的目的,就是控制她的精神与肉体。当洛丽塔不想继续不伦之恋,投奔了奎尔蒂时,她发现自己依然是被利用的工具,并没有找到真正的依靠。从家庭的弃儿到社会的弃儿,洛丽塔的遗弃情结愈发严重。
上世纪50年代,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在“教育即生活、学校既社会”[15]的原则指导下,许多机构利用假期开办各种营地活动,许多家长也相信参加夏令营大有裨益。然而营地鱼龙混杂,并非安全的避风港。洛丽塔出于好奇与营地的男孩查尔斯发生了性关系。由于学校监管不力,她没有接受应有的行为教育,缺乏超我道德的约束,表现出的是病态的自我。学校的活动围绕“戏剧表演、跳舞、辩论、约会”进行,忽视道德和精神教育。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缺失使她觉得自己不被人重视,有一种弃儿的感觉,这种遗弃情结成为构成她悲剧命运的重要一环。
(二)恋父情结
恋父情结又称厄勒克特拉情结,弗洛伊德将其定义为“女孩恋父仇母的复合情绪,是女孩性心理发展的第三阶段特点,在这一阶段,女孩对父亲异常深情,视父亲为主要的性爱对象,而视母亲为多余,并总是希望自己能取代母亲的位置而独占父亲。”[16]自幼丧父的洛丽塔从未与成年男性进行过深入接触,母亲也并未告诉她与成年男性接触时应注意什么。亨伯特利用她的无助与无知,接近并利用她,潜移默化地影响她。亨伯特的行为是洛丽塔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正是他的诱导使她渐渐步入歧途。她一次次爱上富有经验的年长男子,不仅是一种恋父情结的表现,也是对黑兹夫人教导她的禁欲思想的一种逆反。与亨伯特的爱情不仅使她生理上早熟,也使她的心理发生重大变化。精神分析理论最为重视的是后天因素给人带来的影响,而在人的整个生命轨迹中,儿童时期是人格塑造的最关键期。不正常的成长与爱情氛围,培养了洛丽塔畸形的恋爱观。她将恋爱和恋父混淆,将依恋和爱情模糊,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心理和行为。恋父情结将她的恋爱观完全扭曲,导致她被哄骗、迷惑、勾引,最终也成为她心理畸形与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五、结论
纳博科夫在接受采访时回应了他的艺术观,他强调小说的虚构性,把写作当成一场文字游戏,并将讽刺效果巧妙地融入创作。小说中的亨伯特虽排斥精神分析学,但在自述时却无意识地强调自己幼时的经历影响了其恋爱对象的选择,多次重复自己被困在了“时间的牢”里。他虽不接受心理医生的疏导,却愿意去精神病机构进行治疗;洛丽塔试图离开恋童癖患者,体验正常的爱情与生活,最终却难产而死。这种矛盾与讽刺不但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也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虽然纳博科夫本人并不欣赏精神分析学,但《洛丽塔》却体现了他对精神分析学无意识的接纳。小说中所谓的“时间的牢”只是一个隐喻,实际上困住两位主人公的是他们在不堪的过往中内心形成的种种情结,畸形的情结导致扭曲的心理,进而导致了悲剧人生。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看《洛丽塔》,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生悲剧,更窥探到了悲剧之后的某些原因,即家庭和社会创伤给人带来的种种情结。情结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在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人的成长,塑造着人的个性。良好的情结促人向上,令人快乐,负面情结使人消沉,甚至让人毁灭。洛丽塔内心深处的不良情结对其悲剧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创伤对人的成长、性格和心理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和谐人格的养成不仅在于家庭,更在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无法释怀少年时期经受的创伤与挫折,为各种不良情结所困,纷繁复杂的社会必定会放大这些情结的危害,给其一生带来重大影响。
——《洛丽塔》的叙事心理学解读
——《洛丽塔》的成长小说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