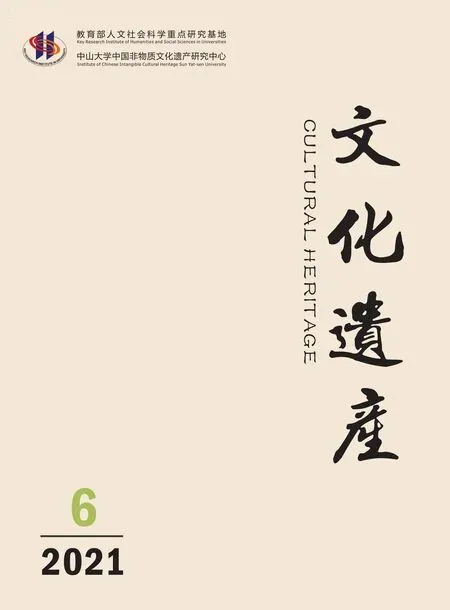《清俗纪闻》的民俗比较意识*
李 宁
引 言
记录我国古代民俗的文献典籍数量众多,历代各种“岁时记”多是此类。但由外国人编写的专门记录我国古代民俗的著作却并不多见。《朝天录》和《燕行录》是古代朝鲜使臣来中国朝贡时对其所见所闻进行的记录,但却不是记录我国明清两代民俗的专书。而日本江户时代出版的《清俗纪闻》则是一部专门记录我国清代民俗的著作。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相当于我国明末至清代的一段时期。该时期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开放长崎一地允许与中国、荷兰进行贸易往来。处于自身利益考量,江户幕府派驻长崎的地方长官中川忠英命当地官吏及翻译官(即所谓“唐通事”)向来日贸易的清朝商人详细调查清朝各类民俗事项,调查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年中行事、居家、宾客、冠服、饮食制法、乃至婚丧嫁娶诸般礼仪等。1799年刊刻出版的《清俗纪闻》即是这一调查的书面记录。
钟敬文(1)钟敬文:《芸香楼文艺论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第3页。、曲彦斌(2)曲彦斌:《〈清俗纪闻〉说略》,《辞书研究》2004年第6期。两位先生都曾向国内引介该书,指出该书在清代民俗研究上的重要价值。书中展现出的两百多年前日本人搜集中国民间风俗情报的广泛与精细程度及其对中国事物的高关注度,也一度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时至今日,以《清俗纪闻》中的民俗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仍不多见。王凌(3)王凌:《〈清俗纪闻〉日本人眼中的清代民俗》,《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11月23日第3版。、徐晓光(4)徐晓光:《〈清俗纪闻〉探赜》,《沧桑》2013年第4期。从总体上介绍了《清俗纪闻》,高薇(5)高薇:《论18世纪日本的中国观——以〈清朝探事〉〈清俗纪闻〉为中心》,《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借助《清俗纪闻》探讨18世纪日本的中国观。真正从民俗细节考察《清俗纪闻》一书的是李宁和马慧。李宁(6)李宁:《〈清俗纪闻〉中的清代汉语和清代民俗》,《文化遗产》2017年第2期。确认了该书所记民俗的地域属性,马慧(7)马慧:《从〈清俗纪闻〉饮食部分诠释东南沿海社会形态——以士绅与普通民众为中心》,《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则专注于该书的饮食风俗。
本文指出,除了“图文并茂”这一特色以外,《清俗纪闻》的民俗记录还带有强烈的比较意识。从书中“他者”的比较视角,读者可以更清晰地体察我国古代民俗的细节和文化内涵,认识某些民俗在东亚文化圈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本文分“清俗与古风”“清俗与日俗”两类探讨《清俗纪闻》中的民俗比较意识。
一、清俗与古风
满清入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大地开始进入漫长的异族统治时期。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实施严酷的薙发改服政策,“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从发式到衣着服饰,甚至饮食、宗教、婚冠丧祭等各种礼俗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满清民俗政策的厉行,对崇尚古礼、笃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中原汉民族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震撼。此时,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等国,通过外交使节、商船贸易等途径,也在第一时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朝鲜王朝表面上向强大的清朝纳贡称臣,其文人士子的内心却以坚守中华正统为己任,贬低满清为夷狄,猛烈抨击民间各种“胡俗”,自称“小中华”。
而日本方面则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崇尚古风、古俗、古礼,承认清代礼俗已经蛮夷化,如《清俗纪闻》黑泽惟直序“夫国于天地而有立焉,日月彝伦推诸四海而无所不准,则奚必华贵而夷贱哉。然必推中国而华之以贵之者,以其三代盛王之所国,而礼乐文章非万国所能及也。”(8)[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方克、孙玄龄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序第3页。这是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圈内典型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又如《清俗纪闻》林衡序“抑夫海西之国,唐虞三代亡论也,降为汉、为唐,其制度文为之隆尚,有所超轶乎万国而四方取则焉。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土风俗尚寘之不问可也。”(9)[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序第1、2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而今斯编所载清国风俗,以夏变于夷者,十居二三……然三代圣王之流风余泽延及于汉唐宋明者,亦未可谓荡然扫地也。则又清商之来琼浦(即长崎)者,多系三吴之人,则其所说,亦多系三吴之风俗,乃六朝以来故家遗俗确守不变者。”(10)[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序第3页。这一贵华贱夷而又留有余地的矛盾心理在《清俗纪闻》的一条条民俗问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即问询者往往十分在意某一民俗事项的古今差异,并如实记录。下面举几例以观之。
(一)冠礼
今之清代,冠礼之古旧仪式已绝世无传。既无男子于几岁加冠之制式,亦无于十三四岁之间视其成长情形庆祝元服(加冠)之事。女子亦无于几岁上笄之仪式。十岁以上之女子一旦许嫁,即上笄。但此日之庆贺并非为上笄,乃意在庆祝许嫁而设酒宴。(11)[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331页。

通过观察,当时负责询问清俗的长崎小吏当然可以推测出清代冠礼已然消亡的事实。而为《清俗纪闻》作序的日本学者士人自然也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当时中国“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的遗憾和对清人“辫发腥膻之俗”的鄙夷。尽管如此,这丝毫没有妨碍编者在“卷三 冠服”按文武、品级将清朝官员的朝服黼子、腰带、帽子上的朝珠以图画的形式逐一细致描绘出来。另外,“卷七 冠礼”篇幅很短,除上面引文外,下文将“剃发”视为加冠(加冠,日文原文为“元服”),介绍了剃发的详细操作方法以及剃发人、剃头店等项,并绘有剃头刀、木梳、竹篦等图像。
(二)绾柳送别
官民均于旅行前四五日,由朋友或亲戚设送别酒宴,此时必有赆仪。官员之间互送银子,商人之间赆送亦皆用银子。民间则送缎匹,而以银子为薄仪。此外,并有携酒肴等送至郊外或船路二三里之遥之行事。采用古时绾柳等故实之事,则已全无。(14)[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55页。
这里记录的是送别时的习俗,有设酒宴、赠送银子、送缎匹等作法。但又特别补充一句“采用古时绾柳等故实之事,则已全无。”绾柳,与“挽留”谐音,又称折柳,是我国古人送别时的一种特别的习俗,今已失传不见。而从《清俗纪闻》这里的记载来看,似乎早在清代,江浙地区折柳送别的习俗就已消失。
据戴明玺(15)戴明玺:《“折柳”的历史演变、文化意蕴和宗教情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诗经》中已有“折柳樊圃”的句子,汉乐府古曲也已有《折杨柳行》,但二者均与离别、送别的意义无涉。折柳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当始于西汉。据《三辅黄图·桥》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16)《三辅黄图》,撰者未详,毕沅校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9页。而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折柳的意象大量进入诗人的笔下,且专门表达离别时的悲愁与相思之义,用于送别的场景。刘禹锡《杨柳枝词八首》“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17)刘禹锡:《刘禹锡选集》,吴汝煜选注,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285页。李白《劳劳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18)李白:《李白诗选》,胡云翼选辑,上海:上海教育书店1948年,第192页。张籍《蓟北旅思》“客亭门外柳,折尽向南枝”。(19)张籍:《张籍集注》,李冬生注,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88页。
历史上,日本曾多次向大唐派出“遣唐使”学习中国文物制度,深受唐文化的滋养。而熟读中国古代典籍、诗词的日本读书人肯定早已对中国折柳送别的习俗耳熟能详,故而在“卷十 羁旅行李”一卷中特别确认一下这一古俗,但却得到了“今已全无”的否定回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和“柳”这两种在中国人看来完全不同的树木,在日语中都训读作やなぎ,二者无别。
(三)授茶
双方允诺两三日后,选择吉日,即天德、月德等吉日。送去下聘书简。此时,将送给女方之茶叶装于小锡罐中,数量约数十罐至一百罐左右不同。不称送茶,而谓之授茶。据传茶可不移植根而结籽,故古人以茶为结婚之礼。此必其遗风也。(20)[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343页。
茶本是中国特有之物。茶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南方产茶区的婚俗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带去的嫁妆中,就有当时的名茶。这可能是我国茶与婚礼联系的最早记载。(21)周衍平:《江南婚俗与红妆茶器》,《茶博览》2014年第1期。元好问《德华小女五岁能诵余诗数首以此诗为赠》“牙牙娇语总堪夸,学念新诗似小茶”,(22)元好问:《元好问诗词集》,贺新辉辑注,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548页。将茶的鲜嫩之貌赋予了少女气息。茶表示少女的纯洁,进而寓意夫妻爱情的贞洁。茶树四季长青,表示爱情永世长青、新人白头偕老。茶树多籽,既可表示爱情绵延繁盛,又寓意多子多福。又明代浙江钱塘人许次纾(1549-1604)《茶疏·考本》中说:“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植子之意也。今人犹名其礼曰下茶。南中夷人定亲,必不可无,但有多寡。礼失而求诸野,今求之夷矣。”(23)楼璹等:《耕织图诗 补农书 北山酒经 笋谱 茶考 茶疏》,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269页。古人认为,茶树只能以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因此茶又象征夫妻之间的爱情坚贞不二、至性不移。
故民间男女订婚,要以茶为礼,茶礼成为男女之间确立婚姻关系的重要形式。茶成了男子向女子求婚的聘礼,称“下茶”“定茶”,而女方受茶礼,则称为“受茶”“吃茶”,即成为合法婚姻。如女子再受聘他人,会被世人斥为“吃两家茶”,为世俗所不齿。
《清俗纪闻》所记“授茶”为清代江南地区民俗。而据了解,至今浙江一些地方仍保留茶礼的婚俗。比如浙西地区“食茶”指媒人奔波于男方女方之间进行说合,而女方答允婚事后则立即给没人泡茶、煮蛋,借助公开的“茶礼”表示许婚之意。(24)唐黎标:《茶杯里的婚俗》,《华夏文化》2006年第4期。再比如浙江南部的畲族在新娘嫁到男方后有“吃蛋茶”的风俗,而在浙江泰顺,新娘的嫁妆除了茶叶以外还要有精美的茶盘,茶盘上装点有山水、花鸟、人物等图案。(25)黎小萍、陈华玲:《茶礼与婚俗》,《茶业通报》2001年第4期。
(四)埋胎衣
胎衣放入小磁罐中加盖包好后,在宅中洁净空地挖掘深约三四尺之坑加以埋置,永远不动。无选择埋置方位及添加物品等事。古时,有与古钱一文同埋之说法,但当时已均不用。(26)[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318页。
胎衣,即胎盘和胎膜的总称,又名胞衣。胎儿于母体中孕育时,胎衣为胎儿提供营养。而当婴儿呱呱坠地,胎衣则无所用处。但由于胎衣与人生命的密切关联,中国汉民族自古以来有埋胎衣的习俗。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古代,生命的诞生与婴儿的成长充满各种未知的危险,稍有不慎就会生病甚至造成夭折。人们迷信可以通过埋胎衣的仪式,保佑婴儿健康顺利地长大成人。
据张静怡(27)张静怡:《汉族埋胎衣民俗初探》,《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古人埋胎衣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秦汉以前。埋胎衣有很多讲究,体现在埋置的时间(吉凶日)、方位、器具、注意事项等方面。据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卷三十五《小儿藏衣法五首》记载:“儿衣先以清水洗之,勿令沙土草污。又以清酒洗之,仍内钱一文在衣中,盛于新瓶内,以青绵裹之,其瓶口上仍密盖头,且置便宜处,待满三日,然后依月吉地向阳高燥之处,入地三尺埋之,瓶上土厚一尺七寸,惟须牢筑。令儿长寿有智慧。若藏衣不谨。为猪狗所食者,令儿癫狂。虫蚁食者,令儿病恶疮。犬鸟食之,令儿兵死。近社庙旁者,令儿见鬼。近深水池,令儿溺死。近故灶旁,令儿惊惕。近井旁者,令儿病聋盲。弃道路街巷者,令儿绝嗣无子。当门户者,令儿声不出,耳聋。著水流下者,令儿青盲。弃于火里者,令儿生疠疮。著林木头者,令儿自绞死。如此之忌,皆须慎之。”(28)王焘:《外台秘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5年,第978页下。
类似此种记有埋胎衣习俗的医书很可能在江户时代以前就已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知。日本人丹波康赖(912-995)《医心方》中就已经引用了我国六朝时期德贞常所著《产经》“藏胞衣断理法”。(29)丹波康赖:《医心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5年,第513页下。而古籍记载中埋胎衣时多有纳古钱同埋的作法,因此调查者在此进行确认,结果得知“与古钱一文同埋”之作法在清代已不见。
而日本也有埋胎衣的习俗,且多埋于生产时的地板下,或者厕所前面、大门等处。在茨城县浮岛一带,有将十二条三寸长芦草和十二粒完整无伤米粒与胎盘一起埋于屋内角落的习俗。(30)[日]中川忠英著,村松一弥、孙伯醇编:《清俗纪闻2》,东京:平凡社1966 年,第59页。滋贺县神崎郡,男孩的胎盘要与笔墨算盘埋在一起;女孩的胎盘则与五彩线、针埋在一起。(31)马兴国、宫田登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5·民俗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9页。从这两例来看,日本埋胎衣往往会另外添加物品,因此负责调查的长崎官吏很可能据此问及清朝商人中国是否也有同样做法。
(五)请城隍庙神像、祀孤
清明期间,各州县均奉敕命将该地城隍庙中之神像用轿请出。自古以来,对曾任知府、知县等官职而有政绩者,逝世后得敕命为该地守护神,并建庙安置,谓之城隍庙。如各地均有该处之城隍为某代某官之不同传说。神像为木制,头部及手足皆可活动。衣冠等则按该人在世时之品级装饰。因处于城隍之间,故称城隍庙……神像前桌子上陈列三牲供物,祭祀已无子孙吊念之亡灵。此谓之祀孤。本官及诸官吏行礼后,众人随之参拜。因知府、知县治理生民,故称阳官,而城隍治理亡灵,故称阴官。城隍之仪仗格式,在府准照知府,在县准照知县。(32)[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26页。
这里记载了请城隍庙神像的习俗,且称“自古以来”就有。请城隍庙神像是中国民间城隍信仰的一种仪式。城隍本指护城河,城隍信仰确实在清代以前就已存在。据范军(33)范军:《城隍信仰的形成与流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城隍信仰起源于远古的土地神崇拜。从三国时期开始,城隍开始向人格神转变,并广泛流行于江南地区。唐朝时, 城隍信仰广泛传播于全国各地。宋初, 城隍祭祀被正式纳入国家官方祭祀大典。明清时期, 城隍信仰更是吸收佛教地狱审判、赏善罚恶的观念, 城隍自此后不仅是城市的保护神, 而且成为阎罗阴司的派出机构的冥官和阴阳两界的司法神。《清俗纪闻》详细记载了清代江浙地区清明节期间请城隍庙神像的具体做法,包括神像材质、衣冠、供品、人物来源、阴官阳官之别等细节内容。
“神像前桌子上陈列三牲供物,祭祀已无子孙吊念之亡灵”的仪式称为“祀孤”。《汉语大词典》词条“祀孤”:“祭祀孤魂。旧时江南民俗,于特定的节日祭祀无人祭祀的死者。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江南城隍庙》:‘每岁中元及清明,十月一日有庙市,都人迎赛祀孤。’”(34)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汉语大词典》第七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第836页。《燕京岁时记》初刊于1906年,它所记载的清代江南祀孤习俗与刊行于1799年的《清俗纪闻》的记载是一致的。这也可见《清俗纪闻》作为清代民俗史料的重要参考价值。查考国内文献及语料库,“祀孤”一词似乎首见于《燕京岁时记》。《清俗纪闻》可以将该词的首次出现提前到18世纪。
(六)东篱赏菊
九月九日为重阳。约会朋友等人携酒食登山,作诗,弄诗竹,终日游玩,是谓之登高。在有菊花之地方,尚有东篱遗风进行赏菊者。(35)[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5页。
清李光地《月令辑要》卷一载“齐景公初置重阳”。(36)(清)李光地等:《月令辑要》,清康熙时期内府四色套印本,第58页右。可见重阳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节日,很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重阳节的习俗有登高、插茱萸、放纸鸢、赏菊、饮菊花酒、食重阳糕、摊煎饼等。《清俗纪闻》记载的重阳习俗有登高、食栗糕、食登糕、天后庙做戏谢神,并特别补充一句“在有菊花之地方,尚有东篱遗风进行赏菊者”。(37)[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5页。
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钟爱菊花,有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38)陶渊明:《陶渊明诗选》,渭卿选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到了唐宋时期,重阳赏菊成为风俗。(39)乔凤岐:《重阳节与重阳习俗演变》,《传承》2013年第9期。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40)王维、孟浩然:《王维、孟浩然诗选》,章池注评,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119页。是千古传唱的名句。白居易《闰九月九日独饮》“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41)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62页。《清俗纪闻》所谓“东篱遗风”即指重阳赏菊、饮酒的习俗。这一记录未必是被调查者主动交待的,而很可能是调查者追问后被调查者被动补充出来的。陶渊明的诗、唐人的诗在日本文人中早已扎根,重阳赏菊符合日本人对重阳节的文学想象。
据刘晓峰(42)刘晓峰:《重阳节在日本》,《文史知识》2010年第12期。,重阳节在唐代就已经传入日本,且其风俗与菊花密不可分。平安时代的皇室贵族常常举办菊花宴。到了江户时代,重阳节是日本“五节句”即五大节日之日,且被称作“菊之节句”,人们饮菊花酒、食板栗饭,祈愿长寿。
如上述几例所示,在《清俗》的民俗调查记录中,诸如“古时”“古代”“古礼”“遗风”“自古”这样的字眼随处可见。这充分显示出日本知识界对清代以前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江户时代的日本闭关锁国,日本人无法出国,对中国风俗的了解只能通过询问来日的中国人得知。但实际上,在清商到访日本长崎之前,中日两国已有了至少千余年的文化交流。很多中华风俗传入日本,有的甚至扎根日本,成为日本风俗,如加冠(日本称元服)、埋胎衣、重阳饮菊花酒登高。有的风俗虽未进入日本社会,但日本士人也已通过阅读中国典籍有所了解。换句话说,调查者们对中国民俗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这些储备均来自清代之前的“古代”。
正如《清俗纪闻》黑泽惟直序所说“我东方古昔盛时,聘唐之舶留学之员传乎彼而存乎此者,乃皆三代圣王之礼乐。则今日民间通行礼俗有不与彼变于夷者同也。”(43)[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序第2页。出于“华贵夷贱”的文化优越感,调查者屡次确认某一古代风俗是否尚存,某一风俗是古代遗风还是清代新俗,某一风俗是否合于古礼。又如:“结婚后一个月左右,有新娘回娘家归省之事。此时,须赠送各种礼物以做为人事……此为古代归宁之遗风也。”(44)[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386页。“古时有八岁入学之说。”(45)[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278页。“每七请僧道诵经吃斋之事为古礼所无,乃时兴风俗,当时全国均如此。”(46)[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61页。“无虞禫之祭。”(47)[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99页。
二、清俗与日俗
在将清代民俗与“古代”民俗相比较的同时,《清俗》在记录相关民俗事项的时候还常常提到与之相应的日本民俗,或指出清国无日本某某民俗,或以日本某物比况清国某物,指出清代民俗与日本民俗的相同与差异之处,有意识地对二者进行比较。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中日民俗比较有约五十处左右。下面我们将这些清日民俗比较大致分饮食习惯、居家生活、佛教等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饮食习惯
日本人过年有吃杂煮(ぞうに,即烩年糕)的习惯,但清代中国“无日本在年初时食用之杂煮汤一类食品”。(48)[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6页。日本人早餐喜吃鱼,但清俗“早饭多食粥及干菜、酱瓜、干萝卜等菜。鱼、肉菜类则只用于午晚餐”。(49)[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270页。日本人吃米饭喜欢将麦粒与大米一起煮食,但清俗“一般村落小户,多食用混有多种谷物菜蔬之饭。其中,麦饭为煮饭之际在水尚未干时放入面粉,于锅内搅拌焖蒸后食用。分量虽有不同,但无将整麦粒混入饭中之事。此外,根据时令尚有混加大豆、小豆、黑豆、粟、黍等炊煮食用之事。市中之人除极下贱者外,无食用此种食物者,即使从事力作者,亦吃米饭。”(50)[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271页。日本茶碗一般无盖,但清俗“通常茶碗均为盖碗”。(51)[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159页。日本实行分餐制,各人吃各人的饭菜,各人有各人的碗筷菜碟,但清俗“无各人单独之菜碟”。(52)[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06页。
当然,在饮食方面,中日两国也有相通之处。如“卷四 饮食制法”详细记录了豆豉的制作方法,并特别注明“豆豉,日本称之为纳豆。”(53)[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254页。中国的豆豉和日本的纳豆均为大豆发酵制品。豆豉在汉朝的《史记》中已经出现。(54)《史记全本新注》(全五册),司马迁著,张大可注释,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222页。豆豉随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后,被改造为纳豆。现代科学(如李里特等(55)李里特、张建华、李再贵、辰巳英三:《纳豆、天培与豆豉的比较》,《中国调味品》2003年第5期。)认为,豆豉和纳豆并不相同,二者在生产工艺、使用的菌种和发酵参数方面各具特色。但《清俗》的编者认为中国的豆豉和日本的纳豆没有区别。
另外,日本在宴请宾客时礼仪繁多,故而在调查清商时也问得十分细致。卷九名为“宾客”,详细记录了从下帖请客、陪客、厅堂摆设到宴席规矩、宴席进行顺序、座位顺序等各个步骤和细节,甚至妇女酒宴、如何应对吊丧来客等也有记录。而很多日本待客习俗在中国是没有的,这在《清俗》中均有记录。如关于请客,“无由宾客方面在宴会前派人或自己前往道谢之事”。(56)[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390页。关于宴席上的规矩,“无喝汤之后再吃肉之事。于开始时喝汤,系失礼之举。……对整烤煮烤之菜肴,无自何处下箸、何处开吃吃用之规定。在上点心及其它品种时,亦无由上宾向陪客寒暄之事。”(57)[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00页。“客人来到时,主人须更衣,戴帽。一般均穿着新做之华丽衣服,宾主均无另外之礼服,亦不拘颜色。”(58)[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02页。关于上茶,“仆人将茶逐碗端出。茶是将茶叶放入茶碗中,浇入热水盖上盖子而端出。无以茶壶沏茶斟给客人之事,亦无浓茶、淡茶之固定制式。”(59)[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04页。关于收席后解手,“洗手时客人自身站立,将手放入面盆中洗,无有仆人在旁浇热水之事。每人洗后,仆人即更换热水,使众人依次洗手。但均不漱口,更无用酒漱口之事。”(60)[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07页。
(二)居家生活
“卷二 居家”讲到居家之构造,“距大门以内约两三间处建有仪门。仪门内建有类似日本之玄关式样之一间宽敞房间,来客时于此处接待,称为厅堂。又名外厅或公堂。”(61)[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65页。这里将中国用于待客的厅堂比作日本的玄关。再如楼房,“苏州、杭州等地,城里城外临街房屋均是楼房。大致上与日本住房相似。”(62)[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109页。关于冬季取暖,指出清代风俗一般使用手炉、脚炉,“亦有类似日本‘被炉’之式样建于地上之地炉、石炉者,但南方温暖地方不使用此种火炉。”(63)[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158页。关于女孩发型,“至十岁左右将额前之头发剪成约五六分长的披发,披散于前额,如日本之‘切秃’式样。”(64)[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324页。又比如指出“皂隶,类似日本之‘足轻’”。(65)[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168页。
凡此种种,皆是用日本的相关事物来比况中国事物。
至于中日两国在居家生活方面的差异之处,则有以下记录。日本人酷爱干净,有每日泡澡的习惯,至今而然,但清俗“历本中列有汤沐之日及剃头之日。夏天隔三四天、四五天入浴以此。绝无每天在热水中沐浴之事。”(66)[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157页。另外,官员至民宅之时,“无更换靴子之事”。(67)[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18页。
(三)佛教
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以后,逐渐融入日本社会,带上了日本色彩。现代中日两国的佛教领域在很多风俗上有较大差异。《清俗》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些差异在清代就已存在。日本僧人可以娶妻、吃肉,但清俗“禁止僧侣娶妻。但亦有名为应付僧者,虽不娶妻而吃肉,居住于市中,承接在家中举办佛事诵经等。”(68)[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562页。日本寺庙前一般有洗手处,但清俗“寺中多不设水盥,故于家中洗手后前去。”(69)[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3页。日本古代寺庙往往与国家或地方政治界关系密切,但清俗“僧侣如不受天子之招,绝无至朝廷之事。因此,既无于文武官员相当之品级,亦无由官方给各寺领地之事。由官方施舍田地等事,亦极少见……无总寺、末寺等制度。”(70)[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521页。且“无有类似日本之僧正、檀林等名义官位及红衣、紫衣、触头、独礼等品级。”(71)[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522页。“无专供官员祈祷之指定寺院。……无由寺院向天子、各官衙献上护摩、神阄、护符之事。”(72)[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547页。在僧人穿着方面,清俗“禅宗穿着法衣袈裟。无类似日本挂络之物。”(73)[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524页。
另外,日本人死亡时一般请僧人做法式超度,但清俗“无在死去时到寺庙申报请僧,或送葬时送至寺中以及僧徒来送丧之事。”(74)[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第461页。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日本不少风俗礼仪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日本很多民俗仍然拥有自己的特色之处。《清俗纪闻》一书旨在记录清代江南浙江一带的风俗习惯,但却在很多地方有意识地与日本本国风俗相互比较。如果说将清俗与古风比较是日本人受中华文化圈“华夷之辨”思想影响的产物,那么其清日民俗之比较原因何在呢?
正如曲彦斌先生(75)曲彦斌:《〈清俗纪闻〉说略》,《辞书研究》2004年第6期。所指出,长崎长官中川忠英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编纂、刊刻《清俗纪闻》一书是有其功利性目的的。一方面,通过详细记录清代民俗的《清俗纪闻》一书,使新担任清日商船贸易管理职务的长崎小吏了解清商老家的风俗习惯,以便“审其风俗,明其好恶,察其情伪”,(76)[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序第5页。从而更好地管理来日贸易的清朝商人,服务于中日贸易的实际事务。另一方面,德川幕府实行闭关政策,日本人不得出国,长崎成为日本仅有的对外交流的窗口,通过编纂《清俗纪闻》一书,也可以为当时的普通日本人了解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提供便利。这样,考虑到该书的读者是长崎贸易小吏和对中国事物感兴趣之人,其大量的清日民俗比较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现代中国是清代中国的延续,而现代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也直接承袭了江户日本的习惯。《清俗纪闻》中关于中日两国民俗相同和差异之处(尤其是差异之处)的记载大多延续到今天。如日本人早餐喜吃鱼,而中国人早餐多吃粥;日本人喜吃麦饭,甚至配以捣碎的生山药放入米饭中共食,中国人到日本旅游时视为新奇;日本自古至今实行分餐制,而中国到了清代早已是合餐制;日本人酷爱泡热水澡的习惯和进门前脱鞋等风俗在江户时代就已存在。这一方面说明了民俗活动具有鲜明的国别性、地域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民俗作为人类的习惯性生活行为,具有高度的稳固性和传承性。
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两百多年前日本官方组织编写的一部专门记录我国清代江浙一带民俗的著作,《清俗纪闻》的记录和编写带有强烈的民俗比较意识。明清鼎革之际弥漫整个中华文化圈的“华夷之辨”思想促使编者关心清俗与古俗的差别与联系,而向负责清日贸易实务的日本官吏和对清朝事物感兴趣的日本民众介绍外国民俗,则成为其清日民俗比较的重要原因。
从这些随处可见的清俗与古风、清俗与日俗的比较描写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编者强烈的日本主体意识。从这一“他者”的比较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反观我国古代民俗的细节和文化内涵,认识某些民俗在东亚文化圈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了解当代某些中日民俗差异的历史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