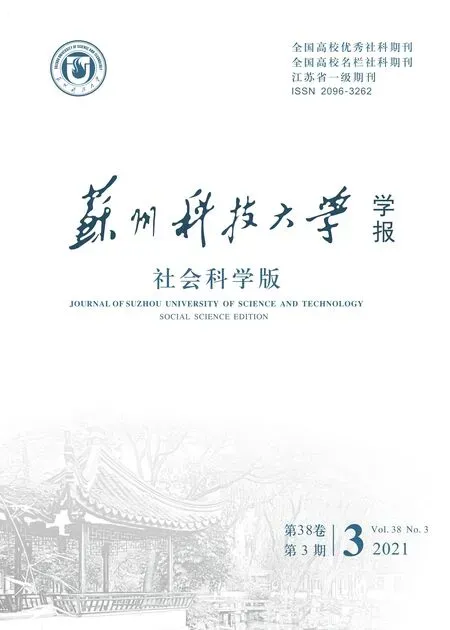高启辞官原因新论*
刘召明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高启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众多待解的疑问,如高启的死因、高启为什么辞官、高启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等。其中,探究高启辞官的原因,对于深刻揭示高启的死因有直接的启发作用,对于厘清高启的生平行迹、深入研究高启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一
关于高启辞官的原因,考察历来文献资料,可概括为以下四种。
(一)“年少未习理财”说
此说来自高启的自述。高启《志梦》载:“至(洪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暮,出院还舍,有控马驰召余二人,上御阙楼俟焉。既见,奖谕良久,面拜启户部侍郎、玄懿吏部郎中。启以年少未习理财,且不敢骤膺重任,辞去。玄懿亦辞。上即俞允。各赐内帑白金,命左丞相宣国公给牒放还于乡。”[1]945
《明史·高启传》采纳了高启的自述:“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2]732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在此基础上又加上“孤远”的原因:“三年七月廿八日,与史官谢徽俱对。上御阙楼,时已薄暮,擢户部侍郎,徽吏部郎中。自陈年少不习国计,且孤远不敢骤膺重任。徽亦固辞。”[3]“孤远”的原因未出现于明人笔下,当是钱谦益的个人判断。汪端《明三十家诗选·高启小传》沿袭“孤远”的原因:“三年秋,太祖御阙楼召对,擢户部侍郎,以孤远不敢骤膺重寄辞,乞放还于乡。”[1]1029
(二)“用人不当”说
晚明文震孟从朱元璋选人用人的角度,认为高启辞官的原因在于朱元璋所用非人:“国家官人,当视其才。如高先生之材,宜为翰林,不宜为户部。其以不习握算辞,可谓允矣。”[4]这与高启“未习理财、难膺重任”的观点相当,只是分析角度不同。
今人史洪权则结合高启为户部侍郎之前的三任户部尚书无一幸免于贬谪的命运,认为高启辞官的主要原因在于“户部侍郎一职既高且险,除坚辞不受之外,他别无选择。……朱元璋对高启不惜高位,却不能用其所长,展其所能,致使后者全身而退,这只是君臣难以遇合的又一典型”[5]。
(三)“避祸”说
晚明黄景昉认为:“高季迪编修辞户部侍郎之擢,力请罢归,意但求免祸耳,非有他也。卒死魏观难。时方严不为君用之禁,其肯为山林宽乎?高归,不能秽迹深藏,若袁凯然,顾炫才援上,宜其及矣。”[6]他认为高启辞官在于免祸,而且非常肯定(“非有他也”)。陈田也持相近意见:“入史馆后骤擢户部侍郎,以不能理天下财赋力辞。盖亦有托而逃。观其《京师寓廨》诗云‘拙宦危机远’,其志可见矣!”[7]陈田从“避祸”的角度揭示了高启辞官的真正原因是“有托而逃”,与黄景昉的观点基本一致。
(四)“不合作”说
钱伯城先生认为,“从一开始,高启对这次带有强迫性的征召,内心就是抵拒的”[8],“明太祖之所以蓄意要把高启置于死地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乃是高启作为当时东南地区士大夫阶层一个代表人物同张士诚政权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明朝政权的依违态度。后者似乎尤为重要,依违态度说到底就是不合作态度。这对一个刚建立的新政权来说,是不能容忍的”[9]。蔡茂雄也同意“不合作”说:“高启是位心细的人,他了解自己坚辞户部侍郎,是不跟明太祖合作的举动,可能因此招来祸害,所以处处小心。”[10]宋云彬则把高启“不合作”的原因归结为“遗民情结”:“他为了一篇《上梁文》,竟受腰斩的酷刑,其间必有远因在。他当元末,不做张士诚的官,屏居乡村,吟咏自得。入明后,力辞户曹,去之唯恐不速。他对于新朝,没有多大情感,而对于旧朝却颇有些《黍离》《麦秀》之感,在他诗里常常可以见到的。”[11]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诸说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彼此有较强的关联性,如“未习理财”说与“用人不当”说、“不合作”说与“避祸”说。诸说基本上是结合有关史料记载做出的推断,并没有结合高启在南京期间的诗歌创作对其生活与精神状态进行分析,因此在辞官原因的揭示上或与实际情形有一定的脱节之处。
二
从高启在南京的时间线看,其仕途之路非常顺利,可以说是一路升迁,“超秩”提拔。高启洪武二年(1369)正月赴京修史,八月《元史》书成,之后在内府教胄子;次年正月授开平王二子经,二月为翰林院编修,七月为户部侍郎。
按照一般的事理、情理逻辑,高启的仕途一帆风顺,深受帝王眷顾,又无其他意外发生,怎么会在被委以重任时辞官还乡?笔者以为,要寻找其中的原因,还要通过深入分析高启在此期间的诗歌创作,准确把握其真实的心理状况,找到合乎逻辑的答案。
从洪武二年正月赴京修史到洪武三年(1370)七月辞官,高启在南京的时间仅为一年半。其辞官的原因或隐藏于这一有限的时间段之内。据笔者统计,高启在南京期间的诗歌创作数量至少有195首。①笔者据金檀《高青丘年谱》、陈建华《高启诗文系年补正》、贾继用《吴中四杰年谱》等统计。据谢徽等人的记述,高启在此期间的诗歌创作结集为《凤台集》,但未见单本刊刻流传。这些诗歌的内容类型与数量大致如下:赠答诗79首,自述诗58首,写景纪游诗19首,咏物诗16首,题画诗6首,台阁体诗13首,咏史诗4首。高启在南京期间的赠答诗数量最多,占此期诗歌总数的40%。这与他身处帝都京师、人际交游广泛、官员流动频繁有很大关系,如高启诗云:“群材萃京师,有若奔海川。”(《送王哲判官之上党》)[1]282高启在南京期间创作自述诗58首,占此期诗歌总数的30%,则又说明除应酬性的赠答唱和外,高启常以自述诗记载在南京时的个人际遇感受。
笔者检索这195首诗发现,涉及表现仕宦痛苦、抒发客愁离忧的诗歌有60首,占此期诗歌总数比例竟高达31%!其中以自述诗为主,少量存在于赠答诗、咏物、写景纪游诗中。而恰恰是这些私人化的写作与表达,更真实地反映了高启在南京期间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概而言之,宦情忧苦与客居乡愁是高启在南京期间私人化诗歌创作的主题,这些诗歌主要表现诗人仕宦生涯的痛苦,对家乡与亲人的思念。
在京师期间,高启虽有参与修史的荣耀,有陪谒君王的自豪,也有与同僚唱和的欢愉;但他对按部就班的仕宦生涯是极其厌倦的,内心是痛苦无奈的。为了上朝,他不得不早起整装,踏霜雪,冒严寒,穿越京城:“正冠出门早,杳杳钟初歇。嘶骑踏严霜,惊鸦起残月。逶迤度九陌,窈窕瞻双阙。长卿本疏慢,深愧陪朝谒。”(《晓出趋朝》)[1]288而风雨中上朝更让他苦不堪言:“漏屋鸡鸣起湿烟,蹇驴难借强朝天。”(《风雨早朝》)[1]759如果遭遇极端天气,则让他感觉毫无尊严:“朅来京师每晨出,强逐车马朝天阍。归时颜色黯如土,破屋暝作饥鸢蹲。”(《京师苦寒》)[1]413《早出钟山门未开,立候久之》《早至阙下候朝》则表达了他在等待上朝时的疲惫与无聊。仕宦南京的上朝生活令高启痛苦不堪,他的自由个性与森严刻板的朝廷秩序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这种精神上的痛苦经历甚至在高启辞官归乡后仍挥之难去:“昔年霜街踏官鼓,欲与群儿走争疾”(《晓睡》)[1]347,“却忆候东华,朝衣寒似水”(《睡觉》)[1]293。这为我们深入了解高启辞官归乡的原因提供了注脚。
如果说高启仕宦生活的痛苦源自其个性中对闲适与自由的追求,那么他对家乡、亲友的思念则来自仕宦南京的漂泊客居之感。
修史完毕后,高启从天界寺迁往钟山里。虽有乔迁新居之喜,他却道“谁言新舍好,毕竟未如归”(《自天界寺移寓钟山里》)[1]474-475。他一心所想的,是“不如早上乞身疏,一蓑归钓江南村”(《京师苦寒》)[1]413。在送人入吴的赠答诗中,高启常借以抒发对家乡的强烈思念之情,如《送葛省郎东归二首》其二:“桃叶渡头闻唱歌,孤帆欲发奈愁何!君归是我来时路,山水无多离思多。”[1]740在送行之后,高启对家乡与友人的思念更加凄苦悲凉:“别时酒忽醒,客去唯空舍。风雪雁声来,寒生石城夜。遥忆渡江船,正泊枫林下。”(《送周四孝廉后酒醒夜闻雁声》)[1]279另外,在《送金判官之吴江》、《送葛省郎东归二首》(其一)、《送陈四秀才还吴》等送行诗中,高启也都表达了难以排遣的思乡之情。
高启对家乡的思念往往与吴中风物相系。在南京期间,他无心赏花:“两年京师不见花”(《江上看花》)[1]315,但他却对故园的花非常怀念:“想见故园初到处,窗前梅发又新年”(《送人之娄江》)[1]837,“帝城春雨送春残,雨夜愁听客枕寒。莫入乡园使花落,一枝留待我归看”(《夜闻雨声忆故园花》)[1]738。《吴中亲旧远寄新酒二首》《京师尝吴粳》《闻人唱吴歌》则表现了品尝家乡特产、听闻吴歌勾起的思乡之情。
另外,无论独处孤坐,还是与朋友相聚,高启总难以摆脱对家乡的思念:“不是羁人是木肠,怕愁不敢易思乡。醉来独灭青灯卧,风雨从教滴夜长”(《夜雨客中遣怀》)[1]768,“逢君共把金陵酒,忘却今朝在异乡”(《寒食逢杜贤良饮》)[1]780。《客舍雨中听江卿吹箫》《蛩声》《夜坐天界西轩》《寓天界寺雨中登西阁》《春来》《寺中早秋》《四月朔日休沐雨中》《清明呈馆中诸公》《京师寓廨》《至日夜坐客馆》等诗都表达了他客居京城度日如年的思归之情。
高启的客愁除了对故乡的牵挂,还包括对亲人的思念。高启与妻子周氏伉俪情深,除南游吴越与仕宦南京外,两人未曾长久分离。应召赴京修史是高启一生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尽管高启一度感到荣耀,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亲情始终居于首位:“佳征岂不荣,独念与子辞。”(《召修元史将赴京师别内》)[1]274所以,赴京前他流连不舍:“几向江头买去船,自嗟行计日流连”(《赴京留别乡旧》)[1]663,“只愁使者频催发,不尽江头话别情”(《被召将赴京师留别亲友》)[1]637。这些诗作真实反映了高启出发前的心理活动。赴京途中,高启更为离别亲人、家乡而伤感痛苦,于是不停地写诗寄情,作有《将赴金陵始出阊门夜泊二首》《晓出城东门闻橹声》《舟次丹阳驿》等。
高启在南京期间写了许多表达相思别离之苦的亲情诗。刚到南京一个月,高启作《离江馆一月有感》:“忆得离家一月期,天边明月半圆时。遥知此夜闺中望,比着他宵分外悲。”[1]785为了抒发对家人的思念之情,高启深夜在天界寺写家书:“谁怜古寺空斋客,独写家书犹未眠。”(《夜写家书》)[1]816他收到妻子来信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风从故乡来,吹诗达京县。读之见君心,宁徒见君面。”(《答内寄》)[1]280见字如面、倾情倾心的亲切让高启倍加思念妻子。另外,《客中忆二女》《仆至得二女消息》则表达了对女儿的思念与怜惜之情。
由上可以看出,高启是一位非常珍视人伦亲情、留恋故土乡梓的诗人。客居京华的孤独与寂寞、无聊与痛苦令高启厌烦倦怠,度日如年。即便家人至京后,高启思乡欲归的迫切心情也未消失:“但忧兄姊尚远隔,言笑未了仍歔欷。何当乞还弃手版,重理吴榜寻渔矶。”(《喜家人至京》)[1]390然而,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辞官归乡:“几度欲归归未得,空弹长铗和高歌。”(《客中述怀》)[1]664
应当说,这些表现仕宦痛苦与客愁离忧的诗歌反映了高启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暗示了其仕宦南京时期的心理活动指向:辞官归乡。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宦情忧苦与客居乡愁是高启辞官归乡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三
高启是一位真诚的诗人,其诗歌创作往往是他内心活动与情感指向的真实反映。这是我们由诗歌作品分析其辞官原因的基本依据。
作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缶鸣集序》,应当是高启最早的诗学理论表述。在该序中,高启曰:“古人之于诗,不专意而为之也。《国风》之作,发于性情之不能已,岂以为务哉?”[1]906而作于洪武三年(1370)的《独庵集序》中,高启更明确指出“意”为“诗之要”:“意以达其情……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1]885在高启看来,诗歌并非美刺或教化的工具,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与真实表现。“他认为诗歌的功用在于抒发性情,歌吟自适,也不谈什么厚教化、美人伦之类,与理学家的诗论形成鲜明对照。”[12]
与高启同时赴京修史、同官翰林、同任新职、同时辞官、同舟返乡的同郡好友谢徽在《凤台集序》中说:
忆予被召修《元史》,与季迪同至京师,居史局者数月,又同入内府教西学弟子员。今遂同官翰林为史属,顾惟出处之际,盖未尝一日不与季迪同。而凡身之所历,目之所寓,发而歌诗,则有不可得而相同者,季迪虽有教余而终不能如季迪之能言也。[13]
依谢徽对高启的观察与了解,高启在南京期间所表现的人事、情感都是真实可靠的,是“身之所历,目之所寓,发而歌诗”。因此,依据这些诗歌,对高启辞官原因的探究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高启是一个追求自由个性、不愿受任何拘束的诗人,如其诗云:“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池上雁》)[1]151被迫应召赴京后,高启再也无法像他作《青丘子歌》时那样,在诗中表达对自由个性的追求与豪放不羁的性格;再也不能毫无顾忌地酬唱赠答、诗酒风流,他不得不在日常的私人化写作中表现被压制、被束缚的痛苦情感。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高启归乡后的诗文中感受到他尽享闲适的愉悦心境,进一步理解其辞官的原因。
高启辞官归乡后,虽然北郭诗友四散飘零,交游酬唱大大减少,但他深切体会到辞官带来的安闲、慵懒与舒适。快到家乡时,“江净涵素空,高帆漾天风。澄波三百里,归兴与无穷”(《至吴松江》)[1]292。回到家乡后,“闲人晴日犹无事,风雨今朝正合眠”[1]759,“休轻一枕江边睡,抛却腰金换得来”(《雨中晓卧二首》)[1]760。另外,《始归田园二首》《晓睡》《睡足》《示内》《晚坐南斋写怀二首》等都表现了高启经历压抑痛苦的官宦生涯后放松自我的真实心态。
有学者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应当注重生活史、心灵史的研究,以充分了解作家真实的生活状况与精神世界。[14]结合高启的诗学理论及其归乡后享受闲适与亲情的诗歌创作,可以确定高启在南京期间的诗歌创作完全基于其自身的真实感受与真情实感。因此,宦情忧苦与客居乡愁可以作为高启辞官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之前相关研究所没有重视的。
四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几种辞官原因,笔者结合有关资料,试作简评如下。
高启托辞“年少未习理财”,是否属实?高启时年35岁,固非年老,但已不再年少,正是担当大任的盛年。高启虽然没有专习理财,但他是追求事功、抱负远大的治国理政之才,以其能力而言,完全可担当重任。
在《送刘侯序》中,高启写道:
昔吴之富擅南服,其属邑旁郡,亦号蕃庶。自窥西疆相望残毁,而松江以东,一柝之警不起,民恬物熙,独保完实,斯其民亦幸矣。然数年间,军旅之需殷而赋敛之役亟,彼创残疲羸者,既不可以重困,则凡有所征,舍兹土奚适哉?故刍粟者往焉,布缕者往焉,朝驰一传需某物,暮降一符造某器,输者属于途,督者杂于户,地虽未受兵,而民已病矣。于是怨咨之声流,刻弊之形见,视他邑之民,虽葺破垦废,而泰然田庐中,无发召之劳,无课责之苦,反若有不及者。吁,其幸乃所谓不幸欤!今太尉知其然,慨然思得良吏以抚循之,而刘君获在选焉。[1]895
可见,高启虽未专习理财,但对地方赋税、田地、户籍等了如指掌。另在《送蔡参军序》《送江浙省掾某序》《送黄省掾之钱塘序》等序中,都可看出高启施政一方的谋略与才干。
高启自幼饱读史书,“无书不读,尤邃于群史”[1]1029,对历史、时局、人事洞察深刻。高启深知历代政治统治得失,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深刻的治国理政识见。如在《威爱论》中,他强调治军、治国当威爱并行、相兼并济的重要性:“或又曰:然则威可以无爱矣乎?曰:何可以无爱也?专爱则亵,亵则怠;专威则急,急则怨。怨与怠,其败一也。故爱而恐其至于怠也,则摄之以威而作其气;威而恐其至于怨也,则济之以爱而收其心。爱非威恩不加,威非爱势不固,威爱之道,所以兼施并行而不可偏废者也。虽然,岂特为将之事哉!使国君而知此,则国可以治;天子而知此,天下可得而理矣。”[1]848-849在《四臣论》中,他认为善治之国必需四类大臣:“社稷之臣、腹心之臣、谏诤之臣、执法之臣。”[1]849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他洞察深刻,义正辞严,字里行间透出治国理政的卓识远见。这种眼光与见识源自高启对历史人事的熟稔、对历史进程的深刻思考,非一般人所能及。
由此可以看出,高启既不是迂腐空谈的书呆子,也不是只会舞文弄墨的风流诗人,而是关心时事、富有谋略、精通理政的才干之士。以高启之才出任户部侍郎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据《明史·职官志》,户部有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2]1739高启授侍郎一职,只是协助尚书,并非主持户部全局。钱穆也认为高启辞官难以自圆其说:“季迪之自身乞退,则仍不能圆其说。年力尚强,又无老亲,乃必一意而求去,是非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乎?在下者相率以求退之大义要其上,乃使在上者积忿内蕴,明祖之礼士甚至,而其待士也甚酷。而季迪之终以盛年乞退牵累受极刑,惜哉惜哉!”[15]
曾有人提出高启辞官的时间节点问题:“如果高启一意拒绝与朱元璋合作,那么选入西清授经、擢任翰林编修皆是很好的辞官机会,可是高启并没有如此选择。究其原因,除用世之心不死外,朱元璋的恩宠也使他很难就此拂袖而去。”[5]其实,这一问题也并不难理解。《元史》修成后,“老病者,则赐归于乡”(《天界玩月有序》)[1]286,而高启并不符合条件。作为精通经史的儒学之士,高启在被选入西清授经、擢任翰林编修之时,正是人尽其才,同样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所以,在被任命为户部侍郎时,他才以“年少未习理财”这样貌似正当的理由辞官。
关于“用人不当”说。洪武初年,朱元璋一改元朝重吏轻儒的风气,以儒治国,尊儒重儒,招贤纳士,“或言刑名钱谷之任,宜得长于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狯,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16]。朱元璋胸怀宏图,求贤若渴,下诏征贤,为历代开国所未见,致使“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明史·选举志》)[2]1712,“隐者之庐殆空”(《送徐先生归严陵序》)[1]882。但是,朱元璋对儒士委以重任的结果是“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明史·叶伯巨传》)[2]3991,以致很多儒士无法胜任。官员迁转变更速度非常之快:“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为不多,所任名位不为不重。自今数之,在者有几?岂不深可痛惜乎!”[2]3995叶伯巨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所为求治太速之过也”(《明史·叶伯巨传》)[2]3995。用人不当是洪武初年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职位都用人不当,也不意味着高启在户部侍郎的位置上一定做不好。高启以“年少未习理财”为辞官理由,貌似合乎自身实际,但其心底是否别有考量,则属另一问题了。这也正是后人从不同侧面探究其辞官真实原因之所在。
“避祸”说有一定道理,却值得进一步商榷。虽然洪武一朝重典治乱,但是洪武三年(1370),重典惩儒、文人遭难罹祸的例子未见史载。相反,朱元璋继续下诏求贤,“诏求贤才可任六部者”,“诏守令举学识笃行之士,……命有司访求通经术明治道者”(《明史·太祖本纪》)[2]23-24。事实上,洪武年间文人的处境自洪武六年(1373)《大明律》正式更定后才逐渐恶化。建文帝即位后曾谕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明史·刑法志》)[2]2885洪武九年(1376),叶伯巨上书:“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禄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明史·叶伯巨传》)[2]3991这说明文人的处境与心境较之前已发生改变。到洪武十八年(1385)时,朝廷发布10条“大诰”,其一为“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明史·刑法志》)[2]2885。从此时起儒士处境异常严峻,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没其家。从这一时间线索看,洪武三年(1370)儒士的处境还比较安全,高启辞官以求“避祸”的可能性不大。另据统计,洪武二年(1369)八月《元史》修成后,参与修史的29人中除3人不知所终、9人接受官职外,有17人请求辞归。徐大年后又参与纂修《礼书》,书成再次请辞,高启曾为之作《送徐先生归严陵序》。因此,就高启洪武三年七月辞官时的情形而言,朱元璋尚未“严不为君用之禁”。至于高启对未来是否有隐忧,还不能完全排除。
“不合作”说事实上是其他诸说的表现。明代至今,说高启不合作的原因,或是“年少未习理财”;或为“用人不当”;或在“避祸”;或在于高启同张士诚政权的密切关系,对元王朝的“遗民情结”。事实上,高启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前密而后疏,前热而后冷。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称“吴王”前,高启曾多次歌颂其仁政,但在其称王后,高启未再有颂扬文字。高启在张士诚政权被灭后为晋陵徐君所作《野潜稿序》中说:“当张氏擅命东南,士之抠裳而趋、濯冠而见者相属也;君独屏居田间,不应其辟,可谓知潜之时矣。及张氏既败,向之冒进者,诛夷窜斥,颠踣道路,君乃偃然于庐,不失其旧,兹非贤欤?然今乱极将治,君怀负所学,可终潜于野哉?”[1]881高启认为张士诚称王是“擅命东南”,这与他始终以元为正统的观念一脉相承。张士诚政权灭亡后,高启虽有《吴城感旧》《兵后出郭》等诗抒发关于朝代更迭、人事代谢的感慨,但他更关心的是天下治乱、苍生百姓,而非同情一族一姓之兴亡。而且他认为明朝兴起是“乱极将治”,可见其对新王朝充满期待,甚至高启辞官后,在诗文中也一直对朱元璋歌功颂德。另外,《高青丘集》没有一篇怀悼元政权的诗文。因此,高启对元朝的遗民情结根本不存在,“不合作”说的立论基础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