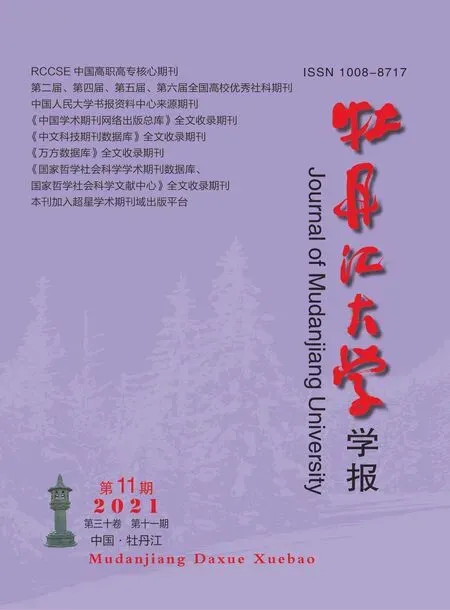人生为本,艺术至上
——《地狱变》与《道连·格雷的画像》时空叙事之比较
贾思敏 祁晓冰
(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芥川龙之介(1829-1927)是日本新思潮派代表作家,因其短小精悍又针砭时弊的语言风格,对社会现实及复杂人性的犀利刻画,被称为“鬼才”。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以短篇小说居多,早期作品多历史题材,《地狱变》就是其中之一。小说故事发生在堀川府,堀川大公留下众多遗闻逸事,其中“地狱变”屏风最为凄厉吓人。画师“良秀”性格怪异,恃才傲物,为创作“地狱变”屏风,频繁对弟子们施暴,以记录弟子们的狼狈和恐慌,甚至还要求大公准备一幕火烧活人的场景,未料大公却将良秀女儿作为火烧对象,认出自己女儿的良秀惊恐万分,但旋即对地狱屏风的执念让他却转悲为喜,在目睹了女儿被活活烧死的惨烈场面之后,他圆满完成了地狱屏风,之后悬梁自尽。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是爱尔兰唯美主义作家,《道连·格雷的画像》是其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俊美的贵族少年用灵魂交换青春的故事。画家贝泽尔因道连·格雷的美貌为其画了一幅画像,格雷惧怕自己的美不如画像永恒,决定用灵魂交换为代价让自己的容貌定格于画中的样子。在格雷的每一次堕落之后,他的肖像就会变得狰狞和丑陋一些。最后格雷企图把已经丑恶至极的画像销毁,却正好刺中了自己的灵魂,这时,丑恶出现在格雷脸上,而艺术肖像却恢复永恒的俊美。
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和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都与艺术至上思想有关,两部作品都通过对人生与艺术的探讨,反映作家对人性以及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思考。两部作品的叙事艺术都非常独特,都有着多层次的叙事时间与空间,艺术时空的建构可以传达出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审美意识,《地狱变》和《道连·格雷的画像》营造了多层次的互为映像的时空场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表达了作家的世界观和艺术观。
一、人生图景的线性表达
时间叙事通常可以分为线性时间叙事与非线性时间叙事。“在现实世界里,即使恰好在同一时间里发生了两件事,用语言表现它们时,也就必须采用先说其中一件事,然后再说另一件事的形式;或者部分交替着说两件事。总之都需要变成线性形式。”[1]线性时间叙事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方式,作者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在文本中讲述故事,没有太多的技巧。《地狱变》和《道连·格雷的画像》,故事情节总体都符合线性时间叙事的模式,能有很完整的情节线索支撑着全文展开。但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两部同属于20世纪初期的作品,叙事时间有现代时间叙事技法的痕迹,所以作品叙述局部会因为多重叙述主体及现代写作心理内倾性等原因,开篇存在追忆、跳跃和穿插,但这些细枝末叶处未曾影响文本大体时间走势。这两部作品的线性叙事时间缓缓地展开,塑造出复杂的人生图景。
在《地狱变》中,故事先介绍了堀川府,交代了大公命令良秀画地狱屏风的缘由经过以及相关人物。在现实的堀川府中,享有霸权的大公威逼指挥着行径古怪的画师良秀,残害活生生的人,以这些被迫害的人的恐惧痛苦扭曲的形态做模特,呈现地狱苦难的图景,这两人无疑是制造地狱的魔鬼;画中的所画的罪魂,上至公卿,下至乞丐,各种身份的人,都在惨烈的地狱中受着各式折磨,展现出堀川府现实的生活图景——现世的地狱。而《道连·格雷的画像》的开篇,就引入了画家贝泽尔和亨利勋爵的争论,一个指向艺术,一个指向现世人生。在艺术和现实享乐人生的选择中,格雷选择了亨利勋爵的阵营,选择以现世享乐法则出没于上层社会,正是这一选择,使格雷一步步因过度享乐而走向堕落的人生。
线性时间叙事在让作品拥有完整清晰的线索的同时,也谱写了人生百态的图景。在作品塑造的人生图景里,这两部作品同时安排有一个罪恶的施暴者如堀川大公及亨利勋爵充当旁观者以及诱导者的作用,都借用画家良秀及贝泽尔的画笔下的艺术魅力构造了地狱般的困境,同时都塑造了地狱中唯一的女性天使形象如良秀女儿及西碧儿。不管是现世社会中的仲裁者,创造者,还是被压迫者,都是生命赞歌中复杂人性的谱写者。作者笔下的各阶层人物用不同的生活状态及复调意识真实再现了人生图景的全貌。
二、艺术图景的非线性建构
非线性时间叙事通常是因叙事时间与新媒体、新叙事方法、图像与声音的结合,产生和传统线性叙事不同的特点,并以此来增加文本的吸引力与艺术性。
作品《地狱变》中,作家良秀构造出一幅全人类地狱般的艺术性图景;而《道连·格雷的画像》则是画家贝泽尔建构的一幅人性善恶与艺术交织的图景。这两幅图的起笔到完成贯穿了全文,而时间走过的踪影便在画中留下了痕迹。时间的流动和图像结合起来,时间图像化的非线性叙事很好地传达出了这两部作品所要展现出的人生如画、人生艺术化的主题,也更好地展现出这两幅艺术图景背后的故事性与神秘性。
在《地狱变》中,很少出现明确的时间词,时间的流逝很大程度上被图像可视化。良秀绘画,一向是必须亲眼目睹生活中的惨剧,才能画得逼真。所以在画地狱屏风的过程中,良秀不断用活人做实验,展现出深陷地狱的凄厉场景,最终才完成了画作。叙事时间徜徉在画家良秀的画笔下,故事情节不断推向高潮。起初良秀只是用自己的噩梦呓语吓跑弟子,后来用铁索紧紧缠住弟子的身子观察弟子在无助中挣扎的模样,再后来让一只凶狠的怪鸟和猫头鹰去袭击弟子,旁观弟子在胁迫逃命中的恐慌。良秀正是在这一幕幕真实的场景中慢慢补齐他构造的地狱图景。时间叙事随着地狱屏风的逐渐勾画,成了画作的点睛之笔,亦是叙事的高潮之处——良秀女儿在烈火中皮焦肉烂,化为灰烬的地狱般受难场面,浓墨重彩地体现了地狱的毁灭本色。在画作完成后,故事情节的时间叙事驶入终点,良秀怀着对女儿的愧疚悬梁自尽,奔向女儿用生命铸就的地狱中。
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同样体现了时间叙事图像化的手法。王尔德在这部作品开篇的时候就讲到亨利伯爵联想到一些面色苍白的东京画家,他们力求通过一种本身只能是静止的艺术手段,来表现迅捷和运动的感觉。[2]时间的踪影同样隐匿在这幅格雷的肖像画中。文中出现过几次重大转折,都体现在画中。第一次是格雷未婚妻西碧儿的死亡。由于西碧儿缺乏艺术美,格雷无情地与她解除了婚约,西碧儿因爱情绝望而死亡。这时画像第一次因他的自私冷漠发生了些许变化,画像中格雷的嘴角露出了冷酷的表情。之后格雷不停地出入上流社会,干着各种利己享乐的事,于是记录格雷灵魂的画像也渐渐变的可憎可怕。第二次转折是画家贝尔泽的死亡。画家贝泽尔是格雷青春美和艺术性灵魂的塑造者,而亨利勋爵则是这些美好品质的间接破坏者。在贝泽尔看到自己多年前精心设计的画竟露出令人作呕的模样并发出狞笑的时候,格雷呼喊着是画像毁了自己,所以他也拿起刀子朝向了这个目睹一切罪行的贝泽尔,贝泽尔当场死于非命。这时画像中的一只手出现了湿漉漉亮闪闪的红色露珠,仿佛画布在冒汗沁血。第三次转折是格雷的自我毁灭。格雷偶遇复仇的西碧儿的弟弟,身陷被追杀的胁迫恐惧中,但在和朋友射猎时,竟意外射死了敌手。格雷感觉这世上再也没有他罪行和丑恶灵魂的知情者,他曾经一度想重新做人。这便是故事发展的高潮,也是现实中的格雷想要和画像中的自己对峙并决一死战的时候。可这时画像中的样子出现了更加鲜红和更大面积的红斑与血迹,这表明格雷已坠入杀人狂魔的深渊,无药可救。故事的结局是画像重生,格雷毁灭。格雷试图用曾杀过人的刀子毁灭画像,可是他刺向画像却引来了杀身之祸。格雷和画像中的自己交换了灵魂,在此期间,格雷所犯下的罪行,画像都代为承受,但当画像毁灭之后,往期的罪行就返回到格雷的身心,连同最后那致命的一刀。警察发现格雷的尸体时,他形容枯槁,皮肤皱缩,面目可憎,而画像如青年时的格雷一样,俊美依旧。
三、室内外空间转换书写主体的迷失
叙事学研究存在一个时间维度,也存在一个空间维度。法国学者让·伊夫·塔迪埃认为:“文学作品建构了两种结构,即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在展开的作品中为读者建构了静态和动态的组织和体系,而时间结构为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经历的时间。”[3]《地狱变》与《道连·格雷的画像》的空间叙事艺术同样具有相似性。
《地狱变》和《道连·格雷的画像》都体现出物理空间上画室内外、以及画像内外上的对立。作为画家的良秀和贝泽尔,对自己的艺术作品倾注了心血。画室外的人生图景,画室内的灵魂画家,与画师笔下的艺术图景紧密相依,在空间转换中激荡着主体与客体的交融及反抗,思考着艺术美与人生道德的冲突。
在《地狱变》中,前六节都属于开阔的画室外——堀川府。堀川府是一座宏伟豪华的宫殿,这座府邸的主人堀川大公专横霸道。崛川府的画师良秀,在大公手下俯首称臣,内心无比孤独。良秀号称当朝第一画家,但实际并不为人尊重。在专权的社会中,艺术家良秀处处受到嘲笑和奚落,甚至因为他矮小的身姿被人喻为猴子,他的画也被称为歪魔邪道。目空一切的良秀唯独在乎的人是他的女儿,而大公对女儿的强占和对良秀的刁难,让良秀在霸权统治下的社会处于失落个体的局面。打败良秀的不是被轻视的绘画艺术,而是人间地狱中的复杂人性。不难看出孤傲的画家良秀在画室外是失落的个体,主体对外的迷失让他寄居在自己的画室内。在隔绝外界社会的画室内,良秀能根据自己作图的风格和形式进行艺术创作,完成地狱屏风的图景。良秀除了完成对艺术的追求之外,更是直面自己的内心。在这一个由自我主体建造的独立空间里,良秀是自己的主人,他在室内会做噩梦,也会因感情脆弱而独自掉眼泪,宣泄自己的情绪和所处的艰难处境。良秀是孤独的,正如画室内的蛇,这一形象在两次绘画的关键时期出现,这条蛇是豢养来写生作画的,只为艺术而生。蛇是在圣经中最早出现的动物意象,在旧约圣经中,蛇常常象征与上帝敌对的势力,代表抵抗上帝的魔鬼,同时在圣经新约中,常常把蛇和撒旦魔鬼联系在一起,试探着耶稣。[4]画室中的蛇无疑是良秀痴迷于艺术的另一面,对周遭势力喊出了自我的呼声。
《道连·格雷的画像》的背景是19世纪末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助长了上层社会奢靡之风,同时也带来许多生态问题。在这样的城市背景下,使得生命个体充斥着困惑、焦虑与不安。在混乱的外部世界,个体受到外界的压迫,导致主体的迷失,格雷就是这样一个经不住外界诱惑而步步坠入深渊的人物形象。王尔德笔下的外部世界弥漫着纸醉金迷、靡乱享乐的社会实景——“在我们这个如此狭隘和庸俗的时代,在这个热衷于赤裸裸肉欲和实利的时代。”[5]格雷的世界观及人生观、对爱情及艺术的理解都在时代的利诱下畸形发展,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格雷将这幅画像放在一个并无旁人的室内空间里,隔绝了一切社会因素,有的只是个体灵魂和艺术的交流。如果说这幅画像是一面特别的镜子,映射着格雷的面貌,同时更是影射着格雷的灵魂。王尔德自身践行着唯美主义的纲领,为艺术而艺术,因此在室内空间体现出主体个性的唯美发展。从室内的装饰可以看出作者内心艺术世界的建构,如“挂着几张珍奇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壁毯”“桌上的一面象牙框子上雕着爱神的镜子”“法国赛佛尔产的古老小磁盘”“波斯毡子作面的无靠背长沙发”以及“遮盖画像的屏风——是用染成金色的西班牙皮革制成的,上面拷有路易十四时代花哨的风格”“比利时壁毯”“意大利大箱柜”。室内古典文艺的装潢和外部肤浅并物欲横流的世界形成对比。王尔德许多作品都体现出室内外二元对立的偏爱,室内空间文艺的装潢体现了作者审美艺术的终极追求,同时也体现出了传统道德相应的自我约束性。格雷每做一件恶事,这些变化都会间接投射到肖像上,进而在安全的室内空间进行反思自我,控诉自己不道德的行为。危险的室外空间往往对格雷产生着吸引力,代表艺术审美理想的室内空间是格雷受道德约束的信仰场所。格雷正是在室内外的一进一出中,感受到外部现实世界和内部艺术世界的对比,同时通过画像觉察到自己灵魂的丑陋。但格雷想在空间转换中找到平衡和救赎,显然是不可能的。格雷受到现实社会污浊了的灵魂唯有走向毁灭,才能让艺术的肖像恢复如初。所以在格雷想毁掉画像和他的全部罪行时,鲜血淋漓的灵魂和肮脏的青春脸庞全数归还给了现实中的格雷。
四、画像与现实的交错呈现双重人格
在一定程度上,画像充当着一面镜子的角色,画像外真实的人物群像与人生百态,艺术性地复影在画像内,传达出作者对社会现实与艺术观念的多重理解。画像内外构成了物理空间上的张力,也展现了相关人物的双重人格。这其中交织着画家良秀与贝泽尔对画作的苦心孤诣,女性以良秀女儿和西贝尔为代表的生命牺牲,旁观者堀川大公和亨利伯爵的引诱。良秀和格雷无疑是两部作品人物形象中最具有丰富阐释性的人物,是源于艺术,终于毁灭的代表人物,两者在文章结构上都存在着人物复影现象,以此塑造人物在现实人生与艺术间的双重人格,展现人物自身的冲突。
在《地狱变》中,良秀是一位善于写实的画家,所画之景皆来自于生活的复刻。屏风中的地狱之景是下层人民生活实景的写照,充斥着良秀弟子和女儿经受的非人苦难。屏风中画着的十殿阎王和他们的下属,正是堀川府中堀川大公及其他公卿大夫的压迫者群像;遭鞭痛打、压在千斤石下、叼在怪鸟的尖喙上、受鬼卒们虐待的罪魂,正是画像外良秀虐待弟子的一幕幕真实场景。画像中最凄厉的场景是一个女子在狂风卷起的牛车里燃烧着,这苦难亦是良秀女儿在实际生活中的苦难。在画像与现实的切换中,同时存在着痴迷于画艺的良秀,和充满人性“良秀”的复影现象。良秀瘦弱的样子似猴而被嘲讽为“猿秀”,一只由丹波国进贡的猴子却被叫为“良秀”。良秀和猴子的关联并不止于这里,而是基于和女儿的关系上。良秀是一个恃才傲物的画家,对女儿的关怀和爱是良秀唯一的人性表达。对于猴子,在女儿从小公子手下为它求情并救下它后,它像通了人性一样日日陪伴在良秀女儿身边。在良秀女儿得了感冒躺在床上时,小猴就守在她枕边,愁容满面地咬自己的爪子;在她遭受大公的凌辱时,猴子去找人求救并像人一样跪倒在人的面前,连连扣头表示感谢;在她被火烧的最后关头,猴子更是跳入火中紧紧地抱住她,这是猴子人性的表达,更体现了一种父爱的光辉。但这和痴迷于地狱屏风,甘愿让女儿为艺术献出生命的良秀又有所不同。一定程度上,猴子作为艺术家良秀的影子,是良秀冷漠人性的温情刻画,让这部充满阴冷色调的作品又多了一抹亲情的守护和人性的温暖。
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格雷和画像中的自己存在复影现象。格雷作为生命体的物质实体,而画像中的格雷是艺术人格的表达。从起点来看,是现实社会中格雷的美和青春,创造了画中的自己。这两者是并行发展的,格雷交换灵魂以换取永恒艺术般的青春和美貌,而画像中的自己便要承受衰老和罪恶,所以格雷每做一件错事,画像都会留下痕迹。虽然任何一个人的灵魂都使外界琢磨不定,但王尔德借助画像中格雷灵魂的一步步堕落,使其灵魂的痕迹可视化。在一定程度上,现实中的格雷和画像中的格雷是一体的,格雷常常去放有画像的房间独自审视画像,凝视自己的灵魂。起初因为画像中的美貌产生了极度自恋的行为,逐渐走向享乐腐朽之路,画像中体现出来的美是诱导格雷犯罪的原因;之后因画像中的自己变得丑陋不堪,才激发了格雷想要毁掉画像的决心。毁掉画像中已然真实的自己,就意味着在现实中承认肮脏的自己,并同时毁灭真实的自己连同外界虚假的自己。
在艺术与人生道德观的冲突中,这两部作品都通过相似的时空叙事传达出以画像为代表的艺术永恒价值。在芥川的艺术至上观念与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文艺实践下,有着东西方文学对人生、人性的不同思考,两部作品在东西文化背景下,都展示出了世界文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