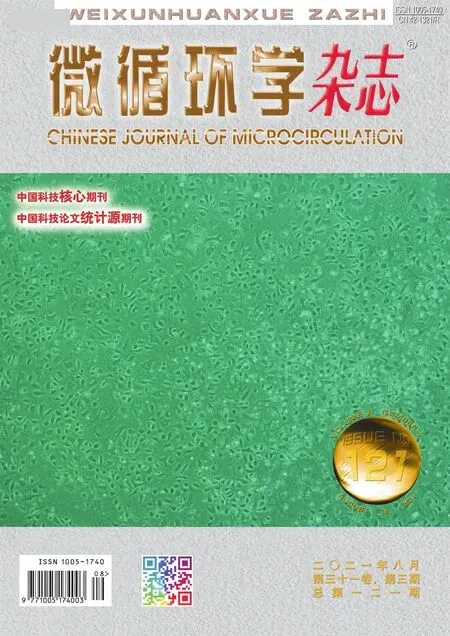雌激素在绝经期女性抑郁症中的作用及机制探讨*
孙 婷综述 李 艳审校
近年来,抑郁症的患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1],全球有超过3.5亿人罹患抑郁症,近十年来抑郁症患者增速约18%,截至2017年,中国有超过5 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其中女性平均发病率为65%,男性平均发病率为35%,且67%的抑郁症患者超过35岁,但接受治疗的患者不足7%。在抑郁症患者中,与男性相比,女性抑郁发作持续时间更长,复发频率更高[2],且女性抑郁症主要发生在围绝经期和月经周期的低雌激素阶段,在此阶段内,雌激素降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功能失调,患者的情绪和认知功能会降低,海马的体积及海马区域的活动也会显著的减少,抑郁症风险增大[3]。
虽然大量的学说或假说已被广泛用于解释抑郁症病因的分子机制,但目前关于抑郁症发生的其它机制,尤其是雌激素相关的绝经期女性抑郁症发生的机制仍然只有部分的了解,本文针对雌激素对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的影响及发生发展机制的关系作如下综述。
1 雌激素的抗抑郁作用
雌激素是一类具有神经保护作用的甾体激素,属于性类固醇激素,主要由雌性动物的卵巢分泌。除了在生殖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外,雌激素在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及发育中也必不可少,与记忆、学习及行为活动紧密相关[4]。生理性雌激素主要包括雌酮(E1),雌二醇(E2)、雌三醇(E3)三种形式,其中E2活性最强,且在绝经过渡期迅速下降。E2的下降与大脑的一些变化有关,包括认知变化、对睡眠的影响和对情绪的影响,这些作用已在啮齿动物和非人类的临床前模型中得到证实[5]。李晓晓等[6]对围绝经期大鼠的研究表明,外源性补充E2可以改善去卵巢大鼠的行为学,改变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水平,海马神经元的数量,从而发挥抗抑郁作用。来自王小云等[7]的临床研究表明,更年期抑郁症患者血清雌激素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提示更年期抑郁症患者出现的抑郁症状可能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关。此外,Ha等[8]报道,长期使用雌激素可减少衰老过程中脑白质丢失,提示雌激素对老年女性的海马区及其它重要脑区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绝经后女性抑郁症的发生亦与雌激素水平波动密切相关。有研究[9]报道,血清E1和E2水平与绝经后老年女性的焦虑及抑郁评分呈负相关,且血清 E2 水平与郁抑症等级呈非线性关系,似乎呈阈值效应。Shaukat等[10]对42例女性抑郁症患者的研究显示,外源性补充雌激素能够有效地改善围绝经期及绝经后女性的抑郁症状。
2 雌激素抗抑郁作用的机制研究
在正常脑的老化过程中,有许多系统发生了变化,其中较多系统显示出与E2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多巴胺能系统、胆碱能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而这些系统对大脑认知功能至关重要。雌激素可能通过此类系统发挥抗抑郁作用,也可能通过直接的神经保护作用缓解抑郁症的发生[11]。
2.1 雌激素通过雌激素受体(ER)发挥抗抑郁作用
神经系统是雌激素作用的主要靶系统,雌激素与其受体结合后可影响神经元的活化和凋亡、神经元的电生理特性、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合成及调控cAMP 反应元件结合蛋白-BDNF信号通路等机制,调节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而具有神经保护作用[6]。雌激素受体包括经典雌激素受体ERα、ERβ和非经典雌激素受体G蛋白偶联受体(GPER)、G(q蛋白偶联的膜雌激素受体(Gq-mER)。经典和非经典雌激素受体都参与E2的神经保护作用,包括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ERK 1)-ERK 2和PI3K神经保护信号,以及抑制促凋亡的JUN氨基末端激酶(JNK)信号转导。因此,已有研究表明ERα、ERβ、GPER和Gq-mER的选择性激动剂可模仿E2在体内和体外的神经保护作用,并可以被雌激素受体拮抗剂、雌激素受体沉默和雌激素受体敲除阻断[12]。
此外,有研究报道,雌激素可能通过ERα及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神经元共区域化直接影响CRH水平,进而影响HPA轴导致抑郁[13]。ERα基因rs9340799和rs2234693的多态性与老年女性的情景记忆、愤怒情绪以及焦虑抑郁有关,且ERα基因rs9340799多态性可能影响抑郁症的发展和转归[14]。另外,动物研究表明, 雌性小鼠和大鼠脑中的ERβ可促进神经生发, 调节机体对应激反应的敏感性及神经内分泌改变, 进而减少抑郁样行为[15],支持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抑郁症的理论。
2.2 雌激素通过调节神经递质发挥抗抑郁作用
“神经递质假说”近年来已成为解释抑郁症发病机制的里程碑式假说,雌激素与神经递质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也层出不穷。雌激素对神经递质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雌激素可增加中缝背核中5-羟色胺(5-HT)的合成,5-HT通过5-HT受体(5-HTA)发挥情绪调节作用,其中5-HT1A受体激活后具有抗抑郁及抗焦虑作用[10]。另外,5-HT的调节功能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在经前期、围绝经期及绝经后易出现抑郁,此阶段内5-HT反应性降低,E2治疗后5-HT反应性恢复[16]。虽然E2单独作为抗抑郁药物在围绝经期和绝经后抑郁症中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但雌激素-5-HT相互作用可能通过5-HT能系统的认知和情绪调节功能影响抑郁症状。②雌激素可能通过与胆碱能系统的相互作用调节认知功能进而影响抑郁。卵巢切除动物的雌激素替代抵消了胆碱能拮抗剂对空间学习和记忆的负面影响。对绝经后妇女的研究同样表明,雌激素替代物可以防止胆碱能拮抗作用后的言语工作记忆、情节记忆、学习和注意力受损[17]。然而,雌激素的有益作用仅在胆碱能系统相对完整的动物中可见,这表明雌激素通过调节胆碱能功能,而不是通过单独的平行机制起作用。③雌激素能影响多巴胺(DA)的代谢,促进DA的合成和释放,并能上调DA受体的表达和功能,雌激素可通过对DA的影响发挥抗抑郁作用。有研究表明,慢性E2治疗可增加纹状体和伏隔核中的D2受体密度,而纹状体D2 mRNA水平保持不变,表明E2可通过非基因组作用调节D2受体的密度[18]。另外,Field等[19]通过雌性大鼠卵巢摘除构建围绝经期抑郁模型,并发现与未去卵巢大鼠相比,去卵巢大鼠纹状体DA含量显著降低,证明了雌激素可以增加纹状体DA的含量,甚至可以增加下丘脑和垂体前叶内DA的释放进而缓解抑郁症状。
2.3 雌激素通过影响HPA轴发挥抗抑郁作用
HPA轴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急慢性应激反应,在抑郁症的病理生理中也具有重要作用。正常情况系,HPA轴可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态;在抑郁症和慢性应激状态下,HPA轴过度活跃,下丘脑和垂体糖皮质激素受体(GR)表达降低导致负反馈调节脱敏,进而导致HPA轴的过度激活糖皮质激素(GC)分泌的持续增加,致肾上腺肥大和皮质醇(COR)分泌增多[20];而E2可通过HPA轴上调GR,降低血浆COR水平,从而减轻焦虑和抑郁样行为[21]。另外,HPA功能改变在女性抑郁症的病因中可能尤为重要。皮质醇对压力反应确实表现出性别差异,并且它会因月经周期和怀孕而改变,在月经周期的低雌激素阶段,女性在急性心理社会应激期间表现出更大的负面情绪反应和更少的海马活动[3]。这些发现表明雌激素水平可能调节女性HPA轴的功能。
2.4 雌激素通过抗炎作用发挥抗抑郁作用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炎症与抑郁症密切相关,大脑中促炎细胞因子过度表达会促进焦虑和抑郁样行为的产生。雌激素是一种具有抗炎作用的性类固醇激素,在抑制抑郁症的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关脂多糖诱导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炎症的研究表明,绝经后妇女体内雌激素的缺乏可能会增加IL-6的产生,雌激素可以降低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炎症反应活动,减少炎性因子如IL-6、TNF-α的释放和NO的产生[22]。也有报道称IL-1β与孕酮之间呈负相关。孕酮先前已在神经元损伤和感染模型中显示出抗炎作用[23],可能是通过调节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上的孕激素受体来实现的。此外,大量的动物实验也证明雌激素可通过抗炎作用发挥抗抑郁作用。夏磊通过卵巢切除(OVX)构建围绝经期抑郁小鼠模型,发现雌激素缺乏状态下,小鼠会出现抑郁样行为,且小鼠海马组织内炎症因子、核苷酸结合和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家族3(NLRP3)炎性小体水平升高;而雌激素及ERβ激动剂DPN可降低小鼠海马组织内炎症因子、NLRP3炎性小体水平,进而改善OVX小鼠的抑郁样行为[24]。Xu等[25]通过动物实验也证明,雌激素缺乏导致NLRP3炎性小体激活,从而导致海马体神经炎症、抑郁和焦虑,且雌激素对海马体炎症和抑郁焦虑样行为的调节依赖于ERβ。抑制NLRP3炎小体可改善OVX引起的抑郁和焦虑样行为,表明NLRP3炎小体在雌激素缺乏引起的抑郁和焦虑样行为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支持雌激素可通过抗炎作用发挥抗抑郁作用的理论。
2.5 雌激素通过肠道微生物发挥抗抑郁作用
近年来,关于肠道微生物对抑郁症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肠道微生物对抑郁症的影响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包括HPA轴的改变、糖代谢和氨基酸代谢的改变、神经递质和短链脂肪酸的产生、免疫调节及迷走神经的调节等[26]。人体的肠道微生物群具有功能性,对激素中间体、代谢物和免疫信使都有局部和远距离影响。新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和雌激素之间相互作用,微生物群可以将人体摄入的类雌激素化合物代谢成生物活性形式,类雌激素化合物也可以促进某些细菌的增殖和生长[27]。另外,Cross等[28]也报道肠道微生物与雌激素的代谢密切相关,来自实验模型的数据表明,雌性大鼠比雄性大鼠对肠道损伤和炎症反应的抵抗力更强,雌性大鼠胃肠道粘膜通透性在整个发情周期内波动,卵巢切除引起的雌激素缺乏会导致肠粘膜屏障功能受损。这一证据支持,类固醇激素除了在生殖功能中具有重要作用外,在胃肠道内环境稳态维持和调节疾病易感性方面也必不可少。人体内的雌激素有结合雌激素和游离雌激素两种形式,二者可以相互转变,此过程需要肠道微生物的参与:肠道微生物参与雌激素的肠肝循环,且肠道微生物群可以分泌β-葡萄糖醛酸酶来调节雌激素,β-葡萄糖醛酸酶是一种将雌激素解偶联成活性形式的酶,使其能与雌激素受体结合并引起下游的生物学效应;除了解偶联反应外,体外研究表明在有氧和厌氧的条件下,肠道微生物能将雌酮转化为E2;在厌氧条件下,肠道微生物还能将16-α-羟雌酮转化为E2[29],提示雌激素与肠道微生物密切相关,两者相互作用可能对抑郁症的发生发展至关重要。另外,有研究报道[40],雌激素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的变化,人类肠道微生物群也存在性别差异。例如,男性类杆菌和普雷沃氏菌的水平高于女性,表明性别因素(如性染色体基因表达差异或性腺激素水平差异)在肠道微生物群调节中的作用。
3 小结及展望
综上所述,绝经期抑女性郁症发病机制复杂,虽已认识到本病的发生与雌激素紧密相关,但雌激素水平降低是导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的病因还是引起绝经期抑郁症的病理生理改变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以前大量的研究已经阐明雌激素受体、神经递质及神经内分泌改变对绝经期抑郁症的影响,近年来炎症及肠道菌群成为解释雌激素降低导致绝经期抑郁症的重要理论,但其机制仍未完全明确。未来应该更多的关注炎症、肠道菌群及各个系统相互作用对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的影响,动态监测抑郁障碍患者雌激素水平的变化及其与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患者的病情,便于对患者进行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