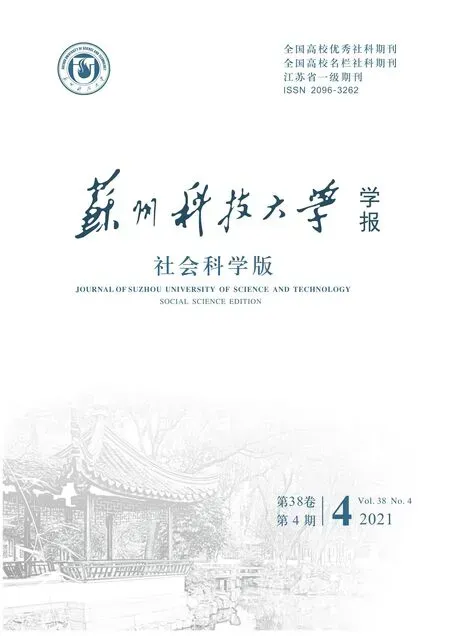法相庄严齐物论
——章太炎对《齐物论》的唯识学解读
韩焕忠
(苏州大学 宗教研究所,江苏 苏州 215123)
一、引 言
章太炎先生所著《齐物论释》一文,是以佛学,特别是法相唯识宗的思想义理诠释《齐物论》的名篇,也是他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表达自己平等观的一部力作。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从外祖父朱有虔读儒书,既长,入杭州诂经精舍从俞樾习古文经学。1897年至上海任《时务报》撰述,因参与维新,为清廷通缉,不得已避往台湾,次年东渡日本。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被捕入狱。1904年在狱中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赴日,受到孙中山热烈欢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展开论战。1911年辛亥起义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出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并参加张謇组织的统一党,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反袁,被软禁,直至1916年袁死后才获释。1917年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习国学为业,晚年愤日本之侵略,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章太炎著述宏富,刊有《章氏丛书》及《续编》《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2014年两度将其著作整理出版为八卷本的《章太炎全集》,今人汤志钧所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全二册,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所辑太炎生平事迹最为详尽。
章太炎生在国族危亡之际怀有强烈的救国之志。《齐物论》谓帝尧“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1]8,太炎释云:“物有自量,岂须增减,故宁绝圣弃知而不可伤邻也。向令《齐物》一篇,方行海表,纵无减于攻战,舆人之所不与,必不得藉为口实以收淫名,明矣。”[2]118-119由此可以说,太炎著《齐物论释》具有强烈的矫正时弊的意识,是他试图以佛教唯识学融摄老庄及西方思想以建立一种救世哲学的思想实践。作为疏释《庄子》的名篇,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受到了研究庄子和章太炎的学者们的普遍关注。远者如黄宗仰、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人皆有论及,近者如方勇的《庄子学史》第三册设有“章炳麟的《齐物论释》”一节,谓章太炎“以佛理阐释《齐物论》,又将庄子哲学中的齐物平等与近代的自由、平等思想相联系,这不能不说既是对庄子研究的一种新尝试,同时也是以《庄子》为中介,予全新的西方思想以中国化的解释的一种新尝试,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3]。刘固盛、刘韶军、肖海燕三人合著的《近代中国老庄学》设有“章太炎的庄学成就”一章,谓章太炎“引用了大量的佛家唯识宗思想来解释《齐物论》,甚至可以说是一篇讲解佛教唯识论思想的文献,而庄子的《齐物论》反倒成了例证以作陪衬”[4]。陈少明的《〈齐物论〉及其影响》设有“排遣名相之后——章太炎《齐物论释》研究”一章,谓“该书借佛学的名相分析,为原作各种隐喻式的陈述提供巧妙而内涵丰富的解说者,比比皆是。其思想视野,具有把东(道家、佛学)西(科学、哲学、宗教)方形上学融于一体,表达对人类生存状态普遍关切的情怀”[5]。姜义华的《章炳麟评传》设有“对‘人与人相食之世’的哲学抗辩:《齐物论释》”一章,谓章太炎“将唯识学与《庄子·齐物论》结合起来,名为诠释《庄子》,实际上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齐物论释》及《齐物论释定本》便是他把佛学与老、庄哲学和合为一的成果”[6]。孟琢的《齐物论释疏证》“既是对《齐物论释》的文本注释,也是对齐物哲学的思想探研”[7],还对《齐物论释》的初本和定本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细致的分疏。先贤时彦的相关论述为我们全面、深入地研读和理解《齐物论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诸多便利。本文仅就章太炎如何将法相唯识学作为一种诠释《齐物论》的方法略做探讨,以就正方家。
章太炎在疏释《齐物论》时运用了大量的法相唯识学名相、概念、术语,自然也吸纳和汲取了法相唯识宗的思维方式。细绎其文,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章太炎在疏释《齐物论》时主要运用了法相唯识宗的“四寻思”义、阿赖耶义、“三自性”义等思想义理。
二、“四寻思”义
章太炎在《齐物论》解题中运用了法相唯识宗的“四寻思”义。在章太炎看来,法相唯识学的“四寻思”就是涤除名相执著、实现万物平等的基本途径。“四寻思”,即《瑜伽师地论》三十六所说的名寻思、事寻思、自性假立寻思和差别假立寻思,由此可以认识到各种事物不过是虚幻不实的名字表达,是心识相分的因缘变现。所谓自性以及事物间的各种差别无非一种假设,从而获得“名寻思所引如实智、事寻思所引如实智、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2]75,达到诸法无差的境界,实现万物一往平等的理想。
章太炎将唯识宗的“四寻思”义运用到《齐物论》的解读之中,《齐物论释定本》的题解即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阐发。《齐物论》云:“言者有言”[1]6,太炎认为这是“于名唯见名”的“名寻思”[2]75。《齐物论》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1]6,太炎认为这是“无执则无言说也”[2]75,即破除执著于名言概念术语的“名寻思所引如实智”[2]75。《齐物论》云:“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1]8,太炎认为这是“于事唯见事”的“事寻思”[2]75,乃“性离言说”的“事所引如实智”[2]75。《齐物论》云:“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1]5,太炎认为这是“于自性假立唯见自性假立”的“自性假立寻思”。《齐物论》云:“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以无有为有”[1]6,太炎认为这是“彼事自性相似显现,而非彼体”[2]75,明乎此,也是具有“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2]75的体现。《齐物论》云:“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1]7-8,太炎认为这是“于差别假立唯见差别假立”[2]75的“差别假立寻思”[2]75。《齐物论》云:“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1]8,太炎认为这是“可言说性非有,离言说性非无”[2]75的意思,即“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2]75的体现。《齐物论》中的这一段话向称难解,章太炎运用法相唯识宗之“四寻思”义的方式对之加以解说,引导人们将理解的重点放在破除名言概念执著的思维和智慧上,为人们理解和把握《齐物论》的核心思想提供了一条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路径。
章太炎指出,不仅《齐物论》中的这一段可以与法相唯识宗的“四寻思”义相对应,而且整部《庄子》可谓“华文深指,契此者多”[2]75。也就是说,在章太炎看来,“四寻思”义可以在《庄子》诠释中获得极为广泛的运用。
三、阿赖耶义
章太炎在解读《齐物论》时运用了法相唯识宗的阿赖耶识之义。阿赖耶识,意译为藏识,有能藏、所藏、执藏三义:自其能够收藏万法种子而言,为能藏;自其为前七识所熏所依而言,为所藏;自其为第七识即末那识执著为我而言,为执藏。阿赖耶又有“阿罗邪”“阿陀那”等不同的名称,代表所强调的意义不同。概言之,阿赖耶识是法相唯识宗解释诸法生起的总概念,为法相唯识宗最重要的范畴。
章太炎认为,《齐物论》中所说的“吹万”[1]5,就是对阿赖耶识的譬喻。他解释说:“天籁中吹万者,喻藏识,万喻藏识中一切种子,晚世或名原型观念。非独笼罩名言,亦是相之本质,故曰吹万不同。使其自己者,谓依止藏识,乃有意根自执藏识而我之也。”[2]78也就是说,在太炎看来,《齐物论》中解释什么是天籁时提到的“吹万”二字,就是对阿赖耶识的譬喻,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具有含藏诸法的功能,这自然是就其作为“能藏”来说的。其中,“万”字就是譬喻阿赖耶识中所含藏的一切种子的,也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所谓的原型观念。它不仅概括了一切思想观念,而且包括了所有具体事物。可见,这个“万”字的内涵是纷繁复杂、包罗万象的,因此《齐物论》谓之为“吹万不同”,这显然是就其“所藏”的一切种子来说的。《齐物论》又谓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是由自己形成的或者发出的,这实际上就是末那识执阿赖耶识以为自我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出,对于《齐物论》中“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1]5一句的解释,太炎就运用了阿赖耶识的能藏、所藏、执藏三义。
章太炎还触类旁通,将法相唯识宗的阿赖耶识之义运用于《庄子》其他篇章的解释。他说:“详佛典说第八识为心体,名阿罗邪识,译义为藏,亦名阿陀那识,译义为持。《庄子》书《德充符》言灵府,即阿罗邪,《庚桑楚》言灵台,即阿陀那。”[2]78也就是说,第八识阿赖耶识因为要强调意义的差异,所以还有阿罗邪、阿陀那等不同的称谓,如称为“阿罗邪”,重在强调“藏”的意义;称为“阿陀那”,重在“持”的意义。太炎由此指出,《德充符》中的“灵府”[1]22就是阿罗邪;《庚桑楚》中的“灵台”就是阿陀那。《庚桑楚》有语云:“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业入而不舍,而更为失。”[1]98太炎释云:“夫灵台有持者,阿陀那识持一切种子也。不知其所持者,此识所缘内执受境,微细不可知也。不可持者,有情执,此为自内我,即是妄执。若执唯识真实有者,亦是法执也。不见其诚己而发者,意根以阿陀那识为真我,而阿陀那识不自见为真我,然一切知见由之而发也。每发而不当者,三细,与心不相应也。业入而不舍者,六粗,第五为起业相,白黑羯磨熏入本识,种不焦蔽,由前异熟,生后异熟,非至阿罗汉位,不能舍藏识杂染也。每更为失者,恒转如暴流也。”[2]78-79《庚桑楚》的本意也许是说无意识中所具有的不恰当的想法就可以在行动上造成诸多的过失,但经过太炎的这番法相唯识学解读,变成从阿赖耶识中含藏的诸法种子在不知不觉之间转变成纷纭复杂的世间万象。二者之间固然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其不同之处也是非常显然的。太炎有见于二者间的相似性,因而指出:“今此《齐物论》中,言使其自己,以意根执藏识为我,义与《庚桑楚》篇参伍相成矣。”[2]79这意味着《齐物论》所说的“天籁纷纭”都是“使其自己”的结果,可以与《庚桑楚》中所言“灵台有持”而“每更为失”相互对照者进行理解。但是,由于太炎以“吹万”为阿赖耶识之譬喻,以“灵台”为阿赖耶识之别称,因此这两句《庄子》的名言也就变成对种子转变现行的叙述。
在释“咸其自取,则怒者其谁”时,章太炎用到了阿赖耶识有关相分和见分的学说。他先引《摄大乘论》无性释中见、相二义,然后说:“是则自心还取自心,非有余法。知其尔者,以现量取相时,不执相在根识以外,后以意识分别,乃谓在外,于诸量中现量最胜。现量既不执相在外,故知所感定非外界,即是自心现影。既无外界,则万窍怒号,别无本体,故曰怒者其谁。”[2]79既然见分和相分都是阿赖耶识的题中应有之义,见分对相分的认识或者感觉自然就是自心的自我认识和感觉,因为在自心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的事物。故而人们在认识和感觉事物之时,不应从认识和感觉的器官及能力之外寻求现象。实际上,人们所感知的那个外界,即便呈现出“万窍怒号”般的热闹场面,也都不过是自心展现的影像而已。太炎此释,实即法相唯识宗“唯识无境”之义。《知北游》云:“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1]92太炎释云:“物即相分,物物者谓形成此相分者,即是见分。相见二分,不即不离,是名物物者与物无际,而彼相分自现方圆边角,是名有际。见分上之相分,本无方隅,而现有是方隅,是名不际之际。即此相分方隅之界,如实是无,是名际之不际。此皆义同《摄论》,与自取之说相明矣。”[2]79太炎以“物”为相分,以“物物者”为见分,以见、相二分之间的不即不离解释“物物者与物无际”,以个体事物的独特性解释“不际之际”,以个体事物不存在真实的独特性解释“际之不际”,并认为《知北游》中的这些说法是符合《摄论》的相关内容的,可以与《齐物论》的“自取”之说相互阐释和发明。太炎此释一方面彰显了阿赖耶识见分和相分之义在《庄子》诠释中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无疑会强化《庄子》注重自我和内心的思想倾向。
章太炎运用法相唯识宗的阿赖耶义诠释《庄子》的地方还有不少,此不赘举。通过对阿赖耶识之义的运用,太炎强化了《庄子》特别是《齐物论》的唯心内涵,为他在主观意识中破除名相执著、实现万法平等的致思取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三自性”义
章太炎在诠释《齐物论》时还用到了法相唯识宗的“三自性”学说。“三自性”即《显扬圣教论》《瑜伽师地论》等所说的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众生不了解诸法性空的真理,对于自我及诸法,遍加计度,他们执著地认为那些表达自我及诸法的名相和概念就是自我真实的自性,故而称之为“遍计所执自性”;从佛教的立场看,一切诸法皆依众缘相应和合生起,皆为虚妄,都无自性,故而称之为“依他起自性”;诸佛菩萨圆满体会到诸法空性,成就真实不虚的圣智境界,故而称之为“圆成实自性”。很显然,在“三自性”中,遍计所执自性仅是凡夫的执著,也是各种烦恼的根源;依他起自性是法相唯识宗对世间诸法的阐明,既可由之解释凡夫的执著烦恼,也可以借之阐明诸佛菩萨的解脱境界;圆成实自性则是诸佛菩萨所达到的圣智解脱境界。法相唯识宗的“三自性”学说义通凡夫,因此具有非常强大的诠释功能。
章太炎运用法相唯识宗的“三自性”学说,解释了《齐物论》由无物之境至是非之彰、成亏之起这一过程。《齐物论》云:“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1]7太炎释云:“无物之见,即无我执、法执也。有物有封,有是有非,我法二执,转益坚定,见定故爱自成,此皆遍计所执自性,迷依他起自性,生此种种愚妄,虽尔,圆成实性实无增减,故曰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当其操弄诸调,不能同时并发,故知实性遍常,名想所计,乃有损益增减二执。苟在不言之地,无为之域,成亏双泯,虽胜义亦无自性也。……此解前破遍计所执,后破随逐遍计之言。”[2]100这就是说,在太炎看来,《齐物论》所说的“未始有物”之境正是无我执和无法执的境界,即相当于诸佛菩萨所证得的圆成实自性阶段;后来有了事物,有了事物之间的相互界限,还有了对事物的是非判断,太炎认为这是由于不了解名相和概念的依他起自性,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诸多虚妄见解,形成遍计所执自性。即便是遍计所执自性如此强烈,也不会对事物自身的圆成实自性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和危害。因为这些由遍计所执自性所形成的损益增减二执,都不过是在思想中对概念和名相的执著而已。如果达到了“不言之地,无为之域”,就可以充分展现出圆成实自性的空无自性来。太炎认为,《齐物论》的这些说法既可以破除人们对事物自身的遍计所执,又可以破除人们对相关名相和概念的遍计所执。我们知道,破除执著、彰显真实是佛教的终极目标,太炎以“三自性”义对《齐物论》所做的诠释,等于承认《齐物论》的相关做法在佛教意义上也具有终极的意义和价值。
章太炎运用“三自性”义解释《齐物论》的地方还有不少。《齐物论》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1]7太炎释云:“夫断割一期,故有始;长无本剽,故无始。心本不生,故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计色故有,计空故无,离色空故未始有无,离遍计故未始有夫未始有无,此分部为言也。不觉心动,忽然念起,遂生有无之见。计色为有,离计孰证其有?计空为无,离计孰证其无?故曰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无孰有也。”[2]106换言之,在太炎看来,人们所谓时间的有始与无始,空间上的有(存在)与无(不存在),都是站在某一个角度上执著计度的结果,显然属于遍计所执自性的范畴。太炎又指出,法相唯识宗的“三自性”义不仅充斥于《齐物论》之中,也广见于《庄子》的其他篇目之中。例如,《大宗师》有所谓“阴阳于人,不翅父母”[1]27,太炎认为此似计阴阳为有;《庚桑楚》有所谓“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使之,心使之也”[1]98,太炎认为此是明确主张阴阳为无;《达生》有所谓“凡有貌相声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远?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通乎物之所造”“物奚自入焉”[1]74,太炎认为这些说法阐明了事物的形成无不是自心所造的产物。换言之,在太炎看来,《庄子》中诸如此类的说法,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人们对事物的执著计度,是形成诸法遍计所执自性的关键。
太炎总结说:“如是依他、遍计等义,本是庄生所有,但无其名,故知言无有者,亦指斥遍计所执自性也。呜呼!庄生振法言于七篇,列斯文于后世,所说然于然不然于不然,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义,圆音胜谛,超越人天。如何褊识之夫,不寻微旨,但以近见破之。世无达者,乃令随珠夜光,永埋尘翳,故伯牙寄弦于钟生,斯人发叹于惠墓,信乎臣之质死旷两千年而不一悟也,悲夫!”[2]137其言下之意,法相唯识宗的依他起自性、遍计所执自性等义理,是庄子本有的思想观念,只因没有形成相应的概念,所以未能被见识偏狭的人们认识到。太炎此论无异于向世人宣称,他对《齐物论》所做的唯识学解读,就等于使庄子在两千多年之后遇上了万古知音!
五、余 论
除了运用法相唯识宗的思想、义理和思维方式,章太炎在解读《齐物论》时还运用了不少般若学和华严学的思想观念。
佛教般若学是阐明诸法性空的学说。在章太炎看来,《齐物论》的宗旨同时也是《庄子》一书的基本思想倾向,与佛教的般若思想极为一致。他指出:“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次即《般若》所云,字平等性,语平等性也。其文既破名家之执,而即泯绝人法,兼空见相,如是乃得荡然无阂。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虽复泛爱兼利,人我毕足,封畛已分,乃奚齐之有哉。”[2]73离相、破执是般若学的主要思维方式,证成诸法性空则是佛教般若学的目标。诸法既然在本性上是空的,那么也是无物不齐的“一往平等”,故而深合庄子的齐物之旨。佛教般若学常以真、俗“二谛”说法,太炎认为庄子亦有此义。例如,《齐物论》有“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1]6的说法,太炎释云:“随俗谛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依胜义说,训释三端不可得义,无义,成义,则虽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可也。”[2]97胜义,即真谛的意思。太炎此论显然具有将庄子的《齐物论》视为佛法胜义或者真谛的意味。《齐物论》有“忘年忘义”[1]11及“游乎尘垢之外”[1]9之说,太炎释云:“忘年谓前后际断,仲尼所谓‘无古无今,无始无终’,乃超乎穷年矣。忘义谓所知障断,老聃所谓‘涤除玄览’,乃超乎和以天倪矣。忘年为体,穷年为用,比其应化,则死生修短惟所卷舒,故能止于常转,不受飘荡,寄于三世,不住寂光。……能见道者,善达生空,则存亡一致;已证道者,刹那相应,则舒促改观。夫然,故知游乎尘垢之外,非虚语也。”[2]126-127在般若学的语境中,前后际断、所知障断是佛所证得的境界,寄于三世、不住寂光则是菩萨慈悲度生的无住境界。此释可以表明,在太炎的心目中,庄子早已跻身于佛教的圣贤之列。
华严宗以阐发法界缘起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摄入重重、圆融无碍为极致,是高度中国化的佛教。章太炎对于华严宗深有研究,故而在《齐物论释》中亦多有援引。例如,“能见独者,安妙高于毫端;体朝彻者,摄劫波于一念,亦无侅焉”[2]107。“见独”“朝彻”,都是修行得道者所达到的非常高深的微妙境界,将佛教世界里的最高山峰,即妙高峰纳入非常微细的秋毫之端,将佛教表示世界一个生灭周期的时间段,即一劫摄入极其短暂的一念之中,微细、短暂并不妨碍妙高的高大和劫时的漫长。太炎此释显然是对华严宗十玄门中微细相容安立门的运用。其释“万物与我为一”[1]8云:“本末有生,即无时分,虽据现在计未有天地为过去,而实即是现在,亦不可说为过去说为现在,以三世本空故。今随形躯为说,此即并生,而彼一一无生有生诸行,非独同类,其实本无自他之异,故复说言万物与我为一。详《华严经》云: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法藏说为诸缘互应。”[2]107在太炎看来,人们对空间所做的本末划分,对时间所做的长短区别,包括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等说法,实际上都是虚假的,因为一切的时空本性都是空无所有。职此之故,人们从世俗的意义上所说这个我及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种并生的关系,不仅是同类,而且没有自我与其他的差异。太炎认为,这就是“万法与我为一”的真实意义,也就是《华严经》表述的“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境界。太炎此论,无形中将庄子的《齐物论》带到华严宗事事无碍的无尽圆融之中。
在战国时期形成的《齐物论》对于百家争鸣中的是非、穷通、智愚、贤不肖等问题感到十分厌倦,强调世间所有的事物都各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笔者认为,章太炎将《齐物论》的宗旨概括为“一往平等之谈”是很有道理的。在古印度反婆罗门教思潮中兴起的佛教也以“众生平等”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后来继起的大乘佛教则以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价值取向。因此可以说,太炎运用法相唯识宗、般若学、华严学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疏解《齐物论》,不仅具有思想史的合理性,还使道家和佛教这两种异质思想文化在共鸣中得到丰富、发展和提升。太炎撰出《齐物论释》初稿的1910年和写成定稿的1912年,恰逢辛亥年前后,正是革命形势高涨的关键时期,彼时平等观念正借助革命的声势扶摇直上,深入人心。太炎以革命元勋、国学大师的身份撰著此论,盛倡平等,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必然会起到推动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从这部著述中体会到太炎从中国固有观念中寻求革命理据的苦心孤诣。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