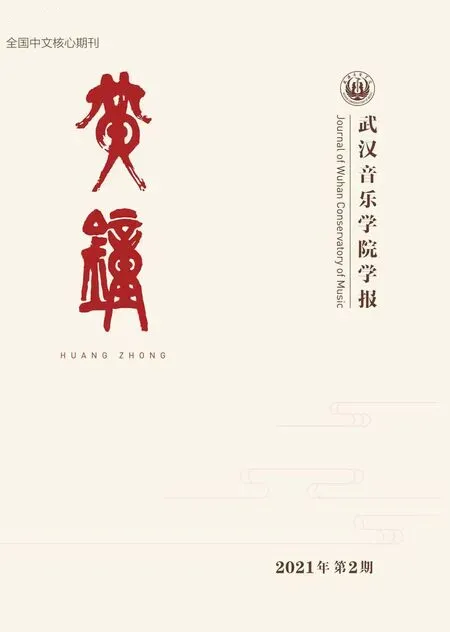忆恩师
蒲亨建
2020 年10 月与孙凡通话,她告诉我,武汉音乐学院会在2020 年底举办刘正维先生九十寿辰庆典,未料翘首以盼中,等来的却是吾师于2020年11月26日病逝的消息。
吾师身体一向康健,虽已九十高龄,却尚未达到我的预期。听孙凡说是不慎摔了一跤后便卧榻不起,这与我父亲当年的情况相仿。我的理解:人的身体机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退化。特别是到了老年,即使身体无恙,也不能有半点儿闪失,若有磕碰,伤病一旦触发便很难痊愈。
斯人已去,留下的只有难以忘却的记忆。我于1985年考上吾师的研究生,考试过程很有些戏剧性。当时的音乐学专业只有周畅先生“中国音乐史”方向招研究生。刚考完,听闻临时增加了“戏曲音乐”方向,由刘先生招生。刘先生当时只是讲师,但研究成果已相当突出,除在顶级刊物《音乐研究》发表了《梁山调腔系论证》①刘正维:《梁山调腔系论证》,《音乐研究》1983年第1期,第49—74页。等重要论文外,还有后来获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国一等奖的专著《戏曲新题》②刘正维:《戏曲新题——长江中上游小戏声腔系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问世,故被特许获得破格招生资格。
对我来说,可谓“绝处逢生”的天赐良机。所谓“绝处逢生”,一是因为我并不适应周畅先生的考题,觉得有点儿悬;二是有感我的“特长”只可能在刘先生的方向寻得“出口”。
周畅先生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上颇有建树,但也许是该科目本身特性的缘故,知识性考题较多,我不喜欢背书,记忆力的考试是我最怕的东西。其中有道考题是:周朝王的乐队是什么?在宫悬、特悬、轩悬、判悬中做出选择。我不知道,只能瞎蒙,觉得“宫悬”可能是个陷阱,不能填它。结果正确答案正是“宫悬”,此分必丢。
另一个考题是:用什么方法判定古代某种乐器的年代(好像是编钟)?这是一个“音乐考古”知识题,我也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只能使出我当工人的见识:用红外线探测仪③探测工件伤痕的仪器。。也肯定丢分。
刘先生的《戏曲音乐》只有两大考题:一个是论述题,一个是戏曲唱腔创作题,正中我下怀。
接到录取通知前,吾兄告诉我:刘老师对其中一个考生的答卷非常满意:唱腔写得很好听,而且,肯定读过张庚的《中国戏曲通史》。我一听,有把握了:十有八九说的是我。刘先生的这两道考题似乎是为我量身定做,我隐约感觉到我与先生之间的某种“天作之合”的默契。这种“默契”,一直在延续。进校后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想搞戏曲音乐史还是戏曲音乐形态?我稍一思忖,便果断回答:戏曲音乐形态。刘先生颌首微笑。仅此简短问答,便决定了我毕生的研究方向。
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便不由得感叹:人生道路的走向,有时似乎就在一闪念之间;但在这种貌似偶然的“一闪念”的背后,却仿佛有着一种天然的默契——或称“天意”。吾师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总是呈现为平易近人的亲切;但他对学生的鞭策,却有着一种“绵里藏针”的锐利。坦白地说,我考上戏曲音乐研究生时,对传统戏曲音乐几乎一无所知。刘先生之所以看中我,大概只是我的那点儿尚可塑造的“灵性”。
刚进校一个月,他就叫我给“戏曲音乐专业进修班”上一堂课。这个班的学生全是湖北各地戏曲团体的音乐骨干,其中有后来的大咖蔡际洲、姚艺君等,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刘老师之所以鼓励我上这堂“课”,缘于一个小插曲。吾师总是早晨八点准时端个茶杯到我宿舍给我上课。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上课过程中总会不时走神儿。有一次我思想又开小差了。“小蒲,想啥呢?”“我在想……”“具体说来听听?”我在纸上边描边谈了一个朦胧的想法。“咦?有意思!好好准备一下,下周给他们讲一堂课,如何?”这就是点燃他让我给戏曲大专班“开课”的导火索——他给我施压,并非空穴来风,总是“事出有因”;在他那温和、热忱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一种殷切的期冀。
刘老师审查我习作的方式很特别:不看,直接念给他听。在他看来,如果念得咯咯巴巴,语气不通,那就是思想还没有理顺——至少文字表达没过关。1990 年发表在《乐府新声》的《“主腔融变体”——戏曲音乐体制发展的历史趋势》④蒲亨建:《“主腔融变体”——戏曲音乐体制发展的历史趋势》,《乐府新声》1990年第1期,第35—38页。一文,就是我当时念给他听的文章。和后来发表在《音乐研究》的加强版《传统、现代的完美结合与逻辑延伸——现代京剧唱段“乱云飞”的艺术、历史价值再认识》⑤蒲亨建、翟清华:《传统、现代的完美结合与逻辑延伸——现代京剧唱段“乱云飞”的艺术、历史价值再认识》,《音乐研究》2009年第3期,第71—79、88页。,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这种为文水平的进步,就跟吾师对我的特殊训练方式相关。
刘老师为文,一如其为人:谦逊温和、深入浅出;通俗流畅,平中见奇。他永远面带微笑,永远对学生一点一滴的进步表露出由衷的欣慰。无论是跟随他三年的学习,抑或后来的偶尔相见以及数次信件往来,他总是密切关注我的学习与研究动态,并提出温和而中肯的意见。哪怕我的某些观点与他的看法相悖,也从未流露过一丝愠色。
后来我的研究趋于抽象,逐渐“脱离”接地气的传统路子,刘老师对此深表理解。这既出乎我的意料,也在意料之中。所谓“出乎意料”,即他一向反感“坐而论道”之空谈,坚持“言之有物”之学风;所谓“意料之中”,则在于他既秉承传统,又不拘泥传统,具有一双敏锐发现新视界的慧眼。特别是他学术生涯的后期,明显地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互渗透、交相辉映的双重特色;他的研究,总是在不断突破、不断超越,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力前行,其“平衡论”“板块论”“三色论”之三大新颖创见即为明证。
我现仍保留、并将永远保留刘老师与我的通信记录:
信件一
从星海音乐学院2017 年第二期学报读到了你和强君说曹教授的关于“音声”的文章⑥蒲亨建、蒲亨强:《“音声”之疑——质疑当下流行的一个音响概念》,《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39—45页。。很好!为你们高兴,为我国音乐学界的某些不良风尚注射了一针清凉剂。我为有你们这类同行感到兴奋!谢谢你们兄弟!
信件二
看到来信,非常高兴。知道你更在深究形态学,深有所盼。望常联系。
信件三
新年一喜,新文一喜。老友
信件四
老友:祝贺你又有两篇大作,等候拜读。
这种“亦师亦友”、平易近人的话语,让我倍感温暖。我不擅长抒情,只能如实地记下我记忆中的点滴痕迹;吾师您没有走,您的音容笑貌将永远存留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