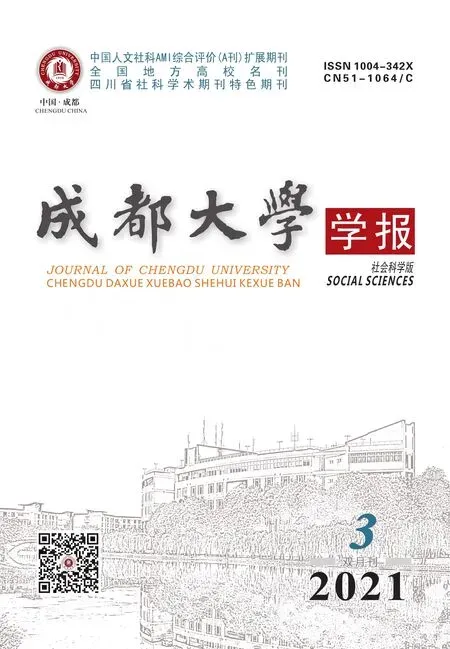《电火光中》与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家国民族之思*
李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732)
《女神》第二辑第二部分“泛神论者之什”中的第二首为《电火光中》。全诗由三首诗组成,最初发表于1920年4月17日的《时事新报》。1921年收入《女神》初版本时,第二首做了较大修改。1928年收入《沫若诗集》时,第二首又有变化。下文将结合这两次改动,以组诗第一首《怀古——Baikal湖畔之苏子卿》和第二首《观画——Millet的〈牧羊少女〉》为对象,探讨渗透于其中的郭沫若对家国民族的诗意思考。
一
在《电火光中》的第一首《怀古——Baikal湖畔之苏子卿》中,诗人想象苏武在贝加尔湖畔穿着游牧民族的服装牧羊:
电灯已着了光,
我的心儿却怎这么幽暗着?
我一人在市中徐行,
恍惚地想到了汉朝的苏武。
我想像他披着一件白羊裘,
毡巾复首,毡裳,毡履,
独立在苍茫无际的西比利亚荒原当中,
背后有雪潮一样的羊群随着。
我想像他在个孟春底黄昏时分,
正待归返穹庐,
背景中贝加尔湖上的冰涛,
与天际底白云波连山竖。
我想像他向着东行,
遥遥地正望南翘首;
眼眸中含蓄着无限的悲哀,
又好像犹有一毫的希望燃着。[1]105-106
据藤田梨那解读,这首诗需要与发表在《时事新报》1920年4月17日上的《电火光中》的题为《观画——Millet底〈夕暮伴归羊〉》的第二首联系起来考察。《观画——Millet底〈夕暮伴归羊〉》,“描绘的人物分明是苏武,而且这首诗和第一首一样,同是吟诵苏武,也就是说第一首诗和第二首诗都与米勒《夕暮伴归羊》有关,作者将米勒《夕暮伴归羊》中牧羊人与苏武的形象重叠在一起,将苏武汇入米勒的图画中。《电火光中》第一首诗的景画和意象来源于米勒《夕暮伴归羊》是无可置疑的。”[2]96笔者认同这一看法。
郭沫若于1919年通过有岛武郎的《米勒礼赞》关注到米勒。米勒(1814—1875)被称为法国最杰出的农民画家。他的画作《夕暮伴归羊》应该大概就是创作于1856年至1857年间的被丰子恺译为《日没时驱羊归家的牧者》的作品。丰子恺对该画作及此时米勒创作的相关作品评论道:“冥想的农夫,牧者,大牧场的诗的寂寥,眠在斜阳里的广漠的平野;或浸在冷的月光中的牧场的水气,上升的、温暖的蒸气在空中浮动的夜景,是这几幅杰作中最得意的描写。”并认为这之中存在着宗教因素,指出“米勒在痛苦中用他的严肃来发现宗教的欢喜”,“作这画的画家的痛苦是道德的,故自然、故善;是善的,故美”[3]。但在郭沫若这里,米勒画中的宗教因素荡然无存,他由牧羊人联想到自己,融进了他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索。
藤田梨那、马云、陈云昊等学者都注意到了《电火光中》的米勒,并因此考察了米勒对于中国新文学的意义。但马云对此问题的简单描述尚未触及《电火光中》的家国民族[4];陈云昊的讨论未免过于强调“反抗”与“个性”[5],反而遮蔽了《电火光中》苏武形象的深层意义;藤田梨那的兴趣则在于郭沫若与米勒的关系。而在我看来,此诗的关键是苏武形象以及由此表现出的诗人郭沫若的家国理念。
藤田梨那认为,《电火光中》第一首“通过缅怀苏武表现作者身在异国他乡所感到的乡愁与孤独”[2]93。按照字面意义做如此理解并无不妥。郭沫若到日本求学后,曾在给父母的信中诉道:“男想,古时夏禹治水,九年在外,三过家门不入;苏武使匈奴,牧羊十九年,馑龁冰雪。”“留学期间不及十年,无夏、苏之苦,广见闻之福,敢不深自刻勉,克收厥成?宁敢歧路忘羊,捷径窘步,中道辍足,以贻父母羞,为家国蠹耶?”[6]231由此可见,苏武正是留日学生郭沫若的镜像。苏武南望,正如郭沫若在博多湾海岸满怀壮志西望中国。如此,《怀古——Baikal湖畔之苏子卿》就不仅是单纯的“乡愁与孤独”,其深层意蕴需结合郭沫若当时的处境和思考方能凸显。
和近代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面对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郭沫若的国家民族观念较为明显地彰显出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于成都求学期间,他就写下了不少爱国主义诗篇。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和同学出于爱国激情,将锅碗瓢盆都卖了,下着不再在日本求学的决心,毅然回到上海。这些都体现了在帝国主义掀起的侵华狂潮之下,郭沫若对于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守护之情。
写作《电火光中》时,郭沫若正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求学。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位于博多湾岸边,此地修建了一些博物馆。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Museumizing Imagination)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7]对于日本人关于战胜元军的宣传,郭沫若不以为然,他并不认为日本人在当年战争中靠实力能够取胜,那是自然环境帮助了他们,因为范文虎带领的元军刚好遇到了风浪。在《箱崎吊古》中,郭沫若有如下感慨:
那六百三十八年前元朝的大将,范文虎将军,带了四千只的楼船,十多万的同胞来攻讨日本的时候,全军覆没了,不是就遇着这般怪风,就在这博多湾的海上,就在这闰七月初一日的一天么?
我跑到了——我跑到博多湾的海岸了!
四千只的楼船——啊啊!还在海上翻!
惊砂扑面来,我看见范文虎同蔡松坡指挥着十多万的同胞战——同怪风战,狂涛战,怒了的自然战,宇宙间一切的恶魔战……
我的同胞哟!我奋勇的同胞哟![8]
诗中四次出现“同胞”。范文虎带领的十多万大军,有蒙古人、汉人、色目人,现在都成了郭沫若的“同胞”。郭沫若此处浓郁的“同胞”意识,和日本的博物馆等民族主义场域的反向哺育有关。他写信给远在四川老家的弟弟:“又有《辽金元史》一书,请把那《元史》考查一考查,其中有《范文虎传》么?……请一并详细考查考查,愈详愈好,细抄一份给我。”[6]260可见,他有意识地同日本对这次战争的叙述展开来自别一民族的抗争。多年后郭沫若回忆他在九州帝国大学求学时“体会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因此我也就学会了爱我的祖国。为了我的祖国能够从以前的悲惨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就是贡献我自己的生命,我也是心甘情愿的”[9]。
蔡松坡即蔡锷,1916年9月被黎元洪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11月病逝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四川是郭沫若的家乡,蔡锷病逝的医院正属于郭沫若当时就读的大学。郭沫若和蔡锷是有两重缘分的。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军人,他在反袁斗争中表现突出,对于重造民国有贡献。郭沫若在诗中让蔡锷穿越到六百多年前,与范文虎一起统领十万大军。这一联想表明,在郭沫若的意识中,蔡锷所代表的近代意义上的中国这一民族国家是传统中国的延续。范文虎不仅仅是元朝的将军,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有意思的是,《箱崎吊古》中并没有直接出现日本这一范文虎的征战目标。在诗中,范文虎和蔡锷带领大军“同怪风战,狂涛战,怒了的自然战,宇宙间一切的恶魔战”。这体现了郭沫若的民族国家意识超克于当时日本的博物馆之处:一个民族一定要通过打败其他民族去生存吗?民族生存之道主要是和“自然战”,而不是和其他民族作战。
近代各国的博览会中大都内蕴着民族主义思想。1914年,大正博览会在东京上野举办,东京市议会议长中野武营在开幕式致辞中说:“我等要和国内有志诸士共同振兴正气、矫正世弊,以此达成国家真正的富强。”其民族主义情绪昭然若揭。在东京大正博览会的带动下,1918年,九州帝国大学所在的福冈也举办了工业博览会。在写作《电火光中》的一个月前,郭沫若在给宗白华的信中报告了他和田汉参观福冈市工业博览会的情况。郭沫若气愤地写道:“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10]可见郭沫若在这次博览会中受到了强烈刺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胜国,其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在郭沫若留学的大正时代,“被看作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的北一辉、上衫慎吉的思想,以及内务省——特高警察、在乡军人会代表的日本保守反动势力,他们在这一时期成为日本社会事实上的中坚力量”。“占日本总人口82%(1920年(大正九年)人口调查时)的郡辖区人们所拥有的是,把国家放在优先地位的想法,也就是国家主义思想和皇室中心主义的历史观。”[11]150-151日本普通人的“国家主义思想”在儿童中也有体现。郭沫若在小说《未央》(1922年)中有如下细节:“一出门去便要受邻近的儿童们欺侮,要拿棍棒投石块来打他:可怜才满三岁的一个小儿,他柔弱的神经系统,已经深受了一种不可疗治的疮痍。”[12]在此情况下,民族情感受到伤害的郭沫若十分思念他自己的祖国,在《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等诗歌中尽情吟咏。
由此,我认为郭沫若在《怀古——Baikal湖畔之苏子卿》中塑造的那“往南翘首”的苏武不仅仅表现了诗人的“乡愁与孤独”,而且在这“乡愁与孤独”的深处,是身处排外性的民族意识高涨的日本大正时期的郭沫若的浓郁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二
《电火光中》的第二首《观画——Millet的〈夕暮伴归羊〉》在收入《女神》初版时,除前六行外,后面全部改写了,标题也改为《观画——Millet的〈牧羊少女〉》。
该诗前六行是:
电灯已经着了光,
我的心儿还是这么幽暗着!
我想像着苏典属底乡思,
我步进了街头底一家画贾。
我赏玩了一回四林湖畔的风光,
我又在加里弗尼亚州观望瀑布……[1]106-107
前两行和《怀古——Baikal湖畔之苏子卿》中前两行文字相同,类似于《诗经》中的复沓结构。这六行的重点是第五、六行,按字面意思应是观赏两幅画作。陈永志注释说:“指的是两幅风景画。——原画未见,查考未果。待识者指正。”[13]这两幅画画名是什么,作者何人,确实比较费考。不过其中的四林湖畔是比较有意味的。
四林湖畔和郭沫若当时最敬重的两位德国文学家歌德和席勒有关。四林湖位于瑞士,1797年,歌德游览了四林湖地区,对当地退尔的传说印象深刻,建议席勒以此题材创作剧本。1803年,席勒创作了《威廉·退尔》。剧本以四林湖畔的田园风光开幕,四林湖畔附近三州的民众对于奥地利属下总督的迫害难以忍受,秘密结成自由联盟。退尔认为自己安分守己,没有加盟。总督畏惧这位神箭手,要求退尔用箭去射放在退尔儿子头上的苹果。退尔拿了两支箭,并坚定告诉总督,假如第一支箭射中了孩子,第二支箭就会射死总督。退尔成功射中了苹果。总督加紧了对退尔的迫害。退尔终于射死了总督,这成为四林湖畔民众运动的动员令。这个剧本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中国有马君武等多人的不同译本。
郭沫若是熟悉《威廉·退尔》的。1923年,他在讨论神话时曾从歌德的《渔歌》联想到《威廉·退尔》剧本开幕的那首渔歌:“亲爱的读者哟,且听他同一的材料,弹出别样的歌声。”[14]263他还将这首渔歌翻译出来,以《渔歌》为题收入《沫若译诗集》。郭沫若明确提到《威廉·退尔》虽然是在1923年,但他对席勒早有崇拜。在写作《观画》前,他在和田汉、宗白华等人的交往中多次提到席勒,他和田汉还想做中国的歌德和席勒。当郭沫若看到这幅有关四林湖畔的风景画时,他思绪所到之处应该是《威廉·退尔》所表现的弱小民族反对殖民者、奋起争取自由和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郭沫若写于1920年的《狼群中的一只白羊》和《胜利的死》中也有表现。《狼群中的一只白羊》以日本世界日礼拜大会上朝鲜牧师的演讲被制止为题材,表现在朝鲜人亡国处境下的抗争与悲剧命运。《胜利的死》写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马克司威尼以绝食抗争英国殖民统治的事迹。“两首诗都反映了郭沫若对帝国主义者、殖民统治者的憎恨,对反抗殖民统治的弱小民族的同情与声援。”[2]152中国的处境和朝鲜、爱尔兰类似,郭沫若对朝鲜和爱尔兰的关切饱含着自己的民族国家之思。四林湖畔之于郭沫若也有类似的意义。同是在异族压迫之下的弱国子民,郭沫若对于四林湖畔的故事感同身受。《观画——Millet的〈牧羊少女〉》中的四林湖畔既是诗人看到的画面,也是用典,苏武在贝加尔湖畔遥望南方祖国叠加上四林湖畔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喻示着诗人对作为半殖民地的祖国的关切。
三
修改后的《观画——Millet的〈牧羊少女〉》第七至第十六行咏道:
哦,好一幅理想的图画!理想以上的画图!
画中的人!你可便是苏武胡妇麽?胡妇!
一个野花烂漫的碧绿的大平原;
在我面前展放着。
平原中也有一群归羊,
牧羊的人!你可便是苏武胡妇么?胡妇!
你左手持着的羊杖,
可便是他脱了旄的汉节么?胡妇!
背景中好像有一带迷茫的水光,
可便是贝加尔湖,北海么?胡妇![1]106
诗人此处所观之画是米勒的《牧羊少女》。此画作于1863年,次年,米勒以此画参加巴黎沙龙美展,获得极高赞誉,此画成为米勒的代表作之一。画面右前方是围着红头巾、披着旧毛毡披巾、衣衫褴褛、拄着木棍低着头的少女,少女背后是一群白羊,远处隐约可见湖泊。画面处于灿烂的夕阳之下,单纯柔和,充满了泥土气息。笔者同意部分学者的解读:这幅画表现的是农民单纯而虔敬的宗教情怀,少女低头祷告,是感谢上帝赐予了她牧羊的机会。但郭沫若对这幅画进行了创造性联想,他把这位牧羊少女想象为苏武归汉后留在西伯利亚的胡妇。
苏武娶胡妇最早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闵之,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闻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后通国随使者至,上以为郎。’”[15]苏武在匈奴娶胡妇是当时的风气使然,张骞等人在匈奴也都曾娶胡妇。据葛剑雄研究,“汉人之所以能大大方方地娶胡妇,除了当时人的观念开放外,汉匈双方还有实际需要。匈奴是游牧民族,物质生活艰苦,人口增长率低,所以除了大量掳掠汉人外,还特别重视婚配生育。”“苏武等娶有胡妇在当时并非秘密,更不是什么绯闻,所以连皇帝都认为是正常现象。”[16]
苏武娶胡妇这一史实,后人有四种解读。
第一种是为尊者讳,避而不谈。正如论者所说:“虽为历史真实,但后人为标榜苏武气节,对此常避而不谈。宋元南戏《牧羊记》中苏武道:‘充饥皆草籽,相亲是猩猩’,指的是苏武牧羊的北海荒无人烟,强调他的冷暖无人问,并非苏武与猩猩的婚恋情缘。《牧羊记》中有‘遣妓’和‘义刎’二出,演卫律劝降不成遂遣妓女张娇迷惑苏武,苏武不为所动,张娇愧而自刎,这无疑进一步突出了苏武的忠臣形象和他的气节品质。”[17]这种观念一直到现今都还存在着,前些年有中学语文教材在收录苏武传记时,就将这一段删除了。[18]
第二种是曲为之辩。闻一多在1916年曾论道:“苏子卿娶胡妇,卒蒙后世訾议,私窃疑之。《新安文献志》载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随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数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所虏内人中自择,乃取其最陋者,人莫能晓。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无顾恋也。子卿之妻于胡,得非勣之见耶?”[19]这就将苏武娶胡妇说成是苏武为了归国所用之计谋。
第三种是从传统文人士大夫趣味出发,感叹连苏武这样的英雄都过不了美色关。《东坡志林》载:“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20]《鹤林玉露》引《东坡志林》这段话后感叹道:“乃知尤物移人,虽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无如人欲险’,信哉!”[21]
第四种是在明代“情学思潮”[22]的影响下,充分肯定“情”的重要性。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论道:“古之忠臣孝子,皆情为之也。胡忠简公劾秦桧,流窜海南,临归时,恋恋于黎倩,此与苏子卿娶胡妇相类。盖一意孤行之士,细行不矜,孔子所谓‘观过知仁’,正此类也。”清人笔记中议论道:“自古忠臣义士皆不拘于小节,如苏子卿娶胡妇,胡忠简公狎黎女,皆载在史策。近偶阅范文正公、真西山公、欧阳文忠公诸集,皆有赠妓之诗。数公皆所谓天下正人,理学名儒,然而不免于此,可知粉黛乌裙,固无妨于名教也。”[23]清末吴人达在其翻译的宫崎来城的《虞美人》序言中说:“自古惟真英雄,有真性情。苏武之眷眷胡妇,项羽之不能忘情虞美人,类非浅夫俗子所可与语。”[24]
但《观画——Millet的〈牧羊少女〉》对苏武胡妇的书写显然不能归结到上述解读方式中去。不过,《女神》初版本中关于胡妇的书写还没有完全从传统视角中解放出来。《汉书》提到胡妇是因为她的儿子苏通国。后人提到胡妇,无论是从“养生”的角度,还是从尊性情的角度,皆以苏武为主体,胡妇仅是话头而已。在《女神》初版中,胡妇究竟是同苏武一起牧羊呢,还是独自牧羊?这从诗中看不出来,她为什么要持着苏武“脱了旄的汉节”,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这在诗中也看不出来。也就是说,胡妇在《女神》初版本中还没有成为具有内容的主体,她仅是一处风景。
精彩的修改出现在1928年出版的《沫若诗集》中。此处,《观画——Millet的〈牧羊少女〉》的最后六行都重写了:
平原中立着一个执杖的女人,
背后也涌着了一群归羊。
那怕是苏武归国后的风光,
他的弃妻,他的群羊无恙;
可那牧羊女人的眼中,眼中,
那含蓄的是悲愤?怨望?凄凉?[25]
这就明确了画面是“苏武归国后的风光”,而且将“胡妇”改成了“弃妻”,一个“弃”字,倾向性毕现。如果说传统解读都是从苏武角度出发,此处的“弃”字就扭转成胡妇的角度了。胡妇是被“弃”的,读者自然同情于她。米勒《牧羊少女》中的少女低垂着头,看不到她的眼珠,更看不清她的眼神。但诗作特意写到她“眼中”,“那含蓄的是悲愤?怨望?凄凉?”于是,读者随着诗人一道,走入了胡妇的内心,胡妇活了,她的内面凸现出来。胡妇不再是苏武的附属,她和苏武成为两个独立的主体,在诗中产生了张力。
既然苏武是郭沫若的镜像,融入了郭沫若的民族国家之思,那么《观画——Millet的〈牧羊少女〉》中的胡妇自然也就令人想到了安娜。安娜即佐藤富子,和郭沫若在1916年年底结合。郭沫若写这首诗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郭沫若系念着祖国,势必要回国效劳,而作为异国妇女的安娜该怎么办呢?是一同回去呢,还是分开?这让郭沫若陷入十分深刻的矛盾中。而《电火光中》正反映了郭沫若的这一矛盾。当然,这一矛盾其实不仅是个人的家庭问题,假如没有当时特殊的中日关系,即便娶了一个异国的女子,又能算什么问题呢?
四
《观画》中的“胡妇”之所以成为“弃妻”,是因为郭沫若对于带回安娜的前途不抱希望。原因在于和日本女人结合,跟当时留学生界的“爱国伦理”有所冲突。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回顾说:
1918年的五月,日本留学界为反对“中日军事协议”的事体,曾经起过一次很剧烈的全体罢课的风潮。在那次风潮上还有一个副产的运动,便是有一部门热心爱国的人组织了一个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认为汉奸,先给他们一个警告,要叫他们立地离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对待。这个运动在当时是异常猛烈的,住在东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而离了婚的也很不少。[26]34
这是一次爱国主义的学生运动,但有些行为过火了。郭沫若在这次风潮中的表现值得注意:第一,郭沫若没有舍弃安娜;第二,郭沫若参加了六高中国留学生的全体罢课;第三,罢课持续了两个星期,协议没有取消,于是留学生又提议全体回国,有大约一半留学生于6月3日复课,其中包括郭沫若。
这事件说明在当时日本留学生界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一种“爱国伦理”,这种伦理包含着新的等级秩序,包含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求血统的“纯洁性”。对于和日本妇女同居并生子的郭沫若来说,被迫和这种“爱国伦理”保持一定距离。他愿意加入这样的爱国组织,但他的资格首先要受审查,就像《阿Q正传》中的阿Q,“革命”没有叫他,他想姓赵也姓不成。所以郭沫若对这种“爱国伦理”有所抵抗。他没有舍弃安娜并复课,说明这种抵抗的存在。对于那些行为激烈而中止学业回到中国的部分留学生,郭沫若的态度应该和他在《创造十年》中谈到1915年那次因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而回国的留学生时的态度差不多:“跑北京的代表们听说是段祺瑞亲自接见过一次,嘉奖了他们要他们回到日本安心求学,说政府是决不做有损国体的事的。这一部分的代表有的早回来了,有的留在北京在运动做官,又有一部分南下到了上海,和派到上海的代表们合在一道,现在在办着救国日报,空空洞洞地只是一些感情文章。我看他们通是一些政客啦!”[26]34说这些学生“通是一些政客”,充分表明了郭沫若的不屑。
一方面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屑,即便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是自己的“同胞”。另一方面,郭沫若对于敌国的国民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同情。1923年,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及其妻子被日本宪兵杀害,郭沫若写下了《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以示纪念。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明确指出:“国境之外,也还有人道,也还有同胞存在!”“我们古代的哲人教我们以四海同胞的超国家主义,然而同时亦不离开国家,以国家为达到超国家的阶段。”“我们现在是应该把我们的传统精神恢复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从事于文艺的人,应该极力唤醒固有的精神,以与国外的世界主义者相呼应。”[14]122-123这通常被当成是郭沫若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证据,但是,当郭沫若在此处说国境之外还有“人道”,还有“同胞”存在时,他显然想起了1918年日本留学生界那次强迫中国留学生和日本爱人离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行为,也和他在《电火光中》的思想是相通的。他对大杉荣及其妻子的悼念,是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的真诚表露。
上述分析也表明,作为《电火光中》的作者,郭沫若不单单是以国家和种族对人与人做出区分,他对这种区分十分敏感,很多日本人做出这样的区分,很多中国留学生也做出了这样的区分,这对他有影响。但他并没有完全步此后尘,而是跳出这样的逻辑,同情所有被压迫被损害的弱国子民,以及殖民国家内部的人民,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是相通的。不断修改的《电火光中》,既有苏武对祖国的思念,也有敌国“弃妻”的“怨望”。郭沫若对待民族主义思潮的这种超越性的态度,在1920年就有了,1928年,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参加了实际革命行动的郭沫若通过修改《电火光中》进一步明确了这种超越性。也正是这种超越性,成为作为五四时期爱国学生的郭沫若和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的有效通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