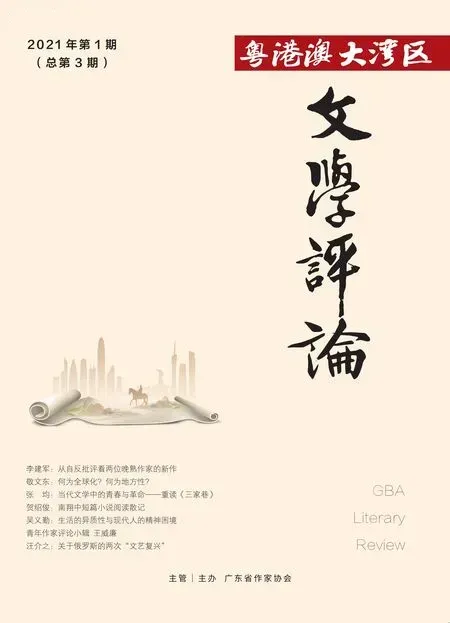关于王威廉的四则阅读札记
李 唐
当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音箱里正巧播放的是李摩根的音乐。李摩根是美国传奇的小号手,在60年代的爵士乐大潮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的经历同样令人唏嘘:年纪轻轻就成为了著名的唱片公司Blue note 最出色的小号手,却在最应该绽放其才华的时候死于女友枪口下。
为什么要提到李摩根?这篇文章的主角是王威廉,他们二人的领域、年代、人生经历都完全不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近期一直在重读王威廉小说的缘故,从李摩根的音乐里,我居然听出了他们二人的一些共通之处。
请允许我摘录一段关于李摩根的评论:“他独具个性的音乐语言,每个音符都仿佛烙下难以磨灭的情感。……在颇为低沉而清晰的钢琴伴奏下似乎在暗示着这个霓虹璀璨的城市背后不可名状的孤寂。……仿佛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侵蚀性彻底表露无遗。”
这确实也是我当初听李摩根时的感受。与同期其他爵士乐手不同,李摩根既没有沉浸在优雅的金曲演奏中,也没有像约翰·科川、杜菲那样进行惊人的先锋爵士实验,使爵士乐变为普通听众耳中的“噪音”……李摩根巧妙地平衡着“流行”与“实验”的尺度,在不失清冽的乐句中,又让音乐具备了“可听性”。
而这正是王威廉与李摩根的共通点之一。
王威廉的小说极具个人特色,并且有明显的“异质”色彩。但同时,他的故事和文字并未拒绝普通读者。即使是对文学并没有太多接触的读者,相信阅读王威廉的小说时也不会有阻碍。王威廉写作时像是一名出色的演奏家,把控着小说的整体节奏,细致、耐心而有条不紊地抵达自己想要触碰的核心。
而王威廉小说中的另一个特点,就如同形容李摩根的音乐那样,充满了城市的孤寂,以及这种孤寂对灵魂深处的侵蚀。下面,我尝试用几个关键词来谈谈个人对王威廉的小说的看法。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文学评论,只是阅读后的一些感想,或者说,是有关王威廉小说的阅读札记。
侵入
王威廉小说的背景大多发生在城市,这跟作者成长与生活的环境密不可分。根据王威廉的自述,他的处女作是中篇小说《非法入住》。当时他住在大学的筒子楼里,刚刚接触社会,“带着对生活荒诞的发现、愤怒和绝望,写出了这样一篇放纵的小说”。多年后,作者自评这篇小说“直面了我们不堪的生活处境”。故事当然发生在城市,讲述了一个蜗居在九平方米小屋里的男子,如何对抗他的邻居——因脖子瘦长如鹅而被称为“鹅男人”的一家六口,并最终败下阵来。
“鹅男人”一家子挤在逼仄的小屋里,利用主人公的善良与懦弱,先是借口“鹅男人”的儿子考试需要休息,借住在主人公家里;紧接着,“鹅男人”的父母也强行住了进来,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并以“鹅男人”一家的胜利告终。他们大摇大摆地占有了主人公的房间,吃饭、睡觉,俨然新的主人。主人公无力扭转这样的局面,他的反抗是与“鹅男人”的妻子通奸,以此来维系自己脆弱的尊严。小说以富有寓言性的事件结尾:主人公像是“鹅男人”一家那样,强行占有了另一个新搬来的女人的房间。经过心力交瘁的战斗,他最终也成了一名入侵者。他的灵魂被自身的无力及外界的恶意所侵蚀。
作者自陈“那种滋生出的仇恨与恶意,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微不足道的,又是顶心顶肺的,这一切并不完全取决于涵养,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处境”。
确实,这是一篇既现实又抽象的小说。它使我想到了卡塔萨尔的名篇《被占的宅子》。就像标题所示,这篇小说同样是讲入侵者,讲一个宅子如何被外部力量占据。只不过,《被占的宅子》里的外部力量更加抽象,小说里只是写那莫名的力量逐渐占据了兄妹俩的房间,却并未写明那力量究竟是什么。没有可能,可能性便放到了最大。它可以是恐惧、邪恶、时间,也可能隐喻着当时的社会环境,甚至是更遥远的历史。
相较而言,《非法入住》并没有那么抽象,它有很明确的表达。就像作者本人阐释的,小说可以视为“北漂”“蚁族”的生活与精神境遇,那种置身异乡和被冒犯的普遍情绪。不过,这么理解虽然与当下现实作了巧妙勾连,可是小说的内核也随之变得简单。因此,我依然想把它当成一则寓言故事: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人,他的心是“初始的”,尤其是,这还是一颗敏感的心灵。当他遭遇到外部环境的挑战时,此前脆弱的价值观就变得摇摇欲坠。外部世界正在侵入他的内心,迫使他改变内部的生态。
事实上,王威廉善于书写那些格格不入的人。他们虽然已经社会化,但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初始状态”,而与世界/外部的对抗就成了文学的主题。就像《倒立生活》里的“我”与“神女”,他们与外部世界呈对抗状态,并且他们反抗的是无处不在的“重力”。王威廉的小说里,主人公常常是对现实不满的人,他们也会有抱怨,但并非是对具体事情的不满,而是具有穿透事物表层的目光,抵达了问题更本质、也更遥远的地方。但是,那些本质问题往往是无解的,它们背后可能是一片虚无。好在小说家并没有义务去解答问题,文学要呈现的就是人在虚无的本质中的纠结、反思,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生而为人的意义。
这也是王威廉小说的可贵之处。他并不去简单复刻现实主义的鸡零狗碎,简单地演绎生活里的愁苦。他的人物永远带着格格不入的场域,保持在某种冲突的境况里,因而主动或被动地具有了哲思气质。
空间
王威廉小说中的空间别具意义。在许多作品中,人物都与逼仄、压迫、神秘的空间密不可分,比如《信男》《我的世界连通器》中的仓库、《鲨在黑暗中》的地下迷宫、《非法入住》里的出租屋等等。这些空间成为人物精神状态的外化体现,同时也构建了属于王威廉的城市文学的风格。
中国的城市文学尚在起步阶段,写作者们仍在摸索城市文学的表达方式。正巧前段时间我采访了拍摄《文学的故乡》的导演张同道老师,他提出了有关“乡村伦理”与“城市伦理”的相异之处。
按照张老师的说法,乡村里很多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人们之间有一种稳定的关系,包括爱和恨,都具有传承性,相互之间有着文化渊源;可是城市里就形成了全新的人际伦理,即使住在对门也不知道对方是何人。
在乡村,人们思考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在城市,人们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很适合形容城市人的生存状态。城市人不再生存于大的自然环境中,而是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生活体系。
每个人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时就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我,思考人与自我的关系。当我们与自我面对面时,很容易感到孤独,因为我们意识到自我本质上是孤独无依的。一切都变得脆弱不堪。我们能抓住的是什么?也许唯有记忆、情感与想象。就像卡夫卡《洞穴》里面不停寻觅的未知生物,以及贝克特许多小说里那些孤寂架空的空间。正像帕斯卡尔所说,我们发现了宇宙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我们被抛弃在了荒凉的宇宙中:
“我看到整个宇宙的恐怖的空间包围了我,我发现自己被依附着在那个广漠无垠的领域的一角,而我又不知道我何以被安置在这个地点而不是在另一点,也不知道何以使我得以生存的这一小点时间要把我固定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先我而往的全部永恒与继我而来的全部永恒中的另一点上……我看见的只是各个方面的无穷,它把我包围得像个原子,又像个仅仅昙花一现就一去不返的影子。”
这个时候,人需要一个出口,需要构建自我的精神空间。这个出口更多是指精神上的。比如《信男》里的“我”,在生活中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单位里的“我”木讷呆滞,“我”的名字就叫“王木木”),被打发看管仓库。仓库是一个封闭阴暗的空间,映照着“我”的精神状态,“我坐在桌边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老人,的确,朦胧的昏暗宛如老人的记忆,而纷飞的细尘惹起我慢性咽炎的发作,我一声声咳嗽着,感到自己的骨头就要散架了。我摊开信纸,开始写信,写信成了我和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
由于工作、感情都不顺利,挂念的女儿也随着前妻去了另一座城市,“信男”事实上对人生的价值产生了迷茫。外部的世界令他无所适从,仓库就是退守内心世界的表现。仓库既囚禁了他,也带给他安慰和安全感。但他毕竟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精神维度上需要抒发的出口,需要精神上的交流。可是现实生活里的交流只会带给他伤害(前妻的无情,同事和领导的轻蔑),写信就成了一种安全的交流方式。与其说他是给女儿、领导写信,不如说是写给自己。他要不停地诘问自身的存在,从而用这一行为确定自身的存在。
“信男”的形象酷似贝克特《马龙之死》一类的主人公,他们仿佛处于濒死状态,外部世界极力想要抹去他们的存在。然而,为了使自己不至于人格解体,他们用回忆、写作、讲故事来抵御虚无。《马龙之死》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依靠喃喃自语的讲述,回忆甚至编造记忆,创造出一个个并不曾存在的人物,由此来确立自身。
“信男”就是“马龙之死”般的人物,他痛恨像垃圾桶般的邮筒,但理由却是“从来没弄丢过我一封信,一封都没有,真他妈的混蛋,对我这样的信男来说,为什么不弄丢我的信呢?那样我就可以一封又一封地写下去,而不必担心会改变这个世界的什么结构,哪怕是风吹草动的小小改变”。
写信(或者说写作)这一行为已经不是为与他人沟通,而是为自己的存在找一个理由,具体的对象已不再重要,他所面对的是存在的虚无。
《我的世界连通器》则将“出口”具形化了。小说里的主人公仍然工作在仓库里,原因比《信男》更加荒谬——因为“我”与领导同名同姓,因而引起了憎恨。但故事发生的地点则转移到了主人公“我”的家中。“我”无意中邂逅了一名神秘的邻家女子颜如水,两个人迅速坠入肉体的欢愉中,尽管后者是有男朋友的。近似动物性的享乐使“我”感受到了某种情感的空洞与幻灭。“我”想爱,却不敢触碰爱,身体的享受反而使“我”愈加孤独。最终,颜如水离开了,空调发生火灾,拆掉空调后“我”的房间里出现了一块空洞。奇怪的是,洞却带给“我”莫名的安宁,它仿佛成了“我”与世界的“连通器”,让我感到了“生命的富足”。
“洞”象征了一种精神的出口,同时也暗暗指向了写作的意义所在。
写作
写作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此巨大,以至无从回答。我突然想起佩索阿的一句话“通过迷失去寻找我们的人格”。也许,写作就是在命定的迷失中所做出的艰苦追寻,从而更加看清自我与世界。因此写作不会提供答案,它永远是一种过程,就像是人一生漫长的行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
出于有意或是无意,王威廉有为数不少的小说里都出现了“写作者”的形象。有时,写作者是与主人公相遇的他者(如《神女》《捆着我,绑着我》等),更多的时候则是主人公自己。我想,原因除了王威廉对于写作者比较熟悉外,选择于此应该更有深意。得说明的是,作家写作家并不是容易的事,甚至是冒险的。正如理查德·耶茨在小说《建筑工人》开头写的那样:“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作家写作家,很容易陷入自恋或自怜,再加上,读者虽然在读小说,但并不一定对作家这个身份本身感兴趣。王威廉一定也知道这个“忌讳”,不过,他还是毫无负担地让大量的写作者形象出现在文本中。
在王威廉的小说里,写作者形象承载了两种作用:启迪与探索。前者如《捆着我,绑着我》,主人公因为一只猫无意中结识了5 楼的邻居——没错,是一名女作家。当时,主人公正深陷在自身的困惑中,他与女作家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交谈。这里“作家”的形象赋予了对话以“合法性”,毕竟当她说出“人在完全面对自己生命的时候,或说完全置身在自己生命当中的时候,人是无法承受的”这种话时,她如果不是作家或哲学家,确实不太符合常理了。最后,面对主人公关于自由的困惑时,她提出了一种荒谬的解决方法:用绳子绑着自己,人为造成困难,将无形的、虚无的困境,转化为有形的、可感的常态。类似荒诞的场景也出现在可视作姊妹篇的《倒立生活》中。里面的女主人公“神女”和“我”为了对抗生活无形的“重力”,将家具利用绳索全部固定在天花板上,过上了倒立的生活。这里,写作者的形象承担了启迪、引领的角色,将主人公引向未知的生活。
而另一种写作者形象,则更加贴近作者本身——外部世界小心翼翼的探索者。就像前面提到的“信男”,写作是他们与世界沟通的“连通器”,也是他们思考人类本质问题的渠道。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是在过程中获得意义的形式。写作者的形象能够比较便利地呈现这种探索的精神维度。
与此同时,写作者也在反思着自身。小说《生活课》里,作者就安排了一出家庭“闹剧”:中文专业出身的“我”由于跟妻子争论该谁洗碗,造成了家庭冲突。妻子说出了这么一番话:“你的生活就出在这里,总是不屑于谈论生活的问题。”“一地鸡毛就是生活的本质,我看你到今天也不明白,每天活在真空里似的,一点也不现实,一点也不脚踏实地。”
话既是小说里面向读者的情节,我想,也是作者王威廉对“写作者”形象的反思与戏谑。对于写作者而言,生活是“超越一地鸡毛的努力”,但很多时候,写作是写作者们的避风港,“超越”“探索”也可能转为“逃避”。就像是在王威廉小说中几次出现的“仓库”意象,里面就隐隐有着与世隔绝的意味。
出世好,还是入世好?这是一个争论了上千年的问题。也许“避而不得”才是常态。写作者想要逃避生活,逃进故事和文字中,那确实是精神上的安全地带,却时常如沙堡不堪一击。写作者的心灵由于不甘于受外部世界侵入而真诚,但同时也可能滋生另外意义上的虚假。对此,王威廉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小说《第二人》中,王威廉进行了一次对写作者形象解构式的书写,并且拿“自己”开刀:“我”——也就是作者本人,曾发表过小说《内脸》(这也是王威廉真实发表过的一篇小说)的作家,莫名其妙被绑架了,并且被送回了小时候上学的故乡。绑架“我”的人是“我”的小学同学刘大山。刘大山因为玩汽油瓶烧坏了脸,毁了容。在小学时代,他就是孩子王。而刘大山绑架“我”,正是跟“我”发表的小说《内脸》以及“我”的作家身份有关。
原来,刘大山进入社会后,他的一张丑脸总是带给身边的人恐惧。他活络地利用了这点,霸占了老板的女儿,之后生意越做越大。毁容的脸成了他震慑别人的法宝。就像是从古至今的弄潮儿一样,他已经熟练地运用别人的恐惧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不过,他什么都有了,内心却异常孤独。世界上并没有人真正理解他,他靠暴力去驯服他人,却无法得到满足。后来,刘大山无意中读到了“我”的小说《内脸》,认定“我”是可以理解他的,便将“我”绑架过来。要注意的是,刘大山所要的“理解”,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解释,而是真正的、消灭了人与人之间心灵隔阂的“终极理解”——成为他。
小说即是打破心灵隔阂的努力,但也只是一种无奈之举,或者说替代品。因为心灵的隔阂是无法被打破的,正如哲学家康德将世界分为“表象”与“物自体”,前者可以通过感官和理性去认知,后者则是完全无法被认知的客体。他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无法被认知的永恒客体。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隔阂是注定的,像经典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人类补完计划”,就是要打破心灵的隔阂——利用大冲击,将人类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自我与他者的隔阂。这恐怕是我见过的对人类最骇人听闻,也是最悲观的审判。
小说的结尾同样骇人听闻。认识到心灵隔阂无法消除的刘大山,选择了“另辟蹊径”——让“我”真正理解他的方式,就是把“我”也毁了容,成为他。当“我”置身于和他同样的境遇中,理解确实比想象要更进一步。
同时,这也是对写作行为的一种“诛心”的颠覆。作为写作者,我们真的能理解他人吗?我们所谓的理解是不是只出于我们的一厢情愿?我们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认识自我、他者和世界?
历史
人类的世界总是置身于两种时间中:过去和未来。所谓“当下”转瞬即逝,与其说它是时间,不如说是状态。因此,人最需要了解和思考的,就是关乎过去和未来的问题。过去的事构成了历史,而历史则对未来影响深远。
在王威廉的小说里,有一部分即是直面历史的作品,它们探讨的不再是当代人的生存境况、爱情、迷茫等等,而是以当代生活为基点,增加了历史维度。这批小说以《书鱼》《绊脚石》《鲨在黑暗中》等为代表。
《绊脚石》的历史感非常强烈。小说以“我”在火车上偶遇了一位欧洲血统的苏奶奶为开端,勾连起了苏奶奶和“我”祖辈们的苦难史,并且,作者选择的节点和身份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苏奶奶的祖辈是奥地利的犹太人。1938年,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公开化,苏奶奶的父母想要借助中国大使何凤山的帮助,逃离德国。不过,苏奶奶的父亲只搞到了一张签证,就让已有身孕的妻子先行一步到达上海。没想到,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一别即是永别,她再也没得到过丈夫一丝一毫的消息。
后来,苏奶奶在一家教会医院出生,为她接生的医生接纳了她和她的母亲,成了苏奶奶的中国爸爸。在交谈中“我”得知,苏奶奶将要去香港,从香港坐飞机去维也纳,也就是她的家族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苏奶奶随身带了一块刻着她外公外婆名字和简介的黄铜板,她要把黄铜板镶嵌到曾经他们生活过的地方,成为一块绊脚石,“它是不会绊倒任何路人的,它要绊倒的,是曾经对人类犯下罪恶的人,是对这些罪恶无知的人,是还想继续犯罪的人”。
这里,“绊脚石”的意象成为一个宏大的象征,它代表着作者对历史的态度——不但不能遗忘,还要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告诫人们,因为“现在,就连战争的遗迹也没有了,就像从来没打过仗,世界永远是和平的,永远是平静的”。
人类重蹈覆辙,往往源于历史很容易被遗忘,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同样会导致深刻的教训:傲慢。现在我们是否自认为已经熟知了历史,从而掌握了历史规律,可以跳出历史规律?对此要打个问号。世界依旧动荡,我们是活在历史中的人,无法真正看清历史的真面目。“历史不能被遗忘”固然已经成为共识,但历史同时却成了一种景观,一种政治正确,一种游戏,一种标榜,唯独缺少了最重要的感同身受——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法避免,历史则是超越隔阂的唯一可能。因此,最后“我”才会说“我是真的想先把自己给绊倒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忍受不了一点滞涩,变得太平滑了。我也变得太平滑了,我已经让太多东西就那么轻易滑过去了”。
相比《绊脚石》的“纯正”,《鲨在黑暗中》则可看作前者的反面。《绊脚石》里,“我”对历史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而《鲨在黑暗中》的“我”以及“我”的家族成了中国近当代历史的缩影。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了一系列大历史,“我”以及“我”的家族选择的是逃避历史,逃避历史对个人的戕害。
小说中,“我”的祖先曾死于天地会与清兵的战斗,并且据说在三元里杀死过英国侵略者。后来,为了躲避战乱,“我”的曾祖父将小地窖改造成了密室。清朝灭亡,军阀混战,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时,曾祖父便躲进了密室中。之后,孙中山准备北伐,曾祖父投身革命,结果杳无音信。到了“我”的祖父那辈,继续修缮、扩大地下密室,成功躲过了日本侵略战争。抗战胜利后,祖父开始在市教育局工作,因为写了“反诗”流放边疆,再无音信。
从“我”的家族史中,能够看出荒诞又合理的“魔咒”:“我”的家族的命运均被绑在了历史这架马车上;并且,作为逃避历史的地下室,曾祖父和祖父借此躲过了战乱,毫发无伤,可一旦走出密室,投身历史,便会得到悲惨的下场。
很明显,这是作者故意为之。历史在这里更加复杂化了,如果说《绊脚石》讲述的是“历史之后”的人该如何面对历史,那么《鲨在黑暗中》则直接讲述的是“历史之人”。历史在这里成了欲望与厄运的混合体,“我”的祖辈们并非是单纯被历史裹挟的人,恰恰相反,他们主动追逐历史,最终被历史吞噬。
“我”以及“我”的父亲,正好对照《绊脚石》差不多即是苏奶奶和“我”之间的同辈,面对历史的态度却截然相反。《鲨在黑暗中》里的父亲被历史吓坏了,从此只躲进密室中。此时,地下密室经过几代人的修筑,已经宛如迷宫般复杂,而“我”就是成长于地下迷宫中,与历史隔绝开来。对于父亲和“我”而言,历史是可怕的事物,会带来厄运。
恐怕,比起《绊脚石》里充满责任感的“我”来说,《鲨在黑暗中》的“我”更接近真实的普罗大众。历史面前,个体都是渺小的,比如我们经常会用“螳臂当车”来形容看不清历史大势的人的可笑而悲惨的命运。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在那胜利者的背后,却有无数个“我”的祖辈。
那么,面对历史,我们作为个体究竟何为?是像《绊脚石》里的“我”那样主动承担历史,还是像《鲨在黑暗中》的“我”对历史避之不及?也许,这个问题过于巨大,无法简单给出答案。不过,王威廉还是隐隐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鲨在黑暗中》再次出现了“写作者”的形象,也就是“我”的父亲。而他的写作,源自恐惧。在这里,写作不再是为了沟通,正如父亲写什么他人无从知晓;在这里,写作回归了本质——与自我的对话。父亲的形象犹如卡夫卡,后者写下了荒谬的人类社会的预言,但卡夫卡的本意绝非成为一个“反乌托邦”的作家,他的写作同样出于恐惧,笔下的世界不过是其恐惧的缩影。正是由于写作者忠实地记录下了内心的恐惧,反而成了时代的预言家与记录者。
忠实,这或许是一名写作者唯一能做的事。他记录下真正的恐惧与虚无,同时,他也观照着周边的一切。由于恐惧,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意外地合二为一了。恐惧在写作这一行为中,具有了超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