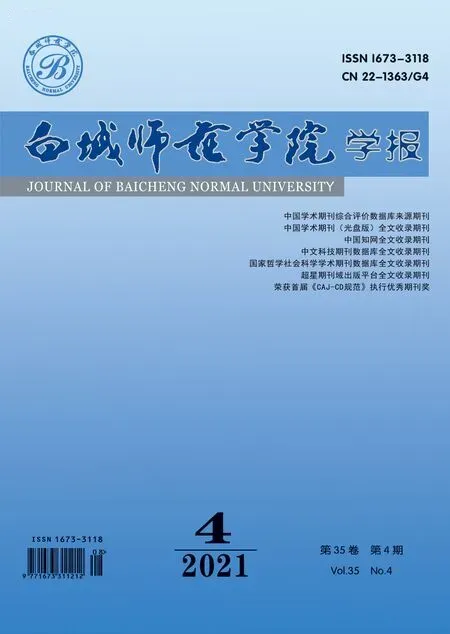荒野中的先知
——新西兰剧作家布鲁斯·梅森及其早期戏剧创作之管窥
李伟娟
(白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布鲁斯·梅森(Bruce Mason,1921-1982)是新西兰文学史上第一位重要的职业剧作家,将一生奉献给了新西兰的戏剧事业。他“对新西兰舞台的贡献是任何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他是奠基人,也是里程碑,重要性就如尤金·奥尼尔对于美国戏剧的发展一样。”[1]新西兰评论家约翰·史密斯(John Smythe)曾认为,梅森的戏剧与新西兰其他任何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一样有价值,特别是对于捕捉新西兰的社会本质方面更为突出。梅森的戏剧生涯近30年,他的创作直接影响了众多的青年剧作家。梅森在他的剧本中探讨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主题:性别政治、殖民主义以及帕克哈身份认同(Pakeha,来自欧洲的新西兰白人)等。无论是以《裁决》(The Verdict,1955)为代表的针砭时弊的“社会问题剧”,以《桃金娘树》(The Pohutukawa Tree,1957)为代表的反映土著文化与欧洲文化碰撞、冲突的“毛利剧”,还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以《黄金季节的结束》(The End of the Golden Weather,1959)为代表的展示青少年成长历程的“独角剧”(solo play),均对新西兰戏剧舞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虽然一生都饱受争议,喝彩与抨击并存,但始终坚守他钟爱的戏剧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梅森集演员、经纪人、导演、剧作家、评论家于一身,五次获得英国戏剧联合会创作奖,并获得奥克兰全国戏剧创作竞赛奖和国家文学基金会奖学金。
一、布鲁斯·梅森:荒野中的先知
20 世纪50 年代的新西兰戏剧没有形成文学潮流,“由于缺少戏剧赖以生存的观众,缺少专业创作团队和专业剧团,也由于受剧场的限制,本地的戏剧创作多年来一直停留在业余水平上。”[2]正是以布鲁斯·梅森为代表的本土青年剧作家的异军突起,为新西兰戏剧注入了新鲜血液。梅森“摆脱了当时流行于欧美的自然主义,建立了自己的风格”,[3]为新西兰戏剧舞台带来了一股清流。
布鲁斯·梅森于1921年出生于新西兰的首都惠灵顿。他的父亲极具喜剧天赋,母亲曾为他的木偶剧院做了一个红色镶边的天鹅绒幕布。这种家庭氛围使他从小便对戏剧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成为他日后走上戏剧创作之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1940年,梅森在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读书期间,尽管主修法律和语言,他仍积极参加大学生戏剧俱乐部的各项活动。1941 年,梅森参军,进入新西兰皇家海军志愿预备役部队服役,1943年离开新西兰前往英国途中,他看了一些战时剧场的演出,特别失望,便萌生了自己创作戏剧的想法。二战期间,在英国伦敦,梅森不仅深受浓厚的反法西斯情绪的影响,而且还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梅森在戏剧创作中表达政治意图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梅森认为戏剧不能只是作为中产阶级消遣或娱乐的工具,而应当大力宣传政治;戏剧更应该致力于反法西斯和批判中产阶级伪善的价值观。1945年从海军退伍后,梅森从伦敦回到惠灵顿,在维多利亚大学完成了学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梅森与未婚妻戴安娜·肖(Diana Shaw)结婚后,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惠灵顿联合剧院工作,他曾担任联合剧院的秘书,扮演过一些小角色。1947年梅森当选该剧院的经理。梅森一直在酝酿创作关于新西兰和新西兰人的剧本,因此于1949年辞去了联合剧院的工作,携妻子去了伦敦,希望能够从英国剧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并适当发展自己的风格。在英国,梅森与剧作家约翰·博因顿·普里斯特利(John Boynton Priestley,1894—1984)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在伦敦梅森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1952年,梅森与妻子回到惠灵顿定居并重新到联合剧院工作,开始了自己的戏剧创作。梅森为了在舞台上完美地呈现自己的作品,使其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在得心应手地运用英语创作的同时,他不仅学习了拉丁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汉语和毛利语,还钻研音乐,为自己的剧作作曲配乐。
在梅森近30年的戏剧创作中,他的题材均源于自己的祖国新西兰,并将新西兰和新西兰人置于剧本的中心地位,英国人物是以外来者的身份出现在他的剧本中,均为陪衬人物,次要角色,而他们的殖民地“表亲”新西兰人则是主要角色。尤其可以称道的是梅森在20 世纪60 年代创作了以毛利人生活为题材的5 部毛利剧,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毛利文化与欧洲文化互相碰撞、互相渗透的主题。20 世纪70 年代梅森又专注于独角戏的创作与巡回演出,观众反响强烈。
梅森一生创作了34 部剧。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强烈渴望社会安定,希望能为存在的社会问题找到满意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他又偏爱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希望人人都能言所欲言,行所欲行。”[4]简而言之,梅森特别注重戏剧的社会功能,并对这一创作初衷始终坚定不移。梅森对新西兰戏剧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他自己却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新西兰最了不起的剧作家,但我的确是最持之以恒的一个。这些年来,我同其他许多人一道创造了新西兰戏剧发展的大好气候。戏剧是我们的主要艺术,今后无疑会大放异彩。”[5]梅森被誉为“荒野中的先知”,毕生致力于创建新西兰本土剧院的艺术家,为新西兰乃至西方戏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布鲁斯·梅森的早期戏剧创作:浓缩的现实世界
布鲁斯·梅森的戏剧生涯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大致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梅森在其早期剧作中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新西兰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但他对中产阶级的批判仍然停留在道德层面。
梅森在20 世纪50 年代初开始在新西兰的戏剧界崭露头角。他于1953 年创作的第一部戏剧《爱的契约》(Bond of Love)在惠灵顿的联合剧院上演后,便一鸣惊人,大受欢迎。同年6月,《爱的契约》在由惠灵顿联合剧院组织的全国戏剧比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一个月后,该剧在一年一度的英国戏剧联合会(the British Drama League)“惠灵顿节”(Wellington Festival)中赢得了新西兰最佳剧本奖杯。在随后的5 年间,梅森陆续创作了《晚报》(The Evening Paper,1953)、《裁决》(The Verdict,1955)、《特许粮店》(The Licensed Victualler,1955)、《适例》(A Case in Point,1956)、《绞尽脑汁》(Wit’s End,1956)以及《荒野之鸟》(Birds in the Wilderness,1957)等剧作。
梅森最初的戏剧创作尚未摆脱英国戏剧传统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束缚,如在《爱的契约》《晚报》等剧本中,梅森塑造了一系列来自英国的人物形象,并通过这些人物的视角来审视新西兰。在《爱的契约》中,英国姐妹埃德娜(Edna)和萨莉(Sally)怀揣梦想来到新西兰,希望能过上“乌托邦”式的生活,而她们不得不面临严酷的现实,她们被两个以自我为中心、要求苛刻的男性所利用。埃德娜经常被丈夫伯特(Bert)殴打奴役,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最终与伯特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埃德娜允许伯特与其他女人满足自己的性需求,他就可以与埃德娜保持婚姻关系。事实上,他们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对于萨莉来说,她甚至没有机会与她所谓的男朋友乔治“签订”姐姐与姐夫那样的“契约”,因为乔治拒绝娶她,但她要随时随地、无偿地满足乔治的性需求,她被迫过着极有可能沦为妓女的单身生活。梅森在《爱的契约》这出剧中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性爱问题以及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所处的低下地位,借此抨击了新西兰当时的婚姻制度。通过伯特和乔治这两个人物形象,梅森揭露了新西兰中产阶级男性的两面性及其伪善行为,他们私下交往无度,而在公共场合却冠冕堂皇,如正人君子一般。同时,这部戏也反映了梅森对理想的中产阶级婚姻生活的深度思考:性爱不是婚姻生活的全部,幸福美满的婚姻要建立在夫妻双方平等、尊重、互敬互爱基础之上,而女性要获得幸福、平等的婚姻,不仅要摆脱男性的压迫与束缚,更要自强自立、自尊自爱。
《晚报》是梅森创作的备受争议的一部剧,很多人认为这部戏歪曲了新西兰人的形象。《晚报》的背景设置在一个传统的新西兰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之中,这个家庭中温顺的父亲欧内斯特(Ernest)整日埋头于晚报之中,母亲埃尔弗里达(Elfrida)是一个趋炎附势、善于钻营的势利小人,他们唯唯诺诺的女儿温瑟姆(Winsome)被其母牢牢掌控着,他们的远房亲戚菲利普(Philip)从英国来。在原版中,菲利普是剑桥大学的心理学讲师,在修订版中,菲利普被塑造成一位诗人,在新西兰南岛的山脉中寻找他的缪斯。菲利普闯入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中,试图改变他们的价值观。菲利普竭尽全力启蒙温瑟姆,让受到严密保护的她“睁开眼睛”,但他却无法打败强大的埃尔弗里达。菲利普无奈回到了英国,温瑟姆仍然安全而感激地依附于母亲的束缚之中,而父亲欧内斯特则继续在他的报纸里“冬眠”。借助这部戏,梅森抨击了中产阶级家庭根深蒂固的陈腐观念对下一代成长的不良影响。尽管在菲利普的鼓动下,温瑟姆一度试图走出母亲为她构建的“牢笼”,但她的反叛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只能安于现状,继续做母亲的乖乖女。温瑟姆的脆弱虽源于母亲的强势,但更与父亲的不闻不问密切相关。在温瑟姆的生活中,作为父亲的欧内斯特只是个旁观者。梅森似乎在告诫人们,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席。
从《裁决》这部剧开始,梅森笔下的人物完全“去英国化”,所有人物均为地地道道的新西兰人。《裁决》是梅森于1955 年创作的,这部剧的创作灵感源于一起真实的谋杀案。梅森以一年前在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发生的臭名昭著的谋杀案作为该剧的蓝本,批评和驳斥了新西兰中产阶级的社会价值观。15 岁的波琳·帕克(Pauline Parker)和 16 岁的朱丽叶·胡尔梅(Juliet Hulme)在公园用袜子里的一块砖头作为武器,谋杀了波琳的母亲。这部剧的标题与其说是针对陪审团的裁决,不如说是针对中产阶级道德的判决,同时,抨击了中产阶级评判谋杀的双重标准。正是这样一群中产阶级观众,在媒体的怂恿下,乐于看到这起谋杀案成为流言蜚语的素材,而一年后却不再理会他们曾经认为梅森在这部剧中使用了所谓不恰当的主题。梅森创作这部戏的真正意图在于揭露和抨击中产阶级的伪善,而非针对陪审团对这起谋杀案的裁决。
《裁决》之后,梅森借助《桃金娘树》和《黄金季节的结束》两部剧,畅快淋漓地发出了新西兰本土的最强音。约翰·史密斯认为《桃金娘树》是一部真正伟大的剧,是每一个新西兰人和海外游客一生中都应该不止观看一次的好剧。《桃金娘树》为梅森的早期戏剧创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结语
梅森这位“荒野中的先知”,一生致力于新西兰的戏剧事业,对新西兰及西方戏剧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梅森的戏剧舞台便是一个浓缩的现实世界。通过描绘现实世界,梅森揭露了新西兰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良好愿望,希望人们通过相互间的宽容和真诚,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6]而从他的早期戏剧创作我们便可窥见这一创作基调,即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通过戏剧舞台,梅森力图使新西兰人坚定改变混乱的旧世界、建立和谐的新世界的信心。梅森的早期戏剧创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戏剧传统,为新西兰现实主义戏剧的日趋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