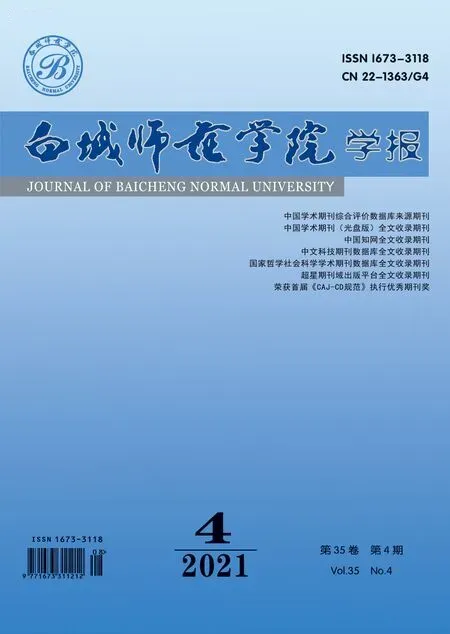论洪峰小说中个体对孤独的抗争
李 博
(白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洪峰是善于描写孤独的,其塑造的主人公不论时代、不分男女、不计年龄都可以处在孤独的状态中。孤独可以用来当作其笔下主人公通用的标签,这种强烈的孤独感,首先来源于作者本人的生命历程。回顾洪峰的人生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拥有强烈的、独立的、自由的人生观、价值观,他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不介意他人的眼光,甚至逐渐远离世俗的社会生活,在已有的人生中,洪峰勇于打破既有的规则,并能够坚持自己的选择,这种种行为都标榜着洪峰始终处于孤独的人生状态。于是,孤独也就成为其一以贯之的审美表达方式。与此同时,洪峰把自己在生命中闪耀的抗争精神,也投射到其小说的主人公身上,让孤独的个体抗争成为他们的自带属性,下面我们就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了解洪峰笔下个体抗争过程中产生的孤独感。
一、抗争的对象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曾说过:“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1]这句话中很有意思的是主语的变化,从“我”到“我们”。当生命个体遭遇荒谬的时候,必然会对自己的生命状态产生质疑或否定,此时,反抗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我反抗”中的反抗行为不只是为了个体,而是在抵抗荒谬现实的同时,使每一个人都不再感到荒谬,从而达到“我们存在”的目的。从古至今中西方文学中都不缺乏勇于奋起反抗的人物类型,从加缪的《局外人》中被判死刑的莫尔索到鲁迅《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遗憾的是走上抗争之路的个体面对荒诞的世事,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天生属于少数派,存在本身就是孤独的象征。他们为了改变世界而抗争,却不被世人所理解,洪峰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也没有逃离这种命运,他们一方面要同现实中的荒谬相抗衡,另一方面还要抵抗弥漫在心底的孤独情绪。
《湮没》中的小职员、《奔丧》中的秘书、《蜘蛛》中的经理,他们都在各自的生命中陷入无法言说的虚无与荒诞之中。“那些日子我十分无聊,有点想不出办法打发日子”,“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的头很疼同时又感到空虚和无聊”。[2]《湮没》中的小职员在小说一开始就已经处在空虚、无聊的人生状态中,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并尝试寻求解决之道,于是他开始谈恋爱,与异性的交往帮助他有效地打发时间,主人公甚至乐观地认为熬过初夏进入盛暑或者秋天冬天他的情绪就会好起来。小说中“我”对自己的问题认识得很清楚:“我最大的愿望是人们不注意我最好是无视我的存在。”“我怕和别人交谈……因为你不得不说一些你不想说的话却不得不把想说的话闷在心里”。[3]主人公感到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虚伪、麻木与欺骗,其他人能够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主人公却敏感地感知到这种生活本身的无意义,但是他显然不清楚真正有价值的生命是怎样的,所以只得本能地对抗荒诞的现实。但是抵抗的行为又带来新的问题,因为孤独是生命的本质,女朋友只能提供肉体的刺激,却无法排解内心深处的痛苦。小说中作者描写主人公深夜独自一人行走在雨中,通过孤独地拥抱自然而感受到生命的乐趣。无独有偶在小说《奔丧》中,洪峰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小知识分子。小说在主人公的思想意识中展开叙述,而“我”在叙事时常常游离于现实与幻想之间。主人公仿佛站在高处俯视现实世界的种种闹剧,无论是亲属之间的争执,还是吃饭、睡觉这样的日常行为,甚至是父亲的遗体与葬礼,他全程以旁观者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其孤独而独特的精神世界。在主人公绝对理智而冷漠的叙述中,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荒诞的感觉。这种面对现实世界的方式,就是主人公对抗荒诞的表现,而他违背世俗常理的行为也使其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从现实到精神,主人公都处在孤独的反抗之路上,而他反抗的对象即由血缘、道德、伦理构筑的虚伪的生活。如果说上两篇文章中的主人公还是过于消极,缺乏明确的反抗行为,那么《蜘蛛》中的经理在面对相似的孤独感受时,则更加主动地进行了反抗。主人公在前半生白手起家,拼命赚钱,不惜为此背弃良心,忽略家人,但是当他终于获得一定的财富时,他为之奋斗的初衷早已消失。朋友的冷漠、家人的离心,导致他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于是他作出一系列的举措试图得到救赎:他考上了大学,却不愿意就读;他给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却没有真正的善意;他无意中帮助了一位陌生人,刚刚感受到“生活变得有意思”,却发现对方是个骗子;他与妻子原本是患难与共,却不能够有福同享。他所有的反抗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失去一切只剩下金钱的主人公也彻底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迷失在金钱织成的罗网中,品味孤独的滋味。
洪峰的小说常以荒诞为出发点,以荒诞的生活为反抗的对象,塑造了一系列反抗者的形象,他们在面对空虚、无聊的生命时,孤独地尝试做出改变,却最终失败重又归于孤独。但是在抗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究竟是什么。[4]
二、抗争的过程
存在主义的先驱雅思贝尔斯认为人生有界限状况。所谓界限状况是指当人在生理上遇到极端的情况,如生病、性命垂危,此时人就可能清楚地认知死亡终究不能逃避;而在伦理的角度上,当人们因自己或他者遭遇到不公平、不公正待遇,而对世界上的善恶报应产生怀疑时,那么他们就处在精神与道德的界限状况。生理上的界限状况在人生中时常会出现,即使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亲人、朋友的离去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识;而伦理上的界限状况在战争年代或者世事动荡的年代容易发生。洪峰小说中就经常描写发生在战争中频繁而轻易的死亡,在十年浩劫中人与人之间的倾轧、迫害,而后期创作中作者多以金钱、性爱对人的诱惑,来体现现代人的道德沦丧,良知泯灭。每当这种界限状况出现时,就说明我们得到了一个深刻认识生命本质的机会,这时候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可能会出现飞跃,超越自我而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状态,把个体生命价值放在更高的层次上来实现,这种精神飞跃在洪峰的小说中就表现为个体生命开始孤独抗争的过程。
说到抗争的过程,小说《瀚海》中姥姥的两次出走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作者对这两次出走的描写很耐人寻味,而姥姥这一形象在洪峰的小说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她充满传奇性的一生,既体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也反映了旧社会女性朴素的抗争精神。小说中“我”对于姥姥的存在,情感上是亲近的,这种亲切的情感体现出作者对姥姥寄托着独特的审美情感。不同于作者对奶奶或姥爷形象塑造的模糊、情感的淡漠,对姥姥的描写具体而不乏温情。姥姥的恋爱、婚姻、生育儿女、老年生活统统用相对温情的笔调呈现出来,小说中多次写到“我”与姥姥的互动,但是着墨最多的还是关于姥姥的两次出逃。第一次出逃的过程作者写得相对简略,姥姥与地主家少爷偷情,并生下了一个女儿,由于女婴被姥姥的父亲残忍地溺死,为了反抗父亲的暴虐,实现自己的爱情,姥姥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出走,而出走的结果即爱情的结束。情人的惨死对姥姥的打击可想而知,作者有意忽略了对姥姥情感或思想的描写,留下的唯有姥姥形单影只后的孤独境遇。相比第一次反抗家庭、争取爱情这样明确的原因,姥姥第二次出逃的过程被细致地表现出来,却忽略了出走的缘由。这次姥姥已经嫁人,嫁为人妇的姥姥在“一点兆头也没有”的情况下离家出走。她要逃离的是身边的男人或者是贫瘠的生活,对于这次出走作者用唯美的笔调描绘了黄昏的乡村景色,“高远的天空”,“几片绒绒的云安详地悬浮”,“几株黑色的树探出黄绿色的庄稼地十分孤寂”,[5]一幅幅静寂的图景衬托出姥姥出逃之路的孤独,是不是正是为了逃离这种孤独、寂寥的人生状态,逃离这片荒凉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男人,姥姥才决然地出走,然而人生是荒诞的,人们无法预知未来,第二次出逃以更加戏剧化的方式结束了,迷失方向的姥姥最终自己走回到决心逃离的村庄。“命中注定”姥姥的两次出走都惨淡告终,但是每一次出走都是姥姥自主意识促成的对生活的自主反抗,在一次次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姥姥虽然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却勇于承担反抗带来的危险与责任。每一次选择出逃都把姥姥置于更加孤独的境遇中,却也显示了姥姥本质上具有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朴素愿望,且为此付出了努力。当姥姥回到姥爷家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反抗之路的结束,是不是说明姥姥真的认命了?笔者认为姥姥的反抗并没有因出逃失败而结束,当她面对愤怒的姥爷时,她“夸张地叫一声就扑进对方的怀里”,这种行为显然是姥姥面对看似不可改变的命运,开始使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新的反抗:如果不能逃离那么就征服他。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姥姥生命价值的真正所指,但是在一次次出走中,姥姥的个体生命不断选择成为真正的自己,甚至在姥爷死后,当婚姻的禁锢解开后,姥姥因儿子的不孝而选择再次离开。如此一来,姥姥的一生完成了从父亲、丈夫、儿子的压迫中自觉的三次反抗,反抗的过程虽然或是荒诞、或是失败,但是当“我看见姥姥十分安静地躺着,跟睡觉时没有两样”[6]地离开人世时,“她依然十分高大”,我们无法否认姥姥的个体生命价值应该是实现了的,因为只有自由的灵魂才能无惧死亡。
三、抗争的结果
如果真实的世界是荒谬的,当个体生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以它为出发点,就很容易把我们原先建立的一切虚幻知识与价值观全部打破,再重新开始建立新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就是个体生命抗争的结果。就像《和平年代》中的秦朗月,她的一生都在不断面对生理与伦理的界限状况,丈夫死于战争、爱情被扼杀、“文革”中受迫害、儿子的成长,她总是在不同阶段感到生活的痛苦与命运的无常。但是秦朗月作为一位深情的妻子、一位坚强的母亲、一名理智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她总是进行孤独的抗争,如帮儿子打架、反抗李树满的侵犯、接纳孤儿盼盼,每一次反抗都让她的思想出现质的飞跃。秦朗月在一次次接受了现实的基础上,一方面心里知道现实生活的荒诞与不公,另一方面只能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改变自己,适应社会的改变,找到生命新的意义,做出选择后形成新的自我。因为人生是荒谬的,所以要幸福只能靠自己争取,在人生的旅途中,反抗者抗争的结果无外乎孤独地追逐生命中的幸福,让自己尽量增加对生命的品味能力,以及对生命的把握。
相对比秦朗月成功地在孤独的抗争中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思想飞跃,也有人因抗争失败而惨淡收场。个体生命存在世界上的意义有时体现为获得他人的理解,当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或者想要被理解的对象拒绝理解自己时,就是人生价值不能实现,也就是人生失去价值。既然人生没有意义,那么个体生命似乎只有一死了之。洪峰在对生命的价值进行思考的过程中,为生命价值的实现设置了许多可能性,其中有一种实现方式就是他人的理解。在长篇小说《和平年代》中,李树满这一人物形象就验证了洪峰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也展现出抗争的另一种结果。小说中李树满曾经是文工团的领导,在试图强奸秦朗月失败后,也经历了人生中种种磨难与痛苦,当他再次见到秦朗月时,已经对自己当年的行为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于是,抱着赎罪心态的李树满希望获得秦朗月的宽恕,当他善意地接近秦朗月一家人时,却被明确地拒绝。这种拒绝成为李树满的心结,当李树满把自己人生的意义寄托在秦朗月的理解与宽恕上时,为了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为了追寻内心的平静,他开始坚持每天去秦朗月家门口等待,在等待中得到精神的抚慰。显然,李树满认为时间可以帮助他获得秦朗月的理解,但是这种孤独的坚守并没有换来理解,只是加深了李树满内心的虚无感。所以,当孩子们拒绝李树满的礼物时,也就关闭了李树满实现生命价值的大门,意识到这一点的李树满最终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李树满每天撒网捕鱼,其目的不是捕鱼,固定的地点、收获的微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捕鱼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孤独的守候,但是,被救赎的目标随着孩子们的拒绝而破灭,他的生命也就失去了价值,可见真正的绝望是一种内心的体验,无关外在目标的达成与否,所以自杀成为李树满必然的归宿。
对生命价值的不断思考应该是每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必经过程,虽然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但是“存在先于本质”却是公认的法则,不同的不过是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存在主义理论还有很多,包括主张“人是走向死亡的存在者”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及认为“一个人的本质是在选择之后所得到的结果”的法国哲学家萨特,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永远不会停止,也似乎永远不会寻找到所有人都认同的标准答案。那么,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来说,对于个体生命内涵的概括,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洪峰在运用存在主义思想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把自己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带入到作品中,也成为我们探讨其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