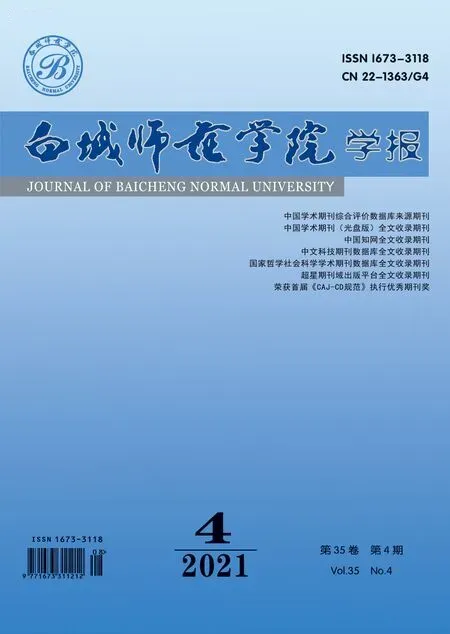戴望舒现代诗意象探究
平 燕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安徽 滁州 239000)
戴望舒在诗歌意象的选择方面较为开放,他在吸收中国古典文学精髓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基础上,从自然与生活之中采撷意象,并根据自身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抒情需求来组织意象,营造出丰满的艺术情境,在引发情感共鸣的同时,唤起读者的想象与联想。深入研究戴望舒诗歌意象的构建及其传递出的审美追求,能够帮助读者从多维度审视现代诗歌艺术,体验现代诗歌广阔而深远的美学意蕴。
一、戴望舒诗歌意象的建构
(一)“泪”的诗歌意象
“泪”在戴望舒诗歌中出现得较为频繁,含有“眼泪”“哭泣”等字眼的作品往往呈现出愁闷、迷茫、哀伤的情感基调,这主要源自外部现实和内在特质的双重作用。当时社会环境较为动荡,诗人心系家国命运,同时面临着个人理想的幻灭,内心细腻、深沉的情感不得不以诗歌的形式一吐为快,在这种情境下,“泪”的意象虽然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孤寂与苦涩,但他并未就此堕落,而是充分、热切地体验生命的悲苦,尽力保持清醒的思考,并苦苦求索人生的出路,在悲哀中流露出希望。
在诗歌《闻曼陀铃》中,戴望舒以拟人手法表达曼陀铃的“哭泣”,曼陀铃于水上升起,哭泣着徘徊至“窗边”与“花间”,却终究无法寻回“昔日的芬芳”,在反复的寻而不得中,空留失望与疲惫,只能“懒懒地,到梦水间消歇”。全诗流露出诗人上下求索、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及梦幻破灭之后的忧伤与惆怅之情。[1]这与当时阴晦的社会氛围紧密关联,包括戴望舒在内的青年群体,满怀理想与期望,始终心有不甘,但终究抵不过残酷的现实,陷入沉沦与幻灭。令人欣慰的是,在感伤低迷的心绪中,戴望舒并未失去冷静思考的能力,这使他的诗歌兼具理性与浪漫之美,散发出爱与希望的光芒。以诗歌《静夜》为例,其中包含“泪”的意象,描绘深夜时刻,“你”的低泣令“我”不安,你我陷入同样的悲哀,但在伤心的同时,“我”也深知眼泪无用,便给予“你”安慰,并邀“你”细述悲伤的原因,在沉寂微凉的深夜里,“人静了,正是好时光”。可见戴望舒并不甘心沉沦于悲伤的情绪,而愿意敞开心扉,积极应对生命的考验,这为他后来投身时代洪流,为民族大义而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梦”的诗歌意象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反映出“寻梦”的过程,在他的诗歌中,有二十首左右包含“梦”的意象,表达出对自我命运的感慨、对现实社会的无可奈何、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面对激烈的社会变动,文学创作显得迷茫,戴望舒也曾陷入这样的沉郁心绪之中,加之个人感情受挫,使他产生“人生如梦”的哀叹,一时间心灵无处安放,只能在梦中寻求依托,这在诗歌《生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人丧失生活兴致,只看得见人世孤苦,希望在梦里感受片刻温存。此外,戴望舒的“梦”反映出对乡野生活的追忆与向往,在《小病》一诗中,他事无巨细地描写家乡小园的菜蔬、阳光、微风,这与都市的浮华形成鲜明对比,表达出对故乡田园的思念。在另一首诗歌《妾薄命》中,戴望舒也流露出对现实生活的绝望,仿佛世界成为一片冰冷的“荒原”,可见诗人在现实中感受到无限的孤寂、疲倦,渴望灵魂在幻想的美梦里安眠。[2]
纵使诗人有千般苦闷,认为梦是唯一的救赎,终究还是要让心灵回归现实生活,这在戴望舒的诗歌中就体现为对“寻梦”的执著,诗人的特质赋予他非凡的想象力和丰盈的主体意识,使他坚信美梦终将实现,并甘愿听从命运的召唤,以艰苦的追寻和奋斗赢取那终极的幸福,这流露出诗人心性的转变,更反映出一代“寻梦人”的心灵历程。戴望舒在《寻梦者》中深刻表达了“寻梦”的坚定信念,为求那“金色的贝”,甘愿“攀九年的冰山,航九年的旱海”,并精心地呵护它、培育它,直到它于某个暗夜里绽放,“吐出桃色的珠”,为鬓发斑白的人们升起静静的梦,诗歌中那句“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具有感人至深、催生奋进的力量。
(三)“水”的诗歌意象
“水”是戴望舒诗歌中的主要意象,原因有三:一是戴望舒长期居住于南方水乡,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对水有比较亲切的情感,对“水”意象可信手拈来;二是戴望舒气质柔弱,倾向于以“水”而不是“山”作为诗歌意象,使诗歌彰显柔性之美;三是戴望舒热爱古典诗词,诗歌中自然多见“水”或与水有关的意象。
在戴望舒的诗歌中,并不侧重于描写“水”意象本身,而是将“水”视为表达诗情的方式,在《单恋者》一诗中,诗人先是赋予自己“单恋者”的身份,接着设问自己单恋的对象,是烟水中的土地?静默的落花?或是陌路丽人?再开始描绘自己“夜行”的经历,以及内心激荡的情感,流露出悲愁、沉重的心绪。[3]
但客观而言,“水”意象并非完全象征柔弱,“滴水穿石”“洪水猛兽”等词语都彰显出“水”的刚强和力量,这在戴望舒的《流水》一诗中有所体现,全诗描绘“一切的水”汇聚成“水流的集体”,冲过顽石、泻过草地,从山间、乡村、城市涌流而过,“奔流到太阳的家乡去”。从该诗所传递的情感可知,戴望舒逐渐超脱狭隘的个人情感,心灵被更伟大的理想所激荡,他甘愿做“一滴水”,参与到集体事业中去,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在后来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诗歌中,戴望舒更为热切地表达了对祖国的挚爱以及对民族解放的坚定信念,他不仅是“雨巷诗人”,更是时代的勇士,以笔为剑,刻写出爱与希望的华章。
二、戴望舒诗歌意象探源
(一)传统与现代相融合
戴望舒对诗歌意象的选择取决于“诗情”表达的需求,他既继承我国传统文学中的古典元素,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性,又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风格,赋予诗歌中西互通、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美感。
戴望舒在《诗论零札》中表达过自己对诗歌题材与意象的态度,他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其内涵,如同西子与东施之间的美丑之别,并非源自蹙眉或捧心的表现,而是由于内在本质的差异。因此,与形式相比,戴望舒更注重诗歌的内容,只要能唤起全新的“情绪”,他很乐意运用传统意象。在他的经典诗歌《雨巷》中,就提到“丁香”和“雨”这两个古典意象,其中的“丁香”别名“百结”,在很多传统诗词中象征着忧郁、高洁、美好,例如“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杜甫)、“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商隐)等。而“雨”的意象更是肇端久远,在《小雅·采薇》中就有“今我来兮,雨雪霏霏”的表达。在戴望舒的《秋蝇》《旅思》《寂寞》等诗歌中,也提到“木叶”“芦花”“春草”等古典诗词意象,赋予诗歌优雅迷人的古典韵味。
基于戴望舒包容开放的诗歌艺术观,他在采撷传统意象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思维,开始摒弃精致、华丽、浪漫的表达方式,转而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诗歌艺术,尝试用淳朴、真挚的心灵看待日常琐碎的事物,赋予它们生动的美感与深刻的感情。[4]诗歌《我的记忆》最能反映戴望舒创作观念的变化,全诗充斥着“酒瓶”“粉盒”“厌倦”“笔杆”等琐碎而质朴的意象,诗人用他的心灵和妙笔点亮了这些平凡事物,并将它们组合成优雅感人的诗篇。戴望舒欣喜于自己的新创作,对《我的记忆》这首诗格外偏爱,在戴望舒后来创作的《秋蝇》《灯》《深闭的园子》等诗歌中也沿袭了这种风格。
(二)古典与现代的美学意蕴
戴望舒注重诗情的传递,他将中国传统意象与西方现代理念相融合,赋予诗歌全新的美学意蕴,使诗歌散发独特、自然的意境之美。意境是传统文学所坚守和追求的一种艺术品位,源自“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具体到诗歌艺术,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方式将特定意象完美组合,便能生发出潜在的、含蓄的意境之美,触发人们的情感与想象。以诗歌《印象》为例,戴望舒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将“渔船”“深谷”“残阳”“古井”等传统意象相互融合,营造出凄清、落寞、虚空的意境,铃声飘落到深谷、渔船航行至烟水之中、珍珠堕入古井、残阳轻敛、微笑逝去,这一切既唤起读者对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所描绘的秋郊夕照图的印象,又使读者眼前浮现西方印象主义绘画的光影之美,在优雅、精致的形式之下,诗人内心的孤寂、伤感与迷茫跃然纸上,轻轻潜入读者的心灵深处,引人沉思默想。[5]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时代洪流的冲刷与洗礼中,他逐渐超越自我局限,走出闭锁的精神世界,由“雨巷诗人”成长为关注社会现实的“大写的诗人”。与此同时,他的诗歌也更加彰显古典与现代的交融之美,这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全诗运用超写实主义的手法融合“繁华”“荇藻”“蓬蒿”等意象,唤起读者的多重感官,引发强烈的感情激荡与独特的审美体验,诗歌一扫往日的颓废压抑之情,虽面对残酷现实,却流露出乐观向上、不屈不挠的气魄,传递激人奋进的爱与希望。
三、戴望舒诗歌意象的审美追求
(一)意象的多意化
美好的诗歌能够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和体验,使人被那“意象”的弦外之音所牵绕,反复捉摸其具有更广阔和深远的内涵,不断赋予诗句多元化的意蕴。戴望舒的诗歌便具有这样的魅力,他对生命有浪漫的追求,对现实生活有独特的思索,诗人的理想太过纯粹、美丽、神秘,无法用直白的语言进行表达,只能借助于直觉性、象征性的诗句近似地传递出来,这不免使他的诗歌显得飘忽不定,富有暗示性和朦胧美,要求人们用心品味其意象,才能一窥堂奥,获得深刻的感触和审美体验。
在《乐园鸟》中,诗人描绘乐园鸟苦寻归处而不得的情景,象征孤独的求索者怀有美好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在寂寞之中,不遗余力地追求永恒的幸福,该诗中的“乐园鸟”意象具有多重意涵。在《雨巷》一诗中,戴望舒运用了通感、象征的手法,将各种意象相互叠加,唤起读者的多重感官和主动联想,当人们诵读该诗时,那些优雅的诗句也会重生,激荡起读者丰富的审美体验。[6]此外,比喻也是戴望舒赋予意象多元内涵的常见手法,以诗歌《偶成》为例,诗人用“迢遥的梦”这一模糊意象比喻生命中的美好之物,它们永不消逝,只是“像冰一样凝结”,当“生命的春天重到”,自然冰释花开,诗人并未赋予意象特定的内涵,为读者留有广阔的想象空间,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追求。
(二)意象的生活化
戴望舒擅长运用各种意象来传达诗情,常见的意象多来源于自然,如明月、残阳、落花、秋天等。在传统哲学理念中,外在物象与人的本体之间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诗人借助自然之物的特性、色彩、规律传达内在感情,在《流浪人的夜歌》一诗中,戴望舒将残月比作“已死的美人”,在山头为她细弱的灵魂哭泣,而诗人早已厌恶人世的黑暗与荒诞,甘愿与残月同沉。诗歌《夕阳下》中,戴望舒运用“残日”“古树”“落叶”“晚烟”等意象的组合,营造出低迷、萧瑟的暮色景象,传达无法言说却又深沉压抑的寂寞与忧愁之感。[7]
除自然意象之外,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使他在平凡的生活事物里发现诗意,传递出更为诚挚、朴素、细腻的情感,最为有名的诗作是《我的记忆》,全诗一改往日浪漫、精致的风格,转而选择一些具体的、生活化的意象来描绘往昔记忆,诸如“烟卷”“酒瓶”“花片”“粉盒”等,此类意象传递出更为亲切动人的情感,瞬间便攫住了读者的心灵,那燃着的烟卷、破旧的粉盒、绘着百合的笔杆、未喝完的酒瓶仿佛瞬间被点亮了,在往昔轻软的阳光下闪动着,成了富有灵魂之物,将诗人的记忆娓娓道来,引人共鸣、令人玩味,那些记忆永不休止地在诗人耳边低语,使他凄凄地哭泣,或沉沉睡去,但诗人却永不厌烦它,因为它是诗人内心最为温柔而忠实的爱。正是由于意象的生活化,才使《我的记忆》具有质朴而非凡的美感,开启了戴望舒诗歌创作的新里程。
(三)意象的组合美
1.流动式意象组合
与形式相比,戴望舒更注重诗歌的内涵,他在意象的选择上较为开放,认为无论何种题材和意象,只要组织得当,都能达到传递诗情的目的。在戴望舒的诗歌中,经常以某一中心意象的变化、扩展,带出更多的意象元素,赋予诗歌深远、广阔的意蕴。以《流水》为例,全诗以“流水”作为中心意象,流水随着诗人激荡的情感不断汇聚,汹涌着穿过暗黑的林,冲过顽石、泻过草地,向着目的地奋勇向前,展示动人心魄的力量之美。在《深闭的园子》《古神祠前》等诗作中,戴望舒也运用了流动式意象组合的手法,强化诗情,扩展诗意。
2.轴心式意象组合
在《我的记忆》一诗中,戴望舒将“记忆”视为轴心意象,将其人格化,在叙述记忆的过程中,逐渐引出大量生活化的意象,赋予“记忆”鲜活的生命形态,通过丰富的意象群,传递出一种朦胧之美,引发读者想象与联想。在《乐园鸟》《单恋者》《我的素描》等诗作中,戴望舒都采用了轴心式意象组合的描写手法,围绕轴心意象,构建出完美的意象群,通过意象之间的互补,成功塑造轴心意象的形态。[8]
3.并列式意象组合
在诗歌《印象》中,充斥着许多并列的自然意象,例如“深谷”“烟水”“铃声”“古井”等,这些意象被诗人的悲伤情绪串联起来,相互之间形断意连,具有一致的情感基调,营造出迷茫、寂寥的氛围,传递诗人内心的悲伤与忧愁。此外,《三顶礼》中恋人的“唇”“眼”“发”,《古意答客问》中的“床头明月枕边书”等,都属于并列意象。
四、结语
通过古典意象、自然意象、生活意象的完美组合,结合现代化表现手法,戴望舒创作出情感丰富、意境深远的诗歌作品,使读者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窥探到诗人隐秘的精神世界,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通过对戴望舒诗歌意象的深入研究,能够向读者展示戴望舒诗歌的艺术技巧和风格特色,有利于读者了解现代诗歌艺术的魅力,体验其丰富的内涵与深沉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