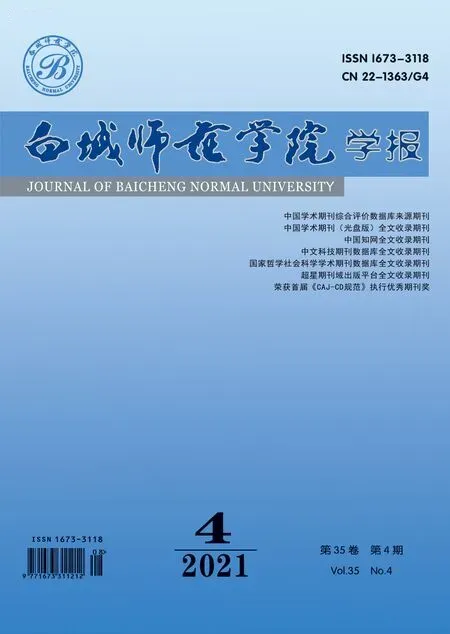黄汉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论述
王华春,邓可玉
(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管仲,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辅佐齐桓公治理国家、进行改革,使得齐国国富民强,并称霸五国。《管子》一书借管仲之名,集管仲思想之大成,但此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尤其是《管子·轻重》十九篇的成书年代,学界至今仍有争议,包括西汉文景成书说、武昭成书说、新莽成书说、战国中期说等。《管子》原有86 篇,现存76 篇,分《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等8组。囊括政治、经济、哲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管子》经济思想尤为丰富,特别是《轻重》诸篇既对中国古代经济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又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管子》问世后,历代有人评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学东渐,加之部分学者留学归来,将西方经济学说及经济政策引入国内。一方面,使得中国近代对《管子》经济思想的讨论具有了中外比较和经济学理论的特点。[1]如梁启超较早对管子经济思想进行研究。1909 年,他写《管子传》,特别辟出《管子之经济政策》一章,分析管子经济思想,开启现当代学者对《管子》经济思想的学术研究,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重点议题之一。另一方面,西方的教育课程体系逐渐被引入国内,[2]国内高校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甘乃光、李权时、熊梦、唐庆增等学者编撰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均对管子经济思想进行了评述,但其研究对象并非《管子》全书,其评述也毕竟有限。
黄汉所著《管子经济思想》由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是民国时期第一部研究《管子》经济思想的专著。[3]1935 年 4 月,黄汉将《管子为战国时代作品考》一文发表至《安徽大学月刊》第二卷,后该文收录进《管子经济思想》第二章。关于黄汉其人事迹从书中蛛丝马迹可推断出他的一些信息:如篇末落款“稿于云汉斋”可知其居所地名为云汉斋;书中“凡例”说明他曾请周予同、李则纲、王正平、罗根泽四位学者审阅书稿,而这四位学者都与安徽大学相关联,①周予同1932 年至安徽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并主编《安徽大学月刊》;李则纲为安徽籍著名历史学家,1935年前后曾授课于安徽大学;王正平至少在1934年5月时,仍是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因《安徽大学月刊》上发表有他的论文和演讲稿;罗根泽著有《管子探源》一书,当时任教于安徽大学。可知黄汉本人也与安徽大学有着深厚渊源;书中多次熟练运用先秦诸子思想和相关古籍且引用亚当·斯密、布丹、李斯特·费夏、马尔萨斯等人的经济学理论,甚至对各国经济政策非常熟悉。例如,黄汉论述各国盐税政策,“英、比两国之盐法,乃自由制,听人民自由贩卖,国家既不专卖,复不征税;德、法、荷兰诸国……不限制人民之运销,而就盐之产地征税……美国、丹麦、那威(挪威)、西班牙、葡萄牙及革命前之俄罗斯……对本国出产之盐,不征收租税,而对外国输入者则税之。意大利之盐法……制造归民,运销归国,或官民共制,运销归国,贩卖归民……欧洲大战前之奥匈……制造运销,概归政府办理,民无得预焉……《管子》之盐法……与意大利之盐法,差类似之。”[4]以上可知黄汉不论西学还是旧学的功底都非常扎实,对海外经济理论与实践比较了解。
《管子经济思想》共分为十个章节,对《管子》一书中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考察了《管子》的成书年代、核心观念、哲学基础,分析了《管子》的货币学说、财政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农业政策、分配与消费等,并给予管子经济思想极高评价:“《管子》一书,经济思想之丰富,在中国旧籍中几无其比。而其立论之新颖,思想之一贯,尤为罕见。”[5]虽然黄汉其人具体信息和研究需要学界发现更多的资料并加以考证,但可以确信的是,黄汉学术思想是传统学术文化和西方学术思想交融的产物,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形势下形成的,体现了中西交融、古今互通的特点。研究黄汉的学术思想,有助于理解中国近代《管子》经济思想研究过程中中西结合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现在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采用中西杂糅的研究范式
清末民初,万象更新。西学东渐影响逐步扩大,儒家正统地位遭遇威胁,逐渐式微。导致诸子学说的研究重新获得重视。有学者认为,民国初年的管学研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分别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杂糅论、胡适为代表的西学论和钟秦主张的传统研究法。[6]所谓中西杂糅法,即在研究内容中比较西方经济思想与《管子》经济思想的异同,显示出《管子》经济思想的优越性。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用西方学术观点验证和阐释管子经济思想。如梁启超认为《轻重》《乘马》篇等包含有大量的国计民生思想,为同时期希腊人所不有,因而《管子》经济思想远领先于同时代的古希腊。黄汉《管子经济思想》一书沿袭了这一中西杂糅的研究范式,“既欲研究中国古哲之经济思想,则不能不向故纸堆中求生活,解读原文,爬梳整理,集中材料,然后用科学方法分类研究。”[7]
首先,黄汉在绪言中对当时国内经济思想学界的研究持批判态度。“今之学者不专心以求我国之经济思想,徒从事于西洋经济思想之研究;不察国内经济状态之背景,不审度国情,徒事剿袭,强为之用。故自欧洲归来者,则以欧洲之经济政策为号召;自美洲归来者,则以美洲之经济政策相标榜;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观乎年来国内经济思想之紊乱,财政行政之无标准,可以喻之……故学者如不欲解决中国现代之经济问题则已,如欲解决之,必得研究本国之经济思想整理之,批评之,以明了我国经济之背景;同时研究西洋之经济思想,整理之,批评之,以为他山之助,庶几中国之现代经济问题,得迎刃而解!”[8]学者忽略国内经济背景、状态,专事西洋经济思想研究,且留学于不同国家的学者标榜相应国家的经济学说,导致国内相关研究非常混乱。若要解决中国现代之经济问题,必须研究本国经济思想。力主以当时中国背景以及传统文化为本位,拒绝照搬西方理论。其次,黄汉认为“国民经济观念,在欧洲近数十年始形注重,而《管子》则在二千年前,已力言之”。[9]充分肯定《管子》经济思想优越于西方之处。最后,黄汉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非常熟悉,在书中多次引用并与《管子》经济思想加以比较。例如,在论述《管子》货币经济思想时,黄汉认为其与巴丹(Bodin)的货币经济理论如出一辙:“《管子》之经济思想……最有价值之学说,即货币学说是也。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于一千五百七十三年,始发明于法人巴丹(Bodin),而管子已先西人二千年发其端。”[10]并且采用西方近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用图表方式说明《管子》一书中货币数量、商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变动关系。[11]再如,在论述《管子》无税思想时,引用亚当·斯密对租税作用的论述,用西方近代税收思想分析税收的必要性:“官有地即官有资本之收入;对于支给大文明国之必要费用,非徒不当,且亦不足,故此必要费用之大半必当出自租税;即人民贡其私的收入之一部,以作君主或共和国之公共收入也。租税为国家或公共费用之唯一收入,则国家或公共之政务,均有以赖之。政务不可旷,则国家之收入不可无也。”[12]
二、推崇《管子》国家干预主义思想
黄汉认为,《管子》以国民经济观念为本,力谋国民生产的发达思想比西方早两千多年。他批判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经济理论,认为其虽促进经济发展,但也造成贫富分化等种种不良后果:“其结果虽使经济日益发达,但贫富悬殊,阶级倾轧,种种恶果,亦随经济发达而日甚。”其原因是,“盖人类生活,必互赖互助,不惟个人与个人间相互提携,即个人与社会亦相互推进。在国家界限未除,而以人类为前提,空倡大同主义,则徒为强国攫取市场以经济势力凌压弱国之饰词。若以个人为单位,而倡自由主义,则世界充满自利、竞争之思想,因人类智慧之不同造成阶级之悬殊。此均非人类之争议。故在国家藩篱未撤去以前,当以国民福利为前提,谋国民经济之发展。国家藩篱撤去以后,大同主义实现,当以人类福利为前提,谋世界经济之发展。今日之国家离世界大同相差尚远,而斯密氏大倡其自由主义,此其陷于谬误而不自觉也。”[13]这一思想与梁启超可说是一脉相承。梁启超认为,管子提倡的国家主义较之古希腊“有市府而无国家”,影响深远,泽被后世:“中国则自管子首以国家主义倡于北东,其继起者率以建国问题为第一目的,群书所争辩之点大抵皆在此。”[14]这一结论同样建立在批判亚当·斯密理论的基础上:“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国人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15]可见,“国民经济”观念是梁启超研究管子经济思想的核心议题。
黄汉以国民经济观念为基础,概括叙述了《管子》一书主要内容:“《管子》本乎国民经济之观念,力谋国民生产之发达,使民富国足。其于财政政策,则主张无税,以免病民。谋私经济之收入,以充政费。故盐、鱼、铁、矿、森林,均归国有,使少数人民不得挟其雄厚资本,操纵货物,发生价格独占之弊。农业政策,则保育农民,统制米谷。调剂谷价,俾免谷贵伤民,谷贱伤农。工业政策,则禁止奢侈工业品,奖励普通工业品,以一般国民之需用。商业政策,国内商业政策,则统制物价,使富商豪贾,兼并之技无所施。国外商业政策,则贸易国营,发展经济竞争之手腕。分配政策,则求贫富之齐。其于消费,则力倡节俭,奖励储蓄,以谋国民经济之充实。总之,《管子》之财政政策、经济政策、分配、消费等,均本其国民经济观念而出发”。[16]
这种国民经济观念概括言之即“内则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外则不脱帝国主义色彩也”。[17]诸多学者持有相同的观点,如张国柱认为的,《管子》“富国强兵,扩张领土”,“国家主义色彩”“视国家为一团体,除对国内农工生产,借力奖进,以求本国的产业尽量发展外,对外则以整个的国家团体为单位,利用贸易的力量,进行其经济的与政治的侵略。非使富国强兵,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种主张,实由时事使然。”[18]甘乃光主张:“《管子》的经济学说,近于国家社会主义,略带些保育政策的色彩,和孟子大略相同。”[19]俞寰澄认为:“我国古代诸家论,涉及经济者大都趋重自由经济。史记货殖传所称‘最上因之,其次利导之’。足概其凡。惟管子独重统制经济,以为立国强兵之寿夭。晚近惩于资本制度(资本只是机器发明后,时势造成之制度,无主义可言)之流弊,竞尚统制经济。当备战及作战时,统制更严密,管子于二千年前,已发其端。”[20]
黄汉这一思想与近代中国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密不可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以持久和平局势为理论前提,而这一前提在当时的世界局势中并不存在,这种情况下,富国强兵是首要目的。如果实行自由贸易,会受制于发达国家,只有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才能维护本国利益。
三、提倡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
哲学基础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因哲学基础不同,研究结论往往不同甚至相反。黄汉运用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管子》经济思想。首先,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观点解释唯物主义的概念——“哲学本体论中,主张以精神之原理,视为实在之本质,欲据此以说明一切现象者,通称此为唯心论。本体论中,主张实在之本质为物质,以物质为宇宙根本原理,欲据此以说明一切现象者,曰唯物论”。[21]并进一步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经济基础稳定,附属于基础之上之上层建筑,亦从而稳定。经济基础不稳固,则上层建筑之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亦无从稳固。不谋经济基础之稳固,而图上层建筑之安定,结果终归失败之一途。”[22]其次,他明确提出《管子》与中国古代其他先哲多以唯心主义为立论出发点明显不同,认为“唯《管子》一书,以唯物主义为其经济学说之出发点”。[23]最后,他用唯物主义哲学理论阐释了《管子》一书中的诸多思想。“唯物主义,则治国之术,首在使国家经济基础巩固。国家经济基础巩固,然后一切政治法律教育方可设施。”[24]
在教育方面,“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①《管子·牧民》篇。说明物质基础稳固,才能建设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支配精神生活。在政治方面,“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②《管子·治国》篇。这是因为政治现象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越发达,政治表现形式就越高级;财富越充足,政治斗争就越缓和。因而,一个国家经济条件越好,就越容易统治。在法律方面,“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①《管子·版法解》篇。法律同样为物质生活所支配。一方面,人类违反法律的大部分原因是贫穷,如果物质不充足,犯罪率就会提升;另一方面,法律是统治人民的工具,如果物质不充足,刑罚杀戮都不能起到震慑民心的作用。在军事方面,“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明于机敏,而明于机敏无敌。②《管子·七法》篇。战争胜败关键不在于器械的精良程度,而在于国内经济是否发达。聚财是首要条件。在人类欲望方面,“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③《管子·禁藏》篇。物质生活维系人类生命,人为了维系自身生命,会不断地进行谋划,想要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在满足基本欲望后,再满足更高层次的欲望。因而物质生活驱使着人类行为。通过以上分析,黄汉认为《管子》一书是将“关于物质生活之支配精神生活;物质条件,左右礼义荣辱”这一道理阐发无遗。[25]黄汉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理解得十分透彻,并且在实际研究中灵活运用现代哲学基础阐释《管子》经济思想,鲜明地提出《管子》经济思想是少有的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先哲理论。不仅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使得两千多年前的《管子》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
四、对《管子经济思想》的总体评价
黄汉对于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不发达之原因的分析切中肯綮。一方面,他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指明最大原因乃学者“讳言利字”,“在昔我国儒者,原未以言公利为戒。如孔子罕言利,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之腐儒,不辨孔、孟之不言私利,对于公利,则未常不言,乃自鸣高尚,假学斯文,无论其为开辟财源,或掊克聚敛,概以‘长国家而务采用者,必自小人矣’之论调对之。以故学者群以研究治生之术为羞,以提倡理财为耻。数千年来,此风不衰,羞称管、商,不言富强,拘迂之谬,遗害至今。”[26]可见黄汉认为,利分公私,虽孔孟不言私利,但不应因噎废食,耻言公利。另一方面,他从历史文献研究现状的角度分析,认为子书对经济的论述比经书更多,但辨伪之风盛行阻碍了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近来辨伪之风颇盛,每尊古抑今,贵远贱近,以为真则珍之如圣经,以为伪则弃之若粪土……流风所被,成为习尚,辨伪日甚,古籍日无。以为著者真伪,无关于书之价值;但必须鉴别时代,究其原委,以免学术系统之混乱。若不问其内容如何,徒以伪而弃之,是因噎废食,乖谬孰甚!”[27]同年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持同样的看法,“余以为《管子》虽系伪书,然书中之经济理论,亦极有研究之价值,以其确能代表其本人之经济思想也。此书虽非管仲手著,但书中主张,多与管仲生平执政之设施相符合……故我人不因《管子》书为伪书而不研究,亦不因《管子》一书,杂有他人著作,遂将《管子》与管仲之经济思想,分开研究。”[28]黄汉一书突破管子研究中真伪、年代的问题,并不拘泥于《管子》书中某些篇章是否为假托管子所作问题,专注于管子经济思想的实质性研究。
黄汉还通过系统梳理中国经济思想史,对管子经济思想进行定位,并给予较高评价。他认为先秦诸子中与经济思想有关系的不外乎儒、道、墨、法、农五家,而这五家的经济思想各有其局限性,因此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无重要地位。儒家重农思想在孟子著作中“可窥一二”,但并没有专门著作传于后世,且义利观念相混合,以精神生活支配物质生活;而道家“寡欲”、反对使用器械的主张给经济思想以摧残;墨家对中国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交利兼爱、消费论、劳力,但这些思想与伦理观念相混合,并不纯粹,且汉以后因为内在矛盾和外界压迫一蹶不振;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经济思想以重农抑商为核心,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中亦无重要贡献。所以诸家无一家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执牛耳”,而管子的经济思想不仅没有上述诸家的缺陷,反而兼有诸家所长:倡无税、谋税费充实国库、注重物质生活但又倡导节俭、农业商业同样重视以及创立货币学说,成为后世阐发该学说的渊源。
黄汉在书中将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使得分析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黄汉对《管子》经济思想的分析仍不脱“治国”之目的,所以在书中多次将《管子》经济政策与当时的社会情况进行联系。例如,论述《管子》工业政策,“管子则以首在器械,器械精,则战争胜。器械劣,则战争败。器械……足以影响战争之胜负。此深符合近日战争之实况,近日战争,则以器具之精粗论胜负也。今日国家,靡不埋首精制战具,以求杀人之速,列强之所以号称强国,则以其陆海空战具之精而且多,及杀人之器之毒而且速也。回观我国,徒仰给于他人,精制之战具无有,此我国之所以弱也。”[29]黄汉认为《管子》对于军事器械非常重视,进而认为军事器械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更为重大的作用。再如,论述《管子》商业教育思想,“今日世界商业竞争之剧烈,为有史以来所罕见,各国对商业教育,靡不注重。我国近以外人不费一兵,不折一矢,足以制我死命,故亦感觉商业教育之重要,而有商业学校及大学商科之设。但此皆偏重于学问,缺乏经验,往往有商学院之大学生,对于商业普通常识,不若一小贩,由此毕业之学生,反不能服务商界,此我国书匠教育之失败也。《管子》以商业之匪易,必学问与经验俱兼,二者不可偏废,故力倡教学做合一。商人子弟,必旦夕随其父兄从事于商业,悟得利之由,知时间之差异而发生物价之变动,并了然现时之物价。”[30]黄汉强调当时商业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提倡如《管子》一样,学做结合。以上显示了他作为学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
黄汉引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相结合,开启民国时期《管子》经济思想研究,结合民国时期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特别是受制于当时日益严峻的外部压力以及国内振兴实业的期望,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国家干预功利性和介入经济各个环节的工具性色彩,该研究中西杂糅,体现出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求发展的思想烙印。总体上看,《管子》经济思想集大成了一些商品流通环节规律并提出国家调节物价抑制富商蓄贾兼并行为等正面主张,但相比于其本质上人为调节商品供求从中渔利以获取国用,正面积极主张反而占据次要地位,且这些积极主张除了唐代刘晏合理使用以外,更难以找到其他成功实践案例。在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管子》经济思想中人为渔利等消极面,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发挥其经济思想的积极合理成分为全面深化改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