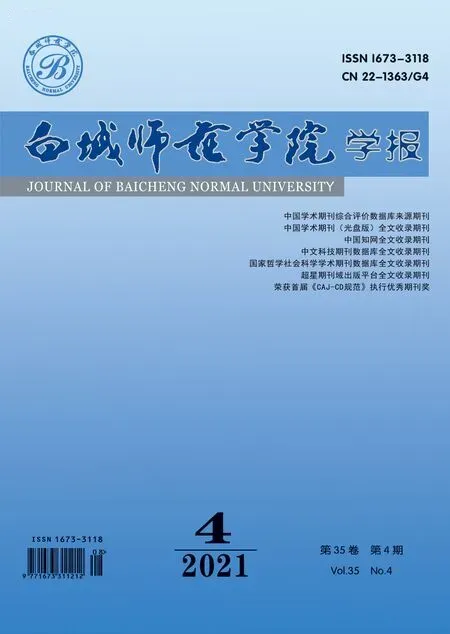吉林西部民间传说与地域景观的互生共构
周梦焱,贺韬羽
(白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民间文学是由人民大众创作,通过口述方式进行流传的语言艺术形式,是表现人民群众生活、思想与感情及总结自然、社会等知识的重要方式,也是人们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民间文学也是民众信仰的一种载体。吉林西部民间文学是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品的收集整理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完成,作品中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东北地区底层民众的思想观念、伦理意识、情感好恶、生存智慧和审美趣味,具有流传广泛、地域性突出等特征,在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省区域经济文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区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又与地域景观相互交融,景观成为传说的物化显现,传说又反向建构景观,二者既相互融合又相互补充,形成了互生共构的关系。
本文从二者互生共构的关系出发,围绕吉林西部重要的景观群——查干湖景观群及民间传说,探讨二者共同完成了地域文化叙事,形成了完整的地域文化影像。
一、民间传说再现地域景观
在地域文化的发展中,口传叙事往往转化为地方文化资本,并进一步向读者进行“文化展示”[1]。民间传说作为口传文学的重要文类,它对地域文化的展示,多与地域景观相互交融,多维度呈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生活影像。
“景观,一般意义上,是指一定区域呈现的景象,即视觉效果。‘景观’最早的含义更多具有视觉美学方面的意义,即与‘风景’(scenery)同义或近义。”[2]从这一概念出发,考察吉林西部民间传说对地域景观的呈现是多个维度的。
首先是呈现自然景观。“一个地方地理环境主要是由气候、土地、河流、湖泊以及动植物资源等自然因素构成的,这些自然因素所形成的景观也就是自然景观。”[3]查干湖,蒙古语为“查干淖尔”,意思是白色圣洁的湖,主要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是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也是吉林省内最大的天然湖泊。这里环境优美、景色秀丽且动植物资源丰富。[4]而关于查干湖的民间传说,则用质朴的语言描写当地的自然景观,展现了地方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查干玛拉沁老人》传说中描写查干湖自然风光秀丽优美:“这湖白亮白亮的,形状溜圆溜圆的像十五的月亮;湖水比牛奶还香甜,比露珠还洁净……遍地开满了查干花。”在《查干湖和青山头》的传说中描述:“查干少布立刻变成了一个白亮白亮的湖泊,这个湖里的水呀,像银子一样洁白,像甘露一样甜美。有了这个湖,这儿的水草又丰美起来了,牛羊又繁殖起来,这里的牧民又过上了幸福生活。”从传说中对查干湖自然景观的描写可以看出,查干湖一带非常富饶,景色十分优美,查干湖名称由来的传说也是基于当地的自然条件而产生的。
查干湖民间传说中还描绘这里拥有的渔业、芦苇等动植物资源。在《拉希仁钦大法师入住郭尔罗斯宾馆夜梦》传说中描述:在查干湖地下有一个叫金河的河流,里面“波光粼粼、鸟鸣鱼跃、蒲苇连绵……”因此,从查干湖相关传说中对查干湖大量的自然景观的描写可以看出,查干湖不仅风景秀丽、水草丰美,而且动植物资源尤其是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
另外,这些民间传说也为我们呈现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尤其是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场景。在《成吉思汗祭湖》《老把头选婿》的传说中有对于查干湖冬捕活动的详细描写,其中涉及到冬捕中包括鱼把头、副把头、跟网、把矛、走钩、小套、送旗、打更以及车老板等工种,使用马、胶轮车、渔网等工具,按照祭湖、把头寻找鱼群位置、下网眼、定网窝和收网等流程进行冬捕。《皇帝渔猎传说》写到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传说每年春节过后,皇帝都要携群臣到查干湖举行“头鱼宴”,宴会以鱼虾一类食物招待群臣及使节。通过这些民间传说中的描写可以看出,查干湖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查干湖冬捕活动展现了当地世代流传下来的原始渔猎场景,形成查干湖民众所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地域景观对民间传说的物化
地域景观对传说的物化主要表现在:地域景观并非是独立存在,它往往以传说文本为依托,与传说文本叙事相互依存。景观对传说的物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自然景观体现,二是围绕自然景观建构人文景观。
2002年,经吉林省政府批准成立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在此周围建设了一系列与地域文化相关的查干湖景区。到现在为止,该地区的景观已经成为吉林省乃至北方著名的景观群。景观群的主体与核心是查干湖这一自然景观,近年来,又陆续形成了成吉思汗像、成吉思汗庙等雕塑与建筑,使民间传说中成吉思汗这一历史人物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得到展示。
《臂上的猎鹰》中传说有一次成吉思汗在狩猎返回途中,进入了扎木合布置的帐篷。扎木合仇恨成吉思汗,在帐篷里设了插满枪尖的陷阱,并在上面放了地毯和茶几作掩饰。成吉思汗随扎木合进入帐中后,身上的猎鹰突然飞到地毯上,成吉思汗便看到了下面的陷阱,于是将扎木合推到毯子上,扎木合就掉到了陷阱中。由于猎鹰救了自己一命,成吉思汗更加宠爱它。此后,成吉思汗常把一些勇士比作他臂上的猎鹰,当地人也因此更加喜爱猎鹰。另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是《追马的故事》,相传有一天,铁木真正追着偷了家里八匹马的盗贼,在途中发现一个年轻人正在解牛,但不知从何下手,铁木真上前帮忙并表明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强大的自信心:“在会解牛的人的面前,牛就是零碎的。而不会解牛的人就无从下手。战争也是这样的道理。”听到这样的豪言壮语,这个叫勃斡尔的年轻人决定做他的助手,并成了他手下最出色的将领之一,后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国。
正是基于这些传说,查干湖风景区修建了成吉思汗建筑群,是对民间传说的直接物化,建构了与民间传说相对应的人文景观。成吉思汗被称为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正如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所写:“铁木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组织家暨军事家之一,他在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光辉成就,在二十世纪之前,很少人可跟他媲美。”[5]成吉思汗庙等景观群通过实物、雕塑、绘画、文字等表现形式,详细记录了成吉思汗的成长历程及丰功伟业,使传说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得到具体体现。另外,这些建筑群还展现了民间传说中所蕴含的成吉思汗的精神和美好品质,折射出当地人对成吉思汗具有的英勇、重情义和知恩图报等精神品质的推崇和认可,这些品质更与东北人的精神品质相契合。
三、传说与景观的互生共构
文学艺术作品赋予地域景观新的意蕴,而地域景观又嵌入当地民众的生活中,成为撰写地方志的背景性知识,同时,也“作为地方社会的一种书写方式和表达系统”[6],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众对于地域文化的书写与艺术表达,形成了互生共构的关系。
吉林西部民间传说丰富了地域景观内涵。在查干湖地区,丰富的渔业资源成为当地人最直接的经济来源,也形成了当地独有的渔猎文化。每年查干湖冬捕之前要举行隆重的“祭湖醒网”仪式,对于这个仪式的来源,在当地流传的《成吉思汗祭湖》传说中有所描写:成吉思汗率领九翼铁骑,在晨曦时分,来到位于查干湖北岸的“青山头”台地。在“苏鲁绽”的引领下与众人一道手托“九九礼”,在九堆冲天圣火的喇叭声中……站在祭台前,面对查干湖,对日九跪,对湖九拜,齐声高诵《查干湖祭词》,接着将奶酒洒进查干湖,意为让芳香的奶酒与一望无际的查干湖永久融为一体,而在这个传说中写到的成吉思汗祭湖仪式也逐渐演变为现在查干湖冬捕的祭湖仪式。祭湖仪式至少表达两层含义:一方面是通过祭湖祭祀天父、地母、湖神,保佑万物永续繁衍、百姓生活安康;另一方面是通过祭网仪式唤醒已经沉睡的渔网,祈愿张网下湖能顺畅平安。目前,在查干湖旅游文化中的冬捕祭湖仪式经过发展演变后比较完整,在朗诵祭词以及将祭品倒入湖中后,鱼把头会从湖里捞出一条具有美好寓意的“开湖头鱼”,并将其拍卖。随着现在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渔猎文化在部分地区仍然存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传统渔猎文化中,人们使用传统捕鱼工具且以捕鱼为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渔猎文化也逐渐萎缩和消失,具有仪式感的冬捕祭湖则在这样的变化中,更多成了文化传承的载体。
景观设计加深了人们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记忆。景观作为自然外物的存在,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相对具有稳定性,在时间的变化中得以保存下来,人们在继承景观文化的同时,也使文化焕发新的活力。在查干湖景观群中,无论是成吉思汗建筑群,还是每年冬捕时的“祭湖醒网”仪式,都使得区域历史文化以极强的仪式感进入了民众的公共记忆,在民众的知识体系中得以稳固和流传。
此外,地域景观与民间传说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地方文化记忆。正如《景观叙事:讲故事的设计实践》一书中所论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故事的世界,并且用故事来塑造这个世界”。[7]从叙事理论的角度看,景观也是一种叙事,是一种“讲故事”的艺术形式,它和民间传说在同一区域共生,并共同言说区域民众的文化记忆。民间传说因其早期的创作主要是在民众中口头流传,而后才由文人收集,转化为书面文本,因此,其所表现的内容大多与日常生活、民众质朴的愿望等相互联系,而景观尤其是人文景观则能够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建构。它既依附于传说,又以新的方式、角度对传说进行拓展、挖掘和重组,能更深刻全面且直观形象地表现历史文化记忆。
综上,地域景观是民间传说的物化显示,民间传说也丰富了景观内涵。二者之间又以地域文化精神为支撑,形成了互生共构的关系,既使民间传说得到很好的存续,又将景观熔铸于地域文化系统,唤起民众的历史文化记忆,激发对地域文化精神的认同,使地域文化精神得以更好的展示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