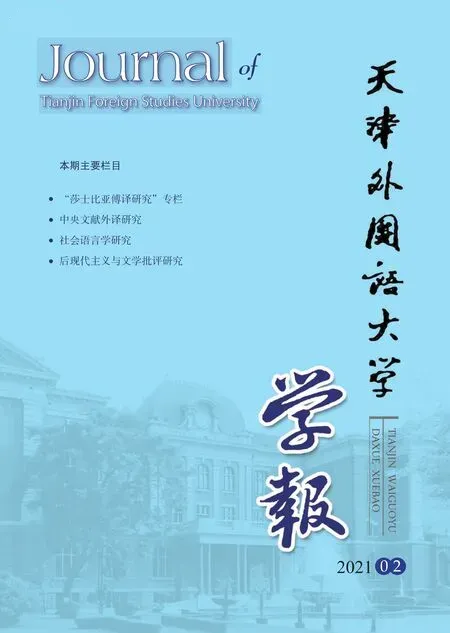从“原味儿莎”看傅光明莎剧翻译的语言风格
王岫庐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谈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人们总会想到卷首班·琼森(Ben Jonson)称颂莎士比亚的献诗:“不属于一个时期,而归于千秋万代!”(Wells,2005:88)四百多年过去了,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声誉证明了这一点。他创作于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剧作如今依然在世界各地被广泛阅读、上演、研究。在中国莎士比亚经历了漫长的经典化过程。自晚清的《澥外奇谭》、《吟边燕语》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介绍给中国读者之后,经由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卞之琳、方平、辜正坤等诸位方家的译笔,莎翁剧作在中国读者心目已经俨然成为西方戏剧艺术的典范。
近年来,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傅光明新译莎士比亚全集系列。目前傅光明已经完成并出版莎剧第一辑新译本四部(《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赛罗》)和第二辑五部(《李尔王》、《麦克白》、《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他在译余还写成莎翁“五大悲剧”的导读合集《天地一莎翁》、“四大喜剧”的导读合集《戏梦一莎翁》以及研究莎剧原型故事的《莎剧的黑历史》。在这些译著中,傅光明提出自己新译的追求,他希望让当代中国读者真正领略“原味儿莎”的风采。本文从戏剧翻译的相关视角探究翻译中的“原味儿莎”到底是什么,并通过对《仲夏夜之梦》唱词与对话选段的译本比对,对戏剧翻译中文化适应的重要性提出重新思考。
二、新译的理由:追求“原味儿莎”
名著重译是一件相当慎重的事情。莎翁剧作现有的各种译本各有所长,尤其是被评价为“译笔流畅,文词华瞻”(罗新璋,1984:2)的朱生豪译本以及“才学两优,译作兼行”(龚鹏程,2007:5)的梁实秋译本,在中国已经拥有大量读者。这种情形下重译莎剧完全可能冒着劳而无功的危险。因此,最初听说傅光明先生以一己之力重译莎剧的时候,笔者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还有些将信将疑,但同时也心怀期待。毕竟我们必须承认翻译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一方面,即便再优秀、再出名的译本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另一方面,语言习惯、时代气息、读者审美期待的演化也不断召唤着新译本的出现。诗人、翻译家王家新认为,翻译家进行重译之前应该思考自己的翻译和之前的译本有没有重要差别,是否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如果重译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新的价值,那它就是有必要的(黄尚恩,2013)。用本雅明(Benjamin,1968:71-72)的话来说,译作是原作的“来生”(after-life),是原作生命的延续,在不同的翻译里原作得到新的更茂盛的绽放。
傅光明在重译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时候,为自己的翻译理念作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定位,他提出要为中国当代读者呈现一个“原味儿莎”的莎士比亚。在《为什么要新译莎士比亚》一文中傅光明(2018:9)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解释他所说的“原味儿莎”:“简单来说,无论阅读,还是研究莎翁,要想领略‘原味儿莎’,便应努力以今天的现代语言呈现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语境。倘若总让莎翁笔下的人物不由自主地随口说出一连串的自带中文语境的成语,无疑不够‘原味儿’吧?”
其实,“原味儿”到底是什么,如何在跨文化的语码转换中保留“原味儿”,恰是翻译研究关注的最核心问题。译者如果在翻译中添加了太多自己的风格,那读者就没有机会欣赏到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了。强调对原作的忠实是传统译论的一贯主张,承认译者的主体性又是当代译论的主流观点。这两者之间并非无法调和。尤其是针对莎剧这样的经典作品,译者的态度往往更为严肃,虽然不同译者对莎剧风格、文笔方面的把握有差别,但希望忠实于原作的愿望始终是一致的。莎剧译学界对于朱生豪译本的评价是遣词典雅,文笔流畅,但受限于时代、条件和个人风格,也出现了不少缺疵疏漏,尤其是原作不够雅驯的地方,朱生豪往往作了回避或删除的处理。相较之下,梁实秋(2007:538)译本更强调“保持莎氏原貌”,尤其着意莎剧原本的嬉俗部分,“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其真”(梁实秋,2001:2),但整体而言,梁实秋的散体译本诗味稍逊。此后方平先生等人在诗体翻译方面进行了宝贵的尝试。时至如今,译界得出结论是翻译莎剧应尽量逼肖原作,在内容、剧情方面还雅以雅,以俗对俗,在形式、风格方面以诗体译诗体,以散体译散体,这些已然成为大家的共识(陈国华,1997:26-34)。那么傅光明提出的“原味儿”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德国释义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982:1)1813年在一篇演讲中提出过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Either 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 him; or he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 him.)。施莱尔马赫甚至明确指出,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必须严格遵循其中之一,否则作者和读者就无法相遇。在施莱尔马赫的启发下,美国翻译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1995)一书中曾提出“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ing)这两个对翻译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术语。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根据目标语表达惯例、读者期待或社会规范对译文进行相应处理。韦努蒂(Venuti,1995:34)认为,译者应该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来昭示而不是企图掩盖自己在翻译中的介入和操纵。这一策略在韦努蒂的研究中亦称抵抗式翻译策略或少数族化翻译策略(resistant or minoritizing translation strategy),它更加强调翻译在对抗强势语言、文化及其规范中的作用。
乍一看,傅光明说的“原味儿莎”强调对莎士比亚原剧的忠实,这就很容易联想到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让读者向作者靠拢,或是韦努蒂所说的异化。而实际上,异化和归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翻译的伦理态度,而并非二元对立的翻译策略。为了存他者之异,故意在翻译中使用诘屈聱牙的话语策略,在小说、诗歌的翻译里也许多少具有实验性的先锋意义,但绝不是戏剧翻译的好方法。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戏剧是一种基于集体经验的艺术形式,既需要有可读性,也要具备可演性,要求译者将目标读者或观众的感受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傅光明在翻译莎剧之前曾花心思研究过老舍。老舍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也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语言俗白精致,充分利用口语与方言的鲜活自然,又不乏“俗中求诗”的格调和品位。老舍(1999:175)曾说:“从技巧上说,写大众曲艺有四诀——用字通俗,句子顺溜,音节响亮,叙事生动。”对于编剧艺术的看法,老舍和那个曾经在泰晤士河南岸为平民写戏的、“浑身烟火气、十分接地气”的莎士比亚应该是有共识的。而傅光明希望在翻译中呈现的“原味儿莎”恰是氤氲于这样的“烟火气”和“地气”中。若想在跨文化的旅行中再现这样的气息与味道,最可靠的做法还是依靠目的语本身,通过通俗、顺溜、响亮、生动的目标语言来呈现。
三、新译的工具:今天的现代语言
傅译莎剧的立足点就是这样通俗、顺溜、响亮、生动的目标语言,“它是翻译给母语是中文的读者看的,若读起来别扭、拗口,语言跟不上时代,势必影响莎剧的广泛接受”(卞若懿、傅光明,2019:3),但同时傅译莎剧的指向却是“原味儿莎”。用傅光明(2018:9)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以今天的现代语言呈现伊丽莎白时代的语境”。因此,他在翻译中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精神风格的强调,二是对译作语言现代感和流畅性的重视。但这两者并非异化、归化的简单对应,前者并非强调字字对应的忠实,后者也并非要让莎剧中的人物穿上长袍马褂,打扮成本土人物。也许有人会质疑,难道不是用古雅、华贵的中文才能更好地对应四百多年前的莎剧原貌吗?下文暂以《仲夏夜之梦》一剧中的几个例子来探讨傅译莎剧的特色。
《仲夏夜之梦》第三幕结尾处精灵帕克(Puck)遵循仙王的旨意,将魔汁滴在拉山德的眼睛上,让一切恢复正常。帕克在此时说了一段独白,音意俱美,二音步短句和四音步诗句错落有致,大多双行押韵(间中三行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顺畅悦耳。我们就以这段独白的翻译为例,对比不同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效果。
On the ground
Sleep sound:
I’ll apply
To your eye,
Gentle lover, remedy.
Squeezing the juice on LYSANDER’s eyes
When thou wakest,
Thou takest
True delight
In the sight
Of thy former lady’s eye:
And the country proverb known,
That every man should take his own,
In your waking shall be shown:
Jack shall have Jill;
Nought shall go ill;
The man shall have his mare again,
And all shall be well.
王元化先生(1998:218)曾说朱生豪译本“优美流畅, 而且在韵味、音调、气势、节奏种种行文微处, 莫不令人击节赞赏”。就这首诗的翻译来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的层面看,采用的翻译策略都偏归化,译文确实优美流畅,但细枝末节方面尚有可推敲处。诗体方面长短句交织,主体采用七言和五言的节奏,对句押韵,结尾民谣隔行押韵,符合中国读者对诗的期待。词汇的层面嵌入了“残梦”、“酣睡”、“神仙”、“幻觉”、“百般”、“消却”、“欢爱”、“旧人”、“满心欢乐”、“情不自禁”等中国传统诗文库(Repetoire)中的语素,读之感觉自然流畅。
梦将残,睡方酣,
神仙药,祛幻觉,
百般迷梦全消却。(挤草汁于拉山德眼上)
醒眼见,旧人脸,
乐满心,情不禁,
从此欢爱复深深。
一句俗语说得好,
各人各有各的宝,
等你醒来就知道:
哥儿爱姐儿,
两两无参差;
失马复得马,
一场大笑话。(朱生豪译本)
朱生豪译本中有几点值得斟酌的地方。一是对原诗叙事顺序的改写。原诗将解药的效果,即可以看到原先爱人的眼睛(In the sight/Of thy former lady’s eye)放在二音步短句的最后一句点明,而朱生豪译本中一开头就将“神仙药,祛幻觉”的药效告诉了读者,并且又说“百般迷梦全消却”,“醒眼见,旧人脸”,抒情成分增强,但戏剧效果却打了折扣。二是对原诗最后一段英国乡间俚语的翻译。原诗中Jack shall have Jill的直译就是“杰克会得到吉尔”,Jack和Jill是常见的英国农村青年男女的名字。The man shall have his mare again字面意思是男人会得到他的母马,但这里mare一词暗指女性,且略带性的挑逗意味①。诗的最后一段用俗语表示男欢女爱天经地义。朱生豪译本中将Jack和Jill这两个名字替换为“哥儿”、“姐儿”,这是典型的归化处理,方便中国读者的理解。但“失马复得马”这一句在目标语境中难免引发对“塞翁失马”的联想,容易引起误会。Nought shall go ill一句译为“两两无参差”略显过于雅驯,不似原作的乡野气。而最后And all shall be well一句译为“一场大笑话”,意思和原文出现了较大的差别,这样译可能是为了迁就韵脚的需要,但因韵害意始终还是要不得的。相较之下,梁实秋的翻译更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思,语序上也完全贴近原文。
在地上
睡得香;
在你眼上,
我要滴上,
温柔的情人,一点药浆。
[挤药浆滴上赖桑德眼睛]
当你醒了,
你会得到,
真正的喜欢,
只消一眼瞥见
你原来的爱人的眼睛:
乡间俗语说得不错,
每个男人都会找到老婆,
这道理你醒来就会明白:
杰克娶吉尔,
一点没有错儿;
男的又都找到他的女的,
一切没有问题。(梁实秋译本)
梁实秋译本内容上更贴近原文,但有意思的是,The man shall have his mare again这句也还是采用了归化意译的方法,即“男的又都找到他的女的”。译文删去了母马这个意象,只保留了女性这一信息,失去了原诗中大胆淳朴的性暗示。而且梁实秋译本诗的韵味上就稍逊了些,不但句子的字数参差,韵脚也不如原诗齐整。我们再来看傅光明的译本:
躺在地上,
香甜入眠;
温柔情人,
给你眼上,
滴液疗伤。(挤汁液在拉山德眼上)
待你醒来,
你一定会,
满心欢喜,
你会一眼瞥见,
昨日情人的眼;
有句乡间俗语说得妙,
是男人都得把老婆讨,
这道理你醒来便明了:
杰克要把吉尔娶,
一点毛病也没有;
男人的母马失复得,
有情人终将成眷属。(傅光明译本)
傅光明的译本在形式方面基本保留了原文长短交错的节奏。中文诗行看起来字数参差,但节奏是齐整的,前半段两顿,后半段三顿,也照顾到部分韵脚,尤其保留了中间过渡部分的三行连韵,读起来音乐感很强。诗末保留了原文有关嬉俗的表述,如“杰克要把吉尔娶”,“男人的母马失复得”,还用了源自方言、当下走红的表述“一点毛病也没有”,最后用喜闻乐见的俗语“有情人终将成眷属”收尾,读之感觉生动活泼,俗中有雅,俗在其言,雅在其情。若说不够妥帖之处,傅光明译本也是有的。其中“温柔情人,给你眼上,滴液疗伤”这句出于句式和韵脚的需要,对原诗语序作了调整,但调整后的中文表述会让人误以为帕克自称是温柔情人,而实际上“温柔情人”是解药(remedy)的名字。这几句倘若改为“让我为你,滴在眼上,情人药浆”可能更合适。
帕克这段独白的特点在于俗中见诗,俗中见雅,傅光明译本诗意盎然,雅俗互见,可谓是“原味儿莎”的一次成功再现。和独白相比,戏剧中的对话有时候会因为话轮转换的节奏与时间呈现出更复杂、有趣的特点。《仲夏夜之梦》第一场中海伦娜深爱德米特律斯,后者却对赫米亚一往情深,然而赫米娅其实有自己的心上人拉山德。海伦娜和赫米娅这对好闺蜜之间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HERMIA
I frown upon him, yet he loves me still.
HELENA
O that your frowns would teach my smiles such skill!
HERMIA
I give him curses, yet he gives me love.
HELENA
O that my prayers could such affection move!
HERMIA
The more I hate, the more he follows me.
HELENA
The more I love, the more he hateth me.
HERMIA
His folly, Helena, is no fault of mine.
HELENA
None, but your beauty: would that fault were mine!
赫米娅:我向他皱着眉头,但是他仍旧爱我。
海丽娜:唉,要是你的颦蹙能把那种本领传授给我的微笑就好了!
赫米娅:我给他咒骂,但他给我爱情。
海丽娜:唉,要是我的祈祷也能这样引动他的爱情就好了!
赫米娅:我越是恨他,他越是跟随着我。
海丽娜:我越是爱他,他越是讨厌我。
赫米娅:海丽娜,他的傻并不是我的错。
海丽娜:但那是你的美貌的错处;要是那错处是我的就好了!(朱生豪译本)
荷:我对他皱眉,但是他爱我如故。
海:愿我的微笑能学得你的皱眉的技术。
荷:我给她的是咒骂,但他报我以爱情。
海:愿我的祈祷也能这样打动他的心。
荷:我越厌恶他,他越追随我得紧。
海:我越爱恋他,他越厌恶我得很。
荷:是他发痴,海伦娜,错误不在我。
海:你没错,是你的美貌错;但愿那错属于我!(梁实秋译本)
赫米娅:我向他皱起眉头,可他依然爱我。
海伦娜:啊,愿你蹙眉的本领教会我微笑。
赫米娅:我对他发出诅咒,他却回报爱情。
海伦娜:哦,愿我的祈祷也这样叫他动心!
赫米娅:我越是恨他,他越是使劲儿追我。
海伦娜:我越是爱他,他越使劲儿讨厌我。
赫米娅:海伦娜,他发傻犯蠢不是我的错。
海伦娜:错在你的美貌;但愿我有这个错!(傅光明译本)
莎士比亚原剧中的这段对话发生在海伦娜和赫米娅之间,海伦娜因为自己心爱的人爱着好闺蜜而伤心酸楚,而无辜的赫米娅又因为被朋友的心上人纠缠而心烦意乱。两人的对话一句接着一句,一个话轮接着一个话轮,人物的内心动作丰富,对话的动作性强,戏剧场面生动有趣。赫米娅抱怨一句,海伦娜就接一句感叹。赫米娅的抱怨是为了向好闺蜜自证清白,而海伦娜的感叹则是伤春少女的自怨自艾。原文虽然是对话,但节奏相当齐整,均为五音步抑扬格或扬抑格,对句押尾韵,且往往抑扬相对,使得两人的对话环环相接而又层层推进,如同大海上的波涛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
从形式上看,朱生豪译本没有注意句长与押韵,梁实秋译本相对工整,对句押韵;傅光明译本相当整饬,大致保持每句六顿,处理尾韵的时候注意到原文后两个话轮以扣字押韵,通过同一个字重复谐声,更显出海伦娜和赫米娅两人心里的焦急和苦恼。从语言方面看,朱生豪译本总体上流畅易懂,但个别选词如“颦蹙”用作口语稍嫌文雅;梁实秋译本尽可能直译原文,但部分表述如“愿我的微笑能学得你的皱眉的技术”,“他越追随我得紧”,“他越厌恶我得很”读起来比较拗口,折损了原剧的趣味;傅光明译本最接近我们当下生活中的语言,两个因为爱情拌嘴的妙龄少女跃然纸上。当然这也不是说傅光明译本是无可挑剔的。例如,The more I hate,the more he follows me./The more I love, the more he hateth me.中是有hate这个词的重复回环的,傅译“我越是恨他,他越是使劲儿追我”,“我越是爱他,他越使劲儿讨厌我”没有体现出来。若将前句改译为“我越讨厌他,他越是使劲儿追我”效果就更接近原文了。
四、重申流畅作为翻译策略的价值
傅光明努力“以今天的现代语言”呈现“原味儿莎”的理念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以流畅作为策略,在戏剧翻译中实现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尝试。这个词在翻译研究中有时候会被看作是和归化完全一样的概念,部分原因在于Venuti提出归化(domestication)之前就采用过acculturation这个术语。韦努蒂(Venuti,1992:5)认为,文化适应就意味着要选择“流畅的翻译策略对异域文本进行归化处理(a fluent strategy performs a labor of acculturation which domesticates the foreign text)”,并将文化适应看作是“对文化他者的归化,使他者能够被理解、被视为是熟悉的、甚至是相同的,完全嵌入目标语中流通的意识形态文化话语编码之中(they inescapably perform a work-of acculturation, in which a cultural other is domesticated, made intelligible, but also familiar, even the same, encoded as it is with ideological cultural discourses circulating in the target language)”(Venuti,1991:127)。在强调文化差异和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这一企图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去涵盖他者文化,将差异消融于事先预想的相似性之中的做法显然是政治不正确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翻译中的文化适应就是归化,而结果就是同化,就是弱小民族文化身份被主流文化吞噬的过程(acculturation is domestication; it leads to assimilation)(Lahiani,2008:114)。
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文化适应理论已经发生了从单维向双维乃至多维的转变,最初将文化适应等同于同化的观点已经不能够充分描述目前多元文化互动的现实。在翻译研究中将文化适应等同于归化的看法也显得过于简单而难免片面(王岫庐,2020:71)。在实际翻译工作中,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流畅的翻译策略等同于对他者文化之异的弱化、过滤、遮蔽乃至篡改。傅光明莎士比亚新译本的价值之一便是提醒我们重新审视流畅的价值,看到“以今天的现代语言”呈现“原味儿莎”的理念,记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莎士比亚,并读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莎士比亚。
注释:
① 这一表述可能是莎士比亚的独创,但后来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英语习语。德莱顿在他的作品中也曾借用过这一说法:“Then all shall be set right, and the man shall have his mare again.”(LoveTriumphant,Act III,Scen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