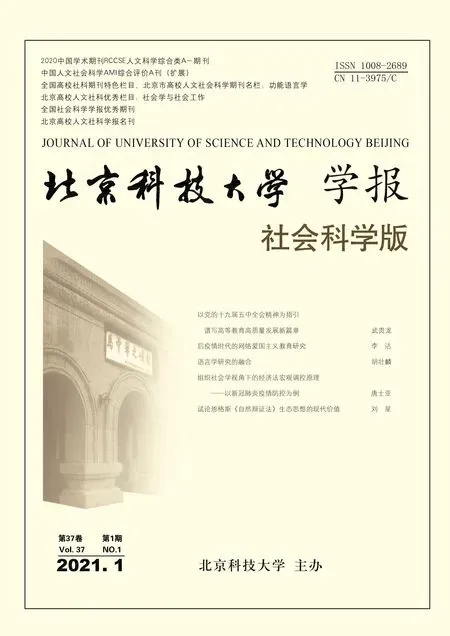论京派乡土小说诗化叙事的多维意境
卢月风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湛江524000)
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相连,作家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也会受到社会局势制约,就乡土小说而言,同样出现了多远的叙事纬度。 而京派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美学品格被称道,大概经历了20 世纪20 年代中期的兴起,20 世纪30 年代的繁盛,20 世纪40 年代逐渐消散的过程,但影响力至今仍绵延不绝,其中废名、沈从文、师陀、萧乾、凌叔华等人是代表作家,他们始终崇尚个体的生命体验,坚守自己的艺术追求,对宗法制社会传统表示认同,乡土书写总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这一创作模式或许与战乱不断的社会语境不相融合,但经过时间的沉淀,作品中那崇尚自由,清淡或浓烈,静穆或喧闹的生命形态,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等诗化抒情传统又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不仅丰富着现代文学的诗意空间营造,也为当代文坛的乡土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 健康、优美的生命形态
如果小说创作是对生命的追求,那么京派作家以极其柔和的笔调书写着乡土的宁静和谐与乡民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呈现出一种自然、健康、优美的生命形态,有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朴素美,寄托了作者浓烈的乡愁乡情与心向往之的“田园梦”,发掘人性之善之美,重铸现代民族道德品格。 废名深受周作人“个性”与“地方性”的乡土观影响,以故乡黄梅为叙事背景,从对风俗的摹写寄托独有的生命体悟。 如《桥》由多个短篇构成,每个篇幅又可以独立成章,从结构上看,既没有叙事性很强的故事,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是几个天真烂漫的农家之子琐碎生活日常的记录:细竹的幽默,琴子的细腻,小林的木讷,大千的恋旧,小千的直爽,他们虽性格各异,但真诚善良的心灵却是相通的。 席洋说废名的《桥》:“仅见几个不具首尾的小故事,而不见一个整个的,完全的大故事。 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像读一首诗,有时像看一幅画,很少的时候觉得是在‘听故事’,所以有人说这本书里诗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是不错的。”[1]也可以说,作品虽背离了小说的某些特征,却更接近诗的规范。 如《桥·钥匙》中的人物自然地与意境相融合,人化为风景的一部分,一个个充满诗意的意境完成了小说内容与情感的表达;《桥·蚌壳》借佛经中“投身饲虎经”的故事注解生命的意义,小林觉得自己即使不幸被老虎吃掉,换来“它的毛色好看,可算是人间最美的事” ,人性的善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散发着夺人眼目的光辉。 《桥·桃园》中“捏扇子的女子,翻一叶手扇,其摇落之致,灵魂无限,生命真是掌上舞了”[2]169,这是居住在天禄山的自然之子牛大千的形象,小林从那摇曳的折扇中窥见了生命的姿态,增强了文本的诗情画意。
同为京派作家的沈从文认为写作是颂扬一切人类的美丽与智慧,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创作于艺术,乃是敬畏自然,信仰生命。 他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身份卑微的妓女、水手(《柏子》)、童养媳(《萧萧》)、长工(《贵生》),还是天真无邪、情窦初开的农家少女,亦或是渡船老人、桔子园主人(《边城》《长河》)等,都恰如其分地阐释了生命本真之美。 从三翠(《一个女人》)、王嫂(《王嫂》)、桂枝(《小砦》)的性格中捕捉到了生命的坚韧之美,从阿黑与五明的感情中体会到生命因爱情的灌溉而变得醇厚(《阿黑小史》)。 《边城》中“祖父”的原型是沈从文在北平穷困潦倒时那个曾经给予他两百铜子帮助的卖煤油老人,这不足为道的“两百铜子”使他感受到了人性的善良。 “翠翠”的原型源自沈从文游玩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儿”哀悼家中老者死亡的哭泣,她的“纯朴”与“悲苦”触发了沈从文对生命的思考。 美好生命的陨落不免使人想到“美丽总使人忧愁”的叹喟,生命的美好与人生的悲哀总是遥相呼应,形成沈从文式的忧郁,作品中的人物不为现实物质欲求所累,懂得随遇而安的生存哲学,充满着淡雅之美。
师陀30 年代初登上文坛,抗战全面爆发后因短篇小说集《谷》而一举成名。 他常常以“乡下人”自居,一生执着于对生命真谛的思考,发掘人的生命力顽强向上的一面,以熟悉的故乡建构起诗性的“果园城”世界,同沈从文心中的“希腊神庙”有某种相通性,这一“广义上的地域家园,既有泛指性,又有特定内涵”[3]《毒咒》在强烈的“精神返乡”意识驱动下用柔和的笔调写出生命的舒展自如之美。 《寒食节》中的长赓对主人忠厚老实接近愚蠢,体现了农民的淳朴善良,从他对少爷无微不至的关爱中仿佛看到了一个光辉的父亲形象。 《人下人》中叉头集勤劳、忠厚、宽容美德于一身,他追求简单的生活理念,除了自己而外,什么都不过问,有吃的饭,有睡的觉,就是好的世界,爱他喂的牲口,甚至这些动物的每个器官,所做出的每个动作都能使他感到温暖,细微处有生命的本真。 如果长赓、叉头是身份卑微的“人下人”,那么《葛天民》中的葛天民,《孟安卿的堂兄弟》中的孟季卿,《落日光》中“吃闲饭”的少爷等,他们可谓是乡土社会落魄的地主、乡绅,当褪去了昔日“人上人”的风光后亮出了生命朴实的状态。 葛天民每天在自己的农场里观察玫瑰花的长势、保存下波斯菊的种子、替那些绅士们养育各种稀奇的树苗,“生为一个中国人,他有财产,有儿女,有好的岁数,他便等于有了一切;他不再想指望什么了,不再为自己找苦头吃了”[4]167,这种悠然安适的生活犹如契诃夫《醋栗》中的尼古拉·伊万内奇穷其所有对平庸个人幸福的追求。 孟季卿不屑于同兄长争夺家产,做起了“安乐公”,结果本来属于他的三进大宅遂成空场,沦为夏季果园城人们纳凉的好处所。 对他而言,物质财富乃身外之物,精神的自由更为重要。 “吃闲饭”的少爷重回故里,尽管一无所有,但却能从对已逝爱情的追忆中重获活着的信念,且与长工之间不是传统主仆之间的仇恨,而是相互依靠的温暖。 师陀笔下这些超越世俗的生命个体散发着健康、淳朴、率真之美,诠释了自由诗性的人生境界。
回首萧乾、凌叔华等京派作家乡土小说的诗性建构,他们在书写理想生命形态时,习惯于塑造坚守乡土本色的“城市异乡者”形象,用真与善抵御都市的欲望与势力。 杨义说,读萧乾的小说,在文字间能感受到一颗“敏慧的诗心”,如《邓山东》中的邓山东,从乡下流落城市以卖杂货为生,但他身上没有一般小商贩的逐利、圆滑与世故,而是坚守诚实的品格,了解儿童的喜好后,担子里经常会塞满各种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带给他们无穷的乐趣。 《篱下》以乡村顽童世界与城里老爷世界的不相容为契机,凸显乡土自然人性顽强的生命力。 凌叔华的《杨妈》《奶妈》写的是离开乡土到城市做佣人的女性勤劳、坚韧的性格,美好的心灵,恒久不变的母爱,在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中,她们对传统精神的守候显得弥足可贵。 废名《浣衣母》塑造了在城郊靠浣衣维持生计的农妇李妈形象,她乐于助人又热情好客,荷包里经常放满各种糖果点心,专为出城路过的孩子们准备,突显了乡土人性的朴素与良善。 实际上,京派乡土小说中原始、优美的生命形态或被安置在偏僻的湘西、黄梅等远离喧哗闹市的环境,或以高度物质化的现代城市为背景,有意把进城的“乡下人”理想化,以宗法农耕文明中健康、圆融的生命伦理对抗现代都市文明丑陋的一面,通过淳朴善良的人格之美矫正现代文明中扭曲的人性。 因此,京派作家眼中的乡土多超越具体实指,更像是审美的想象与精神的乌托邦,彰显着诗性的意义。
二、 如梦如幻的风景画
固然生命的美好令人心存向往,但其脆弱也是不争的事实,而相对于生命的短暂易逝,乡村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美则更为持久,且乡土本身与自然风景就有某种通约性,更能体现小说的诗性品格。 废名、沈从文、师陀等京派作家擅长织绘风景,由景而缘情,诗意晕染在文字间,体现了主观抒情的叙事格调。 他们坚持自然本位的哲学观,追忆诗意的田园,表达人情与人性的美好。 像凌叔华本身就有画家的身份,无疑如诗如画的乡土风景是其美学思想的外在显露,云林山水之妙被描摹得鲜活生动。
废名的《桥》堪称经典,小说故事发生在喧嚣闹市之外的史家庄,因偏僻而亲近自然,人与景融为一体,和谐共生。 如《行路》写道“人在自然之前的自惭冥顽”,“鸟兽羽毛,草木花叶,人类的思维何以与之必映呢? 沧海桑田,岂是人生之雪泥鸿爪”[5]175? 这里用对比的手法强调自然风景之美。 《蚌壳》对夜空中繁星的描写“望着天上的星,心想自然总是美丽的,又想美丽是使人振作的,美丽有益于人生”,星星点缀了天空,也使傍晚乡间的羊肠小道更富情趣;《荷叶》呈现出“一只雁,一株树,一个池塘,这样的世界好看极了”,习以为常的雁、树、池塘等自然风景构成了简单却温馨的画面,洋溢着宁静恬淡之美。 此外,废名还擅长捕捉生活中诗意的细节传达内心丰富的情感,像树藤间的花、河岸边的杨柳、夜里的桃花等,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显得清晰可爱,扑鼻而来的浪漫气息令人流连忘返。
沈从文认为废名的乡土小说是最纯粹的农村散文诗,曾坦言自己的创作也深受其影响,“对农村观察相同,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6]100。 并进一步指出:“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 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的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情诗。”[6]294“最后一首情诗”正是对田园牧歌式的古典审美趣味的不懈追求,对传统文化规范的认同。 《菜园》中“夏天薄暮,溪水绕菜园折向东去,水清见底,常有小虾小鱼,鱼小到除了看玩就无用处。 晚风中混有素馨兰花香茉莉花香,菜园中原有不少花木的,在微风中掠鬓。”[7]93平淡朴实的语言把静谧、闲适的农家菜园描绘得何其生动,与其乐融融的母子亲情,古典式耕读之乐的生活场景相互映照。《长河》有对乡村秋天一派萧瑟景象的描写, “半个月来,树叶子已落了一半,只要有一点微风,总有些离枝的本叶, 同红紫准儿一般,在高空里翻飞。 太阳光温和中微带寒意,景物越显清疏和爽朗,一切光景静美到不可形容”[6]143,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乡村自然风物的神韵,枯树直冲云霄,空灵之美油然而生,既有“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宁静、阴柔之美,又不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粗旷、雄伟之美。 沈从文还不时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中汲取营养,《边城》中“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 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8]6。 由远及近呈现边城人的居住环境,依山傍水、码头上的小蓬船、半水半路的吊脚楼,这样的乡土风景可谓“文中有画,画中有诗”,不承担审美之外的任何叙事功能。
王晓梦认为:“废名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以田园牧歌情调营造诗意古典意境,他的小说反映乡村风景、风俗、人情之美,令人感悟到诗意的轻盈灵动和人生的静谧恬淡。”[9]实际上,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的田园风光、自然之美不只是废名、沈从文乡土小说中频繁诉说的对象,我们从师陀所营造的“果园城”世界,萧乾在城乡文化差异中构建的“孩童世界”,同样可以听到婉转动听的短笛声,令人流连忘返。 “远远的小屋顶上冒出炊烟,在空中飘飘,卷舒,不见了,新的青色的烟又升上来。 小山坡上有白点蠕动,大致是羊了,这一切都渲染着橙色,沐浴在宁静的大气里”[10]58。 这是师陀在《过岭记》中对小茨儿故乡景致的描写,屋顶的炊烟、山坡上的羊群、变幻莫测的云朵,幽静、安详的画面久久在脑际回荡,足以净化人的灵魂,产生愉悦的心情。 师陀在小说《巨人》中吐露出自己不喜欢家乡,却怀念着那里自然的风景。 诚然,对于古代作家来说,他们对故乡的感情倾向于单纯的热爱、思念,而现代作家的“爱乡心”要复杂得多,像师陀这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也是一种相互平衡的心理机制。 尽管他有时对故乡丑陋的人事、民众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充满厌恶,但那里广阔的原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自然景象却难以忘怀。 杨义在谈到《果园城记》时指出:“它是一首首朴素而纯真的乡土抒情诗,一首首柔和而凄凉的人生行吟曲。”[11]425师陀作品中抒情诗般的自然景致象征着他对故乡的热爱,时间在果园城几乎是停滞的,人们仿佛永远无法迈向明天,生命变的萎缩、低靡,像孟林太太、素姑一样在被遗忘的环境里终老一生。 有评论者[12]说:“时间遗忘了这里的风景,风景依然是那样的美丽。”确实如此,乡土风景没有因时间而褪去绚丽色彩,“向日葵孤单单的伫立着,垂首倾听着什么,样子极其凄惶”,“犁过的高粱同谷地,袒露出褐色的胸怀,平静的喘息着,在耀耀的阳光下午睡” (《秋原》)。 这里运用拟人的修辞使物人格化,平常的“向日葵”、“刚犁过的高粱地”似乎具有了像人一样的行为举止,生动、逼真地再现了大地万物的神性之美。
整体上来看,京派乡土小说中诗意的风景与牧歌情调总是相互衬托,也迎合了生态伦理中“回归自然”的价值观,具有悠长、舒缓之美。 杨义说,“沈从文的小说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11]619,这就肯定了沈从文乡土小说“返璞归真”的情趣。 事实上,废名对乡土自然景观和谐之美的反复吟唱中同样饱含牧歌的特征,他不仅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还接受域外文学影响,尤其受到英国田园作家哈代描绘宗法制乡土风景的启发。 无独有偶,沈从文同样受到哈代的文学理念感染,比如《德伯家的苔丝》中群山环绕、碧水蓝天是苔丝的生活环境;《卡斯特桥市长》中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到来,使工业化的“威赛克斯”世界冲击着宗法制农业社会,人们渴望从纯净的自然中寻求精神慰藉。
作为诗化乡土叙事不可缺少的“风景之美”在废名、沈从文、师陀等作家笔下被表现得淋漓尽致,“风景”在他们眼中是纯粹的审美对象,不会像革命作家那样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而把叙事内容消融在自然中,人性的淳朴、向善同自然之美相得益彰,其审美性超越复杂的社会指涉意义,持续沁润着我们的心田。
三、 生动隽永的意象
环境、情节和人物是小说的基本构成元素,而诗性的意象却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 一般情况下,诗歌长于运用别出心裁的意象以增强美感,同理,小说中的意象也有其独特价值,尤其以“写意”为主的乡土小说。 刘易斯说[13]65:“同诗人一样,小说家也运用意象来达到不同程度的效果,比方说,编一个生动的故事,加快故事的情节,象征地表达主题,或者揭示一种心理状态。”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意象已是屡见不鲜,而京派作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能够摒弃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小说中营建“诗性”的氛围、优雅的意境,迷人的田园风光,农人悠然自足的生活理想,打通现代与古代文人的精神联系,创造一个具有古典韵味的纯美世界。
废名较早开启了诗化乡土小说创作,他擅长记录日常生活中富有诗意的细节,营造出清新淡远的意境,令人赏心悦目的世界。 如翠竹、菱荡、桥、佛寺、灯等意象与人物交相呼应,在隐逸闲适的环境中流淌着坚韧豁达的生命意识,彰显着诗意栖居的生活理想。小说《萤火》中那盏造型简陋的“灯”不仅能照亮夜行者前进的路,而且能给予人们以力量,大千告诉细竹,如果提着灯走夜路碰到野兽,只要放在旁边的灯还在,就会无所畏惧。 《荷花叶》中小千的“荷叶灯”既照亮了黑暗的屋子,还诠释着生命的字句。 而虎耳草、枣、蕨菜等植物频频被沈从文拿来象征乡村男女对甜蜜爱情的向往。 由于童年经历了家庭变故与亲情的冷漠,大自然的旷野、落日、黄昏、炊烟慰藉了师陀落寞的精神世界,创作伊始,家乡这些熟悉、唯美的意象成为反复描述的对象。 师陀有“大地守夜人”的称呼,幼年时期没有真正感受过多少温情,“哥哥打我,母亲打我,另外是比我大的孩子也打我”[14]270,受到惩罚之后常常逃到旷野直到晚上悄悄回家,甚至读书的时候思绪也会飞向开阔的旷野,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更多机会亲近自然,对自然意象情有独钟。 这些乡土风景始终未曾远离师陀的记忆,“旷野”“夕阳”“黄昏”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那时日已将暮,一面的村庄是苍蓝,一面的村庄是晕红,茅屋的顶上升起炊烟,原野是一片静寂(《落日光》)”[15]185“我目睹了夕阳照着静寂的河上的景象,目睹了夕阳照着古城树林的景象”[15]222。 这些司空见惯的自然意象隐喻着人们安详、自足的生活状态,并能给人以温暖的情感体验,包蕴着生命的自由、澄明之境。 就连那些荒芜、衰败的自然物像都被描摹得充满诗意,记录着师陀对生命的独特体验,“颓坍了的围墙,由浮着绿沫的池边钩转来,崎岖的沿着泥路,画出一条接界”“霞光照射着残碎的砖瓦,碎片的反光,将这废墟煊耀得如同瑰丽的广原一般” (《毒咒》)[15]166。 落满灰尘的荒园,无人问津、衰败不堪的“废墟”并不妨碍师陀对生命的诗意表达,超越现实层面之上的是生命从繁盛到萧条再到颓唐的写照。 纵观文本中出现的或温馨或凄凉的意象,无不关涉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也可以说是人物内在心理的延展,借此我们可以窥见生命的蜕变过程。
尽管师陀一再声称自己的创作不从属于任何流派,但他的乡土书写还是打下了“京派”的风格,初登文坛时的小说集《谷》就发表在沈从文担任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并得到赏识。 他们还常有书信往来,刘增杰[14]175曾说:“沈从文以自己生命的美丽滋润着师陀的心田。”基于此,可以说善于绘制风景、构建诗性的意象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 废名《竹林的故事》用“竹”的品性象征三姑娘内心的纯洁与善良,而《边城》中也多次出现“竹”的意象,小说开篇就有“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深翠颜色,逼人眼泪”的景物描绘,四周被竹子环绕的茶垌是叙事环境。 主人公翠翠因竹而得名,“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16]3,“竹”的青翠欲滴正是美好人性的象征,并充当了故事发展的情感符号,为翠翠与船总顺顺两个儿子之间难以取舍的爱情纠葛做了铺垫。 事实上,“竹”的爱情寓意可谓源远流长,自古就有“青梅竹马”指涉青年男女之间情投意合的爱情,古典诗词中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的意象。 除了“竹”的爱情寄意,翠翠梦中的“虎耳草”也有懵懂爱情的寓意。
动物意象与植物意象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长河》中每天跟随夭夭的那只“大白狗”,它可以衔回因乌鸦抖动树枝掉在地上的橘子,关键时刻又是勇敢的卫士,看到主人受到保安队长和师爷的为难时会发出大声的狂吠。 “黄狗”是《边城》中经常出现的意象,看起来不起眼的动物却有着人的灵性,它是推动翠翠与傩送相识、相恋的桥梁,当看到翠翠受委屈时会发出汪汪的叫声,充当主人保护神的角色,凸显着动物的灵性。 “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两个人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这里分别用“小兽物”和“老虎”意象来形容可爱、天真活泼的翠翠, 以“拟物”修辞带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有着统摄小说整体结构的作用。 《萧萧》中“猫”是一个被多次提及的意象,萧萧那孩子气的“嗨嗨,看猫呵”,果然使哭闹不止的小丈夫破涕为笑,慢慢合眼入睡。 从文中不难发现,这只猫一直扮演着哄逗孩童的角色,化解人力难以解决的困境,增进了童养媳与三岁小丈夫之间的感情。 类似的动物意象在沈从文小说中还有很多,《三三》中的“鱼”是三三消遣娱乐的方式之一,对“可以钓鱼吗?”的不同回答则暗示了这个思想单纯的农家女孩爱憎分明的情感。 《王嫂》叙述了城里做女佣的农妇王嫂经历了大女儿早逝的痛苦,儿子在战场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生活的不幸没有击碎她对生活坚定的信念,依旧平静地做着该做的活,“大公鸡” “小母鸡”“小黑狗”等动物意象在她眼中仿佛蕴藏着精神的寄托,是一种达观顽强、平和冲淡的生活姿态的写照。 总之,沈从文小说中的动物意象常常被赋予人性内涵,营造出温情、暖意、和谐的氛围,唤醒人们内心至真至善的情感,以诗意的意象淡化人物悲情的命运。
四、 结 语
“健康、优美的生命形态”“如梦如幻的风景画”“生动隽永的意象”等内容共同构成了京派乡土小说诗化叙事的内容,废名、沈从文等作家不遗余力地在山水之美、人性之善及意象之真中挥洒着抒情的笔致,坚守文学的审美阵地,企图以文化寻根的方式找寻民族道德振兴的思想资源,实现理想的人性重建,尽管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语境下显得捉襟见肘,但历史终究无法遮蔽其文学价值。 如果抛开激进的社会功利主义文学观与历史进化论思想,不难发现京派作家构筑起的诗意空间,是带着恋乡情结的记忆重组,是精神家园的象征,他们在现实与想象的落差中体悟理想的生存状态,重新思考自我救赎与民族灵魂更新的途径,意义深远。
京派作家以原始宗法乡土社会形态为依据,有意创造文本内涵的朦胧感,礼赞静谧和谐的乡村生活,书写健康、优美的生命形态,营造古朴清新的乡野图与生动隽永的意象空间,建构起同“现实人生”遥遥相对的理想宫殿。 这样的叙事路径推动了乡土审美现代性的发展,对当代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积极借鉴,如刘绍棠、汪曾祺、阿城、古华等作家笔下的乡土世界都或多或少地延续着京派的诗化叙事风格,追求一种自由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样态,一定程度上升华着乡土审美主题的书写空间。
——师陀小说《争斗》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