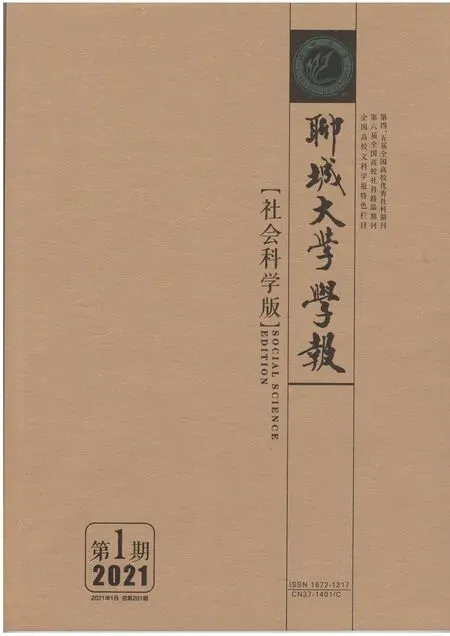隆平续考
——曾巩存世文献与《隆平集》比对研究
李俊标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北宋史学名臣独撰之当朝史,传至今日最为著名者莫过于所谓曾巩著《隆平集》。但自南宋《郡斋读书志》即对其著作权持怀疑态度,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确认为:“其出于依托,殆无疑义。”①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7页下。然而辩驳之声亦随之响起,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辩证·隆平集》最具有代表性。②余嘉锡撰:《四库提要辩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0-270页。由此肯定之论渐为主流,至当代王瑞来先生《隆平集校证》可谓集大成者。此类辩驳多如王瑞来先生所言“多是围点打援,以旁敲侧击为主”。③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页。如此,确难有实证之可言。王瑞来先生由是多着眼于《隆平集》文本本身搜寻证据。然多有遗憾处,其亦非能广泛而深入为之。而由曾巩传世文集入手予以佐证,更少有人为。今即自《曾巩集》以及其他史籍中择取与《隆平集》相关之篇章逐一辨证,④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如此直接实据,以期有助于《隆平集》真伪之辨析。
《隆平集》共二十卷,其书可分前后两部。前部卷一至卷三似类要,分为二十六目,依次为:圣绪、符应、都城、官名、官司、馆阁、郡县、学舍、寺观、宫掖、行幸、取士、招隐逸、却贡献、慎名器、革弊、节俭、宰执、祠祭、刑罚、燕乐、爱民、典故、河渠、户口、杂录。后部卷四至卷二十为传记,共三百二十九篇。《曾巩集》卷四十九《本朝政要策五十首》近似《隆平集》前三卷类要,《曾巩集》诸多《墓志铭》《行状》《传》《杂识》则近似《隆平集》后十七卷传记。今由是概分二类,逐一疏证如下,所列条目名称,以《曾巩集》为基准。
一
(一)贡举
《曾巩集·本朝政要策·贡举》:“自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以来尤盛,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亦复故。开成中,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进士外以经中科者,亦不过百人。至太宗即位,兴国二年,以郡县阙官,旬浃之间,拔士几五百,以补阙员而振滞淹。又未命官,而赐之绿袍靴笏,使解褐焉。”①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658页。《隆平集·取士》中有一段与之几乎相同:“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为盛,每岁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八十人,既而复故。开成间,连岁放四十人,俄仍旧制。太宗即位,旬日之间,放进士三十三人,经科百九十六人,并赐绿袍木简。未命官而释褐,新制也。”②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69页。若仅就此对比而言,或以为两者如出一辙必是同一人所为。如叶建华于《〈隆平集〉作者考辨》中即以此为《隆平集》乃曾巩所作重要实证之一。③叶建华:《〈隆平集〉作者考辨》,《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页。然再核对宋元相关史籍,可知此实乃当时通识。如《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二:“自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以来尤盛,当时每岁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旧额为七十人,寻亦复故。开成中,连数岁放四十人,旋复旧制。进士外,以经术登科者,亦不及百人。自帝即位,以州县阙官,故旬浃之中,贡士几三百人,将以补缺员而振滞淹也。”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356页下。《长编》卷十八,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丙寅:“上初即位,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先是,诸道所发贡士凡五千三百余人,命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张洎、右补阙石熙载试进士,左赞善大夫侯陶等试诸科,户部郎中侯陟监之。于是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覆试进士,赋韵平侧相间依次用,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赐绿袍靴笏,锡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393页。《玉海》卷一一六《太平兴国八科》所征引当时《实录》亦曰:“自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尤盛,每岁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旧额为七八十人,寻亦复故。开成中,连数岁放四十人,旋复旧制。进士外,以经术登科者,亦不及百人。自上即位,以州县阙官,旬浃之间,拔贡士几五百人。先是,戊辰,御讲武殿试进士,上亲作诗赋题,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阅所试,定其优劣,为三等,凡百三十三人,并赐及第。”⑥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2143页下-第2144页上。《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举士》:“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滞,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于是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姓名,上御讲武殿覆试,内出诗赋题,赋韵平仄相间,依次用。命李昉、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试诸科,得二百余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皆先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⑦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79页。《宋史》卷一百五十五《志第一百八·选举一》与之相同。⑧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07页。
数量统计最为纷繁,梳理上述史料可知,取士数量有分数与总数之区别。《长编》《文献通考》《宋史》表述最清晰,尤以《长编》最为明确。先是,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戊辰讲武殿之覆试,得一百九人。《长编》《文献通考》《宋史》均如此。《玉海》以为“百三十三人”,有误。随后,庚午覆试,《长编》明确以为“得二百七人”。《文献通考》以为“得二百余人”,稍有模糊。《宋史》“得二百人”,亦是以整数笼统以言。再之,《长编》记载:“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文献通考》与《宋史》均大致以为“一百八十余”。后,又加之特赐“七人”。如此,总数,共五百七人。《曾巩集》“拔士几五百”,《长编》“凡五百人”,《玉海》“拔贡士几五百人”,《文献通考》《宋史》“凡五百余人”,即是如此。《曾巩集》仅列举一总数,与史实相符。而《隆平集》所列两数值“放进士三十三人,经科百九十六人”,均不得要领,不知所云。《长编》《文献通考》《宋史》均为“进士”“诸科”,而未有单独之“经科”。由上述征引诸史料可知,《隆平集》此条记载全错。王瑞来先生于《隆平集校证》中依据《玉海》以为:“据此,知本书所记‘三十三’,似为‘百三十三人’之误。”①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72页,第134页,第131页。《玉海》此数值乃第一次戊辰之试,且有误。而《隆平集》所言“三十三”,实不知乃何次录取之数值,无法与《玉海》相比对。
(二)雅乐
《隆平集》有“燕乐”条,与《曾巩集》之雅乐乃完全不同性质之音乐,故而内容迥别。而就曾巩心性气禀而言,雅乐与之最为贴合。相应之,曾巩一生所为艺文,散文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名垂千古。诗则稍逊;而与燕乐相伴之词章创作更是乏善可陈。其一生唯一一首词作为《赏南枝》,整个宋代再无人用此调创作,可见此调之乖剌,②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6页。此词最早载于宋代黄大舆所编《梅苑》,署名曾巩。此外,宋代再无其他著作谈及曾巩创作此首作品。难怪世俗传闻有所谓“曾子固短于韵语”之论。③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2页。
(三)佛教
《隆平集》有“寺观”条,与《曾巩集》之“佛教”,两者可谓相应。然“佛教”揭示佛教之敝,阐述宋朝抑制佛徒数量之政策。此与曾巩一生行事一以贯之。而“寺观”则客观列举北宋佛寺道观,与之迥异。
(四)史官
《曾巩集》“史官”条详细记载起居注之原委:“淳化之间,从张佖之请,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以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谔掌舍人事焉。……又令郎、舍人分直崇政殿,记言动,别为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谔始也。”④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661页,第663页。《隆平集》卷三“杂录”中则明确记载:“以起居注进御,自起居郎梁周翰始。”⑤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72页,第134页,第131页。两者对比,“杂录”不仅仅是少了“李宗谔”,而实不知起居注之记载乃“郎、舍人分直”,主笔起居注不仅有起居郎,更有舍人。
(五)户口版图
《曾巩集》本条记载:“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百六,户二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六十五。兴国初,有上言事以闰为限,三岁一令天下贡地图与版籍,上尚书省,所以周知地理之险易,户口之众寡。至道初,又令更造天下州县户口之版籍焉。”⑥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661页,第663页。《隆平集》有“户口”条:“建隆元年,版籍之数,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开宝九年,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户二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六十五。”⑦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72页,第134页,第131页。两厢对勘可见,“县六百三十八”,为“县六百三十”。“县一千八十六”,为“县一千八百六”。今查检宋元相关史籍,太祖元年与末年各组统计数值如下:《全宋文》卷五四四 《包拯七·论历代并本朝户口奏》:“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后取剑南,平岭表,下江左,辟湖湘,所得户口方逾百万;至开宝九年,渐加至三百九万五百四户。”⑧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册,第1页。《长编》卷一:“总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户(注:按总数不符,应作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此国初版籍之数也)”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6页。《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历代户口丁中赋役》:“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乾德元年,平荆南,得户十四万二千三百。湖南平,得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三年,蜀平,得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开宝四年,广南平,得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八年,江南平,得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五。九年,天下主客户三百九万五百四。”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6页,第8534页。《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五《舆地考一·总叙·唐氏周九服唐五服异同说见封建考》:“宋太祖皇帝受周禅,凡州、府、军、监一百三十九,县六百六十一,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③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6页,第8534页。《宋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八·地理一》:“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计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户三百九万五百四。”④脱脱等:《宋史》,第2093页。
综上各种史籍,《本朝政要策·户口版图》与《隆平集·户口》数值基本相同,两种县数之差异,当为多年版本流传之讹误。而在开宝末年户口统计上,这两种典籍与历来史籍截然不同。《本朝政要策·户口版图》与《隆平集·户口》均为“二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六十五”,而《论历代并本朝户口奏》《文献通考》《宋史》均为“三百九万五百四”。此数值代表当时主流意见,亦为后代所继承。如《汴京遗迹志》卷十二《杂志一·宋户口总数》即是如此记载。⑤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09页。《曾巩集》与《隆平集》所载数值甚少见,当是有误。然由此罕见正可窥知《本朝政要策·户口版图》与《隆平集·户口》两者应该有大致相同之来源。
(六)任将
本条涉及诸位宋初战将,可与《隆平集·武臣》相比勘者如下:
1.董遵诲 《曾巩集》“任将”记载:“董遵诲屯通远军四十年”,而《隆平集》卷十六《武臣·董遵诲传》则是“守通远军十余年”,两者迥异,非一人执笔所为。《隆平集·董遵诲传》全文仅二十四字:“董遵诲,范阳人。有方略,善御夷狄,守通远军十余年,蕃汉悦附。”⑥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482页,第135页。而《隆平集》卷三“杂录”中却载有一段长达七十字之生动描写。“杂录”远丰富于本传,正可见《隆平集》之错乱。另检阅《东都事略》卷二十九《列传十二·董遵诲传》、《宋史》卷二百七十三《列传第三十二·董遵诲传》、《全宋文》卷七八二《张方平一·对手诏一道》、《全宋文》卷五一四一《周必大一二八·经筵故事十三首》,均为“十四年”。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东都事略》,《宋代传记资料丛刊》第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脱脱等:《宋史》,第9343页;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7册,第17页;《全宋文》第231册,第131页。《曾巩集》有误,或为经久流传“四”“十”错版。而《隆平集》则不能确知多少年。
2.王彦升 《曾巩集》本条中记载王彦升最突出之特点为“好勇”,而《隆平集·王彦升传》则有一半篇章详细记载王彦升“残忍”之性,与“任将”之描述迥异。
(七)契丹
《隆平集》卷十二《夷狄》相应有“契丹”条,然两者所论迥异。《隆平集》历述自唐以来契丹历史。至宋朝,则略去太祖,直接从太宗开始记载,更叙述至仁宗庆历年间。而《曾巩集·契丹》仅始于宋,从太祖开始,至真宗咸平为止。文中所记地点,《曾巩集·契丹》为“祁沟”,而《隆平集·契丹》则为“岐沟”。
(八)文馆
《隆平集》相应有“馆阁”。两者之差异处在于:
1.“文馆”于宋代从太祖叙起,而“馆阁”则从太宗写起,于太祖只字未提。
2.关于兴建三馆之地点,“文馆”以为“太宗始度升龙之右”。“馆阁”以为“诏经度左升龙门东北车府为三馆”。两者一左一右,迥然有别。今查检宋代相关史籍,《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十《崇文院》记载:“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太宗幸三馆,顾左右曰:‘是岂足以蓄天下图书、待天下之贤俊邪!’即日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2779页上。《长编》卷十九,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上初即位,因临幸周览,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书,延四方贤俊耶! ’即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别建三馆。”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422页。《全宋文》卷三八五〇王云《重修秘阁记》:“太平兴国二年,车驾临观,喟然叹曰:‘若此之弊,乌足待天下之贤俊?’遂命有司,度地升龙门左,督工经营,栋宇之制,焕然一新。”⑥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7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6册,第132页。另,《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后集》六“百官类·史馆”,以为此文乃王岩叟作。可见,当以“左”为是,《曾巩集》有误。而就文句而言,《隆平集》显然同于《宋会要》《长编》。《曾巩集》则与《重修秘阁记》相仿。两者一为官方史籍,一为私人著述。由此亦可见,《隆平集·馆阁》与《曾巩集·文馆》史料来源之不同。
(九)边防
本条涉及诸位宋初战将,可与《隆平集》相比勘者如下:
1.潘美 《曾巩集》本条记载潘美一事迹:“太宗既平晋,隳旧州,迁之榆次,又迁三交,夺故军之险而守之,得胡人咽喉之地,自潘美。”①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678页。对此,《隆平集》卷十一《宣徽使·潘美传》亦有相应记载:“太平兴国四年亲征,刘继元降,因命美镇太原。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号故军,最险阻,戎人之咽喉也。美帅师袭之,虏众遂遁。”②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338页。两者虽详略有别,然内容主旨相仿。其中均都提到一最为险要之地“故军”,可谓“戎人之咽喉”,潘美攻克之,尤以见其战功之卓著。因此,有宋相关史籍均有记载。然今检阅《长编》卷二十二、《东都事略》卷二十七《潘美传》、《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编卷一《潘武惠公美传》、《宋史》卷二百五十八《列传第十七·潘美传》,此地名均作“固军”。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第48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东都事略》,第138页;杜大珪辑:《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编卷一,《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史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脱脱等:《宋史》,第8993页。《曾巩集·边防》与《隆平集·潘美传》如此一致,当有相同之来源。也从一侧面证知,《隆平集》中确有曾巩所撰文稿。
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对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有着很大的专业要求,但是我国很多审计专业人员都是从财务方面的人员转型而来,这就使得他们对于审计的专业知识掌握并不多,导致所做的审计报表也并不严格,对审计问题的处理能力较差。企业的科技创新需要审计部门做好一系列的报表、评估文件以及各类预算、国家政策等。若审计人员对审计知识的掌握不高,必定会导致决策实施时出现各种问题,使得决策出现错误的结果。其次,企业也缺乏对审计人员的资格认证[3],以及对于他们的专业培训,使得一些新上任的审计人员对于企业独特的审计要求掌握并不完善,无法快速的将审计知识运用于审计工作中,这对于企业的创新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2.王全斌 《曾巩集》本条记载王全斌:“宋兴,葺镇州西山保障,自王全斌。”此为王全斌一生行事之要迹,《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编卷一《王中书全斌传》《宋史》卷二百五十四《列传第十四·王全斌传》均有记载。④脱脱等:《宋史》,第8919页。故而《曾巩集·边防》中予以着重指出。然《隆平集》卷十六《武臣·王全斌》中并无此事。且全传尤为简短,共一百一十九字,远逊于《琬琰集》《宋史》之记载。
二
(一)狄青
《曾巩集》卷五十二《杂识二》长篇叙述,详细记载了狄青征讨侬智高叛乱之事,可谓狄青一生最为重要之行事。将之与《隆平集》卷十一《枢密·狄青传》相比,两者文字矛盾处有如下诸点:
1.《杂识二》“广原州”,《隆平集·狄青传》作“广源州”,《宋史·狄青传》亦作“广源州”。⑤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九十《列传第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719页。
2.《杂识二》“连邕、宾等七州”,《隆平集·狄青传》作“破邕及沿江九州”,《宋史·狄青传》亦作“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
3.《杂识二》“青至宾州,悉召陈与裨校凡三十二人,数其罪,按军法斩之”,对此人数,《隆平集·狄青传》作“三十一人”,《宋史·狄青传》作“三十人”。
4.《杂识二》“乃下令宾州具五日粮”,《隆平集·狄青传》作“遂下令止具十日粮”,《宋史·狄青传》亦作“令军中休十日”。
5.《杂识二》“归仁庙”,《隆平集·狄青传》作“归仁铺”,《宋史·狄青传》亦作“归仁铺”。
6.《杂识二》“裨将孙节”,《隆平集·狄青传》作“前锋孙节”,《宋史·狄青传》亦作“前锋孙节”。
两者叙事差异处有如下诸点:
1.《杂识二》载有曾公亮询问狄青治敌方略一事,《隆平集·狄青传》无,《宋史·狄青传》亦无。
2.《杂识二》详细记载张忠、蒋偕战败之事,《隆平集·狄青传》无,《宋史·狄青传》仅一句“先是蒋偕、张忠皆轻敌败死”。
3.归仁庙(铺)决战胜利之因,《杂识二》以为:“先是,青已纵蕃落马军二千人出贼后。至是,前后合击。贼之标牌军为马军所冲突,皆不能驻。军士又从马上以铁连加击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败智高,果焚城遁去。”①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718页,第565页,第567页,第580页。《隆平集·狄青传》则是:“青躬执白旗麾骑兵进,纵左右翼,出其意外,贼众大溃,斩首二千二百级,获伪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纵火焚城而遁。”②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327页,第367页,第418页。《宋史·狄青传》亦为:“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中及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去。”③脱脱等:《宋史》,第9720页,第9818-9819页。显然,《杂识》与《隆平集》《宋史》迥异。
4.《杂识二》并无归仁铺决战胜利后之记载,如进入邕州城、辨别真假侬智高等。而《隆平集·狄青传》与《宋史·狄青传》均对此有所描述。尤其是记载狄青识破假侬智高之言语,《隆平集·狄青传》:“安知非诈?宁失智高,朝廷不可诬也。”《宋史·狄青传》则是“安知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两者几乎全同。
由上述对比可知《杂识二》有关狄青之记载与《隆平集·狄青传》显著不同。而《隆平集·狄青传》与《宋史·狄青传》相仿,两者当有相同之史料来源。
(二)戚同文、戚纶
《曾巩集》卷四十二《虞部郎中戚公墓志铭》《戚元鲁墓志铭》均涉及戚同文、戚纶父子之行事,将之与《隆平集》卷十三《侍从·戚纶传附戚同文传》相比,两者行文相异处有如下诸点:
1.《虞部郎中戚公墓志铭》:“遭世丧乱,亦不复仕,聚徒讲学,相继登科者五十六人,践台阁者亦至十数。……殁,其徒相与号为‘正素先生’。”④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718页,第565页,第567页,第580页。《戚元鲁墓志铭》:“曰同文,号正素先生。”⑤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718页,第565页,第567页,第580页。两处均为“正素”,加之《墓志铭》之严肃、撰文之严谨,自当非一时偶误,可见,乃曾巩所知即是如此。然《隆平集·戚纶传附戚同文传》、《长编》卷四十四、《东都事略》卷四十七《列传三十·戚同文传》、《宋史》卷四百五十七《列传第二百一十六·隐逸上·戚同文传》,均为“坚素先生”。⑥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36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3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东都事略》,《宋代传记资料丛刊》第9册,第390-392页;脱脱等:《宋史》,第13418页。由此一字之差,即可知两篇文章撰者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笔。更比对具体记载,《隆平集·戚同文传》与《长编》《东都事略》《宋史》属于同类型史料,尤其与《东都事略》几乎完全相同。
2.《墓志铭》:“祥符、天禧之间,学士以论天书绌。”《隆平集·戚纶传》则以为:“祥文荐降,歌诵日兴,纶恐流俗托朝廷嘉瑞事,诈为灵木石之异,幻惑愚众如少君、栾大者,上疏亟论。上嘉纳之。”⑦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327页,第367页,第418页。两者截然相反。更检阅《东都事略·戚纶传》,与《隆平集·戚纶传》一字无差。可见与《戚同文传》相同,均与《东都事略》为同一史料来源。
(三)胥偃
《曾巩集》卷四十三《都官员外郎胥君墓志铭》对胥元衡之父胥偃亦有所记载,与《隆平集》卷十四《侍从·胥偃传》相比,《墓志铭》以为:“考为翰林学士、尚书工部郎中,赠尚书吏部侍郎。”⑧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718页,第565页,第567页,第580页。而《隆平集·胥偃传》则是:“大中祥符五年登进士第,屡历外官。景祐初知制诰,久之,入翰林为学士,权知开封府。”⑨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327页,第367页,第418页。并无《墓志铭》中“尚书工部郎中,赠尚书吏部侍郎”字样。更检阅《东都事略》卷六十《列传四十三·胥偃传》亦是如此,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东都事略》,《宋代传记资科丛刊》第9册,第582-583页。而《宋史》卷二百四十九《列传》第五十三《胥偃传》亦无“赠尚书吏部侍郎”之事。11脱脱等:《宋史》,第9720页,第9818-9819页。两厢比对,《隆平集·胥偃传》与《东都事略》更为接近,史料来源更为相似。
(四)王回
王回乃曾巩挚友,《曾巩集》中反复提及,记有卷十二《王深父文集序》《王子直文集序》《王容季文集序》,卷十六《与王深父书》《答王深父论杨雄书》,卷四十二《王容季墓志铭》。将之与《隆平集》卷十五《儒学行义·王回传》相比,两者行文相异处有如下数点:
1.《王深父文集序》明确记载其“卒于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其年岁为“四十有三”。①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196页。而《隆平集·王回传》则是“年四十二”。②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451页。两者迥异。
2.曾巩反复在文章中对其挚友王回文学才华赞叹有加:“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冏容季,皆善属文,长于叙事,深父尤深。”③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十二《王容季文集序》,第199页。于《王深父文集序》中更是对其二十卷《文集》推崇备至。然《隆平集·王回传》中对其文学成就只字未提。反而在短短一百二十九字传文中旁及其弟“弟向亦以文学知名,善序事,亦早卒”。与《曾巩集》连篇累牍之赞语颂辞相较,差异甚巨。
3.《隆平集·王回传》仅有一百二十九字传文,却于文末以四十二字引述王安石《王深父墓志铭》中评语予以赞许,可见对王安石所言之推崇。然如上文所引,对于挚友王回,曾巩最为了解,《文集》中亦有大量辞章评述其为人为学,更加之曾巩骨鲠之个性,完全不必要引述王安石评语为论断。尤其在《与王深父书》中,曾巩于王安石之学术观点甚为不满,以为“凡介甫之所言,似不与孔子之所言者合”。④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十六《与王深父书》,第264页。如此,更无有引述王安石言论之理据。
(五)孙甫
孙甫事迹见于《曾巩集》者分别有:卷四十七《故朝散大夫尚书刑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兼侍读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孙公行状》、卷五十二《杂识一》。《隆平集》卷十四“侍从”亦收录有《孙甫传》。另见于宋元有关史籍如:《琬琰集》中编四七《孙待制甫行状》、《东都事略》卷六四《列传四十七·孙甫传》、《宋史》卷二九五《列传第五十四·孙甫传》。⑤杜大珪辑:《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编卷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东都事略》,《宋代传记资科丛刊》,第657-658页;脱脱等:《宋史》,第9838-9842页。
1.《隆平集·孙甫传》最为简短,仅二百五十五字。相比于《曾巩集·行状》一千二百一十一字、《东都事略·孙甫传》四百七十一字、《宋史·孙甫传》一千六百四十五字,有大量史实被忽略,甚至不及提要之完备。《隆平集·孙甫传》所述行事有四:张修媛事、杜衍事、尹洙事、范仲淹事。《东都事略》、《宋史》均有记载,且更增加众多其他史实。
2.即使如此疏漏,《隆平集·孙甫传》也有《行状》所无,甚至其他三书均未载之内容。如张修媛事,《行状》虽长达一千二百一十一字,但张修媛事仅“又言后宫”四字概言之,令人不知所云。范仲淹事、孙甫卒后所赠右谏议大夫,《行状》更是只字未提。而孙甫所撰《唐史记》,唯独《隆平集·孙甫传》为“唐史书”,并更记载其另有“文集七卷”。《杂识一》记载孙甫自言“为《唐史记》以自见”,可知《隆平集》有误,当以“唐史记”为是。
3.孙甫所任各种官、职、差遣如下:《宋史》:“蔡州汝阳县主簿、华州推官、大理寺丞知绛州翼城县、永兴司录、知永昌县、监益州交子务、太常博士、秘阁校理、右正言、右司谏出知邓州、知安州、江东转运使、两浙转运使、尚书兵部员外郎、直史馆、知陕州、知晋州、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侍读、右谏议大夫。”⑥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列传第五十四》,第9838页。《行状》:“蔡州汝阳县主簿、华州观察推官、大理寺丞知绛州翼城县、知永兴军司录、殿中丞、监益州交子务、太常博士、秘阁校理、右正言知谏院、奉使契丹、右司谏出知邓州、知安州、江东转运使、两浙转运使、起居舍人、尚书兵部员外郎、直史馆、知陕府、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侍读。”①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647页,第709页。《东都事略》:“永兴军司录、秘阁校理、右正言、右司谏出知邓州、知安州、江东转运使、两浙转运使、直史馆、知陕州、知晋州、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侍读、右谏议大夫。”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东都事略》,《宋代传记资科丛刊》第9册,第657-658页。《隆平集》:“知永兴军司录、秘阁校理、正言、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侍讲。”③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400页。《隆平集》之简略自不待言,而尤为不同处,众史籍均为“侍读”,唯独《隆平集》为“侍讲”。侍读与侍讲乃不同官职,此乃孙甫生前最后之职任,于一生之殊荣尤为重要。据《神宗正史职官志》记载:“侍读、侍讲正七品,崇政殿说书从七品,掌讲读经史,以学士或侍从职事官有学术者充。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只日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始至,率以履见,列墩,命之坐,赐茶。议(当为“讲”)读毕,赐汤,乃退。”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八,第2525页下。由此可见一斑。故而曾巩为其所撰《行状》名为“故朝散大夫尚书刑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兼侍读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孙公行状”,欧阳修也为其写有《墓志铭》题为“尚书刑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赠右谏议大夫孙公墓志铭”。⑤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75页。均直书“侍读”。然而,如此重要职名,《隆平集》却误为“侍讲”。
4.《杂识一》全文记叙孙甫一段长篇大论,以见其刚正不阿之气禀。文末,曾巩对其亦是赞叹有加,“庆历之间任时事者,其后余多识之,不党而知其过如之翰者,则一人而已矣。”⑥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第647页,第709页。然而这些于《隆平集·孙甫传》中未有提及。曾巩于情甚为钦佩其为人,于事得其子孙宜等所属状文由此撰写长篇《行状》,然《隆平集·孙甫传》却是如此疏略简短。一人所撰传记,何以能有如此巨大之差异?且“唐史记”与“唐史书”、“侍读”与“侍讲”迥别。故而,两者当有不同之史料来源,《隆平集》中所收录者并非曾巩所作。
(六)王洙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一《丞相许国吕文靖公》“王洙修《经武圣略》”条录自《南丰杂识》,乃《曾巩集》以及《全宋文·曾巩卷》失收,其全文如下:“仁宗览而善之,命吕夷简用洙直龙图阁。夷简曰:‘此特《会要》中《边防》一门耳,不足加赏。’既岀,乃谓洙曰:‘夷简以修《经武圣略》,欲用学士直龙图阁,而上谓:“特《会要》中《边防》一门耳,不足加赏。”故不果。’洙退归。会上使中人谕具道欲用洙与夷简以为不可者,洙因岀纸笔请中人具记上语。明日,往见夷简,问昨日尝语洙者,夷简复称如昨。洙因岀中人所记示之,夷简起立索笏曰:‘上万几事繁,恐不记夷简语。’其后,洙又修《祖宗故事》。参知政事范仲淹请用洙直龙图阁,上已许之。仲淹又曰:‘乞宣谕岀自上意。’上正色曰:‘当用则用,何必岀朕意?今欲宣谕,是不当用也。’其命遂寝,仲淹大惭而退。此洙自为孙之翰言之。”⑦朱熹辑:《五朝名臣言行录》,《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史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宋淳熙刻本影印。此段记载得自王洙亲言,尤能彰显其性格特点。然《隆平集》卷十四《侍从·王洙传》未有此文。检阅有宋相关史籍,如欧阳修《王翰林洙墓志铭》、《东都事略》卷七十《列传五十三·王洙传》、《宋史》卷二百九十四《列传五十三·王洙传》,均记载王洙曾直龙图阁,然均未记载其中原委。⑧分见杜大珪辑:《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编卷三十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宋代传记资料丛刊》第10册《东都事略》,第57-58页;脱脱等:《宋史》,第9814-9817页。《宋史》更言“修《国朝会要》,加直龙图阁”,似与此记载牴牾。此或因正史不载流传。然此乃王洙亲与孙甫言之,为孙甫所记载。而曾巩或即由孙甫其子孙宜等“以状来属”中所亲见。①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四十七《故朝散大夫尚书刑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兼侍读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孙公行状》,第649页。因此,此少有人知。若《隆平集·王洙》果为曾巩所撰,如此独家所知真切史料写于传记,刻画人物最为生动,然《隆平集·王洙传》完全缺失。
将《隆平集·王洙传》与相关史籍勘对可知,其史料来源近于《宋史》,如上述各史籍均记载王洙无所不知之通识如下:《隆平集·王洙传》:“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筭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王翰林洙墓志铭》:“既长,学问自六经、史记、百氏之书,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官、筭法、方言、训诂、篆隶、八分,无所不学,学必通达,如其专家。”《东都事略·王洙传》:“自六经、史记、百氏之书,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历、星官、算法、训诂、字书,无所不通。”《宋史·王洙传》:“洙泛览传记,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
《隆平集》与《宋史·王洙传》几乎全同。然《隆平集·王洙传》中记载王洙预修史籍有“五朝武经圣略”一书,此于上述各传记中均有记载,实为“三朝经武圣略”。“经武”以为“武经”,可见编撰者之想当然。“三朝”误为“五朝”更显无学。王洙卒于仁宗之世,何能为“五朝”?再次佐证《隆平集》虽多取自《国史》等文献资料,但编撰者水平拙劣,以致错误、疏漏不断。“多误”成为其重要特点。
(七)徐复
徐复事迹见于《曾巩集》卷四十八《徐复传》,《隆平集》卷十五“儒学行义”中亦录有《徐复传》。另见于宋元有关史籍如:《琬琰集》下编卷二十一《冲晦处士徐复传》、《长编》卷一三一、《东都事略》卷一一八《隐逸传一百一·徐复传》、《宋史》卷四五七《列传二百一十六·隐逸上·徐复传》②杜大珪辑:《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编卷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11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东都事略》,《宋代传记资料丛刊》第10册,第813页,据光绪九年淮南书局刻本影印;脱脱等:《宋史》,第13434页。。上述六种史籍所记内容分为两类,《曾巩集》与《琬琰集》相同,其他四种史料所记内容相似。《曾巩集》《琬琰集》所载除却大致内容如善《易》、仁宗召见、与范仲淹交往之外,其他无论是细微描写亦或是主要情节,都与其他四种迥异。甚至连最基本之何方人士、其字、卒年均完全不同。而《隆平集》《长编》《东都事略》《宋史》这四种也有细微差异。由此亦分为两类:一类为《隆平集》与《东都事略》,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另一类为《长编》与《宋史》,除却《宋史》省略一段记载,其他文字几乎全同。如《徐复传》开篇:《隆平集》:“徐复,字复之,建州人。常游京师,举进士不中第,退而学《易》,通流衍卦气之法。自筮无禄,故不复进取,游淮、浙间数年。凡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诸家之说,读之必得其旨。因听其乡人林鸿范说《诗》之所以用于乐者,忽若有得,遂举器求乐之本,而晓然知律吕微妙动作之制。时胡瑗作钟磬,大变古法,复笑曰:‘圣人寓器以声,今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是可用耶?’卒如其言。”③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第453-454页。《东都事略》:“徐复,字复之,建州人。尝游京师,举进士不中,退而学《易》,通流衍卦气之法。自知无禄,故不复进取,游淮、浙间数年。凡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诸家之说,读之必得其宜。因听其乡人林鸿范说《诗》之所以用于乐者,忽若有得,遂举器求乐之本,而晓然知律吕微妙动作之制。时胡瑗作钟磬,大变古法,复笑曰:‘圣人寓器以声,今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是可用耶?’卒如其言。”《长编》:“建州布衣徐复赐号冲晦处士。复初游京师,举进士不中,退而学《易》,通流衍卦气法。自筮知无禄,遂亡进取意。游淮、浙间,以学《易》为事,凡数年,益通阴阳、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诸家之说。他日,听其乡人林鸿范说《诗》,且言《诗》之所用于乐者,忽若有得。因以声器求之,遂悟大乐,于七音、十二律清浊次序及钟罄侈兖、匏竹高下制度皆洞达。上方留意于乐,诏天下求知乐者,大臣荐胡瑗,瑗作钟磬,大变古法。复笑曰:‘圣人寓器以声,今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是可用乎?’后瑗制作皆不效。”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116-3117页,第3117页。三者相比清晰可见,除却极少一二字偶异,《隆平集》与《东都事略》乃完全相同之文章。
《隆平集》于宋代刊刻情况未能明知,今有研究者详论其北、南两宋之众刻本,均乃推测之辞。其唯一实证仅为北图所藏明残本《隆平集》赵伯卫序后有一行题识“淳熙元年掌参知政事姚宪重校寿梓”。②熊伟华、张其凡撰:《隆平集版本考略》,《图书馆论坛》第27卷第5期,2007年10月,第18页。是否书贾所为,真假究竟如何,均不得而知。成书于淳熙七年《长编》虽已提及“曾氏《隆平集》”,但其为钞本、刊本不明。至南宋初年,其流传当未能广远。淳熙十二年由洪迈奏进之《东都事略》当依据《国史》《实录》之类文本编撰以成《徐复传》。《四库全书总目》言:“父赏,绍兴中为实录修撰,偁承其家学,旁搜九朝事迹,采辑成编。”③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史部·别史类》,第449页上。今《隆平集》所存《徐复传》或与《东都事略》一样来自相同之《国史》《实录》,或径自抄录《东都事略》,亦未可知。
李焘于《长编》注中曾明确辨析之:“《曾巩集》有《徐复传》,与《实录》、《正史》略不同,今但从《实录》、《正史》,取《龙川别志》附益之。”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116-3117页,第3117页。一者为曾巩所著《曾巩集》,一者为《实录》、《正史》,两者显然有别。可见《隆平集·徐复传》并非曾巩所作。
(八)尹洙
《五朝名臣言行录 》卷九之六《起居舍人尹公》载有录自《南丰杂识》一段行事,乃《曾巩集》以及《全宋文·曾巩卷》失收,其全文如下:“尹洙当庆历中,与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罢朝政,洙亦为人希时宰意,攻以居渭州时事,遂置狱,遣刘湜按之。一日,谓洙曰:‘龙图得罪死矣。’洙请其事。湜曰:‘龙图以银为偏提,给银有记而收偏提无籍,是以知龙图当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银为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其籍,可取视之。’湜阅籍果然,知不能害,叹息而已。其后,洙在随州而孙甫之翰知安州,过随,二人皆好辨论,对榻语几月,无所不道,而洙未尝有一言及湜者。甫问曰:‘刘湜按师鲁,欲致师鲁于死,而师鲁绝口未尝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与洙本未尝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树立耳,洙何恨于湜乎?’甫深伏其识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谓平生好善之心过于疾恶,之翰以谓信然。’”⑤朱熹辑:《五朝名臣言行录》,《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史部》。此与上文“王洙”条相似,亦为曾巩独得于孙甫。《隆平集》卷十五《儒学行义·尹洙传》以及《东都事略》卷六十四《列传四十七·尹洙传》《宋史》卷二九五《列传第五十四·尹洙传》虽提及“刘湜就鞠”之事,却均以“无罪”一笔带过,不得其要。⑥王瑞来校证:《隆平集》,第432-43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东都事略》,《宋代传记资料丛刊》第9册,第651-657页;脱脱等:《宋史》,第9831-9838页。《东都事略》《宋史》或为不知,然《隆平集》若为曾巩所撰,何以亦是如此?《隆平集·尹洙传》乃全书最长篇章,共一千四百六十七字。全文不厌其烦详细记载其一篇奏疏,安能对此传神写照之事迹弃之不顾?文中又将“直集贤院”误为“集贤院”。加之“初,洙集贤院”、“初,刘平等战没”,两处追述行文错乱。凡此种种,令人实难将《隆平集·尹洙传》之作者与史学大家曾巩相关联。
三
将《曾巩集》与《隆平集》相关文章详细勘对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两者众多篇章史料来源迥异。如“贡举”“史官”“契丹”“文馆”《董遵诲传》《王彦升传》《郭进传》《王全斌传》《狄青传》《孙甫传》《徐复传》等。其二,两者亦有相同之史料来源,如《本朝政要策·户口版图》与《隆平集·户口》,《曾巩集·边防》与《隆平集·潘美传》,有关记载当出自同一手笔,均为曾巩所撰。其三,两者虽是不同史料来源,但《隆平集》显然取自《国史》《实录》之类史籍,如《隆平集》之“馆阁”同于《宋会要》《长编》,《狄青传》同于《宋史》,《胥偃传》《戚纶传》《戚同文传》《徐复传》同于《东都事略》,《王洙传》同于《宋史》等等。其四,《隆平集》之错乱、疏漏亦是可见一斑。如《孙甫传》“唐史记”误为“唐史书”,“侍读”误为“侍讲”。《王洙传》“三朝”误为“五朝”,“经武”误为“武经”。《董遵诲传》、《郭进传》本传所无之重要行事居然被遗漏于《杂录》中。
本人之前曾直接从《隆平集》本身文本入手,比勘大量史料,由此证知《隆平集》多误、粗疏之特点。其既与曾巩有关,也与曾巩无关。有关者,其中有曾巩所撰之文献。无关者,此书并非曾巩所著。①参见李俊标:《曾巩散文考论》第四章《曾巩<隆平集校证>考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而今更从曾巩亲撰文集入手,进一步证知《隆平集》上述特性。《隆平集》的确保留了不少宋代史料文献,流传至今尤足珍惜。《隆平集》更确有曾巩所撰文字,于一代史学名臣、文坛巨擘,亦更多存留珍贵文献。然此书实乃后人依附作伪以成。且编撰者水平拙劣,导致此书疏漏、错误不断,以致“多误”、粗疏成其重要特点。诚如《淮南鸿烈》卷十九《修务训》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②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53页。世人遂由此罔顾史实,执意于曾巩所著。无论于曾巩、于《隆平集》,依据史料严谨实证,实事求是还其本真,方能彰显其真正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