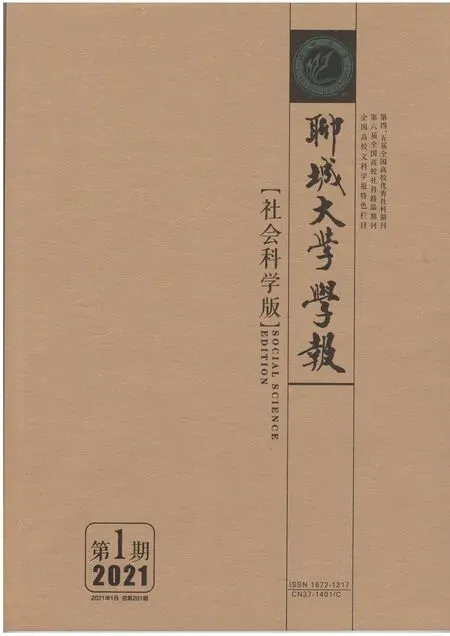李慈铭论史
罗衍军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李慈铭(公元1830—1894年),初名模,字式侯,后改今名,字爱伯,一字莼客,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会稽(今浙江绍兴)西郭霞川村人,晚清官员、文史学家。
李慈铭自幼读书,资分亦佳,“ (道光壬辰年状元、浙江学政吴崧甫)尝举为学之方,分经学、小学、史学、文学、诗学、字学六条为告教,颁所部郡县学以招诸生。其经学、小学二条尤详慎,得读书之法,予之稍知向学实源于此”①[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3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580页。。李氏于道光二十七年19岁( 虚岁) 时首次参加县试,20岁时中秀才,但以后的科考历程却不大顺利,11次乡试皆不中,直至同治九年(1870年) 42 岁时方得中举人。此后又5次参加会试,至光绪六年( 1880年) 52岁时方以二甲八十六名的名次中进士。他自述治学与科考经历:“兄自束发,蒙先人教以诗书,意气奋踔,颇亦不在人后。比家事日落,益自淬厉,冀得一第,以为禄养。既志不遂,乃斥弃田产,入赀为郎,所值屯邅,卒于不振。年垂四十,寸禄未沾,而我母已以穷死矣。”②[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刘再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01页,第1155、1158页。在《四十自序》中,他亦论及此时期的艰辛经历,“仆少怀忼慨,长际时艰。累草贾生之书,常读范滂之传,而请缨无路,谐价是闻。附相如之赀郎,染崔烈之铜臭。为常何作奏,不问马周;闻刘蕡被弹,遂阻李郃。方麴障面,当避朝贵,薄笨生角,不识曹司……忧患孑立,志业尽空”③[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刘再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01页,第1155、1158页。。《清史稿·李慈铭传》则对其生平介绍云:“李慈铭,字爱伯,会稽人。诸生,入赀为户部郎中。至都,即以诗文名于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廕引为上客。光绪六年,成进士,归本班,改御史。时朝政日非,慈铭遇事建言,请临雍,请整顿台纲。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慈铭郁郁而卒,年六十六。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骘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著有越缦堂文十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又日记数十册。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④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86。李慈铭的主要学术领域是历史学,他曾自言:“自经史以及稗说、梵夹、词曲,亦无不涉猎而模仿之也,所学于史为稍通。”⑤[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中),刘再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88页。但张舜徽的《清人笔记条辨》则对李慈铭的学术成就评价不甚高,“李氏少时偃蹇乡里,徒骋词华。及至京师,益徇声色,以羸弱之躯,逐歌舞之地,亲迩卷轴,为日无多,故于朴学家坚苦寂寞之功,无能为役,《清史稿》置之《文苑传》末,实为平允”①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8页。。
窥诸李慈铭的史学观念,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史志撰写体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考订以往史志舛误,重视史志作用的发挥
对清代学术史的变迁,梁启超明确指出历史札记的作用,主要在于储存著书之资料,“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之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②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李慈铭勤于涉猎文史著作,在阅史过程中,他对于史志的编纂体例和内容安排,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学界对《南史》改动宋、齐诸书,颇多责难,李慈铭则意识到《南史》中氏族连合为传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并进一步指出历史撰写须仔细推敲撰述意图,不可轻易进行讥讽。“《南史》之改并宋、齐诸书,诚多未善。于《宋书》所载朝章典故,刊落尤多,《南齐书》中关系之文,亦多删削。惟其与氏族连合为传,则别有深意,殊未可非。盖当时既重氏族,而累经丧乱,谱牒散亡。北朝魏收《魏书》犹多子姓合传,南朝则沈约、萧子显、姚思廉等,专以类叙,于兄弟子姓,分析太甚,李氏故李矫之。其书本为通史之体,与八书各自行世,故先以四代帝纪,次以四代后妃,而各代列传。又皆先以诸王,其诸臣则有世系者皆联缀之,以存谱学。盖欲考时代先后,自有本书,固并行不悖者也。大凡古人著述,须细细推其恉,不可率尔讥之。”③[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1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7698-7699页。他并且设想集合历代正史所不载之说部资料,仿照正史纪传名氏次序,为之考证,论断真伪,“阅《宋稗类钞》,予观宋人说部颇不少。每欲集自《世说》、《语林》,以至明季说部,依各代正史纪传名氏次序,为载其正史所不载者,各条下仍注明原书出处,而为之考异,并加按语,论断其真妄。其史传中无名字者,则依类序入,名之曰《史誊》”④[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2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347-1348页。。他忧心于儒者治学所存在的“高言虚张”之弊端,大力倡导“践履之实”,呼吁治学须坚其根柢,“自《汉书》传儒林,历史因之,至宋而有道学之别。呜呼!谁为此名,可谓不学者矣!道者,六经是也。儒者之所习,无二学也。维伊洛立教,渐为空虚,高言愈张,实学滋晦。朱熹思以博考审辨,求践履之实,而其时程学大行,专门名家之儒久绝于世,无所师受,不能通晓其训故,至于注《诗》述《易》,遂为无本之义,多取不根之谈。《诗》弃《小序》,尤为口实。斯岂通人之蔽,抑亦晚学之征乎?要其弟子,若蔡元定、蔡沈父子,皆能有所著述,以翼经教,视夫程、陆之门人有殊焉。九渊兄弟,负绝人之才具,具高明之识,深穷理欲,抗异新安,分道并驰,至以睽辙。师心太过,几流猖狂。衷其间者,惟吕祖谦。永嘉之学,醇醇近古,而际代学者驰骛洛闽,敷说心性,并为一谈,深而益肤,畅而益支,乃转相推崇,以自掩饰。盖亦知所学根柢不坚,姑习大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思孟命脉真传,至是始出,汉唐千载未涉其境,更取异名,别于儒林,以文其不学之迹,言语日繁,性道日歧。沿及明代,五百余年,遂无有知学问者。呜呼!可慨也已!是真儒学之厄,圣道之累也”⑤[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中),第805-806页。。他提出的史志撰写要立足于“实”的主张,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李慈铭相当重视志书的编写,在《越中先贤祠目序例》中,他提出二十六条编写凡例,“至先贤入祠之数,遍稽史传,综覈志乘,旁及四部,博考精求,进退之间,致严致敬,不敢稍参私见,轻信偏辞。五夜盟心,鬼神共鉴”①[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中),第1016页。。他认为志书的编纂应依类分编,批评以往志书编纂的舛误,“谓著录之例,大小《戴记》当依类分编,如《汉志》别出《弟子职》、《小尔雅》例,《周易经》及《十翼》亦当分载。夫《弟子职》本是古书别行,非班、刘所出。《小尔雅》今在《孔丛子》,《孔丛子》明是伪书,特窜入《小尔雅》以示可信,是后人之窃《小雅》,非《汉志》之析《孔丛》,乃欲缘斯谬肊遍乱古经,则卦书之文当别收于图绘,庚歌之语且分录于诗篇,此其不可解者三也”②[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第1110页,第1110页,第1111页,第1244页,第1245-1246页,第1248页,第1364页。。同时,他强调府县地志的重要地位,指出厘清古今地志沿革的重要性,“谓府县地志,当以人物为重,不在考覈疆域。夫古之地记本不及人,后世滋繁,意存夸饰,识者犹以为非,今谓四至八到可以略举,古今沿革无须过详,是则志以地名,先亡其实,人以地系,先迷其邦,将晋宋之扬州尽为广陵之产,秦汉之会稽悉成东部之英,其不可解者四也”③[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第1110页,第1110页,第1111页,第1244页,第1245-1246页,第1248页,第1364页。。他针对史志撰写的不同对象,指出其撰写要求的差异所在,尤为强调碑志、传状称谓撰写的严谨性,“盖称谓莫严于碑志、传状,不容一字出入,郡县官名一参古俗,皆乖史法。降而至序、记,则可稍宽矣。又降而至书、问、笺、启,则更可稍宽矣”④[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第1110页,第1110页,第1111页,第1244页,第1245-1246页,第1248页,第1364页。。他以浙江地方志的编纂为例,阐明编纂清晰准确的地方志书的必要性,“《拟修郡县志略例八则》:地志以疆域为重。疆域之限,村镇城邑。古今易名,当以山川为识,况越中千岩万壑,山水国也。而自嘉泰、宝庆两志,山水错杂,散而无纪,其名亦古亦今,往往按籍以求,则今无可指;即地以问,则书无可徵。万历、乾隆,率沿其体,棼乱讹溷,甚不可也”⑤[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第1110页,第1110页,第1111页,第1244页,第1245-1246页,第1248页,第1364页。。地方志编纂的原则何在?李慈铭认为,应是“有善可纪者,略其疵,恩桑梓”、“无事可书者,贵弗录,明丹青”,“乾隆两志,艺文最疏,当为《越中经籍志》,稽其存佚,详记卷数,并略载书中大恉,如《崇文总目》《四库提要》之例”⑥[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第1110页,第1110页,第1111页,第1244页,第1245-1246页,第1248页,第1364页。,“或补或删,必徵必信,闻见之世,甄录尤严。有善可纪者,略其疵,恩桑梓也;无事可书者,贵弗录,明丹青也。任怨任劳,勿遗勿滥”⑦[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第1110页,第1110页,第1111页,第1244页,第1245-1246页,第1248页,第1364页。。李慈铭对以往史志进行了比较,认为以班固所撰为最佳,欧阳修次之,沈约、魏收所撰及《隋唐志》又次之,其他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虽以志名,却纪传错出,“《史志策》(辛亥乡试策对第二道):自来史志之可据者,班氏为最,欧阳氏次之,沈约、魏收及《隋唐志》又次之。《隋书》各人分撰,旧本每篇或题名,或否,固已不能尽知。《新唐书》虽或云《天文历志》出于刘义叟,世系诸表出于吕夏卿,而要为欧阳氏所裁定。其他号为‘志’者,若叶隆礼《契丹国志》,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则又虽以志名,而纪传错出。其曰杂记、杂录、杂载者,皆诞妄无端绪,多近小说,不足以考见制度,此又不足论者也”⑧[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第1110页,第1110页,第1111页,第1244页,第1245-1246页,第1248页,第1364页。。
在对以往历史撰著进行认真、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针对历史记载中的一些欠缺和不确定之处,李慈铭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如他针对《汉书》中的一处简要记载,即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注释补充,“取亲中群厕腧,身自、擀洒。(《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苏林曰:贾逵解《周官》云:腧,行清也。孟康云:厕,行清。腧,中受粪函者也。东南人谓凿木空中如曹谓之腧,慈铭案:清,即今圊字。曹,本字当作槽。腧,本字当作窬。《淮南注》云:窬,空也。又案:《说文》:厕,清也。此传厕腧,自当如苏、孟解说,为厕中函粪之空木。盖中群厕腧皆秽亵不洁之物,故为亲瀚之”⑨[清]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67-168页,第139页。。他对《汉书》中的《说》三篇加按语云:“《说》三篇。(《汉书·艺文志》)慈铭案:此即《弟子职说》也,似应连属上一行。王伯厚以为《孝经说》。案:上已出长孙氏、江氏、翼氏、后氏、安昌侯等说,自《五经杂议》以下皆以它书附入,非指《孝经》矣。”⑩[清]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67-168页,第139页。有的历史考订,其用意则在于修正原有记载文饰之处,以正本清源,如他在阅读《晋书·周访传》时,对周访行迹的认识即反映了这一点,“闻敦有不臣之心,访恒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晋书·周访传》)。慈铭案:此等语盖出访之家传,由其门生故吏粉饰言之。其实访固敦之爪牙也。使访果有此心,则访殁后,不应其二子抚、光皆抗逆王师为敦效死力矣”①[清]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69-670页。。对《汉书》中有关少帝及济川、淮阳、恒山王是否为汉惠帝之子的记载,他通过细读文本,指出他们皆为惠帝之子,诸大臣不予承认的原因在于“自为身谋”,“于是阴谋乃为少帝及济川、淮阳、恒山王皆非惠帝子(《汉书·张陈王周传》)。慈铭案:此事详在《吕后本纪》,于《勃世家》略之。著阴谋二字,以见少帝及三王本惠帝子。诸大臣自为身谋,恐日后取祸,遂诬而害之耳”②[清]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上),第158页,第236-237页,第5页。。他注意通过多个史料来源厘清某一记载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其对子赣事迹的考证即印证了这一点,“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贮鬻财曹、鲁之间(《汉书·货殖传》)。王氏鏊曰:夫子称赐货殖若曰富贵在天,志道者所不必问。而赐犹未能忘情,则于进学有妨焉耳,岂若后世孜孜于利者比哉。而班氏遂列于《货殖》,谬矣!慈铭按:文恪之言,本于程氏。然以货殖为商贾,汉时经师,相承旧说。《韩诗外传》:子贡,卫之贾人。王充《论衡》:子贡善居积。何氏注《论语》亦云:惟财货是殖。盖舜为陶胶,鬲举于鱼盐,懋迁有无,固非圣贤所讳。以子贡货殖为无其事,此宋儒之说,非夫子之旨,故不得以班氏为非也”③[清]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上),第158页,第236-237页,第5页。。
二、对历史人物、历史事迹不拘于成说,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总体上仍属于传统“君明臣贤”的史学观念,难以与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相比
杨树达《<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序》云:“往者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元、郑渔仲、章实斋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张天如、王船山之流是也。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洪筠轩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王西庄之所为是也(西庄书至驳杂,兹据其一部分言之)。批评史籍,其途差狭,自刘、郑、章外,殆不数见。自宋至清初,则批评史实最盛之时期也。清儒治学,恶蹈空,喜征实,彼惩于批评史实之虚而无当也,故变其道而趋于考证,于是考证派之两枝,于乾嘉之际同时并起,而继其后者第一枝为盛。越缦先生乃承钱、洪之流,而为有清一代之后殿者也。”④[清]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上),第158页,第236-237页,第5页。可见,他认为李慈铭读史札记之内容主要在于考证史实,然考之李慈铭读史札记可知,考证史实与评论史实,乃是其札记相辅相成、交相为用的两个方面,将二者对立起来看待,并不符合李氏读史札记之本意。
李慈铭博览群书,读史札记占了其日记的大量篇幅,日记中时见记录其阅读史书的日常,如“读《史记·袁盎晁错列传》”⑤[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641页,第641页。、“夜雨声尤紧,读《史记·司马相如传》”⑥[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641页,第641页。。在读史札记中,他对史书中的某些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在《纣之不善论》文中,他认为不应夸大纣王的恶行,并进一步指出,在史书的撰写中,存在夸大前朝君王恶行,溢美本朝君主的行为,认为应该如实直书,慎重撰写,“吾独以为后世之南北史、《宋书》、《齐书》、《北齐书》及今所行之《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等,诚非人主所宜观也。惜乎司马氏之《资治通鉴》于三国六朝五代诸君之事,犹不能慎之又慎,别择而书之也”⑦[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中),第748页,第753页。。他撰写《卫定姜论》《暨艳论》》《王曾论》《李沆论》等,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如《暨艳论》云:“君子之不能胜小人,其害至于如此。不惟君子所不及料,亦岂小人之始计哉?”⑧[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中),第748页,第753页。《王曾论》云:“大臣之用心,当与天下共见,诚敬孚于人,信义格于众,潜移默化,不动声色,而不仁者远,乃斯以为善用其术矣。”①[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中),第756页。从而通过札记,阐明其撰史应秉笔直书,仕宦应诚敬信义的观点。
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李慈铭进行了思考,指出统治者要维持统治,须推行仁政、与民休息,不可横征暴敛、残民以逞,他以秦朝与隋朝的衰亡为例进行了阐述,“自古废嫡立庶,覆族倾宗者多矣,考其乱亡之祸,未若有隋之酷。《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之有国有家者,可不深戒哉。此等名言法戒,不亏良史。自宋以后,奉敕修史之臣,不敢为此言矣。又杨玄感等传论,发挥隋氏兴亡之由,其辞甚美。又云: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道,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亦名论也”②[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8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5543-5544页。。对史书上的一些“定见”,他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如在《唐宣宗论》中,他对前人称宣宗为“小太宗”提出商榷,指出唐宣宗任用弄臣,大兴佛教不能控制藩镇势力,煽动宦官势力,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唐朝的衰败,“恃其私智,以钤天下。所肱髀者,如白敏中、令狐綯辈,又皆人奴,惟汲汲谐媚,且日寻于蔓劾峭诋以快其报复之私。故回鹘巨患也,德裕指纵诸服,草薙而禽獮之,遂不能国,而帝以为婚姻,且有功,下诏招集之,而嫁罪殄灭者为奸臣,然则刘悟亦尝立功矣。使积子孙有在者,亦当继之旌节乎”③[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第1250页,第1251页。;“唐季宦官之炽,则尤帝煽之”,“帝处可为之势而不振,而藩镇宦官亡天下之局以成,虽有善守者,不能为也,况懿宗乎?”④[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第1250页,第1251页。
对于历史上的贤臣良将,李慈铭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叹息于唐末将领王师范的遭遇,“师范之事亲也,以舅得罪故,为母所怒,则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见,三年拜省户外不敢懈。其事君也,昭宗以师范附朱全忠,命杨行密部将来瑾攻青州,且欲代为平卢节度,而师范闻昭宗在凤翔,哭曰:吾为国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与行密结盟,潜兵赴难。及闻弟之被执,则以数十万众遽降于全忠,可谓贤者矣。乃卒见酡雠人,湛族于洛,临死执义,谓不可令昭穆失序,慗于先人,宴饮从容,依次就坎,又何其天道之冥昧也!抑天将举世禽兽之,而人道不绝者,违天不祥,故必尽灭乃止,无俾遗种于世耶!哀哉!”⑤[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3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519页。他不以朝代长短而论君主之功过,高度评价后周的历史地位,赞扬后周世宗柴荣的历史贡献,“是周于天下最有功,失天下最无罪。宋承其业,遂以混一,安享廿八帝。至钦宗蒙难,建炎南渡,犹籍国初削平江南吴越之伟业,其初之得江南,乃藉世宗大举伐唐之功”⑥[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2册,第1275页。。
对于明代历史,李慈铭亦在札记中谈及自身看法,如他通过分析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事迹,指出成祖背君篡位的不义之处,认为这违背了君臣之道,须受到谴责,“郑和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药灯之诅咒,难染之藉手,彼发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改参夷而典僧,缘其释然于博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兴帝(尝作兴宗或原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处华夏,服事其圣子神孙,尚论懵如。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终古,此则可为痛哭者也”⑦[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8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2915-12916页。。在《明庄烈帝论》中,他对崇祯皇帝的经历进行分析,指出崇祯身死殉社稷的行为虽可歌可叹,但他喜怒无常、刻薄寡恩、猜疑臣下等性格,正是导致其亡国殉身的重要缘由,从而指出君主的个人特性在王朝兴衰中的重要性所在,这种认识无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庄烈帝之死社稷,盖至今道之,未尝不流涕也。……盖君人者,患莫大于自圣,祸莫亟于多疑。庄烈纂祚,手翦大奸,自以为圣明天亶,不世出之主矣。由是菅束宇内,土苴大臣,以命帅为弄婴儿,以僇谏为清朋党。……繁苛督促,轻喜易怒,盖至十七年而易相五十,然后知其亡也决矣。无论其奸贤错置,人不能展其志也。迹其于五十人中,大抵排群议,出独见,不次而擢之。夫以一人傲戾之见,违盈廷好恶之心,不计成效,予以重枋,已足以致乱矣”①[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第1252页。。
在李慈铭所作的诗作中,亦有通过讴歌历史人物和历史事迹,表达其历史观念者,如他撰写了《杂咏后汉事十二绝句》,抒发他对汉朝历史的观感,在《冬夜读后汉书李固杜乔传》中,他表达了对李固、杜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赞叹,呼唤历史正气充盈天地间,“严冬夜气肃,坐读李杜传。二公志违天,岂计死扞难。危言留信史,寸心与不烂。鬼神共魂薄,金石立可贯。中流悬一壶,万古竟长旦。回复涕泗下,孤愤触羁贱。悲风起中宵,静听万物战。吾心出光明,短檠一灯敛。奇节在天地,读书兆忧患。名士固不祥,惨恻迫世乱。杀身以成仁,卑末无自见。紞紞更鼓终,掩卷起三叹”②[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上),刘再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6页,第15页。。
李慈铭倡导撰史要出于公心,不可因受人际、血缘关系而有意曲笔、回护,而损害史书的真实性,他通过考察史书撰写案例对此予以阐述,“魏自孝武入关,以东魏为伪,以高氏为贼臣。其后洋又先纂而纬终灭于周,以为俘虏。隋承周,唐承隋,则高氏之为贼为僭伪益著。乃唐初称之为北齐,为之修史与魏周并者,何也?盖以李百药之父德林,薛收之父道衡,颜师古之祖之推,皆尝仕齐,颇被任遇。温大雅彦博之父君悠亦堂为文林馆学士,高士廉之,祖岳为齐清河王,士廉既功臣国戚,大雅兄弟任用百药等,皆久综文史之职,故协力跻之,列于帝统,而高氏穷凶极暴,颇知崇尚文学,优容儒士,遂得久假不归。此以知修史诸臣,出于私心,而有国者不可不重文士,所以藉其力者,非浅也”③[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1册,第7775页。。
三、密切关注时局,具有家国情怀,但囿于自身认识,具有一定的守旧排外意识
李慈铭尽管仕途不顺,远不能进入清朝统治官僚体系的核心层,只能成为宦海中的边缘人物,但他仍对国家时局保持强烈关注。他一方面通过撰文和记录日记,自行议论时政;一方面则通过为某些官员起草章疏文牍,充当“帮闲”的角色,间接表达自身对时局的诉求。在辛酉政变之前,李慈铭即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四的日记中记曰:“当国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嘱为检历代贤后临朝政事,予随举汉如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辽睿知(景宗后)、鳃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 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无贤称者亦附见焉,亦为考定论次,并条议上之。”④[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3册,第1890页,第2070页。为垂帘听政寻找历史依据,这正迎合了此后慈安、慈禧太后意图垂帘听政的意图。当然,因李慈铭边缘人的地位,他并未因此在仕途中得以更进一步。在同治元年( 1862年) 正月,他继而为掌山西道监察御史朱潮起草奏章,言“粤寇之祸, 滔天十余年,陷地千万里,为史册中所罕见”,“贼势益横,凡在臣民,无不枕戈泣血”,提出“谨防西北,协剿东南”⑤[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3册,第1890页,第2070页。的方略,可见在国家秩序控制方面,他具有一些符合时政需要的创见。
在其诗作中,李慈铭对太平天国运动、外敌入侵等均有描述,表达了对社会动荡、民众遭受苦难的叹息和对社会安定的渴求。描述太平天国运动情形及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诗作,如《感事述游》:“烽火惊传遍九州,索筝尚恣犊辕游。狂吟烂醉供今日,胜水残山入早秋。云带边愁随旅雁,波分暮色到闲鸥。江头谁识行歌意,击木苍茫写百忧。”⑥[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上),刘再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6页,第15页。《近闻四首》:“秣陵自古帝王州,两载羶腥未即收。岂是赵辛持异议,颇闻安史自相仇(先是贼首洪秀全为其下杨秀清所杀,近闻秀清亦死)。海䲡尚掣南征力(时刘雁川尚踞沪上),铜马还深北去忧(时僧王围连镇,胜都统围高唐,俱未克捷)。将帅屡膺殊锡宠,凭谁支手奠金瓯?”①[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上),第30页,第36页,第70页,第112页。《喜闻官军收复武昌黄州汉阳三郡贼势日蹙》:“江汉横流几岁更,喜闻捷奏下三城。一军朔漠光明甲,百战南丰子弟兵(时提督塔齐布公、侍郎曾公功为最)。从此上游增险守,更期诸路协师贞。须知枕戟行间苦,尽入深宫问夜情。”②[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上),第30页,第36页,第70页,第112页。《寇逼》:“寇逼将三舍,浮生奈此何?所忧慈母老,敢谓一身多。有福安贵贱,无才触网罗。去留都未可,避世愧蹉跎。”③[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上),第30页,第36页,第70页,第112页。这些诗作尽管存在史实讹误,以及仇视太平天国的局限性,但亦为我们留下了反映当时历史状况的宝贵资料。其《庚申八月感事四首》则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侵入京师,咸丰帝逃往热河,民众蒙受苦难的状况,“名王铁骑镇沾中,大息藩篱指愿空。孤注何曾谋寇准,吁留几见约陈东?绝怜沧海横流速,尚想神京拱卫雄。东望翠华应下泪,昭陵松柏起西风(上以初八日东狩,次日为文皇帝忌辰)”。④[清]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上),第30页,第36页,第70页,第112页。
当然,作为一个处在历史巨变中的传统文人,李慈铭存在固守传统,排斥外来科技和文化思潮的局限性。他在描述其时曾国藩、钱鼎铭冤杀民妇的案件时,即用因果报应观念看待曾、钱的病逝,显有不当之处,“颇闻乙巳庚午间,直隶有夫外出,不告其家人,或控妇杀其夫。时曾文正为总督,太仓武进钱中丞为臬司,竟磔其妇。越三年而其夫归,官吏揭制之,不得白。文正之梦猝以心痛,而钱中丞之卒于河南,则群言其见鬼为厉,生疽落头,然则鬼神亦有不可尽欺,而报应亦有未尝不速者”⑤[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0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7153页,第7453-7455页。。
总体来看,在时局急速变迁的时刻,李慈铭虽在一定程度上考证了史实,并对以往的历史编纂、历史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其历史观仍属于传统范畴,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基本上受限于传统“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的观念中,其史学观与明末清初的张岱、黄宗羲等人相比,非但未能凸显进步性,反而呈现出明显的退守趋向。如关于同治年间清政府欲开铁路之事所引发的争论,李慈铭转引并认同李鸿章幕僚赵铭反对修筑铁路的看法,“此事当国老谋,自非耳食者比。然开千古之未有,费既不赀,法四夷之不经,事将益拙。故不必持奠山川之高论,为正疆界之迂谈。而途既捷,则沟渠益废而不修。道既开,则盗贼且从而思逞,业舟车者无所得食,则患甚于裁驿递设戍守者。无以为险,则祸烈于夷城池。故古之大臣不贪非常之功,不为惊人之事。利不变法,权不害经。而况尚无必是之见,虚设或然之利,贷强邻以启戎心,冀减息以悬厚报乎!此诚达者所慎言,愚夫所搤腕也”⑥[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2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8917页。。当时的外交家、思想家郭嵩焘著有《使西纪程》,介绍西方的科技、文化、思想状况,主张向西方学习,李慈铭对此大加反对,指责郭嵩焘对西方“极意夸饰”,认为《使西纪程》的印行对世道人心危害巨大,“殆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⑦[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0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7153页,第7453-7455页。他指责主张积极学习西方的马建忠为“市井无赖,与夷厮交通”⑧[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14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0539页。。这些标志着面对风云变幻的时代发展,李慈铭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
鲁迅对李慈铭以日记引起他人重视、彰显自身地位和作用的行为进行了讥讽,对其日记评价不高,认为从中“时时看到一些做作”,“吾乡李慈铭先生,就是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 这显然不像日记的正脉,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⑨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6 页。;“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⑩鲁迅:《怎么写》,《鲁迅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蔡元培则对李慈铭的历史考证和历史评论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其“史评新证翻新议,国故乡闻荟大观”①蔡元培:《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2页。。
李慈铭作为清代晚期的文史学家,其史学成就尽管不能与其绍兴史学前辈张岱、黄宗羲、章学诚等相比,但他通过长期的历史札记撰写,考订了以往史志书写的某些舛误,对史志编纂体例和内容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新的看法,对以往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评论,并将历史变迁与当时时局相结合,关注国家安危、体恤民生,这是难能可贵的,亦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启迪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