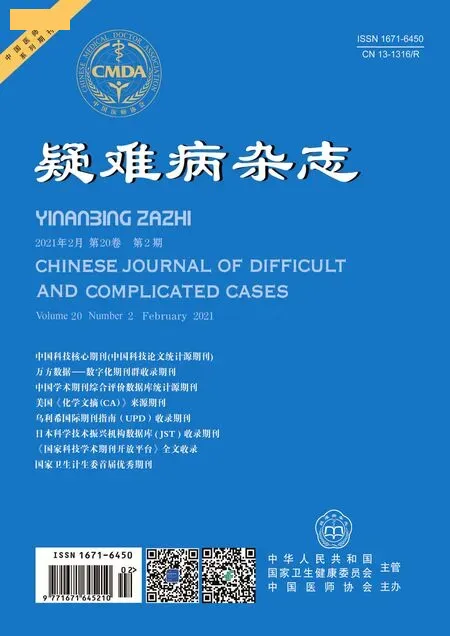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2与肿瘤的关系及其调节机制研究进展
张伍综述 刘修恒审校
G蛋白偶联受体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GPCR)是与G蛋白连接的最大膜受体家族,能够被激素和多肽等不同的配体所激活。 GPCRs与配体结合后能激活细胞内的G蛋白,通过不同的信号转导通路调节不同的细胞生理病理反应。人类基因组中含有多个GPCRs基因,占全部人类基因组3%左右。GPCRs已成为药物研发中最重要的药靶之一,大部分研究着重于其负调控因子——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GRKs)。GRKs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包括氨基端、羧基端和中心活化区。其中心活化区可活化激酶的别构部位,而氨基端可识别底物,羧基端则负责锚定作用。G蛋白信号调节区具有GTP酶活性,能通过增加GTP的水解来调节相应的信号传导过程。
GRK2基因所编码的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家族的成员蛋白,可使β-肾上腺素能受体,非GPCR细胞表面受体及细胞骨架,线粒体和转录因子蛋白质在内的多种其他底物发生磷酸化。以啮齿动物为模型的相关实验表明,该基因在胚胎发育、心脏功能和代谢中的调节作用。其相关调控途径包括DAG信号通路、IP3信号传导通路等。其功能在于特异性磷酸化β-肾上腺素能受体和相关受体的激动剂,可能引起脱敏从而改变细胞内一系列的生理病理过程。
1 GRK2调节机制
1.1 GRK2调节细胞增殖与代谢 GPCR受到激动剂刺激后会发生磷酸化, 可通过GPCR-ARRESTIN-MAPK的级联调节,或与EGFR或其他生长因子受体的交互作用,激活经典的G蛋白依赖性MAPK刺激导致脱敏作用[1]。药物帕罗西汀能够阻断S1P诱导的S1P1(sphingosine-1-phosphate-1)受体磷酸化,并能显著降低PMA诱导的FTYp诱导的磷酸化,这与GRK2在该机制中的主要作用是一致的。其机制在于GRK2通过磷酸化且与 MAPK途径下游的相关受体发生交互作用,在上皮细胞中,GRK2通过与GIT-1结合而增强了S1P1受体对MAPK的刺激作用从而促进了星形胶质细胞中趋化因子受体对β-ARRESTIN-MAPK的激活。另外,GRK2增强了上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中整合素对MAPK信号传导的反应,并增强了HEK-293细胞中的表皮生长因子的表达[2]。但是,GRK2减弱了血小板源生长因子(PDGF)诱导平滑肌细胞的增殖,以及IGF1依赖性的人类肝细胞癌增殖[3]。推测GRK2使这些生长因子受体的磷酸化脱敏来实现。
在癌症进展过程中,不同类型细胞中的代谢变化适应了肿瘤微环境的变化。通过整合癌细胞系细胞内的代谢谱与转录组和蛋白质组学数据,可观察到协调葡萄糖和一碳代谢的肿瘤标志物,这表明癌症中碳代谢的调控与正常细胞有重大区别[4]。肿瘤细胞内由于氧气和养分的量总是处于波动中,线粒体功能和氧化还原状态也跟随变化。自噬和蛋白水平的稳定,增殖和分化网络的信号等都会重新进行调节。GRK2不仅能控制代谢率和肾上腺素能受体,而且已成为胰岛素抵抗与肥胖及线粒体功能的重要研究对象。此外,在发生胰岛素抵抗的高脂饮食小鼠模型中,GRK2水平升高,体内实验观察到激酶水平的降低可预防和逆转胰岛素抵抗和肥胖表型的进展[5]。
1.2 GRK2调节上皮细胞的迁移运动 GRK2在不同细胞类型的迁移中起重要作用。当其转膜效应增加,EP4受体过度脱敏,环磷酸腺苷(cAMP)水平降低。GRK2作为G蛋白偶联受体的负性调节剂,可特异性地活化GPCRs,使其磷酸化,从而介导受体脱敏。由于GRK2可触发各种趋化因子受体的脱敏,因此可在炎性反应过程中调节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中趋化因子活动的信号。此外,LPS可通过降低GRK2水平从而避免CCR2受体脱敏,以此来帮助CCL2诱导的巨噬细胞迁移[6]。GRK2还可通过不同的机制在上皮细胞迁移中起促进作用,例如 GRK2可磷酸化细胞骨架连接蛋白和根蛋白,增强其肌动蛋白的重塑、迁移和侵袭能力。 GRK2还可通过增加MAPK刺激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来维持趋化信使和整联蛋白中存在的极性持久性。最后,GRK2能够通过激活HDAC6来控制微管动力。 HDAC6是一种胞质内的组蛋白脱乙酰基酶,在乳腺癌和其他类型的肿瘤中高表达,HDAC6通过调节皮质激素或微管蛋白乙酰化或去乙酰化的动态变化来控制细胞的生长、运动和侵袭[7]。在对EGF的反应中,GRK2与HDAC6结合并使其磷酸化,从而增强了其α-微管蛋白脱乙酰基酶活性,导致了迁移细胞边缘处的微管蛋白脱乙酰化,其运动能力由此得以强化。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相互作用蛋白1(GIT-1)是一种有多个结构域的蛋白,能够支撑起在黏着斑和细胞边缘处参与细胞迁移的同类物质, GRK2磷酸化HDAC6前需先借助于外部刺激在S670处使GRK2磷酸化[8]。因此,通过特定刺激来动态调节GRK2的磷酸化状态和亚细胞定位,从而可以快速切换信息交流的配体,从而使GIT-1信号体和脱乙酰MTs在皮质极性和膜突起中起协同作用。
1.3 GRK2调节肿瘤细胞内的血管生成和炎性反应 肿瘤微血管内通常有高度血管生成和渗漏,由于缺乏血管周细胞,血管变大和扩张,导致血液供应不足。随之导致的缺氧又进一步促血管生成和促炎性因子分泌,使这一过程不断强化。在这种微环境中,肿瘤相关脉管系统,肿瘤浸润的免疫细胞和间质转化细胞之间相互作用推动了肿瘤进一步的发展[9]。GRK2作为重要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Ser/Thr激酶),可维持炎性免疫细胞和非常规炎性免疫细胞之间的平衡,是炎性免疫反应中的关键调节蛋白。炎性免疫细胞的浸润、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及内皮功能有关的信号传导都受其调控[10]。GRK2还是内皮细胞活化和成熟的几种途径的信号节点,在GRK2下调后,内皮细胞对相关血管生成刺激的反应增强,从而改变了这些细胞形成管状结构的能力,进而打破了肿瘤细胞内炎性反应和血管生成因子的平衡。京尼平苷等药物可通过增加抗炎细胞因子IL-4和TGF-β1来降低促炎细胞因子IL-2的生成,从而增强Th1细胞耐受性,增强Th2活性并具有Th3驱动作用。在该过程中淋巴细胞内的cAMP水平和GRK2表达上升,共同发挥免疫调节作用[11]。此外,GRK2水平降低将会影响TGF-β信号,从而通过及时地反向调节ALK1和ALK5的受体来控制血管生成的激活阶段和分解阶段,这一过程同时也促进了巨噬细胞通过改变内皮细胞的化学趋化分泌及促进血管渗漏发生,导致肿瘤进展,从而升高低氧诱导的髓样细胞趋化因子梯度[12]。
2 GRK2与常见肿瘤
2.1 GRK2与肝细胞癌 肝癌是最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拥有最多的患病人数和最高的致死率,其进展快、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的特性使其研究具有重大意义[13]。肝癌具有极高的侵袭性,微血管侵犯(MVI)被认为是肝癌早期复发及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也是肝移植受者选择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与肝癌的诊断、发生、术前预测及预后密切相关[14]。实验表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血管紧张素Ⅱ(Ang Ⅱ)与肝细胞癌的增殖、侵袭和转移具有重要联系,研究表明该过程是通过抑制肝细胞内GRK2和相关受体的功能表达来实现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1(TNFR1)及Ang Ⅱ的受体AT1R和AT2R广泛分布在肝细胞表面,GRK2在其中如何调节其与肿瘤的一系列病理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Ang Ⅱ可以通过AT1R促进各种组织的血管收缩、炎性反应、纤维化和细胞增殖,而通过AT2R的信号转导则具有相反的生物学效应[15]。 TNF-α的生物学作用主要是通过2种具有不同结构的受体进行:TNFR1和TNFR2。Ang Ⅱ是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中的关键激素,该系统在肿瘤血管的形成和生长中起重要作用[16]。TNFR1是NF-κB介导的促炎细胞存活反应和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关键调节剂。 TNFR1调控的NF-κB信号失调是癌症、炎性反应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基础[11]。TNFR1几乎在所有组织细胞的表面表达,其信号转导具有引起炎性反应和促进细胞凋亡的双重生物学效应。而TNFR2主要在免疫系统的细胞中表达,部分情况下具有促进炎性反应发展的作用,但绝大部分情况下表现为很强的抗炎活性,可以很好地保护细胞[17]。在来自肝癌患者和肝癌小鼠的不同肝脏样品中,对比肿瘤和临近正常组织发现,AT1R、AT2R和TNFR1表达水平明显不同,数据表明AT1R和TNFR1的过表达将促进HCC细胞的生长、迁移和侵袭,而高水平的AT2R引起相反的作用[18]。GRK2极有可能参与TNF-α和Ang Ⅱ的受体调控。
已知GRK2是重要的信号分子,可以影响HCC细胞的多种生物学活性。例如,GRK2通过抑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的表达水平和早期生长反应来抑制HCC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另有实验结果也表明,HCC患者和HCC小鼠肝脏组织中的GRK2水平显著降低,并且Bel-7402细胞中GRK2表达的下调促进了HCC细胞的生长相关特性。这些发现表明,GRK2抑制了HCC的发生和发展。在HCC细胞中,Ang Ⅱ、TNF-α和GRK2的水平与细胞的生长、迁移和侵袭有关,从而影响HCC患者的预后[19]。为了进一步明确细胞因子对肝癌发生和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肝癌细胞内Ang Ⅱ、TNF-α和GRK2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2.2 GRK2与头颈部鳞状细胞癌 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源自口腔、咽和喉内黏膜上皮的恶性转化,是全球第六大最常见的癌症类型[20],患者确诊后存活率往往很低。在患者中观察发现,1/2以上的HNSCC患者经历了复发,并且大多数死于区域和远处的转移性疾病,淋巴结转移是其重要的不良预后因素。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状细胞癌需要采用多学科治疗的方法,包括手术+放疗、伴或不伴化疗及同步放化疗。诱导化疗目前仍存在争议。靶向药物西妥昔单抗已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的治疗中取得满意的效果。针对程序性死亡蛋白-1及其配体的抑制剂也显示出显著的功效,然而,只有少数患者可以从单药治疗中受益。为提高免疫疗效,联合免疫治疗成为可选策略[21]。尽管目前已有手术加放化疗结合的治疗方式,但患者的远期存活率仍未明显改善[22]。因此,更好地了解HNSCC发生和恶性侵袭信号通路中的分子变化,以用于开发新的治疗策略,是改善患者存活率和生存质量的重要研究任务。
上皮间质转化(EMT)是HNSCC病程中的关键过程。在肿瘤细胞侵袭和癌症进展中。 EMT由复杂的信号通路网络调节,导致转录因子的诱导,miRNA表达的变化,以及表观遗传和翻译后修饰的过程。随着鳞状细胞癌(SCC)和未分化梭形细胞癌的进展,已观察到EMT状态与肿瘤转移和复发之间的相关性[23]。GRK2除了在GPCR脱敏中的典型作用外,由于其与细胞增殖相关的信号网络之间的功能联系,正在成为潜在相关的调控子。在高度分化或未分化的HNSCC肿瘤中,GRK2表达较低, GRK2水平是HNSCC细胞中EMT特征的相关决定因素,HNSCC的发展与参与各个阶段的关键分子变化密切相关。在HNSCC细胞中观察到内源性GRK2的下调会触发其发生间充质样改变,此特征往往提示其体内侵袭行为增强[24]。总体而言,这些数据表明,HNSCC细胞中内源性GRK2表达的下调有利于EMT进展,促进恶性肿瘤细胞的运动和侵袭性发展,使其变得更具攻击性,转移到正常的组织和细胞,使肿瘤的恶性程度进一步提升,大大降低预后效果。故对GRK2与HNSCC发生发展的一系列分子机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2.3 GRK2与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是老年男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前列腺癌在男性群体中发病率、病死率逐年上升,而对某些特定类型又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因而寻求新的分子机制以开发新的治疗手段显得十分必要[25]。前列腺癌通常始于前列腺中的雄激素依赖性病变,可通过雄激素剥夺疗法成功治疗。但是,随着肿瘤发展为非雄激素依赖性状态后,则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 前列腺肿瘤从雄激素依赖型向非雄激素依赖型过渡的相关因素尚未完全明确,这也是改善疾病预后的主要障碍。 最近的证据表明,即使没有添加雄激素,非雄激素依赖型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也受到雄激素受体(AR)的调节,这表明AR可能被雄激素以外的其他因子激活[26]。
研究表明, GPCR极有可能参与了前列腺肿瘤的雄激素依赖型向非雄激素依赖型的转变过程。对比恶性前列腺癌标本与临近组织和良性组织,其GPCR表达水平明显上升。此外,前列腺癌患者的前列腺中表达高水平的GPCR配体, GRK2ct肽的表达限制了血清诱导的PC3细胞增殖。表达GRK2ct的PC3细胞生长速率下降与G亚基调节ERK活化一致,后者可控制生长因子调节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过程[27]。Gβγ亚基在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和存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靶向抑制Gβγ信号表达可使体内肿瘤生长速率显著降低。
此外,在前列腺癌患者的组织样品中观察GRK2 mRNA和GRK2蛋白的表达情况时,发现GRK2在平滑肌细胞中的表达高于腺细胞。这与前列腺样品中平滑肌β2-肾上腺素受体的磷酸化可能是由GRK2介导的猜想相一致[28]。GRK2负责与cAMP/PKA无关的β肾上腺素受体磷酸化,因此被称为“β-肾上腺素激酶”。 GRK2类为GRK的“β-肾上腺素受体激酶”亚家族,可在下尿路、逼尿肌平滑肌细胞中表达[29]。在受体激活后,GRK2从Gα亚基和相关受体上解离后,会被异三聚G蛋白的β/γ亚基激活,GRK2通过受体的磷酸化作用引发受体脱敏[11]。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参皂苷Rg3 可改善中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疗效及预后,由此可能涉及对患者血清TGF和VEGF的影响,而此通路是否受GRK2调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30]。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前列腺平滑肌的α1和β2肾上腺素能受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α1-肾上腺素受体的活化引起β2-肾上腺素受体的磷酸化。这可能会增强α1肾上腺素的收缩,并可能由GRK2介导,后者在前列腺平滑肌中表达。因此,对恶性前列腺癌中表达水平上调的GPCR及其配体的研究,对前列腺癌的转化机制和潜在治疗具有重大意义。
3 小结与展望
GRK2是一种多功能蛋白,在多种肿瘤细胞中异常表达,可作为肿瘤标志物的潜在调节剂。GRK2在体内的表达失衡,将会影响到恶性肿瘤的一系列病理过程,故可考虑检测细胞或组织内的GRK2水平来指导对肿瘤患者的检测和诊断,对其研究将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的研究尚有许多未明之处,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如在肿瘤细胞中,GRK2水平或活性的变化是否能够调节代谢网络或线粒体功能;趋化因子受体CXCR4和CXCR7等其他潜在的GRK2靶标在一系列肿瘤中高度表达,并在转移中起作用,但尚未完全了解它们在癌症进展中的作用;此外在肿瘤微环境中存在的其他趋化因子介导的信号传导,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也是未来有意义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