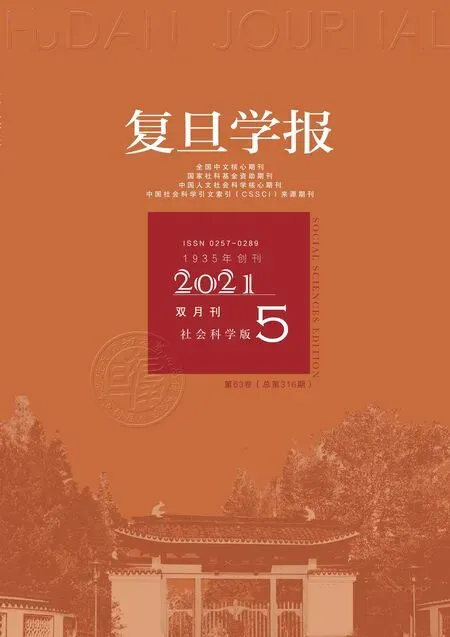主持人的话
章 清
十多年前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拜访叶文心教授时,即已获悉她与北美的同行计划“重读”列文森。作为西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创者之一,列文森之重要性自不待言。他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提出的一些问题,至今仍在发挥影响。不过,相较费正清、史华慈及一批海外华人,列氏受到的重视确实不够。文本“难读”之外,还缘于其有不同于致力破解“革命之谜”及重新认识“传统中国”的问题意识。叶文心教授利用伯克利的资料“重读”列文森,正可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结合多年的阅读经验,叶教授提出应重视以时代知识为背景的阅读与书写方式,在阅读传记的时候,需把传记文本内涵的知识架构放入历史框架中。这篇论文也据此“示范”了对列文森的“重读”,不仅展现了列氏如何在伯克利把中国近代史建制成一个学门,发展出一套相关论述,还指明列文森的中国研究具有明晰的自我学术定位及鲜明的研究立场。这个立场强调的是从世界史的建构出发,认定中国经验在其中完整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即力图“在世界中发现中国”。
“在一个为西方学生而设计的历史学学程里,中国应当表述什么意义?”带着这样的问题,列文森给出了他的答案:无论古代或者近代中国,所展现的经历都具有广泛的思想意义。“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我们自己现在提出来的说法,想对现代世界作全面的理解,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我们自己在道德上以及知识上所认识到的欧洲与美国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就必须从普世意涵的角度来研读中国历史,而不是从我们切身的政治或文化需要出发来读它。”相应的,对于中国的研究,列文森也秉持思想史的方法,关切如何把“思想”结构成为历史,从汉语文本的思想意涵出发,开展跨汉语语境的史学对话。文章也据此指出:列文森所提出的思想史阅读方法,至少包含对两个层面的关注,其一是对思维承载者的关注,其二是对文本历史性的关注。亦即是强调,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是“思想”,而是“思维活动”。对文本的解读,一方面需把特定文本放置在思想承载者所处的时空框架之中,一方面也需把同一个时空框架中生产出来的不同文本拿来相互校读。而无论是对梁启超的描绘,还是对儒家中国的分析,列氏都贯穿着这样的思路与立场,指明晚清及民国的中国思想界,在走出中国、走进世界的同时,往往回头走进中国的过去,以寻求心理与知识上的平衡。
不只是思想史,文学史、哲学史皆不断在泛起“重写”的声音。结合其阅读体验,叶文心教授也道出:重写已经成为话题,前提却是虚心“重读”。重读列文森也就是审视他所搭建的大架构,反思他的方法,认识他的同辈以及其后北美中国学界在学术研究上的各自选项。这个重读不但可以明晰北美中国近代思想研究曾经走过的道路,同时更可以作为重新出发的起点。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列氏有关梁启超、儒家中国的代表作,陆续介绍到中国,引出不少话题。据悉,同样出身伯克利的刘文楠已经完成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重译,期待着这样的“重译”,更能催生对列文森的“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