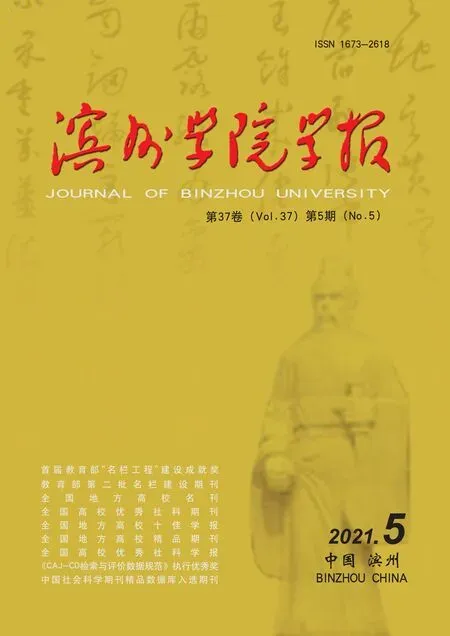《尉缭子》研究述要
李元鹏,刘 苏
(1.军事科学院 战争研究院;2.军事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尉缭子》最早的著录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宋代元丰中期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武学必读之书,影响日大。
一、关于成书年代及作者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艺文志》承自刘歆的《七略》,由此可以推定《尉缭子》一书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即已流传。宋代以后,疑古之风渐盛,南宋陈振孙在其所著《直斋书录解题》中首次对“武经七书”本《尉缭子》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道:“按《汉志》杂家有二十九篇,兵形势家有三十一篇,今书二十三篇,未知果当时本书否”[1]360,怀疑为后人假托之作。以后对该书的质疑之声不断,如清代姚际恒即以《尉缭子·战威》中讲了与《孟子》完全相同的话,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而认为“岂同为一时之人,其言适相符合如是耶?其伪昭然”[2]20。姚鼐亦说:“尉缭之书,不能论兵形势,反杂商鞅刑名之说,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3]52,认为内容驳杂,当是后人杂取众说纂辑而成。谭献认为:“阅《尉缭子》。世以为伪书,文气不古,非必出于晚周,然精语不可没也。”[4]近人黄云眉在《古今伪书补证》中也对今传《尉缭子》与《艺文志》所录之《尉缭》的一致性提出质疑,将今本《尉缭子》视为伪作[5]129。只有明胡应麟在《四书正伪》中认为:“宋世以孙、吴、司马、韬、略、尉缭、李卫公为‘兵家七书’。孙武、尉缭,亡可疑者。”[6]31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古兵书竹简,其中有《尉缭子》竹简残卷。从残简书写字体,及不避汉初皇帝名讳来看,可以断定成书时间当在秦汉之际以前[7]。另据裘锡圭先生的认识,“从一部书的开始出现到广泛传抄,通常总要经历不太短的一段时间。这几种书的著作时代应该不会晚于战国”[8]64。据此,《汉书》附注中关于《尉缭》为“六国时”著作的说法是可信的,伪作之说不成立。
关于尉缭,史籍无生平事迹记载,仅在《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自注“六国时”三字。《尉缭子》开篇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一句,遂《隋书·经籍志》中《尉缭子》下注:“尉缭,梁惠王时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一句,即秦始皇时也有尉缭,而所处时代比梁惠王时晚数十年。郑樵《通志》注“梁惠王时人,隋志一卷”[9]798,宋王应麟称其为六国时人,施子美《七书讲义》则称尉缭为“齐人也,而所著之书乃有三代之遗风。”[10]515明茅元仪《武备志》称其为“魏人”。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称:“尉姓缭名,魏人,鬼谷之高弟,善理阴阳,深达兵法,与弟子隐于夷山,因惠王聘,陈兵法二十四篇。”[11]216以上说法,均未给出其说的史料来源。
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认为:“《史记·秦本纪》云:‘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其计以散财物赂诸侯强臣,不过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据此可知尉缭籍贯及时代。”[12]38即认为尉缭为秦始皇时人。钱穆则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史记》尉缭子说秦王在始皇十年,今传尉缭书有梁惠王问,年世不相及。后人因谓今所传者乃兵家《尉缭》,在梁惠王时,而始皇时杂家《尉缭》则佚。”[13]570
对两个尉缭子的认定,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尉缭为梁惠王时人,以何法周的《〈尉缭子〉初探》为代表,该文从今本《尉缭子》对社会问题的描述性文字,以及引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推断尉缭为梁惠王时期人[7]。第二种观点则从军事学的角度,从书中反映出的战争观、军制、阵法等推断作者为秦始皇时期人,主要以龚留柱的《〈尉缭子〉考辨》为代表[14]。此外,尚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梁惠王时的尉缭与秦始皇时的尉缭为同一人,以徐勇校注的《尉缭子·吴子》一书为代表[15]。作者对梁惠王生卒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梁惠王在位59年,卒于公元前310年,故而认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与秦始皇十年与始皇答对的为同一人,也即尉缭不满二十岁时见于梁惠王,近九十岁时见于秦始皇,并在旁证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推定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关于尉缭其人的问题,学术界已有比较深入的讨论,但因史料缺乏,所有结论均依逻辑或常理推断,虽不乏灼知独见,但无论哪一种结论根基都不稳固,缺乏坚实可靠的证据。相对而言,认为两个尉缭为不同时代的两个人,较好理解。在没有新的、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维持对尉缭其人所处时代悬而未决的状态,当是客观和科学的态度。
二、后世对《尉缭子》的研究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在“杂家”和“兵形势家”分列有《尉缭》二十九篇和《尉缭》三十一篇,目前所见的《尉缭子》仅有二十四篇,仅从篇数上看,与《汉书》著录的两个版本均不相同。此后,《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尉缭子》五卷,列入杂家。《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尉缭子》六卷,均列为杂家,兵家中不见有著录。
颜师古引刘向《别录》曰:“(尉)缭为商君学。”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云:“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16]309,所言尉缭,亦指杂家。贞观初年,魏徵等人编纂《群书治要》,选录《尉缭子》中的《天官》《兵谈》《战威》《兵令》四篇。
明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寘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17]539。明代宋濂在《诸子辨》中称:“《尉缭子》五卷,不知何人书。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问’知之,或曰齐人也,未知孰是。其书二十四篇,较之《汉志》杂家二十九篇,已亡五篇。”[18]27清代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中说:“权势二字,乃明允谲诈残忍,以商鞅、韩非、尉缭为师,贼道殃民之大恶,读孔、孟书者何忍效之?”[19]可见王夫之也将《尉缭子》归入商君一派。
《尉缭子》另有逸文数条。如唐代徐坚撰《初学记》卷二十二武部引用《尉缭子》:“一贼挟剑击于市,万人无不触辟者,臣以为非一人独勇,一市万人皆不肖也。”[20]528《初学记》卷二十四宅部引《尉缭子》“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历代之宅”[20]578。唐代虞世南撰类书《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尉缭子》“天子文衣文缘”[21]541,宋代《太平御览》卷六八四、卷六八六同引《尉缭子》“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缨”[22]3062。
有学者根据上面数条所论多属古代礼制范畴,而与兵法无涉,因而推断,今本的《尉缭子》流传自《汉书·艺文志》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如顾实称:“《初学记》《御览》引《尉缭子》并杂家言,是其书唐宋犹存。《史记》曰:‘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其计以散财物赂诸侯强臣,不过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此当为杂家尉缭,非梁惠王时之兵家尉缭。”[23]153
北宋《崇文总目》将《尉缭子》列入兵家,这是《汉书·艺文志》之后第一次关于兵家《尉缭子》的著录。宋元丰四年(1080)神宗诏令朱服、何去非等人选定武学教材,经反复权衡,最后确定《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入选,合称为“武经七书”。此后《尉缭子》多被列入兵家。《宋史·艺文志》著录《尉缭》五卷,列入兵家,无杂家。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称:“《汉志》杂家有《尉缭子》二十五篇,兵形势家有《尉缭子》三十一篇。今杂家亡而兵家传二十四篇。”[24]913
明代胡应麟认为:“然《汉志》兵家自有《尉缭》三十一篇,盖即今所传者,而杂家之《尉缭》非此书也。今杂家亡而兵家独传,故郑以为孟坚之误,舛矣。”[25]267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肯定了这一说法,“故胡应麟谓兵家之《尉缭》即今所传,而杂家之《尉缭》并非此书。今杂家亡而兵家独传,郑以为孟坚之误者,非也”[26]2535。近人吕思勉认为:“今《尉缭子》二十四篇,皆兵家言,盖兵家之《尉缭》也。二十四篇中,有若干篇似有他篇简错,析出,或可得三十一篇耶。”[27]142但亦有如梁启超称:“《初学记》《太平御览》并有引《尉缭子》文,为今本所无者,其言又不关兵事,当是杂家《尉缭》佚文,然则此二十九篇至宋初尚存矣。”[12]39他认为尉缭为两人,都有著作传世,今本《尉缭子》乃是杂家《尉缭》与兵家《尉缭》两部书拼合而成。
学术界对于今本《尉缭子》传自何处尚无定论。一些学者认为,两种《尉缭》原是两本不同的书,今本由兵形势家《尉缭》三十一篇流传而来;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认识,即今本《尉缭子》由杂家《尉缭》二十九篇流传而来。还有学者认为,《汉书》的分类本身有误,是将一书分列为两类之中,从而引起误解[14]。
目前所能见到的《尉缭子》版本,古本主要有:一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其中有六篇,即《兵谈》《攻权》《守权》《将理》《原官》《兵令》与今本《尉缭子》对应篇章内容基本吻合。但《兵令篇》的字体及简式与其他几篇不同,反与同见一块篇题木牍的《守法》《守令》等篇相同[28-29]。二是《群书治要》节录的四篇。这是唐魏徵摭拾群书辑成,选有《尉缭子》四篇,即《天官》《兵谈》《战威》《兵令》。文字与竹简本基本相同,被认为是最接近原书的本子。三是《武经七书》本。现存宋本《尉缭子》是陆心源皕宋楼所藏,清光绪年间流入日本岩崎氏静嘉堂。另有清人影宋抄本《朱服校定武经七书》之《尉缭子》,书藏于我国台湾地区。[30]从宋代以来流传的都属于今本《尉缭子》,有二十四篇,分别为《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可以看出,“武经”本的《兵令》篇被分作上下两篇,这与竹简本和群书治要本不同。
据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理学家张载曾注有《尉缭子》一卷,当是最早的注本,但已散佚。现存《尉缭子》最早注本是宋金时期由施子美注解的《尉缭子讲义》,该书是《武经七书》的全注本。序言中称:“三山施公子美为儒者流谈兵家事。年少而升右庠,不数载而取高第,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今得其平昔所著《七书讲义》于学舍间,观其议论,出自胸臆。又引史传为之参证,古人成败之迹,奇正之用,皆得以鉴观焉。”[10]序
明清两代注本很多,比较重要的有明代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刘寅感于当时传本《武经七书》除孙子外,其他六书均无注,且阙误甚多,遂“删繁撮要,断以经传所载先儒之奥旨,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格言,讹舛者稽而正之,脱误者订而增之,幽微者彰而显之,附会者辨而析之”[31]刘宾序。篇名下有题解,重要的文句下有详解。该本在当时为武经善本。
清代有丁洪章辑注《武经七书全解》本,有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赐书堂刊本。该书体例新颖,有“全旨”以提其纲,有“节旨”以挈其领,“注”以训其字义,“疏”以释其句理,同时参订历代注家之言,备载战例,间有发挥。
谢重纶撰《武经全题讲义通考》本,有清康熙德庆堂刻本。作者在序言时说:“以故七子之书得窥前人奥旨;间又旁引六经,参以诸史,证以时解,为之条分缕析,融会贯通,不使割裂琐碎。务在语语归宗,题无剩义。”[32]85除对重要文句加以评点外,间有发挥。
朱墉辑有《武经七书汇解》,有光绪二年(1876)岭南古经阁书坊刻本。序言称:“疏解有浅深,汇集有先后,既统括其大纲,更纂序其神吻,必使无义不彻而止。”[11]217
除以上几部重要注本外,明清尚有合《武经七书》同注者达数十种之多,如焦竑的《尉缭子品汇释评》、赵光裕的《尉缭子正义》、阮汉闻的《尉缭子标释》、沈应明的《注解尉缭子》、陈元素的《标题评释尉缭子》、陈玖学的《评注七子兵略》等。
民国时期《尉缭子》版本较少,有《子书百家》本,为1911年鄂官处重刊本,《尉缭子》为其中一种,分上下卷,无注。此外有1940年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所编《古代兵经》之《尉缭子》。该本评注与《施氏七书讲义》完全相同,没有新的发挥。
近人对《尉缭子》也做过一些整理、校勘工作,特别是银雀山竹简出土以后,国内外陆续出现了20余种研究《尉缭子》的版本,如华陆宗《尉缭子注译》、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武经七书注译》之《尉缭子》、钟兆华的《尉缭子校注》、李解民的《尉缭子译注》、刘春生的《尉缭子全译》、徐勇的《尉缭子浅说》、张秦洞的《尉缭子新说》等。我国台湾地区有刘仲平的《尉缭子今注今译》、联亚出版社的《尉缭子兵法》等。
三、《尉缭子》的军事思想价值
《尉缭子》中保留了较多先秦时期的军事观念、军法、军令、军礼等内容,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从思想上看,《尉缭子》是一部言兵而不止于兵的著作,书中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广,除治军、用兵原则外,还对国家治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农战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阐发。
(一)“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卜筮和星占等军事预测行为是先秦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大量占卜战争吉凶的内容。《周易》中也有“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周易·复·上六》)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繁仍,卜筮等方式仍被用来占卜战争吉凶,但逐步被以经验为基础的、符合军事运行规律的、更为科学的军事认识所取代。
《尉缭子》开篇即明确表达了反对迷信神鬼,主张依靠人的智慧认识战争。尉缭对梁惠王迷信《刑德》进行了批驳,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在人而不在天。“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天官》第一)。清代学者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评论道:“尤妙在以黄帝之言,证黄帝之事。”[11]217尉缭以武王伐纣的例子加以说明:“昔武王之伐纣也,背清水,向山之阪,以万二千人击纣之亿有八万人,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官之陈哉?”(《天官》第一)纣王兵败的原因在于“人事不得”。他坚定地认为:“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天官》第一)这里用了一个“智”字,是将军事行为看作是智力活动的结果,人的作用的发挥就反映在智力的运用上,通过深入思考才能准确地把握、筹划和引导战争,所谓“人事”即体现在这里。在《战威》和《治本》篇中,尉缭对这一认识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说:“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矣。”(《战威》第四)“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第十一)这些论述指明,无论面对战争,还是社会变革,都要弃虚蹈实,要求己而非求天。
(二)“不得已而用之”
《尉缭子》对于战争的残酷性认识深刻,但同时也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放弃武力是不现实的。他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兵令》上第二十三)《尉缭子》主张义战,所谓义战,即“诛暴乱、禁不义”(《武议》第八),认为义战贵先,即“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攻权》第五),而对“争私结怨”的不义战争,则应采取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即“怨结虽起,待敌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攻权》第五)。
在进行义战时,他要求对敌国“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则足以施天下”(《兵教下》第二十二),并强调“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武议》第八)。《尉缭子》还着眼于军事和政治的内在关系,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以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兵令上》第二十三),即军事行为是由政治所决定的,故军事要从属政治。
(三)攻守权谋
《尉缭子》强调战前谋划的重要性,“夫蚤决先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勒卒令》第十八)。决策一旦形成,就不能轻易更改,而应当始终坚决贯彻到底。在战争指导上,《尉缭子》重视研究掌握敌我双方情况,强调战略上知彼知己和宏观上的总体运筹。主张要依据实际情况来建立城防,即“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兵谈》第二),若城邑、人口与粮食供应都相适应,则内可以固国土,外可以胜强敌。强调战略决策要从本国实力出发,并具体列举了大国、中等国和小国应采取的不同的战略策略,即所谓“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武议》第八)。《尉缭子》反复强调要“权敌审将,而后举兵”(《攻权》第五),“先料敌而后动”(《战威》第四)。要权衡利弊,慎重决策,并从战略上量敌用兵。他说:“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阨。地狭而人众者,则筑大堙以临之。”(《兵教下》第二十二)
《尉缭子》反对分散兵力,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第二十三),主张进攻首先要迅速集中兵力,“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攻权》第五)。要掌握主动,先机制敌。他说:“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将帅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从者,则我败之矣。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攻权》第五)《尉缭子》十分重视防守谋略,在防守作战准备上,主张必须做到据险设防,兵员充足,武器精良,“千丈之城则万人守之。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此守法也”(《守权》第六)。在作战编队上,主张既要有防守部队,又要有出击部队,“出者不守,守者不出”(《守权》第六),既区分任务,又要相机配合。在作战方法上主张援兵从外线打击围城之敌,所谓“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守权》第六),强调“救必开之,守必出之”(《守权》第六),增援部队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共歼围城之敌。反对消极防守,主张攻防结合。要奇正变通,“正兵先合,而后振之,此必胜之术也。”(《兵令上》第二十三)要善用权谋虚实相济,“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战权》第十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排列不同的阵势,“陈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兵令上》第二十三),向内列阵是为了保护阵中安全,而向外数组是为了防敌突袭。
(四)“赏如山,罚如溪”
统一行动的前提在于统一的制度和统一指挥,《尉缭子》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只要“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制谈》第三)。具体而言,《尉缭子》中从营区划分到战场上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从战斗编成到信号指挥,从将帅受命到各部队任务的区分,从单兵训练到大部队演习和校阅,都有明确要求。对军队的着装、徽章、从军、戍边、宿营以及车阵等也都做了具体规定。如对徽章的规定,“将异其旗,卒异其章。左军章左肩,右军章右肩,中军章胸前,书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后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兵教上》第二十一)。
《尉缭子》强调依法从严治军,强调要明法审令,公允执法,“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武议》第八)。反对徇私枉法,坚决杜绝当时社会存在的“千金不死,百金不刑”(《将理》第九)。同时他又指出,国家应该给将士以实际利益,对待士兵的生活不可不优待,“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战威》第四)。只要“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即能做到“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就能“以少诛众,以弱诛强”(《制谈》第三)。
《尉缭子》谈治军虽承认赏罚是治军的两种手段,但似更倾向于发挥罚的作用,有多篇提及连坐制度。不可否认连坐有其有效性,可以把部队全体的责任下放到每名士兵身上,不使一人置身事外,保证了将领对部队的有效节制,同时还能防止军队整体溃散,然而这种方式责任认定模糊,难免殃及无辜,使惩戒面扩大。
(五)兴农战
先秦时期对农战论述最多的是《商君书》,《尉缭子》也重视农战,将其视作富国强兵之策的基础。《尉缭子》提出“兵胜于朝廷”,即作战胜利的基础在于国内政权统一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是政权稳定的前提,所以尉缭提倡在不放弃生产的情况下,做好战争准备。他说:“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制谈》第三)他还说:“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而亲之,地不任而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櫜,而威制天下。”(《兵谈》第二)尉缭农战思想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要加强国家对市场的管理,通过繁荣贸易来增强经济实力。他指出:“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武议》第八)他还指出:“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认为有粮还要有严格的管理,方能保证粮食送到兵士的口中,否则“人食粟一斗,马食菽三斗,人有饥色,马有瘠形”(《武议》第八)。
总之,《尉缭子》是一部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影响较大的古代兵学名著。明代学者朱墉对其评价颇高,认为:“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11]217尽管《尉缭子》成书很早,但其兵学价值并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渐暗淡,而是始终闪烁着真理之光,对指导今天的军事理论研究仍具相当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反复研读。
——重读《孟子见梁惠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