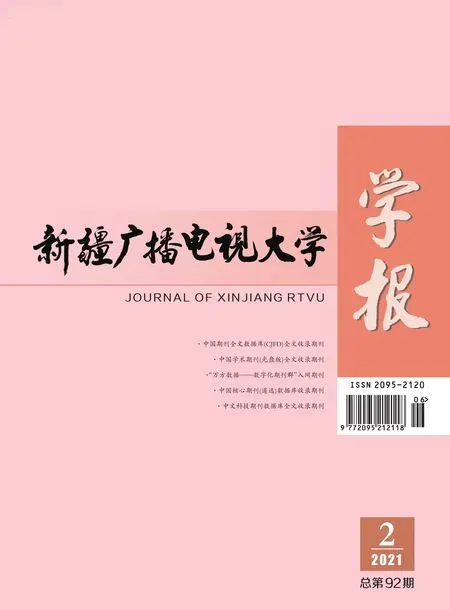论《史记》中的虚构性叙事
张 琳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史记》作为一部史传文学,其主要的构成部分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班固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2377后代也有不少学者肯定《史记》的实录精神。但除去真实的记录之外,书中也不乏作家虚构的内容,合理的想象与虚构使作品更加丰富生动。本文对《史记》中的虚构性叙事进行系统的梳理,并探讨《史记》中虚构性叙事的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
一、《史记》中的虚构性叙事
叙事可以讲述真实的事件,即非虚构性叙事;也可讲述虚构的事件,即虚构性叙事。一般来说叙事是具有虚构性的。在《史记》中所出现的虚构性叙事有不同的类别,既有志怪类的虚构,也有内容和场景设置上的虚构,还存在对心理独白和人物私语之处的虚构。
(一)对超现实事件的叙述
《史记》虽然是史传文学,司马迁本人也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2]2756但其中仍存在许多关于神话传说、怪事逸闻的描述,正像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说:“史记于‘怪事’‘轶闻’,固未能芟除净尽。”[3]对于较早的历史事件例如《十二本纪》中的许多叙述,司马迁就延续了这种史出于巫的传统[4]。
如《殷本纪》中记载:“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2]81《周本纪》记载:“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2]99《秦本纪》载:“女脩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2]151这些对女子有孕和产子的描述带有神话色彩,给伟人的出生渲染了神秘肃穆的氛围,从出生的奇幻彰显他们身份的与众不同。此外还有对神异事迹的描写如张良遇老人赐他《太公兵法》,后发现老人其实是一块黄石等。
《史记》中还有对神兽的描写,如《周本纪》载:“有二神龙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於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2]129其中记载龙的唾液变成了蜥蜴,一个宫女见到它,没有丈夫就怀孕生子了,宫女丢弃的孩子被一对夫妻捡到后起名为褒姒,并献给了周幽王,周幽王因为过度宠幸褒姒而废掉申后和太子,令褒姒做皇后,伯服做太子,甚至烽火戏诸侯,最终招致了周国的灭亡。按照此处的记载,龙涎变为玄鼋使女童怀孕生女,其实是对妖女的附会,“褒姒只是被后世史学家妖魔化的对象,是西周灭亡的替罪羊”[5],这些描述暗示她从出生起就是祸患,从而使周国灭国之罪聚焦在褒姒身上。据钱穆《国史大纲》所言:“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不需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6]可见烽火戏诸侯一事极有可能全然为虚构,西周的灭亡很大程度上是政局所导致的[7]。此外如《高祖本纪》记载武负、王媪常见到刘邦身上有龙出现。秦始皇曾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怀疑是自己带着云气,就藏匿在山林沼泽之间,但每次吕后都能找到他,原因是刘邦“所居上常有云气”[2]296。这些描述显然是虚构出来的带有神话色彩的事迹。
(二)情节和场景上的虚构
《史记》中有不少情节和内容是司马迁根据具体的情境虚构出来的,在场景的设置上自然也有自行构想之处。
如《项羽本纪》中写项羽兵困垓下时:“闻四面楚歌,夜起饮帐中,与虞姬歌阙和之,泣泪数下,左右皆悲,莫能仰视。”[2]283此场景是项羽被困之时的情境,但兵败后项羽与众士兵尽皆战死,司马迁又如何得知如此详细的画面呢?可见是为了展现项羽的英雄气概以及壮士末路时的悲壮氛围而构建出的这幅画面。关于项羽之死的描述,《项羽本纪》中所写的是项羽兵败后东渡乌江,遇到了吕马童,“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2]283但在结尾的太史公曰中却说项羽“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2]287,在《高祖本纪》中写的则是:“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2]320《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也有记载为:“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1]1824但从阴陵奔向东城需要些时间,“东城与乌江又相隔二百六十华里的路程”[8],可见项羽有可能并非在乌江自刎而死,而是兵败后死于东城,那么在《项羽本纪》中对乌江自刎情节地点的设置也可能是司马迁为突出项羽的豪杰之气而融入了自己的构思。
情节上的虚构也见于对赵氏孤儿的描写,《史记》中对赵家事迹的描写是根据《左传》演变而来,但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史记》将《左传·宣公二年》和《左传·成公八年》的事件融合,增加了奸臣屠岸贾的形象,将晋灵公和赵盾之间的君臣矛盾变为了屠岸贾和赵氏一门的忠奸之间的斗争,还增添了将军韩厥因保护赵氏孤儿而自刎的情节。用来代替赵氏孤儿的婴儿也由别人的孩子变成了程婴自己的儿子,使得故事更为曲折离奇,富有悲剧色彩。可见在叙述赵氏孤儿一事时,司马迁为了彰显忠义思想而进行了部分虚构和改编。
(三)心理和细节上的虚构
对于人物的心理活动和部分交谈,《史记》更多地采用虚构的方式进行呈现,因人类自行思索的内容鲜少会公之于众,密语也难为人探知,因此不得不用虚构性的叙事进行补充。
《李斯列传》是《史记》中十分精彩的篇章,极为成功的刻画出了李斯这个人物形象。李斯年少时见到厕鼠非常肮脏,常四处逃窜,而仓鼠安然住在大房子之下,发出了:“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的感叹。身成名就之后,李斯说:“磋呼!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 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这段话中有对位极人臣的担忧,也有对权势富贵的炫耀之情。以李斯所处的地位和谨慎小心的性格,这样的独白不会为外人所道,因此这里的记载并不是李斯确凿言之,而是作者合理推之。还有《晋世家》中记载晋灵公派鉏麑刺杀赵盾,见到“盾闺门开,居处节,鉏麑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2]1515这段话是自《左传》改编而成,古人对此也有许多疑问,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提出:“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9]李元度在《鉏麑论》一篇中说:“况既槐死矣,‘不忘恭敬’数语,又谁闻而谁述之邪?”[10]鉏麑既然已经自尽,那他死前所说的话肯定是无人听到也无记录可查的,所以这些言论其实是史学家合理构想出来的。除此之外,如《晋世家》中骊姬想要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做太子,于是在晚上对晋献公哭诉太子申生想要谋反的话语,又如卓文君偷听相如弹琴时“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2]2601的心理活动等描写均是司马迁虚构而成的。
《项羽本纪》在写鸿门宴时提到“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以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2]266-268。”用细致入微的描绘将鸿门一宴描述的惊心动魄。司马迁并不在现场,却清晰地写出了每个人的座次甚至位置朝向和每个人的神态动作,仿佛他亲眼看见一般,可见对细节如此具体的描述应为司马迁根据人物的身份地位虚构出来的。
二、《史记》虚构性叙事的原因
(一)时代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制约
《史记》采用虚构性叙事的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外部条件的限制,“自西周时起,统治者根据其长期统治的需要,加之以崇德观念和史鉴思想,对夏商神权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和补充”[11],汉武帝为巩固统治将儒学与政治相结合,君权神授成为主流的思想。司马迁曾从师于孔安国和董仲舒这两位儒学大家,因此受到了儒家天命观的影响,在他笔下,帝王将相常有与众不同之处[12]。比如《高祖本纪》中所写汉高祖刘邦身上的许多奇特之事,不仅出生时有异象,而且长得“隆准而龙颜,美须髯”[2]291,左边大腿上还有足足七十二颗黑痣,这种种异于常人之事其实大多是为了展现刘邦身上的帝王气象而虚构的,用“龙”“云”“蛇”等神秘的意象预示刘邦最后获得的功绩,使刘邦的形象变得神秘奇异。其余还有许多圣人有异象的记载,如《五帝本纪》写黄帝“生而神灵, 弱而能言”[2]1-2,《越王勾践世家》写勾践“长颈鸟喙”[2]1573,《秦本纪》中写秦始皇“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2]197”《项羽本纪》写听闻舜和项羽都是“重瞳子”,并由此推断项羽可能是舜的后裔。在董仲舒“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中,这些在圣人身上发生的异象其实是天命的体现,司马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将这些奇异之事记载在《史记》中。司马迁跟随汉武帝参与过许多封禅和祭祀的仪式,见证了天意对巩固统治的作用,因此用天命观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解释,这是受阶级局限性所制约。其实司马迁对于天命的思想也有所疑问,如《伯夷列传》中论述了其实支配社会兴衰的是人,《项羽本纪》里也反对了项羽所说的“天亡我”,认为是项羽暴虐,所以才导致失败。但由于当时认知水平的限制,司马迁并不能以唯物主义思想解释一切行为,因此虽然持有怀疑态度,但仍将它们记录在了文中。
司马迁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地继承和发展,除去客观原因外,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想通过天命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劝。司马迁将自己的褒贬寓于笔下,通过文章暗示有德之人会受到上天的庇佑,而暴戾之人则会受到天命的惩罚。如《外戚世家》写:“高后崩,合葬长陵。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2]1759暗含吕氏不应争夺皇位,汉室因施行仁政受到了上天的庇佑。实际上是在劝说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以德治国。
此外,《史记》中不仅记载了帝王将相的功业,也记述了许多小人物的事迹,包括刺客、游侠、商贾等,其中不少故事的素材来源于民间,许多材料有残缺失传之处,因此司马迁要凭借自己的合理推测将事件原本的面貌尽力还原。就像钱钟书所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3]虽然作品中存在推测和虚构的成分,但司马迁尽力做到让笔下所述接近历史真相,而非无端捏造,因此并不妨碍《史记》实录的本质。
(二)对文学艺术性和历史完整性的追求
司马迁年十岁则颂古文,自幼就饱读诗书,跟随名家学习,后来跟从武帝云游各地,眼界开阔,文采绝世,因此在创作《史记》时在准确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也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在《史记》之前也有史传文学出现,《春秋》主要记录一些大事,但事件之间缺乏关联,叙述十分简单,王安石因此评价它为“断烂朝报”。《左传》在其基础上做了扩充,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在叙事语言和结构上更为成熟。至于《史记》,在准确的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又运用虚构性的叙事手段在故事的细节和人物的心理独白等方面进行了增色,从而让作品浑然一体,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2375的整体构造。
如在描写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时,从荆轲将地图呈上时的“图穷而匕现”[2]2227,到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拿着匕首,秦王挣脱后因剑长无法立刻拔出,再到群臣大惊失色,各有表现,写得惊心动魄,异彩纷呈,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美感完美融合在一起。又如讲述完璧归赵时穿插了人物的对话、心理活动、动作细节等,将二人对峙时的场景刻画的剑拔弩张,无微不至。蔺相如见秦王无意将城池抵换给赵国便“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并且“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2]2148,使秦王因为惧怕蔺相如摔毁玉璧而不敢抢夺,最终蔺相如得以将和氏璧完整带回赵国。这段情节的叙述中虽然存在虚构的成分,但在还原事件的同时让故事更为波澜曲折,以蔺相如为主的叙事视角使得读者更加强烈地体会到他的谋筹,展现了蔺相如的机智和司马迁对他的欣赏之情[13]。
三、《史记》虚构性叙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史记》中对奇闻异事的描述和虚构色彩使得其超越了历史范畴,具有了极大的文学价值,对中国后世的叙事学影响深远,以至于司马迁采用的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和“尚奇”思想“几乎成了后世叙事文学或隐或现的一种自觉追求”[14],后世小说、戏剧等均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唐传奇就受到了《史记》虚构性叙事艺术手法的极大影响,可以说“唐传奇就是对‘尚奇’精神的一种延续”[15],因而唐传奇也具有情节奇特、想象力丰富的特点。例如《柳毅传》中讲述了唐代的一名落榜书生柳毅见到了一名放羊的女子,她自称是龙王的女儿,嫁人后被虐待,柳毅替她传了家书,女子被叔父救回,柳毅之后续弦的妻子就是龙女的化身。这篇唐传奇不仅有对爱情和亲情的描写,也反映了唐代的婚姻生活和当时士人的生活境况。“唐传奇由于叙事内容的丰富性和叙事手法的细节性,其艺术表现力大为提高”[16],而唐传奇的核心成就,正在于通过虚构超越了现实,作家通过虚构创造了高于唐代社会生活的艺术真实,揭示了现实的本质。
对于小说而言,虚构性是其本质特征,文学的叙事就是用话语来虚构艺术世界,离开了虚构性叙事,也就不能称之为小说。以《聊斋志异》为例,不仅在结构上继承了《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按时间叙事的方式,也发展了其中“实中有虚”的叙事原则。可以说“真正有意的虚构是在唐传奇那里完成,而到《聊斋志异》则达到了极致。”[17]如《画壁》讲述了一个书生到寺院游览,恍惚间竟然进入到了壁画中与画中少女幽会,少女的朋友们调笑着让她梳起少妇的发髻。忽然有使者巡查,女子便将书生藏在床下,正在惊慌之时,听到寺中老僧呼唤书生,书生便从画中走了出来,画上女子的发型竟从少女的垂发变成了妇人的螺髻。整个故事似真似幻,趣味横生。其中人进入画中、与画中人共同生活的虚构描写使得整个故事引人入胜。
托尔斯泰说过:“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18]不论是在史传还是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绝对的真实其实是不存在的,合理的虚构使作品更为精彩纷呈,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而坚持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虚构也是将史传文学与小说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准。《史记》中的虚构性叙事使文中的情节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立体丰满。由此可见艺术的虚构对于艺术的典型化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创造典型性的情节和形象,使作品具有超越现实的美感和更高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