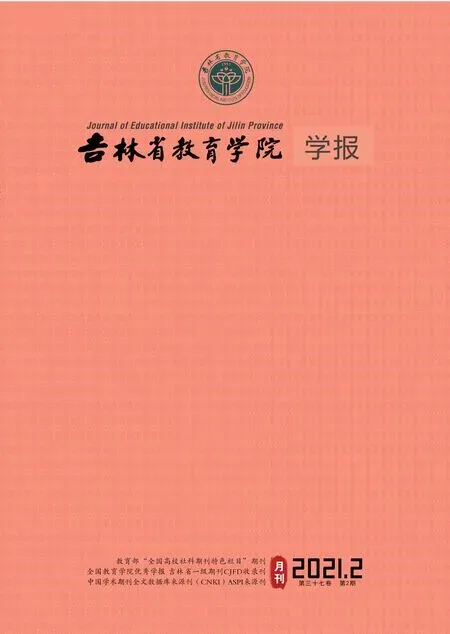脚踏实地的质朴英雄
——论《鼠疫》中的英雄观
王 菲
(吉林省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是20 世纪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他曾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有过一段传奇之交,虽然后来二人在哲学思想上渐行渐远,但加缪仍以自身实力推动了法国存在主义流派的极大发展。
《鼠疫》(La Peste)是1957年加缪获诺贝尔奖时的提名作,小说以其“简洁、明晰、纯净”的独特艺术风格诠释了作者深邃的哲学思想。小说描述了一个叫阿赫兰的海滨城市发生的一场持续近一年的鼠疫之灾。20世纪40年代,鼠疫在阿赫兰爆发,政府采取封城措施,阿赫兰成了一座“孤岛”,所有“岛民”都被迫承受着流放感和疏离感的折磨,忍受着恐惧和绝望的侵蚀。面对鼠疫带来的荒诞现实,医生、记者、政府职员、神甫等生活中的普通人开始了各自以及共同的反抗。加缪在《鼠疫》中并未采用宏大的叙事,而是用冷静的口吻叙述了一段阿赫兰人民抗击疫情的“编年史”。《鼠疫》彰显的英雄观有别于传统式的英雄观,加缪通过对平凡人物勇于对抗荒诞现实的描写,传递了一种脚踏实地的质朴英雄观。
二、“理想化的传统式英雄”——充满悲壮色彩的英雄主义
“英雄”是西方文学中支配并主宰着人物塑造的一个经久不衰的母题:中世纪的骑士英雄、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英雄、17 世纪的古典主义英雄、18世纪的启蒙英雄、19 世纪的拜伦式和撒旦式英雄、20 世纪的海明威式英雄,都可以视为“英雄”母题在不同时代的变体。在“英雄”母题的流变过程中,“理想化的传统式英雄”成为了一种经典的英雄主义形态:大众所熟知的英雄形象,大多被“崇高、伟大、悲壮”这些关键词所定义,尤其是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他们常常被塑造得超乎寻常的勇敢、无畏,充满了悲情色彩,这类英雄形象经常使观众深受震撼、感动泪流。如电影《勇敢的心》中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他带领苏格兰人民反抗英格兰的压迫,追求民族独立,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提出了著名的悲剧“净化说”,他指出,悲剧的作用主要在于激发个人的怜悯和恐惧情绪,使之得到宣泄,并转化为相反的激情,起到“净化”的效果。上文提到的这种勇敢无畏的经典英雄形象和其充满悲壮色彩的英雄故事确实能为读者和观众带来心灵的净化和情感的升华。然而,如若仔细审视这种经典的英雄主义形态,就会发现诸如此类的“理想化的传统式英雄”凸显的是崇高伟大而非平凡渺小,倡导的是超越现实而非基于现实,标举的是激情澎湃而非冷静审慎。这种超越现实、轻易就能唤起人们情感震荡的英雄主义稍有不慎,就很容易滑向米兰·昆德拉口中的“刻奇”(Kitsch)。“刻奇”一词源自19世纪的德国,原义指保存一些破烂作为一生中某个事件的纪念,后被引申为用煽情手法表达模式化的思想与感情,以激发大众共鸣。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赋予了这个词更多的阐释。他举例,当看见草坪上奔跑的孩子,由刻奇引起了两行“前后紧密相连”的热泪。第一行泪说,看见了孩子在草地上奔跑,多好啊;第二行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而“第二种眼泪使刻奇更加刻奇”。昆德拉还将刻奇阐述为“灵魂的虚肿症”“傻瓜的俗套逻辑”以及“一个人在具有美化功能的哈哈镜面前,带着激动的满足看待自己”等等。昆德拉认为,刻奇的实质是一种欺谎、伪崇高和过度赋义,一种表达了“自我伟大的非个人化的不真实的激情”。刻奇几乎成为一种哲学,它过滤掉了生活中的偶然和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得以在道德上抵达无可置疑的崇高,在美学上制造感人肺腑的激情。
刻奇是危险的,因为它一直在预谋情感的放纵和高潮的来临,这种预谋会剥夺日常生活和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并导向一种极权主义,而这种极权主义将会限制人类生活的多种可能性,扼杀生命的真实希望。昆德拉认为,刻奇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导致全民道德失范,进而导致社会分崩离析。但与此同时,他深刻地意识到,由于人具有追求意义的基本需求,因此,具有赋义属性的刻奇很难被消解。但人们应该用理性和良知保持警醒,寻求真相,不落入刻奇的圈套。
二、“行动中的英雄”——《鼠疫》中的质朴英雄观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也对刻奇持非常排斥的态度,韦伯心中的英雄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类型——首先要求智性的诚实,即以清醒的认知获得深刻的现实感,而非以激情超越现实。要勇于面对真相,基于现实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做出改善、改良和改造。韦伯心中的英雄主义立足于实际,是在祛魅后的现实世界中脚踏实地的英雄主义。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写道:“重要的是成为伟大,而不是显得伟大。”这句话透露出的罗曼·罗兰的英雄观与韦伯的不谋而合——英雄并不等于“非凡”。成为英雄并不需要成为身份显赫之人,即“显得伟大”,相反,平凡人也可以拥有英雄的品格,坚守信念,努力成就英雄般的事迹,这才是“成为伟大”。
阿尔贝·加缪的小说《鼠疫》构建了一部阿赫兰城居民对抗疫情的“编年史”。在叙述者眼中,阿赫兰是个“丑陋”的城市。那里“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也没有花园”,是个“毫无色彩的地方”。阿赫兰的人们“工作十分辛苦,但永远是为了发财”。他们把做买卖看作最重要的营生,却也懂得享受凡人的生活乐趣,“他们爱女人,爱看电影,爱洗海水浴。然而,他们非常理智地把享乐的时间留给礼拜六晚上和礼拜天,一星期里别的日子,他们要尽心尽力去赚钱”。阿赫兰是当代许多工业城市的缩影——“这个城市的市容和这里的生活面貌都很平庸。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大家也不难打发日子”。阿赫兰人的日子虽显平庸乏味,却也平静如水。人们依照习惯生活,倒也过得怡然自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席卷了这座海滨城市,阿赫兰人的平静生活瞬间被击打得粉碎。在与鼠疫抗争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人们每天都在目睹生离死别,无时无刻不在恐惧和绝望中煎熬。然而,在恐惧和绝望之中,却涌现出一群质朴的英雄,他们默默地恪尽职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拯救阿赫兰人的性命、抚慰他们心中的创伤,为鼠疫肆虐的黑暗城市燃起希望的火种。
贝尔纳·里厄是阿赫兰的一名医生,以其高尚的品格吸引了其他“英雄”与之并肩战斗,是战疫“英雄”们的灵魂人物。作为一名专业的医者,他敏锐地发现了鼠疫的端倪,并恪守职责,第一时间报告给政府,督促政府发布疫情通知。疫情当前,里厄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凭着医者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过硬的业务能力与鼠疫抗争到底。为了恪守医生的天职和使命,他牺牲了家庭和情感生活,一天只睡四小时,只要是醒着,就一直与鼠疫作斗争。在明知道鼠疫的肆虐无法阻挡、鼠疫杆菌永远不会灭绝的情况下,里厄仍在行动着,因为要“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走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之举。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在面对疫情加重的威胁、无辜孩子和挚友塔鲁的病逝时,里厄虽意识到了生活的荒诞性、悲剧性,但并未放任自己沉浸在消极的情绪中,而是继续前行、挽救生命。凭着强大的意志力和责任感,里厄才能经受住诸多考验。他明白,“在他还看不见尽头的这段时间,他的职责已不再是治愈病人。他扮演的角色只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判死刑”。面对病人家属不住的哀求,他只能秉公办事,让大家隔离,于是他收到了病人家属“您没有心肝!”的指责。可正相反,“正是他的心肝帮助他忍受这每天二十小时的劳累,在这二十小时里,他眼睁睁看着那些天生为活下去的人们一个个死去;正是他的心肝支撑他每天重新开始工作”。鼠疫以其荒诞的方式让生者备受精神煎熬,里厄也一样,鼠疫发生之前他恰好将妻子送到几百公里外的疗养院疗养,夫妻二人关山阻隔,无法团聚。但里厄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他的行动并没有停止,他不相信帕纳鲁神甫“鼠疫是上帝对阿赫兰人的集体惩罚”的说法,而把“与大自然本身作斗争”视作追求真理的一种方式:“既然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归结为一个死字,上帝也许宁愿人们别相信他而全力以赴去同死亡做斗争,宁愿人们不要抬眼望青天,因为上帝在那里是不说话的”。医生里厄让读者看到,“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里厄的道德就是行动的道德”。
让·塔鲁在鼠疫发生的几个星期前刚刚定居阿赫兰,他外貌敦厚、淳朴善良,有着清醒的头脑与和善的性子。作为阿赫兰的外来者,他像“局外人”一般对这座城市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在阿赫兰生活的点滴,“算是这段艰难时期的一种编年史”。塔鲁在鼠疫肆虐之时选择与里厄共同战斗,自愿陪同里厄到处出诊,并积极组建志愿者小队,助政府一臂之力。塔鲁的战斗不仅是为了阿赫兰的居民,更是为了救赎自己。在塔鲁眼中,自己“早已患上了鼠疫”,他所指的“鼠疫”是一种抽象意义,象征着人性的泯灭。塔鲁洞悉了这个社会的荒诞法则——“即使比别人优秀的人们也免不了去杀人,或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在当今世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塔鲁认为,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想要不染上“鼠疫”且不把疾病传给别人,就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强烈的同情心。塔鲁不想成为“鼠疫”患者,所以他选择站在受害者——被鼠疫折磨的阿赫兰人一方,和他们脚踏实地并肩抗疫,这样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塔鲁像一名倔强的战士,怀揣着激情,单方面与荒诞的世界宣战,并用实际行动改变自己和周遭的环境。这位人文主义斗士虽然最后感染鼠疫,离开了我们,可他用实际行动摆脱了人性的“鼠疫”,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政府职员约瑟夫·格朗,是一位“将近五十岁,黄色的小胡子,高个儿,有点驼背,窄肩膀,胳臂腿都很细”的小老头儿,说话时仿佛一直在字斟句酌。他的梦想是写出一本漂亮的诗集,让出版方读上第一句就惊呼“脱帽致敬”。为此他不断打磨润色自己的诗句,每天都坚持创作。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是加缪大为褒扬的英雄。格朗在卫生防疫机构做统计工作,在鼠疫期间,这位老公务员每天都兢兢业业地记录和计算着疾病数据,确保为外界精准地传递疫情的最新动态。在业余时间,他还经常去给里厄帮忙。格朗在抗疫过程中像一只认真的工蚁,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使二加二只等于四,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再次要求之后”。这名认真的老公务员是再平凡不过的英雄,但他在抗疫期间所做的一切,足以让大家对他脱帽致敬。
雷蒙·朗贝尔是一名外地记者,因工作需要来到阿赫兰,却意外因鼠疫被困于城中。封城伊始,朗贝尔到处奔走,想方设法要离开阿赫兰,回到家乡与爱人团聚,但他处处碰壁,无奈只能被迫留在城中。在朗贝尔自己看来,他与里厄并非同道中人:朗贝尔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且为爱而死”。里厄则用理性的语言说话,“生活在抽象观念里”。然而,在目睹里厄一行人抗疫的过程中,朗贝尔被逐渐“感化”,尤其在得知里厄与妻子也分隔两地、无法团聚,却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为阿赫兰而战时,朗贝尔终于顿悟了。在梦寐以求的出城机会到来时,他选择留下与里厄一行人一同战斗。面对里厄让他出城去和朝思暮想的妻子团聚的建议,朗贝尔的答复是“但如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可能感到羞愧”。朗贝尔讨厌英雄主义、讨厌“扮演英雄”,却在这场鼠疫中实现了人格的升华,从开始的事不关己、一心逃离到后来加入志愿者队伍、与阿赫兰人同呼吸共命运,他将个人的幸福追求抛之脑后,转而为阿赫兰人的公众幸福而奋斗。朗贝尔没有意识到,他已然成为了英雄。
朗贝尔是在荒诞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与之对应的,还有小说中的奥东法官和帕纳鲁神父。奥东法官在小说中甫一出场,就展现出并不招人喜欢的形象,“一半像过去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一半像殡仪馆埋死人的人”。他对待自己的孩子并未显示出父亲应有的亲切和蔼,反而显得漠不关心。然而,随着他的小儿子在鼠疫中不幸染病去世,奥东法官也进了隔离营。在隔离的日子里,他回想起了亲情的温暖。于是,在隔离解除后,他义无反顾地返回了隔离营做起志愿服务,因为“这样可以感觉离他小男孩儿近一些”。奥东法官在志愿服务中染上鼠疫去世,可他在去世前,也通过行动做出了改变,成为了抗击疫情的斗士。帕纳鲁神甫在鼠疫初期为全市人民进行了第一次布道,宣称这场鼠疫是上帝对阿赫兰人的“集体惩罚”,是在警告他们停止堕落。他谴责同胞们对上帝的怠慢,要大家即刻反省。然而,当和里厄一同目睹奥东法官的小儿子被鼠疫折磨至死的残忍画面后,帕纳鲁神甫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冲击,觉得“这已超过了人类的承受能力”。自此,他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开始撰写论文《神职人员可否求医问药?》。帕纳鲁神甫的思想转变在第二次布道时有了充分的体现,“如果说不信教的放荡之徒遭雷击是罪有应得,那么孩子受苦受罪就无法解释”。在帕纳鲁神甫看来,对上帝的爱意味着全身心的投入、全面的忘我。但其实,在目睹了鼠疫给同胞们带来的沉重苦难时,他内心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但他又不容许自己背叛信仰,内心受到煎熬。当帕纳鲁神甫感染鼠疫死去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仍经受着内心的挣扎,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帕纳鲁神甫身上,人道主义已然觉醒。奥东法官和帕纳鲁神父也是在鼠疫之中成长起来的英雄,各自经历了精神和思想上的蜕变。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叙述了荒诞英雄西西弗的故事:西西弗被诸神判罚,把一块巨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石头因自身重量会一次次滚落。对世人来说,“没有比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惩罚了”。然而,西西弗却用行动表达着对诸神的抗争和蔑视,他沉默着推举岩石,“静观一切没有联系的行动,这些行动变成了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创造的,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善始善终,并很快以他的死来盖棺定论”。《鼠疫》的主人公们身上映射着西西弗的影子,在面对鼠疫和神的惩罚所带来的荒诞时,躬身入局,勇敢前行,共同牵引着历史前进的车轮,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质朴英雄的力量。
三、结语
加缪的《鼠疫》不仅生动地描写出一部阿赫兰人的抗疫“编年史”,也向读者展现了潜藏在普通人身上巨大的英雄力量。这些人并未头顶神圣、崇高的英雄光环,与传统的英雄形象不同,他们的体魄或许不够强健,他们的性格或许并不完美,甚至还流露出明显的人性的弱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伟大”。《鼠疫》中的英雄真实、鲜活、平凡且质朴,他们并非传统式的悲情英雄,可却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自我,在困苦的逆境中迎难前行——正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默默奉献的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那样,他们虽平凡却伟大。正如小说结尾所言,病毒和细菌或许永远不会灭绝,考验可能会再次降临,但只要人们像西西弗一样永不言弃,各尽其能地积极反抗,人生就是有意义的、快乐幸福的,这就是加缪透过《鼠疫》传达给世人的质朴英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