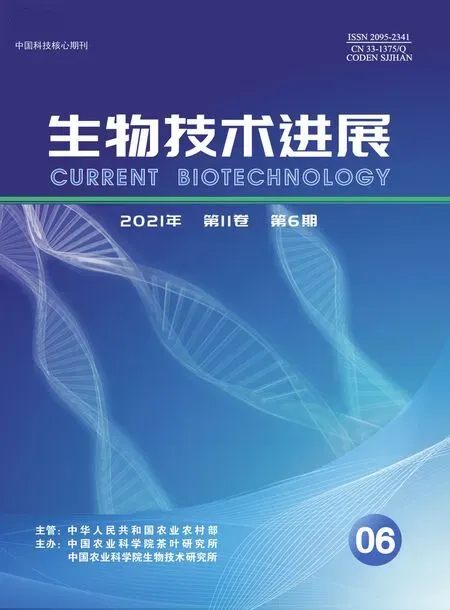胰岛素生长因子2 mRNA结合蛋白3与肿瘤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郭子豪,裴铁民,梁德森*,袁帆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肛肠外科,哈尔滨150001;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护理部,成都610041
癌症某种程度上属于表观遗传性疾病,即基因表达的遗传发生变化,并非DNA序列变化的结果,因此针对表观遗传机制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生物体基因表达中,RNA结合蛋白(RNA binding protein,RBP)扮演重要角色。每个RBP均可与多个RNA结合,通过影响其表达和翻译,从而发挥广泛的生理调节作用。其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 mRNA结合蛋白家族(insulin growth factor 2 mRNA binding protein family,IGF2BPs)作为RBP的一种,其由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 mRNA结合蛋白1(IGF2BP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 mRNA结合蛋白2(IGF2BP2)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 mRNA结合蛋白3(IGF2BP3)构成。IGF2BPs作为转录后的精细调节剂,不仅与肿瘤细胞增殖、存活、化疗抵抗以及侵袭相关,而且在侵袭性的恶性肿瘤中表达上调,与多种癌症的不良预后和转移相关。本文对IGF2BP3在部分肿瘤及组织中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以期为其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研究提供参考。
1 IGF2BPs家族的生物学功能
IGF2BPs家族成员在结构上包括2个N端的RNA识别基序(RNA recognition motif,RRM)和4个C端的KH结构域,其中,与KH结构域结合的是一致的GG(m6A)C序列。因此,各家族成员间表现出特有的相似性,尤其是IGF2BP1与IGF2BP3具有高达73%的氨基酸同源性[1](图1)。IGF2BP1因其特殊的结构功能在多种癌症中表达,并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IGF2BP1的N端RNA识别基序可通过靶向依赖的方式提高IGF2BP1与RNA结合所形成复合物的稳定性。在体内,C端的KH结构域可以调节IGF2BP1与ACTB 3′-UTR中顺式决定簇的结合。而在体外,IGF2BP1可与编码区不稳定性决定因子结合[2],从而发挥调节作用。在KH结构域中,IGF2BP1属于特殊的m6A阅读器成员[3],通过与N6甲基腺苷(N6-methyladenosine,m6A)相互作用于靶向mRNAs[2],从而间接发挥修饰作用。在正常和应激条件下,IGF2BPs家族均能以m6A依赖的方式促进其靶mRNA的稳定性和存储,从而影响基因表达量。研究表明[4],m6A可以通过调节丙酮酸脱氢酶激酶4正向调控癌细胞的糖酵解。因此,m6A通过调控IGF2BP1间接参与癌细胞的生长过程。研究发现IGF2BP1在部分原发性癌症中,IGF2BP1的高表达可影响某些相关mRNA的合成,且IGF2BP1中ACTB、c-Myc等mRNA的高表达又与肿瘤细胞的不良预后及转移相关,说明IGF2BP1高表达与肿瘤细胞侵袭性的相关性较高[5]。此外,体内轴突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IGF2BP1的参与,甚至在轴突发育的各个阶段均可能需要IGF2BP蛋白的指导和参与[6]。

图1 IGF2BPs家族结构示意图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IGF2BPs family structure
IGF2BP2可以靶向作用多种转录产物,并依靠这种多靶向性,使IGF2BP2在胚胎发育、神经元分化、脂质代谢、胰岛素抵抗和肿瘤发生等生理病理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IGF2BP2与我国汉族人群中2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IGF2BP2与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相关[7]。由IGF2BP2基因介导的LINRIS/IGF2BP2/MYC轴可以促进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细胞的增殖[8],从侧面间接证明了IGF2BP2与CRC的相关性。有研究发现[9],GHET1低表达可以调控AKT/mTOR和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来抑制子宫颈癌(cervical cancer,CC)的进展,而IGF2BP2可与GHET1相互作用,说明IGF2BP2与CC之间存在相关性。在一项关于乳腺化生癌(metaplastic breast carcinomas,MBC)的研究中证明了CCN6/IGF2BP2/HMGA2轴具有治疗意义,且IGF2BP2与MBC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10]。提示IGF2BP2自身抗体在癌症筛查、诊断和治疗方面的潜力较高[11]。
IGF2BP3位于人类的7p15.3染色体上,编码69 kD蛋白质。在细胞质中,IGF2BP1和IGF2BP3形成大的(运动直径为200~700 nm)核糖核蛋白(ribonucleoprtein,RNP)颗粒,称为糖体。而在细胞核中,IGF2BP3和HNRNPM控制细胞核内cyclin D1、D3和G1编码转录本的命运。IGF2BP3是一个典型的多结构域RNA结合蛋白,在识别靶点方面具有特异性和多样性,并为多域RNA结合蛋白的多价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12]。IGF2BP3的表达也与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转移和侵袭相关。Ennajdaoui等[13]研究发现IGF2BP3是通过调节与miRNA-mRNA的相互作用来影响恶性肿瘤的表达的。Jønson等[14]研究发现IGF2BP3通过与let-7家族竞争性抑制影响HMGA2的表达。Schmiedel等[15]对应激诱导配体研究发现,IGF2BP3直接下调NKG2D配体ULBP2和间接下调MICB促进癌细胞的免疫逃避。提示IGF2BP3的高表达环境有利于促进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过程。且在大多数实体肿瘤中,IGF2BP3的高表达与预后不良有关,因此,IGF2BP3可能成为一种有前途的标志物以指导人类实体肿瘤的临床诊断和治疗[16]。IGF2BP3可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高表达,且具有一定侵袭特征[17](图2)。

图2 GF2BPs家族主要通路、转录因子以及mRNAFig.2 The main pathways,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mRNA of the GF2BPs family
2 IGF2BP3的肿瘤相关性研究
2.1 乳腺癌
乳腺癌(breast cancer,BC)作为一种高度异质性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的生命安全。CD44是细胞中的黏附蛋白,在肿瘤细胞的生长、转移等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IGF2BP3可与CD44 mRNA结合,增强CD44的表达,提高成纤维细胞IGF2水平,IGF2可进一步激活BC细胞的Hedgehog信号通路,进而刺激BC细胞增殖和耐药。研究表明,lncRNA在BC的发生发展中也具有重要作用,CERS6 AS1通过与IGF2BP3结合可促进BC的进展,增强CERS6 mRNA的稳定性,进而促进BC细胞的增殖[18]。有研究发现CERS6 AS1在BC组织和细胞中的高表达可促进BC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19]。除上述机制外,Wang等[20]研究发现沉默IGF2BP3基因后,IGF2BP3与miR-3614-3p协同作用下降,从而导致TRIM25 RNA的表达降低,使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受到抑制,进而调控BC的发展进程。
2.2 妇科肿瘤
卵巢癌和宫颈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隐匿,早期患者症状及体征不明显且缺乏有效的筛查手段。因此,研究病理类型发病机制对癌症的早期筛查、诊断和治疗均有重要意义。卵巢的原发黏液性肿瘤在疾病的早期诊断阶段缺乏明显的特异性,目前可使用的临床标记物较少。有学者对IGF2BP3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及患者生存率进行了分析,证明IGF2BP3在卵巢黏液性肿瘤中具有高表达性,与恶性肿瘤呈正相关。提示IGF2BP3可用于卵巢黏液性肿瘤的鉴别诊断以及监测肿瘤的进展[21]。卵巢透明细胞癌(clear cell carcinoma of ovary,OCCC)是卵巢上皮性肿瘤亚型中较少见的一种,且晚期的OCCC也是预后最差的组织类型。有研究通过对比IGF2BP3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卵巢表面上皮与正常组织基因表达情况,以及记录后续的实验数据,结果表明IGF2BP3的表达可作为OCCC患者预后的生物标志物[22]。其中,即使是在Ⅰ期OCCC患者中,IGF2BP3仍可作为预后不良的生物标志物[23]。此外,IGF2BP3还可作为OCCC早期诊断的标记物,且优势明显,在宫颈癌组织中IGF2BP3研究价值也较高[24]。甲基转移酶样3(methyltransferase like 3,METTL3)通常在宫颈癌组织中高表达,且与宫颈癌预后不良相关。IGF2BP3的低表达可间接抑制METTL3,进而抑制子宫颈癌细胞的增殖[25]。表明IGF2BP3是具有潜在致癌活性的细胞调节因子,可作为未来妇科肿瘤方面干预治疗的靶点[22]。
2.3 胃肠道肿瘤
我国消化道肿瘤特别是胃癌(gastric carcinoma,GC)和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东亚地区,GC是常见的癌症死亡原因之一。有研究发现通过下调IGF2BP3能显著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肿瘤抑制基因miRNA(miR-34a)的表达与IGF2BP3的表达呈负相关,miR-34a的沉默[26]造成了IGF2BP3的高表达。因此,IGF2BP3与miR-34a的负相关性间接证明了IGF2BP3在GC的预后监测中是有潜力的生物标志物。在肿瘤细胞中有数千种环状RNA,而含纤连接蛋白3B环状RNA(circFNDC3B)可以降低E钙粘蛋白水平,促进GC上皮间充质转化,以及GC细胞的增殖和转移。其中,circFNDC3B通过形成circFNDC3B-IGF2BP3-CD44 mRNA三元复合物发挥功能[27]。IGF2BP3是该复合物中重要的一员,有研究表明micar-125a-5p/IGF2BP3轴在胃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28]。Yang等[29]通过利用RNA免疫沉淀(RNA immunoprecipitation,RIP)和m6A RNA免疫沉淀(N6-methyladenosine RNA immunoprecipitation,MeRIP)等方法,发现下调作为m6A阅读器的IGF2BP3可以抑制肠癌细胞周期中S期的DNA复制,以及肿瘤组织中的血管生成。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下调IGF2BP3可以抑制PI3K/AKT通路,从而抑制结直肠癌细胞的增殖,实现G0/G1期阻滞,进而影响细胞增殖[30]。
2.4 肝癌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消化系统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癌症死亡病因中居于第3位。LINC01138是HCC中高表达的致癌长基因非编码RNA,其是一种致癌驱动因子,可与精氨酸甲基转移酶5(protein arginine methyltransferases 5,PRMT5)相互作用,促进细胞增殖、侵袭和转移,并通过阻断泛素/蛋白酶体依赖的肝癌降解从而增强其蛋白稳定性[31]。因此,通过IGF2BP3影响LINC01138/PRMT5轴可能是治疗HCC的新思路。有研究发现[32],虽然IGF2BP3在HCC中呈高表达,但是在高、低级别异型增生结节及癌旁非瘤肝组织中均不表达,同时,还发现IGF2BP3在HCC中的表达情况与血清AFP水平、HCC的分化程度以及是否伴有脉管侵犯相关。且IGF2BP1、IGF2BP3联合GPC3后能显著提高检测HCC的敏感性,有助于HCC的诊断。说明IGF2BP3在HCC的监测、诊断以及病情评估方面潜力较大。miR-let-7a是一种抑癌miRNA,在多数癌症细胞中低表达。Waly等[33]通过研究发现MIRLET7A3基因甲基化可对miR-let-7a产生相关性抑制,发挥致癌作用。IGF-Ⅱ和IGF2BP2/IGF2BP3是miR-let-7a的潜在靶点,miR-let-7a模拟物可降低IGF-II和IGF2BP-2/3的表达,从而抑制IGF信号通路的致癌作用。除作用于miR⁃let⁃7a基因,IGF2BP3还抑制miR191-5p诱导的ZO-1信号传导,进而增加HCC细胞的侵袭性[34]。因此在肝癌的分子靶向治疗过程中,当上游的靶向基因出现耐药性时,针对IGF2BP3的靶向治疗可成为一个较好的替代点,从而衍生出更好的治疗思路。
2.5 胰腺癌
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作为人类最致命的恶性肿瘤之一,生存率较低。IGF2BP3的表达贯穿于胰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与患者的预后和总生存率密切相关[35−36]。Pasiliao等[37]研究发现IGF2BP3通过增强CD44和KIF11的表达促进肿瘤细胞的基质粘附、运动和侵袭,进而增强肿瘤细胞的前转移行为。Kugel等[38]发现IGF2BP3是let-7的下游靶基因,并通过负性调控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icotinamideadenine dinucleotide,NAD+)依赖性组蛋白去乙酰化酶Sirtuin 6(histone deacetylase Sirtuin 6,SIRT6)介导的Lin28b表达,参与肿瘤细胞的表观遗传程序,影响PDAC的发生发展过程。在Lin28b通路中,SIRT6是潜在治疗靶点,且IGF2BP3也可作为PDAC的新治疗靶点。因此,IGF2BP3基因可作为开发有效的PDAC治疗策略的潜在靶点[38-39]。
2.6 食管癌与肺癌
IGF2BP3在肺癌细胞中虽然也存在高表达,但关于IGF2BP3在肺癌发生发展中的具体机制解释较多。有研究发现,IGF2BP3通过降低p53蛋白的稳定性促进肺肿瘤的发生[40]。Lv等[41]研究表明FOXM1诱导的circ-MMP2(circ-0039411)参与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LUAD)细胞的恶性增殖,circ-0039411通过与IGF2BP3相互作用可增强FOXM1 mRNA的稳定性,形成正反馈回路,从而促进LUAD的发生发展。IGF2BP3不仅在LUAD中有一定的临床治疗意义,且与包括食管癌在内的多种恶性肿瘤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17]。IGF2BP3在食管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igh-grade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of the esophagus,HGIN)中高表达,有研究认为IGF2BP3可作为HGIN术前诊断的补充组织标志物[42]。在关于侵及黏膜和黏膜下层的食管腺癌的治疗方案中,IGF2BP3的表达与肿瘤浸润深度、淋巴转移的发生率及预后不良相关。因此,IGF2BP3对于早期食管腺癌治疗方案的制定有一定的指导性作用[43]。Sakakibara等[44]研究发现,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ancer,ESCC)在所有组织分型中占比较高,在ESCC患者中,IGF2BP3在食管鳞癌组织中高表达,临床实践表明其表达程度与患者预后不良呈正相关[44-45]。
3 IGF2BP3与其他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胎儿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s,HSPCs)在血液病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Lin28b需要与IGF2BP3相互作用,二者的协同表达可在体内有效地重新激活胎样b细胞的发育,参与生物学调节。在b细胞的原始细胞中,Lin28b和IGF2BP3结合于相同的位点,共同稳定数千个mRNA,包括b细胞调节因子Pax5和Arid3a以及IGF2BP3 mRNA,形成了一个自动调节环,该机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生物学基础[46]。另一方面,成年哺乳动物心脏损伤后再生能力有限,而新生儿心脏在出生后可短时间内再生,因此,有研究认为,编码细胞因子的Ccl24和IGF2BP3可作为心肌细胞增殖调节因子[47],并为促进心脏再生基因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4 IGF2BP3治疗应用方面的研究
IGF2BP3广泛运用于临床,如IGF2BP3的免疫组化染色可提高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对胰腺癌的诊断准确性[48]。在HepG2肝癌移植瘤的药物联合治疗方案选择方面,由于IGF2BP3在恶性肿瘤中呈现高表达的特性,因此,IGF2BP3 mRNA的表达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对比指标,刘莲等[49]研究表明阿霉素和红景天苷联合用药的效果优于单独用药。另一方面,宫颈癌是最常见的恶性妇科肿瘤,然而常规的靶向药趋于耐药。研究证明[50]下调DARS-AS1可抑制IGF2BP3的表达,并间接抑制宫颈癌细胞的生长。因此,针对DARS-AS1的研究可成为宫颈癌治疗的潜在靶点。同时,USP11可能通过USP11-IGF2BP3轴通路参与结肠癌、直肠癌的发生发展[51]。研究发现异烟肼衍生物可通过降低IGF2BP3抑制HCC细胞的生长,且IGF2BP3可作为HCC的治疗靶标[52]。因此,在某些疾病的药物形成耐药性时,针对IGF2BP3的分子治疗开拓新的治疗靶点,可为新药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5 展望
IGF2BP3在调控肿瘤细胞命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其不仅在多种癌症中有独特的致癌方式,且IGF2BP3在调节人体的生理功能上也发挥重要作用。IGF2BP3的高表达与多种类型肿瘤中不良预后相关,但IGF2BP3的作用机制是否还存在其他方式,在其他通路中是否有更佳的基因治疗靶点,IGF2BPs家族的中的IGF2BP1、IGF2BP2的具体功能等问题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