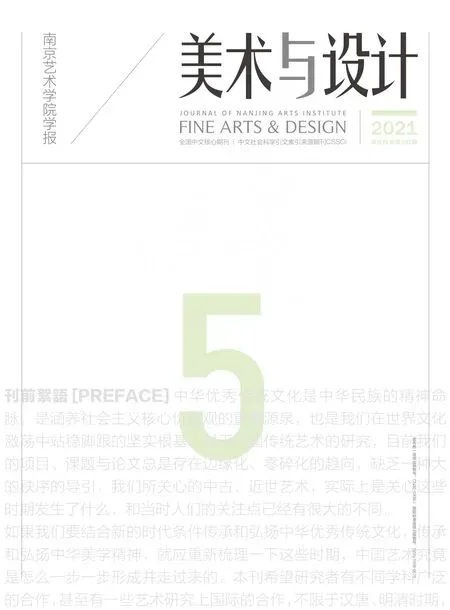“四王”画派:一个关涉滕尼斯“共同体”概念的社会学命题
曹院生(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020)
目前关于“四王”画派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对其艺术渊源的追溯、笔墨色彩等形式运用的深层探讨以及“四王”仿古、伪古的个案考察,还有关于“四王”画派研究范式发展的宏观回顾等皆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文将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社会学家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出发,探讨清初“四王”画派的形成、统一和完善,及其默认一致的绘画范式等相关问题。
一、王氏一族绘画共同体的形成
讨论“四王”还得从王时敏说起。“(王氏)望为太原,自嘉定之南乡寺沟,割而系太仓州籍,遂为州甲族。”[1]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官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肃”。其父王衡,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授编修。王时敏官至太常寺奉常。王家家大业大,诗书传家,常常会邀请一些文人士大夫来家里雅集,或吟诗作画,或听戏,或欣赏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而倡导“南北宗论”的董其昌和陈继儒是他家常客。王时敏从小就接受董其昌“南宗正脉”绘画思想的启蒙,后成为画坛领袖。“一时儒雅高江东,气韵吾推里两翁”的“里两翁”即是同村的王时敏和王鉴。
王时敏生有九子,其中有几位在绘画方面颇有建树。如二子王揆画传家学,丘壑深沉逸秀;三子王撰画仿大痴,笔墨超逸,深得其父衣钵;七子王摅的绘画鉴赏力非同一般,能一眼识出王时敏未能“以造化为师”之憾,而仅仅满足于“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八子王掞作画秀逸不群,曾画扇为王石谷赠行;九子王抑精绘事尤长墨梅。除了自家子弟,王时敏对姑、姊外家子甥皆视如己出,尽心培养。如吴世睿,亦能画,画风酷似其舅。
至王原祁时代,其族人又以王原祁为标杆,学而从之,以画知名者有王宸、王玖之、王三锡、王鸣韶等。刘建龙《正脉:娄东王时敏、王原祁家族暨艺术综合研究》中“王氏一族画人录”列举了39人之多,[2]其中不包括笔者上文所列举的王时敏的五个儿子,他们承王时敏、王原祁后多以画知名。可见绘画成为王氏一族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他们在一起享受着绘画的乐趣、彼此之间相互中意和互相给予欢乐。
滕尼斯说:“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3]40在此,滕尼斯将共同体设定为人类意志的完善统一,它意味着人类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恰恰是彼此分离的,也正是通过这种分离,人类才能意识到意志保持统一的状态。众所周知,不同条件下的人类个体之间在原始的、既定的、自然的状态下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形式,其中以最强有力的方式结合为三种关系: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在这个天然的族亲关系中,自然存在着一种根植于意志而发展成为共同体胚胎的倾向和力量,然后在共同的生活中,相互中意相互肯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体。据此,王时敏一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自不待言。
那么,胚胎于王氏一族共同体中的绘画群体,他们的结合是不是也构成一种共同体?
在这血浓于水的亲情欢乐里融进了不少原本就令人舒服或者变得令人舒服的绘画乐趣、习惯和回忆,遗传性地保持着一种共同的绘画倾向和力量,并且形成了一种持久延续的相互肯定的关系。这种相互肯定源自共同体成员在绘画学习与交流中对绘画思想的默认一致,是形成绘画共同体的先决条件,其具体表现为深得王时敏的衣钵,画风与王时敏相似。其实这里既有对王时敏绘画范式相互中意的亲密性,还有此范式不轻易外传的隐秘性,更有排他性地相互肯定此范式,或者说他们不会选择别的绘画范式,这就是一种人类意志的完善统一。不仅如此,“在一个人的回忆中,另一个人的形象和行为必然会与一切令人舒服的印象和经历结合在一起。而且比如越是受到外来的威胁,越是想起这个群体,结合就越明显,越强烈,越密切,因此,种种情况都会促使他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同发挥作用。”[3]50也就是说这个群体还表现为统一对内对外发挥作用,是一种现实的和生机勃勃的结合。可见,滕尼斯所谓的“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是在共同体里的生活。”[3]43“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3]45说的就是王氏一族绘画群体的共同生活。可想而知,王氏一族的绘画群体就是一个绘画共同体。
在倡导家学传承的中国,重视血脉传承的意志强化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力。家学的存在与延续,常常内化为一个家族的精神与使命,每一个家族成员皆有一种务必使其持续发展下去的意志力,它有赖于母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长期保持对家学的乐趣、相互的习惯和相互给予的欢乐与回忆。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是最为持久的、最强有力的结合方式,“在父亲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中,这些方式达到了统一和完善。”[3]50我们知道,通过婚姻,父亲与子女的关系里普遍存在着一种统治不由人的纯粹的权力和暴力,父亲的地位被提高到天赋人权的地步,彰显了在共同体意义上的统治理念,要不怎么会有“天地君亲师”这一说法?当然,这种统治并不意味着使用和支配共同财富以谋取私利,而是指作为父亲要负担起生养和教育子女的任务,传授大量的生活与学习的经验,使得孩子获得成长并回报这个共同体,由此而建立一种真正的相互关系。王时敏作为“父亲”,他为儿孙确立了绘画“范式”,尽力培养他们,传授他们绘画经验;继而王原祁作为“父亲”,继续完善此绘画规范并培养其下一代,从而使得这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绘画共同体得以统一与完善。
总之,在父权家长制里,王氏一族绘画共同体成员基于原始宗教的渴望,对绘画家学传承的意志表现出了天然的、排他性的完美统一,从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享鲜活的绘画生活。毋庸置疑,父权制成为这个绘画共同体形成的根本机制。
二、绘画共同体内的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许多家庭结合起来,并按照一定的社会形式居住在一起。各个家族成员都有劳动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从而形成某种不同的劳动分工和享受分配,产生着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
同理,在王氏一族绘画共同体中,所有成员都有资格共享家族内的财富,如绘画范式,以及体现绘画范式要义的绘画教育和绘画典范作品。王氏一族绘画共同体共享的绘画范式是董其昌所确立的“文人画范式”,即以笔墨为中心,形象为笔墨服务,意境出于笔墨。[4]它颠覆了“六法”所确立的以形象为中心,笔墨服务于形象,意境出于形象的古典绘画规范,是对元代山水画以形象与笔墨皆为中心,意境出于形象与笔墨的绘画范式的创新。这个共同体所接受的绘画教育也是董其昌提供给王时敏的教学模式,即从董其昌等杰出画家所作的“临摹粉本”入手,①“娄东王奉常烟客,自髫时便游娱绘事,乃祖文肃公属董文敏随意作树石以为临摹粉本,凡辋川、洪谷、北苑、南宫、华原、营丘树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语拈提,根极理要,观其随笔率略处,别有一种贵秀逸宕之韵不可掩者,且体备众家,服习所珍。昔人最重粉本。”见[清]恽寿平《瓯香馆集》,《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再通过“仿”“拟”“摹”南宗绘画达到“不待仿摹而古人神韵自然凑泊笔端”的境界,[5]923并以之彰显共同体绘画范式要义。其绘画典范作品则包括王时敏在“南宗正脉”指导思想下收藏的南宗绘画作品及董其昌、王时敏、王原祁等优秀画家所创作的作品。与此同时,在此共同体中,付出了辛勤劳动并取得了可喜成就还能者享受到更多的权益。如王时敏、王原祁等因绘画能力强、创作产量高赢得了许多让人羡慕的荣誉、地位和威严,充分体现了共同体中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如果说这个荣誉和威严是对其绘画专业成就的回报,那么还有一种荣誉和威严的享受是回报他们在共同体内行政事务管理上的呕心沥血。
如前所述,王时敏不仅为王氏一族绘画共同体培养了许多的画家,而且培养了王掞、王揆、王原祁等位高权重的官僚,并参与到朝廷绘画艺术建设,足见王时敏的深谋远虑,而琅琊王氏王鉴一族则日益家道中落。
王原祁甫成进士后专心从事绘画,遵照康熙“稽古右文,崇儒兴学”的文化策略,配合康熙完成了几个大型文艺事业。他参与《康熙南巡图》的绘制,充任《佩文斋书画谱》和《万寿盛典》的总裁,可谓恩宠有加。不仅如此,为了迎合康熙所推尊的程朱理学,王原祁要求作画须“理”“气”“趣”俱到,画面呈现出“清真雅正”的“中和”之气,正是因为其绘画体现了儒学正统的底色,康熙将其定为画之正统。当然,将“四王”画派树立为正统画派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因为它是当今画坛的一面旗帜,另一面是因为它是江南文人集团的一面旗帜。
王时敏、王掞、王原祁等为了王氏一族共同体的命运,为了维护绘画共同体的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付出就有收获。此外,还有一种享受的优越感,其本身常常会外化为一种权力的行使和命令的发布。于是,八十二岁的王时敏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立遗嘱时,“诸子以西田小筑尤公一生意志所注,宜少留以存付托,请于分授田中各出数亩凑成百亩以补此项。盖仰体公意,将以西田让付子掞也”。[6]437-438诸子“仰体公意”就是尊重王时敏的意见将西园分割给王掞。西园是王时敏晚年生活、娱乐、会友之地,也是太仓州及其周边地区文人士大夫的活动中心,有其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王时敏将西田交付给他有其长远目的。同时又将王氏一族书画收藏这一资产传给了王掞,可能还是考虑到诸子之中王掞仕途最为显赫,为家族的兴旺发达能够提供极大的保障,同时还考虑到他酷爱书画及收藏,易于世守吧!还有一部分则给了王原祁的父亲王揆。①周亮工《清晖阁曾贻尺牍》卷一有王时敏《行书致王翚札》,中云:“又从弟索大笔,细观如山樵长轴,与大儿所藏子久,次儿范中立二帧。”清顺德邓氏宣统三年(1911)刊本。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十六岁的王时敏特地将《小中见大册》交给了王原祁,这一册山水可是“四王”绘画正脉的典范,寄托了王时敏对王原祁延续画学的厚望。
一句话,作为高贵者的王时敏,他享有的荣誉和感激就是拥有对家族财产分配的权利和行使命令的权利;作为高贵者的王掞、王揆、王原祁等,他们也享有荣誉和感激,在占有和分割财产的时候,最好的土地和绘画藏品通过普遍意志划归到他们的名下,成为他们的永久财产。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家族或村庄里,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制度里,合乎自然的分配理念和神圣化的传统决定强烈地主宰着整个家族或村庄生活的一切现实,包括绘画共同体生活的一切现实,以及与之相应的现实的、正确的、必要的秩序理念,而“交换”“购买”“契约”以及“规章”这些概念事实上并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它们属于“社会”概念而不属于“共同体”概念。
显而易见,这种家族遗产的分配,一方面显示了父权制下父亲的威严,同时又强化了继续保持、滋养和培育绘画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财产分割里关于享受和劳动的交互关系。比如王掞,在朝廷中位列内阁大学士,乃首辅大臣,谁能肯定王翚、王原祁、宋骏业参与的那些绘画盛事与他这个首辅大臣没任何干系?不可否定,他对王氏一族这个绘画共同体成员的关照既是一种本能,也是一件让彼此都高兴的事情。这种高兴与他自己享受手中权力的内心喜悦是相互交融的,一方面为自己的权力而自得,笑起来很天真;另一方面为保护族人而高兴,笑起来特别温柔。当然,所有这一切皆源于这个有着血缘关系的共同体。
总之,在王氏一族绘画共同体中,各种关系全部表现为意志的相互确认和彼此服务,而且其中的每一个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力的平衡状态:从关系中获得更多的享受对应于为关系付出更沉重的劳动和斗争。虽然这种辛劳和斗争本身是一种乐趣或可能成为一种乐趣,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较大的共同的力量也是较大的进行帮助的力量,贡献得越多享受得越多,而较少的享受也就与较轻松的劳动相一致。
三、三种威严:年龄的威严、强力的威严、智慧的威严
滕尼斯说:“有一种优越的力量,它被用于下属的福利或者根据下属的意志实施,由此也为下属所首肯,我把这种力量称为威严或权威。比如有三种威严:年龄的威严,强大的威严,智慧或者智力的威严,它们相互之间是不同的。它们又在父亲的威严里结为一体,如高居于他的家人之上,保护、提携、领导着他们。”[3]53而在王氏一族绘画共同体中,王时敏就是这样的一位极具威严的人物。
先说年龄的威严,它主要用来衡量法官的工作和公正的性质。在处理绘画共同体内因各种困难所产生的矛盾时,作为“老人”的王时敏要超然其上冷静而公正地去处理其中的事务,解决问题避免矛盾恶化,维护共同体的发展。如上文所说的符合整个共同体意愿的财产分割的处理。
此外,王时敏自作主张忍痛割爱变卖自己所收藏的书画珍品以解家族贫困之危。甲申之变后灾害不断,官府逼粮急迫,王氏一族家庭经济每况愈下,生活困苦不堪,从其丙午年的致王抃家书十通可知王氏一族穷愁至极:“八弟王掞虽幸弋获,遂其平日攻苦之志,然一番大费,房户中籫珥衣被之类,典质殆尽,尚多那撮。赊取诸物,无术措还,我又赤手无能资助。”[7]为了家族的生存大计,在康熙壬寅(1662年)至辛亥(1671年)间,这个继明末项元汴、韩世能、董其昌之后的又一“收藏冠海内”的大收藏家变卖了大量的家藏书画作品解决大家的困顿。②自1785年题王时敏《仿元六家图册》中辑出,上海博物馆藏。再说强大的威严,它必须通过经受残酷的斗争,表现出所需要的勇气和勇敢,以完美地呈现出它是一个贵族应有的威严。在大是大非、生死存亡和前途未卜之际能洞察出其中的厉害,避免危险,才是真本领。在王氏一族共同体中,父为子纲,其中不乏父权制的统治,自然保持着族人对王时敏自然威严的信仰,此外人们还敬畏其高贵的出身,这种敬畏意味着以直接的方式将这个现实的和想象的首领同王氏一族的祖先结合起来,从而保证了王时敏的神圣出身和权威性,这既方便了他行使自己的权力又获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感激。当其权威累积到充盈于太仓州时,其强大的威严更不必说。比如,为了王氏一族大共同体的利益,他毅然选择失节,率全城之人跪迎清军入城,投降清廷,然后又不遗余力地培养自己的子孙进入清廷的政治核心。毋庸讳言,王时敏的失节换来了王氏一族大共同体的兴盛,也就保住了绘画小共同体的利益。在整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中,王时敏表现出了其强大的威严和果敢。
最后是智慧的威严,它作为艺术精神领袖的威严,被视为宗教信仰,凌驾于一切其他的威严之上。
在亲属关系里,中意和记忆产生着感激和忠诚,在相互信赖的共同生活里亲属关系真实地呈现出来。在亲属关系里,祖先是神;在邻里关系里,父亲和祖先一样正在变成神;在朋友关系里,被祖先和父辈所信仰的朋友也正在变成神。“四王”绘画共同体里居住着董其昌和“四王”等神一样的人物,这个共同体的力量以杰出的方式存在于他们身上,他们在继承南宗绘画的过程中创造奇迹,确立和完善文人画范式。“他们作为父辈和法官,作为主子和头领,作为管教的师傅和教师,本身就是这些人的威严的原始的载体和楷模。”[3]57于是“四王”在绘画共同体中获得了神一般的精神领袖的地位而受人膜拜。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他通过完善董其昌的文人画范式实现其智慧的威严,同时他又将这种智慧的威严当作一种福利惠泽于共同体。如给共同体成员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传授绘画心得,进行绘画批评,奖掖后学,甚至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提携他们,在作他们的品上作赞誉性的题跋等等,弘扬绘画事业,壮大绘画共同体。
总之,高高在上的“四王”尽心培养和提携着共同体成员在绘画道路上迈进,集多种威严于一身的他们自然会使弱者心生畏惧,当然仅仅是畏惧就会产生否定或拒绝,但是他们在绘画活动中的各种善行和恩惠会唤起整个共同体成员对他们的尊敬意志。只要这种意志占优势,在畏惧和尊敬的交织中敬畏之情必定油然而生,于是温柔和敬畏对立,善意和尊重对立,有机的绘画共同体关系才得以形成。也就是说,绘画共同体内有一种优越的力量,无论是来自“四王”还是其他的优秀者,常常被用于下属的福利或者根据下属的意志而实施,并为下属首肯。也正因为这种力量的存在,它一直在保持、滋养和培育着王氏一族绘画共同体的发展。
四、三种共同体及其形成机制
如前所述,王时敏与其儿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绘画共同体。在这里,王氏一族的绘画爱好者一起生活在一个保护着他们的屋顶之下,围着同一个“灶台”劳作,又围着同一“餐桌”共享食物,共同占有和享受着美好的绘画生活。优秀的先辈王时敏和王原祁等具有一种优越的力量,像那看不见的神灵一样被加以崇拜,他们大权在握,维护着诞生于父权制度下的这个家政式绘画共同体。
血缘共同体作为本质的统一体发展和分裂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就像亲属是血缘共同体的普遍的特性,邻里则是地缘共同体的普遍的特性。
王时敏和王鉴同里,住在一个村庄里,他们有共同的田野,或者仅仅有农田划分你我的边界。在这块土地上,人们不断地接触、相互的习惯、彼此非常熟悉,在共同的生活中遵守共同的秩序和管理。那么,在这个地缘共同体中生长出来的地缘性绘画共同体所赖以生存的“水土”是什么?他们信仰的“神灵”是哪个?
我们知道,王时敏望属太原王氏,而王鉴望属琅琊王氏,同姓不同宗,两个家族之间始于王锡爵和王世贞时期“以同里缔交”,[5]929二人以叔侄相称。[8]他们俩皆是董其昌的学生,可以说董其昌的南宗绘画思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水土”,董其昌是他们绘画世界里信仰的“神灵”。王鉴曾作《梦境图》向他心中神一样的董其昌致敬,其自题曰:“予趺坐中堂,观左壁画,乃思翁笔,幽微淡远,不觉抚掌赞叹。”[9]王鉴在图中描绘了一个“令人有天际真人之想”的理想国,在这个国度里,董其昌的“幽微淡远”王鉴将其称之为“异香”,这是何等的信奉和膜拜!
因为同姓同里,又以同族叔侄辈分相称,加之二人在绘画中相互首肯且以画名闻乡里,所以当时的吴伟业、周亮工、恽格皆习惯地将其合称为“二王”。虽然此时的“二王”与后来大家所称的“四王”初无关涉,但不可否认它标志着地缘性绘画共同体的形成。
滕尼斯说:“根据家族类推,被视为共同体的占有和享受的最有明确界限的形态是村庄和城市。家族和村庄两者分开之前是部族,部族已经被称为家庭之前的家庭,但是同样,尽管特征不是那么清楚,也可以理解为村庄之前的村庄。因为它本身当然包含着这两种主要形式的可能性。因此在部族之内,父权家长制性质(由生育来阐明的一切威严都必须集中在这里)和结义的性质(情同手足)相互混杂着,统治的性质和志同道合的性质相互混杂着。”[3]68-69在家族里父权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村庄里结义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又不得不承认,在家族里不乏情同手足的精神,在村庄里不乏父权制的统治,因为一个村庄都会维持一个杰出的家族应有的高贵而天然的威严,敬仰德高望重和高贵门第,并将其部族的首领直接地等同于部族共同的祖先加以祭祀和膜拜。如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祀乡贤祠,学者私谥(王时敏)为恭孝先生”。[10]“祀乡贤祠”就是在村庄里的祠堂接受地缘共同体的祭祀,而不是在家祠。其实,这就是地缘共同体中村庄结义制下的一种习惯或习俗。同理,在地缘性绘画共同体活动里,前往乡贤祠祭祀和膜拜王时敏等杰出的绘画精英也成为一种习俗。
之所以要保留这种习俗或习惯,是因为邻里关系在本质上受制于共同体居住这一条件的限制,会面对比亲属关系更多的困难,因而它更需要寻求固定的集会习惯和各种神圣仪式的支持以获得共同的意志和力量。不可否认的是,共同体成员在这种固定的习惯、习俗和仪式中所获得的宗教力量往往比他们所遵循的文人画范式更具有凝聚力和张力。由此可知,父权制和结义制交互作用是形成地缘性绘画共同体的根本机制。
作为行动的统一体,血缘共同体逐渐分化为地缘共同体;作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意义上纯粹地相互影响、彼此协调,地缘共同体发展为精神共同体。在此,人们总是以有机的方式和意志的相互肯定而结合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方式的共同体。在上述三种共同体之间,它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从前的方式包含着后来的方式,或者后来的方式相对独立于从前的方式。“因此可以观察到这些原始的方式的各种很容易理解的名称相互并存:一、亲属;二、邻里;三、友谊。”[3]54亲属有家作为他们的生活场所,一种爱的记忆温暖了彼此;邻里在村庄里共同生活,某种特定的习惯和习俗支撑着彼此;友谊独立于亲属与邻里关系,以一致的工作、一致的思维方式作为条件和结果。“由于职业或艺术上的相同和相似,最容易产生友谊。”[3]55脱胎于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的“四王”画派就是精神友谊的产物,在这个精神性绘画共同体中有他们通过共同的精神所创建的、被庆贺的神,它就是董其昌、“四王”以及体现他们绘画精神意志的文人画范式。
王时敏“奖掖英髦不遗余力,人素钦佩”“平生爱才若渴,不俯仰世俗,以故四方工画者踵接于门,得其指授无不知名于世,海虞王翚其首也”。[11-12]接踵而至的四方工画者有王翚,他是虞山人,经王鉴推荐而来,居王时敏家学习绘画。他和“二王”既不是亲属关系,又不是邻里关系,只是师徒关系而已。当王翚、王原祁加入“二王”绘画群体并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时,尤其是当虞山、娄东画派日渐壮大并加入其中时,“四王”画派的形成则水到渠成。彼时以“二王”为核心的绘画共同体是地缘性的绘画共同体,而此时以“四王”为核心的绘画共同体则是精神性的绘画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中,他们有一致的工作和一致的思维方式,并且有相互肯定、默认一致的绘画范式。这种艺术意志自然是来自于董其昌的文人画规范。这些绘画艺术上的志同道合者就像他们信仰上的教友,他们在绘画学习中时时刻刻受到一种精神纽带的约束,为一项共同的绘画事业而工作。他们既不完全共享同一个家庭,也不完全共享同一块土地,而是共享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一座神秘的城市或者一种神秘的大会,它们仿佛有一种艺术家的直觉,由于一种创造的意志而活灵活现。
也许有人会说,王翚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不同宗同里,只是作为朋友和志同道合者,他们本身的相互关系最不具有一种有机的和内在上的必然性质,也不受本能制约,而且这种关系似乎是建立在偶然或者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其实不然。在友谊关系里,记忆体现为对他人的感激和忠诚,特别真实地表现出相互的信任和依赖,虽然它不是天然的、有机的,但是每一个个体都希望通过相互间的交往获得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知识与能力,并且熟练地掌握它。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师徒关系还显示出一种父亲的威严。人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徒弟侍奉老师,应当像对待父亲一样恭敬,要学习老师的为人处世和技艺,哪怕只当了你一天的老师,也要终身作为父亲那样敬重。那么这种事师如父的敬重从何而来呢?它来自“学三年,帮三年”的生活,它是一段持续不断的接近、频繁的接触,它意味着彼此的相互需要、相互肯定,同时也意味着相互的阻碍和否定以及各种纷扰的发生,但只要友爱大于分歧就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关系。当然,只有当他们之间的接触频率和亲密程度达到一个确定的界限时,他们就能承担共同体的生活。
可见,“四王”画派这个精神性的绘画共同体是在父权制、结义制和师徒制合力作用下形成发展的,并非建立在偶然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那种建立在偶然和自由选择意志之上的结合属于“社会”概念。[3]136-138
五、默认一致的文人画范式
默认一致是绘画共同体成员共有的相同的、有约束力的绘画思想,它是把人整合到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每一个工画者都有欲望和理智,都必须通过绘画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理智和存在的意义。作为同一个绘画共同体的成员,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自然法则就是大家在绘画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中彼此都要尊重一个真正的和基本的意志,这个意志就是源自绘画语言本身所发展和培育出来的本质意志,即绘画范式。然后,大家在相互默认一致的范式指导下从事绘画工作,并以此作为工具解决绘画中出现的正当问题,最后共享绘画成果。正如滕尼斯所说:“默认一致就是建立在相互间密切的认识之上的,只要这种认识是受到一个人直接参与另一个人的生活即同甘共苦的倾向所制约,并反过来又促进这种倾向。因此,结构和经验的相似性越大,或者本性、性格、思想越是具有相同的性质或者相互协调,默认一致的或然率就越高。”[3]59
那么,“四王”画派从血缘共同体到地缘共同体再到精神共同体所默认一致的绘画范式是什么?那就是前文所述的文人画范式,而最能体现这个范式的典范作品就是董其昌和“四王”所作的一系列的“临摹粉本”。
王时敏从小就以董其昌所作的树石画稿为“临摹粉本”,这些“临摹粉本”包括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小中见大册》,它们具有相同的品质,皆是体现文人画范式精髓的典范,有学者就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小中见大册》称之为“南宗正脉”。①有人说此册是董其昌所作,也有人说是王时敏、王翚等人所作,王静灵将此册归属为王时敏作。见王静灵《南宗正脉:王原祁与<小中见大册>》,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8)。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二月,董其昌为王时敏作《唐宋人诗意图册》(纸本十六开),虽然每一图诗意不一样,但是每一图各取法某一家之图式与笔墨,或董源,或米芾、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等人,内容与形式和《小中见大册》一致。此时王时敏二十六岁,准备入都为官,可能是董其昌为其送行而作,供其临摹学习。
董其昌的另一个学生王鉴,也曾作此类的“临摹粉本”。如其所作的《宋元名迹缩本》则从古代绘画经典中获取图式与笔墨技法以提升自己对画史的理解。王时敏赞曰:“斫轮妙手,借余所留粉本神而明之,缩成此册,神采宛在,纤毫不遗,洵足洞心骇目。”[5]931此处“借余所留粉本”说不定就是董其昌为王时敏所作的那些“临摹粉本”,此缩本就是对董其昌的继承,一方面作为教材之用,另一方面作为创作资料。
“二王”之后就是王翚和王原祁。据载王翚曾经以“临摹粉本”的形式仿唐宋元名迹不下四次。第一次是康熙八年(1668年),王翚赴白下看望周亮工为其仿宋元山水十六幅。[13]120第二次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时敏出其所藏宋元名画供王翚临摹《小中见大册》(上海博物馆藏);第三次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王翚为东海司寇作《仿唐宋之诸家山水册》二十开。王时敏跋曰:“回环展玩,如探海藏,如罗宝纲,不觉目眩魂摇。但惜先有所归,勿获乞为家秘,朝夕坐卧其间,殊不胜怅惘耳。”[13]125由此可知此册比前一册更值得“家秘”,如武功秘籍一般珍贵,它充分证明了上文所说的绘画共同体的秘密生活;第四次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臣翁作《卧游图》十六帧。[13]126这十六帧分别是仿右丞、关仝、巨然、唐解元、痴翁、米元晖、刘松年、赵荣禄、黄鹤山人、董北苑、梅花庵主、赵大年、倪元镇等。这些粉本皆成为此共同体绘画规范额典范,是学习的最佳教材。
虽然从“二王”到“三王”“四王”,绘画共同体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但其范式却没有改变,体现此范式的各种临摹粉本仍在以不同的版本反复绘制。
王时敏将此类“临摹粉本”视之为“家秘”并不为过,它是王氏一族延续画学的“葵花宝典”,也是“四王”画派的重要教材之一。王原祁考取进士以后,康熙十六年(1677年)王时敏将其《小中见大》册传给王原祁,王原祁说:“先奉常于丁巳夏初忽以授余,其属望也深矣。余是年卅有五,拜藏之后,将四十年,手摹心追,庚寅冬间,方悟小中见大之故,亦可以大中见小也。”[14]此册可谓是王家画学的“衣钵”,王时敏将其传给王原祁,“其属望也深矣”,实乃指望王原祁将其发扬光大。王原祁拜藏之后,四十年间手摹心追,方悟其“小中见大”之意,可见此册在王原祁画业追求的道路上扮演了多么重要而关键的角色。不仅王原祁从中收益无尽,他还将其传给了他的弟子。
王原祁在教导他的弟子时,常将《小中见大册》作为教学模块使用。他曾运用各家笔法绘制了一套十二开的《液萃》册页给他外甥兼弟子李匡吉,并在册后自题表达自己对弟子的“良工苦心,端有厚望”。①自王原祁自题《仿古山水图》册中辑出,此图乃王原祁为其弟子李匡吉绘制,现藏故宫博物院。这种做法和王时敏将《小中见大册》传给他的做法一致:一是遵守绘画范式,二是传衍家学,三是捍卫绘画共同体的正统派地位。
所谓捍卫绘画共同体的正统地位,就是坚持“四王”画派的“清真雅正”之风。众所周知,董其昌的绘画思想包含了儒、道、禅三家美学思想,而且禅学思想占重要地位,由此董在追求宋画妍美工致时又不放弃元画的真率随意。“四王”画派是继承了董其昌的绘画美学,但是它扬董画之“清丽”弃其“荒率”趋于符合儒家“中和”美学思想所要求的“典雅平正”。然而,董其昌的绘画思想并不仅仅影响“四王”画派,明末清初很多的绘画群体皆从其多重复杂性的绘画美学中获得滋养。如集聚于扬州地区的一批攀附官商鬻画于市的“扬州八怪”画家群体和聚集在南京的一批遗民画家群体“金陵八家”,他们画风荒率但富有创新精神,对“四王”画派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于是王原祁俨然集三种威严于一身对此发出忠告:“明末画中有习气恶派,以浙派为最。至吴门、云间,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赝本溷淆,以讹传讹,竟成流弊。广陵、白下,其恶习与浙派无异,有志笔墨者,切须戒之。”这既是对其全体共同体成员的忠告也是对其它绘画群体的宣战,更是维护其绘画共同体的正统地位。此时“四王”之名目还未出现,因为“人皆知其实为定于一尊之官学画派,斯时倘使畀以‘四王’之名目,未免翻觉有贬损身价之嫌矣”。所以阮璞指出,“四王”之名目起于“四王”死后,娄东和虞山已成强弩之末之势,为图振兴大计才祭起“四王”大旗,抗衡“异端”才提出来。此乃实话。
总之,“四王”画派积极地将绘画艺术纳入儒家道统,使绘画艺术趋于儒者对道统的追求。在绘画共同体内,自始至终对文人画范式保持认同意识;开创文人画的“清真雅正”之风,坚持南宗绘画的正统意识;坚持以“临摹粉本”为教材进行绘画教育,践行弘道意识。
结论
“四王”画派基于对原始宗教的渴望,在父权制、结义制和师徒制的合力作用下胚胎于血缘性绘画共同体,统一于地缘绘性画共同体,完善于精神性绘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全体成员对文人画范式相互肯定,默认一致,相互占有,共同享受,贡献越多者获得的荣誉和权力越多,对弱者的保护和滋养的责任越大,体现了共同体内的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对董其昌文人画范式的默认一致,表面上出于绘画思想的选择意志,实质上是“无免疫力”的被传染和扩散,只要这个绘画共同体的形成机制是基于父权制、结义制和师徒制的合力作用下,其成员所默认一致的绘画范式只能出自本质意志,似乎没有其他的绘画范式可供选择。
顺带说一句,基于“遗民思想”的金陵八家、基于“盐商经济”的扬州八怪,基于“黄山写生”的所谓“黄山画派”,以及其他基于“对形式的渴望”(沃林格尔语)的绘画群体皆出于选择意志,严格意义上它们皆属于“社会”概念而不属于“共同体”概念,也就不能称之为画派。也许有人会说此研究的观点暗含对滕尼斯“共同体”的偏爱和理想化,有一种怀古复旧的浪漫主义情愫在其中,但是这不正与我们现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志一致吗?如果是这样,不妨将此研究的观点视为一个意外的收获,以便为传统中国画派的考察提供另一面相的认知。